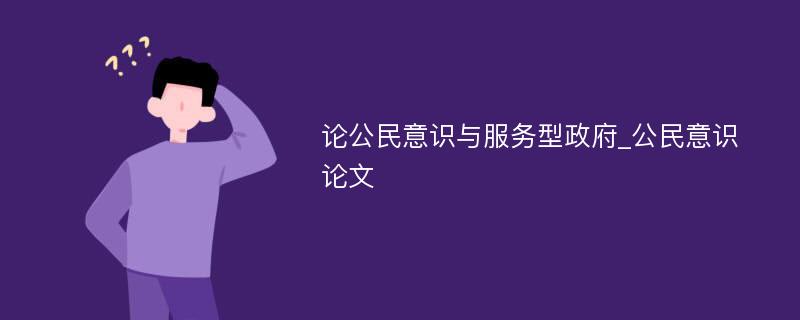
公民、公民意识和服务型政府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刍议论文,意识论文,服务型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1887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寻求用更专业的、新的思想方式管理国家时,中国正处在清朝末期,那时的中国政府还在用传统的封建方式管理着国家。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时,管理国家的思想和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但初步的民主方式尝试不久,袁世凯等人的倒行逆施、军阀混战,北阀统一不久日本入侵东北,继而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这一系列的灾变使民主、法治的思想传播和制度建设在起伏跌宕的国情中变得十分艰难和缓慢。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选择了苏联的管理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虽说在经济恢复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过于僵硬的管理模式和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导致“十年浩劫”,最终,改革之路成为政府绝处逢生的选择。当我们回头看时,西方现代的行政学研究已延续发展了近百年,其政府管理模式和理念也在不断蝉变。不管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上,在西方国家是其逻辑发展的结果,而在中国,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政府的行政改革都得一步步地做起,同时存在着不断跳跃式的借鉴。比如,在官僚制发展并不充分或者说缺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转变着职能,给自己提出阶段性的目标,而学界的研究也阶段性地发生着迁移,从对传统行政学的基础性研究到对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宣扬……正是在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近年我国学者提出了“服务型政府”概念并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探讨,同时,政府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在社会发展上,公民的权利正逐渐更多地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意识也日渐觉醒,这也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正基于此,本文将就公民、公民意识和服务型政府作一番探讨。
1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之一是人们在精神、情感上不再僵化,已较自觉地接受那些被普遍认为有益的事物和价值,比如民主的观念、法治的观念、人权的观念和环保的观念等等,而公民的观念也在这期间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只有人们深入地理解了公民概念的内涵,才会使公民的意识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促使中国社会向着公民社会发展,这样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才会逐渐达成。
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公民”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公民”一词同民主一词一样是个舶来品。“公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其内涵突出政治性和美德,它更鲜明地表现着一种公共性。到古罗马时期,公民的内涵得到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等得到法律的认可,它具有了某些与近代以来在法律上相近的意义。但到了中世纪,神权和君主的统治使公民发展的历史中断。近代的公民概念是建立在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等个人权利得到突显。公民权利的发展是公民概念发展的重要内涵,有学者指出:“公民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民事权利是在18世纪,政治权利是在19世纪,社会权利是在20世纪。’”[1]17这一概括也说明了公民概念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并不断地得到演进和丰富。
中国古代没有公民的概念,也没有与之含义相近的词,以儒家思想等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只有“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甚至到了100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首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仍充满关于臣民的表述,只不过从中也看到了个人权利的曙光和无上的皇权初次受到一定的约束。康有为是近代较早提出公民概念的人,他在《公民自治篇》中写道“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1]165。但他说的公民还不完全是近代意义上的概念。直到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国民、人民才具有了近代“公民”的内涵,被赋予以往完全没有的作为公民应有的诸种权利,后来在其他的法律文件中公民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公民一词在50年代初的有关法律文件中开始出现,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最初的近30年中,政治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使得作为公民的权利几乎被忽略并缺乏保障,政治超越在法律之上。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不断地努力,宪法与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使公民的权利逐渐得到尊重,公民在维护权益方面逐渐有所好转。但是在人们的普遍的思想意识中,公民的概念还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公民意识还处在觉醒向建立和提高的过渡中。比如,在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很多场合和语境中还在不断地使用人民、群众和老百姓这些词语,其实其中更多的情况应该使用公民或与之相同的国民的概念。这也充分说明了传统文化中君臣思想和等级观念在大多数的国人心目中仍是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
与公民相比,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与它相对的是敌人。而公民的概念要大于人民,《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就是说,即使在监狱服刑的人作为公民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和宗教信仰权等等也同样要受到《宪法》的保护。现实生活中,有时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其实完全可以用公民一词,公民的概念更会突显法治的色彩。因此,让每个人都清楚公民的概念,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逐渐走向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像群众、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既带有传统的等级观念的含义,又带有某种无权被动的下层的色彩,它们在许多场合应被公民一词所取代。因为词语是有价值取向的。既然在理论上普遍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公民,那么未来的服务型政府就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公仆”。
因此,突出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让公民的意识和意志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核心,是未来我国改革工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性工作。
2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后,在法律上就昭示了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但这不等于在现实中会完全理想地达到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度,现实生活远远要比法律文本所指涉的内容复杂得多。公民在何等程度上理解了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换一种说法就是公民意识达到什么水准,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和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尺度。对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其传统文化中缺乏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基础的民主与自由,在人们的思想中公民意识即使在今天也十分淡薄。比如即使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措施表示疑义,往往也更多的是从期望得到更多的呵护,而不是从公民权利或公众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会去想政府的存在正是基于公民的存在,公民的权利是政府应当依法保护的而决不是政府所赐予的,政府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和表达民意的机构。人们更习惯于服从,习惯于被管理、被领导,普遍地缺乏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法律自觉。
因此,在探讨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语境下,公民概念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性因素,而且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因素。
公民意识首先是权利意识,因为没有权利,公民就不可能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一个人能较清楚地理解到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首先意识到他的权利并意识到可以用法律来维护时,我想这个人就具有了较高的公民意识。如果他能认识到“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4,那他就是一个具有很高公民意识水准的公民了。
公民的权利意识说到底是一种法律意识,同时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公民意识中也是很重要的内容。现在的世界,民主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民主已能完全用法律来保障其实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倡导者登哈特在谈到公民的权利时认为:“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恢复一种基于公民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公民权。按照这种观点,公民会关注广泛的公共利益,他们会积极地参与,并且会为别人而承担责任。换言之,公民会去做一个民主政体中公民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去管理政府。”[3]这表现出美国社会的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带有着古希腊的公民的特色——积极地关注公共事务。而在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中国,公民意识中也应充分地注重民主、参与和责任,努力不断地健全法律法规来促进公民的民主和参与的实现。
关于提高公民意识,首先,要提高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如果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淡薄,其权利诉求和责任意识就不会很好地表达,社会进步和变革也就缺乏动力,公平、正义和法治等等观念就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公民的意识是可以培养的,诸如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等等,当然还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参与等等观念,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宣传使之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逐渐地变成人们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一方面,可以从学生做起,从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贯穿其中,另一方面,在社会上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使缺乏公民意识的成人也会逐渐改变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同时,在法律上要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使公民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保障。这样就会逐步而有效地提高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
其次,要注重提高全体公务员的公民意识。作为公务员同时也是公民,但这并不能说所有公务员都有较高的公民意识,然而由于公务员工作的特殊性要求他必须具有较高的公民意识,不然他如何能很好地尊重公民的权利?公务员的特殊性决定,公务员的公民意识绝不能低于全体公民的水准。只有具有较高公民意识的人才会懂得尊重公民权利,才会自觉地服务于公民。基于目前公务员录用的标准和培训的要求,其公民意识在理论上应具有较高的水平,必要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运用也会促进公务员的公民意识达到一个较好的水平,这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个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总之,提高公民意识会促进公民在法治、平等、权利和参与等等方面认识的提高,会有利地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3 近七八年来,“服务型政府”得到了行政学界的普遍关注,在理论层面上给予了较深入的研究,同时,近期我国政府也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自己行政改革的一个目标。那么什么是服务型政府呢?笔者在这里将作一番探究。
根据李传军的研究,“服务型政府”的概念首先是由张康之提出的,然后在行政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逐渐深入的研究[4]。张康之最初是这样表述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的,在《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中他写道:“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服务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5]。在该文的结尾他明确地提出“呼吁服务的政府理念,期望服务型政府的产生”[5]。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创新的意义,不但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的行政改革,使这一理论上的探讨得到现实改革的汲取和认可,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诸多研究中,刘熙瑞的提法较为著名,也更加完备,他是这样表述的:“何谓服务型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6]在这里,因为刘熙瑞的概念研究后于张康之,所以表述上明显地更加严密,突出了公民的地位和意志,同时也对服务型政府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刘熙瑞在概念中表示政府“为公民服务”要比张康之的政府“为公众服务”更加清晰严谨地表达了公民在未来政府行政中的地位。
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探讨之中,还有许多疑问有待回答。在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之前,张康之指出:“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中迄今存在过的政府大致属于两种类型:统治型的政府和管理型的政府。”[5]按照逻辑推论,服务型政府之前的管理型政府应是得到完善的发展和运行,最终因其在现实中出现理念与运行的一系列问题,于是不得不由服务型政府取代。那么,就出现疑问了,我们目前的政府在管理型政府上处于什么状态,对此应该作出准确的判断,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基础的构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往往都是跨越式的行进,这之中有时不免要回头审视一下,这其中是否有重要的环节需要补课。比如,有人说要完全扬弃官僚制,但有人又指出我国的官僚制发展的不完善,还谈不到完全放弃。其实这里说的官僚制,它就是管理型政府运行的一套成熟的管理体制和理论。因此,对现在政府的长处与弱点的深入研究和准确判断,对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对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十分重要的。行政改革是一种政府运作的转型,而不是在全新地创造政府。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公民应处于核心的位置,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意志要得到保障和体现,因为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公民服务的。如何在法律上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公民的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艰巨而迫切的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任务。服务型政府无疑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它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正如罗尔斯所说的,“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4。否则,公民的权利无法实现,公民的意志难以体现。所以说,服务型政府应充分体现法治政府的特色。
从现实的层面讲,服务型政府不应仅仅是提出一种目标,或者以设立一些便民的服务机构或措施为主,它应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的,是运行明晰的而不是模糊的;是程序明确的而不是随意性的,概括而言,“服务型政府”应是一种合理的制度设计,正如波普尔所说的,“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7]合理制度的稳定性之特质,会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安定和福祉。
从总体来看,服务型政府不管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还是行政改革的目标,都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在突出公民本位、提高公民意识的基础上,使社会逐渐走向法治化,逐渐实现行政改革的预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