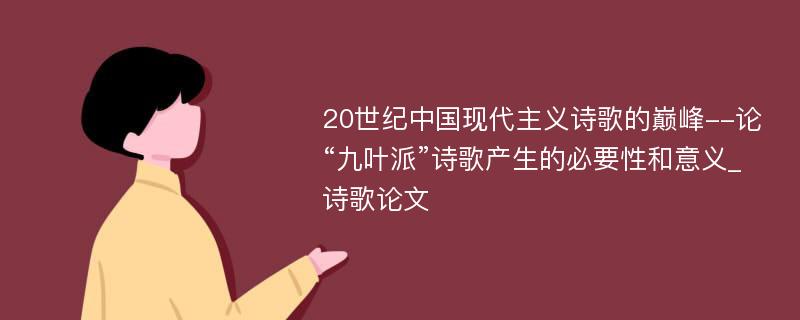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论“九叶派”诗歌出现的必然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现代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6)04-0097-06
一、“九叶派”的缘起与势出必然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争频仍,血火交迸,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如此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中,30年代臻于成熟的“现代诗派”,由于一心表现一己的心灵感受,远离了如火如荼的时代、惨绝人寰的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民众,故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随着部分诗人转向现实主义,“现代诗派”已是名存实亡了。
作为诗歌流派之一的现代主义诗歌,并不因为“现代诗派”的衰亡而停止向前发展。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作为世界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一部分,经过迂回曲折,终于走出困境,走出低谷,达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阶段。
在当时的中国,幅员广大的领土被分为革命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抗战胜利后,就是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两部分)。在革命根据地,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诗歌无一例外成为革命战争的宣传武器。所以,此时现实主义成为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成为革命浪漫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在杀敌战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确实起到鼓舞士气、鼓舞斗志的革命号角的战斗作用。而现代主义诗歌显然因为不能适应战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无法在革命根据地立足。
然而在国统区,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的统治下,革命斗争只能在地下进行。所以,作为革命号角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在国统区却无法像在革命根据地那样发挥应有的战斗作用。此时,现代主义诗歌就悄悄地在革命根据地与国统区之间的夹缝中求得一席之地的生存。
由于是在国统区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此时的现代主义诗歌与30年代“现代诗派”不同,它总结了“现代诗派”衰亡的教训,认识到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逃避现实,远离民众,钻入艺术的象牙塔,是取败之道。于是,它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同时,它又与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不同,后者由于革命斗争和对敌战争的需要,为了最大限度地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所以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为“大我”,抒发一己之悲欢的“小我”,在这里就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国统区,由于社会的大环境不同,诗人又是以个体为存在方式,一般不从属于某个政治组织,不受其领导和制约,所以可以充分表现其个性。这些诗人大多留学国外,又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故而更尊崇艺术与个性,并努力寻求西方现代派艺术与古老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交汇,寻求现实生活与心灵世界的交汇。于是,在国统区,一个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诞生了,这就是与革命根据地诗歌、“七月派”诗歌鼎足而立被称为“中国新诗派”,后被称为“九叶派”的诗歌流派。
这样一个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却因其现代主义的倾向、多元化的艺术观念,为新中国成立后极左的意识形态和狭隘的艺术观念所不容。“九叶派”虽然没有像“七月派”那样被卷入“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批判运动中去,可是同样长期遭到冷遇、歧视、批判,以致长期濒于销声匿迹,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这个流派中的成员,这九位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备受迫害,如穆旦;有的改行不再写诗,如曹幸之(杭约赫)后来成为著名的书籍装帧家;有的一度投笔从商,如辛笛一度从事工商和银行事业;有的则被错划为右派,如唐湜,被遣返老家温州受尽折磨。新时期的春风终于吹绿了这九片濒临枯萎的叶子。直至1981年,《九叶集》问世,人们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在那风起云涌、血火交迸的40年代,还有这样一种沉静优雅、含蓄深邃的诗,而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这些诗竟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仍然给人以深刻的感悟和强烈的震撼。1982年,又出版了除杭约赫以外的8位诗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作品合集《八叶集》,作为对《九叶集》的补充。
让时间倒流到40年代。“九叶派”应该是80年代的命名,40年代时,应该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就统称为“九叶派”。
“九叶派”的出现,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九叶派”的出现与两份创刊于上海的诗歌杂志《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有关。《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以丛刊的形式出版的,每月出版一册。《诗创造》由臧克家、曹幸之、林宏、沈明、郝天航等人集资发起,由曹幸之主持具体的编辑事务。《诗创造》在《编余小记》里提出了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在《诗创造》发表作品的作家和诗人有一百多人,发表的作品风格多种多样,有抒情诗、十四行诗,有山歌民谣,也有政治讽刺诗。作品的内容多数是反映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及斗争。此外,还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诗论。《诗创造》是1947年创刊的,一年后的1948年11月,《诗创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
《中国新诗》于1948年6月创刊。由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编辑。由唐湜执笔的代序《我们呼唤》堪称《中国新诗》的宣言,表达了他们对历史、时代、现实人生、艺术和个性的见解。也许是言辞激烈了些,强调了“强烈的人民政治意识”,《中国新诗》与《诗创造》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当时为《中国新诗》撰稿的大多是大学教师、学生、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中国新诗》的读者,也大多是爱好新诗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在《中国新诗》这块园地里,由编辑、作者、读者共同对新诗的爱好、研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逐渐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流派。这就是当时被称为“中国新诗派”,后来被称为“九叶派”。
“九叶派”的出现看来似乎是偶然现象,但实际上,它的出现是必然的。首先,“九叶派”的出现是由社会现实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40年代的中国,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使当时的社会成为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人间地狱。而在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步的、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不会置身事外,必定要以诗歌来吐露自己的心声,表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态度。由于诗人的个性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在总的方向和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诗人们选择了不同的诗歌表述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现实主义已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诗人为代表的自由体新诗的成就,确定了现实主义诗歌在当时诗坛上的主导地位,而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新民歌、新叙事诗,也配合着革命斗争而十分红火。同在国统区的“七月派”,以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诗歌,高唱着昂扬的旋律。在这种情况下,富有个性特征、又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九叶派”诗人,在客观上,不可能如革命根据地的诗人那样,高奏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战歌;在主观上,他们那中西文化的深厚修养所形成的诗歌观念和审美追求,也不能接受现实主义诗歌那种直白浅露、粗粝的形式,号筒般的宣传;由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现实的动荡不安,又不可能再回到30年代“现代诗派”那样,一心钻入象牙塔,写那种远离现实生活、朦胧晦涩的所谓“纯诗”。“九叶派”诗人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加以交融。因为现代主义诗歌原本来自西方,在中国,没有生长的土壤,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做某种程度的交汇和契合,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其次,从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九叶派”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艺术潮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不会因为时代、社会的外部因素而使其完全消亡绝迹;即使在某一时期衰落了,也会在同一时期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重现。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重现,意味着对原有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改造和重新整合。所以,从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别是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主义诗歌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加以改造和整合,而“九叶派”诗歌正是经过改造和整合的现代主义诗歌。
事实证明,把现代主义诗歌加以整合和改造,兼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两美,正是“九叶”诗人最佳的选择,也是他们对新诗的最大贡献。
二、“九叶派”诗歌达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
以“九叶派”为标志,说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已达到高峰。要对一个诗歌流派做这样的判断和评价,就必须将它之前的诗歌流派作为参照系,加以比较。在“九叶派”之前的诗歌流派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新月派”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象征诗派以及现代诗派。
在诗歌内容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一点上,“九叶派”与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九叶派”继承了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关于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传统。然而在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一问题上,两者却有判然有别的分野。这种分野来自诗人感知方式的不同。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将客观现实,包括客观物象、景象、事象作为表现对象,并且仅止于此。而“九叶派”则不然,它虽然也将客观物象、景象、事象作为表现对象,但是其目的并非仅仅停留在描摹这些对象本身,而是着重表现由这些对象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受到的启示、感悟到的哲理。
“九叶派”与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分野还在于主观自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不同。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以客观现实为第一位,主观自我是次要的,甚至受到排斥。这种状况无论在战时环境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如此。现实主义诗歌必须表现现实生活中重大的政治斗争和事件,抒情必须抒革命的、集体的“大我”之情,而主观自我,也即“小我”,则被当作“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仅不能表现,而且应当加以排斥和批判。而“九叶派”则恰恰相反,在主观自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上,以主观自我为主。以主观自我为主,意味着主体意识的强化。强化主体意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在诗歌反映现实这一问题上,彻底改变了机械反映论所带来的弊病,变被动反映为能动反映。能动反映使诗人能主动地把握外部世界,既依据题材,又超越题材。所谓超越题材,就是不停留在题材本身,而是经过诗人主体意识改造过的题材。也就是说,“九叶”诗人在主观自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上,是将客观现实主观化。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九叶”诗人除了将客观现实主观化外,还将主观自我客观化。所谓主观自我客观化,就是将诗人的主观自我、内心感受等作为客观的分析、研究和审视的对象。我们知道,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视意识,亦即内省意识。内视意识或内省意识就是将与外宇宙相对的内宇宙作为审视对象。而内宇宙的复杂、奥秘并不亚于外宇宙。所以,“九叶派”是将客观现实主观化与主观自我客观化相结合,其中心还是主观自我。诗人将客观现实的题材经过主观自我的处理,也即主观化后,将所感受到的经验、情思加以沉淀、体味,然后,又超越内心,以知性的眼光来观照,来思考。最后,这一切升华为体现艺术经验的诗的要素,诗的灵魂。这样,写出的诗就既不是现实生活的刻板描摹,也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心灵独白,而是融合了现实生活与心灵感受,是现实生活触发了诗人内心的感受、经验和体验。
在抒情这一点上,“九叶派”与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划清了界线。抒情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核心和灵魂。当然,不止是浪漫主义诗歌,抒情一向被认为是所有诗歌的核心和灵魂。而对于浪漫主义诗歌来说,抒情更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本质。没有抒情,就不能称为浪漫主义诗歌。
“九叶派”恰恰在这最关键、最要害的一点上,向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发起挑战。“九叶派”与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对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观念的对立。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以抒情作为核心和灵魂,是继承了“诗即抒情”的传统的诗歌观念。而“九叶派”对这种传统的诗歌观念进行大胆的挑战,提出拒绝单纯抒情的全新的诗歌观念。“九叶”诗人袁可嘉对“诗即抒情”的传统的诗歌观念就感到深恶痛绝,他不无激烈地说:“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比放纵感情更为厉害。”[1] 放纵感情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之一,也正是它的弊端之一。诚然,在诗歌的诸要素中,情感无疑是其中之一,是不容忽视的。诗人在创作诗歌时,要完全排除情感的作用,处于所谓的零状态中写作,是不可能的。“九叶派”的诗人们也深知这一点,他们并不是一概反对情感在诗中的介入,他们所反对的是单纯强调抒情,以情感涵盖诗歌的一切,而情感是难以涵盖诗歌的一切的。情感的花朵必须在理性的阳光照耀下,才能灿烂地开放。情感必须经过主体意识的沉淀、体验,必须经过思想的审视,才能转化为诗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九叶”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尽量避免原生态的情感直接入诗,而先在理性和思想的审视中,加以沉淀、过滤和升华,然后,还不能尽情宣泄,而是将之融会到诗人的理性思考、判断和评价之中。这种思考、判断和评价又水乳交融般和情感的载体、对应物交相渗透。所以“九叶”诗人乃至给予他们深刻影响的里尔克、冯至所创作的诗,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和情感的简单的反映,而要远为复杂得多。这样的诗最大限度地节制情感和情绪的洪水泛滥和宣泄,而以理性和知性的闸门来限制和规范它。情感和情绪只有经过启人心智的理性和知性的规范,才能达到更深的层次。这样的诗体现了感性与知性的结合,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契合,情感与智慧的融合,情绪与经验的综合。这样的诗才可望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兼美的境界。
以建筑美为追求目标的“新月派”,是新格律诗,也即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为何说“新月派”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这是因为虽然“新月派”也受到西方外来诗歌形式的影响,但是,在本质上,“新月派”诗人都有深刻的挥之不去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情结。闻一多所强调的诗歌的建筑美,就是要以西方诗歌的优点来救赎中国古典诗歌的不足,改变中国古典诗歌死板、僵化的缺点,以创造一种新的、力求完美的诗歌形式。所以“新月派”所重视的是形式,新古典主义也是一种新形式主义。而这恰恰是“九叶派”不能容忍的。“九叶派”更注重内容,不能接受任何形式主义。至于诗歌的形式,“九叶派”更倾向自由化,而不能接受“新月派”的诗歌形式的建筑美。除了反对“新月派”豆腐干式的建筑美外,“九叶派”对诗歌形式并非轻视,相反,是非常讲究的。“九叶”诗人辛笛在《辛笛诗稿·自序》中,就曾对诗歌的艺术形式问题有很精辟的论述,说明“九叶派”对艺术形式的重视。他说诗歌“首先就必须从意境(现代说法就是指印象、意象)出发”,可见他对意象的重要性的认识。“九叶”诗人唐湜在《飞扬的歌·后记》中,也指出,诗必须“将感情凝结在深沉的意象里”。“九叶”诗人由于既有深厚扎实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又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便自觉地将庞德、艾略特的意象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意境的理论结合融会在一起,于是就最大程度地张扬意象艺术,意象成为现代主义诗艺的核心。所谓意象,就是心灵(内心世界)与外物(外部世界)相契合的产物。“九叶派”所提出的“思想知觉化”以及寻找“客观对应物”都离不开意象。他们就以此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大量地、密集地运用意象。这使他们的诗显得形象生动,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九叶派”对意境的追求,使诗呈现一种浑然的、整体的美。
由此不难看出,同样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继承,“新月派”的所谓“建筑美”,只是停留在诗体的形式上,而“九叶派”则在更深的层次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关于意象、意境的传统理论,并沟通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理论,创建了自己的诗歌艺术理论体系。
当然,“九叶派”除了在意象、意境等深层次艺术形式上有独特的建树外,即便在诗体、语言等艺术形式上也有创造性的探索。“九叶派”在诗体上既克服了“新月派”诗歌太拘泥于格律,显得呆板、僵化的弊病,又避免了浪漫主义诗歌因过于放纵感情,而显得散漫无序的自由体散文化的缺点,正如“九叶派”在抒情方式上,既不像浪漫主义诗歌那样直接、放纵、强烈,又不像“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那样过于隐晦曲折一样,“九叶派”在诗体的探索上,找到了在散文化和格律化之间游刃有余的形式,兼两者之所长。“九叶派”虽然还是用自由体写作,但是这种自由体却与散漫无序的散文化迥然不同,与整饬板滞的格律体也大相径庭。“九叶”诗人所采用的诗体是自由中有限制,限制中有自由。诗体的句式、分行都视内容而定。
“九叶”诗人对十四行诗这种形式也很中意,认为较能表现他们邃密的情思和深沉的哲理思考。他们笔下的十四行诗就显得舒卷自如,既有一定的韵律,又有较大的自由度;讲究音尺,又不过于拘泥,句式排列宽严适当。所以他们笔下的十四行诗成为最能体现他们情思和知性的、得心应手的诗歌形式。
“九叶”诗人在诗的语言上也进行了精心的淘洗和锤炼。而他们在语言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们的诗歌观念和主张,即诗的知性化服务的。为了达到诗的知性化的艺术效果,他们在驾驭诗的语言时,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即将抽象的词和具象的词结合,互相替代,以达到感觉和知性的统一。如唐祈的《女犯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屋里孕育。”“死亡”本是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抽象的词,而“鼓着盆大的腹”则是具体的形象。两者结合,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不仅增强了女犯监狱的恐怖氛围,而且发人深思。又如袁可嘉的《空》:“我乃自溺在无色的深沉/夜惊于尘世自己底足音。”“深沉”是抽象的概念,抽象的词,而“自溺”则是具体的动作,把两者结合,使“深沉”这个抽象的词给人一种像深水那样的感觉,使“深沉”这个抽象的概念有了具体的外形。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加强了诗的知性化,将诗的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由于这种虚实结合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正常的联系规律和逻辑关系的故意违背、扭曲、变形的基础上的,故而,这样的诗给人一种巨大的惊奇感,一种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冲击力。“九叶”诗人因此在诗的语言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将诗的语言从传统的描述功能转变为表现功能。
除此以外,“九叶”诗人在诗的语言上还运用了通感、远取譬、象征等手法,使诗收到陌生新奇的艺术效果。通感就是感官感觉的互相替代、错位和转移。通感能造成新鲜奇妙的艺术体验和艺术效果。如辛笛的《门外》:“如此悠悠的岁月/那簪花的手指间/也不知流过了多少/多少惨白的琴音。”“琴音”应该是听觉形象,却以视觉色彩的“惨白”去形容它,给人以新奇的感觉,并且增强了“琴音”的感情色彩。同样,唐湜的《诗》:“灰色的鸽哨渐近、渐近。”鸽哨应该是欢乐的声音,而用视觉的色彩“灰色”去形容,就改变了鸽哨原有的情感基调,这是因为诗人自己的情绪低落,因而欢乐的鸽哨,在他听来显得也那么凄凉。通感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诗的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诗的语言的表现空间。
所谓远取譬,就是在看来没有共同之处的两种事物中,寻找某种意义上的相同之处加以类比。如唐祈的《故事》:“早晨,一个少女来湖边叹气/十六岁的影子比红宝石美丽;”“青海省城有一个郡王,可怕的/欲念,像他满腮浓黑的胡须。”十六岁少女的影子与红宝石从外表上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在美丽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就具有了可比性。同样,郡王的欲念与他满腮浓黑的胡须,前者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欲望,后者则是具象的东西,两者也毫不相干,无相似之处,可是,在不断增长这一点上,则毫无二致,故可相比。远取譬的运用,使诗的语言尖新奇巧,令人反复玩味不已,增强诗的陌生化效果。至于象征的运用,“九叶”诗人既继承了“象征派”,又超越了“象征派”,他们运用象征,不像“象征派”那样晦涩、生硬。
总之,“九叶派”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使他们的诗日臻成熟,趋于完美。
最后,“九叶派”和与之相近的30年代的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以及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也有很大的区别。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一味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生吞活剥,不能加以消化,融为已有,所以写出的诗,不仅晦涩难解,而且洋味十足,难怪被讥为不是中国诗了。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吸取“象征派”的教训,不是刻意模仿,而是认真吸收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经验,结合自身的艺术修养,超越“象征派”而自成一派。但是,无论是“象征派”还是“现代诗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脱离现实生活。而“九叶派”形成于40年代后期,其诗人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暴风雨的洗礼,他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所以不仅不可能脱离现实,相反,他们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在诗歌创作中真实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九叶派”借鉴、总结“象征派”和“现代诗派”学习西方现代派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认识、思考和体会,再加上他们深厚扎实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和修养,融会贯通,遂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那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容,而又富有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现代主义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
“九叶派”与“象征派”、“现代诗派”还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象征派”和“现代诗派”都是主情的,属于主情的象征诗。主情的象征诗追求情感与意象相契合,通过意象的象征、暗示来表现情感,而这样的情感大多缠绵悱恻,只是一己的悲欢,且情调消极颓唐,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诗风朦胧迷离。而“九叶派”则是主知的,属于主知的现代诗。主知的现代诗着重于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和思考,并且以玄思入诗。虽然“九叶派”也大量运用意象,但是,与“象征派”和“现代诗派”通过意象的象征、暗示来表现情感不同,“九叶派”的意象具有更多的理性内涵。在他们的诗中,抽象的理性思维和机智深邃的哲理最为突出。他们的诗以表现经验代替抒情,诗中情思深藏不露,冷静隽永,诗句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诗风深沉玄奥。
上面论及在诗体上,“九叶派”与“新月派”的不同,其实,在这方面,“九叶派”与“现代诗派”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虽然两者都以散文化的自由诗为主要诗体,然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崇尚的是表现诗人情感、情绪的体验。在诗歌形式上,他们强调以诗情的强弱起伏为特点的诗的内在节奏,来取代“新月派”所主张的诗的外在韵律。而与“现代诗派”“不借重音乐”、不讲究韵律不同,“九叶派”因为不主情,而是主知,不屑于单纯的毫无节制地放纵抒发个人情感。他们的主体的情感、经验经过转化升华,成为一种艺术情绪,成为诗的经验。由此,他们在诗歌形式上探求兼有自由诗与格律诗之美的形式。“九叶派”的诗歌形式依然属于自由诗,具有散文美,但是,又重视诗的形式美,注意诗的音乐性、自然的节奏和和谐的韵律。应该说,“九叶派”的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他们的诗兼有自由诗与格律诗双美的形式。
总的说来,“九叶派”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上是达到高峰、趋于完美阶段的一个流派。“九叶派”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融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精神之中。它对于在它之前的诗歌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诗派都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超越。“九叶派”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诗必须表现情感”的传统信条,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更新了固有的诗歌观念。
“九叶派”既面对世界,又面对传统,它不仅继承、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而且还继承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特别是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婉约派诗人的传统,表现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艺术财富皆可为我所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而又加以扬弃和超越的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恢弘的气魄。
“九叶派”提出“新诗戏剧化”,主张新诗的结构应是戏剧化结构,就是要“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到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1],这样其作品所体现的特点就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这种诗的结构的戏剧化,就是诗人规避自己直接站出来抒情宣泄,所谓“间离效果”,也就是和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以作品中的静止的、富有雕像美而又互不相关的一个个意象排列组合着,犹如画面和戏剧场面,而在这些看似客观形象的意象的深层,却跃动着诗人丰富深邃的情思。当然,由于当时社会的腐败和混乱,客观现实的黑暗,迫使“九叶”诗人更切近现实生活。他们的有些诗如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袁可嘉的《上海》、《南京》等很像活剧和讽刺剧。即便如此,诗人们也不是直抒胸臆,而是让读者从诗人们所勾勒的人物和画面中,领会诗人的真意。当读者会意一笑时,说明诗人已收到讽刺的戏剧效果。“诗的戏剧化”取代了传统的诗歌的直抒胸臆,意味着诗歌突破单纯抒发情感的模式,而转向表现人生经验,意味着“九叶”诗人背叛传统,另辟蹊径,找到了以诗的方式把握客观世界和传情达意的全新的途径,因此大大拓展了现代诗歌的艺术表现空间,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九叶派”为中国新诗,特别是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标签:诗歌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学论文; 新月派论文; 现代诗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艺术流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