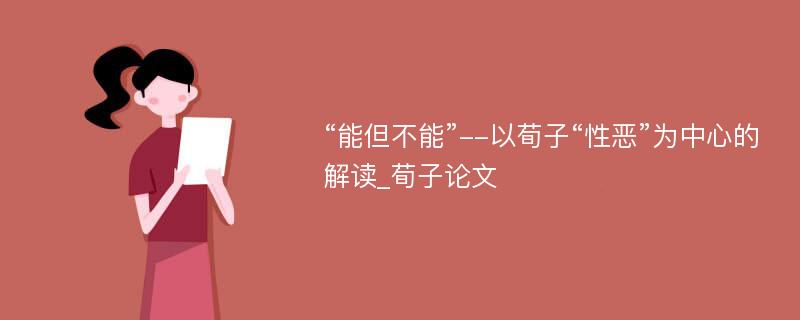
“可以而不可使”——以荀子《性恶》篇为中心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而不论文,可使论文,性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2)04-0005-12
一、引言
在某种意义上,荀子思想是以“性恶论”作为其重要标识的,至于此一看法在理论上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回事,①而在阅读《性恶》篇时,荀子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句,更如同一部交响曲的主部主题一样,反复奏响。的确,在理论上,人之性既然为恶,则为善何以可能?此为学者常常追问之事,但荀子却也确确然宣称“涂之人可以为禹”,此中似尚可分解,此其一也;其二,在学者的理解中,恶既属之于内在的人性,善之伪似乎纯成了外在的形塑,不过,荀子也曾确确然表明“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似乎“性”与“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内外关系,而有其复杂的内在关联[1]410。要言之,荀子的“性恶论”一方面认为人生而有感官耳目之欲,好利而恶害,若顺是而无度量分界则必为恶,另一方面荀子又断言人皆可以为禹舜,而同在《性恶》,荀子在面对“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的“自难”时,荀子却给出了“可以而不可使”的回答,这种回答似乎通过直接诉诸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行性之间的辨证对问题进行了回答。
不过,话虽这么说,若执诸荀子思想的脉络系统,此“可以而不可使”一句所蕴涵的理论问题实可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学者在研究荀子思想时,虽对此已有阐发,但或格于文义,或限于《性恶》篇之文本等等,而对其间所可能包含的“意义剩余”不免有所遗漏,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疏解。
二、质具与知能
荀子“可以而不可使”一说在《性恶》中是以“自难”的形式提出的: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
此处“圣可积而致”是一个普遍判断,在没有预设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此句大意约等同于“涂之人可以为禹”,而“可以”与“不可使”皆是一个尚待解释的概念,人们或问“有什么条件使圣可积而致?又是什么原因使圣不可积、不可使?”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刘殿爵(D.C.Lau)教授早年所批评的那样,荀子所谓的“可”乃是一个语义含糊、模棱两可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示“可能的”(possible),也可以表示(道德上)“可允许的”(morally permissible)②,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荀子的相关解说。在此句前一段,荀子亦以“自难”的形式解答何以“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问题,荀子云: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此段之中心意思即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而荀子的论证策略却包含了几个方面。依荀子,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原因在于“其为仁义法正”,“为”者,行也,谓其能实行或实践仁义法正。无疑,此“实行”或“实践”是以“知”为前提的,亦即涂之人若要成为圣人,即必须“能为”、“能知”仁义法正,此处“能知”是内含在“能为”之中的。但是,若要“能为”仁义法正,在理论上就必须先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此一问题又涉及两个方面:人本身(认识主体)有能知之性,对象事物有可知之理[2]35-74。在《解蔽》篇荀子已有明言:“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又言“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③以此观念,荀子认为,作为对象事物的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依李涤生,“质”谓本质,指人的聪明;“具”谓才具④,故而结论是涂之人行其所知之仁义法正,日加悬久,便可成为圣人。此处所谓的“知(之质)”、“能(之具)”其实就是《正名》篇中所说的“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的“知”、“能”,它是先天具之于人、不待后天学习而有的能力⑤。
荀子接着又用假设的反证法来进一步证明“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荀子假定:1.若仁义法正本无可知可能之理,那么,即便禹也不能知仁义法正,不能行仁义法正;2.若涂之人本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那么,他们在家则不知父子之义,在国则不知君臣之正。然而事实与此相反:1.禹之所以为禹,表明其事实上能知、能行仁义法正,仁义法正也有可知可能之理(行文中省略了此一点);2.而涂之人在家知父子之义,在国知君臣之正,表明涂之人先天具有知之质、能之具,故结论是:人人皆有其能知、能行仁义法正之质、具。既然人人有可知、可能之质、具,本之于仁义法正的可知可能之理,有以求知(伏术为学),有以实行(积善不息),那么,人皆可以为禹、“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便可得而证明。
大体上可以说荀子的上述说明还是比较顺畅的,前一节对“认识何以可能”的论述,在先秦儒家中独具风采;后一节的类推虽不免遭人诘难,但总体而言还有格有套。不过通观其思想之系统,学者依然会追问,荀子既然主张“人之性恶”,今又谓人有“知之质、能之具”而可以为仁义法正,即此“知之质、能之具”是不是属之于性?若是,则这种意义上的性又究竟是善还是恶?如果此“知之质、能之具”不是人性本有之能力,即荀子便不能说明其来源于何处;如果是人性本有之能力,似乎就不能说人性是恶的[3]335。
对于类似的问题,学者已有各种不同的解说,要言之,荀子“人之性恶”的说法仅仅只是把其特定意义上的“性”看作是其有关“人”的学说中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已,此一说法不仅意味着“性恶”说只是荀子人的学说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还将进一步指出,荀子所谓“恶”的“性”并不是其人性论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人性论中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即便是这一部分内容,如果它果真要成其为“恶”的话,也必须具备“顺是”的条件。假如我们局限在《性恶》篇来了解,那么,荀子有关“人之性恶”之“性”说的只是人性中的“情欲”部分,包括人的天生的生理感官的欲望和人的心理的欲望以及各种嫉恨憎恶的情绪反应等。但在《性恶》篇中,荀子论人之性除了上述所说的“情性”、“情欲”之外,还论及其他有关“人性”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却不在他所述说的“恶”的范围之内,如上述所言的“知之质,能之具”即是[4]。
但此处的问题是,荀子所云的这种“质”和“具”究竟是属“心”还是属“性”?此一问题在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在《性恶》篇的脉络中,再加上将荀子言性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分法,那么,我们大体可以将荀子此处所讲的“质”和“具”归之于广义的“性”的范畴之中⑥。不过,无论是陈大齐先生还是李涤生先生皆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荀子此处所讲的“质”和“具”虽是人生而有的、先天本然的,但它们是出于心而不出于性[5]553;“性”与“知”各为独立的心理作用,并不相互涵摄,故性中不能有知虑⑦。若依此理解,即荀子此处所说的“质”与“具”当不属于“性”而属于“心”,如是,则虽然我们可以承认,荀子所说的“人之性恶”之“性”说的是人性中的“情欲”部分,但我们却不能遂下断语,将“质”和“具”也归之于“性”,至少在理论上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平情而论,陈大齐和李涤生两人将荀子在《性恶》篇中所说的“质”和“具”划归到“心”而不是“性”的范畴中去,有其充分的分析和相当的理由,尤其是陈氏通过对荀子心理论的分析,对性、情、虑、伪、事、行、知、能等概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认为性、知、能三者构成了荀子心理作用的三个成分,类似于当今心理学所说的情、知、意,其看法相对来说较为客观。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荀子那里,“心”乃常常作为一切心理作用的总称来使用的,心不仅指认知、思虑,而且有时正如陈氏所指出的那样,也指情本身,如言“心至愉而志无所诎”(《正论》),此处“心”大体可作“情”解;又如“故人之情……心好利”(《王霸》),心之“好”被列为“情”的一个部分,此即“心”当指“情性”而言。我们已经知道,荀子言“质”和“具”是指人先天的能知、能行的能力和才具,就其言“能知”而言,它的确隶属于“心”,但此心常常有非常广义的理解,涉及人生而有的情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时可作为“心”来理解,有时又可以作为广义的“性”来理解,因而,在这一点上,两者常常不免有交叉重叠之处;而且荀子自己也常将“心之知”当作“人之性”来了解,如在《解蔽》篇中,荀子即云:“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杨倞注云:“以知人之性推之,则可知物理也。”杨注对“知”与“性”的关系诠解不力;梁启雄则谓:“‘以’当为‘可’,‘可知’犹‘能知’。‘能知’是人的本能,故曰‘可知,人之性也。'”[6]304李涤生同样取“凡以知”作“凡可以知”,谓“人之性为‘能知’,物之理为‘所知’盖人有能知之性,物有可知之理也。”[5]498由此而观,当有些学者将荀子所言的“质”与“具”了解为广义的“性”时,似乎并非只是毫无根据的主张,对此,我们不妨作如此相应的理解;同时,这也意味着,荀子《性恶》篇中所谓的“人之性恶”的“性”只是其更为广泛或广义的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7]60-61
三、“可以而不可使”
荀子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此一论说包含了圣人与普通人具有相同的质具知能,类似的说法在荀子的书中也多有表述,如在《荣辱》篇中荀子就曾明确地指出: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上述说法表明,禹和桀、君子和小人在材性知能以及各种感官能力和自然欲望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此处“材性知能”云云,大体上等同于“质具知能”。但是,荀子在强调君子小人之所同的同时,亦常常明示君子小人之所异,如同在《性恶》篇荀子即云:“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此处分别圣人、君子、小人、役夫之知并非从人先天所具有的材性知能上说的,而是从其后天学习习染而有的结果来说的,故荀子一方面云:“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荣辱》)另一方面又云:“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相反,“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性恶》)然而,问题在于,依荀子,既然小人之知能,足于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暂且搁置其他原因不论,则小人何以不为君子之所为?此即引入“可以不可使”的说法,荀子云: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性恶》)
在上述句式中,人们的直观感受是,“可以而不可使”是对自难问句中的“可积”和“皆不可积”的对应性回答。其直接的意思是说,理论上人人可积而成圣,而现实上人人皆不可积而成圣,这显然是一矛盾的判断,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荀子对“可”字的含糊用法,前引刘殿爵教授对荀子的责难也被倪德卫教授所提及⑧,而John Knoblock教授便直接将“可积而致”之“可”翻译成“possible”,将“皆不可积”之“可”翻译成“can”,⑨,而后者之“can”或“can not”在字义上却颇为含糊,它既可以指谓主观上的“能”或“不能”,也可以指谓客观上的“能”或“不能”,而客观上的“不能”已然包含了不被允许的意味。但无论如何,就实看来,荀子此处“皆不可积”所表达的意思是“现实上人人皆不能积”,此即荀子在后面何以会说“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的真正原因。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得以解决,盖理论上人人皆可积而成圣与现实上人人皆不能积而成圣之间尚需一套理论上的铺陈方能使两者条贯起来,亦即为什么不能?何种不能?对此,荀子的回答是“可以而不可使”,杨倞注云:“可以为而不可使为,以其性恶。”杨倞增一“为”字,与下文“小人可以为君子”云云相应,可谓端的,但缀之于“性恶”却在文义上与此说相扞格,故冢田虎直谓“此注不通”。[8]955李涤生则谓:“‘可以’,就理言,亦即就先天条件言。‘不可使’,就意志言,亦即就后天人为言。”意即人人皆有可以积学为圣的先天条件,而不肯者不可强使积学也。[5]554就“不可使”代之于“不肯”而言,此释原为荀子所含之意,盖荀子亦谓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故云“可以而不可使”。“不肯”指的是意志的自愿品格,故不可强使之。基本上,李氏所注较恰当地解释了涂之人可以为禹而未必然为禹、虽不能却又无害可以为禹,以及工匠农贾可以相为事而未尝能相为事的例子,相比之下,“足可以遍行天下”的说法,由于荀子继言“未尝有遍行天下”,以致此一基于经验观察的比喻有可能变成一“险语”,形成与“足可以遍行天下”的完全对反,乃至可能直接将“涂之人可以为禹”也被招致否定⑩。
平情而论,荀子此说虽不甚严格,然其意思却未尝不明。不过,如若进一步追问,荀子此处所说的“不肯”依然可以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尤其当荀子将“不可使”解释指向为“不肯为”时,虽语词上只有“不可”与“不肯”一字之转换,但在意思上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滑转,盖涂之人若要成为君子或圣人,即便具备先天的材性知能和主观上的“肯”的意愿,也可能还会有某些客观上的不允许,如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肯也,实不能也,此固是极端之事例,不足以此苛难荀子,然此一现象本亦由荀子言“可”字之多义所包含。实际上,荀子本人也意识到此类问题,前引荀子谓材性知能、好荣恶辱、好利恶害为君子小人之所同,而造成他们之间的“别”,除了所谓的“不肯”外,荀子又云“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荣辱》),虽然荀子所答之重心在“求之之道”,且就“求之”二字视之,似乎依然保留着个人的主观选择的意向因素,但其仍难避免有模糊影响之忧,我们不禁要问,此道为何?依荀子,“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荣辱》)荀子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忠、信、修正治辨以及虑之、行之、持之、成之之对比中,似乎将此道归结为注错习俗,“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荣辱》)此处“可以为”云云如果联系到上文所谓小人“不知其(意即君子)与己无以异”的“材性知能”而言,把它理解为一种“禹桀之所同”的潜在能力显然是恰当的。不过,在上述的文脉中,荀子明显不在强调此种“可以为”的潜能,而重在“注错习俗”对这种潜能的“扭曲”,故而此处“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云云在意义上似乎滑转为一种“关于可能性的模态概念”,显示“可以为”在此注错习俗中所指涉的可能性(11),故荀子又云:“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荣辱》)杨倞谓“注错”与“措置义同”;“习俗,谓所习风俗。节,限制之也。”杨注端的。王先谦则训“节异”为“适异”,李涤生认为非是,“节”非虚词,乃引礼文王世子“其有不安节”,注“节”为“居处故事”,进而引申为“生活旧方式”,故“注错习俗之节异”意为“后天的措置习染的生活方式不同”[5]64,王天海所注大体与李注相似。[8]140如是,荀子之意思便转而成为:君子小人在先天条件上是一样的,之所以有的人成为尧舜,有的人成为桀跖,原因在于其后天所处、所习的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所致。荀子类似的表述在书中多有体现,今仅举一例: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
“积”谓积累;“靡”,杨倞注“顺也。顺其积习,故能然。”锺泰、梁启雄、李涤生皆主“靡”为“摩”;王天海谓“靡”有习染、影响之义,故“积靡使然”,“犹言逐渐习染使之而然。”[8]332此处所当注意的是,无论是习染影响、生活方式皆是后天的因素,再加上居楚而楚、居越而越的言说,荀子之意似乎要向人们表明,之所以有的人成为君子,有的人成为小人,除了有内在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外在的客观环境;并且,相对于人的先天的材性知能而言,后天的习染积累、摩荡塑造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假如我们的追问即此而止,似乎荀子的相关观念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盖强调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在孔子、孟子那里在在可见,不烦赘引。可是,如果我们细心揣摩荀子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其对后天环境的强调,却不免会产生一种与荀子“可以为”之宣说多少有些相反的看法,此亦非捕风捉影的闲议论,至少荀子的相关言说隐约地包含着这一点。前引荀子谓君子小人之别在于“君子注错之当,小人注错之过”,几乎所有注家皆偏于解说“注错”之义,这是有道理的,而所谓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说到底就是一个人生存的后天环境;但各注家对“注错”之“当”或“过”的问题却鲜少解释,大凡只谓“合于礼义”(12),更多的则是对此忽略不论。依笔者的看法,此处恐尚有“剩义”存在。简言之,将注错之“当”或“过”了解为合不合礼义的确是其中的一层意思,此一层意思偏于强调“可以为”的个人选择,亦即个人选择是否恰“当”,还是个人选择出现差“过”?但注错习俗之“当”或“过”在荀子的思想系统中似还有另一层意思,此即是习俗环境本身之“当”或“过”的意思,在此一层意思中,人所面对的习俗环境似乎并没有选择的空间。依理,人固可以选择以创造新的风俗和环境,但从荀子文本的语境中,他显然在意或强调此已成的后天环境的良莠、好坏对人(或为君子或为小人)的制约和影响,故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之说。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说,在荀子,“注错习俗”本身的“当”或“过”已然超越了个人选择的范围,在特殊的、世衰道丧的“注错之过”环境中,小人欲成君子,“可以为”之“肯”已远退于次要的位置,“不可使”之“不能”意义为之突显,在此种情况下,小人欲成君子,似更有待在位者或君子之驯化启导(13),此一观念同时亦为荀子强调“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作了某种理论上的预设和铺垫。荀子又云: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荣辱》)
此段意思清楚,各注本亦无原则争议,所言人之情可如此、可如彼,乃谓端视教化而定。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横生枝节,故造繁难,我们似乎就还应鼓起勇气追问,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生于汤武之世还是生于桀纣之世,已然纯系乎个人的运气,且此或安荣或危辱的习俗环境对于个人而言又是无法选择的,却对个人成君子或成小人产生莫大影响,虽人之情可如此可如彼,但在汤武或在桀纣,其结果却可能远若天壤。甚至在此语境中,荀子所声言的君子小人“可以相为”的作用已隐而不彰,反而习染环境对人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此类问难是否出于对文本的过度诠释而纯粹妄加于荀子呢?看来似乎并不完全如此。荀子又云:
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荣辱》)
此处“生”作“性”解,指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之情性(14),意即人生来就具有小人之性,又遇混乱之世,习混乱之俗,故而小上加小,乱上加乱。荀子给出“遇”与“得”二字,意谓人是被“抛入”此世的,世道良莠之“遇不遇,得不得”,对于个人而言固然是既与的(given)、无法选择的,但此一坚硬的、存有论的事实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后天修为在作出反思之前就早已被此“先有”的既与世道、风俗(或危或辱,或乱或治)所笼罩、所占领(15)。试设想,对于已经陷入乱世乱俗之中的人而言,礼义之道、先王之音固不可得而闻,而眼前世界,蔽障重重,满坑满谷,贪欲横流。人欲依其“可以”之“肯”顾自超拔,又岂可易得?荀子所谓“以小重小,以乱得乱”不正是在此特定的习俗环境中民情下自沉埋之描述么?正因为如此,荀子指出环境的作用,而云: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劝学》)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
此云蓬草生于麻中,不用扶持自然长得挺直,白沙与污泥混在一起,自然和污泥一样污黑,其原因正是环境所渐之故,而此后天的环境对人成为君子的影响具有“不扶而直”(即环境即教化)的作用,同样,对于人成为小人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所谓“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若缺却贤师、良友(谓君子也)之启导,依然不能“优入圣域”,而只能随顺环境一滚而滚。故云白沙质性虽美,然陷于污泥,只能一污而污,岂有他哉。由此荀子教人“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我们暂且撇开“就士”不论,如前所云,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其所居环境究竟是尧舜之乡还是桀纣之乡,似乎并非是个人主观上的“择不择”的问题,而是被抛入的恰巧的“遇不遇”的问题,假如碰巧所遇为莺歌燕舞、和谐美善之世,此自是幸莫大焉;若命途乖舛,所遇为淫污衰丧、邪说暴行有作之乡,则“可以为”的空间又究竟有多大(16)?在极端情况下,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有关“恶的平庸性”的思考及其对康得“善良意志”之诘难,或许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此一问题的深入思考[9]。若再联系到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的言说,此习染环境的力量似乎使人相信足于销蚀“小人君子可以相为”的言说,而“不能相为”倒好像成了唯一的现实(17)。
四、“君子”
然而,这样一种理论上的蠡测本身就充满了挑战和兴味。说其是“挑战”,此即意味着,若后天环境对君子小人之可以相为果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荀子“人皆可以为禹舜”之宣称就可能沦为一种戏论,这既不能说服荀子,连我们自己也很难说服;说其是“兴味”,此即意味着,如果人人皆可以在衰丧沉沦的环境中轻其所“肯”即可成为君子,那么,教化的重要性固然很难看出,关键是,荀子对君子的器重及其特殊的角色、功能定位又无法得以安顿。
细参荀子之文本,基本上荀子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来下手处理的。
先说君子之与习俗环境。荀子之所以强调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不仅基于理论的思考,而且也与经验的观察密切相关,更与他借此设置以高扬君子之作用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荀子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以声色货利、暴力战争露其精彩的时代,此自毋需赘言,所谓“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正论》),一方面,“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尧问》);另一方面,即是百家异说之间,或是或非,盈盈而无定准,“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儒效》)浸淫摇荡之下,趋炎附势者有之,徒骋巧辩者有之,是非之道不明,伦理道德崩塌,礼义教化夷荡。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背景下,荀子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埶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荣辱》)此处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杨倞注云“开小人之心而内善道也。”久保爱谓“内,音纳。”[8]145所言端的。问题是,何以在同样的环境中,众人之成德向善要等待君子来开导启迪,而君子何以独独不受此环境之影响?此一问题又可以分为两面,一是荀子对君子(包括圣人)的特殊了解,可属于另一理论问题,今暂且不表(18);一是荀子的确认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小人若要依其自身的“肯”的意愿成为君子,是很难靠得住的,在此一意义下,虽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但此处的“可”只具有抽象的意义,或只是关于可能性的模态概念,其实际意义当由君子之开阐启迪来完成。
然而,这样一种解释是否有误解或污枉荀子之嫌呢?荀子的确清楚地宣称“人皆可以为禹舜”,此处暗含有人人在先天能力上的平等;然而,正如学者所知,荀子思想还有另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严守君子生民(小人)、智愚贵贱的等级之分(19),所谓“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荀子类似的言说在《礼论》、《富国》、《王制》等篇章中在在可见(20)。在此前的论述中,我们似侧重于说明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小人“肯”其为君子并不可靠,必有待君子或圣王之启导,但此一脉络似乎并不构成“人皆可以为禹舜”的反题的“强判断”(strong claim)。今荀子直接宣称君子与生民百姓之间不仅在贵贱、贫富、轻重上存在分别,而且在智慧、能不能等先天能力方面似乎也存在着不平等,此一言说对荀子“可以而不可使”、尤其是对其“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的说法便构成了一个不小的威胁(21)。从原委之了解上看,荀子之有此一主张实可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作出解释,就历史而言,荀子之时,国强君威之势渐成,风气趋于贵君而贱民,荀子乃就时势而主尊君,此固环境使然(22);就理论而言,荀子之此一观念亦可上接于孔子,盖孔子亦曾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又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之,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而荀子在《正名》篇中则云:“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杨倞注曰:“故,事也。言圣人谨守名器,以道一民,不与之共事,共则民以他事乱之。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此段原在说制名乃圣王明君之事,不可与生民共。杨倞就文本脉络出此解,可供一说。但对何以不可以示人即未作详释。郝懿行则云:“故,谓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难晓,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与共明其所以然,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比之下,郝说更弥(23)。尚需指出的是,在上述脉络中,所谓“不可与共故”之“不可”乃是“不能”之义,或更准确地说是“不易”之意,盖其前提条件乃是“民愚而难晓”也,谓其“愚”,则有“不能”之意;谓其“难”,则有“不易”之意。今案之于荀子文本,所谓生民百姓愚而难晓之意,在《天论》篇言“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礼论》篇言“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事鬼也”中凿凿可寻(24)。理论上,生民既愚而难晓,则必须等待圣王和君子,犹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此亦理有固然也,故荀子云: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之”,谓君子也。引者注)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富国》)
生民百姓之劳力、社群、财富、生活环境和人生寿命,包括材性知能,为天地所生,不过若要借此“肯”其为君子,成其为大人,却似乎离不开圣王和君子之开示与照拂。只是,在上述脉络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个人“肯不肯”的选择权,剩下的似乎只是被动的接受权,亦即只能等待和接受圣人的成全(25)。有时候,在荀子笔下,对圣王和君子之师法所起作用之描述,实不免让人心情跃如与砰然,盖其点化之功,犹如电光火石,倏然而动,歙然而化,如荀子云:“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荣辱》)若理论上可以如此说,则待荀子言“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时,我们可以推知,荀子对生民百姓之地位、贵贱、知能等等不能同于圣王君子,实在其思想中已另有定见,而此一定见乃指向现实中的“不可能”、“不允许”(26)。荀子云:
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王制》)
“埶”,同势,谓势位:“澹”,杨倞注:“澹,读为赡。既无等级,则皆不知纪极,故物不能足也。”不能足则争,争则乱,乱则穷。若人人分位平等,无贵贱之别,国家当然不可治理;同样,官吏势位没有差等,意志行动就不能一致,众人身份没有差等,就谁也不能役使谁。审如是,荀子认为,必须设立君子与百姓之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不限于后天的,而且如前所言,似乎还包括先天的,君子智而敦慕,百姓愚而难晓;而对于生民百姓而言,便只能等待圣王君子之阳光雨露,否则,既逆于“天数”,即群居和一之社会秩序便无由达成。至此,荀子乃转而极言君子角色、地位之重要,荀子云: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致士》)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
依杨倞:“始,犹本也。言礼义本于君子也。”此句犹言君子是生礼义(之道)之本(27),故云天地生君子,君子生礼义(之道),以礼义治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才有条理秩序。所以,君子是与天地相参共成化育的,是万物之总领,人民之父母。无君子,则自然世界失其秩序,人文世界失其统领,而社会人群呈其至乱亦理有固然,势所必至者。
话说至此,人们不免或问,何以在孟子力主“民贵君轻”、民为主体的背景下,荀子却一反常态,大唱贵君贱民之论?或许,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看,此间原因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对战国中后期,随着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崩瓦解,诸子平等意识之兴起(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墨子的“兼爱说”等)的一种反拨。果如是,我们即可理解荀子何以特别重视社会等级之划分,特别重视君子优于众人的观念(28)。一方面,荀子要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宣称“人皆可以为禹舜”,这是其苦心构筑教化哲学不能不预设的最低的理论底线;另一方面,荀子又要在观念上对抗战国中后期兴起的众人平等的“早期启蒙”意识,故表现在此一主题上,荀子在严守君子与百姓等级之别外,面对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这一稍显轻巧的断言,荀子“可以而不可使”的讨论,则使此一主题变得更为复杂,至少他通过对“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性恶》)的观察,认为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性格构造”(different make-ups)(29),故而,荀子主题突出、目标明确地主张君子与众人的不同(30),认为贫富贵贱、君子百姓之间的等级秩序具有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性质。君子是董理天地之人,生民只有接受君子之“董理”,才可避免做“方外之民”,故云“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道》)依荀子,圣王和君子都是先觉者,都负有觉后觉得莫大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子不仅可以是世俗权力意义上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哲学意义上的王。他们地位既合天地之理,所谓“天地生君子”:他们的责任便是为天下立法,为生民立命,所谓“君子理天地”。或许在荀子眼里,生民百姓只需要行义守礼,而不必知礼义之由来及其道理,他们只需接受礼义之道,而非询问、选择礼义之道。君子所创造的礼义之道,本质上就如同医生为病人开出的处方一样,当事人其实不必知其所以然,只管照章办事罢了。或许因着这一观察问题之角度,有学者认为,孟子虽评杨、墨甚厉,然而在荀子看来,正是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偏离了“贵贱有等”的先王之制,对百姓“滥于同情”,故荀子批评孟子以及邹鲁之儒仅至“俗儒”之境,因为他们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儒效》)(31)的确,众生平等、民贵君轻是善好的价值,然而,若着眼于“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那么,在荀子看来,这些价值却因其违逆“天数”而成了哲学的天敌,先王之制的天敌,也成了达成社会秩序、开继万世太平的天敌,故当在其所清扫的“奸言邪说”之列:若人人都是君子、圣王(32)——原则上是允许的,但事实上却很难被允许——天下反倒没有秩序(33)。
五、“积学”与“心之所可”
假如上述疏解还有一定的根据,则当我们讨论“可以而不可使”此一命题时,我们所面对的荀子似乎始终有两副不同的面孔,亦即现实世界中的荀子与理论世界中的荀子。就前者而言,如前所述,荀子对“可以”先作一理论上的悬设,然后对“不可使”之义解释为“不肯”,再将“不肯”滑转为现实中的“不能使”、“不允许”,此一思路与荀子后效论和合理主义的心灵若合符节,若放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的脉络中考察,荀子的此一思路毋宁说是平实而可理解的。但在此一过程中,由于荀子的用语措辞遗留有甚大的想象空间,不免导致人们对其“人皆可以为禹舜”的宣称一时产生信念上的摇动。
然而,当我们的视角由现实转向理论的领域,我们便发现,荀子对“可以”之“肯”不仅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而且其诠解之理论力度和深度亦给人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现实世界中的荀子对“不可使”之了解,乃不得不使其注意论说在存在世界中的实践的“可行性”(practicability)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理论世界中的荀子对小人君子“可以”相为的论证,乃必使其全力于注意论说在理论之普遍性方面所具有的“可欲性”(desirability)。我们不妨认为,“可行性”与“可欲性”之间的交叠与紧张,正是荀子“可以而不可使”此一命题所以呈其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委所在。
G.E.M.Anscombe曾经认为,假如人们把某事物认作是可欲的,那么,我们可以径直地认为,被需要的某事物的特征,就是需要者对其在某方面的可欲(34)。我们暂且撇开事物、欲望、价值等等复杂的关系不论,孟子即有所谓“可欲之谓善”一说(《尽心下》)。“可欲”包含着人的自由,故有云“求则得之”、“求在我者”;同时,某事物之所以为可欲,对需要者而言,其所以能“可”之,必含有普遍必然性之判断;最后,就某事物之为可欲的对象来说,我们亦可以说“可欲”之所以为“可”,主要不是由于“满足”(35),而是主要基于“需要和评价”,这种“需要和评价”是以反思为基础的,此点类似于Harry Gordon Frankfurt所谓的人的“第二序欲望”(36)。“需要和评价”包含“满足”,故它可以为人“可其所欲”提供动力保障;但“需要和评价”不等于“满足”,因为它的最后奠基是理性的认知、评估与决断。人若随顺其第一序之自然欲望,不经反思与评价(用荀子的话来说即无度量分界)顺而求之,其结果是合于“犯分乱理”,与善果无关。故我欲求某物,盖缘某物能给我满足,从而认定某物即为善,此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盖对某物的欲望并不构成该物为善的充分条件。由此而观,“可欲”之“可”不是出于个人主观的好恶,甚至也与个人的欲望的心理事实没有关联。可欲之所可的对象出于理性的反思和评价。
就荀子而言,圣人或成圣乃是其所欲的目标和对象,盖圣人乃至善之象征,而所谓“善”,在荀子之字典里,“正理平治”至少是其重要的涵义之一,而圣人恰恰体现了“尽善挟治”(《儒效》)、全德备道的品质,荀子云: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正论》)
荀子相关之说明甚多,不待一一列举。问题在于,“所欲”并不等于“可欲”。若所欲之圣是可欲的,则必须满足所有人皆具有成圣所需要的先天条件,此点荀子乃凿凿言之。但如前所云,荀子间或也会流露百姓愚而难晓之意,此处之“愚”应当是一种弱解释,不应是先天知能上的纯粹无知,体察荀子之文本,此“愚”之实际意义当是“陋”,盖荀子认定人皆可为尧禹、为桀跖、为工匠、为农贾,并认为“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荣辱》)对此杨倞注云:“言人不为彼尧、禹而为此桀、跖,由于性之固陋也。”若将“愚”归之于“性”,即此“愚”并属于先天的、生而有的属性,依此理解,其结果固将颠覆“人皆可以为尧禹”的断言,而圣之“可欲”也必将丧失其普遍必然性的基础,这对于拳拳致力于教化百姓的荀子而言,不啻是自讨繁难,故杨注难通。锺泰则谓:“案《修身篇》曰‘少见曰陋’,后文以陋与塞、与‘愚’并言,正少见谓,盖言不学也。杨注以陋属性,非是。”(37)“少见”、“浅陋”是结果的描述词,其原因则是“不积”礼义、“不学”礼义,故荀子下文接着云:“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杨注:“变故,患难事故也”,疑非是。冢田虎则云:“故者……谓性之故也……言为尧禹者,乃非其性异也,起于变化性之所以恶,而成乎修饰之,待性之恶尽,而后德义具备者也。”依此理解,则我们可以说,圣人与百姓在成圣的先天条件上本无不同,差别只在于前者愿意“积”礼义和“学”礼义而后者不愿意,且不可强使,故人之所以可以为圣,端在其积学和化性起伪的工夫(38)。
荀子有关“积学”和“化性起伪”的工夫,学者已多有讨论,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再做铺陈。尚需指出的是,荀子言学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学”是改变人们身份等级和愚而无知的快捷的唯一途径,荀子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圆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儒效》)对应于贵贱、愚智、贫富,荀子连用三个“俄而”以见“学”之功效,在儒学史上,尚无有出其右者。其二、“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指导和“知”的工夫实践,而且还是一种制度安排,荀子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此处,“属”谓学而归;“为”谓学以增进(39)。其三、“学”还是人禽之别的一个重要标准,荀子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当年孟子言人禽之别在人有“四端”,荀子代之于人有义、辨、群、分;今荀子又言礼义之学为人禽之界端,“学不可以已”,即便是圣人也应学之不断,“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大略》)至是而直将学之所以为人翻出新面貌。上述言“学”之三义,通乎道德与政治,亦为荀子言“所欲”所以为“可欲”之重要途径,无疑也。
固然,荀子言“可以而不可使”,在语气上似轻于“可以”,而重在“不可使”。然而,无论荀子是看重环境之因素,还是主意于圣王或君子之作用,“可以”始终是一条不可和不得摇动的底线。“圣可积而致”之“可”除了前此所说的种种因素之外,荀子还有另一种说法,此即是“心之所可”(40)。有关“心”的特点与作用,学者讨论甚多,今不赘;而对荀子“心之所可”的了解,笔者也已撰文作了初步的探讨。尚需说明的是,荀子言“心之所可”乃是西方学者颇为热衷的一个话题,D.S.Nivison、Bryan W.Van Norden、T.C.Kline Ⅲ、David B.Wong、Janghee Lee、Aaron Stalnaker等人皆对此有重要的阐发(41)。基本上,对荀子“心之所可”的讨论,乃主要围绕着《正名》篇的一段论说而展开的。荀子云: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为之节制(依胡适,此后九字,今本阙。今据日本学者久保爱所据宋本及韩本增)……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胡适将“心之所可”一句看作是荀子思想的特色,可谓中肯与端的[10]322。细分析之,就“可”而言,似重在意志之肯断;就“心”而言,似重在认知之作用,Janghee Lee教授则对此有更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在荀子那里,“心的等级结构允许情与欲、意与知在心的统一体之中共存,然而,那些出于天性自然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却必须待心之所可后活动。”(42)而A.Stalnaker教授则认为:“荀子用‘可’字依次既表达‘可能性’(possibility),也表达‘许可’(assent),正如在《正名》篇中所说的,‘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此一双重意义有助于他表达这类判断的力量:所可——‘我们所许可的’与‘我们认为可能的’,具有完全相同的意思表达。”(43)的确,在荀子看来,对于涂之人而言,为禹的先天条件既已具备,虽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难免于下自沉埋的可能,但若借助积学工夫、君子之启导以及“心之所可”的发动,理论上,为禹、成圣本身的可欲的普遍性依然可以确立,盖对成圣的心理结构而言,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可”与“欲”是一对最为关键的概念,“欲”是性,“可”为心,“可”因“知”而出现,“可”与“不可”因“知”而造成。如是,即“心”便控制了行为,而“欲”不论如何强烈似乎也不可能转化成行为,所谓“天性有欲,心为之节制”。由此而观,小人之“不肯”为君子、为圣人,更多的是为欲望所主宰以及意志力的缺乏所致,而君子“不肯”为小人,即将“心之所可”所包含的理性、意志和价值评价作了进一步交融。Van Norden(万百安)甚至认为,荀子明显否认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的主张,而他正是通过刻画人之所“欲”与人之所“可”之间的区别来实现的,“相反,孟子已经宣称,人必定求其所甚之欲(a human must seek that which She desires the most),而荀子则断言,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此决定者不是其所欲,而是其所可。”(44)暂且撇开孟子的问题不论,至少在荀子,一个人的行为的“可”与“不可”必基于心之“知虑”和“辨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意志决断,依荀子,这种“心之所可”可以在欲望与行为完全相反的情况下发动行为,实现与欲望背道而驰的心知的目标,此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人有舍身救死之决断。荀子通过此一事例向我们透露出,“心之所可”包含着知、情、意综合而有的深沉的力量,并借此而撑起其“人皆可以为禹舜”的教化哲学的根基。
六、简短的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中心主题是荀子“可以而不可使”的主张,虽在文本根据上以《性恶》篇为中心,然而,其所旁及的范围却涉及《荣辱》、《儒效》、《王制》、《解蔽》、《正名》等等,颇有名不副实之意味。然而,一旦想起经典之思想系统,犹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的特征,内心也便多少为之释然。基本上,与孟子一样,荀子在理论的普遍性上明确宣称“人皆可以为禹舜”,但多少与孟子有些不同的是,荀子似乎以更为冷峻和现实的目光来打量世界,故而,一方面,他对“可以”给予理性的普遍性的基础,同时也赋予“心之所可”以深沉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不可使”又置诸于客观的现实世界中加以理解,注意到理论之“可欲性”在实际世界中可能遭遇到的诸多曲折以及人的“意志无力”问题,给人呈现出一幅合理性主义的心灵图像。无疑的,其间也包含许多有待发覆的问题,文中间或有所提及,但系统之了解,当俟诸另文。
注释:
①唐君毅先生便认为:“谓荀子之思想中心在性恶,最为悖理。”(《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东方人文学会1974年修订版,第111页。)
②D.C.Lau,"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in Mencius and Xunzi",Virtue,Nature,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ed by T.C.Kline Ⅲ and philip J.Ivanhoe,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0,p.201,p.216.(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BOAS)15[1953]:541-65)
③此处荀子一方面说“心生而有知”,另一方面又说“凡以知,人之性”,即知是属心还是属性?尚待疏解,笔者已撰另文加以处理,此处不赘。
④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第553页。北大注释本《荀子新注》谓“质”为才具:“具”为条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9页)。以“条件”释“具”易使人联想到外在的一面,总觉隔了一层。
⑤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荀子强调“真积力久”、“学不可以已”、“知之,圣人也”所包含的意义。
⑥鲍国顺《儒学研究集》,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鲍氏通过对《性恶》篇的分析,将荀子所说的“各种生而具有的性的成份”划分为三大类,亦即情欲、知、能。
⑦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6年版,第47页。陈氏对荀子心理作用的分类分成性、知、能三个部分,学者可参见第33-46页。
⑧David S.Nivison,The Ways of Confucianism,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1996,p.204,p.208.西方学者翻译“可”字各有不同,如倪德卫为“possible”、B.Van Norden和T.C.Kline Ⅲ为“approval”,而A.Stalnaker教授似乎更倾向于“assent”,参阅A.Stalnaker,Overcoming Our Evil,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6,p.73,p.137.
⑨John Knoblock,Xunzi: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Vol Ⅲ.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159.
⑩有关“足可以遍行天下”一句,在解释和翻译上存在歧义,今提供学者的相关观点以供参考。J.Knoblock把它翻译成“walking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whole world”,而B,Watson 即把它译为“to every comer of the earth”(参阅B.Watson,Hsun Tzu:Basic Writing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pp.167-168)。依庄锦章的看法,荀子的此一类比在Knoblock的译文中指的是一种经验的可能性,虽未尝有人足遍行天下,但它在经验上是可以做到的,相反,Watson的译文却指向经验上的不可能。故庄锦章教授主张Knoblock的译法,因此一译法“意味着荀子一方面否认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从未否认每个人有成为尧舜的潜能。”当然,庄氏也认为,在荀子那里,潜能与实能之间存在逻辑的鸿沟。参阅Kim-chong Chong,Early Confucian Ethics—Concepts and Arguments,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2007,p.71.
(11)参阅冯耀明“荀子人性论新诠:附《荣辱》篇23字之纠谬”,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十四期,2005年7月,第190-191页。本文兼采冯耀明与邓小虎的观点。
(12)如李涤生《荀子集释》,第64页。北大《荀子新注》释为“举止得当”。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页;John Knoblock将“当”译为“devising plans that are suitable to the occasion”,将“过”译为“transgressing what is appropriate”,大意与北大本相似,但强调了场合,参阅Xunzi: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Vol Ⅰ.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191.
(13)荀子有此一观念本不奇怪,夫子亦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14)李涤生《荀子集释》,第66页;王天海《荀子校释》,第145页。
(15)此一相关理路,伽达默尔已有言说,参阅氏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16)依荀子,在这种情况下,圣王和君子的作用乃具有决定性的,此后一节将会作出论述。
(17)从荀子强调“人习其事而固”(《君道》)、“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儒效》)等等言说中,我们多少可以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18)参阅拙著《合理性之寻求》,第175-206页。庄锦章教授则提供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回答,虽然君子和涂之人同样具备“知”与“行”仁义法正之理的认知和工具性能力,但是前者愿意学,而后者不愿意。参阅Kim-chong Chong,Early Confucian Ethics:Concepts and Arguments,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2007,pp.71-72.
(19)此处所言之“君子”涵义较为广泛,亦即既意指有位者、有品性者,亦意指地位、品性兼而有之者。
(20)荀子重礼,主礼之目的在养,而手段则在“别”,故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又见《礼论》)
(21)荀子此说之真实意思当非谓百姓在先天知能上不能成为圣王或君子,主要用意在显发君子之作用。
(22)荀子尊君,就其所言“君”之规定言,主要是理想意义之“君”,非现实中之君主,故与法家相区别。
(23)李涤生《荀子集释》采郝懿行之说,第521页,而王天海《荀子校释》不与,第907-908页。
(24)秦家懿曾云:“荀子认为受过教育的君子与普通的人的分别,在于前者能运用道德理性,而后者则只笃信命运吉凶。在商代宗教背景中,包括在王室宗庙中的占卜、舞蹈求雨等活动的对照下,我们在荀子的学说中发现一个分化过程的开始:上层阶级日渐遗弃这些宗教活动,而一般平民百姓却仍然相信天人感应与吉凶等事,这是成为精英分子的传统的儒学与基层的民间宗教分离的开始。”参阅秦家懿、孔汉思著《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1页。秦家懿的观点富有启发,可供参考。我们想指出的是,在荀子时代,上层阶级(如君子)是否已经遗弃宗教活动,又是如何遗弃的,容或都有可商量处。
(25)牟宗三先生在其《荀子与名家》一书中,将荀子思想的特点概括为“天生人成”,其涵义固然广泛,但上述所言亦当是其中另一涵义,“人成”者,谓圣人成之也。
(26)为避免误解,此处所谓的“不平等”乃就社会制度之现实安排必当有“惟齐非齐”之格局而言,而非他意。实则荀子尤主张于不平等中暗寓平等,所谓“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此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
(27)荀子在《性恶》篇亦有类似的说法,而谓“礼义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此处,君子与圣人就其皆为创设礼义之道之人而言,其义大体相同。
(28)尤锐在“荀子对春秋思想传统的重新诠释”一文中,非常敏锐地指出荀子所以措意于春秋时期作为“等级制度秩序”(hierarchic order)的礼的重要意义,该文所涵摄的诸多主题颇具启发,参阅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十一期,2003年12月,第137-183页。
(29)参阅Kim-chong Chong,Early Confucian Ethics:Concepts and Arguments,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2007,p.72,p.73.
(30)我们曾言,荀子在“天论”篇强调指出区分“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意义,这一意义在此一脉络下更可鲜明荀子的政治哲学意识。所需注意的是,我们大多数学者只注意到荀子强调等级的表面意义,而未及深究荀子对坚持先王之道中所内涵的等级制度的用心:在荀子之心目中已隐约蕴含着,若无等级,果真让诸子包括墨子或孟子的人性论说包含的平等思想一任发展,则社会之乱象将无所底止。而且,事实就是,若“分均”、“势齐”、“众齐”变成现实,社会便根本无法治理。
(31)参阅王庆光“论晚周‘因性法治’说的兴起及荀子‘化性为善’说的回应”,载《新原道》第一辑,第150页。不过,此处必须指出的是,孟子思想提供给人可解释的空间很大,虽然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配合其“民贵君轻”的观念可以为平等意识开启一隙之门,但孟子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君子或圣人与众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故在他的思想中,“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是圣人,而不是普通百姓;而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更可见其没有政治上之平等观念。当然,若细究之,其间仍有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32)在此意义上的君子、圣王不仅仅是从权力意义上界定,而且也从德性意义上界定,具有即圣即王的含义。
(33)2008年,笔者在台大高研院作“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的报告时,曾提出相关的看法,当时有些学者对我的这种观点持有异议。几年过去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打算改变相关看法的主意。同时,我还想指出,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理绪上正乃脱胎于荀子。
(34)Cf.G.E.M.Anscombe,Inten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D.S.Nivison认为,在荀子看来。善之所以为善,在于它使人满足(the good is good because it is satisfying)。参阅David S.Nivison The Way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p.87.
(36)Harry G.Frankfurt,"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Concept of a Person",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LXⅧ,1(January 1971):pp5-6.
(37)见李涤生《荀子集释》,第66页;王天海《荀子校释》,第142页;北大本《荀子新注》谓“见识浅陋”,第45页。
(38)《性恶》篇云:“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儒效》篇云:“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类似说法甚多。
(39)萧公权对荀子此说评之曰:“陈义甚高,于理甚当,于不平之中暗寓平等,上承孔子以德致位之理想,下开秦汉布衣卿相之风气。以视孟子世禄之主张,则荀子于此更能解脱封建天下之影响而趋向于维新。”参阅氏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40)必须说明,为圣“可以而不可使”还涉及有关人的构成的诸多方面,就荀子言,有心、性、情、伪以及义、辨、群、分,且《性恶》篇荀子又给出多种论证如“荀无之中必求于外”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加以讨论。
(41)笔者在《心知与心虑——兼论荀子的道德主体与人的概念》(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台北,第27期,2012年1月,第35-74页)一文中有部分相关介绍,为避免重复,本文不准备再作叙述,敬请读者原谅。
(42)Janghee Lee,Xunzi and Early Chinese Natural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49.
(43)Aaron Stalnaker,Overcoming Our Evil,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6,p.73-74.
(44)Bryan W.Van Norden "Mengzi and Xunzi:Two Views of Human Agency",in Virtue,Nature,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ed by T.C.Kline Ⅲ and Philip J.Ivanhoe,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0,p.118.有关荀子与孟子对“心”与“欲”之间关系看法,Van Norden的观点似乎也为Janghee Lee 教授认可,此间理绪复杂,可以进一步讨论,笔者已撰文另作处理,此处不赘。参阅Janghee Lee,Xunzi and Early Chinese Natural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p.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