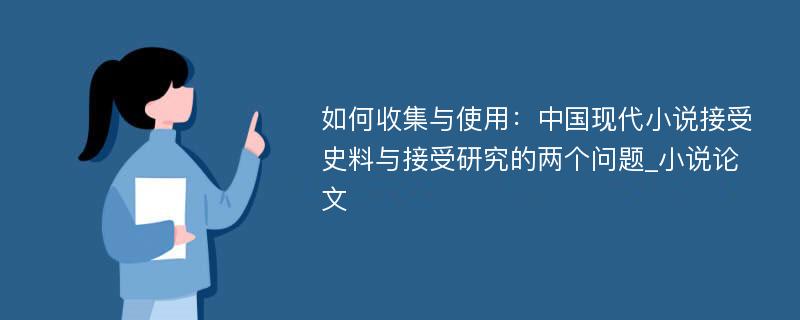
如何辑与如何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如何用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2)01-0180-06
史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并严谨地运用第一手原始材料,返归现场,还原历史,做出符合历史本相且客观的评价,是每个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笔者近几年来在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中,发现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辑录者的“偏”、“漏”、“瞒”;二是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的“添”、“改”、“删”。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现代文学史接受视野的生成与深化),有必要将这些问题指出来与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也希望能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研究有所助益。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侧重点在于这些史料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产生的影响,而不是这些史料背后的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辑录者的“偏”、“漏”、“瞒”
如何辑录史料和辑录什么对于成熟规范的古典文献学而言,自有其基本的辑录原则和严整的操作规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而言,虽然对此有所借鉴并达成相应的学术共识,但由于岁月动荡所造成的史料遗缺,或时代语境对接受者观念的束缚,或者当事人或其亲属对可能关涉利害关系的顾虑,等等,如何辑录与辑录什么就成为辑录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表现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的辑录上,对这一问题的顾虑就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偏、漏、瞒的问题,对现代长篇小说接受视野的生成与展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谓“偏”是指辑录者由于受接受观念等的影响而有意对接受史料表现出的倾向性,从而使呈现的接受视野基本为该文本的正面阈值的择录,而非全面的客观的视野呈现。这虽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该文本的接受史态,但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辑录立场,依然遮蔽了历史的原貌,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来的接受者。这种因显在的倾向性所导致的史料缺辑笔者称之为“偏”。当然,“偏”与“漏”不同,也不是“瞒”。“漏”是因为客观条件所限不知尚有相关文献造成遗缺;“瞒”则是有意隐瞒,多是将负面的史料刻意隐去。若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为例,“偏”多指仅列入资料索引但不节录其原文。“漏”和“瞒”则既不见正文也不见索引,但“漏”为非主观因素所致,“瞒”则为主观因素所为,二者有着较为明确的界限。明晰了这一区分,我们就可以对“偏”、“漏”、“瞒”的现象作进一步探讨了。
先说“偏”。文学接受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因而西方有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对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来说也不例外,而且越是有影响的作品接受的分野就越为显在。例如,当年《子夜》的接受实际上是在多向的质疑声中拉开序幕的,陈思、禾金、门言等都对《子夜》提出了不同的认识[1],但在《茅盾研究资料》和《茅盾专集》中[2],这些不同的质疑声并没有全文或部分节录其内,若以这两本史料所辑录的文章为中心梳理《子夜》的接受史貌,则会认为《子夜》自出版始就获得了高度的肯定,实际上,《子夜》的接受是在多向的质疑声中拉开序幕的[3]。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围城》中。方典(王元化)的《论香粉铺之类》和张羽的《从〈围城〉看钱钟书》两文在《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中也未予以节录[4]。当然,这两篇文章学理性不强,是否节录见仁见智,但如果将当时这两篇并不长的反对声音节录于书中(即便是其中的一篇),既能反映出《围城》的接受史貌,也能达到为接受者提供检阅便利的目的。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对《围城》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争议,还因为后来的接受者在反驳《围城》的攻击时往往举其为例,若能节录其中,自然能使接受者事半而功倍。另具典型性的是前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华思的遭遇。《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华思很快写了《评〈骆驼祥子〉英译本》一文,高度认同这部表现“一个想到北平谋生的青年农民的偶有的快乐与数不清的烦恼的直朴的故事”,将它视作了解中国普通人民的人道主义及其不可毁灭性的一本“最适当的著作”,认为它能在美国传播,是“中美了解事业中的一件大事”。[5]然而,这篇极具重构意义的接受视野却未能辑文于《老舍研究资料》,令人遗憾。如果说《子夜》、《围城》的辑录之偏或许有维护文本的“经典性”之意,那么《骆驼祥子》的辑录之偏是否是由于阐释者为美国人而当时——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美观念尚存偏见而失之于文呢?
再说“漏”。史料是个无底洞,穷尽史料的意愿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随着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以及全国各大图书馆(含高校图书馆)相应资料库的建立,许多所需史料足不出户就可通过电脑予以检索,极大地方便了史料的辑录,一大批以往未被人们发现的史料也重新被发现。例如杨邨人的《茅盾的〈子夜〉》[6]、尉迟憩亭的《赵子曰》[7]、石岩的《读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8]、凯蒂的《关于〈引力〉》[9]、中山大学文学院关于《〈春寒〉讨论总结》[10]等等,仅就笔者近几年搜集整理现代长篇小说的新接受史料为例,未见于各研究资料索引的就达50余篇,若再肯花时间或随着高校资料库检索系统的更加完备,拣“漏”过百并非不可能。当然,这个“漏”是正常的“漏”,但对接受史貌的归纳与梳理以及接受视野的拓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于《骆驼祥子》的接受有学者认为:“对《骆驼祥子》的批评意见在当时竟比肯定要多!”[11]还有的学者直言:“《骆驼祥子》生不逢时,民族危亡在即,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问世,即使后来注意到它的存在也没有精力写成像样的研究文章。”[12]这显然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而关于《春寒》的接受很可能被误认为无人问津等。但有些“漏”如《萧乾研究资料》[13],没有辑录一篇关于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的接受文章,就令人感到失望,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说“瞒”。瞒是一种刻意的主观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为贤者讳当是主要的原因。例如,在《叶圣陶研究资料》中[14],钱杏邨并不认同《倪焕之》的“扛鼎性”,他说:“茅盾说,《倪焕之》是十年来的扛鼎之作,但我们却不能说出《倪焕之》是如何的‘扛’法。”这一视野出自《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原载《现代小说》1929年第3卷第3期,署名刚果伦,后收入神州国光社1930年5月出版的《文艺批评集》第190—205页。但辑录者辑录的只是《文艺批评集》中的《关于〈倪焕之〉》一文,而对《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关于《倪焕之》的否定性接受文字“视而不见”,这就有“瞒”的嫌疑了。再举一典型的实例。李克异(1920-1979)是现代优秀作家,原名郝维廉,又名郝赫、郝庆松,笔名吴明世、袁犀、李克异等。由于他在日伪统治华北时文名显赫,如何编撰《李克异研究资料》就成为编撰者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本由李士非等人编集而成、由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李克异研究资料》,就成为只收集李克异正面史料的一本“半成品”,而关涉其负面的材料则全部未予以收录,这就不能用“漏”来解释,而只能是“为贤者讳”的“瞒”了。例如,1942年11月《华北作家月报》第2期曾刊登一消息:《斡旋会员郝庆松献金》:“会员郝庆松前由本协会派遣赴济南一带视察治运状况,一路收获颇多,今为感谢皇军赫赫战果,自动愿尽枪后国民之诚,将治运视察旅费金提出一百元,献金与北支派遣,当由本协会代为斡旋呈送北支军局矣。”同时还刊有一文:《由都市到乡村——治运视察报告会讲演词之三》,作者郝庆松,文中有如下字句:“在乡下我看见了英勇的日本军,治安军,他们在千难万苦之中,从事着职业工作,对于本次治运运动之一的‘幽灭共匪’,不待言说的持有着坚定的信念。而农民们出由各方面协力这工作,修护着道路,修建关楼,双手□是的从事着这样困难艰苦的工作。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这一伟大丰实的理念,倘说是由农民之手,由农民之力完成的,也非恰当。”毫无疑问,这是郝庆松附逆时的发言,辑录于书对后人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存在。在长篇小说《贝壳》的接受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这部小说曾于1943年获“大东亚文学奖副奖”,而且因之引起了一番争议[15],但是,这一争议现象同样失收于《李克异研究资料》。至于批评的接受视野,哪怕是较为准确的评价,如麦耶(董乐山)认为“很显然,作者的目的,是想藉这一本小说,暴露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丑恶”,但由于作者对于知识与教养的价值的否定理解,使作者“没有把握到它们的本质,只表面地看到了一些它们被歪曲施行了的一些丑恶的现象,便贸然发出这种‘对人类的哭声,对于人类的绝望’。于是,便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淖,在《贝壳》这本小说里的人物,便全是‘苍白而贫血的’,而其思想,也是颓废的,怀疑的。”[16]该书也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这本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与权威性产生怀疑。历史就是历史,刻意隐瞒决非史料工作者所应有的态度。《敦邻》、《杂志》、《华北作家月报》等是日伪时期著名的文学刊物,甚至可以说是研究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基本杂志,许多省级以上图书馆或老牌大学图书馆都有馆藏,编撰者未能将这些基本的材料搜集于内(索引仅收《华北作家月报》第7期),史料难觅恐不是主要因素。我想,这不是个案,对于沦陷区作家,对于附逆文人(例如《张资平研究资料》至今未能出版),如何辑录和辑录什么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二、创作者的“添”、“改”、“删”
创作者勿庸置疑拥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但本文所指的并非是作家对小说文本的修改,而是指创作者(也偶含辑录者)对接受史料的添、改、删,即对小说《前言》与《后记》的添、改、删。由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曲折多变,跨越不同时代的作家们为了应和时代的语境在重版旧作时大多对《前言》或《后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对《前言》或《后记》的添、改、删就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如果这种调整是一种正常的创作感言与思绪传达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或者说需要接受者对这一接受史料加以辨伪,否则极易堕入虚假推定、以假乱真的泥沼,甚至对文本产生误读,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了。
我们同样先从“添”说起。茅盾的《子夜》自1933年1月出版以来,一直沿用初版的《后记》,直到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再版《子夜》时,才新添了茅盾应邀写的《再来补充几句》作为新的后记。从此,这一版本成为新时期最为通行的版本,而茅盾在其中关于《子夜》的创作意图及主题的阐释亦广为流传,特别是策应“社会性质论战”与“反对托派说”的观点,影响深远,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理解《子夜》创作意图与主题的唯一视野。如钱理群等就认为:“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子夜》的主旨所在。”[17]但是,如果以此对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回答托派说”的创作意图与文本的客观呈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罅隙,即: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由与结局走向并不契合作者对创作动因的理性揭示。例如,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并不是败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手中,而是败在杜竹斋的倒戈上。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要是吴荪甫他们的友军杜竹斋这当儿加入火线,‘空头’们便是全胜了。”也就是说,当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相互胶着甚至略占上风时,善于见风使舵与投机经营的杜竹斋见义忘利,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多头”,使得吴荪甫最终一败涂地。又如,茅盾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是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但文本的实际结局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既没有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只有周仲伟被迫买办化,而吴荪甫只是对此有过动摇的念头),也没有与封建势力妥协,而是以一种悲壮的破产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商战之旅。因此,茅盾的“回答托派说”实际上成为预设《子夜》创作意图的一个温柔的陷阱。所以,夏志清将《子夜》视为一部“透彻地表露1930年的中国面貌”,“给中国社会来一个全盘的检讨”的小说。[18]而这正与茅盾在初版《后记》中的自述——“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相契合。再比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1957年出版《茅盾文集》第四卷时,茅盾在《第一阶段的故事》之末增添了《新版的后记》。与原《后记》不同的是,茅盾特意提到了小说的人物“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说:“这本小书的结尾已经写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到陕北去。这是象征着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或地主的家庭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间的觉悟分子已经认识到唯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这才中国民族能够解放,而个人也有出路。”这一进步的表态,无疑迎合了当时的期待视野。的确,小说的结尾也确实写到了仲文、桂卿等商量着准备去陕北的事,但如果我们稍加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何家庆并不赞成仲文他们去陕北,何小姐虽然也想去但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方案,而仲文自己又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又觉得现在一心想到西北去的人们中间,有不少是一时冲动,好奇心,更有不少是借了投身到革命的最前线的美名,实行逃避他在后方的艰苦而需要耐心的工作;这种浮薄偷懒的心理必须赶快纠正才对!”又当做何解释呢?又比如巴金的《寒夜》。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关于〈寒夜〉——〈创作回忆录〉之十一》一文,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小说的创作动机及意涵。因这是巴金在20世纪80年代后系统地以创作回忆录的方式谈自己的创作,因而此文作为“附录”被广泛地收入《寒夜》的各版单行本及巴金的研究资料中。在文中,巴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并非如此。1947-1953年间的上海晨光本《寒夜》并没有这句话,“她需要温暖”正式出现在小说中是1955年5月新1版、1958年3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寒夜》单行本,而且意义已发生了改变。因此,有的接受者认为:“小说结尾所表达的思想,才是整部作品的关键所在——‘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我们认为这不只是对曾树生个人悲剧的同情,更是对那个时代所有不幸女性的尊重与关怀;或者说既是对‘寒夜’的控诉,更是对‘温暖’的呼唤!”[19]显然是将巴金建国后迫于新形势下的一种改写理解成建国前的文本,而且轻信了文末“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完”的标注。再比如姚雪垠的《长夜》,在上海怀正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的《后记》中,作家开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故事在我肚里藏了二十年了,其中的英雄们早已死光了。每次想起来这个故事,我的眼前就展现了无边忧郁的、萧条的、冬天的北国原野,而同时我的心就带着无限凄惘,无限同情,怀念着那些前一个时代的不幸的农民英雄。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也了解他们的心。……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不顾一切地要做叛逆者,却只能走那条在两千年中被尸首堆满的,被鲜血浸红的,为大家熟悉的古旧道路。这条路只能带向毁灭。但这是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错怪他们!”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长夜》时,作者重写了一篇《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作为《前言》,关于小说的内容则这样写道:“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一般的农村生活,而是土匪生活,是通过写一支土匪的活动反映二十年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原和北方的农村生活。”而这种土匪,即“在《长夜》中所写的武装斗争,就是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20]。立场、观念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目前学界普遍将《长夜》看作一部土匪小说而忽略了对社会因由的审判,忽略了对原作中潜存的创作情态的体察,不能不说与作者的“误导”有关。至于茅盾借出版《茅盾文集》之际在《后记》中将《腐蚀》的主旨定向在暴露“1941年顷国民党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21],从而使一部可以读作青年成长小说的视野至今未能生成,也令人叹惜。而写出特定时代青年成长的“难言之痛”其实才是茅盾创作《腐蚀》的本意。[22]
再说改与删。改与删是现当代作家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作家在重版原作时均删改了原有的《前言》或《后记》。有的作家在删改时注明了删改的情况与日期,有些作家则依然标注初始的日期,造成原来即如此的假象,从而改变了文献的真实性,更有甚者在作家去世后擅改《前言》或《后记》,这就改变了文献的性质而成为伪文献。例如,迄今为止出版的各种《寒夜》的版本,《后记》都做了一定的删改,即便是目前最为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后记》的写作时间虽标识为1948年1月下旬,但若核之于1948年的再版本(包括三版本),也是一个删改版,即:都删去了巴金与耿庸间的一场小的恩怨。这虽然对理解文本而言无大碍,但对于全面理解当时的接受主潮及其潜流以及巴金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而史料的真实性也打了折扣。还有《山洪》。这是吴组缃创作的一部表现底层民众觉醒意识的优秀之作,1946年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后未再版。1982年,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该作时,作者对《赘言》(也包括小说)做了较大的改动,原本不足800字的《赘言》被删去近300字而仅存430字,而这430字又被作者改动了16处22字,变动不可谓不大。其中最重要的是作者关于文本的语言实践,即:通过方言刻画人物性格,展现小说的乡土气息的操作实践被作者悄然无痕地抹去了。这就遮蔽了原稿的本相。因为《山洪》颇具韵味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鲜明生动的人物对话,删去了这一点,作者为之做出的艰辛探索就无从谈起了(更让人惋惜的是作者在修订本中删改了原稿中的山乡土话,反而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从史料的真实性而言,新版《赘言》末的时间地点依然标注为“1942年5月16日渝郊白鹤场”,但实际时间为1981年,其真实性也荡然无存了。有接受者以之为据探讨吴组缃的小说艺术且失察于吴组缃小说的语言艺术[23],其接受视野的偏差显然缘自史料的失察。如果说作家的自改尚有情可原,那么编辑者的擅改就难以让人理解了。还是巴金的《寒夜》。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寒夜〉手稿珍藏本》。应该说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事,但是,该书虽然标明是初版手稿本,但《后记》却并非1947年3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本的《后记》,而是做了较大删改的压缩版,不免令人感到不解。诚然,原手稿中没有《后记》,但编者既然是以手稿本出版,又特意说明以初版本校对,那么,附之以初版本的《后记》当在情理之中,否则,接受者也面临着重新选择透析巴金彼时创作心境的史料问题。同样,在探析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的创作动机时,如果接受者不核查1933年开明书店版的《山雨》,以为《王照研究资料》所收的《山雨〈跋〉》即是1933年9月《山雨》的原《跋》,那就错了。此文不仅做了改动,而且做了较大的改动。具体地说有如下三点:1、讹文(编者独自改动的字),即:原文为“军国主义”,改为“帝国主义”;原文为“外国兵士”,改为“日本兵士”等。2、衍文(编者独自增加的字),即:原文没有“以”,增加了“以”;原文没有“变化”,增加了“变化”等。3、脱文(漏掉的字),即:原文为“痛苦妇女的失望与觉悟”;“离开上海之后”等。此书出版于1983年,此时王统照先生已去世了26年,不可能修改自己的文章,而短短不到730个字的《跋》被辑录者改动16处36个字,看似更为通顺亦符合现时的理解了,但这一改动既不是作者的原意也对文本的接受产生了影响。有学者以之为据并印证王统照《山雨》的现实主义精神[24],由于论者未对史料加以辨伪,同时又对文本中“革命青年与痛苦妇女”的“失望”缺乏论述,难免令人感到遗憾。其他如《一个女兵的自传》的接受研究中一些接受者轻信作者的自述以至以讹传讹等[25],亦令人遗憾。
史料工作是一项艰苦而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今的评价体系下,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工作,但史料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不能轻视。但在如何辑与辑什么以及如何用与用什么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问题。没有深入探索的精神、全面客观的态度,史料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质疑;而“穷尽”了相应的史料却又进行了“必要的”删改,史料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接受视野的生成也会产生偏差。然而,据笔者对目前已出版的所有的研究资料集认真核查后发现,其辑录的有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史料,都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原文不一的问题,若不进行认真核查肯定要掉进失误的陷阱,甚至一不小心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以讹传讹的蔓延。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又不可能不利用已整理的相对系统的史料,不可能不在前人已开创的基础上拓展我们的视野,但如果每一个作家或作品都要我们自己从零出发,每一个材料都要在核查之后才敢放心使用,且不说工作的难度与工作强度太大,仅说史料辑录者的初始意义又在何处呢?看来,如何辑与如何用真是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标签:小说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骆驼祥子论文; 子夜论文; 围城论文; 长夜论文; 山雨论文; 倪焕之论文; 茅盾论文; 巴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