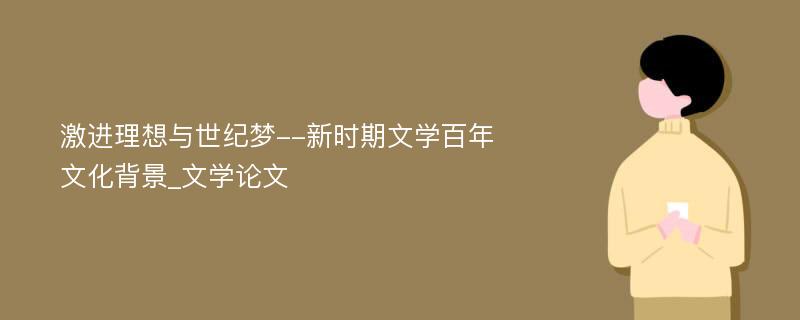
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新时期文学的百年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新时期论文,之梦论文,文化背景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新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内涵是相对历史而言的,作为新时期表意形式的新时期文学,尽管充分表达了它的功能特征,但它在文化层面与百年文化传统仍密切相关,公共话语是它的主要表达形式。百年文化传统的弥散和延宕在这一时代的文学中有鲜明的承传关系。“体用论”的华夏中心主义独尊心态是实用的,而对“他者”认同的取向同样隐含着功利用意。因此,试图在文化层面解决富国强民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它也超出了文学能够有所作为的范畴。激进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世纪之梦的期许。
关键词 文化传统 反传统 新传统
新时期文学对于中国作家和它的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辉煌的旧梦,一个无法重临却值得不断重温的过去。作为再生中国对梦想追求的表意形式,它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短暂历史的文化精神。虽然每一时期都会形成不同以往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但旧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因此而被排除在外,“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靥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文化作为一个绵亘不绝的整体, 意识形态的变化并不能取代它自身的发展与延伸,事实上,它的发展与延伸始终包含着传统的文化内容。1986年,当新时期文学历经十年时,对它的讨论和总结达到了高潮,无论那里含有研究者多少感情上的成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论是全面肯定还是全面否定,或是部分肯定又部分否定的意见中,它们无一不与我们百年来文化或文学的核心话题密切相关[2]。 这一有趣的现象为我们揭示的秘密是:被命名为“新时期”的文学仍然存在于百年的整体之中,我们仍为百年来的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命题所困扰。新时期文学的激进姿态,救世情怀,情感矛盾以及专制式的态度都有丰富的历史营养,有着无可置疑的先辈们的血缘遗传。
文化史的研究者们注意到: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以己为独尊[3]。 正如蒋延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的:“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走,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对不肯通融的[4]。 这体现的正是目空一切的“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1840年,西方以坚甲利兵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 近代思想的先驱者们开始了思想维新。 魏源于1842年编成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5] ”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邻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6]”的看法。 这就是逐渐形成的著名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之源。特别是后来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体用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一思想的要害不仅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被动性适应,在文化层面上,它固守的仍是“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立场,仍对本土文化和既定秩序有不能放弃的情感依恋。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炮舰和纺织机是常常带着它们的哲学一起来的。然而1860~1890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滥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就可进入现代[7]”。因此, 从“唯我独尊”到“华夏文化中心主义”都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虚设的文化大国心态。
1898年1月28日,四十岁的康有为六次上书大清光绪皇帝, 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书》。康氏在上书中说:“变则全能,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不到半年的时间,光绪皇帝便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变法的决心[8]。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其主要内容不仅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同时亦触动了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等等。但在洋务派、顽固派的推诿敷衍或置之不理的抵制中,这些变法诏令大都变成了一纸空文。“百日维新”悲壮地失败了,“维新人物”或血溅菜市口,或亡命四方,免于追究的也遭到了监视。其中最为感人的是谭嗣同,他拒绝海外避难的劝阻,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10]”。慈禧太后不经公开审讯便将谭嗣同在内的“戊戍六君子”斩于北京菜市口。临刑前谭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1]”这虽是一次失败的变革,但它却启动了二十世纪激进的求新求变史,也激起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壮的救世情怀。
美籍华裔学者张灏在评价戊戍变法思想家们的意义时指出:他们“世界主义”的思想取向“使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可资选择的秩序,这种秩序迫使他们发现既存秩序基本制度的偶然性和缺欠[12]”。发现了中国的危机不仅是制度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危机。因此,自那一时代起,为了回应这双重危机,激进的姿态便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新传统。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拒绝的态度上。在五四时期,这一态度达到了空前的激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许存有其它方面的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则是出人意料地一致。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吴虞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给予了没有退路的彻底否定。但是,为了传播新思想,彻底推翻礼教的文化专制,除了必要的思想启蒙之外,还需要中介性的手段,有趣的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五四的文化主将们都同时想到了文艺。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开篇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3]。四部不列,名士不齿,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小说将被启用的时候,突然身价倍增,并首次被赋予了直接参予和承载社会变革的重大使命。此后的文学便开始有了“角色”的位置。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5],陈独秀亦认为“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16]。鲁迅则说得更为直接:“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7]。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所有的介入者几乎都对文学有功利性的期待。不要说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直言不讳地要求了文学的内容,既便是胡适的“八不主义”,也隐含了更适于表现“当时整个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携手同行的时代新内容”[18]的形式需要。自那一时代起,无论文学的内容或形式,便都有意无意地具有了“意识形态”性。文学的这一特性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已被各种文本充分地肯定过,但肇始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文学家们为了文学的独立和“自治”付出过怎样的努力,以及文学的救世情怀又曾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们。因此杰姆逊教授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他甚至多少有些感慨地强调:“第三世界对我们今天的教训再没有比这一点更为及时和迫切了”[19]。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杰姆逊教授的感慨并非没有道理,但纵观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内忧外患的深刻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形成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呢?百年来激进的反传统,忙于启蒙救亡,忙于社会变革重建民族的主体性等等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不仅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检讨和反省,既便是陷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流露出了情感上的矛盾。曾是反传统斗士的周作人曾寄希望于“思想革命”,但不久他便发现了启蒙的无望,与其“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顿臭打”不如去寻“做哑巴”[20]的乐趣了。他终于放弃了“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者”[21]的角色,而沉溺于和谐境界,去感受“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22]的“幸福”了。也许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更集中典型地传达了知识分子情感上的矛盾和危机。社会要求“我”装扮的“角色”和本来面目的“自我”发生无可弥补的分裂。“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在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23]”这些真实情感的流露从某种意义上已经预示了知识分子内心冲突无可避免的危机。但作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存在着选择的可能,同时也存在着“被选择”的可能,他们事先预设的关切之点和角色的自我定位,就是被选择的先在条件。在许多场合人们都曾遗憾和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形成独立的属于这个阶层自己的传统,这诚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但是如果联系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具体的历史处境,对知识分子独立传统的要求是不是有些不切合实际了呢?即便是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这一传统距我们更加遥远了还是切近了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百年来的文化背景对于“文革后文学”的影响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历史不能给予“如果怎样……就怎样”的假定形式,但发现百年来“新传统”的缺陷和局限则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反思百年来文化新传统的思考中,无论海内外的学者都对激进的反传统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24],但那里仍存在着理论的预设,缺乏操作的可行性,比如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论就是其中的一例。而一些在态度和方法论上总结教训的文章则要显得平实和富于启发性。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反传统的“传统”,“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静。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的焦躁不安——其极端便是史称‘文化大革命’的那场全面痉挛”[25]。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以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或许新文化的激进方式本身就是违背新文化而适合旧文化。……旧文化最可怕的也许不是它的文化内容,而是它唯一的、专制的存在方式和排它性,用新文化的专制去替代旧文化的专制,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态度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专制方式本身就是对新文化内容的否定和背叛”[26]。这种“专制的文化态度”同它反对的对象——“以己为独尊”的传统文化意识有一种心态的一致性。这种关联的揭示会使我们认识到,传统并不是身外之物的其它东西,而弥漫渗透于我们的四周,我们的行为和心态无不投射于它的巨大背景之上,这也是讨论“文革后文学”必须将其放置于百年背景的真正动机。
与“专制的文化态度”的揭示相联系的是对激进的反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27]。郑敏先生指出:“二元对抗”是“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往往站在一个中心立场将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对对对抗性的矛盾,并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拥护其一项,打倒另一项。这样就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而非敌对的关系强扭成对抗的敌我矛盾”[28]。郑先生列举了几组人为的设置的对立项,认为激进的胡、陈拥护其中的一项时,必定要“打倒或活埋”其中的另一项。如果我们同意郑敏先生的看法,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激进主义在向对象发起进攻时恰恰陷入了对象思维方式的泥沼,在思维方法上暴露出了先天的局限。
那是二十世纪的早春,“新传统”的创造者在早春的浓雾中寻找着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富强梦,他们不得已以决然激进的方式作出了文化选择,因此连同他们的局限一起不仅共同构成了那代知识分子的独特性,而且也连同他们的局限一起构成了馈赠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和财富。那一时代的浓雾似已散去,然而我们身处的这一时代又为我们布满了新的浓云密雾,也许就在我们反省检讨百年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发出的声音正来自历史遥远的回响,我们无法走出我们的有限性,因此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自我的发现和批判,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的情怀。
“中西之争”已成为百年文化史的“元命题”。国门被西方用武力强行打开之后,西学也以各种方式涌入了本土。西学的涌入强烈地动摇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那种妄自尊大的心态不啻于经历了一次八级地震。那种误认自己为中心的幻觉打破了,西学如同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窥见了“他者”眼里的“自我”形象,那远不是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远不是自我设定的那个“自我”,它的丑陋残缺之处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这个“镜中之像”第一次致命地毁坏了自塑的主体。但是这“镜中之像”仍然是不真实的虚幻之像,这是“他者”眼中塑造的又一个“他者”形象,即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将中国作为“他者”塑造的形象。但是,在这“镜”与“像”的关系之中,很少有人能够确认真实的“自我”,一种误认的现象几乎普遍存在。但无论确认还是误认,在“镜像”的关系之中谁都会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为自己寻找一个位置,这也是文化的自我定位。
然而,这一定位的过程却是痛苦的。文化冲突导致了一种焦虑和危机的文化心态,要富国强民、拯救危亡,重新建立起主体和自信,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价值理性作出的选择;但微妙而无处不在的本土文化仍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这不仅来自“减轻文化冲突而造成的传统文化自尊心受到创伤的感情需要”[29],同时也来自如列文森所说的“文化同一性”[30]。这一矛盾的心态发展为极端的形式就必然产生了“中西之争”。由于历史精神的巨大趋动力,“西学”派呼啸而下,声势夺人,而“儒雅”的“中学”派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并不断地受到讨伐批评,被斥为一种顽固的“保守”势力。后来的研究者曾指出:“通常人们在评价历史现象时,容易性急地突出主流,贬抑支流,批判所谓逆流,然后评定主流、支流、逆流对文学发展的促进或反动作用。但如果承认文学的历史发展是由各种不同导向的力所构成的合力所支配,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某些通常被看作‘支流’或‘逆流’的批评,也可能在针对‘主流’的纠偏中客观上起到某种制衡作用,批评史发展的‘合力’中不应当简单否定或斥贬这一部分制衡的‘力’”[31]。这显然是出于对“主流”霸权性的某种警觉,是对权威话语的一种自觉抑制。
无论是认同“他者”也好,固守本位文化也好,作为一种回应挑战的策略性的文化选择,他们都必然要体现出各自的洞见与不见。“西学”派在态度上由于彻底断裂了与传统的关系,一时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共识的思想武器,浮躁的寻觅又促成了一种见异思迁的文化心态。这一心态从本质上说又都没有能够超出进化论的范畴,因此不断重临起点却永无归宿。百年来,西学派的趋势新心态使他们既不属于本土文化,又流浪于西方文化之外,无论是谁都很难在某一思想上生根并长成大树。梁启超有名的“今日之我不惜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性格,也是百年来激进的知识界的写照。
认同“他者”原本的意愿是赶上西方,重新获得主体性的确立。然而在趋新心态的驱使下,在洞见了西方“先进”与奇异的同时却掩盖了由于行为模式而造成的不见。这一不见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后果,它不仅走上了最初意愿的反面,而且造成了极不健全的文化品格,这在“文革后文学”发展中的那种单一取向中已明显地暴露出来。
向“他者”认同在历时性上就有一种步入后尘的“滞后”性。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严复1895年在《原强》中介绍了进化论,比进化论的故乡晚了近四十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便进入了“后现代主义”话语,而我们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现这一话语形式,晚了又近四十年。向“他者”认同本来源于一种不平等的焦虑,但结果却是永远无法获得与“他者”共存的时空,这有如主仆无法并行的处境,平等早已经丧失了。后来郑伯奇在回顾白话文学运动到五卅事件这十年的历史时说:“回顾这短短十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遍”[32]。类似的说法来评价“文革后文学”也常常不绝于耳。从表面上看这概括似乎很具说服力,并对嘈杂纷乱的新文化已经具有了一种反省乃至批判的姿态。但只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一描述的浮泛便昭然若揭。“对于西方历史来说,任何一种新兴的思想、学说,无论它如何以叛逆的、反抗的姿态出现,你都能从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思维逻辑的衍展中发现它与产生它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33]。论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例,认为它的科学基础、社会生活基础和思维泉源都清晰可辨。它对古典哲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否定是在一种历史逻辑的发展中进行的[34]。但在进化之光烛照下的向“他者”认同的思想过程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历史的逻辑联系。所有“新的”东西只能引起接受者短暂的震惊而不可能怀有持久的关注,以1985年的“新方法论”为例,它的骤然兴起与迅速平息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正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作家心态含有“自我颠覆”危机的根本原因。
文革后,“铁屋”再度开裂,各种思潮再次拥入国门,这自然有利于激活我们“一体化”的僵硬话语,但庞杂的“理论大市场”也确实形成了一种“理论过剩”的现象。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普遍意义”只有同具体的历史处境相关才会产生,但文革后的文学界犹如饥饿的人群,一种饥不择食的急切感使人们丧失了谨慎和应有的理智。过分的吞食刺激导致了精神混乱、情感隔膜和消极被动。在各种“新潮”理论的袭击下,文学界的精神已显得支离破碎,主动反映和参与的能力正逐渐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变成了发达国家的理论用户和消费者,并对其产品不断地以抒情的方式进行着赞誉性的说明。青年批评家南帆后来指出:“不久之后人们即已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无法证明作家具有相应的创造能力。其实,作家喉咙所诉说的时常是他人的话语。某种程度上,文学的现状并不是源于创造,而是源于引进”[35]。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作家的心态:没有限度的向“他者”认同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作家正在希图通过文化交流找到一个令人称心的文化矿井;这个文化矿井仿佛珍藏了种种强国之道或者富民之策,作家梦想依靠这个文化矿井迅速赢得一个强盛的文明。不管他们在口头上是否坦白地表露过这种动机,这种动机实际上已明白无误地体现于他们的寻找行为之中”[36]。应该承认,向“他者”的认同付出了文化的代价;一方面第一世界作为文化霸权实现了“文化倾销”,全球文化存在着走向“一体化”的危险,这一“一体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一方面这一“认同”或“倾销”的“两厢情愿”已经蕴含了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这一问题早在十几年前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1980年,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在编写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交流中的“单向流通”现象。如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入侵压抑了民族工业生长一样,第一世界文化的大量倾销,亦使第三世界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受到了压抑,同时亦有可能使第三世界的作家、艺术家极力模仿外来文化产品而失掉了本土艺术的特点[37]。这种“单向流通”的现象在文学领域里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萨特、福克纳、贝娄、斯坦贝克、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弗洛伊德、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大师的名字,文学界努力去接近这些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并常常以引述他们而自豪。然而遗憾的是,“所谓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法国不超过一百个人圈子里的影响,出了这一百个人没有人知道中国文学”[38]。在美国了不起是“两百人”[39],而“日本文学界和青年中普遍流行一句话:中国无文学”[40]。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他者”的视野,甚至以无知和偏见作为无视的理由。这一严酷的事实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使我们有必要认真反省百年来向“他者”认同所付出的文化代价。被“洞见”所掩盖了的这部分“不见”,一经揭示竟会产生一种震憾人心的刺激性。
然而,即便是如此揭示了“外慕”心态所带来的文化代价,但是,回顾“文革后文学”的发展历程,当我们面对“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这些问题时,仍然无法超越价值判断的立场,仍然无法超越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几年的“文革后文学”发展的史实业已证明,既有变幻不定的“新潮”有如旋转木马,荒诞、魔幻,黑色幽默、反英雄反情节反文化反小说不一而足;又有掉头转回传统,古玩花鸟、琴棋书画,烟酒茶食甚至不惜以东方奇观作为新的能指。我们拥有传统,这一点不同于美国,“她从未经历过任何其它的社会制度,她的历史自始至终从未越出中产阶级的精神范畴。由于缺乏资本主义前的传统,作家难以设想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41]。我们既有传统又有来自另一世界的新的体验,我们拥有了可资选择的随意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又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卸给作家承担。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环境使作家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戒备。一般来说,政治环境宽松时,作家基本持“外向”的心态,政治环境紧张时,作家基本持“保守”的心态。面对本土文化,作家既心存紧张又常常怀有情感眷恋,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始终缠绕在作家的心头。即便是在具体的写作方式上,以激进姿态出现的“文革后文学”,仍可以俯拾皆是地寻找到传统文学根深蒂厚的深刻影响,更不要说体现在文学本支中的那些清晰可辨的观念了。“伤痕文学”中的道德化倾向,“反思文学”中的忧患情怀,“改革文学”中的清官意识、“大墙文学”中的落难才子遇佳人的模式,甚至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叙事人那中正平和的人格气质等,都不难在传统文学中寻找到它们的母体,更不要说“闲适小品”、“新历史小说”等向“历史”的直接索取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传统实在是无法摆脱的,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抗争、决裂,或以外来文化取代它,事实上都只能表明一种情感愿望。百年来,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大都源于我们自己对传统的自塑。传统或者是面目狰狞的恐怖的魔鬼,或者是失意出世的避难所。因此,要么一下子打倒,要么固守不放。缺乏的恰恰是对传统理智的清理和分析。如果抹去其“权威”和霸权的面目,它仍然有令人留连的诸多成分。然而对传统不论反了这么多年还是固守了这么多年,“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主流思潮衰落了,作为实用儒学即政治的儒学却依然存在”[42]。“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走着,具体的表现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43]。“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44]。
但是,无论从文化理论上如何阐释向“他者”认同和背弃传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别求新声于异邦”毕竟已经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一个史实。仅以文学理论上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诸多概念如气、理、趣、道、风骨、意境、神思等几乎已经绝迹,除了专门性的著作外,在具体的文学评论实践中几乎已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代之而起的则是如写实、表现、再现、形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西方现代批评术语。面对无可更改的文学发展史实,对于中西文化碰撞的评价大概还远未结束。
收稿日期:1995-07-05
Radical Ideal and the Dream of the Century
——the 20th Century's Cultrual Background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Meng Fanhua *
*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Academy of SocialSciences of China,Beijing,100054
Abstract As an ideological concept,the connotation of the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or called the New Period) isrelative to history.As a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NewPeriod,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is closely related with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s far asits cultural aspect is concerned,although the literature hasdemonstrated its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a great extent,Public discourse is its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Thedissemination and dispersion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hisobviously inheri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era. Thementality of the China-centered theory of using the knowledgeof the west without violat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neseknowledge(" Ti Yong Lun") is very practical. Its functionalobjective is embedded under the superficial recognition of "the Other".Therefore the attempt of solving the political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China at the cultural level is farfrom enough.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surpassed the limitof the practicality of literature.The radical ideal has nottotally realized the dream of the century.Keywords cultural tradition anti-tradition new tradition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讲.沈阳:春风文艺出 版社, 1981.136
[2]
对十年文学有代表性的肯定意见如李泽厚:“这十年是自‘五四’以来新文学最光辉的十年,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也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见《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此外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也对“文革后文学”作了相当高的系统评价。刘再复说:十年文学“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见《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载《文汇报》1986年9 月8日)。何西来说:“人道主义的勃兴、人的重新发现,是主体意识 觉醒的标志,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见《文学中历史的主体意识》,载《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3日)。此外,王蒙(见《小说家言》,载《文学的诱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鲍昌(见《如何评价十年来的新时期文学》,载《文艺报》1986年11月8 日)等均持全面肯定的看法。
全面否定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晓波,他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一文中彻底否定了“文革后文学”。他说:十年文学“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载《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以上意见截然相左,但都可以从中看到它们与百年来文学关注的焦点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3] [4] 李以建.文化选择与选择文化,见:文学评论.1989,(4)
[5]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51
[6]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234
[7]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41
[8][9][10][11] 龚书铎,方攸翰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00~203
[12]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252
[13] 梁启超诗文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114
[14] 人们常常提到的“文以载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等传统,实际上是指“文章”而言,并不是指文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古代文学家还不可能对文学抱有更多的期待,因此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把文学当作拯世救民的传统。只有到了近代,自梁启超始,才逐渐形成了“文学载道”的新传统。毛泽东后来把文艺或文学视为“战线”、“军队”,夸大文学的作用但仍不是始作俑者。他同样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15][16]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0
[1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创作的经验. 上海:上海书店,1935.1
[1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92
[19]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森.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缓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40
[20] 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161
[21] 周作人.谈虎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长沙:岳麓书社,1989.22
[22] 周作人.死亡默想.见:雨天的书.长沙:岳麓书社,1987.17
[23] 刘福勤.心忧书·多余的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09
[24] 反思百年来“反传统”的海外学者的意见,可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金耀基的《从“五四批判”到“批判五四”》、张灏的《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余英时的《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等,以上文章均载《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5] 谢选骏.反传统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见:五四与现代中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1~32
[26] 李书磊.温和的意义.载:光明日报,1988—06—14
[27][28] 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载:文学评论.1994(2)
[29][30]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13,12
[31]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自序.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3.3
[3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第·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3][34] 汪晖.预言与危机.载:文学评论.1989(3)
[35][36] 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1,3
[37]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1
[38][39][40] 李欧凡、李陀、高行健、阿城、文学·海外与中国,载:文学自由谈.1986.(6)
[41] 理查德·H·佩尔斯.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3
[42][43]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5,32~33
[44]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公司,1984.8
标签:文学论文; 新时期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他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