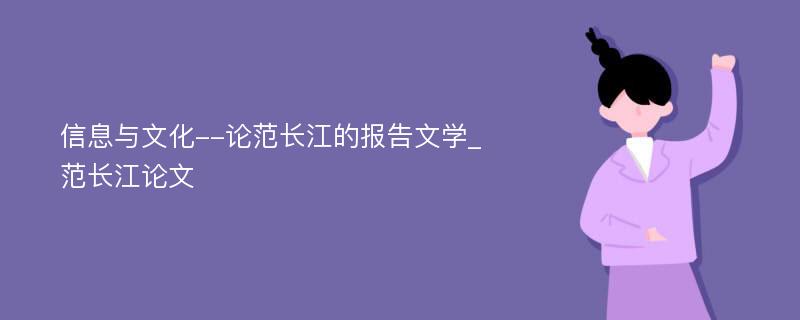
信息与文化:范长江报告文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文化论文,信息论文,范长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信息优势:历史价值的主体
对报告文学文体特质的定位,曾经是众说纷纭的。有所谓报告加文学者、报告之有文学者、报告性文学等等。我以为报告文学的文体使命应是对有价值的信息的有效报告。报告文学所报告的信息当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信息,这种信息反映的应是实然的存在物,且是有报道意义的。此为“有价值”。而“有效”,就是要运用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综合表达手段,使作品负载的信息能够畅达地得到受众的接受。这是研究报告文学必须把握的理论前提。
范长江的报告文学,包括《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线风云》(合著),通常属于游记式作品,但这种游记关注的主要不是风物山川,而是社会世象、人物动态。风景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信息发生的背景,游踪是串联事物人情的线索。长江的作品是作者有关30年代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西北地区社会信息的文学报告。
范长江是有强烈的信息意识的。在写作《中国的西北角》之前,他是天津《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这种准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使他比常人更具有新闻的敏感。他年少却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就使他能了解更多的社会大势,具有相对丰裕的信息存量,也刺激他获取更多的信息。所以,长江能抓住时机,从1935年7月到1937年9月,奔赴相对闭塞的信息源地川、陕、甘、青、内蒙等处进行实地考察采访,通过媒体向公众报告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在写作过程中,也处处表现出长江对信息的重视。报告文学具有新闻属性,它的写作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信息意识在其间显得特别重要。信息的意识,换言之亦是传播的意识。作为信息的传播,长江优先考虑的是接受者对信息的需求与期盼。读者,在长江的写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许多重要篇章的小序中,不止一次地表明其写作是为了有益于读者,是为了“以飨留心国事之读者”。读者意识的强化,增强了作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作者能风餐露宿,不避艰危,将信息及时传播给大众。他表示:“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机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我们要在危机未爆发以前,把这些地带的情形弄个明白。”〔1〕这里长江所说的“情况”和“情形”即是信息。 作者将在危急之中传播信息作为自己的“义务”,这充分表明他有一种自觉的职业意识和信息意识。也可以说他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因为报告文学内存的主体即是信息。报告文学作者,就是运用这种特殊文体传播有社会意味信息的信使。
通览长江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传播信息时,注重信息求大、求新和求正,并且作者自己也作为一个“信息源”,直接表达他对客体信息的评述。作者的这种追求,造就了其作品信息传播的优势。
信息求大,意谓作者重视重大信息的报告。一般来说,受众对于重大信息的关注度更高。从报告文学本体看,它通常更多地负载典型的重要的实体信息,这与小说等追求信息生活化的倾向有所不同。报告文学通过对重大的社会信息的报道,使受众对报告对象的大势能了然于心。长江在采访写作时,求大心理是比较强烈的。他在《塞上行·自序》中指出:“在这一小册子里面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也是长江当时全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基本主题。作者考察采访的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万象作了详尽的报告,并且引导读者从中华民族命运和抗日战争成败的大局观察民族问题。
长江注重报告重大的社会信息,就是要引导受众思考国家的大势,从而关心参与改造赖以生存的社会。他在《塞上行·西北近影》中指出:“记者这回的奔波,是有心研究西北大局的内容……路旁的民众,他们感不到这样的政治内幕,他们只感到粮价、差徭和省钞价格的涨落。他们直接生活以外的事情,他们实在无从知道。”作者希望通过社会重大信息的传播,帮助更多的如“路旁的民众”那样只关心自己直接生活的人们开拓视野,关注思考国是大计。
时新,是影响信息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长江作为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他对信息的求新自有一种职业的本能。
信息求新,在长江身上体现为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在长江之前,还很少有记者深入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采访。那里的信息,由于记者的“缺席”而沉睡着。范长江爬山涉水,横戈壁,入险区,九死一生,敬业可贵。他是第一个系统报道川、甘、陕、青、内蒙的报告文学家。信息求新,也反映了长江具有报告文学家应有的独立品格。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更不允许公开报道其劲敌红军的踪迹。长江不畏专制,客观地展示社会阴霾的现实,这充分表明长江具有一身正气和勇气。这也是他的作品能报道于人先,具有“独家新闻”之优的人格保证。
信息求新,在长江作品中最具价值与意义的是关于红军长征和肤施(今延安)的报告。现有资料表明,在国内报刊上最早报道长征的当是长江。长江于1935年7月14日自成都出发北上, 他将沿途观察采访到的有关红军的情况写进了作品。这些情况散见于《成兰纪行》篇中的《成都江油间》、《“苏先生”和“古江曲”》和《陕甘形势》篇中的《刘志丹与民心之向背》等五六篇作品中。作者自己标明的写作时间,《成兰纪行》为“一九三五年九一八纪念日”,此时红军长征尚未结束。而《刘志丹与民心之向背》的写作时间是1935年11月9日。 长江对长征的报道,由于为时势所拘,未能尽情铺开,用词设语也较谨慎。但作者能随游踪所及,要言不烦地叙写出红军的宣传优势,军事的勇猛和民心对苏维埃的向往,客观报道中流露出鲜明的褒扬倾向。范长江还是第一个公开报道延安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2〕当时作为《大公报》的记者,长江写于1937年4月21日的《陕北之行》是报告文学家对这一神秘之地的首次报告。它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至少早半年,也开了以延安为叙写对象的报告文学写作的先河。《陕北之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伯承等十数名红军高级领导人作了素描速写。
信息求正,也是长江对信息报告的重要追求。信息有真有假,有表有里,有时它会呈现迷雾状。信息报道主体的职责在于客观公正地反映客体,尤其是在信息纷扰、迷乱真相时,能深入信息源地,察其真,辨其伪,传其本,以正视听。信息求正,实际上也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本职之所在。在这方面,长江是十分出色的。
信息求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长江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作者通过采访中共高层领导人,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真诚意愿:“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3 〕长江以亲历见闻廓请舆论,这有利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报告文学在报告客体时,同时也在直接报告着主体。这是由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所决定的。报告文学政论性的特质规定其主体不能像小说叙述者那样隐含在故事的背面,而要站到作品报告的对象中间,并且直接品评报告的对象。范长江作为报告文学的信息主体,他不仅“处于传播过程的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具有主动控制的作用”〔4〕,主要传播着客体重大的时新的公正的信息, 而且主体本身也情不自禁地成为一个“信息源”,发布着自我对客体评价的消息。这种评价往往凝结着主体思想的结晶,或评点事物,或阐发事理,对受众思想有一种敲击、启悟和引导之作用。针对不少民众忧虑中日战争未来的胜败,长江议论道:“我们战争是生路,不战是死路,而日本士兵方面战争是死路,不战是生路,这个根本战争心理,已决定我们彼此的将来了。”〔5〕这种议论,文字寻常, 但比照之中寓有深刻的“战争哲学”:胜利终究是属于正义的人们。
主体自我的信息传达,在语言上是比较节制的,它只是一种“插笔”,它的“插入”常见于可议当议或不可不议的语境之中。长江在《再渡阴山》中叙写了蒙古草原的旅程,写到了在艰难的途中“头车司机”的重要。忽而笔锋陡转,生出一议:“不好的道路,如果有好的司机,也可以渡过许多难关,所以一个国家杰出的领袖,至为重要。”长江这一议论是有所指的,它反映了作者的善思与勇气,是一种有力度的杂文式的政论。主体信息主要作为一种对客体信息的评价插入于叙述之中,它往往能强化受众对客体信息的关注与理解。
由于长江注重信息求大求新求正,并且重视主体的直接参与,所以他的报告文学“虽是新闻报告性质,实际就是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历史”〔6〕,具有很高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文献意义。
二、文化景观:别具一格的文本
如果说信息构成了长江报告文学的主体,造就了其作品的历史价值,那么,文化则展现了长江报告文学信息源地的背景,显示其作品特有的景观。文化景观的创设及其运用,是范长江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
报告文学似乎从来就是“文学的一种战斗的体裁”,作者往往从新闻的政治的视角观照并迅速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诚然,对现实的观照与快捷的传报,是报告文学文体的主要功能,但这并不是其功能的全部。政治、新闻的视角,是报告文学主体观照客体的主要视角,但并不是唯一视角。早期国际报告文学家也注意从文化的视角报道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内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政治性十分突出,文化色彩相对比较淡化。作品普遍地表现出一种浓郁的文化色彩,似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为最。
长江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这与作品表现的对象颇有关联。长江考察采访的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古老华夏的发祥地。这里地处内陆,与外界沟通甚少,积淀着更深厚的中国文化资源。在这种神秘的地带,聚居着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风情习俗,以及相袭久远的宗教传统,也构成此间特有的文化景观。同时,长江作品的文化氛围,也与作者对中国西部文化的熟稔有着联系。长江为四川内江人,对内地的习俗风情耳熟能详,喜诵诗读史,对与西南西北有关的历史与文学知之甚多。再者,长江作品的体式也影响了文化色彩的形成。游记体报告文学与纯然报道现实社会信息的新闻体报告文学不同的是,它在传播以现实信息为主的同时,常常交代现实主体信息发生的人文背景。这样,文化的因子便成为这类游记体报告文学的伴生物了。
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人化的对象与结果均可纳入其间,“凡是由人类调适于环境而产生的事物,就叫文化”〔7〕。 长江作品所展示的并不是大文化的全景,而主要是属于精神文化的人文历史与风情、宗教仪式和民族性格等,侧重于泰勒所谓的“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在内的复合体”〔8 〕的那种文化。
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合成。长江作品的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将现实时态与历史时态交织起来,在对现实的叙写中“闪回”过往的“故事”,从而给读者以一种历史感。作者在《初出阴山》中写到的蜈蚣坝道路“状颇危殆”,“司机多停车入庙施舍焚香叩头,以求消减穿行大戈壁之苦难。另有小和尚在道旁化缘,谓系培修阴山大道之用”。这是写现实所见的宗教仪式。作者由道旁小和尚化缘修道的善举插入“僧人从戎报国,力战外族”历史故事的述说。作品中举出宋、明“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人事三例。这些故事的主人抵御外敌,慷慨赴死,事迹可歌可泣。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焊接起来,以史喻今,用历史的意蕴强化作品的主旨。作者把僧人故事视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价值取向与道德观的载体,旨在激扬在外敌入侵之时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这样光荣的记录,我热诚的盼望,多多的出现于第二十六年以后的民国史上!”
读长江的作品,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对古典诗歌情有独钟。自然,本来是人外的存在,由于诗的“介入”,它就具有了文化的意味。《兰州永登间》是一篇千字文,但作者采诗却有五首之多。古代诗歌的有机导入,使作者描写的对象增添了一种“诗情”和“史意”。读者诵读其诗,亦可随诗之所写作一番跨时空的历史之旅。作者采诗入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地叙写对象,使诗各有其用。先引杜诗《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和柳中庸的《凉州曲》:“……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分别从古来征战之残酷和环境之险恶,写出了青海的“凄凉”。中取李涣《甘泉道中即事》一诗,则描述古代西北的自然和人文风情:“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雪)。海错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先民的生命状态于此昭然可见。末处拈出左宗棠豪放诗:“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遍栽杨柳三千里,未因春风度玉关。”此诗为由古及今的过渡。由左宗棠的“路政”联想眼前满是土沟土窟的所谓“公路”,作者发出“不胜其‘今不如者’之感”。引诗之意在于微讽现实之陋。
故事与古诗都为历史之属。长江也能从现实所见中掘出文化的内涵。他的不少作品表现出民族风情和特有的社会形态。作者展示的西北民族的居住方式也是相当独特的:“地下窑洞,多于地上房屋。往往有所谓村落也者,地面上并不见有房舍,而地下却有若干人家。”〔9 〕这样的景观,为地理文化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材料。作品中有的是对佛事、俗事和民族奇逸之事的叙写,读者披读作品,扑面而来是一种神奇而多味的文化气息。
长江作品文化景观的创设及其运用,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这种功能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强化主体、优化本体和进化文体。
长江报告文学内存的主体,即是有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展示国民党统治下的民生图景,披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事迹等现实社会的重大信息。作者对文化的观照及其反映,不仅提供了现实主体信息发生的背景,而且还是对主体信息的补充,甚至是对主体信息所表达的主题的强化。作者所叙写的文化景观,其中相当部分是直接作用于主体信息的。作者对历史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被他用作对现实的“论证”。《太原印象》可以佐证。作者在写山西现实状况中插入一段与太原有关的史实。赵匡胤想攻打北汉,而他的军师赵普却认为应该“扫清了东南各国之后,然后再攻北汉,基础已固,也不怕外族了”。这一段史料的蕴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是神通的。作者以这一史料作为依据,揭露的是“搁着外族不打,去兼并同族小国”的现实政治。他所引用的许多诗歌也有同样的意义。作者在《战后出阴山》中引唐代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莫教胡马度阴山”。作者改王诗末句为“莫教邻马‘看’阴山”。这一改,表达了长江对国民党无视日寇觊觎蒙地勾当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文化所指是含有透视现实的深意的。
长江作品对文化的导入,也优化了作品本体,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徐铸成曾指出:“为什么过去的许多新闻记者,如长江同志的通讯,看完后大家愿意保存?就是因为有可读性,读完一遍不够,还要读二遍三遍。”〔10〕长江的作品之所以使当时《大公报》和全国的读者都感兴趣,原因之一就是长江的笔下有一种文化的精采。这种精采造就了作品的可读性。长江作品的文化性,拓展作品表现的时空背景,丰富了作品的信息。社会政治信息以外的多样化的文化信息,给读者以新知;神奇的民族风情等给读者带来新鲜的刺激,由此调动起他们阅读的兴趣。此外,诗歌的引入使作品文采斐然可观,对读者也有一种吸引力。
文化的合理切入,除了能强化主体,优化本体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进化”着报告文学这种新文体。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母体是新闻。随着这种文体的发展,其杂交态势日见明显。除了母体的新闻基因外,作品还可纳入真实而非新闻的材料,兼取别门艺术的表达方式。这就使作品由单一的新闻报道模式演变为综合性的多视角报告文体。这或许就是报告文学的进化。长江的作品在内容上既主要报告了作为新闻传播要素的现实信息,同时,又运用了非新闻的“软性”材料;在形式上又随心自然,写法不拘一格,没有新闻报道中某些机械的套数。他的作品新闻报道味少,是有着浓郁的文化色彩的自成一体的报告文学。
注释:
〔1〕范长江:《塞上行·忆西蒙》。
〔2〕〔3〕范长江:《塞上行·肤施人物》。
〔4〕《艺术传播学》,7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范长江:《西线风云·西线战场》。
〔6〕范长江:《塞上行·胡序》。
〔7〕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
〔8〕转引自沙莲香《文化积淀与民族性格改造》。
〔9〕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陕北甘东边境上》。
〔10〕《新闻艺术》,27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