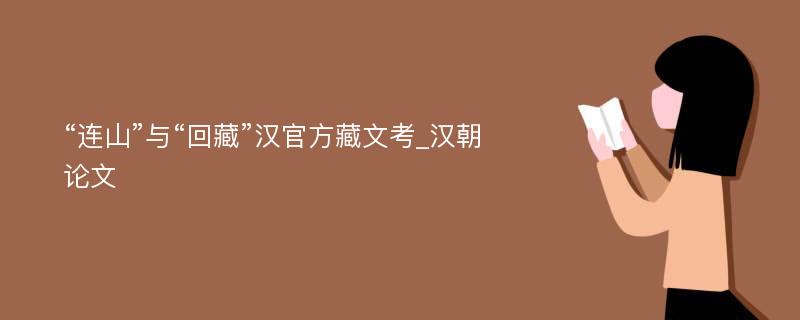
《连山》《归藏》的汉代官藏本之考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4)06-0056-11 《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云:太卜等筮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筮人》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桓谭《新论·正经第几》云:“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新论》的主要思想应该是桓谭在两汉之际长期思考的成果,而《正经》篇的写作是在东汉初期:“言体第四”、“谴非第六”有批评王莽的内容,书中数次言“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则“正经第九”是写作于东汉;《新论》应该是桓谭晚年的作品,因为它没写完,后由班固补写;桓谭卒年当在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①。故桓谭所谈《连山》《归藏》的收藏,是指东汉初期的情况。因为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没有广征图书(民间送谶纬图书是另一回事),东汉朝廷保存的《连山》《归藏》,应该是来自西汉的朝廷藏书。 《连山》《归藏》在汉代中央机构是否真实存在?历代争讼不已,其真相可谓三易研究中的一种阿基米德点,其认定结果影响着系列相关研究。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对辩式论证,兼顾立论和驳论,以给出严谨的、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一、质疑、否定汉代官藏《连山》《归藏》的历代说法 (一)唐宋明的怀疑者乃至论伪者与马国翰等人的回答 《汉志》(指《汉书·艺文志》)未录《连山》《归藏》,是怀疑乃至论伪的根本原因。 《隋志》(指《隋书·经籍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所谓“汉初已亡”,依据即《汉志》未录,视《汉志》未录为无书。从“汉初”到“晋”,汉魏没有从民间得到过《归藏》,因此,“汉初已亡”之语意味着汉魏的朝廷藏书不见是书;未论桓谭说法是否可信,不信则晋前无之,信则意味着西汉朝廷无是书,书是新莽前后神秘出现的。清马国翰《归藏》辑本载:“胡应麟曰:《七略》无《归藏》,《中经簿》始有此书。《隋志》因之,称此书‘惟载卜筮,不类圣人之旨’,盖唐世固疑其伪矣。”马国翰《连山》辑本载:“刘炎曰:或问《连山》《归藏》之真伪,曰:《汉志》不录《连山》,《唐志》则有之;《汉志》不录《归藏》,晋《中经》、隋唐《志》则有之:昔无今有,其伪可知,况其言之不经耶!”胡应麟为明人,刘炎在胡应麟之前,乃宋人。刘炎说《连山》《归藏》“言之不经”,马国翰在《归藏》辑本序言中回答:“虽‘毕日’、‘奔月’颇涉荒怪,然‘龙战于野’、‘载鬼一车’,大《易》以之取象”、“其文非汉以后人所能作也”。宋代还有所谓《归藏》“不文”的质疑,郑樵《通志略》解答:“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而弃之,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 可是,何以《汉志》未载《连山》《归藏》? 马国翰《连山》辑本序言云:“传者甚少,故《汉·艺文志》、《隋·经籍志》皆不著录。”其论没有解答力,《汉志》所载某些书籍也是传者甚少。清严可均《归藏》辑本之案语曰:“《御览》六百八引桓谭《新论》云:‘《归藏》四千三百言。’是西汉末已有此书,《汉志》本《七略》,偶失载耳。”偶然论无理,也不可信。于是,后人提出新原因:刘歆等人伪作论,桓谭乱认论。此皆伪书论。 另外,《连山》马辑本附录里,载录明代黄宗炎之质疑《连山》八万言:“夏之文字几二十倍于文王、周公之辞,岂古昔之方册乎?为此说者亦不明古今之通义矣。”黄氏质疑没得到解答。 (二)郭沫若、王宁的刘歆等人伪作论 王宁《〈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简称“王文”),先引郭沫若《周易的制作时代》之疑语:“《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连山》、《归藏》的著录,我疑是和《周礼》一样,乃刘歆所伪托的东西。”然后云:“刘歆把秦汉以前的一些资料拿来经过删编增益,做成《周礼》,虽不能说全是他伪造的,但其中肯定有他伪托虚造的成分。我认为,《连山》、《归藏》在汉以前根本没有这书,其名目正是刘歆造出来的。”②并说刘歆是据《山海经》等伪造《连山》《归藏》——后来他写了专文论之。 (三)任俊华等否定桓谭说法之诸种理由 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简称“任文”)③,做了较有广度和深度的考辨,大幅推进了历代前贤的说法,乃论伪史上难得的佳作。 任文给出的前提是:《汉志》“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继而推论:“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成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最后得出结论:“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并推定桓谭把某些未明的卜筮杂书视为了《连山》《归藏》。 任文还猜想《新论·正经》的旨意:“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 错认,于当事人而言为假,不是造伪,但于后人而言,假书非真品,也是伪书。 任文第二部分末尾提出两个辅论:一是,“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二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三易没有并行于世。 任文有较大影响。程二行先生云:“《连山》《归藏》……二书就包含在《汉志·数术略》‘蓍龟家’所录‘《周易》三十八卷’之中……汉人所见《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④此说当衍生于任文的臆测语即“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史善刚先生也受任文的影响,任文是其论说的参考文献之一,他关于桓谭说法的可信性问题只有一个臆测性否定句:“桓谭说法有依据吗?恐怕虚构的成分居多。”⑤虚构史实乃造伪。史氏此语所在部分的小标题乃“东汉三家(郑玄、王充、桓谭)对《归藏》之谎说”,概括了其相关论说,把问题指向三家的人品了,可见论伪的演化地步。 应该说,否定方式无论是简句还是论述、无论是臆测还是推理或据实,都有助于学术辩论的深入,如能引起回辩,就能推进学术的严谨化。否定方占据着理由(以致很多网络文章采用其说从而广泛影响普通读者乃至一些学者),另方并未有力地辩论过,因此,否定《连山》《归藏》的真本在汉代中央机构的存在,可谓多年来三易论说界的主流观念。于是,有些易学者变得迷糊,莫知真假。对《连山》、《归藏》的看法,不能再坚持传统的朴素说法了,那些说法有的是随意猜测,如东汉初期学者杜子春所谓“连山宓牺,归藏黄帝”(他是谈占法),就是天花乱坠的臆测。这是高度讲究论证力的时代,需要论证。从学术论证看,肯定方不能漠视否定方的广义证伪工作。 二、《汉志》未录《连山》《归藏》的真实原因 《七略》、《汉志》未载《连山》、《归藏》,是历代质疑、论伪之根本依据。未录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笔者广泛考察,终于发现:对《汉志》的认识,长期来古文献学界存在多个严重的迷误(笔者因此写了数万字作品考辨历代书目体制);其实,《汉志》不反映西汉藏书范围,只反映西汉校书范围,因为定本者不校,故《汉志》不载《连山》《归藏》等大量书籍,是以《汉志》未录这种现象实无质疑、证伪之用,未录现象实非“硬伤”。 (一)西汉朝廷的很多书籍,《汉志》未录 任文所谓“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人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是其论证之首要前提,是采用民国著名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古书通例》提出的《汉志》不录现象三因论⑥——其论流行于当代《汉志》学界、目录学界。 其实,余氏说法有误。刘歆编《七略》之前,国家所存的大量书籍不入校理,远远不限于“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余氏着意法规,是因为他当时参考和辨析了宋代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的四库全书提要,王补有《汉志》未载的27种西汉文献,《古书通例》云,其中属《汉书》所引者有《元王诗》、《汉律》、《汉令》、《五纪论》。 余嘉锡不了解,清代有的学者也谈论了一批未录书: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补充了34种所谓档案类文献,如叔孙通汉仪12篇、叔孙通礼器制度、京房考功课吏法;⑦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指出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所用)、刘向所编《楚辞》等不入《汉志》。⑧ 当代一些学者对余氏说法打补丁,或论档案特殊、非图书,或论谶书属禁书、寓禁于校,或论班固有个人爱好。补丁真能解决一批问题吗? 《史记·天官书》所采的《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唐《开元占经》也采,今为合本,中学历史教材也介绍。《汉志》何故缺录它?司马迁做《史记》的大量原始资料,很多会保留而缺录。 笔者新发现一些《汉志》未录书籍。例如,道家类载录了一批研究《老子》的书,却缺《老子》;刘向编辑的《新序》、《新苑》(后人称《说苑》),是采纂一批残书的内容而来,如《说苑·敬慎》大段介绍老聃之师常枞的贵柔思想,应是短篇《常枞子》之残文,类似残书不少而《汉志》缺录。 可见,《汉志》缺录很多西汉长期存在的书籍(整书及残书),且类型多样,难以估算。 这种现象,有没有根本原因?究竟何因? (二)《汉志》的蓝本是《七略》,反映西汉校书成果:新刻的校定本 1.《汉志》几乎全部是《七略》的“提目”本 由《汉志》序言可知:汉成帝诏令刘向等校书,书成后刘向奏录工作概况;汉哀帝使刘向之子刘歆完成父业,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且刘歆对《七略》曾“删其要,以备篇籍”。删即删繁为简,班固《汉志》(一卷)几乎全部是刘歆《七略》(七卷)的“提目”(指目录摘记)本。《汉志》对《七略》有归类调整和个别增补,在各类小结和全篇总结中一一说明,最后总结云:新“入”了三家的五十篇。值得了解的是,由于工作量浩繁、人手紧张等条件制约,班固兄妹所做的《汉书》,一些记载难达完备。 2.《七略》反映西汉校书成果:新刻的校定本 《七略》的姐妹品为《七略别录》(简称《别录》,二十二卷,唐代还有其书),收集校书工程前后主持人刘向、刘歆的各校书报告,因此,《七略》是西汉校书工程各报告之提要。现存多个完整的校书报告,如《晏子叙录》、《管子叙录》等,反映校书的过程是:校定后,杀青而缮写。缮写本保存在哪?《隋志》载:“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揔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这是转述记载。可见,《七略》的直接来源是温室群书(各书附有书奏)。只有这个来源,那么,这些书只能是缮写本。因此,《汉志》的书目单是校书各报告之“提目”,反映新刻的校定本的情况。而西汉校书工程的实际范围决定《汉志》的录与未录。 3.《汉志》新增三家五十篇,只能是反映《七略》的部分漏记 《汉志》只补三家,不奇怪么?《汉志》新入扬雄《太玄》(十九篇),是班固的个人爱好么?爱好论悖于《汉书》它“志”对一些缺录书的采用或说明。据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考证,《七略别录》收有刘歆的《太玄书录》⑨,那么,只补三家,内有决定性原因,只能是反映如此事实:三家乃《七略》应有而未有者。此不详论。可见,《汉志》只反映西汉校书范围,未超出之。 (三)《隋志》误解了《汉志》的本质 《隋志》的说法成为后人引用的“当然”来源。遗憾的是,问题首先就出在它身上。 《隋志》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是因为它同等看待《汉志》与晋《中经》。其实,它们的录书范围本质上不同:《七略》、《汉志》的对象是所校书籍,可是,晋《中经》、《隋志》的对象是存书(《隋志》的蓝本是《隋大业正御书目》),无论是否被校理,直接依据不是各书奏——因为没有西汉那种各书报告,故西晋、隋代的录书工作无像刘向父子那样的书奏传世,也无提及。《隋志》的误解被历代的一些学者承继。例如,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皆因《汉志》未录而视《鬼谷子》晚出,又如,《法经》被视为晚出。这些误解影响了梁启超等一批现代著名学者的认识;难怪,任文等以为刘歆了解的必载录。 (四)西汉不校有定本的书籍,汉律、汉礼、档案皆有本朝官定本 校书以产生定本,前提是无定本。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即为了解决一些书的文本残缺的状况,方广罗异本以比较,以产生校定本。 那么,有定本的书籍不在校理范围之内。例如,西汉的一批法规、礼仪之书,无论全国有多少写本及一批异本,它们有本朝官方定本,定本在主管机构,这些书则不入校理。礼仪之书本质上不是档案文献。 (五)西汉不校自然的定本,证例:《古文易经》 单本的书(包括弧本和史上独本),无论是否残缺,于目前阶段乃自然的定本,不入校理。存真是校书工程的目的,校或不校皆存真之方式,于单本类书籍,不校是最好的存真。后世学者可以注释形式去校勘孤本,那是研究,限定于信息形态,并不消灭原本的质物性存在。可是,西汉校书不同,是校定而新刻,使之成为范本,意味着那些原本可以且应该被取代。 单本书应该不少。例如,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出示的谶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汉书·王莽传》云藏在兰台(《汉志》未录),这两部内容上应该相关的谶书,谈汉帝再受命,即汉朝的灭亡和再生,是高等秘书,禁止一般人了解,只能是单本;刘向作《洪范五行传》,批此谶书,是史上独本;《常枞子》应该是孤本。 单本不校的重要证例:《古文易经》。 《汉志·六艺略》第一部分“易”,介绍:“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之经与古文同。” 《汉志》书目,无论《六艺略》的易类还是《数术略》的蓍龟类,都未录该书。 比较:(尚)书类书目冠首的是《古文经》(即《古文尚书》)四十六卷,春秋类冠以“古经”十二篇,论语类冠以“古二十”(即《古论语》)一篇,孝经类冠以“古孔子”一篇。 《汉志》何故不载《古文易经》?用之校其余易书的相关内容,它是底本、孤本、自然的定本,自身不被校勘。 (六)《连山》、《归藏》是孤本,西汉不校,故《七略》《汉志》未录 桓谭说法显示,汉代朝廷的《连山》《归藏》,只有一种藏本(导致太卜府没有《连山》这种怪事),是自然定本,无论西汉时期它们藏于何处官家,都不属校理对象,不入《七略》和《汉志》。 三、任文关于《汉志》未录《连山》《归藏》的其它误解 (一)误解了“《易》”名 任文把西汉人称《周易》为《易》当作西汉人不知它易的证据,实乃误解。 第一,语词多义性是语言学简单事实,具体词义由具体语境限定,一般不会混淆。例如,《汉书》里(如刘歆传所录“移书让太常博士”),“书”字是多义用法,有时指《尚书》,有时指抽象书籍,有时指文书(如官名“尚书”),有时指书写。 第二,孔子所谓“易”,不限于《周易》系统(指《周易》及其同质品)。《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比较五经特色之言:“《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四时五行是象数学,令人联想到西汉京房的纳甲易学。现行《周易》的经部没有使用四时五行,孔子所见之《易》何以用四时五行?孔子所见一些谈《易》的文章,未必固定于《周易》,只是笼统谈《易》;除了太卜所掌三《易》原典外,还有它《易》。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之《筮法》篇反映的就是一种它《易》,有扬雄所用甲子数及特殊型纳甲,八卦图也特殊。 应该了解,孔子笼统曰《易》,慢慢成了传统,儒林习言,也扩展至道家。《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庄子·天运》篇有所谓孔子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对儒家六经也是如此称呼。可见,六经的简称在战国时期已流行,源头当在孔子。 第三,孔子从卜筮易发挥出义理易,武帝独尊儒术时期《易经》博士推行义理版《周易》,是易典的发展也是一种阉割,导致西汉一般儒士眼里《易》即《周易》。 第四,西汉人称《周易》为《易》,是简称、亲尊称呼。在具体语境,对亲近的和尊重的对象使用全称有隔膜感,习惯是省略前定词即使用抽象概念式省称,如儒林外者说“孔子曰”而儒林内者言“子曰”。 第五,易典的阉割,加上可简称《周易》为《易》,使得《周易》的简称日渐固化。儒林用语容易导致他人承用、习用。 (二)误解了《周礼》在西汉、新莽的存在 “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 这种有一定流行性的说法,主要用于质疑《周礼》,臆测刘歆在更改书名期间有过篡改。书名的主体词变化,容易令人猜想内容有变。其实没有如此更名。 王莽时期,刘歆恢复在汉成帝时期的增立经书活动(西汉宣帝、元帝时都有增设活动),奏议增加《左传》等多部书于学官、设博士,包括立《周官》为礼经之一。在王莽推行复古改制、崇周公之制的时代,刘歆扩大学官所治不能不包括《周官》(他在成帝时期的增立书单不含《周官》)。 杜子春(刘歆的学生)等东汉前期学者称《周官》,东汉中期后期的马融、郑玄师徒用新名《周官礼》,礼字为类称,正如《左氏传》立为春秋经之一,人或称《左氏春秋》,无涉内容变化。郑玄为大儒,他所注《周官礼》在后世影响大,导致后来流行《周官礼》之名。初唐贾公彦改进郑玄之注,用省称,作《周礼义疏》,遂传《周礼》之名。 “直到王莽当政,《周官》内容才被公开……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 《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则“中秘府”原存其书,而且,《周官》有“传”四篇,说明西汉时期有过一些研究者、有过某种公开性——研究者应该是河间献王府的群士,《周官》在他们那里有公开性;景帝时及其以后一个时期,献王府是中国古籍收集、抄存、研究之中心,还设过博士。另外,《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是间接引用(概括了《周官》对应部分的内容),则司马迁读过该书,还说过武帝封禅前,群儒查阅《周官》。 东汉马融云“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该如何认识? 所谓五家之儒,指传习《易》《书》《诗》《礼》《春秋》的朝廷五经博士;博士属于士,由郎官担任(例如,孟喜先为郎,后为易经博士之一;京房只是个郎官,其三个弟子为郎、博士),低于大夫,一般情况下应该难以查阅皇宫秘书。所谓“莫得见”,只能是马融在他们的书里没看到相关信息,不能证明五经博士都没见过,不能说武帝封禅前查阅《周官》的群儒一定没有他们的人。另外,五经博士只是当时朝廷文人群体的小部分,不等于其他文人。 四、刘歆等人不可能伪造《连山》《归藏》及三易说法 王文的伪造论,乃无据猜测,自身没有论证力,却影响着所谈对象的可信度,此小辩之。 (一)刘歆等人不可能伪造《连山》《归藏》 刘歆等人不可能伪造《连山》、《归藏》,理由如下: 第一,没有相关的伪造才能。那些有过长期易学实践经验的学者会明白这个道理:易术经典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是谁想造就能造的,乱造只出文化垃圾。《汉书》里不见刘歆有易术实践和特殊的超级的易术才能。 第二,没有伪造的动力。桓谭其实是谈论《连山》之基本无用,只是藏品,且太卜府不存。 第三,伪造极容易丢脑袋,若被发现,至少会丢失自己及一批相关者的政治生命。 先看汉成帝时期一桩著名的伪造尚书案。王充《论衡·正说》云:“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在当时的朝廷舆论里,伪造古书罪当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即是认可本来当诛。主持校查者,应该是刘向或刘歆。 刘歆父子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在朝廷上的广义政敌多,如果乱来,下场会很惨。刘向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一直有很强的受压迫感。元帝时期石显专权,萧望之、刘向等名儒受压,入过狱;石显被逐后,王凤代表的外戚势力进一步坐大;成帝时期,刘向等代表的名儒群体与王凤代表的旧式专权群体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汉帝再受命”话题的出现。使皇族精英之一的刘向高度焦虑地感受到王氏势力对皇族的严重威胁,他送过密奏,他的处世只能小心翼翼。刘歆、房凤、王龚希望将《左传》、《毛诗》等立于学官,丞相孔光后来反对,刘等共同写作《移书让太常博士》,得罪群臣、包括朝廷当权者师丹,刘歆担心被诛,自求外任,直到哀帝时期王莽主政了,他才回京城;这也反映刘歆平时与一批官员不和,人缘关系不佳,“移书”不过是爆发罢了。没有罪行的得罪,就担心被诛,若犯下大罪、特别是伪造古书这种死罪,刘歆岂非死路一条? 第四,也没有伪造的辅助环境,太卜府主管等不会冒砍头的风险。 新莽时期刘歆为国师,但他还是没有此类伪造的能力、动力和条件——大家对伪造古籍罪的认识没变,他若伪造,一旦被发现,至少会丢学术声誉和政治生命。 (二)刘歆不可能伪造《周礼》的三易论 清方苞《周官义》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臆测《周礼》为刘歆伪造,康氏甚至臆断《汉书》为刘歆所作。后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名家都介入了讨论,虽然大家不同意刘歆的周公作者说。但一些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后期。今人杨天宇先生论证说:“作于战国说较为允当。”⑩ 王宁先生之云刘歆伪造《周礼》的三易论,只是臆测。 三易论于刘歆无用,没有造伪的动机,而且,造伪违反校理工作的存真原则,有巨大政治风险。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明过校书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存真,这应该是大家的信念。作为校书工作的参加者和末期主持人,加之他在西汉时期的政治处境又比较恶劣,如果造伪,罪行极大,他及其家族及其工作团队,都有极高的政治风险。 校理对象存在多写本,可以比较,其他学者有比较性证据。 五、汉代官藏《连山》《归藏》之群体性铁证 《汉志》的不录没有否定意义,刘歆们不可能伪造《连山》《归藏》、及《周礼》的三易论,那么,桓谭的《连山》《归藏》谈及汉代群官的默认,就是证据群,是无法推翻的群体性铁证。 (一)桓谭说法是证据:任文对桓谭的多种猜测皆是误解 桓谭的说法是证据。相关的质疑、论伪能否成立?其实,任文对桓谭的多种猜测皆是误解。 第一,任文显示,说者没读过《新论·正经》便生臆测。 所谓“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是很离谱的臆测。说者只知篇名,未读过其文。长期来,学界对《新论》只有高度雷同的几句引语,好像该书只残传大家爱引的几句话。其实不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据清人严可均辑本出了校点本,中华书局1985年将《桓子新论》等四家短书合一出版;《新论》辑本,所辑佚文有一万七千多字,保留了一些传世文篇的大体,其“正经”篇,若不含标点符号,近九百字,应该反映了大体。 未考虑语义是否多样,由篇名推想“必”然,是违反逻辑关系的臆测。订正即修正文字文篇误漏等事实类现象,“正”只能是订正么?汉代名家谈文化典籍的“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谓“正易传”,《汉志》春秋部分所谓孔子“正礼乐”,都指思想取向。 第二,任文误解了“正经”的旨意。 “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违反事实。桓谭《新论》之“新”乃思想批评,如“谴非第六”、“启寤第七”、“祛蔽第八”、“正经第九”、“识通第十”等标题即显示思想批评;“正经”并非“订正误漏之处”那种事实类修正,而是指导思想上矫正俗儒解经时力求繁杂而失儒家大义的昏暗。 “正经”篇起语曰:“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然后比较:秦近君(秦延君之讹)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三易里,八万言的《连山》藏于兰台,四千三百言的《归藏》藏于太卜;《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意指被一些学者引用)。 主旨是赞扬要言不烦。视秦氏说经为废话连篇;《连山》八万言却藏而无用,不但普通易术界而且太卜也不用它(本属太卜),不如相对短篇者《归藏》。 桓谭这个批评承继了西汉末期一场严重的经学政治冲突:刘歆等写作《移书让太常博士》,感叹道“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他后面比较《春秋》左氏传、谷梁传、公羊传,批评公羊传“弥离其本事”,赞扬“《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承继了刘歆在该事上的长期努力,也是端正对经书的指导思想。 桓谭的正经思想,即“传”文应该要言不烦,厘正“经”、“传”关系,反对舍本逐末,如《后汉书·桓谭传》所论:“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这在经学时代很重要。 第三,“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如康有为一样,误解了经、传的相对性,误解了两种不同时代的经。《周易》经、传十二篇,经先有,传后出;《汉志》里,《易经》十二篇,是相对于汉代的易说而言,在汉代的立场看,本代的易说称为“传”:可见,上代作品被解释者称为经;时代不同,经篇不同。《周易》经篇的多样性,与三易论没有冲突,因为三易论是谈汉代之前,且领域只涉太卜。 第四,“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 以误解“正经”旨意为基础,进行了离谱的猜想。“于是”前后没有逻辑关系,“被视为杂占的书”乃猜想,“尊之为”视桓谭为乱认者。 第五,任文视桓谭乱认古籍,悖于多种事实。 桓谭是两汉之际的经学大师,少见的耿直之士(当场批评光武帝之迷信谶纬而几乎被诛、后被外放)。他了解两书的篇幅,说明是严谨对待的,校勘上花费过一些精力和耐心,而且所在的语段云:“《古论语》二十一卷,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如此细心、严谨、扎实的研究者,可谓罕见,哪是对立的极端者——高度轻浮地乱定古籍而且是不同藏书机构的古籍? 桓谭谈《连山》《归藏》,有篇幅介绍,是整书性质。汉代官藏整书(不同于残简)很多,都是有名称的,没有无名者实例。传承及收集上来的书不会无名,即便不知原名也会设个新名以称呼。八万言那种鸿篇巨制,必有名称。 桓谭智力上不会分不清整书。如果他是推定,怎么不把小篇幅者推定为《连山》,大篇幅者推定为《归藏》?桓谭谈《连山》《归藏》之名,肯定有据,这种依据不可能在他的想当然,只能在书上(书类多,若面对无名之书,他无法断定何书)。后来西晋皇甫谧、北魏郦道元知道《连山》书名,亦然。 另外,书名了解还涉及太卜、兰台两个系统的管理者之了解,事涉不同藏书机构。 第六,桓谭了解《连山》《归藏》,是在王莽时期么? 任文说桓谭在东汉时期地位低,没资格查阅太卜、兰台处的藏书,桓谭在王莽时期任掌乐大夫时才有资格查阅。其说大错。第一,桓谭一生的最高官衔是在东汉时期所得“给事中”(此“中”指禁中,在一些职务里可代指皇帝)。《后汉书》说桓谭:“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内官(皇帝的私属官员)系列里,给事中仅次于中常侍(而与外官相比则仅低于九卿),是皇帝身边很重要的顾问;给事中不是大夫,非大夫身份者也可加此官名,大夫里只有那些很重要的才加此衔,古代史书多见“某某大夫、给事中”,这种排序显示给事中的地位高于大夫或高于普通大夫,例如,易学家梁丘贺因提前发现兵谋而被提升为大中大夫、给事中,刘向晚年做了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又,司马懿、司马昭在曹魏政权所加禁中官阶皆给事中(汉魏时期中央官制没变)。第二,桓谭做议郎(专掌皇帝的顾问应对,可参预朝政)、给事中,是皇帝的专职智库,需要很广的知识面,当有广泛查阅朝廷秘籍的权利。 (二)一批默认者:《新论》的一些朝廷读者,包括续作者班固 《后汉书·桓谭传》云:“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 说明朝廷重视该书。“初”当指光武初期,因为桓谭卒年当在公元35年,此前离京外任多年。在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时期,即公元25-88年的半个多世纪里,该书肯定有过一批朝廷读者。而且,桓谭谈及《连山》《归藏》的“正经”篇,很重要,在东汉朝廷儒林应该会受重视。他前承汉成帝时期一场重要的经学政治冲突,承继了刘歆等《移书让太常博士》之感叹:“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该文批评力强烈,受到一批人反对,导致刘歆等三人离京。桓谭与刘歆、扬雄关系好,某些学术思想上是同道,彼此欣赏又经常辩论。“正经”篇在思想取向上隐然地肯定了王莽时期刘歆立《左传》等于学官的成绩。桓谭“正经”思想后启班固,《汉志》六艺总论部分有类似批评:“后世经、传既已乖离……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儒林传》末尾反感西汉时期“一经说至百万言”,当指桓谭“正经”篇作为首要责备对象的秦延君《尚书》说。“正经”篇涉及经学指导思想这个大事,乃名著之名篇,容易受正反双方关注,必然了解桓谭所谈《连山》《归藏》。 桓谭在世期间可以修改《新论》;班固续写之,肯定会阅读该书,作为总体上的合著者,他可以且应该修正事实性记载的错误,而且,他是一代巨型史官,会高度重视《新论》里史料的对错,而且,班固长期是兰台官员(后世称其为“兰台太史”),广泛了解文献,且庞然大物者《连山》容易引人注意,且他与桓谭一样很关心书籍的篇幅问题,最清楚兰台有无《连山》。 对于《新论》谈论的事实性内容,那些一般读者和续作者班固都是默认者。 东汉初期的《连山》《归藏》应该是来自西汉的朝廷藏书,来自刘邦初定关中、控制咸阳时期的秦国太卜。刘邦对旧政权官员高度礼遇,类似技术人才不会逃跑且需要新政权用之。 六、《归藏》《连山》在汉、魏、西晋、北魏的传承 (一)晋《中经》所录《归藏》,不是汲冢书《易繇阴阳卦》 王文、任文都认为晋《中经》所录《归藏》乃汲冢书《易繇阴阳卦》,王文只有无据的断言,任文则有大量论述(其旨向性重点在此),好像有据。该怎么看? 考虑到本文篇幅过长,该部分的主要论述,笔者另有组织,乃四千字的小论文“《易繇阴阳卦》非晋代《归藏》,当是它版《易经》”。此小议之。 第一,任文的一些重要猜测不能成立。如,其云《阴阳说》是《易繇阴阳卦》,混淆了一种易“传”(解释)与一种占辞体系。王隐《晋书》谈汲冢简时所云“古书有《易卦》,似《连山》、《归藏》”,推不出《易卦》是《归藏》:“似”非“是”,且其宾语有两个,不等于《归藏》,在三易论视野里表示“非《周易》”罢了,其《周易》观限定于当时的视野。 第二,晋《中经》所录《归藏》不属于汲冢书,可谓证据成群。荀勖作了隐然否定:他主编的晋《中经》载录《归藏》,而他主持的汲冢书整理,有的定名为《易经》,有的定名为《易繇阴阳卦》,那么,在他的视野里,异名者即异书。至于《易卦》是否似《连山》、《归藏》,那是另一问题了。《隋志》重视汲冢书板块(对属于者有一一说明),又重视《归藏》的存亡史,若有汲冢版《归藏》,《隋志》谈《归藏》时必定说明,而事实上没有说明,乃是隐然否定。郭璞是王隐的同事,早期生活在汲冢书整理时期,引《归藏》而不提及《易卦》,即是间接隐示二者无关。——这些否定互相支持,乃证据群,乃任文论述上解决不了的系列阻力位,任文客观上避之。 因此,郭璞、梁元帝等人所谈《归藏》,即传本《归藏》,只能是承自汉代的官存《归藏》。 因此,由于郭璞所谈《归藏》与王家台秦简“易占书”有几个条文相同,二者本质一样,将后者划类为归藏(类称)是合理的。 (二)《连山》的补证:西晋、北魏有其藏书 据《连山》马辑本,《玉海》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语:“《连山易》曰: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语:“《连山易》曰:鲧封于崇。”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注”云:“《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颍水注》云:“《连山亦(易)》曰:启筮亭(享)启筮神于大陵之上。”该条文字有误,《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易》云“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孙诒让《札迻》卷三认为当作“《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 西晋、北魏距东汉不远,引者皆严谨的考证类学者。 唐修《晋书·皇甫谧传》云:皇甫谧乃汉太尉嵩之曾孙,酷爱著述,曾“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同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但他拒绝,终身不仕。 著《帝王世纪》,需读《世本》等大量的朝廷所存先秦史料(对应东汉的兰台藏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这车书不是一部书,否则会谈书名,应该是摘录了先秦各史料。他是否可能利用特殊关系在朝廷阅读过?应该不是,因为该事重要而《晋书》没说。 特别是,北魏郦道元在晚年能直接了解朝廷所藏《连山》。东汉时的《连山》所在的兰台属御史中丞管理,该职在北魏改称御史中尉,该系统的职能当大体不变,郦氏525年任御史中尉,有权查阅《连山》。值得了解,30多万字的《水经注》是他长期工作的结果,他前期的工作是游览天下、实地考察、记录见闻,后期的工作是广引文献——引书多达437种。 西晋、北魏的《连山》只能是承继了汉魏的那部藏书。庞然大物者《连山》几乎无用于朝廷人士,其间没有伪造的动力。东晋朝廷是逃窜而建立的,应该没有它,因为逃窜形势下只能选择高度重要类文献携带。北魏京城(洛阳)区的继承者为东魏,而东魏后期有两个权力中心即洛阳和邺城,东魏的替代者北齐定都邺城,同时洛阳难免有某种相对独立性,都城的这种变化容易导致一批图书随后散失,《连山》之失当在魏齐换代后的那个时期。 收稿日期:2014-02-24 注释: ①孙少华《桓谭生卒年新考》,载《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王宁《〈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5期。 ③下引任文的观点皆见: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载《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 ④程二行,彭公璞《〈归藏〉非殷人之易考》,载《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⑤史善刚、董延寿《王家台秦简〈易〉卦非“殷易”亦非〈归藏〉》,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⑥[民国]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⑦[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载《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上海:开明书局,1936年。 ⑧[清]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⑨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60页。 ⑩杨天宇《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载《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