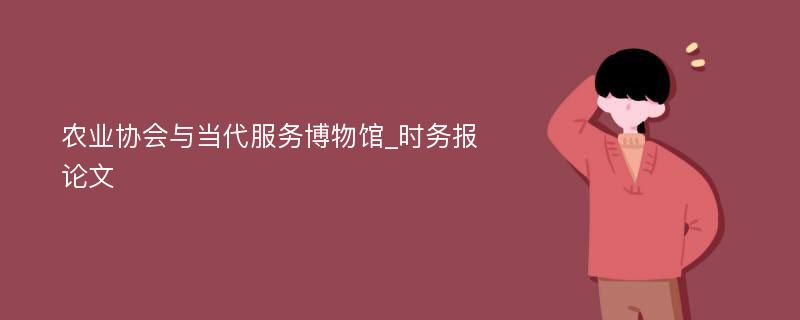
务农会与《时务报》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朝廷颁发上谕:“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①。戊戌政变后,朝廷严禁报馆会名。十月初三日(1898年11月1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折,认为农学会与农学报,“实所以联络群情,考求物产,于农务不无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二十五日(12月8日),清廷同意刘坤一奏农学请准其设会、设报的建议②。务农会③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务农会”及《农学报》依托汪康年与《时务报》馆之助而立。然而,自《时务报》停刊后,“务农会”和《农学报》却并未随之消亡,其境遇颇堪玩味,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十年《农学报》的命运折射出清季以降,近代中国社会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中国农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既往学界对务农会的研究不乏关注④,多集中在《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农会代表人物方面。然因《农学报》数目庞杂,加之资料散佚,给研究增添了困难,以致相关史实语焉不详,有关论述错漏较多。不少文论在叙述务农会产生时,多依据时人回忆和章程条文直接铺陈,对务农会创设的真实诱因、具体过程等仍有忽略,低估了近代学会、报刊创设的现实困难与曲折,缺少细致解读和深入分析。 一、创务农会之设想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三个月后,罗振玉致函汪康年,对其办报之举表钦佩之意,称:“昨与敝友蒋伯斧参军议中国百事,皆非措大力所能为。惟振兴农学事,则中人之产,便可试行。蒋君忻然,急欲试办”,并就此事询问汪康年,希望能通过他的帮助,聘得购买机器,延请农师,及仿行日本铁棒打井之法之东西人选⑤。巧的是:半个月后,朱祖荣鉴于时下洋务诸公“不修农政”的缺事,亦向汪康年道出“拟倡兴农学会”的设想⑥。在汪康年的介绍下,蒋、罗二君致函朱祖荣共商此事。阅信后,朱祖荣自言“不禁雀跃三百,喜予志之不孤也”⑦。至于徐树兰是怎样与蒋黻、罗振玉及朱祖荣取得联系,如何商谈,其间经过哪些途径,谈过什么具体问题等,因原始资料缺乏,难知其详。只知在“兴农事”这点上,罗蒋朱徐四人不谋而合,且均求助于当时颇有声望的汪康年。 当时“西学大兴,有志之士,锐意工商诸政而于农学绝不讲求”,为免“导流塞源,治标忘本”⑧,汪康年亦主张“设务农会,凡农桑种畜之事,悉心考求,辨物土之宜,求孳乳之法”⑨。因而,他积极为“务农会”的兴办造势宣传,在《时务报》上刊出由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和蒋黻四人联名的“务农会公启”十条⑩。从“公启”中可看出,务农会欲办之事,举其要有五端:曰译书报,曰垦荒地,曰试新法、曰购器具,曰立学堂(11)。决意创办务农会,人力和资金的支持至为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公启”中明言:“海内同志愿入会者,请将台衔住址开寄《时务报》馆”,并称“同志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代收”。换言之,事关重要的两方面都与《时务报》馆密切相关。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时务报》沪上同志开设时务会课,出第一次时务会课的题目。其中一题为“论农学”(详论中国农学之宜兴,暨农学新法,各省土宜,以条举详尽为主)(12)。阅毕“时务会课告白”,高凤谦建言:“时务会课以农学命题,所以博采群言而裨农学会也。惟农学一门,中土既无专书,西土亦少译本,读书人士又不留心穑事,欲求通知中西农学,及各省土宜,而能条举详尽者,斯世殆无其人。似宜降格以求,令各省之人,就其见闻所及,详细条引,但求切用,无取具文,下至一邑一乡之所有,一草一木之所宜及。凡附隶于农事者,苟能道具其窾窾,详其功用,即可完卷,无庸繁征博引以求高深。”(13)《时务报》馆采纳了此意见(14)。“时务会课”中“论农学”一题的出现,无疑从一个侧面,为时处初创阶段的“务农会”做了有效的宣传。此外,对于“西土农书少译本”的情况,梁启超亦道:“西人言农学者,国家有农政院,民家有农学会,农家之言,汗牛充栋。中国悉无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为一部。”(15)朱祖荣、邹代钧的言论也可作为当时西方农书翻译情况的佐证(16)。 一个月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1897年4月2日),《时务报》刊登由“农学会同人公启”的“农会报馆略例”,该略章分“报刊凡例,办事规条,筹款章程”三部分。凡例部分对欲办报刊的内容和编纂体例进行了说明;办事规条则对农学报馆的组织情形予以介绍:设理事二人,一总理庶事,一润色书报。日本翻译和英文翻译各一人,司账,写字一人,杂役二三人,即:报馆共计10人左右,但无具体人名;筹款章程中较前“公启”中的规定更为细致详备:“本会银出入,统由汪君穰卿主政,凡诸君助款,请迳寄本馆,由本馆填给本会收条,并送请汪君签字,以昭凭信。”(17)在《农会报馆略例》后,首见四位务农会捐款姓氏(18)。汪康年一如既往地为之宣传(19)。《知新报》则盛赞“与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的上海农学会创立(20)。 需要说明的是:“公启”刊登时,署名人蒋罗朱徐四君并不在上海,因分处两地,他们与汪康年的联系全以信函形式进行。“公启”刊出后,汪康年致函罗振玉与蒋黻,让他们邀上朱祖荣,同来沪晤商务农会事宜。而“农会报馆略例”三部分的具体撰稿人为谁,最后采纳了多少人的意见,难知其详。只知其署名是“农学会同文公启”,意为乃集合众人之意而成,并非单独的个人著述。如蒋罗二君提出他们对《农学报》章的规划(21)。而叶澜则言:“农学会收捐章欠清晰,大致本弟所拟,而改去学问要领,想系归入详章也。”(22) 二、八方响应:农会题名与捐款 “务农会公启”在《时务报》刊出后,“四方君子,谬相许可,或代拟章程,或诒书商榷,崇论闳议,釐然盈箧”(23)。马相伯著“务农会条议”,后收入《农学报》“农会博议”栏(24)。谭嗣同拟《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十八条,提出总会、分会会友“于农学一有新理之得”,互相联络的设计和构想(25)。草拟务农会收款章程的叶澜建议“先须译书习法,购地试验”(26),因其“无款可助”,故欲“将祖遗萧山田三十亩助入公会为试地”,并且打算“派人在会学习农学,将来即派在所助试地上种植”(27)。吴樵则道:“农学会章当与同志观之,惜办事章程甚略,仅后六条”(28)。邹代钧热心表示自己有“德文地学图”,该图“于农学有补”,如能翻译,愿贡献此书(29)。 此外,士绅还纷纷询问相关消息,密切关注农会事宜:前湖南龙山县知县李智俦多次向汪康年询问“农会诸君子到否”,关注“何日出报”的农会信息(30)。三月十五日(1897年4月16日)徐维则亦致函汪康年,问“《农会报》何时可出”(31)。周学熙也问过汪康年同样的问题(32)。卢靖闻之欣慰,认为“农事为工商之本,著效又极速,三十年来识时务者诸巨公独缺而不讲,舍本而逐末,置易而图艰,宜其法愈变而愈弱也”,并询问“《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务农会可否即名为务农公司?”(33) “务农会公启”中曾言:“海内同志愿入会者,请将台衔住址开寄《时务报》馆,以便遇事公同商酌。”(34)“务农会章”亦道:“凡愿与会者,乞赐示衔名住址,俾按先后,以期集事。”(35)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农学报》首刊上,刊登一份“农会题名”,称“以入会先后为序,以后入会诸君依次续登”(36),列出45位列名农会者(37),同时刊登“代捐款诸君名氏住所”共8处9人,分别为江苏张謇、朱祖荣、刘梦熊、邱宪、王锡祺,浙江徐仲凡、邵章,成都陶在宽,桂林龙焕纶(38)。仅丁酉年一年,就有209人名列题名者,占三年农会题名的61%(39)。其中99人为仅具功名的士绅,79位有仕履的官员,32位无任何头衔。而79位官员官衔多为候选训导、记名道,候补知县等一类无重权的虚衔。值得一提的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五名内阁中书(40),户部中郎刘锦藻,刑部中郎王锡祺亦名列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黻和罗振玉均为附生,徐树兰为举人,朱祖荣为廪贡生,四人均为略有功名而无官衔实权的士绅。在士林中籍籍无名,其影响力自是微乎其微。而汪康年因《时务报》的兴办,则已声名远播。故而罗振玉和蒋黻曾请汪康年出任农会经理,总农会事,但汪康年并未答应,“仅允经理银钱”(41)。欲“振兴农学事”,还需晚清大臣的提倡。因此“公启”刊登后不到一周,蒋黻便托汪康年“函请张孝帅提创此举”,以期“天下豪俊闻风兴起”(42)。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三年亦曾尝试由王文韶、张之洞等晚清重臣来主持此事(43)。 务农会及《农学报》之设,除需人脉聚集,取信于人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来支撑运转。务农会会银出入,统由汪君穰卿主政。在《时务报》馆和农会同人的共同努力下,丁酉年,共收到捐款银元4810元,银两350两,含42位捐款人和“直隶临城矿务局”1个捐款单位(44)。 其中蒋黻、罗振玉、张之洞出资各500元,徐仲凡捐300两,其余各人10元到250元不等,助款之人多为列名农会者(45)。需要说明的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务农会曾明确规定:“会员每年纳会金中,谓之会金。其数由银三元至六元,量力之厚薄纳之”。但同时又称:“会中名誉会员以及已捐助之会友不在此例”(46)。若以每位会员纳会金六元计算,丁酉年209位列名农会者,共1254元,远不及实际所收助款4810元。另相形之下,如谭嗣同、叶瀚、吴樵等人,在光绪二十二、光绪二十三年曾为创办《民听报》多方设法,四处筹款,然终一无所获(47)。故而可以推断:“务农会”所得筹款并非会金所聚,而是靠汪康年及《时务报》馆的声望募集而来。 三、好风凭借力:《农学报》的创刊 务农会创设之始,立愿至为宏大(48),但因早期经费未集,同志未多,拟先“捐集款项,创立报章。其他各事,俟创办时酌订章程,先期登报,以期集事”(49)。在汪康年的帮助下,务农会已订购泰西、日本的农书农报,聘请藤田丰八为东文翻译,英法文翻译并已得入(50)。故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上(1897年5月),寓务农会事于报事的《农学报》问世。光绪二十六年前的《农学报》(51)内容包括“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栏,接着为“中西文合璧表”,最后为连载的中国农书、西方农书翻译和“农会博议”。 值得注意的是:《农学报》首刊第一篇文章“农学报略例”,与此前《时务报》上“农会报馆略例”一文,除“凡例”部分文字略有出入外,内容主旨相同。后者文末4位捐款姓氏的名字亦出现在《农学报》第1册的“捐款姓氏”之中。而《时务报》23册上梁启超“农会报序”一文,亦出现在《农学报》第1册上(52)。此外,作为维新报宣传刊物的《知新报》,在梁文发表10天后,刊登的“务农会章”12条,与《农学报》首刊所见“务农会略章”文字一模一样。 较《时务报》言,《农学报》并无论说。虽如此,《农学报》仍道:海内同志,以撰述见教者(必有关农学者),当择优录登“农会博议”,以备众览”(53)。“农会博议”连载“有要于农事者”18篇,其中最引人注意者当属马相伯的“务农会条议”十五条。徐仲凡在读完后,感慨其“条分缕析,言皆有物,非深识静意,何以及此。钦佩!钦佩!”(54)罗振玉亦称“相伯先生细章,业读一过,精密之至”(55)。虽汤蜇仙、吴剑华、朱祖荣则对马君条议的部分内容予以指驳(56),但叶意深认为:“《农学报》已阅至第三册,体例悉协,所载马湘伯观察条议,至为精当。诸家指驳似少体会。”(57)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897年9月7日),因时务会课征文“收佳卷甚”多,《时务报》刊载了此次会课卷次第姓氏五十名,第一名为张寿浯(58)。其“论农学”的文章刊载《农学报》第4-15册中。梁启超的《蚕务条陈叙》和朱祖荣编辑的《蚕桑问答》亦见于光绪二十三年的《农学报》(59)。光绪二十四年,因《农学报》馆“去岁第一期至第十八期之报,久经售罄,补印不易,兹将去年译印已成之书二十三种(其已译未全之书,竢随后印行)编为《农学丛刻》”(60)。 光绪二十二三年的《农学报》每月出报两次,每次约三十页内外,是年共出《农学报》18册。据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97年7月10日),徐树兰给汪康年的信件,称:“弟带回之《农报》,因随同《时务报》派去,仍多折回”(61)。这时《农学报》已经出版到了第5册,徐言可作为最初《农学报》销量的证据。邹代钧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7年12月19日)的来函中提道:“沪上以后寄报多少开呈,祈遍告照行:《时务报》七百册,近来销数稍减;《知新报》一百册;《农学报》五十册;《萃报》五十册。《求是报》、《妇孺报》祈属暂停寄,缘无人购阅耳”(62)。也就是说:早期的《农学报》其销量并不乐观。 然截止到丁酉末,《农学报》的销量却有约3000份(63)。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给康有为的信函中,曾言:“一馆之股,非万金不办,销报非至三千不能支持。”(64)据《农学报》馆统计:丁酉年共收报费4229.525元(65)其中自收报费517.155元,代派处收报费3712.37元(66)。代派处的销量为本埠的7倍多,充分可见庞大的销售渠道的作用。 《农学报》本埠在新闸新马路梅福里本馆及《时务报》馆、格致书室、文瑞楼、著易堂等处销售。外埠截止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在全国16个地区设立66个分销处(67)。销售渠道遍及南北。除南京、广西、浙江三个区域的代销点不同外,《农学报》的流通渠道,均为《时务报》销售分布的范围。较之创办的《国闻报》销路始终局限在北方各省的情况(68),一见晚清办报之不易,二显《时务报》销售渠道之影响。 四、人走茶未凉:农会、农报的时代象征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时务报》停刊。不久后,戊戌政变发生,时局日坏,朝廷封报禁会,“海上志士,一时雨散”。蒋黻主“自行敝馆散会”,且“感于时危,归淮安奉母”。此时的《农学报》已出至40多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振玉托李智俦面陈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请将报馆移交农工商局,改由官报”。刘坤一在请示当局后回复道:“《农报》不干政治,有益民生,不在封闭之列。至农社虽有乱党名,然既为学会,来者自不能拒,亦不必解散。至归并农商局,未免掠美有所不可”,并令“上海道拨款为之,沪道发二千元”(69)。罗振玉在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1899年5月29日)给汪康年的信中道出苦心:“今年农会处万难之势,仍须努力,存此孤注,是私衷耿耿者耳”(70)。时有人曾问于:“农馆得南洋借款,如何章程?”(71)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下(1899年11月),徐仲凡,程少周,汪穰卿,罗振玉四人联名,出“农学会公启”(72)。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下(1906年1月),《农学报》才停刊。 将“务农会”及《农学报》的命运置于动态的社会情境和历史的具体史实下加以考察,可知:《农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为务农会会报。是会由如皋朱祖荣、会稽徐树兰、上虞罗振玉、吴县蒋伯斧诸君所创设,而汪康年力为之助(73)。在前期“定翻译人员”,“购农书农报”,“筹措经费”与“取信于人”上,汪康年及《时务报》馆扮演了主角,故而张元济感慨道:“《农报》已到,同人极为称赞。盖非我公主持其事,乌能臻此?”(74)沈克诚将“广《农学报》,设农学会”之举视为汪康年的作为(75)。李智俦更向汪康年明言:农会“附庸贵馆,尚望始终提挈”(76)。 《农学报》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正式出刊。此前,报馆的筹备工作经由《时务报》宣传及士人与汪康年的书信往来,已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77)。但对于馆外各界人士而言,仅从《时务报》、《知新报》的只言片语中,只能理解其大概拟章,刊物的规模,对于刊物确切名称,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不甚了了。如卢靖认为:“会字古今中外皆属极美之称,独中国则有会匪、会党之禁。《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务农会可否即名为务农公司?”(78)此外,《农学报》也并没有如《时务报》般标明具体的“办事诸君名氏”。加之,《农学报》没有推行试刊,在根本没看到实际报刊的期刊下,列名农会者、捐款者、代售者和报馆之间,谈不上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会纷纷建言,热心助款,愿入农会,自然是因为汪康年,梁启超及《时务报》馆在士林阶层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从《农学报》的创办过程来看,《农学报》和《时务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并非如罗振玉后来所回忆的:“丙申(1896)春至上海设农学报馆,聘译人译农书及杂志,由伯斧总庶务,予任笔削。及戊戌冬伯斧归,予乃兼任之,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当时所谓志士,多浮华少实,顾过沪时,无不署名于农社以去”(79),那般容易和简单。务农会早期“经费难酬”与“无以取信”的两大难题,是在《时务报》馆鼎力相助下得以解决的。会报《农学报》实乃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通力协作的结果。初期主要借助《时务报》的声望和销售渠道,而罗振玉一直参与此事。 然政变后,《时务报》不特未销者无人过问,即已售者亦均视为厌物(80)。而《农学报》在《时务报》停刊后,仍能继续存在,且前后长达近十年之久。在戊戌封报禁会时,仍被张之洞推为“讲农政者宜阅”之报(81)。其后所译农学新书,不减反增,“销行甚畅,所得利益,除偿本金及维持农馆、东文学社外,尚赢数元”(82)。个中因缘,除《农学报》内容少专门论说,无主笔人员,实为一份出新的农学译报,及“务农会”虽有会名,却无实际聚众集会行动,加之得刘坤一、张之洞等晚清重臣之提倡,更在于其乃“中国农政大兴”之兆。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孙家鼐议覆开办大学堂折中,所立诸科,“农学”居其一(83)。八月,御史华辉奏请讲求“务本至计”,提倡“广种植”、“兴水利”,以开利源,该折引起当朝热议(84)。此为农务振兴之机。而务农会创立后,曾宗彦提出“励农学以尽地力”,“明诏鼓舞”上海农学会(85)。上奏当天,光绪即发上谕:著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议奏(86)。不久总理衙门议覆:“所称上海农学会,由江浙绅士创设,行之有效,是风气业已渐开”,并建议南洋大臣查明该会事宜(87)。当日光绪就此下发谕旨:“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88)。至戊戌维新期间,“在条陈急剧增加,以致无法全部处理的情况下,有关农业改革的上书却优先处理。从没有哪一个领域如同农业一样,得到光绪帝的如此重视。”(89)务农会但明农学,不及时政,合于晚清当局振兴农务的时务,自然《农学报》被各方认可和支持亦在情理之中了。 近人惯以罗振玉《集蓼编》内的回忆和“务农会公启”中蒋罗朱徐四人的署名为据,直接铺陈,将“务农会”及《农学报》的出现视为自然而然、轻而易举之事,低估其间蕴含的历史情景和人事关系之复杂性,从而所知与真相相去甚远。《时务报》后,《农学报》的决策过程、最终结局及其对罗振玉“究心农学”标签的塑造,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故事了。 注释: ①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第548-549页。 ③有时亦称“农学会”、“务农总会”,“农会”。本文取此会第一次公启中“务农会”名。 ④管见所及,海内外相关研究,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白瑞华称:《农学报》是更加细分化的农业报刊,于1897年创刊于上海,开始为半月刊,后来改为旬刊。这份刊物在报道有关中国农业改革方面的内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尽管其农业改革宣传是教条式和务虚的,但刊物却惊人地收欢迎。《农学报》于1898年落入日本人手中,共出版315期。(Roswell Sessoms 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td.,1933,pp.94-95);张静庐则指出:《农学报》1897年在上海出版,罗振玉、蒋斧主办。初创为半月刊,石印本,每期约二十五页,内容分古籍调查,译述、专著等。第二年改为旬刊,后让与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期止。(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9页);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又道:《农学报》1898年转给香月梅外经营,且《农学丛书》是《农学报》的合订本(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2页);钱鸥通过考察罗振玉与务农会、《农学报》之事,将罗振玉的名字与“新学”并列,认为其曾经是一个深受维新变法运动的感召,向往新学,积极投身晚清新政改革的时务青年。[錢歐:《羅振玉におけゐ「新学」と「経世」羅振玉におけゐ「新学」と「経世」》,[日本]《言語文化》第1卷第1期,1998年7月,第71-103页];伊原泽周从务农会的创设、《农学报》的刊行、《农学丛书》的编印及东文学社的创办的角度,探讨了务农会在戊戌变法运动史上的地位(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0-292页)。此外,潘君详、章楷、朱光立、深澤秀男、林更生、大川俊陸、汤志钧、石田肇、吕顺长、杨直、杜軼文等人的论述,对“务农会”、《农学报》、藤田丰八和罗振玉等亦有涉及。 ⑤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页。 ⑥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第222页。 ⑧⑩《务农会公启》,《时务报》第13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1896年12月5日)。 ⑨汪康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时务报》第13册。 (11)汪诒年编:《书牍辑存》中,《汪穰卿先生遗文》,[杭州]汪氏铸版,第3-4页。 (12)《新设时务会课告白》,《时务报》第17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1897年1月13日)。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6页。 (14)《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1897年3月3日)。 (15)梁启超:《西书提要农学总叙》,《时务报》第7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896年10月7日)。 (16)朱祖荣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言:“此种西书多未译出,只有《农学新法》、《农事略论》两种,说固未备(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223页);邹代钧也称:“农学书甚可译,此书中国无译本”(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701页)。 (17)《农会报馆略例》,《时务报》第22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1897年4月2日)。 (18)四人为邱于蕃,徐仲凡,刘味清,鹿柴居士李智俦。见《务农会捐款姓氏》,《时务报》第22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1897年4月2日)。 (19)汪康年言:“农会为中国目前至要之事,创办诸君以筹款不易,因先报馆以资研究已延请上等翻译,准四月出报,惟经费未充,不能多印。且不能概送,远近同志,如有欲阅此报者,本埠请迁至新马路梅临福里农会报馆挂号,外省请在各寄售本报处挂号,或函《农会报》馆,均可”。(《时务报》第22册)。 (20)《务农会章》,《知新报》第13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 (21)(2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928页,第2573页。 (23)《农会博议》,《农学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1897年5月)。 (24)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0页。 (25)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1-273页。 (26)(27)(29)(3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555页,第2573页,第2701页,第2981-2983页。 (28)(3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520页,第567页。 (3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519页。 (3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206页。周学熙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1897年4月20日)致汪康年函中问道:“《农务新报》何时可出”。 (34)《务农会公启》,《时务报》第13册。 (35)《务农会章》,《知新报》第13册。亦见于《务农会略章》,《农学报》第1册。 (36)《农会题名》,《农学报》第1册。又:《农学报》资料散佚,“农会题名”与“农会续题名”散见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及姜亚沙、经莉、陈湛绮主编:《中国早期农学期刊汇编》第3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版,第593-640页。笔者据所搜集到《农学报》中“农会题名”内容,进行史料比勘,推断出题名大致时间。 (37)分别为:蒋黻、罗振玉、汪康年、梁启超、徐树兰、朱祖荣、邱宪、马良、马建忠、陈虬(字志三)、叶瀚、张謇、张美翊、李智俦、叶意深、连文冲、陈庆年、陶在宽、沈学、沈瑜庆、凌赓飚、魏丙尧、王镜莹、邵章、邵孝义、龙泽厚、龙焕纶、汪鸾翔、况仕任、王浚中、龙朝辅、刘梦熊、谭嗣同、柳齐、周学熙、高崧、沙元炳、吴廷赓、马燮光、邓嘉缉、胡光煜、桂高庆、李钧鼎、李盛铎、龙璋。 (38)《各处代收捐款诸君名氏住所》,《农学报》第1册。 (39)今所见资料,仅丁酉年至己亥年三年的“农会题名”。据统计:入会列名之人共342位,其中“黎宗鋆,唐才常、黄绍第、曾仰东”两见。 (40)分别为:徐维则、蒋锡绅、文廷楷、张鸿、王景沂、陆树藩、吴燕绍。 (4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524页。 (42)(5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927页,第2927、3156页。 (43)汪诒年编:《书牍辑存》中,《汪穰卿先生遗文》,第3-5页。 (44)《农学报》第1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上(1897年10月);《第二次报销清册》,《农学报》第20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中(1898年2月)。 (45)邱于蕃捐银100元,李智俦捐银300元,但二人的名字见于《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2日),和《农学报》第1册,却未见于11册农会捐款人汇总中,原因不详。 (46)《务农会试办章程拟稿》,《农学报》第1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上(1897年11月)。 (47)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3-496页。 (48)在《务农会公启》中就提到“购田试办”、“办报”,“开厂”、“设学堂”四事。其中“购田试办”一事,虽有建议,却少有实效。李智俦曾向汪康年建议:“张季直殿撰如至申江,请与商议沙洲事,如能指拨少许与农学会,则有立足之地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566页);蒋黻和罗振玉在给张謇的信中也提到:龙研仙大令捐献如皋沙地,由朱祖荣就近照料(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此外,徐仲凡、叶澜,谭嗣同对购地试办的建议分别见于《汪康年十余书札》第2册,第1524-1525页;第3册,第2573页;《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第492页。而“立学堂”亦有打算,如徐树兰致函汪康年询问:“设立农学堂,拟如何办理,有成议不?”(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526页);罗振玉曾请汪康年与陈锦涛、严复酌定《农学堂章程》(《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157页);张元济言:“农学馆开后似可请南洋具奏”,并称“农学堂总宜速开,陆纯伯未必能办”(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20,1731页),但终未果。而“开厂”一事,具体操作较少被人谈及。 (49)《务农会章》,《知新报》第13册。 (51)光绪二十六年第94册后的《农学报》,体例有明显变化,分“文篇”、“译篇”和“连载农书翻译”栏。 (52)《农学报》无文论标题,仅文末书“新会梁启超序”。 (53)《农学报略例》,《农学报》第1册。 (54)(56)《农会博议》,《农学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1897年5月)。 (55)(57)(6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154页,第2446页,第2749页。 (58)《时务报》第38册。 (59)《蚕务条陈叙》,见《农学报》第2册;《蚕桑问答》见《农学报》第1,2,3,5,7,8册。 (60)《本馆告白》,《农学报》,具体时间未知[仅能据其前后告白的时间,推测其为光绪二十四年的告白,且在《农学报》第25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1898年3月)之后],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6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525页。 (63)《本馆告白》:“本馆开创以来,承同志协助,派出之报将三千余分”,《农学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1898年1月)。 (6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65)《农会报销清册》,《农学报》,册数不详,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66)此处代派处报费未算未缴情的报费,《农学报》曾多此发声明,向代派处催要欠费。见《农学报》第9册,第14册,第18册,25册。 (67)分别为京城4处,直隶5处,河南1处,山西1处,江苏20处(5册29处),安徽2处,浙江13处(5册11处),湖北5处,湖南1处,江西3处,福建2处,广东3处,广西2处,四川2处,香港1处,澳门1处。见《农学报》第1-5册,第10册,第12册,各埠售报所名单。 (68)(75)(7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2页,第1125页,第566页。 (69)罗振玉:《集蓼编》,《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2,[台北]大通书局印行1989年版,第713-714页。 (7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163页。 (71)(7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230页,第1694页。 (72)《农学会公启》称:“敬启者,本报开创初由同人协立,既经江督新宁尚书奏改江南总农会,力加倡导,拨款维持,岁月不居,忽忽三岁。去岁至销报三千余分,然因各寄售处报金多不清缴,致度支不给,几至中辍。今年整顿寄售章程,而销数日绌,综计各省官私所销,不及去岁三分之一。设法补苴,幸勉失坠。然核计今年出入款项,除已经挪用之外,以后尚缺千数百圆。窃惟报章为农会基址,报章之有无,关于农会,实非浅鲜。自未便因目前支绌,遽尔停止,谨与同志公议,敬请同会诸君子,合力维持,每人认捐一股,或数股数十股,每股墨银十圆,一面集股为延续目前之谋,一面筹常年经费,及推广销报。俟筹款有著,即停股捐。树兰等各认若干股,以为之倡同人所出股份,即祈于今年冬间,寄沪,以济办报之须,凡人股者,报章出后,照股数寄报,以酬盛谊、古语有之,慎终如始。又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将伯之呼,无任祷企。兹将已认捐之姓氏列左。徐树兰等公启。后为四人捐款:徐仲凡捐壹百圆;程少周捐伍百圆;汪穰卿捐伍拾圆;罗叔耘捐五十圆,同时附呈了“农学报馆开办以来出进款项清单”。(《农学会公启》,《农学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73)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卷六,杭州汪氏铸版1938年版,第6-7页。 (77)如士人来函问出报时间,及《知新报》言:《农学报》拟正、二月间出报。 (78)(8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981页,第3874页。 (79)(82)罗振玉:《集蓼编》,《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2,第711页,第722页。 (81)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83)(84)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7页,第300-303页。 (85)(87)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5-386页,第387-389页。 (86)(88)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国学文献馆1987年版,第30800页,第30858-30859页。 (89)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2-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