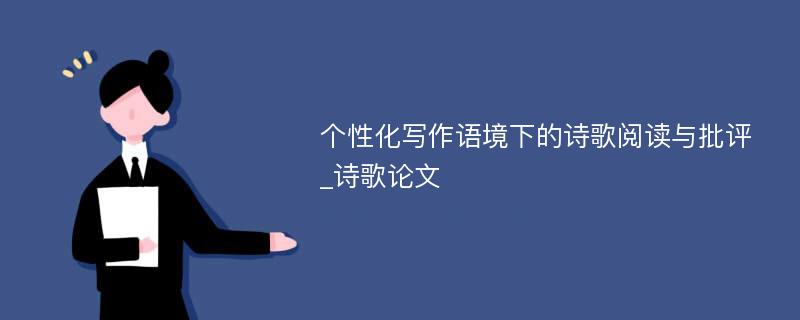
个人化写作语境下的诗歌阅读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诗歌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人化写作作为九十年代突出的诗歌现象,近年来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评价。个 人化写作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由此给诗坛带来的影响则有待继续思考。这是一种更 为个性化、隐秘化的书写方式,必然使传统的阅读与批评方式难以奏效,因此它直接引 发的一个课题是对一种新的阅读与批评方式的呼唤,使之与其自身相适应。而这正是时 至今日仍需反思的。
个人化写作是新时期前十年诗歌运动的延伸与深入,同样也是诗人主体意识的全面觉 醒和诗的本体意识的全面复归的产物。这是两个互动、并进的轮子。主体意识的自觉、 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的复归,导致了对诗的观念、诗的本质属性的全面反思;人的感觉 力和想象力的全面解放,导致了对旧有的诗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的不满与超越。原先的 表现方式与技巧再也满足不了解放了的诗心的需要,回归诗歌本体,成了诗歌实验运动 的自觉旗帜和鲜明主题。
诗歌回归本体,自然要把诗的形式和技巧放在异常重要的位置来加以考虑。诗人们清 醒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形式更重要的美学意义不在其它,而在于它比其它东西更能 对后来诗人产生持久影响。文学思潮的更迭构成文学史的基本骨骼,形成崭新风习,但 在各种文学思潮平息乃至被人遗忘之后,最终突兀出来并作为联系回忆和艺术之媒介的 ,仍然是那些让人不能忘怀的创造性技巧手段。”(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 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页。)这种对形式和技巧的探寻,其热情之高,范 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而这种探寻的结果表明,现代诗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隐秘化趋向 。
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隐秘化首先是为其表现的心理内容所要求的。诗人们认为,诗和 艺术是“人类心灵的深处呈现”,“诗向我们提供的全部内涵就是体验,一种神秘,接 近于不可知的嵌在文字中的感受,一种暗合人类心灵中某种秩序的东西,一种莫名的震 颤。”(注:唐晓渡主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这种神秘感,这种莫名的震颤,靠惯常的感觉方式当然无法捕捉,靠公共的方式也 难以有效传达。这就使得诗人们把诗的创造当作精神的历险,把知觉转化为本能,自觉 地进入诗歌状态之中。
在诗人们看来,书写与生命是合一的。现代抒情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决不是孤立的技 术问题,而是“结构化了人之觉醒的生命表征”。(注:唐晓渡编:《中国当代实验诗 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页。)因此,“人们可以从呼吸的快慢节拍上分析 作者的家族经历或个人创伤,可以从词语结构上判断一位诗人的早衰,还可以在词与词 根、直观与还原、语调与气质、旋律与建筑相对关系上,阐释诗歌的文本意义。”(注 :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7页。)技巧包含着 深刻的心理内容,由于心理一般不会重复,这种技巧当然也无法重复。据此可以看到, 对于个人化写作而言,技巧与生命的贴近也就非常自然了。
个人化书写把技巧放在生命的同等地位来看待,还出于“反文化”、“反语言”的种 种考虑。诗人们提出,“诗必须停止比喻,停止拟人拟物,不再‘像什么’,而是‘是 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运用口语等原生态语言来对抗和超越既有语言秩序,以一种独 特的和个人化的语感和语势,揭示出规范语言无法言及的人的内心真实。反文化、反语 言的努力,也使得这种更具先锋性、探索性姿态的书写具有不可重复性、不可摹仿性的 特点。
个人化写作的这种隐秘性使得诗歌阅读趋向艰难,如果对实验诗人的艺术追求缺少理 解,那么对隐藏在作品里的技巧性功能就不太容易发现,从而影响审美效果。例如西川 的《聂鲁达肖像》,不作细心体味是发现不了其反讽效果的:
经常在一切终结/只有音乐黄昏般浮动时/我注意到/他的肖像挂在墙上/高山、野狐掠 眼而过/巴勃罗·聂鲁达/开始注视/这间房子/它布满尘埃和格言/而我坐在那里/和朋友 聊天/翻阅书报
此诗在轻松随意的陈述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情景、两种姿态动作和两种语言系统,它们 之间显然的差距,几乎表现在每一个词和字里面,聂鲁达尽人皆知的影响和诗歌权威, 构成这首诗的“语境压力”。“我注意到”的轻慢,与“他的肖像挂在墙上”的尊严感 的语义在表面上谐调,但若置于上述语境之中则发现,“注意到”几字已在暗中使之扭 曲,词性由审慎、恭敬偷换为“努力这样做”。后面的句子则进一步降低了陈述的热情 ,肖像挂在墙上的矜持悄悄换作了怕受人忽视的“注视”。“注视”是一个有意义的心 理动作,暗示了主、配角的倒置。诗论家程光炜指出,“这节诗无一个词明显含着揶揄 ,但从始到终都意味着与字面意义相反的东西,词性色彩包括语调的克制,使这两种情 景和语言系统的差异反而十分显著。”(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 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在个人化写作中,技巧成了心灵的直接现实,成为生 命的一部分。技巧的内向化、隐秘化,是现代艺术的基本取向,这也决定了诗的阅读与 批评并不轻松,这是一种艰深的精神探索,要求有更多的心灵的投入。
从新诗潮到个人化写作,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二元对立走向更为多元的分化、变异、 竞争之中,原先诗歌的定向的、逻辑的、有规则的价值选择,变成了五光十色千奇百怪 的展现与奔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诗歌视野更显纷乱、嘈杂,难以规范和把握。
与以往的诗歌不同,个人化写作的文体叙述更直接地来自自我的生命体验。个人化写 作产生的是“体验的诗”。张颐武认为:以往的诗是“解释的诗”,无论那些诗怎样难 懂,它仍有坚固的意义和指向,它仍在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判,它仍然可以在一个二 元的框架中得到确定的意义。例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江河的《太阳 和他的反光》等都属于这一类;而所谓“体验的诗”,则完全不同,我们发现诗不再可 以解释了,诗人只急促地在体验世界的纷乱,用笔抓住和留下这体验,把自我沉入了对 日常生活、对人和物的“无穷无尽的体验”之中。
当年朦胧诗出现伊始,曾使一部分人大呼“难懂”。但即使难懂,也仍可以在人的尊 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的复归中找到意义的掩蔽之所,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释”;“ 体验的诗”则不同,它似乎抛弃了对“意义”的追求,仅仅注重瞬间和自我的体验。自 我的体验是一种生命体验,由此产生伽达默尔所说的“体验艺术”。伽达默尔对体验的 艺术作过高度评价,并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加以阐发,他认为艺术的本质规定性就是体验 ,“体验概念对确定艺术的立足点来说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由此,艺术作品就被理解 为生命之完美的象征性再现,每一种体验似乎正走向这种再现,因此,艺术作品本身就 被表明为审美经历的对象,这便得出了一个美学结论:所谓的体验艺术则是真正的艺术 。”(注: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他进一 步指出了体验的作用:“在艺术的体验中,就存在着一种意义的充满……代表了生命的 意义整体。某个审美的体验,总是含有着对某个无限整体的经验……这种体验的意义就 成了一种无限的意义。”(注: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100页。)在他看来,体验的艺术,才是意义弥满的艺术。
伽达默尔对“体验”的高度肯定,触及了艺术的本质。艺术本身是深层生命的外化, 只有从生命深处出发,才能抵达生命的至高处。联系到“解释的诗”与“体验的诗”, 当然不能说凡是“解释的诗”均无生命体验,凡是“体验的诗”均含深层的生命意义。 这二类诗的不同之点,可能主要在于二者体验的立足点不同,前者更注重于“社会—— 个人”模式,后者更贴近内在生命,可称之为“存在——生命”模式。前者表现为在与 社会对抗中人的人格力量的肯定,后者则更多地转向自我,表现为潜意识、本能、瞬间 感觉的突现。诗的这种转变,同时召唤着阅读的转变,“这诗是什么意思”这类解释的 要求在迅速地过时。“诗人在诗中并没有留下可供解释的路标和踪迹。诗人只表达自己 的体验,读者就只需要自己去体验诗,他可以从解释的艰难中解放自己,保持着新鲜的 、活跃的感觉去接触诗。他对诗的接触大致是感觉的而非逻辑的,是对符号的阅读而非 对整体结构的理解,他的阅读是视觉对‘文字’的观察而非听觉对意义的感知。”(注 :张颐武:《冲突的超越》,见《诗歌报》总第82期。)对于“解释的诗”,读者只须 进入“主题”,而对于“体验的诗”,读者则被要求进入“生命”。这对于读者无疑是 一个更大的考验。因为人的生命深处是一个巨大的黑洞,生命体验具有极大的随机性、 模糊性、不可把握性。苏珊·朗格对人的内在生命曾作过如下描述:“它们就像森林中 的灯光照出的树影,总是变幻不定、互相交叉和重迭;当它们没有相互抵消和掩盖时, 便又聚集成一定的形状,但这种形状又在时时地分解着,或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爆发为激 情,或是在种种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注: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页。)每个生命的内在形态是如此不可捉摸,那么要求读者 的生命进入诗的生命,就有更大的难度。两个生命不可能重叠,体验既是随机的,也就 必然是瞬间即逝的,另一生命无法再去重复体验一次,你缺乏与之相类似的体验,阅读 障碍的存在也就难以避免。
面对诗的个人化写作这一态势,解读态度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在此,我 主张采用“视角交融”模式,即将终极视角与具体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来阅读和看待具 体诗作。所谓终级,是从宏观上、本质上看问题。凡是艺术,都有一个终极目的,它以 审美形式呈现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进一步唤醒人类自我意识,提升人类的精神。换言 之,艺术必须关怀人类的处境、遭遇、命运、苦难、欢乐、未来等等根本性问题。因而 艺术摆脱不了功利价值(艺术的功利价值是精神性、整体性、长远性的统一,是对物质 性、局部性、短浅性的超越),艺术必须对人类有益。从这点出发的评判,就是终极评 判。但同时,艺术又有其不同的个性与基质,由于创作方法、表现方式的不同,呈现出 不同的审美品性和风貌。这就要求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以具体的标尺去衡量。比如说, 对于传统诗,仍然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去衡量,看它现实主义内容的深广度如何,并提供 了何种新的审美信息,对于文化诗,则以文化诗的方式去衡量,看其文化表达的深厚度 如何;对于感觉诗,看它是以何种感觉呈现的,并提供了多少新颖独特的审美感觉;对 于新乡土诗,看它是如何以现代目光来处理古老的乡土题材,使之与现代审美意识相遇 合的;对于生命体验诗,则应以生命体验的深度去衡量。生命过程包括本能、潜意识、 感觉、情感、理性等等,生命体验诗要看它在每一个阶段上的揭示、呈现如何……。总 之,这种微观的具体角度,避免了混淆和强求一律,避免了张冠李戴,有利于不同流派 不同表现手法在各自的艺术轨道上自由地表现和生展。
此外,对于“读懂”二字的理解,也应采取更为宽容的姿态。可以设想,若以传统的 方式,要在个人化书写中寻找出确定的“主题”和“思想”,那既是徒劳的,也是冒险 的。所以,对于这个“懂”应该有更宽泛的外延与内涵。比如说,对于传统诗,主题的 明确领会,才算得上“懂”。而对于其他诗歌,大可不必如此强求。对于感觉诗,你捕 捉了诗人的那种感觉,也就懂了;对于体验诗,你感受到一种意味、一种倾向、一种情 调,这也就懂了。总之,你应当从懂与不懂的“情结”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平静而放松 的目光面对永远处于变幻中的诗坛。
与此同时,诗歌批评态度与批评方式的调整与变革更显必要。诗歌阅读是一种接受活 动,更多地带有感性的特点。诗歌批评则是建立在艺术的接受和欣赏的基础之上、按照 一定的审美标准对艺术接受和欣赏。新时期以来,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相比较,前者落 后于后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诗歌批评自身也在激烈地调整、变异。这种变化的 最大标志是诗歌批评逐步由外部批评走向了内部批评。
由外部批评走向内部批评,这是与诗歌回归本体的审美潮流相一致的。批评更多地关 注诗歌创作机制和内在审美规律的探求,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批评、心理批评、形式 批评等不同侧重的批评方式和批评手段,较之以往更深入了诗的内部和本体。然而,尽 管诗学理论体系各个环节或层次之全面变构创新的意向十分强烈、执著,但对于新时期 以来的诗歌批评,不满的呼声仍然很高。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种不满也表现在诗 评中缺少严格认真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评判。批评远离了文本,放弃了批评者自身的第一 手感觉、体验与审美把握,以致在批评活动中,或大搞新名词轰炸;或哗众取宠、自我 标榜;或生搬硬套、照单仿造,对于诗坛的种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盲目趋从,丧失了独立 的批评意识。谁都不愿承担责任,谁都不愿承担风险。这种主体批评意识的失落,自然 不仅使批评无法完成其肩负的任务,也使其自身难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长和发展。
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批评呢?我认为,真正的诗歌批评,应当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它 必须在对诗歌作品的精辟独到的体悟、理解和把握中呈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并阐释体现 这一价值的艺术构成的规律性认识。它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智慧、审美性与科学性相 结合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它必须能深入作品的内核,同时还得透示生活的深层,并超 越出来,抵达审美理性烛照的高处。它必须能够追寻诗人的足迹,穷究诗人心灵活动的 整个奥秘。因此,批评所涉及的,是包含生命冲动、欲望、潜意识、感觉、情感、理性 的全部内容,也即创造活动的心理全过程。因此,合理的科学的批评必然应该是生命批 评,我称此种批评为“原生命批评”。
生命批评,或原生命批评,是建立在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同构对应的理论基点上的。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形式具有与生命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注: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8页。),这种“逻辑形式”或特 征,包括有机统一性、运动性、节奏性和生长性等方面。因此对诗歌创作尤其是个人化 写作进行生命批评,自然更具合理性。
生命批评要求从生命现象、生命本原出发,对诗作终极性的把握。要求批评者应当具 备诗人的灵性,具有诗人对于生存的敏感以及对于艺术表现的理解。这样就把诗的批评 转变为诗的生展过程的动态批评,批评与诗相依相长,批评的目光始终伴随着诗的呼吸 ,于是批评变得更为敏锐、更切近诗的本身,更具有灵性和生机,因而能够理解诗的生 命和力量,以及它对艺术和人类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批评自身也变得更加敞亮、充 实而完美,使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得以真正的站立起来。
原生命批评作为一种理想的批评的方式,同时也是现代诗歌对于批评的最终要求。现 代诗歌对于人的存在、生存的关怀,使得它更注重于深层的生命原动力、生命意识的开 掘。这种开掘和体察具有个体的深邃性与感受的独特性,批评者若没有这种深邃的体察 ,或不懂得这种体察及表达的独异性,就根本无法接近诗,也就无法进入批评。批评是 一种选择。但对于现代诗,勿宁说更应该是诗在选择批评者。诗的前进,使得传统批评 陷于空前的被动与困惑。批评不再是一种既定模式的简单操作,决非那么省力。它不是 现成价值尺度的随意搬用,而是价值尺度的不断摧毁、探寻与重建。摆在一代批评者面 前的现代诗歌批评,无疑是一个较为严峻的课题,它既诱人,又更具挑战性。
我相信生命批评的有效性。因为一切的艺术,总是以人为中心的,从人出发,并以人 为旨归的。进入艺术,就是进入生命。诗是生命的吁求与外化,诗的感性与智性融合的 性质,与生命现象、生命结构、生命需要、生命发展天然地一致。生命的本质就是诗性 ,诗性也就是生命性。因此生命批评是一种最能进入艺术堂奥与生命深处的批评立场和 策略。
原生命批评因为是关于生命现象、生命形式的批评,必然表现为对生命主体的重视, 在批评过程中将涉及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双方。因此它将体现为对文学主体性的寻觅与 重构。这是一个批评的互动过程,通过互动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建构。由于现代主义文学 是一种对于人的主体性的根本怀疑、对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的焦虑为内核的文学,个人化 写作也借助对潜意识、本能、欲望、隐秘心理的文本叙述,进一步验证了这种现实生存 的普遍危机感,而原生命批评对这种生命存在状态,不只在于简单揭示与还原,更在于 突破与超越,因此原生命批评既拥有感性体悟的灵气,又带有了形而上精神超越的气质 ,这就给文本意义的揭示提供了坚实的根柢及进一步阐释的可能性。
生命批评,或原生命批评,其学术品性与特征可概括为:体验性,深层性,开放性。 体验性,可保证批评者对作品内质的准确把握,而不是隔靴搔痒、主观臆测;深层性使 批评者能超越表层描述,透视作品内在意蕴,而避免在表象间滑行;开放性则是由生命 现象的多样性、无限可能性决定的,它要求批评者突破陈规与封闭,永远以创新开拓的 精神与眼光审视诗的世界,并以自身的理论建构推动诗的前行。由此看来,原生命批评 应当是适合所有的流派和艺术,而对于个人化写作当然更为有效。
也许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混沌无序。我们期待评坛有巨人产生,但时代却未必向你提 供巨人。面对混沌纷乱的诗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出“诗评的纯粹”这一命题。诗需要 纯粹,诗评呢?似乎更为需要。诗歌批评跟诗歌创作一样,需要坚韧、非功利,需要全 身心地投入诗歌状态。诗评的纯粹还要与责任感、使命感相联结,使批评向着艺术与科 学的健全轨道前进。诗评界应着手建立这一高级精神活动的独立学科——诗歌批评学。 这,不论是为了总结、反思,还是为了以后的批评,都是十分必需的。
诗评虽然仍将疲弱,但它将在其本质规定性中获得亢奋,在无序动荡中寻回生机和希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