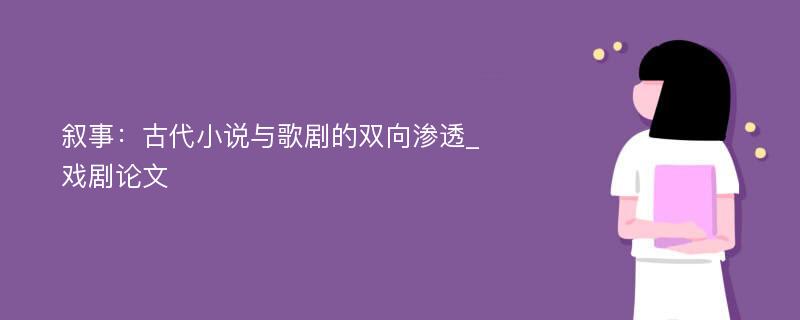
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双向论文,说与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求同存异:中国文学艺术的分类传统
当本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1898-1956)受到中国戏曲艺术的启发,提出“叙事体戏剧”(亦译“史诗戏剧”)的术语时,人们并未曾认识到,他不仅仅是大胆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戏剧样式和戏剧体系,而且隐约地洞见到叙事性在中国戏曲中比在西方戏剧传统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西方的文学艺术分类传统遵循“辨同求异”的基本思路,从亚里斯多德以后,总是以叙事性和戏剧性作为史诗(后世还包括小说)和戏剧诗文类区别的“楚河汉界”。与此判然而别,受到中国“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分类传统中,戏曲和叙事诗、史传、小说等叙事文学虽然从表面上看是截然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却享有共同的内在的艺术特性,即叙事性。因此,在作艺术样式历史演进的通观时,人们特别注意各种艺术样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中曾对杂剧源流作过这样的描述:“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公(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元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可见,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如果用以抒情性为本质特征的诗歌作为参照系的话,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三者是同源异流的,叙事性是它们共同的血缘纽带。即便在作文学艺术样式的横向比较时,人们不是也往往偏好于从大处着眼,超越“末异”,直指“本同”吗?直到晚清蒋瑞藻作《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续编》时,还将戏曲、小说、弹词等混为一谈,并指出:“戏剧与小说,异流同源,殊途同归者也。”(《小说考证》附录《戏剧考证》)
不仅如此,作为抒情文学本质属性的抒情性,作为叙事文学本质属性的叙事性,以及作为戏剧文学本质属性的戏剧性,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传统中几乎从来就是浑然不分、“和而不同”的,文体的个性特征常常在文学的共性特征中和平共处,甚至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结果,是否会丧失某一文体的个性特征呢?不是,恰恰相反,某一文体创造性地吸收了他种文体的个性特征,反而大大地丰富了、并且鲜明地突显了自身的个性特征。换句话说,在某一文体中,他种文体个性特征的渗入,不是取代了或淹没了该文体的个性特征,而是被该文体的个性特征所包容或同化了。因此,中国古代戏曲虽是不折不扣的剧诗,而且还以叙事作为其基本的结构基础,但在本质上依然是戏剧而不是别的什么,依然以戏剧性作为其本质属性,抒情性和叙事性仅是它的辅助属性;只不过戏曲的戏剧性与西方戏剧的所谓戏剧性不同,它渗透着浓厚的抒情性和叙事性。
正是在各种文体长时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过程中,无论是抒情性、叙事性,还是戏剧性,它们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抒情性以抒情式风格为主,同时包容了叙事式风格和戏剧式风格;叙事性以叙事式风格为主,同时包容了抒情式风格和戏剧式风格;戏剧性以戏剧式风格为主,同时也包容了抒情式风格和叙事式风格①。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传统中,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这些基本概念,无疑应有不同于西方文学艺术传统的审美内涵。
本文仅以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这一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三方面分析小说与戏曲的叙事特性,并探讨这一叙事特性的审美内涵及其文化基因。
叙事时间:直线式与立体式的组合
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他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②一般地说,中国古代小说大都采用这种体现时间一维性的直线式的叙事方法,在叙事时间上以故事的顺叙为主。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小说中全然排斥插叙、追叙、预叙等叙事方法,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插叙、追叙、预叙等倒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它们的出现仅仅是作为整体的顺叙框架中的点缀或装饰,而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叙事时间的一维性。作家在叙述故事时,决不随意打断故事时间的顺向流走的大动脉,而是在顺应故事时间大动脉的同时,拓展脉流的四通八达。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故事时间的大动脉(如事件的起承转合,人物的生老病死)始终制约着叙述时间的顺向演进,由此构成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也由此造就了长篇小说的章回衔接。
这种叙事时间的一维性,同样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突出特征。西方古典戏剧总是严格遵循演员的表演时间与所表演的故事时间大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形成了大量使用追叙、插叙的“回顾式”戏剧结构。这种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作频繁回顾的艺术构思特点,使西方戏剧习惯于采用二维性的立体式的叙事方法:过去的事件在现在的事件的时间推进中不断被插入、“发现”。与此截然不同,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故事时间的跨度通常不受演出时间的限制,这就使戏曲家通常采用流水式的分场结构形式,因此在叙事时间整体上总是以故事的顺叙为主,“一出接一出,一人顶一人,务使承上接下,血脉相连”(李渔《闲情偶寄》卷之一《词曲部·词采第二·重机趣》)。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叙事时间的顺叙性,造就了中国古代戏曲的流水式分场结构形式。所以,中国古代的戏曲结构和小说结构,从本质来看,是貌异神合的,都是具有叙事时间顺叙性的直线式的叙事结构。
在整体的顺叙框架中,当需要表现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生活际遇时,中国古代作家习惯于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艺术方式,先叙述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人物的故事,然后叙述同一时间另一地点、另一人物的故事。这时候,虽然几个齐头并进的故事时间段被转换成一一轮流接替的叙述次序,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立体式的叙述时间,但是故事时间的顺向流走的大动脉并没有因此而打断,不过仅仅分流成若干个小动脉,在整体上仍然是顺叙演进的。
这种叙述时间的分头并进,这种故事时间段的轮流接替,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呈现为屡见不鲜的双线并进结构。为了表现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情节的复杂曲折,为了分配角色的劳逸均衡,戏曲故事的叙述往往随着主要人物(即男、女主角)的活动而分别展开,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故事时间顺向流走的大动脉的分流,从而构成双线并进的戏曲结构。
双线并进结构,在早期的戏曲作品如南戏《张协状元》中已露端倪。然而有意识地构成双线并进结构,还应从元末戏曲家高明的南戏《琵琶记》说起。《琵琶记》在戏剧情节的开端之后不久,男主角蔡伯喈和女主角赵五娘的活动就形成双线并进、相互映照之势:一边是赵五娘忆夫临妆感叹,一边是蔡伯喈夺魁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请粮被抢,一边是蔡伯喈洞房花烛;演完赵五娘背着公婆糟糠自厌,接演蔡伯喈当着牛氏弹琴诉怨;演完赵五娘自捧土埋葬公婆,接演蔡伯喈偕牛氏赏月饮酒;……。吕天成《曲品》称道:“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
这种交错并进的叙事结构,让反差鲜明的戏剧场面先后并置,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也造成了独特的象征意蕴。因为在先后承续的叙事序列之间,戏剧情节、戏剧场面作为艺术符号,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地淡化,象征关系则相对地突显:叙事序列之所以先后承续、交替出现,不仅仅由故事情节自身的因果关系所决定,更重要的是由人物的情绪和感受所决定。作家力图借助于同一时间段中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张力,获得强烈的审美效果。
因此,双线并进结构受到许多戏曲家和小说家的青睐。尤其是在才子佳人戏曲小说中,或者是才子与佳人的悲欢离合,或者是一位才子与若干位佳人的风流遇合,大都采用双线并进,交互叙述的方法,分别展开,在直线式的顺叙框架中嵌入立体式的叙事片断。这种直线式和立体式的有机组合,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在叙事时间上的突出特征。
叙事视角: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转换
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从某一角度选择、审视、叙述故事。一般认为,它表现为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叙述者是大于人物,是等于人物,还是小于人物?叙述者大于人物,一般称“全知叙事”;叙述者等于或小于人物,一般称“限知叙事”。
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小说采用的是绝对的全知叙述,即叙述者大于人物,对人物外在世界、人物本身和人物内心世界都无所不知,毫无限制地加以叙述。这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全知叙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确具有普遍意义。但也正因如此,仅仅说明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视角上具有全知叙述的特点,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像说中国人的特点是黄皮肤、黑眼睛一样,仅仅触及的是事物的表象。问题在于,深藏于全知叙述的表象之下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更切合“叙事视角”这一概念,人们常常借用绘画理论术语,称中国古代小说所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叙事视角,从而与西方小说的“焦点透视”相区别。但是对“散点透视”的解说,历来总是语焉不详。
我同意用“散点透视”来指称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并认为所谓“散点透视”应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就“散点透视”的本质而言,它并不是一种无焦点透视,而是一种多焦点透视,如果把小说分割成一个一个的片断,那么每一个片断从表面上看几乎无不是限知叙事或称焦点透视;第二,就“散点透视”的设置而言,每一个片断即使是限知叙事,其内质却仍然是全知叙事,限知仅仅是假象,是叙述者有意假借人物来叙事,从而限制读者的视角,让它聚焦在某一点上,以造成独特的审美效果;第三,就“散点透视”的构成而言,虽然小说的每一个片断都可以是限知叙事,但在整体上却仍然是全知叙事的,换句话说,限知叙事的总和构成了全知叙事。
在无限制中的限制,在限制中的无限制,以频繁转换的限知视角构成无所不见的全知视角,这就是“散点透视”的本质特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两个不同版本的《水浒传》中的片断为例:
【例一】 容与堂本第二十七回
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那妇人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见里面跳出两个蠢汉来,先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那妇人欢喜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干东西。”把包裹缠带提了入去,都出来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妇人看了,见这两个蠢汉拖扯不动,喝在一边。
【例二】 金圣叹本第二十六回
(A)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B)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蠢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干东西。”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C)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D)只听得妇人喝道……
在【例一】中,小说家运用的是典型的全知叙事,他作为叙述者,对人物的一切几乎无所不知,无论是人物的动作或神态(如“那妇人欢喜道”),还是人物的性情(如两个“蠢汉”)。在【例二】中,小说家则有意地运用了限知叙事的方法,通过人物的感官来观察:(B)段以武松为叙述者,一连用了六个“只听得”、“听得”和“听”,把一切发生的事都从武松耳中写出;(C)段“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以下几句,视角转移到妇人身上,叙述者变为妇人;而(D)段用“只听得”打头,视角又转至武松身上。这种叙述者的轮番更迭,便构成叙事视角的频繁转换,使小说家既得以灵活地运用限知叙事,造成特殊的审美效果,又得以满足听众或读者对无所不见的全知叙事的需求。至于(A)段,采用的则显然是全知叙事,有哪一个人物能知道武松的眼睛是“虚闭”的呢?而(B)段中“飞奔出”的是两个“蠢汉”,也决非武松能“听”出来的吧?这种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互相混杂的现象,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家运用限知叙事尚属探索阶段,不免幼稚粗糙,规范不明,不如说恰恰体现出中国古代小说运用叙事视角的基本特点。
据《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的落款,金圣叹批刻《水浒传》在明崇祯十六年(1641)。而据《辛丑纪闻》,十五年后,清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金圣叹才批刻《西厢记》。但是在批改《水浒传》之前,金圣叹却的确阅读过大量的戏曲作品③。因此,金圣叹的《水浒传》改本受到了戏曲创作的影响,借鉴了戏曲文学的某些叙事特点,应该是无庸置疑的。戏曲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叙述者只能化身为人物出现在戏曲作品中,因此戏曲的叙事视角似乎只能是不折不扣的限知叙事。在戏曲舞台上,绝对地说,只能表现人物的所见、所闻或所感,而决不容许任何一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冒然闯入,横加干预。到了明清之际,小说家开始有意识地在某些叙事片断中或多或少地采用人物的限知叙事,恐怕即受到戏曲创作的启发。
在戏曲舞台上,戏曲家还常常假借旁观者来描绘场上人物的外貌、动作和神态,这时,这个旁观者就成了叙述者。《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红娘捎来张生的简帖,故意搁在妆盒上,莺莺梳妆时,情不自禁地打开观看。红娘描绘莺莺的情状道:
晚妆残,乌云軃,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这也许就是小说家运用“只听”、“只见”之类的叙事手法,来构成限知视角的蓝本吧?
然而,即使在戏曲中,限知叙事也仍然未能贯彻到底。如果细加观察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在戏曲中,叙事视角从限知到全知的转移,虽然颇为隐蔽,但却相当自如。戏曲中叙述者的化身为人物,从来就不是等于人物,更不是小于人物,在实质上仍然是大于人物的。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戏曲中的人物常常多多少少地代戏曲家言。因此人物可以看到他不可能看到的事,可以说出他不可能说出的话,于是叙述者虽在表面上等于人物,但人物本应具有的叙事视角的限制,却在无形中化为乌有了。
例如在关汉卿的杂剧剧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物一出场时就有大段的插曲式的自我表白,如《救风尘》第一折赵盼儿对妓妇婚姻的清醒的思考,《望江亭》第一折谭记儿对寡妇生活的深婉的悲叹,《鲁斋郎》的第一折张珪对“衠一片害人心”的恶吏的揭露,《诈妮子》第一折燕燕对那等“不做人的婆娘”讥笑,《西蜀梦》第四折张飞对“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的怨愤,《单刀会》第四折关羽对“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的感慨,等等。这种插曲式的自我表白,虽然也大多符合人物各自的身份和经历,但却显然更多地蕴含着作家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是作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的产物。在这里,我们不是同样看到了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潜相转换吗?
叙事话语:叙事体和代言体的杂交
从叙事话语的角度来看,小说是叙事体,戏剧是代言体,二者的界线原本应该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只要深入解剖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我们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困惑:叙事体和代言体的区别,果真是泾渭分明的吗?
首先我们看到,叙事体在戏曲中被大量地采用。这不仅表现在总体的艺术构思上,古代戏曲家往往追求“以曲为史”的审美境界,“聊将史笔写家门”(蒋士铨《空谷香》卷末收场诗),因而总是以历史著作为参照和蓝本来创作戏曲作品。而且,在具体的叙事话语中,戏曲也大量采用叙事体。例如,戏曲情节中有些不便于或不适于在舞台上直接演出的场面,作家就有意地以暗场处理,而以次要人物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性语言来加以叙述。如元人尚仲贤《柳毅传书》第二折,以电母的大段唱白,来叙述钱塘火龙与泾河小龙的一场激烈的厮杀。清人洪昇《长生殿》第二十二出《窥浴》,写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骊山共浴汤池,就让两位宫女“窥浴”,借她们的唱词来加以叙述。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代言体,因为都是场上人物的多少带有一点性格化的语言,但实质上却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叙述体。这种“假代言”的叙事体,是从说唱文学中由说唱者讲说故事的方式衍化而来的,只不过叙述者由说唱者蜕变为居中的次要人物罢了。
叙事体被戏曲大量采用,赋予戏曲以鲜明的叙事式风格。当然,在戏曲中,叙事体的采用是被戏剧化的。这首先在于,戏曲作品总是在戏剧冲突中叙事的,决不脱离戏剧冲突作单纯的叙事。例如,《长生殿·窥浴》中两位宫女的叙事,就是围绕着杨玉环的得宠和六宫粉黛的失宠这一戏剧冲突展开的,正所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
叙事体的戏剧化还表现为,戏曲总是借人物的所思、所感、所言、所行来叙事的,因此是主观化极强的叙事话语。戏曲家“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王骥德《曲律·论引子》)。例如,戏曲人物上场,总要有一段自我介绍,并对以往发生的事情(包括戏剧情节开端之前的事情和前几场发生过的事情)作一番叙述。有时候,这种叙述似乎显得相当累赘。如《窦娥冤》第一折,蔡婆婆先上场,叙述了一番自从买下窦娥为童养媳以来十三年间发生的事情;紧接着窦娥上场,对大致相同的事情又作了一番叙述。但是细加辨析,其中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蔡婆婆所言,包含着对生活困难的忧虑;而窦娥所言,却更多对自身命运的感伤。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不注重静态的描述,而偏好动态的描述,这一点同西方小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小说中,作家的笔触总是围绕着人物的言谈举止而展开,人物的性格心理、相互关系、生活环境等等,都是经由对人物的言行、对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的动态描述加以表现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这种民族特色,说穿了,体现出一种戏剧式的风格。在小说中本应位居一线的纯客观的描述,反而退居二线,由涂染着人物主观色彩的描述取代了它的位置。因此,优秀的古代小说常常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充满着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清人李渔曾称自己的小说为“无声戏”,在他看来,戏曲说是有声的小说,小说则是无声的戏曲,二者艺术媒介有异,精神内蕴相通。时人“素轩”在李渔《回文传》小说第二卷后评道:“稗官为传奇蓝本。”这也可以代表李渔的看法④。古代小说之所以被大量地改编为戏曲,这显然是个重要原因。在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中,《奈何天》、《凰求凤》、《比目鱼》、《巧团圆》四种传奇,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小说改编的。
而且,代言体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家乐于采用的表现方式。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说:“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这种区别,促使古代小说家自觉地借鉴和学习戏曲的代言体,力图使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适如其人”,切合每个人物独特的身份,表现每个人物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并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鲁迅所说的:“《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同说话看出人来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这一点论者甚多,此处不拟赘言。
至于小说中人物心理描写的发展,也同戏曲的代言体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戏曲家经常运用人物的独白和旁白,来披露人物内心世界,展示人物内心中鲜为人知也难为人知的隐秘。如《西厢记》中,崔莺莺一上场就唱道:“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青春易逝的闲愁和幽怨,溢于言表。而《长亭送别》一出的唱词,更几乎都是崔莺莺的独白和旁白。戏曲作品习用的这种人物的独白和旁白,受到古代小说家的普遍青睐,成为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一种主要方式。
不过,小说中人物独白和旁白的前后或中间,常常有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随意介入,构成代言和叙述的混合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黛玉和宝玉的争吵的片段,我们用省略的形式引录如下:
(A)即如此刻,宝玉心内想的是:“……”(B)宝玉是这个意思,只口里说不出来。(C)那黛玉心里想著:“……”(D)看来两人原本是一个心,却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E)那宝玉心中又想着:“……”黛玉心里又想着:“……”(F)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如果删去(D)、(F),仅存(A)、(C)、(E)中引号内的部分,那么显而易见,这与戏曲中用上场人物的旁白来披露内心世界是如出一辙的。至于(A)、(C)、(E)中引号外的文字,仅仅是古代小说文体行文的需要,现代小说采用分段和标点以后,就可以省略不用了,所以是可有可无的部分。然而(B)、(D)和(F)三段,却决非可有可无,在这里,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强行介入,充当起旁观者和评论员的角色,向读者说明和评论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一来,读者既能畅游人物的内心,又能明晓其间的奥秘,岂非两全其美?
叙事性的审美内涵及其文化基因
在叙事时间上,以顺叙为主,在化立体式的故事时间为直线式的叙述时间的同时,营造独特的立体式的叙述时间;在叙事视角上,以全知视角为主,在无所限制的流动的叙事视角中灵活多变地采用限知叙事,由此构成“散点透视”;在叙事话语上,兼用叙事体和代言体,创作“曲史”和“无声戏”;——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叙事特性。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叙事性具有何种审美内涵呢?我认为,这种叙事性的审美内涵,以整体美和自然美为本,以综合美和通俗美为用。
第一,这种叙事性追求整体美。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无论是事件的展开或是人物生平的叙介,都讲究有头有尾,原委清晰,来龙去脉,历历在目,甚至一些重要的细节都要求明明白白地叙述清楚。当然,这种整体美,就所叙之事而言,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从宇宙的发生写到宇宙的毁灭,也往往没有必要从人物的出生写到人物的死亡;但是就所选取的某一事件而言,整体美的审美需要就要求作家展示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纤毫无遗,滴水不漏。正因为如此,悲剧故事必以死亡为结局,喜剧故事必以团圆为归宿;《三国演义》从黄巾起义写到三家归晋,《水浒传》从“洪太尉误走妖魔”写到“宋公明神聚蓼儿洼”;……。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小说戏曲的增删,“腰斩”者少,而“续貂”者多。
第二,这种叙事性强调自然美。自然美即追求逼真自然,指的是艺术世界不仅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无所不包,变化万千,而且像大自然造物一样,宛然似真,栩栩如生,做到“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王世贞《艺苑卮言》)。所以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评点中,诸如“历历如绘”、“宛肖其人”、“情状逼真”、“化工肖物”、“传神写照”等评语,触处皆是。
第三,这种叙事性崇尚综合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各种体裁,如志怪、传奇、话本、章回,如杂剧、戏文、传奇等,在文体形式和叙事方法上几乎都是“无体不备”具有很高的综合度。孔尚任对传奇戏曲的评述可作代表:
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桃花扇小引》)传奇戏曲不但包容了各种文体形式,而且综合了各种文体形式的艺术方法和审美特征。传奇戏曲是如此,小说、说唱文学甚至史传杂录,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四,通俗美也是小说戏曲突出的审美品格,小说“以通俗为义”(陈继儒《唐书志传·序》),要求“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戏曲也以通俗为美,“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言明说”(李渔《闲情偶寄》)。要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叙事性,总是明确地要求把接受主体(包括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要放在第一位。无论是何种艺术方法,只要有助于或有利于适合、满足或提高接受主体的审美需要的,都照用不误,没有任何限制。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小说和戏曲都同样源于说故事方式。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叙事特性的审美内涵,与源远流长的说故事方式的基本特性有关。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式,概而言之,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史传⑤,二是民间艺术(包括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等)。这两种主要形式共同地体现了中国人在说故事的审美过程中表达与接受的一些基本特性。由于小说戏曲的真正成熟,是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审美趣味渗透的结果,所以对小说戏曲影响更为深重的说故事方式,应该说是史传⑥。例如,史传的任务在于“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认识人物的全貌(《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为整体美;史传追求“实录”,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是为自然美;史传的文章要求“辞多”(《仪礼·聘记》),“捷敏辨洽,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韩非子·难言》),是为综合美;如此等等。
的确,小说戏曲作为一种说故事的文学艺术样式,必然受到定型的传统说故事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但这并没说到问题的点子上。人们还可以追问:传统的说故事方式又是何以成为定型的呢?传统的说故事方式所体现的叙事性,其审美内涵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我认为,这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汉语的语言特性是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近年来时贤们作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普遍地认为其基本模式是“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传统思维方式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易传》提出“观其会通”,即观察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惠施宣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篇》),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强调“天地存亡之为一体”,认为人由生而壮、而老、而死是一个自然过程;汉宋儒家宣扬“天人合一”,也主要是肯定人与天地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传统思维方式也强调辩证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孔子提出“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周易大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吕氏春秋·大乐》说:“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提出“相反相成”的观点。⑦小说戏曲在叙事方法上崇尚整体美、综合美、自然美、通俗美,岂不是可以从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思维方式中溯源正本吗?
与思维方式的研究相比较,对汉语语言特性的研究至今仍相当薄弱,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即与世界上的其他语种相比较,汉语的语法构成和表达方式的确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性。这种独一无二的语法构成和表达方式,不能不对传统的说故事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例如,近年来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说明,因为汉语句子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所以汉语的句式结构,通常是以时序(包括实际动作发生次序和逻辑上动作应有的因果次序)展开的流水句,将迭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参见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汉语流水式的句式结构特点,体现了汉族人语言思维具有逻辑天籁的“因果”顺序的特点,正如启功先生所说的:汉语的文章“以‘文从字顺’为主,上管下多,下管上的极少。主要都是‘因’在前,‘果’在后。”(启功《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五期)这种偏好逻辑事理的因果联系的语言特性,显然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在叙事时间上以顺叙为主的特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情节发展大多注重因果联系性,情节虽然曲折多变,但由系结到解结,主要情节线一贯到底,这种事理逻辑型的叙事时间构造,是否即以汉语流水式的句式结构为“原型”呢?
又如,汉语的人称代词没有明显的单数与复数的区别,在古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大量地省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席)。而且,“古汉语句中主、宾的作用不一定由一个词来负担,有许多在环境中衬托出来的。篇题、主题、主语,是三种东西,但在诗歌、骈文中,它们常常互相借用,密不可分。有时一段的主题即是这段中各句的主语,甚至一篇的题目即是全篇各句的主语。”(启功《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汉语语句构造的这些特点,不就使得叙事文中叙事视角的转移可以随心所欲、流转自如吗?
有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汉语的语言特性与古代叙事文学的叙事特性之间的关系,古人和前人已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一方面还有待于将它们作系统的整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为此,笔者将另著专文论述。
注释:
①关于三大风格的基本特点,可参看[瑞士]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兹维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朱毅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③参见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评语:“吾观元人杂剧,每一篇为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独唱,而同场诸人仅以科白从旁挑动承接之。……自杂剧之法坏,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余折,一折之辞乃有数人同唱。于是辞繁节促,比于蛙鼓;名断字歇,有如病夫。……稗官亦然。”
④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认为:“素轩先生或者就是笠翁先生。”可备一说。
⑤笔者以“史传”概称历史文章,承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之说。
⑥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拙著《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第六章《明清文人传奇的文体特性》第五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2页。
⑦参见张岱年《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概说》,张岱年等著《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