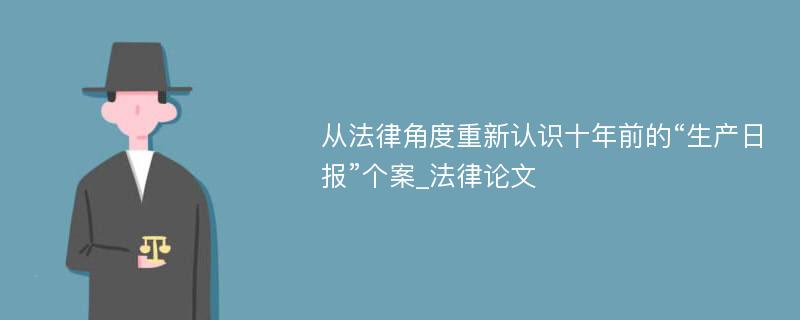
从法律角度对十年前“生产日报单案”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十年前论文,角度论文,日报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山西档案》编辑部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就山西河津试验化工厂生产日报单被偷一案展开了一场讨论。这次讨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修订的前夕进行的,从长远来看,它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界学法、普法起了推动作用。伴随着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相继修订,十年后,我们认为有必要从新的法律视角对该案件进行解析。
一、案情回顾及当时讨论概况
(一)案情回顾
1994年4月18日,陕西省西安化工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赵某、工程师楼某、助理工程师李某3人,持西安标准件厂的介绍信到山西河津市试验化工厂,谎称是该厂的老用户,趁中午工人下班之际,进厂偷偷抄录了生产日报单上的内容和数据。之后他们认为所取材料远远不够,又去撕下6张有关该厂生产的钢铁发黑剂的原料名称、剂量等项目的生产日报单,并试图收买该厂的检验员柴某……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该厂上下的注意,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破之后,公安和检察机关深感棘手,人赃俱获,盗窃行为确凿无疑,但偷几张纸该当何罪?”[1]为此,市政法委多次召集公安、检察院负责人商讨,但无法定论。后来经过山西省科委、太原工业大学专家的鉴定,认为这些数据是技术核心成果之后,河津市公安局才向市检察院报捕。河津市检察院又对此案进行多次讨论,也还无法定论,案情进一步上报运城地区分院。运城地区及山西省检察院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并对此案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从河津市到运城乃至山西省的检察部门,对该案件一直没有定论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虽然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盗窃,但此案是全山西省首案,既无法可依,又无司法实践。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客观决定的。
(二)当时档案界讨论概况
十年前,学术界围绕此案件展开讨论的焦点在于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档案法》的缺陷及盗窃行为的法律认定等。
1、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
在讨论中,有些学者认为生产日报单不是档案,因为归档对文件转化为档案至关重要。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荣声。他认为“文件需经过立卷归档的程序才能转化为档案,对档案工作者来说,这是最一般的常识。车间的生产日报单不可能经过立卷归档,当然不能算是档案,充其量只能算是档案的前身材料”。[2]有些学者认为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还值得商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邓绍兴。他认为“生产日报单在被盗窃时,尚处文件的制作或初期承办阶段,即文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上述生产日报单无论其今后有无保存价值或是否需要保存在车间、还是厂部档案室甚至进档案馆,但是被盗时只能称之为‘文件的前档案阶段’”。[3]在当时的情况下,詹春红和陈永生则认为“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对此案的定案没有直接影响”。[4]
2、《档案法》的缺陷和法律的认定
本次讨论关注的另外一个热点,就是《档案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相关法律的配套衔接还不完善。有些学者认为造成山西检察部门对此案感到棘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档案法》与《刑法》不能实现衔接或衔接不紧密。荣声指出,“《档案法》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也是一大缺陷,对构成犯罪的惩处,既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规定,也没有与《刑法》实现衔接”。[5]邓绍兴认为“虽然有《刑法》第一百条、第一百六十条,可以引用,但相互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有一定的空隙,难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给查处此类案件带来困难。”[6]詹春红和陈永生则认为“《档案法》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不管犯什么罪,都得按照《刑法》的规定来定罪量刑”。[7]在当时的法制条件下,这种观点客观而冷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相关法律修订后对该案的再认识
随着我国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十年之后,我们对案件的认识必然会有所改变。1996年7月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对《档案法》进行了修正;1997年10月1日,我国新修订的《刑法》正式实施。新刑法作了多方面的重大改变,其中之一是盗窃罪一条更加细化,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新刑法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而且同时为该案件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决出口。
(一)从窃取国有档案的角度来看
1、案件定性的关键发生了变化
根据新修订的《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这一新规定来看,判定赵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窃取国有档案罪,其前提主要是看他们所窃取的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因此,此时讨论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对案件的定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它是档案,那么该行为是一种窃取国有档案的犯罪行为无疑。而根据《档案法》第二十四条,其所列举的应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八种档案违法行为中,并没有涉及偷盗国有档案的行为应该追究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但是新《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就改变了这种情况。所以,只要判定生产日报单是国有档案,赵某等的行为就可以依照《刑法》定罪,而不论其偷窃的生产日报单的价值大小。
但本文无意于探讨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只是想说明在新修订《刑法》的规定之下,本来对案件定性没有实质意义的“生产日报单是不是档案”的讨论变得至关重要。这种变化说明档案犯罪行为日益得到国家法律的重视,这是法制建设的进步,对档案工作而言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档案法规建设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法规的完善与发展,不仅是《档案法》、档案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本身的完善与发展,而且也是与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协调。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新修订的《刑法》,对《档案法》中所规定的违法行为有重点地作了选择性规定,从而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档案犯罪问题奠定了基础。《档案法》与《刑法》等其他法律的协调发展,对于我国档案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新《刑法》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档案犯罪行为的明确规定,这对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档案法》与《刑法》的衔接
荣声和邓绍兴在文中分别谈到了《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档案法》需要与《刑法》衔接,具有先见之明,两法修订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十年前两法并不是完全没有衔接,只是没有1997年修订后的两法衔接的那么严密。
(1)其他法律与《刑法》衔接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对刑法作总体援用和对具体条款作单独援用。《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档案法》与《刑法》的衔接是通过《档案法》中的这句话实现了对刑法的总体援用,这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档案法》已经实现了与《刑法》的衔接。这种方式固然有着其操作性差的不足,但这种援用方式的采用有着它客观的历史原因,并非档案法的错误。我国刑法制定于1979年,1980年1月1日实施,而档案法是1988年正式实施的,1979年的刑法内容不可能完全照顾到其后颁布的法律。因此八十年代制定实施的法律大多存在着与刑法衔接不够紧密的现象,这是历史原因所致,并不能认为这是档案法单方面的缺陷。
(2)在1996年《档案法》修订之后,1997年我国《刑法》也作了修订。修订后的《刑法》大大地改善了它与八十年代出台的法律的衔接问题。《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明文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改变了以前《档案法》和《刑法》之间衔接松散的问题,增强了法律的操作性,同时也为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199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发生了一起盗窃国有档案的案件:巴里坤县法院干部兰成仕、李兆斌由于对该院领导胡某某心存不满,他们利用该院档案工作达标之际,盗出刑事案卷25册、执行案卷2册,并栽赃于胡某某。案破之后,哈密市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17日依照《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做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兰成仕犯窃取国有档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被告人李兆斌犯窃取国有档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从这件案件可以看出,过去那种“法律规定几乎没有,而司法解释又过于笼统”[8]的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了。
(二)从侵犯商业秘密的角度来看
1、商业秘密的定义及构成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就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由此可以看出,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个要件:一、该信息必须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二、该信息必须是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信息;三、该信息必须具有实用性(即该信息必须具有能够实际使用的价值);四、该信息必须是经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五、该信息必须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据此,生产日报单中所承载的信息应属于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就像河津试验化工厂厂长柴倬所担心的那样,“逐级上报也好,取保候审也好,那是司法部门的事。现在最令人担心和焦心的问题是,我们厂的技术秘密能否保住”。[9]因此,我们还可以从侵犯商业秘密的角度来认识这种盗窃行为。
2、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及法律规定
侵犯商业秘密罪所应具备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有被侵犯的有效商业秘密存在,二是未经权利人许可,三是以损害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四是有法定的侵权行为,且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方面是侵犯了权利人的专有专用权,另一方面是侵犯了权利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资本和支柱。对此,我国法律也采取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案件性质的判定
此案中,可能有争议的是赵某等人的盗窃行为被及时制止,该行为是否已经给河津市试验化工厂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直接判定生产日报单的价值,从而推定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是很困难的。正如陈永生所说,“被盗窃的生产日报单的价值,就在于上面所记载的河津试验化工厂的技术秘密,而这种技术秘密的价值究竟是多少,显然是不容易确定的。”[10]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赵某等人的行为已经给河津试验化工厂造成了一种无形和间接损失,使工厂的竞争优势遭到严重的威胁。案例中谈到“山西省科委、太原工业大学专家的意见:‘钢铁发黑剂’技术是重要的科技成果,从所盗资料看,它是生产现场的操作记录,包括原料配比、加料数量、实际操作等参数,这些数据是化工生产中的技术关键,是技术成果的核心,一旦掌握这些资料,便可仿制生产”。[11]可见这些参数是该技术核心的商业秘密,而实施盗窃的三人均是该技术的内行,由于当时无法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他们回去后如果将记于大脑中的数据应用于生产或进行成果转让,必然会给该厂的生产和销售带来直接的巨大损失。这种对工厂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的威胁随着三人返回西安将随时存在,这也是化工厂的人最为担心和焦虑的。
因此,生产日报单的追回与否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商业秘密可能已经进入盗窃者的大脑而使化工厂对该商业秘密的专有永远丧失。这种行为的潜在后果是严重的,应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根据《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应的条款予以处罚。
此案虽然已过去十余载,但留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尤其是在日后企业档案的保管中,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好反窃密工作。“亡羊补牢,搞好技术保密,尤为必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