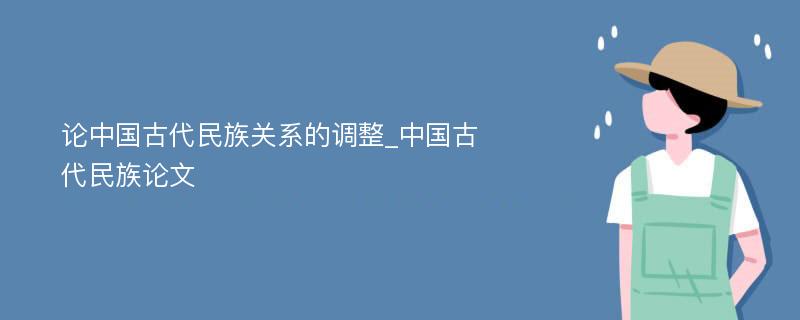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调整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3)06-0033-05
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族关系形态。从总体上来说,历史上民族关系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民族群体动态平衡过程。由于阶级社会的这一决定性条件,民族关系的调整核心实际上是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利益的调整和关系的调适,而大量的各民族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并不在各朝代政策和制度的调整之列,属于地缘、经济等民间需求的自然结果,只不过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借助了王朝政策的力量。
在古代民族关系动态调整的漫长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相互联系和日益接近;既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日益形成着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点;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1]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式是什么?这些方式给中国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怎样的影响?本文在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
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民族关系的调整方式也因此而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宏观可分为制度性调整、战争方式调整两大手段,而且都是以王朝为主体的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主要方式。存在于民间的自然调整具有自发性,但由于封建王朝特有的一些制度限定了其规模,所以这种调整实际上与王朝的总体调整密切相关,缺乏独立性。
一、温和而有长效的调整方式——民族关系的制度性调整
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调整首要方式,也是在民族关系较为稳固条件下的调整方式。所谓制度性的调整就是民族关系的调整纳入了王朝社会管理体制之内,并且使民族关系的调整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府行为。或借助于特定行政机构和机构内人员的活动取得结果,或对调整对象施以独特的管理,从而缓解或解决统治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这一方式的特点就是温和、经济,具有长期效果。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与其后的商周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虽然这一历史时期相关资料缺乏,我们难以掌握当时的历史全貌,但是前人的研究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专事民族事务的朝官,如周有“大行人”掌管接待远方宾客,有“象胥”掌管“异国”来使的语言通译等。可以说,民族关系的制度性调整早已存在。当然,地缘关系对此时的民族关系状况会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受到交通的极大限制。
秦汉时期,汉民族——多个夷夏民族的融合体诞生。由于其有着较为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发展整体上表现出先进性。其所建立的王朝成为本区域内具有强大实力的国家,这使之有能力全面调整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秦朝将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民族划入一定的行政区域,史称“道”,或者“属邦”,但是具体的管理方式史籍所记不详。由于汉承秦制,其机构设置及运转应与秦有相同之处,而且汉的国力也使之对周边民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汉时仍然有“道”的地方设置,同时还有“属国”,汉的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职,但属国的管理则“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最为重要的是汉初中央政府中设立了专门管理属国事务的“典属国”机构,后归并入大鸿胪。这表明至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诞生的重要历史时期,调整民族关系的行政制度已经初步建成,一方面存在着对行政区域的管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中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及其职责得以确定。
就中央机构而言,三国至北魏各政权都设有“大鸿胪”的机构,只有梁改称“鸿胪寺”,后周设“宾部”。隋则依梁称。唐初也设“鸿胪寺”,中间曾改称“同文寺”、“司宾寺”,至中宗时期又恢复原称。宋朝也设鸿胪寺,至南宋则由礼部来管理此项事务,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政权如辽、金,则设部族节度使等职。元朝则未在中央设立鸿胪寺,而是将此项事务归于礼部的“侍仪司”、“会同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都护府”管理。明朝恢复设“鸿胪寺”。至清朝则专设“理藩院”,统一调整境内各民族的关系。
虽然各朝代对其所设机构各有称谓,具体职责有些区别,但是中心任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按照民族关系调整的总体设计,执行一套既定规则。如唐朝的鸿胪寺,据《旧唐书·职官志三》所载:“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而其下所设的典客署则掌“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并负责“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焉。辨其等位,供其职事”等。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中央政权所设的民族关系调整机构,其职责就是针对周边民族的上层,或者说是统治阶级,通过给予一定的官职,满足其一定的经济、政治要求,攻其心而笼其意,使之顺服王朝,为王朝统治的稳定做出贡献,最终达到稳定“江山社稷”的目的。
朝代更替不断,但机构设置在职责、目的、功能等方面却保持了较高的继承性。之所以出现这一历史现象,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的现实,要求其必须不断地调适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使之处在一种平衡或趋于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观念是民族关系制度调整的灵魂。从“统一”到更大范围的“统一”是每个朝代发展实力、扩张势力的核心动力。因此,从秦至汉,从隋唐到宋元,从明至清,在两千年的王朝发展过程中,统一一次次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关系调整的制度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完善。尽管王朝非一姓所建,甚至非同一民族所建,但是都追求一个目标——统一,统一带来的物质、军事乃至精神上的满足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央政府对统一目标的追求,因此,统一的国家观念渗透于各朝各代,为着统一的实现,也为着统一的维护,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也就成了各朝各代制度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根源,也是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结果。
在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中,中央王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管理民族地区事务的,特别是对那些较为偏远的民族地区,而是“存其国号”,“各依本国之俗”。这一思想原则贯穿了从汉到清各王朝对民族地区事务管理和民族关系调整的过程,正是每一个王朝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固,开创性地运用了这一基本思想,从而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又对各具体的地区、具体的民族,采取不相同的具体的措施。如唐朝对所属民族地区实行“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或“羁縻诸州”,而元朝除了以统一的行政区域来管理其他民族的事务,还对边远的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制度,如对西藏在中央由总制院(宣政院)来管理,其下则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在云南诸路行省设立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等等。明朝为了有效地统治南方各民族,实行了土司制度、土流合治,建立军事卫所,推行屯田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存在说明:一方面这些制度是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在统一多民族的古代中国,民族地区在行政上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在中央王朝调整民族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中,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互市、贡纳与赏赐。自汉唐以来,互市就成为中原王朝与民族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如唐与回纥的马绢贸易,明政府与蒙、藏的茶马贸易。在互市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畜产品和农业产品及手工产品的交流。贡纳不仅是一种政治交好的表示,对双方而言又是一种物质的满足。岁时朝贡是双方关系稳定的表示,同时,对中原王朝政治地位的认可只是边疆民族地区上层的愿望之一,由此得到物质利益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民族地区以珍奇、土特畜产品向中央王朝纳贡,同时中央王朝则要根据不同的关系和级别给予一定的赏赐,赏赐的内容除了象征权利的冠带等外,多是中原地区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朝贡的使团往往利用出使过程进行交流,回纥与唐朝的马绢贸易就是通过进贡和回赐进行的,回纥的朝贡使团大多兼做贸易,使者队伍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1]使团一出一入带来的物流相当可观。
二、残酷、激烈的调整方式——战争
任何战争都是残酷无情的,而非人类社会常态。如果说制度性的调整多行于王朝建立之初,或王朝统治已经稳固,民族关系较稳定的和平时期的话,战争则是王朝建立之初或实力强大后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时运用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民族之间的战争并不少见。以这种方式调整民族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破坏性强、破坏范围大,遗留问题多,对地缘性民族关系有根本的影响。
当然各朝代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具体情况、具体情节或性质判断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民族关系平衡状态被打破,矛盾和冲突激化。比如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著名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之间展开的战争。秦王朝在统一诸夏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增强势力,派兵北逐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河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2]随着秦朝势力的衰落,匈奴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势力渐强,当其重新活跃于秦边地区,史籍中便屡见“犯边”之词。就是说,虽然秦朝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压制和打击匈奴的发展,并试图控制之,但到了秦末汉初,匈奴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力量还是强大起来,成为中原政权的劲敌,“犯边”之战不断,汉政权在立足未稳时并未使用战争方式调节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维持了双方几十年的和平关系。
汉政权具有实力后,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双方进行了长达45年的战争,其中有战斗的年份就达23年。[2]其结果必然是使双方都有极大的物耗和人员损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害,尤其是普通人所付出的被枯燥的数字所掩盖的血泪代价。但是大规模的战争也打破了地域的阻碍,在强大的外力影响下发生了民族人口的融合。据不完全统计,在汉匈之争中,仅在武帝时期,汉兵战死、降匈奴和被杀者约14万余人,而匈奴战死、被俘和降汉的人众共约21万余人,除了战死者外,被俘人员最终结果必然是融入当地人中,成为另一个民族群体的成员。匈奴通过战争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据不完全统计,从汉初至武帝,匈奴‘杀略’和战争‘首虏’汉人共约70000人,即便其中一半为死者,尚有30000多人。贰师将70000人降匈奴。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西域戊己校尉陈良等劫略吏士男女2000余人入匈奴,……另外,还有边人奴婢,因愁苦而亡入匈奴者。这样看来,汉人通过种种渠道,被掠、降俘和亡入者,最少限度也有10万人。”[1]从这个角度而言,古代中国民族间由于战争导致的人员大交流,为其后发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客观条件。
在古代民族关系中,任何一方力量强大都可能引起战争。从中原政权的角度综合而言,中国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可分为下列类别:一是为建立统一政权而进行的征战,如秦汉时期征匈奴,战南越,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间的征战,宋辽之争,元朝降服畏兀儿、西夏,征服金朝,平大理,灭南宋等。二是为维护统一的中原政权而进行的战争。中原政权往往与北方游牧民族在经济政治利益上出现冲突,如汉与匈奴之争。中原政权又往往在其政权不稳时各类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在解决激化的民族矛盾时也会利用战争手段进行镇压,如明代对苗族起义,大藤峡瑶、壮各族人民起义,以及清朝对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的镇压等等。三是为了满足中原政权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征战。中原政权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自然视天下之“物”为己有,因此,各民族地区的贡纳是其对某些物质获得满足的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就只有选择战争方式了。比如汉武帝时期对西域大宛之战,不过是为了得到大宛的善马,竟致兴师动众,两次发兵大宛,最后取善马四十匹,与盟罢兵。[3]同样这次战争也得到了意外的效果,那就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为后世对西域的管理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如,唐朝到了贞观以后便“‘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夷’。还经常‘万里遣使。市索骏马。并度怪诊’”[4]总之,无论中原政权是否通过战争达到了目的,无论战争造成了怎样的恶果,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使双方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的手段。
三、多层次的民族关系调整——民族融合
历史上自下而上的民族关系调整并非统治阶级所设计,也非各个不同民族群体所自发,而是基于以上二种主流调整方式,在一定的地缘、经济关系、人口大量被动流动等力量的推动下而实现的。不同民族群体的下层关系得到加强,中国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布不断发生变动都有利于相互的交往,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不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实行的措施、经济交流、战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不同民族人口的大流动,人口的流动打破了某些民族在特定地域生存的状态,也打破了农业社会中特有的人口在特定地域的稳定分布,使各个不同的民族广泛地杂居共处,不断加深交往。
关于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人口的大迁移、大流动和大融合,前辈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极大成果。这些成果都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关于民族人口大流动促成了大融合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首先,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过程中一些措施的实施引起了民族人口的迁移。比如屯田和戍守,从汉朝始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屯田,以获得军队给养。汉在征大宛胜利后便自敦煌西至盐泽,在轮台、渠犁,设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成为汉在西域屯田之始,此后汉族分布区便开始向西北延伸。各朝都有屯田之制,屯田不仅使人口发生流动,也增加了物质和技术的流动。如元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10次发调汉族军民,发给他们农具、耕牛、籽种、衣着及钱钞等赴漠北屯垦,使岭北行省开垦耕田6400多亩。[1]戍守是封建王朝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为完成此任务需要相当数量的兵士开赴边疆地区,因此大量的人员得以流动。据称元统治者为此迁移了大量的蒙古、回回、畏兀儿等军户驻防,估计云南一地就驻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1]戍守、屯田使得不同民族的人口得到有组织的流动,与之相伴生的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区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最终也引发了民族的融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屯田、戍守等制度性的人口流动,从规模到作用和影响来说都是同一时期个体流动所不能达到的。
第二,战乱和社会动荡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为了达到政治统一还是为了维护政治统一都发生过一些战乱,而同时民族地区由于内部的政治纷争也造成过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其中有政权强制性的迁移,在强制性迁移中,有强制性地向中原迁移,也有强制性地迁中原之汉族到边疆民族地区。当然,也有一定的自发性迁移,其中有汉地之民众为了避乱迁移到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人口为避乱而进入中原汉族地区。如,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大多将在战争中所俘的中原地区的工匠等类人强制迁移到其政治中心,并逐渐使之融入本民族中,这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都有发生。史载,成吉思汗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迁至漠北土拉河。此外,虽然很多民族的所谓“内附”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自发的内迁行为,可是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内迁是上层对自己政治、经济利益自保的结果,而非民众的自发,匈奴各部一次次的“内附”就是这样。由于不堪内乱,南匈奴于东汉初年有四、五万人归附汉朝,移驻汉边郡,汉末又有北匈奴百余部近五十余万人归附汉朝,他们有的直接融入汉民族中,有的融入当时北方的其他民族中,如鲜卑等民族,但大多数还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融入汉民族中。
此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持续,加强了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王朝政治稳定时期,中原王朝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民族交流的中心,特别是对一些善事商业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从甘肃沿河西走廊到新疆,由四川到西南各地,由两湖到两广,由华北到东北、内蒙古,都有繁荣的商业通道。商旅来往,络绎不绝。边疆各民族的商人旅居京都的常常成千累万,内地其他各大商业市镇,也经常有他们的足迹”。[5]
总之,政治上的统一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个不同民族群体产生融合的外在环境。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开始,中原政权所直接统治的区域在不断扩大过程中发生了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的民族人口融合,而且中央政权通过一种保持间接统治的区域政治制度不变的“因其俗而治之”的方式,不断强化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度。在各个民族群体的统治阶级之间,由于存在着政治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他们通过各种制度性的措施和政治手段,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了两个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甚至出现了北魏孝文帝那样的以本民族统治者为内生推动力的汉化过程。如果没有此前出现的政治上的统一意识,没有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对从一般性的文化生活习俗到对维系其社会运行的制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
由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调整目标只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因而不仅存在阶级压迫,同时还存在着民族压迫,这是历史上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产生的根源。
〔收稿日期〕2002-12-17
标签:中国古代民族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原论文; 经济学论文; 突厥论文; 东汉论文; 东周论文; 辽朝论文; 南宋论文; 商朝论文; 史记论文; 隋朝论文; 唐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