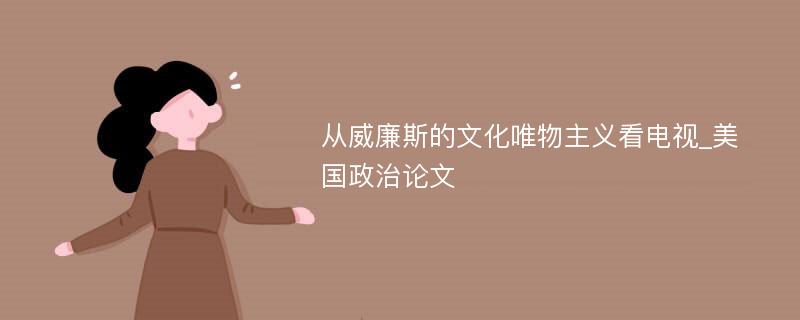
雷蒙#183;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电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唯物主义论文,雷蒙论文,威廉斯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雷蒙·威廉斯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电视经验最雄厚的一个,他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批判流行的电视理论这一理论需求,并在70年代初期萌发验证自己刚刚创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冲动,在美国独特而强烈的电视环境的激发下,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他的电视研究。他运用“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对作为技术的电视、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作为传播方式的电视进行了深入考察,为左派电视研究留下了三个不应当忘却的理论成果:一是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发展起一个完整的批判性的电视研究框架;二是在民主政治规划的基础上,使电视研究具备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三是将社会历史分析引入电视研究,有效遏制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泛滥。
1988年1月26日,往往被类比为英国的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溘然长逝,时年六十七岁。逝世前不久,他刚刚为自己的电视评论集写了一篇序言,并开始考虑对1974年出版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以下简称《电视》)一书进行修订再版①。他之所以做出这些决定,是因为他相信:尽管时间的流逝与电视技术的革新,已经使自己基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验的电视评论与电视研究仅具有相对的历史真理性,但它们却依旧值得青年一代的左派电视研究者借鉴和分享。可令人扼腕的是,猝然离世使得他无法亲自完成这一编选和修订计划。作为一种弥补,阿兰·奥康纳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文选》,雷蒙·威廉斯的儿子安德瑞在增添了一些注释后于1990年修订再版了《电视》。在雷蒙·威廉斯逝世后的二十年间,他原先所预言的有线电视、家庭卫星电视、互动式点播电视等新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普及的趋势;与此同时,新一代的文化研究学者也迅速成长起来,大批电视研究的新成果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以往的平淡景象为之彻底改观。而伴随这种繁荣,作为欧美左派电视研究的开拓者,他却在群星璀璨时趋于被人遗忘。就此而言,将威廉斯的电视研究思想从不应有的遗忘中拯救出来,已经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一、威廉斯的电视研究因缘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威廉斯不仅著述等身,而且涉猎广泛。不过,他所涉猎的领域大抵与“语言”关系密切:“从《文化与社会》到《关键词》,语言问题自始至终是他的思想上热情探究的问题之一。然而,他所指的语言其意义是那么深广,竟隐含衍化到如此众多的方向上,以至人们对是否应该称他为语言学家感到踌躇。在威廉斯看来,语词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②因此,尽管1974年之前威廉斯曾发表过相当数量的电视评论文章,可面对《电视》这样一本系统研究新兴电视媒介的专著,人们还是觉得有些突兀。时至今日,不少研究者私下里依旧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偶然性,不过是威廉斯1972-1973年访问美国的一个即兴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一书在1974生出版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1972年底威廉斯没有到斯坦福大学做政治科学访问教授,他就既没有机会接触与英国非常不同的美国“电视环境”,也未必有一段相对完整的空闲时间来写作这样一本系统的论著③。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威廉斯的电视研究本身也是偶然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在大众文化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因此,从50年代末开始,威廉斯就以各种方式积极体验电视、评论电视。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并于当年向公众播放电视。根据相关的法律文件,国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业。50年代初,这种垄断引起了与电子器材制造、广告等有关的英国中下层经济利益集团日益强烈的不满,他们从1952年开始在全国发起有组织的“压力运动”,要求建立商业电视机构。经过三年多的抗争,英国议会最终于1954年6月30日以微弱多数投票通过允许建立商业电视机构的《电视法案》。1955年9月22日,商业性的英国独立电视公司开始放送节目,国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垄断电视的时代宣告结束④。此后,英国电视业在竞争中开始迅猛发展,很快超越电台,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主导媒介之一。面对电视的强劲发展,当时正在与精英主义的文化偏见进行论战,着力为“大众”、“大众传播”、“大众文化”等概念辩诬的威廉斯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始终积极看待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帮助电视抵御欧洲北美各地知识分子的种种苛责”⑤。在1960年发表的“魔术系统”一文中,他对电视广告进行了出色的分析,肯定“作为现代社会传播的主要形式”,电视广告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途径⑥。在1961年与其他三位学者就电视问题共同发表的一篇长篇谈话中,他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传播的四种模式,而且认为电视能够为他所期望的民主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发挥积极的作用⑦。正是基于这种定位,威廉斯利用各种方式积极而间或地参与电视、体验电视: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他参加了无数电视讨论节目(直播的和录播的),与电视台合作将自己的两部小说(即《乡村来信》和《公共调查》)拍成电视剧,参加系列纪录片的拍摄;1968年至197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周刊上每月发表评论文章,畅谈与电视有关的各种问题……⑧在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中,恐怕只有威廉斯才拥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电视经验,这为他后来研究电视积累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6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些影响广泛的电视理论,而它们的基本取向都是威廉斯所坚决反对或不能赞同的。威廉斯反对的第一种观点是英国主流社会学的电视理论。随着英国电视业的迅猛发展,英国的主流社会学家从50年代末期也开始研究电视问题。他们承袭40年代美国同行的套路,重点关注电视对观众的影响,“经常讨论电视的‘效果’,或者电视所‘导致’的各种社会行为、文化和心理作用”⑨,最终将这种经验研究与英国本土的利维斯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得出了文化悲观主义的结论。这在哈里·皮尔金顿爵士1960年领衔起草的有关商业电视效果的《广播委员会报告》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商业电视为了追求收视率的成功,一味迎合观众,从而降低了观众的审美水平和道德水平⑩。这种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自然是威廉斯要口诛笔伐的。因此,在1960年的“魔术系统”及其之后的电视论述中,他总是或明或暗地批评皮尔金顿爵士的报告。威廉斯反对的第二种观点是因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滋生的各种技术决定论的电视理论。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掀起一场媒介理论的革命。威廉斯起初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颇有好感,但后者很快就暴露出他的文化精英主义的面目,这不能不促使威廉斯转而反对之(11),并在《电视》中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为各种技术决定论的电视理论的源头给予专门的批判(12)。至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以结构主义方法对待文化文本的“荧屏”理论,威廉斯也不赞同,因为它们在看似批判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最终把文本理解为一个脱离社会、有其内在因果规律、自我决定的独立系统⑤。面对这些理论的滋生及其广泛流传,威廉斯没有熟视无睹。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最后,70年初,代表威廉斯后期思想特征的“文化唯物主义”基本形成,威廉斯本人始终存在在实际应用中检验这一新思想的内在理论冲动。“左派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威廉斯思想发展的两大理论来源,不过,在以《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中,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的“左派利维斯主义”显然占据着上风。正因为如此,60年代初以后,以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就批评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这两位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灵魂人物,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且漠视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是“英国民族主义者”,其思想的本质是以“浪漫主义的超越和混乱的经验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14)。与汤普森不同,威廉斯诚恳地接受了这种批评,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戈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并重新整合了自己的思想。197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15)一文表明了威廉斯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初步形成(16),而在实际应用中对这一新思想的理论效力进行检验的课题也就随之提出了。
虽然威廉斯原本并没有专门研究电视问题的规划,但是在美国那种独特而强烈的电视环境的激发下,他久已有之的理论需求(批判流行的电视理论)与刚刚萌生的理论冲动(验证“文化唯物主义”)最终在其雄厚的电视经验基础上发生融合,并在1972-1973年那段相对空闲的访问教授生活中得以实施。
二、威廉斯的电视研究范式及其内涵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研究是验证自己刚刚创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个绝佳选择,因为“在关于技术、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一般关系的当代争论中,电视无疑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它既是前三个领域的交汇点,又是两两之间的相互作用点,就此而言,它当前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无与伦比的”(17)。如果在“文化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电视现象得到有说服力的关注,那么,“文化唯物主义”之于“技术、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一般关系”研究的普遍适用性将能够得到有效的验证。换言之,电视研究是作为解决“技术、社会制度与文化之间一般关系”问题的一般范式即“文化唯物主义”的一次具体运用,我们只有首先领会了这一范式本身,才能对威廉斯具体的电视研究观点获得完整准确的理解。
可能是因为威廉斯研究者大都出身文学之故,人们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解往往偏重于它的理论建构,对于它更深层次的方法论性质则几乎视而不见。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像希金斯这样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专家也未能避免(18)。事实上,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一样,“文化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理论,而且更是一种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指南。具体地说,它是威廉斯基于自己以往成功的文化研究实践,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主要是卢卡奇的总体性学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充实、完善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所总结出来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或方法指南。根据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理论著作中的阐述,兼及他在《电视》等实证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我们可以对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作出如下的重建。
作为研究范式,“文化唯物主义”的前提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状态已经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获得充分发展,与作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关系总体。它因此得出了一条简明的研究原则:必须在这三者构成的关系总体中来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因为现时代的文化现象都是物质性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或体现。那么,在这种关系总体中,究竟哪种力量起决定作用呢?一方面,它肯定,经济基础依旧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但认为不应当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在宿命论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肯定,在现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文化霸权往往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因此,抽象地追问究竟哪种力量起决定作用并无实际意义,重要的是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清楚,对于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而言,它的理论效力并不在于理论证明,而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地应用到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去,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当威廉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范式重新审视自己原本就非常熟悉的电视现象时,他发现,作为技术的电视是同时代人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最多、错误认识也最多的一个话题。面对电视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电视改变了世界。可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根本经不住推敲。因为不管程度如何,其中所包含的技术决定论“都以技术孤立论为基础。这种观点要么认为技术是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自动力,要么认为技术是能够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内容的自动力”(19)。把技术看做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东西,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了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各种“意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作为技术的电视的历史发生,因为正是从各种“意向”中间形成了直接推动电视技术发明的社会需要、社会目的和社会实践(20)。为此,他专门追溯了电视技术的发明与使用的社会史过程:1890年之前,综合成电视的各项专门技术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被分别发明出来,以它们为基础;1890年之后,人们开始预见到电视系统即将出现,并着手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与技术积累,但进展缓慢;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经济利润和军事用途的推动下,“作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工业化生产的早期决定性转型及其社会形式才创造出了新的需要和新的可能性,于是,包括电视在内的各种传播系统就作为它们的内在结果出现了”(21);30年代以后,电视开始进入实用,但在50年代之前一直发展缓慢,原因一是缺乏技术投资,未能有效降低电视接收机的昂贵价格,二是居民能够用于私藏性消费的收入不足;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前述两个制约因素的解除,电视开始普及。
威廉斯并不否认: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发明,电视确实推动了世界的改变,但是他指出,作为技术的电视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依据的是有关社会中现存的政治安排和经济安排”(22)。例如,在英国和美国,“早期的电视制度的基本发展实际上是在‘公共服务’制度和‘商业’制度的对立或竞争中展开的”(23)。“公共服务”制度在英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本质不过是英国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早已存在的文化霸权”中的一种体现(24);不管在美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制度如何标榜“自由”与“独立”,也都无法掩盖它是不同的“资本利益”代言人这一基本事实(25)。作为美国之行的重要收获,威廉斯有了如下进一步的发现:第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的电视制度呈现出资本与国家机器(政治与军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其结果是“再也不可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谁是军品电器商,谁是负责信息宣传的政府部门,谁是最常见的‘商业’广播机构”(26);第二,在商业电视形式下进行的国际扩展中,美国的“商业”电视不仅追求利润,而且“是直接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规范并由它所塑造的文化形式和政治形式,它不仅兜售消费品,而且兜售包含其中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性一方面是由国内资本利益和政治权威所引发的,另一方面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权力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在国际扩张中精心组织出来的”(27);第三,5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出现的电视国际化其实是“美国有计划扩张的结果”,“是美国利益、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合作者以及强大的国际广告公司联手炮制出来的”(28)。
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是威廉斯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面对文化精英主义对电视的种种指责,威廉斯强调,作为大众文化形式的电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它利用自己的技术特点,对新闻、政治辩论与讨论、教育、戏剧、电影、综艺等各种既有的文化形式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改造与发展;另一方面,它还创造出一系列全新的文化方式,如戏剧化纪录片(dramadocumentary)、观光教育片(education by seeing)、日常讨论与谈话节目(discussion)、电视杂志(features)、电视连环画(sequences)以及电视本身。在具体讨论戏剧化纪录片时,威廉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融会贯通创造出一个极为形象的批判观念:“戏剧化社会”(dramatised society)(29)。所谓戏剧化社会指的就是典型化、类型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真实的自我与差异不复存在,人们只能按照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类型化方式去生活、去思想、去言说,生活与戏剧的界限由此消融:戏剧在生活上重复上演,而生活也就变成了一场按剧本演出的戏剧(30)。
初到美国,威廉斯被美国电视频繁的插播现象搞得晕头转向(31),但这种多少具有一点的“超现实主义”经验却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在经受了一次次陌生化体验后,他对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的整体性特点有了全新认识。以1973年3月的某一周为基准,他对三个英国电视频道(两个国营频道和一个商业频道)和两个美国电视频道(国营频道和商业频道各一个)静态的节目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发现:不同的电视频道确实存在不同的节目形态差异,但“每一种节目编排类型中都包含同样重要的文化‘设定’”,正是这种“文化‘设定’”使各种节目形态具有了“各自的特性”(32)。基于这一分析结果,威廉斯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尽管层出不穷的广告把电视搞得支离破碎,但观众并没有被淹没,反倒具有更加完整的电视经验,惟其如此,就在于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是一种基于各自的“文化‘设定’”而精心设计、编排出来的完整的“流程”(flow)(33);第二,这一流程的本质是“特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之流”(34)。对于威廉斯的“流程”观念,80年代以后陆续有一些左派电视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批评(35),但人们都注意到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观念:正是因为有了它,电视研究才开始思考电视节目是否具有整体性以及具有何种意义上的整体性这一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流程”要比其他竞争性观念更具解释力,因为在它这里,整体性是由内在的“文化‘设定’”所构造的,“文化‘设定’”不同,构造出来的电视整体形式也就不同。
与作为技术的电视、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相比,作为传播形式的电视可能是威廉斯思考时间最长的一个主题。因为早在1962年的《传播》一书中,威廉斯就对作为传播形式的广播电视有过专门的讨论,但当时的切入点主要是“自由与责任的公共平衡”问题(36)。而在运用“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再次关注这个问题时,他的认识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首先,他指出作为传播形式的电视对日常生活塑造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我们几百万人观看影子的影子,发现它们的实质,观看各种场面、情境、活动、争吵、危机,直到眼球疲惫不堪为止。生活的侧面以前是在自然主义戏剧中生动地表现出来,现在则成为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内在节奏;举手投足的流程,再现表演的流程成为一种新的常规,一种基本需要的常规”(37);其次,在发表于《听众》周刊上的那些电视评论文章中,他分析了电视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与政治结合态势,而以“文化唯物主义”为中介,他更充分地意识到,现代电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虽然隐藏多年,但起码现在暂时成为了现实。它的名字是立宪专制主义”(38)。再次,他对流行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一研究由于受技术决定论的影响,把电视作为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力量,抽象地研究它的“效果”,并将之归约为“社会化”、“社会功能”等空泛的概念。他认为,仅仅追问“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向谁,说了什么,有什么效果”是不够的,因为这“遗漏了‘意向’,因此也就遗漏了全部真实的社会文化过程”(39)。必须确立“过程意识”,在真实的社会文化过程中,在与“真实意向的关系”中研究电视的效果(40),这样就会看到电视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发挥作用、产生效果的。最后,他日益觉得必须推动电视教育,以召唤人民投身民主文化的建设。利用传播方式建设民主文化是他在60年代初期就形成的一个理想(41),但鉴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不无忧虑地预见到: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电视技术将继续发展,有线电视、家庭卫星电视、互动式点播电视等新技术获将在未来二十年内逐渐投入使用并普及,从总体上看,如果不出现制约的力量,这将导致国际垄断的形成。他就此发出号召,要求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传达自己的意向,使这些新技术避免成为跨国垄断集团的操控工具,同时使之成为“教育和参与民主的漫长革命的现代工具,和城市工业化社会中恢复有效传播的当代工具”(4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日益重视电视教育的作用(43)。
三、威廉斯电视研究的主要成就
进入80年代以后,英美的电视研究日益繁荣,最终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回顾电视研究的历史之时,人们都会提到威廉斯的电视研究,充分肯定他的《电视》与其他几部论著共同推动了英国电视研究在70年代的“戏剧性变化”(44)。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理论评价时,人们往往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他的电视研究的某种轻视,甚至认为他的观点已经过时。例如,在美国学者80年代为一部广泛使用的电视教材《重组话语频道》撰写的“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一章(45)中,以及英国学者90年代撰写的两本教科书《电视的真相》和《电视与社会》(46)中,威廉斯的地位可以用“无足轻重”来形容。必须承认,威廉斯的电视研究主要立足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的电视经验,因此,与当代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及其电视研究走出当代电视研究的中心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左派电视研究的真正起点,他的研究中包含着清晰而完整的左派思想基因或者说“文化‘设定’”,一旦这种基因或“文化‘设定’”出现缺失,左派电视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还能保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特性或激进特性,将不得不成为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威廉斯的电视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应当忘却的。
第一,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发展起一个完整的批判性的电视研究框架。英国社会学家史蒂文森认为,与其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威廉斯的媒介研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它的完整性,他“能够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成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他论述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围之广,人们对此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47)。这一点在他的电视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分析与批判,也包含了对电视受众的经验模式的分析,而前两者最终在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上得到整合。就此而言,尽管后来的左派电视研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大大推进甚至超越了威廉斯的研究,但它们的研究始终没有超出威廉斯所确立的框架边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决定电视发展的各种社会物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威廉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归根结底的客观决定作用进行了初步考察。电视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出来,进而普及并占领日常生活的中心地位?在威廉斯看来,归根结底,这是由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电信技术的发展,为了消化由此带来的成本,资本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需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私藏性消费能力不断上升,资本也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增加技术投资、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再生产规模,使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不断的积累使资本有条件进行新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储备,一旦条件成熟,资本就将把这些新技术投入实际的使用,以创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利润。尽管威廉斯的相关分析还不那么系统和深入,但却足以表明,威廉斯已经触及到当时媒介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电视存在的社会价值。
第二,在民主政治规划基础上,使电视研究具备了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威廉斯之后的左派电视研究蓬勃发展,涌现出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大卫·莫利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一代文化研究学者。与威廉斯相比,他们吸收并运用了更多的欧陆学术资源,研究对象更加微观具体,分析过程更加精致细密,研究结论更加新颖大胆,但面对他们那些高度专业化的学院文本,人们很难感受到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想象。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评论说:“威廉斯在诸种传播结构和民主理论之间创造了一种卓有成效的辩证法,可霍尔在这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48)因为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霍尔等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了电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电视、改变世界(49)。威廉斯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将批判性的电视研究与民主政治规划融合起来,使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具备了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威廉斯的现代性规划具有很大的空想色彩(50),但他那种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探索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实践精神,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当具备的。
第三,将社会历史分析引入电视研究,有效遏制了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泛滥。在1974年的《电视》之后,威廉斯一直没有放松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始终提醒人们注意:“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技术决定论的,哪怕是某种精致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必然的或不可阻止的某种新技术的意义,是有关的各种利益公开的或隐蔽的市场销售的一种产物。”(51)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都肯定,将社会历史分析引入电视研究、系统批判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媒介理论是他的一项重要成就,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阻击,技术决定论思潮会对左派电视研究产生何种消极影响,将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情。让他足以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很少直接提及他的这一重要成就,但后来的左派电视研究确实对技术决定论产生了有效的理论免疫。
从某种意义上讲,威廉斯电视研究成就犹如一笔无形的公共的文化理论遗产,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分享了这笔遗产,但却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因此,想要搞清楚究竟谁是他的继承人、分别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遗产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的就是揭橥以下三个往往被人遗忘的事实,以佐证威廉斯的电视研究确实曾经发挥过的巨大学术效应:第一个事实是,作为当代左派电视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霍尔从60年代后期开始在威廉斯的直接影响下研究电视,尽管7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学术上受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威廉斯的水平,可他的批判并没有能够根本突破威廉斯提供的基本框架,更主要的是,对于所有制和媒介控制等威廉斯有过出色分析的重要领域,他基本乏善可陈(52)。第二个事实是,作为当代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个领军人物(53),彼得·戈尔丁和格拉姆·默克多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研究工作受到威廉斯对电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直接影响,后者的“公共服务”体制与“商业”体制二分法构成了他们的分析框架的基干。第三个事实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以威廉斯的“文化‘设定’”说为基础,对电视新闻报道进行系列经验性和符号学的分析,最终得到了一个现在被广泛接受的经典结论:“新闻具有连贯性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新闻不是中立和客观的,也不是公正和无偏见的报道,而是有赖于与某些特定的阶级有联系的设想”(54)。
注释:
①Ederyn Williams,"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in 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Rout ledge,1990,p.8.
②特里·伊格尔顿:《纵论雷·威廉斯》,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p.7.
④马庆平:《外国广播电视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69页。
⑤Raymond Williams,"Preface",in Alan O' Conner(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Routledge,1989,p.xi.
⑥Raymond Williams,"The Magic System",New Left Review,No.4 (July-August 1960).
⑦Kit Coppard,Paddy Whannel,Raymond Williams & Tony Higgins,"Television Supplement",New Left Review,No.7(January-February 1961).
⑧Raymond Willians,"Preface",in Alan O'Conner (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pp.ix-x.
⑨(12)(13)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p.9,pp.126-128,p.126.
(10)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电视的真相》,魏礼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11)Paul Jones,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57-158.
(14)Tom Naim,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New Left Books,1977,pp.303-304.
(15)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
(16)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威廉斯直到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才“同马克思主义建立正式关系”(特里·伊格尔顿:《纵论雷·威廉斯》)。
(17)(19)(20)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p.7,p.14,p.14.
(18)John Higgins,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Roudedge,1999,p.125.
(21)(23)(24)(25)(26)(27)(28)(29)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p.19,p.36,pp.33-34,p 37,p.40,p.41,p.42,pp.72-74.
(22)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3页。
(30)Raymond Williams,"Drama in Dramatised Society",in Alan O' Conner (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r Selected Writings,pp.3-13.
(31)Raymond Williams,"Impression of U.S.Television",in Alan O' Conner (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p.25.
(32)(33)(34)(39)(40)(41)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pp.85-88,pp.95-96,p.118,p.120,p.121,p.150.
(35)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祁阿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1—150页。
(36)(42)Raymond Williams,Communication,Penguin,1966,p.149,p.122.
(37)Raymond Williams,"Drama in Dramatised Society",in Alan O'Conner(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p.5.
(38)Raymond Williams,"Distance",in Alan O'Conner (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p.20.
(43)Raymond Williams,"Television and Education",in Alan O'Conner (ed.),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Selected Writings,pp.203-215.
(44)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电视的真相》,第111页。
(45)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331页。
(46)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电视的真相》;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媒》,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46页。
(48)(54)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媒》,第60页,第4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50)Paul Jones,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pp.181-194.
(51)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第175页。
(52)Helen Davis,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Sage,2004,pp.41-68.
(53)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