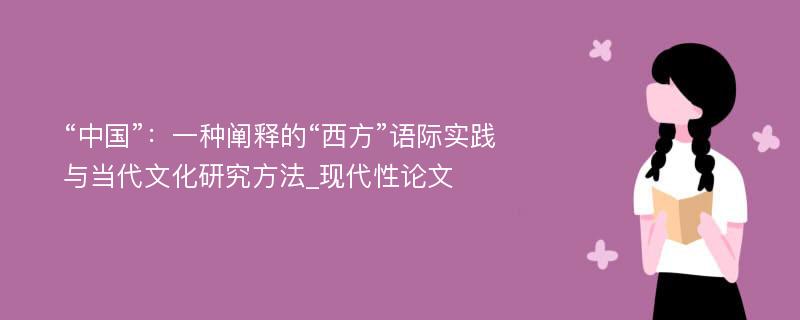
“中国”:一个被阐释着的“西方”——“跨语际实践”与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跨语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对象、范式的变革无法离开研究方法论的变革而独自得到说明。就今天而言,无论是冯友兰生前一直强调的“从中/西问题到古/今问题”〔1〕,还是沟口雄三等大胆倡言的:从“以西方为方法, 以日本为对象”,到“以日本为方法,以西方为对象”〔2〕的转换, 谈的其实都是“方法难题”。而这些也都构成了构建中国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正处于90年代文化研究方法论建设的明显视野之内,虽说它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广泛关注。〔3〕
什么是“跨语际实践”?它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它在哪些方面切中了描述当下中国问题的要害?它目前遇到的困境何在?本文拟就上述几点作一点介绍并谈些抛砖引玉之见,以期得到切中的批评和讨论。
1.“西方/ 非西方”的分析文化现象的整体性框架的弱点——汪晖、酒井直树的问题——现代化论与批判理论难题
我们先来假定一个前提,即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圈自我检视的尺度,是“文明论”的尺度,而它对于非西方文明检视的尺度,则却首先是看该文明“现代化论的程度”的另一相关尺度。这种西方——“文明论”,非西方——“现代化论”的尺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当然是肇始于马克斯·韦伯:具体讲,韦伯在分析西方现代时,一直坚持文明论的尺度。现代化尺度在韦伯此处非惟不是唯一的,而且甚至是被批评的;韦伯对现代合理主义即现代化主义的批评,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中。但是反过来,他在《儒教与道教》中,却完全用现代化合理主义,即“现代化论”这唯一的尺度来看非西方文明。这一尺度被坚持下来,就成为19世纪以来看非西方文明问题的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
这也就是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一文开篇就紧紧抓住的问题:“如果说现代思想从两个方向——即批判理论的方向和现代化理论的方向——上发展了韦伯理论的话,那末很显然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对韦伯的利用主要在后一方面。”〔4〕
汪晖这样提问,并不意味着中国(非西方)文明不要现代化,不要合理化,甚至不要向西方“学习”(文明交往),而是意味着有必要先问一问:西方/中国(非西方)这样的方法论框架是怎么回事, 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说:从“不能被消解的历史主义立场”看,19世纪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奇妙的立场:对自己的文明诉诸文明论的“特殊主义”强调,而对其它文明,则诉诸现代化论的“普遍主义”强加?如果说现代交往行为中的确存在“权力关系”的话,那末这种文化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立场,就表现了西方/非西方文化研究框架和交往行为中,不能不顾及的强势/弱势的权力关系。
由于这个问题不容易一下子就从“西方”或“中国”的哪一方说清楚,所以我想选择哈佛大学酒井直树(SAKA·RUKL)教授论述日本现代性的一篇有名的论文:《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来展开讨论。酒井先生认为,自明治开国时代的学者到今天的铃木大松等,日本学界面对“西方”时,一直在强调日本文明作为“文明”的“特殊性”,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文明”一直采取的是文明论的特殊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们看周边其它文明时,却完全坚持的是看该文明的“现代化程度”的“现代化论”立场,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京都史学派”的观点之中:他们用“合理化程度”制造出中国“国民性”特别有待“改造”的看法,并以此支持“大东亚共荣”的对亚洲的所谓“现代化解放”论。
酒井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日本反对西方19世纪以来仅对西方自己采用文明论的特殊主义立场,并且从现代化的普遍主义尺度出发日本为“井底之蛙”的话,那么,日本对周边文明的态度,却与“西方对日本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只因朝向对象不同而有所异,这也就是说世界范围内的西方与亚洲范围内的日本在现代交往行为中所操的话语立场本是一丘之貉。
与一本叫《日本为什么成功》的畅销书不同,酒井要说明的,恰好是“日本为什么失败”。酒井非常有益地看到: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欲争东/西文明孰劣孰优之时, 它对周边的文明却完全采用的是比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立场,而日本的“向西方宣战”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摆脱和走出西方现代性的方法论视野,这意味着文明间的权力关系不仅可以从西方/非西方的框架中看到, 更被从“非西方的”“亚洲文明圈内”的文明间的权力关系中凸现出来。而且西方/ 非西方的视点不可避免地容易转移视线:比如把迟发展和非西方的问题统统推给“西方压迫”,这样它就通过轻而易举的概念偷换而遮掩了,正是从亚洲文明圈内部,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内在权力关系, 却反而能够更深刻地被看到。
我们把酒井的立场推进一步,似应得出这样的看法:现代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文明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 已经深深地内化为非西方文明(如中国和日本)现代性经验中深刻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规定着我们自己看问题的方式,从而不但使在现代性方法论上,再固守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变得既无意义又无可能,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绝不单是指向对“西方”的批评,排斥和对抗,——对任何“中心论”的批评,首先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即对亚洲中国和日本现代文明内部的权力关系的揭示、反省和正视。这也就是说,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对我们而言,也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现代性经验”的“自我批评”,自我整理和认知。
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与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赛义德(Edward·Said)式的后殖民主义慎重地划开距离:尤其当这位面目不清的美国/ 阿拉伯学者或者有可能在大陆重新鼓动起现代民族主义情绪,重造一个意识形态神话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赛氏并没有更多地去区别和分析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和重重矛盾,而总是喜欢把一个不直接在场的“西方”拉出来当作转嫁危机的唯一对象,这甚至意味着:他有可能是诉诸全体阿拉伯人民之名,却实则代表的是阿拉伯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和利益,即他对话语所作的历史的权力的分析是不彻底的。
这可能同时构成了要批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先生和他在中国的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的发挥者的另一理由:后者不但过于急切地把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内部问题的批评一概斥为“西方的工具”,而且其从“后殖民=反西方”这一简单立场出发,对90年代中国出现的文化文学问题,亦不容易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易言之,90年代本土“现代性空间的断裂”:阶层划分,城乡差别,地区纠葛,使一个判然区别于“西方”之外的“我们”并不可能存在了,90年代最突出的矛盾,可能并不是什么“乡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矛盾,而是现代中国文明内部的纠葛。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前现代”和“农业文明”拒绝现代化的“垂死绝望抵抗”,而恰好是中国在被卷入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后必定要出现的问题。在这个Jackson Lears所谓“Noplace of Grace ”的没有什么同一性的现代性的“同一空间里”,其实并没有一块可以离开“现代”的“农业文明净土”。这甚至意味着,放弃过于笼统的“西方/ 非西方”大框架,回到我们文明自身和内部,为的正是更具体、更深刻地看到植根于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之间的现代交往方式中的权力关系。冯友兰创意地将中/西问题的提法转为“古/今”问题,其实是把现代性的权力关系,内化为中国内在的“时间”问题,而地区差别和阶层分化,则使我们去注意中国现代性的“空间”问题。毕竟,在中/ 西问题第一次在文化领域内提出讨论的“五四”时代,“坚持传统”的《学衡》吴宓诸公,坚持的更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梁漱溟的“三种文明论”,基础正是在黑格尔对文化哲学的现代看法;而在四十年代,强调“民族化”的“新民主主义”,即使不提它的列宁主义来源,它作为民族主义言说的一支,来源也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学。正象我下面要分析的,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当代作家张承志,知识来源更象是纯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地理学”解构史观,谁是“西方”,谁“代表中国”,既然如此交叉,那么中/西分野的两两区别便是失效的。 这也就是“跨语际实践”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刘禾所说的:“把抵抗与主导模式实体化到东/ 西分野上来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东西两者之间经常是界限混淆,互相渗透,依条件的变化而修改关系的。”〔6 〕作为一个过于简单的模式,西方/ 非西方的框架之不足以更准确地探讨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一点正在越来越被今天的学术界所认识到。
2:现代性空间的断裂与跨语际实践——95年小说论争的简短说明。
所谓现代性空间的断裂:即市场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分层,地区分化,城乡差别,在95年突出地呈现出来。这就是韦伯认为的:从现代化论角度看,市场带来的是整合和一体化,而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它带来的却是分化或“分离化”。当一旦顾及到这种社会分层和地区差别,那么现代语境下的整一的“我们”便变得可疑起来,与其说中华文明圈内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与现代化程度低的地区之间正在形成类似于西方/ 中国的权力关系,不如说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的言说立场正在变得日益内在化并无所不在。
其次,现代性空间的断裂同时造成了人口的流动、迁徙:国内的和国际的迁徒。而这种流动其实更为深刻地在改变并模糊着人们的“身份”,这样与“纽约的北京人”和“城里的农村打工者”这种现实中的“漫游者”一样,曾由两位理论家:蔡翔和吴亮先后提出的所谓“文化漫游者”的表述便鲜明地出现在95年的文学叙述之中。
正是当代社会在“流动”中不断的分化和重组,终于使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首要问题”被植入到一个远为复杂的当代语境中来了。对95年而言,这首先使我们关注作为文化热点之一的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我认为对张承志问题的看法囿于理想主义/世俗化问题,必定会因为方法论的偏差造成误解。
关于该作品最不应该不加讨论的起码有两点:一,如果“后殖民理论”是美国国内少数民族批评白人文化优越论的一种理论的话,那么《心灵史》正因为揭示的是中华文明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因而才是一部“真正的”采取后殖民立场的本文。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是美国人的“自我批评”,中国的后殖民主义也应包纳对自己文明的“自我批评”气度,而不应单是批评“西方”。二,“文明交往”问题是伴随现代化而至的突出问题,人口流动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和当今中国的问题,而且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启动一开始就面临的内部重大问题。它突出地表现为现代化如何完成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的难题。 《心灵史》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切入这一文化问题,这正是它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揪住张承志的“红卫兵”问题不是不对,而是只揪他的“红色激进主义”却其实是什么也说明不了,作为言论的激进主义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重要的是某种激进主义可以被接纳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效果。我认为看红卫兵问题就要看“造反运动”——“大串联”——“上山下乡”和“屯垦戌边”的具体历史,即它如何实现了社会动员/ 社会控制的实质,而不是看什么空洞的激进/保守。红卫兵当然是激进的, 但围绕着激进主义推动或阻碍了中国谈问题却永远不可能接触问题的实质。反过来说,难道王朔在推动“统一市场化”方向上就不“激进”吗?王蒙在几十年内顽强地推动文学创作的自由方面就不“理想主义”吗?实际上这样谈问题是先有价值判定但却又根本没有对象和范畴限定的。
关于《心灵史》问题当然还要更深入地触及几个背景材料:①18世纪—19世纪初(始于嘉庆改革,终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导致中原文明以“人口流动”规模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魏源、龚自珍、刘逢禄等正是此时开始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倡导“今文经学”,要点是提出应从地区差别、文明差异角度看问题,批评固守一个文明视点的考据学文人“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②西北穆斯林“东干人”作为交往中介的重要性:由于说汉语,着汉服,东干人往往被中亚穆斯林视为“中原人”,“入侵者”;而作为纳赫什班迪派的一支,以及与传道者马来迟,马明心的关系,他们又拥有、恪守严格教规,东干人是第一次大迁徙中最特殊的文化群落——往来于汉/ 穆斯林之间的文化漫游者群落。③与西方语境中的赛义德一样,中亚问题专家张承志有回族血统而用汉字写作,这意味着他可以纯熟地玩弄汉语于股掌,但却有条件声明不做语言的工具,声称语言无法完整表达自我,指斥语言的异己性和不透明性,其表述作为“粘稠的一团油彩”的语言之外的效果,正说明当代文化漫游者首先是语言上的漫游者。④当我们考虑“红卫兵”张承志一开始创作就具有的文化地理学视点时,就不能不看到,从“造反”到“戌边”,说明红卫兵运动起于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终于这种结构矛盾在空间上的重新安排和组织,它反映的是中国现代性空间的深刻断裂和修补策略之一。尽管这一策略是不成功的。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常年流动人口最高估计在1亿人左右,最低也在5千万人左右,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0。这再一次提示人文科学必须重新思考现代性空间断裂的问题。而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思考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
同样,张炜的《柏慧》的应有之意也在于揭发了汉文明内部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社会分层这种90年代现代性空间断裂。——若说“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源于“城乡”差别的话,那么张炜坚持的是:城乡差别的核心只是经济差别,而经济水平的高低,并不绝对说明文明水平的高下,它充其量只表现了文明间的宰制/被宰制关系。 张炜的立场与其说是前现代的农民,不如说是被裹入现代的“流民”。——这不但让我们看到文化漫游者的另一立场:批判和解构统一的现代市场的社会学立场,而且最终它啼笑皆非地迫使我们承认:如果中国当代作家中真的有所谓“后现代”的话,那么这后现代可能更象是“二张”而不可能是“王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是基于地缘政治,文明论的现代批判理论,后者是基于统一市场的现代化论,这两者间的争辩从来没有达到过共识。
基于全球现代性造成的空间分裂,即由资本主义发生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造成的贫富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被称为“人口流动”的深为我们警省的人类史上的大迁徙。作为这一大迁徙的当代表征,无论《北京人在纽约》多么“通俗”,《心灵史》多么“高雅”,其作为“穿行于不同文明间的漫游者的文化表述”是完全相同的。同样:“Native Beijing In New York”这一标题也象《柏慧》一样绝望的叩问:在急剧迁徙中不断重组的现代空间里,有没有真正的“土著”(Native)?所谓“没有雅致之地”(Noplace of Grace)的意思不过是说,在我们的“身份证”上,“故乡”这一栏也许是根本无法填写的。
最终,如果身处在这个跨文明,跨地域的没有共同性的“共有”的现代空间里,无论是张炜或张承志,还是王朔和姜文,如果有人还在宣称自己绝对代表“中国”或“西方”,“理想主义”或“世俗精神”的某一方的话,我们就要问问他:“你发言的前提是从哪里来”?——而也正是这一点,把我们推向一个必须的解决的方式: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上拓展人文学科的视野,正视甚至接受“跨语际实践”作为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有效针对性。可能只有这种话语有效性才有可能使我们有力地摆脱那些“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的文化炒作者的误导,在深化和直面紧迫课题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当代作家在反复痛苦的挫折中形成的弥足珍视的文化合作和对话。
3:“活动变人形”——被阐释的西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难题在中国现代性内部
80年代后期,王蒙在《名医梁有志传奇》中仿佛表达了如此历史洞见:“道德”、“惯例”、“忠厚”即使不导向专制,起码也导向僵化;而机智、聪慧和幽默却将导向开明和民主。作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符码,梁有志和梁有德讲的正是“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此时亦表达了对无序化的市场的早期担忧,“时代跨上了骏马,庸俗象马蝇一样叮在马腿上,和时代一起放纵驰聘了”。梁有德“干糟了”,梁有志会不会“再干糟了”?小说结尾在1988年春节,“老哥儿俩老泪纵横”,是深刻且有远见的。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肯定没有谁比王蒙更了解在历史上蜿蜒着的当代中国情境:“响鸣向铭香茗……”当所有的表述都无法切中这种复杂语境之时,当实际上是“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根本就没有“内行”之时,我们除了坚持“宽容”还有什么出路?此大约正是曾文正所谓,“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7 〕但更值得强调的是王蒙的另一篇作品《活动变人形》:此作在80年代文化热大讨论中独树一帜。“活动变人形”——“玩具”这个伟大而耸动的标题提示我们:关键不在东西文明的“冲撞”或“冲突”,并且预先将两个文明分别冠之以“文明”或“愚昧”的道德化评判,关键也不在现代文明的“西方”能不能和怎样才能“破除”东方文明的愚昧,而在于“西方”到了中国势必会被阐释,被“变形”,更为关键的则在于我们要的是西方的哪一部分,以及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理解为“西方的”因而是先进的和道德的,又把哪一部分判为落后愚昧不道德的因而便是“非西方的”。因而中国眼里的西方便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或有内在固定本质的它者,而只能是被中国的现代进程不断阐释着的话语的魔方:“活动变人形”;因为很有可能的是,中国人一直在玩一场自我主导的现代性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西方”只是一个不在场的共谋和帮手,有时甚至是增加发言者力量和威慑力,因而被加以充分利用的对手的心理阴影(因为“西方”毕竟打败过中国),于是在文化的两两对话中,谁占据了“西方”,谁就等于占据了道德、文明和现代,无形中也就处于话语的优势地位。
如果说《活动变人形》的深意尚不在此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则同样是深刻而直白的:如果要“救救孩子”,那么“孩子”(倪藻)要的是一顿早餐还是“玩具”?——如果你说:“都要”,即我既要民族国家又要市场,既要民主自由又要物质富裕,既要“理想主义”又要世俗快乐——但现实告诉你的却是,没有这个好事。这也就是说,如果“西方现代性”曾描摹出一个“民族国家”与“市场”相统一的现代性图式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现代性中,这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同一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即使从最“理想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过是正处在追求这一统一的历史过程之中。
因此,笔者一直认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同一性的批评和解构,特别地能够被从迟发展国家的现代进程,尤其是中国的现代进程中看到。也正是这一点,使西方有见地的学者,通过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视野的拓展而产生疑问:西方的现代性的同一性是一个绝对的,真实的统一,还是假定的,历史的统一?于是西方现代性作为曾经是一个“真实的”有固定本质的存在,它的历史性、话语性正是这样被从广阔的第三世界空间视野重新发现出来了。哈茨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作的序中深切指出:
“(西方之所以能得出“民族国家”与“市场”统一的现代性理想典型),不仅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因为各国成长和发展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历史的前进已被消除了。所有这些国家都寻求过近代化之路,这一事实的确反映在严复的观点中,而这一事实已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严复使之明晰地显示出来”。〔8〕
于是,事实上可能是,在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里,民族国家与市场化都不是同时达到的,于是正像在所谓“大我”,“小我”之间有一个权力关系一样,在“早餐”与“玩具”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先/ 后的权力关系现实,这一关系再一次从中国文明内部展示了现代化的普遍主义与文明的特殊主义的权力关系。
于是,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简单的思想方法问题,那就是本来仅仅与现代化有关的西方概念,为何总是被中国思想者从文明论的角度,阐释为与文明有关的概念:比如“科学”,它专指以实验、数据为工具,并最终指向生产发明的一种“机效”,在中国则被阐释为与“终极道德的真实”相关的文明论概念,由此可以解释梁任公何以从倡导“科学”始,又以在“科玄论战”中坚持科学与信仰、价值不可分的“玄学”终。〔9〕又比如“民主”, 韦伯在指出民主制在动员民众方面的诸多好处之时,又从文明论角度批评了它的诸多弊端,而在中国,“民主”一直是作为一种新道德价值关怀而存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揭示我们的起码有三点:①中国思想家只有把西方的现代化概念转译为与道德和文明有关的概念,它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煽动起国民对现代化的热情和关注,而且也只有把传统生活判定为不道德和不文明的,才会使人们更激烈地厌弃旧有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谭嗣同的《仁学》,清王朝就不会被视为一个“不道德”的统治对象被迅即推翻。在这个意义上,戊戍变法实际上成为为辛亥革命作准备的文化革命。②西方现代化概念一旦被从道德文明论角度加以阐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设定也更有可能产生道德控制和产业控制共管的更为严厉的局面(如五十年代到文革)。③从历史上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种奇妙的中国现代性表意方式。许多思想家正是从文明论角度出发,从大文化角度立论,结果却是放在现代化论上。比如汪晖在辨析民初史时就曾指出:民初思想家对“个人”的强调,既是作为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国家、团体的对立物出现,并以此来界定自己,但若我们将其置于民初的近代中国语境中去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个人独立性的强调,恰是以那些普遍性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为目标〔10〕。一句话,没有一个个人独立的“新道德”,就不会有一个富强的新国家。从文明论和道德判断出发“激进”地高扬现代化论,这是一种与中国现代性有关的特定表述。同样,在今天最强劲有力的为“市场”辩护的声音正是来自经济学界,其方式竟然是认为市场就是“最真实的‘人文’所在”,这样,亦等于从文明论的角度来煽动现代化论;我想指出的是,由经济学界的几位朋友盛洪、张宇燕和樊纲出面代表“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发言,走的正是一条从文明论角度阐释、呼吁现代化的路子,〔11〕而在经济学界的常识却是,韦伯就曾经从文明论角度指出过市场的种种不“人文”之处,而也曾反复告诫过“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罢了。
问题是:长期以来将现代化、工业化的信条道德化的思路,算不算一种“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斯大林模式无论指标还是速度都是极高的。)将现代化问题道德化甚至信仰化,鼓励的只是现代化的激进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病理诊断理论”,它没有将中国的现代性当作为应付现实难局而被构建成的,因而也就是可解构的话语,而容易将其视为单一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指明“道德乌托邦”是“不真实的”是永远不够的,而要指明的乃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相粘接的那些道德乌托邦预言同样是“不真实的”,这才算走出了第一步,而接下来的就是:我们何以要去构建与现代化论有关的那一系列“文明论叙事”?“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这两架高能合理化机器,为什么在东方被文质彬彬地冠之以“先生”之谓,以至成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4:跨语际实践:“中国人如何操纵西方话语”成为研究视点
“跨语际实践”的最核心的出发点在于:不仅是研究现代西方话语如何在中国的拓展和“启蒙”,而更是研究中国学者是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这些西方话语的。
就90年代而言,正象我在前面分析的,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于与“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操纵,已然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将其引向反对“西方”宰制乃至与“反帝”意识形成合流,一种则将其引向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内部的地区间的差别和社会分层造成的内部问题。同样,对“市场”概念的诠释和操纵也已判然分野:倡导“市场”者不惜将其冠之以道德文明论的——乃至“真正的‘人文’”的——堂皇之冕;(这种诠释其实已经全然剥离了此一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原有之意)而对“市场”的有力批评,同样也不是来自什么封建回潮,而是来自哈贝马斯关于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危机难题,甚至是由韦伯以来对市场合理化理想典型的描摹出发,对目前中国市场的非合理化因素的批判。
正象王蒙在80年代中后期就曾深刻指出的,不是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和现代话语的操纵——这种某种意义上的“跨语际的实践”,从而竟然形成了两派完全不同的,类似于古文经和今文经这样的因对经义的不同诠释而生成的不断反复的话语纷争。
如果不但考虑西方现代性话语是如何宰制和控制中国的,而且反过来考虑,中国学者是如何诠释、控制西方现代性话语,即如何玩西方这张牌的话,我们就必得承认,话语的权力之争不仅发生在国际舞台的交锋之中,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内部假西方和现代乃至后现代之名而进行的话语纷争之中。论争的焦点尚不在追问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真意”和“原有之意”,而在于对现代西方话语进行再创造和诠释的本土的现实的依据何在。比如所有坚持国内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普遍主义学者,在面对国际和西方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操起了民族主义的文明特殊论武器,这种矛盾的立场和机智的话语控制,凸现出其实是中国特殊的现实处境。
从历史教训看,对这种诠释的话语之争而言,最要不得的是先将双方预先作出道德的和价值的判定,即新/旧,革命/反革命,改革/ 反改革,如此等等,这样就会使学术研究脱离了阐释学的历史的应有之轨,而且脱离开话语对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的逼视。五十年代胡风案中就启蒙主义概念的不同解释,在知识分子中曾被上升为“新”(民主)/ “旧”(民主)的“大纲”之争,所造成后果前车不远;而今天围绕着“文化转型”而进行的讨论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仿佛不“转型”就是“落伍”,而一旦宣告自己在文化上已经“转了型”就万事大吉,且言之凿凿以对方“不肯转型”相威胁,这种明显的短视只能使“斗争”永无止境,使“对话”永无可能。
明显的是,目前,以“剑桥史学派”为代表,已经形成了当代西方的“中国学”,但对我们而言,更迫切的则是要形成当代中国的“西方学”,即研究西方现代性如何在中国被翻译,再创造,再阐释和被操纵的内在复杂过程。套用沟口雄三教授一句话,这便是“以中国为方法,以西方为对象”的另一个视野,这甚至也是我所理解的当代“跨语际实践”的文化研究的最基础的内涵。
注释:
〔1〕参见《三松堂自序》, 及《“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访冯友兰》,戴晴《学者访谈录》,科技出版社,1989年。
〔2〕《什么是没有中国学的中国——与沟口雄三教授对话》, 参见汪晖《真实的与乌托邦的》,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3 〕“跨语际实践”是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副教授刘禾先生提出的概念,见《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载《学人》第七辑,此前已有汪晖的论文《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载《学人》第六辑,以及《个人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秋季卷,均触及此研究方法。
〔4〕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载《学人》第六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5 〕酒井直树《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载米约斯·哈罗塔尼编《后现代主义和日本》,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感谢酒井先生的博士生白培德先生向我提供了该文的汉文译本,白培德的译文已收入张京媛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 载《学人》第七辑。
〔7〕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原文见吴相湘《晚清宫廷记实》第13页。
〔8〕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9〕参见汪晖,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见《天地徬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10〕同上书,《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11〕《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15日。
标签: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政治论文; 道德论文; 张承志论文; 漫游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