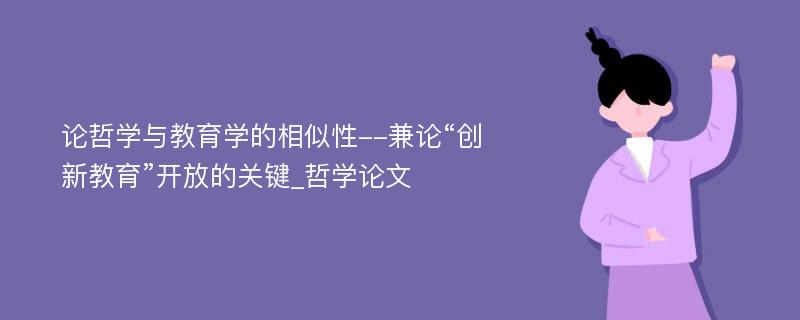
论哲学和教育学的相通性——兼论“创新教育”的开窍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钥匙论文,哲学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和教育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通道,因而使它们不仅成为近邻,而且结为联姻。这种判断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哲学家同时又兼教育学家于一身,几乎成了通例。而且由于哲学和教育学的相互渗透,又产生了一个新生代——教育哲学。
阐发哲学和教育学的相通处,绝不是出于文字玩味的需要,而是企求在当前的“创新教育”理论讨论中,找到哲学这一把开窍的钥匙,去打开教育理论的宝库,把“创新教育”发掘出来。同时,也想贡献一个建议:教育行业的管理者和办学者,若想成为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哲学知识。
一、智慧之学与哲人之路的耦合
哲学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它提供了一种为人类的实践和理论活动所必需的世界观,它的方法论则成为了人们在认识领域进行理论探索进而通向客观真理运动的普遍的科学方法。它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哲”,聪明、智慧之意。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皋陶谟》记载大禹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孔氏传》解释说:“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在古希腊,哲学意为“爱智”。在古印度则意为“见解”、“思想”、“观点”。统而言之,“哲学”,意为智慧之学。
哲学是以“不具体”为研究对象的,每当能对“具体”作出阐释时,哲学就把它交给部门科学,而自己又在“不具体”中探寻。“不具体”就是抽象,就是隐蔽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深藏在个别中的一般。抽象高于具体,本质深于现象,一般大于个别。所以,哲学天生的具有高、深、大的特征。能掌握和驾驭哲学,就等于掌握了智慧之剑,既能俯瞰知识的全局,又能潜入知识的底层,从不同的角度阐明知识的来源,通晓知识的走向,证明知识的真伪。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就是教人实现由不知到知,知少到知多,知浅到知深,知伪到知真,知粗到知精的学问。从而使人与无知告别,向迷信宣战,对虚假斗争。可见,哲学是智慧之学,也是引导人走上智慧之路的路标。
如果说哲学的直接目的是充实人的精神,或使人聪颖智慧的话,那末,教育的目的则是促进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因为,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和劳动一起,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机制。教育的价值不仅是传递知识,而且在于承替人类的创造力。富有创造力的人才具有一套特有的、广阔的态度和价值系统,而不是仅有一套应付事变的技能和方法。
教育学是教育的理论形态和思想指导。它以德、智、体诸多知识的输出与学生接受的功效为研究对象,揭示在学校这个特定空间和计划的学制中,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替补人才的运作规律。简言之,教育学是研究人的培养的学问。所谓培养,在学校教育中就是知识哺育。教育教育,知识哺育,这是对教育的最简解释。因为由劳动创造并积累起来的精神文化,要以独特的方式贮存并传递,没有教育这一中介项是不可想象的。可见,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传递知识为途径,培养通晓世事、深明大义的人。而这种人,在我国古代称之为“哲人”。所以,教育学是关于哲人之路的诠释和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既是哲人之路论,也是知识论。它是研究和揭示人如何获取知识,从而摆脱蒙昧,提高智慧的学问,也是研究和揭示人如何提高知识传授功效,从而改善人的素质,完善人生价值的学问。
哲学是认识论,教育学是知识论。认识和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存在的反映”。“认识是存在的反映”,“知识是存在的反映”。这种共同的本质,就是哲学和教育学之间的由此达彼的天然通道。况且,哲学范畴是人类认识的路标,人们对教育的思考,是假借哲学的基本范畴作为定向标志的。纵观教育思想发展史,任何一种教育理论的基本观念,总是和它的哲学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人类理智探究的早期阶段,教育学还不是独立的科学门类时,它是依存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见,哲学和教育学之间不仅具有“通道”,而且在实际中它们之间已经“相通”了。
哲学解决认识问题,教育学解决知识问题。它们共同解决的都是知与行、学与思、知识与做人的问题。知与行所包括的是认识的来源、验证和归宿的问题;学与思包括的是认识的理性活动和知识的消化创新问题;知识与做人所包括的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等伦理学的问题。在这诸多矛盾中,知与行是基本矛盾。哲学主张在行中求知,即“行——知”观,教育学主张先知而后行,即“知——行”观。把两种观点联结起来,就成了“行——知——行”的公式。于是,它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耦合点,即“行——知——行”中的“知”。这个运行公式,也是哲学和教育学在运行中相互携手,相互补正而共同构筑的螺旋圈。
哲学要回答的是知识的来源问题,教育学要解决的是知识的传递问题。知识的传递,对于受传的个体来说,也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只不过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知识来源问题,是知识传递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认识,教育学研究的是个体的知识。所以,哲学是更根本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要发展,必须不离其根本,即要下功夫学习并掌握哲学。
哲学和教育学相通的新生代,就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以哲学认识论为武器,揭示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辩证法则,即人要改造环境,环境又造就人的双向关系,以及人的知识发源、发展的途径和社会文化沉淀的积极意义的辩证运动。简要的概述,教育哲学是以人的完善和发展为研究对象,揭示个性与塑模的辩证关系。教育哲学具有的思辨性、规范性、批判性的特征,也是哲学的特征。思辨性即抽象,规范性即概括,批判性即综合。
在思想史中,有哲学家用哲学观点去思考教育而创立《教育哲学》的,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也有教育学家用教育学观点去寻找哲学背景而创立《教育哲学》的,如英国教育学家洛克,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等。
二、哲学家与教育学家兼容一身的通例
哲学和教育学的相通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就是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兼容一身,几乎成为通例。下面我们就以中外的实例作个案举证。
古希腊的柏拉图是第一个创立了完备的先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把宇宙魂视为生命精神的根本,认为宇宙魂同肉体的结合便成了人的灵魂。柏拉图主张回忆说,认为知识无须外求,只要内省,知识即回忆。由此而提出了教育过程就是一种回忆过程的教育思想。
柏拉图还把埃及世袭等级制理想化,构筑了一个雅典“理想国”,因此主张等级制教育,以接受“永恒理念形式”的能力为依据,把能力分为优、中、差三等。最善于接受教育的为统治者,而接受教育能力差的为最下贱的劳动者,这样,教育过程的各个阶段对学生进行选择、分类、甄别、淘汰就成为必要了。柏拉图的这种主张,对西方教育产生过持续的影响。在那里,学校教育实际成为一个选择、淘汰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测验、测量、分类和甄别的过程。柏拉图可称为外国思想史上兼哲学家与教育学家于一身的第一人。
1762年,法国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了。这是一部继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富有教育思想的哲学著作。
卢梭设想的教育任务是社会革新,摆脱神性的束缚,充分显示人性。《爱弥儿》就是要使教育人性化的集中表现。在卢梭的观念中,人天生自由,但在文明社会中却无处有自由;德性和良心本来人人皆有,但在文明社会中却因科学、艺术同财富的奢侈密切联系在一起,使社会风气变坏。《爱弥儿》就是提醒人们应当保护儿童免受文明的腐蚀,并要求细心地培植儿童的天性。他提出“按年龄而施教”的理论反映了许多正确而积极的教育观点。
1916年,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批判继承了古希腊以来包括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在批判、吸收中有发展。这本书不失为教育思想史上一次大综合,被认为是现代西方迄今为止,在体系上最为完整的教育哲学著作。
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是实用主义的创立者。实用主义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并力图把经验解释为超出物质与精神、唯物和唯心的对立之外的兼收并蓄的整体。杜威认为经验既包括心理意识的主观的东西,也包括事物、事件及其特性等一切客观的东西。经验所具有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并不是本质的区别,而只是机能上的不同。杜威称它为经验自然主义。
根据经验自然主义的阐发,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而生长的理想目的归结为这样的观点: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或改造。这种改组或改造,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过程的能力。
杜威认为人类演化的主要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进而他论证了儿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见解。杜威认为,儿童的学习和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更加富有成就地同他们的环境取得合作。
在我们列举了国外三位哲学家在阐发他们的哲学观点时,同时也阐发了教育学观点的实例,并被教育思想史认定是教育学家以后,我们应该把视线转向自己。
在我国,首推兼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于一身的,当属孔子。
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他在我国最早探讨了人性的问题,有所谓“性相近,习相远”的概述。以这种人性观为依据,他主张“有教无类”,从而使教育冲破了宫廷的藩篱,而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扩大了人才的来源,推动了已经开始的文化下移运动。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他从其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理论出发,提出了“诗、书、礼、乐”的教育科目。
“诗”是西周以来的诗歌。孔子说“诗”的作用有四:激发道德感情,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归结起来,是教人懂得如何“事父”与“事君”;还可以获得一些“鸟兽草木之名”等自然知识。
“书”即历史。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他又根据鲁国的史记编写了一部《春秋》,起鲁隐公元年,终鲁哀公十四年,简要论述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以周礼为准则,春秋为史实,“寓褒贬,别善恶”,旨在正名分,维护统治秩序。
“礼”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和仪节。孔子说:“为国以礼”(《论语·颜渊》);“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孔子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离开“仁”,“礼”就没有意义了,要求达到“礼”和“仁”的统一。
“乐”即音乐。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对“乐”在培养人的性格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外,孔子还从“学而知之”的认识论出发,提出了学思结合、言行一致的教学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的种种表现,都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学以致用,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从三十岁起,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至七十二岁逝世止,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他所阐述的教育思想,是世界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是名与实符的世界文化名人。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代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学家。在哲学领域,他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融合起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教育学方面,他提出了实行察举和举办太学两项主张。
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举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
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而建议兴办大学,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制度,发展成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我国古代教育是一大贡献。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我国南宋的哲学家朱熹,是集理学之大成者。他以“理”为核心范畴构筑了庞大的哲学体系。认为理具有寂然不动、“无造作”的特点,是一个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东西,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或本原。理在事先,有此理才有此物、此事。他从“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化原则。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四十年,是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是我国教育史上“书院”的创立者。
他著述甚多,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这些书自宋末以后,成为我国封建学校的法定教科书。
朱熹称儿童教育为“小子之学”。他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儿童教育和青年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考察的人。他把人的一生,约略地分为十五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和十五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不是举子教育、单纯的文字训练,而是向儿童灌输道德观念和训练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他编著的《童蒙须知》,对于儿童的日常生活,诸如穿戴、洒扫、饮食、应对、出入、容貌、行态、读书、写字等各方面均作了详备的条文式的规定,用“铭”、“箴”之类的道德训诫、短语,悬挂或雕刻在书斋、门户、盘盂等日用器具上,“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于忽忘也”。朱熹倡导的这种直观警示教育方法,对于今天仍不失价值。
朱熹称大学教育为“大人之学”,包括青年和成人教育。他设想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对于社会中“所当然”的“事”的训练基本完成,进而应弄清其“所以然”的道理,因而大学的基本任务便是“穷理”,即研究义理。其主要途径是熟读五经。他重视读书明理在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作用,是古代道德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根据他的“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知行观,他引《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大学教育的次序。学、问、思、辨属于穷理阶段,笃行包括修身及处事接物。大学教育,始于读书,终于修身,朱熹把它叫做“下学上达”,又称它为“由博返约”。这些认识,足见作为教育学家的见解。
孔子兴私学,董仲舒倡太学,朱熹修书院,他们在办学方式上的创新,连同他们的教育思想,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哲学家同时兼任教育学家于一身,既是真实的,也是无愧的。
哲学家为什么会兼容教育家于一身?除了哲学与教育学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通道,使它趋于必然以外,还因为哲学家本身具有的使命特性,也是促成其必定兼容的自觉原因。哲学家不仅会按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世界和探索人的智慧之路,而且也力求将自己的见解教给别人,影响别人,征服别人。哲学家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独白,而总是期待和唱。于是,自古至今,有过多少流派的哲学家,就会分别建立多少相应的道统并立其门户,从而也就必定会有多少相应的弟子或追随者,即常说的“桃李”或门生。不同的哲学流派或道统,为了把其哲学传授下去,也就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教育理论,从而使不同流派的哲学先贤,同时也兼容教育学家于一身。
我们常说的教育家,实际包括教育学家和教育事业家两大类别。教育学家又叫教育理论家或教育思想家,这类名贤总是因他的哲学、教育学观点的独树一帜而成名。教育事业家又叫教育实践家或教育实干家,这类名士,总是与他们兴办学校,兼任管理的业绩紧密相连。
三、教育兴科技,哲学兴教育
“科技兴国”,这是自“蒸汽磨”替代“手工磨”以后,人们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经验概述。现在,“电子磨”已经替代了“蒸汽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比“科技兴国”的概述更深一层。
与此同时,科技能兴国,教育兴科技,反映科技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这种概括,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和重视。因为懂得科技、掌握科技和发明科技的人,都必定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教育不仅培养了科技人才,而且还履行着传播和传递科技知识的职能。
我们还应该穷根究底地发问:教育如何兴?答曰:哲学兴教育。
哲学兴教育,这个看来生疏的命题,其实早在史实中做了结论。本文前面所列举的哲学家办教育和在教育思想方面提出的见解,就是这一结论的注脚。
下面,我们还想就中国现代高等学校中的北大、清华、南开三大知名学府的兴盛及其与任职的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的人文哲学修养的关系,做点分析。从而进一步验证“哲学兴教育”判断的客观真理性。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以轰轰烈烈,卓有成就,这与他深谙哲学是万万分不开的。他1907年赴德留学,次年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美术史等学科。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由于他有人文和哲学的功底,因此,在主持北京大学的校长时,能提出关于大学性质的真知灼见,“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聘请教师“以造诣为主”,“兼容并包”;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并明确界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在上述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全校编制为十四个学系,改“学年制”为“选科制”。
清华大学的早期校长梅贻琦虽然是留美学机电工程的,但他精通人文哲学。故当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时,他能用中国人文经典《大学》去总结大学,发表了《大学一解》重文。《大学》是儒家提供的教育理论,郑玄注:“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它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所谓三纲领。梅氏在总结大学三十年时,举出了当时的教育在“明明德”中存在三端,即“举知而遗情、志”,即就知而言也非《论语》的善诱、《学记》的善喻、《孟子》的自得,而是“灌输”,并非“启发”。这是一端。老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太少,这是二端。“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这是第三端。
大学的校内任务是“明明德”,大学的校外任务是“新民”,新民就是“大学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建树风气”,而不是大学适应社会。梅贻琦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两端,其一是学生只重专识,而忽通识。“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其二是学术自由不足。宋儒安定胡先生有言,“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梅贻琦认为,“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学术自由,所思所言,可能有不合时宜者,而这个不合时宜处,可能正合于将来,故所以,学术自由是新民大业之奠基矣。
梅贻琦用中国人文、哲学精神娴熟地剖析了当时的大学教育,从而悟出了治校之道。所以办出了“清华”,造就了竺可桢、高士其、周培源、钱三强、梁思成、钱伟长、周光召等科学家以及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吴晗等人文学家、历史学家。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是一位学工科而转向人文的学者。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946年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张伯苓认为,国家的不振和民族灾难之深重,在于愚、弱、贫、散、私“五病”,为痛矫时弊、育才强国,他为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主张学生德、智、体、美四育并进,鼓励学生发展特长。为此,南开大学曾专门通过《特材生办法案》,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宜设法使之尽量发展,并用各种方式奖掖优秀学生”。南开向以体育著称,张伯苓指出,提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而在体德之兼进,尤重在全社会体育蔚然成风。所以,张伯苓积极倡导和组织全国体育活动,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率领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国际比赛。在学校的管理体制上,他规定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方针。又制定了“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
南开在当年所以能与北大、清华相媲配,组成中国高等学校三驾马车,与他以人文精神治校,强调素质教育密不可分。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办学之辉煌,似乎还向我们暗示了一个道理:哲学不仅能管文,而且能管理、管工。按照蔡元培的“学”、“术”分校的主张和实践,唯有治“学”者方可叫“大学”,而治“术”者则叫“高等专门学校”。有人文哲学功底的专家可以治大学,有技术专长的学者可以治学院。这样一来,综合大学的校长人选定有人文哲学功底。这就一改我们学苏联办高校的模式和现状。
本文从论述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开始,进而讲到哲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兼容性,至此又谈到人文哲学与学校领导人选的素质要求,等等见解,都只不过是事实疏理而已。
当前,教育界正在讨论“创新教育”,说到根本,也与哲学相关。
“创新教育”,也就是创造能力培养。凡能力都必定包括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两方面。“行成于思”,行动从思想中来,因此,要具有动手能力则必先培养思维能力。哲学是抽象,抽象本身就是思维,所以,把对哲学的学习和掌握,作为提高思维能力的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然,与“创新教育”相一致的思维是创造思维。创造思维也就是思维无限。让思维的空间广袤无垠,就会有创造。相反,划框框,定调子,思维就受到拘束,就只能复制或再造。复制或再造就无可创新。马克思曾经说过,我的思想不是与法律打交道的对象,法律所能约束的是我的行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页。)正是这样,思维无限应该得到认可。哲学以“不具体”为研究对象,它是在无限中进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起哲学为武器,是进行“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学”和“术”,“道”和“艺”是一种矛盾关系。“学”或“道”是武器,是指南,是普遍;“术”或“艺”是操作,是应用,是特殊。操作受制于武器;应用仰望于指南;特殊不违背普遍。普遍的,指南的,武器的高于操作、应用和特殊。因此,教之根本,在于传“道”;学之根本,在于求“学”。哲学就是“道”,就是形而上,就是“学”,所以它在办学中始终是作为指导的武器放在高于特殊的位置上。这是“教”所以能“兴”的一个原因,或者叫文化或精神上的一个原因。如果抓“创新教育”而怠慢或忽视哲学,那么,就等于扔掉了武器,偏离了指南,而舍本求末。当然,“兴教”除了文化或精神的原因外,还必须有经济的即物质上的原因,那也是学校的希望所在。所以捐资办学,在现今我国又称之为“希望工程”,这也是无须存疑的。
实施“创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持续不断,直至高等教育。因此,小学可以开设手脑并用的“工艺课”,中学可以开设小发明大用处的“实用课”,大学则开设以大哲学为内容的“人文素质课”。大哲学包括:自然哲学、思维哲学、科学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决策哲学、领导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法哲学,等等。既然哲学是智慧之学,就让它成为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并将钥匙交给学生吧!□
标签:哲学论文; 创新教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杜威教育思想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爱弥儿论文; 哲学史论文; 梅贻琦论文; 张伯苓论文; 大学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学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