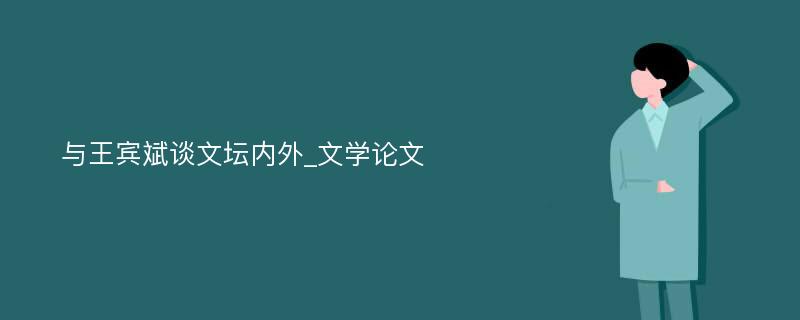
与王彬彬散论文坛内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文论文,王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采访人:瘦马
被访人:王彬彬
采访时间:1995年12月12日晚7∶45
王彬彬个人档案:1962年出生,安徽人,78年考入洛阳外语学院,主修日语;8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获文学博士学位,现职南京军区创作室,按世俗的眼光,他的出名应归于近期文坛上的“二王之争”
大陆文坛最近露了些活气,纵然是吃了洋参丸之类的补药,毕竟能够开口说些话了,但这一开口不要紧,言辞之间竟透着耸人听闻的味道。非但圈内人听着来神,门外的看客也跟着起哄了。
关于王蒙王彬彬之间的争鸣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一二,由于事不关己就不想当真。某日在报社做差的朋友打来长途想让我找王彬彬探探虚实。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离看客为时不远了。囿于手头资料的缺乏,文章一直未能做成。
等到11月份“西方电影与当代中国电影”研讨会在宁召开期间碰到《钟山》杂志的王干时,我又知道敢和王蒙较劲的人原来是咱们金陵城里暗伏已久的“快枪手”(王干给别人封头衔似有“立等可取”的功夫),王干推销同行的热情甚高并答应给我王彬彬的电话号码,与王彬彬通了电话,他说夫人刚生了一女,整天来往于医院与家中,忙得一团糟,过了数日我又打去电话,他答应约个时间聊聊,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采访录。(注:以下“瘦马”简称“瘦”;“王彬彬”称“王”,否则有捞取稿费之嫌)
瘦:你在单位有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平时的时间宽裕吗?主要写评论文章吗?
王:只要出一定的学术成果就可以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还挺多,不过最近很学术的东西写得少,杂文随笔等短的东西不会放弃,它们的价值是别的东西所取代不了的。
瘦:这是一种市民化的需要。
王:这大概不能说是市民文化吧,比如杂文。
瘦:关于“二王之争”,我手头的资料不多,也只是听说,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大约是去年我在《文艺争鸣》上发了篇文章……
瘦:事情是不是主要围绕你的那个“说法”?
王:是的,我提出了“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说法。
瘦:当时你是基于什么动机呢?
王:这个感觉由来已久,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创作心理层面,可以说是个“创作心理学”的概念;另一个涉及到文化人格的层面。从“创作心理学”的层面看,我说的“过于聪明”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聪明”,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形而下的东西过于发达,生存手段技巧过于发达生存智慧过于发达,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情势就会受到压制,艺术创作总需要创作者天真一些,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天真就没有艺术。
瘦:但是我听说有评论家认为,你的这种看法是因为没有对王蒙这批作家经历的切身体验,他们是从历史走过来的人,他们对自我的保护应该得到理解。
王: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能不能被理解是一回事,至于他们具有了这样一种聪明对文学创作的不利是另一回事,比如说这筐桔子烂了不好吃,我仅仅指出桔子烂了不好吃。
瘦:指出的一种带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命题。
王:对的。
瘦:萧乾先生好象也站出来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王:因为我的那篇文章中点到了他。他在1994年的《中国青年》上发了一篇文章举了文联在批判胡风时的一个例子:美学家吕荧曾站出来为胡风说话,后来遭遇就很惨马上被押进监狱,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萧乾就以此作为例子告诫年轻人:人有时候不要过于讲真话。他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不可以理解是另一回事。从一个文化人格的角度讲就不合理。在那场胡风运动中如果完全没有象吕荧这样的人我们的民族会是多么可悲,正是有了他,才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保持住了一点良知。
瘦:你的这篇文章刊出后在学术界引发的震荡很快又在媒体那里产生了炒作效应,本来正常的文化批评硬要被冠之“二王之争”这样带有明显耸人听闻的符号,你个人对此有何看法?
王:这是传媒的特性,所以我从来不掺合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从不使用“二王之争”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不准确的,就包括你今晚来跟我聊聊,如果非要付诸文字。……
瘦:不要提这件事……
王:提是可以的,但希望不要用采访记的方式。
瘦:从个人偏好上讲我也讨厌那种做法,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可能有些生疏。
王:在你之前有很多人来我都拒绝了。
瘦:你回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愿被媒体介入被观照?
王:新闻界要介入毕竟是新闻界的事,我个人无法阻止。很多事情媒体一做就可能歪曲事情的本质,大多数媒体不可能真正进入事情的核心。
瘦:传媒总在讨好它的受众。
王:对。
瘦:前段时间我跟南京的一些人文学者教授做了一些交流,感觉他们对流行媒体比较敬而远之。他们似乎有种顾虑:自己是做学术研究的,如果经常在些街头小报上抛头露面会被同行低视,我说这个时代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价值上讲有些偏颇。
王:这个可以理解,比如你使用了一个“小报”的概念,“小报”这类东西确是针对一个市民阶层,事情一旦变成他们的文字,就成了一种文化快餐式的东西,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问题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有些问题牵涉到一个学者作家文化人内心最隐秘最圣洁的一点东西。你把它拿出来就会变味。
瘦:但是我觉得有些传媒在文化推广上做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比如北京新出的一张38版的《为您服务报》,从定位上看它应该是一张具有大众化(不是世俗化)口味的报纸。但它偏偏腾出一块专版用来做纯学术化的东西(“文艺沙龙”),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就文化界的理论思潮进行仁者见仁式的讨论,该报内部对此专版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样做值得嘉许,因为这里面还包涵着文化传播的意义。所以,你刚才说的作家等类人的内心的东西不容易得到完整的表达和阐述也不是尽然的。
王:我也希望在电视晚报上看到一些很严肃的东西,这总归比一些很扯蛋的东西要好,不过这里面肯定存在一个你所说的天然的矛盾,媒体不可能将两者坚持得很好。坚持得好必然违反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采取一些无关痛痒又具刺激性的手法来迎合其受众。如果定位在很纯正的思想文化的性质上,它慢慢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瘦:你平时即兴写的一些东西比如随笔等是不是也属于市民文化的范畴呢?
王:这些东西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不一定就要属于市民文化的文本。严格来讲中国最早的学术著作(论语)先秦诸子不就是随感式的吗?不可以长短论其本性,作为我来说,我只能把握我的每篇文章本身决不变成迎合市民口味的东西。
瘦:在现代作家群中我个人比较偏好张炜和王安忆,张炜的作品一向大气,而王安忆的小说则具有相当可读性,你认为呢?
王:张炜是当代作家中最具情怀的作家之一。王安忆是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且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好的女作家,至少目前如此。
瘦:作为市民阶层他们在小说的阅读上经常存在种种障碍和困难,有些作品似乎是写作者本身设置的,有些是不是可以归结到阅读者本身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积累上来呢?从评论家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所有的文学问题不可能说得很明了,阅读大概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有时候的确存在一个接受者本身的素质问题,有时是创作者的装神弄鬼,所以阅读上的问题还是要就事论事。作为小说它应该具有故事性,你读任何一个作品前面一二千字能不能把人拽住是很重要的。
瘦:业余时间进行文学阅读的人数,不容乐观,比如我平时忙于琐碎的事务,小说的阅读时间是挤了又挤的,感觉中当代小说是被肢解的,失去了应有的阅读趣味常常面对的是一些堆砌的文字,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你有何见解。
王: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只是现在表现得更为尖锐,有个基本点是肯定的,文学应关注社会,关注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小说一方面应该赢得更多的理解(不是让它去媚俗);另一方面又不可能所有的小说都变成通俗小说。
瘦:苏童我相信是你不陌生的作家,他的作品好象变得越来越……
王:越来越好读呢还是难读?
瘦:他的小说倒没觉得难读,但他的作品总贯穿着阴暗潮湿的气味,不适合在阳光下阅读,他的作品总是很“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当然他现在很成功,作品大多被影视化了。
王:苏童在小说创作中有他的很多特长,作为纯技巧,他的叙事能力是很卓越的,也即是讲故事的能力很突出,这是作家最基本的能力。他的创作有一种很固执的心理倾向,也可以说是他的审美兴奋点老是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往往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事导致一场大悲剧,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体验生活的独特视角。这样一直下去他最好的小说你读了以后总有一种重复感。他最好的作品是过去的一些短篇,写少年时代的。我认为苏童最擅长的恐怕还是他的短篇,但有时候语言又非常流畅一泻如云。
瘦:在我接触的一些评论家中,对于叶兆言似乎较苏童更为青睐,叶的小说人文气息重一些,有大气的东西在里面。
王:叶兆言毫无疑问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如果要分别一下的话,苏童是才智型的作家,叶是技巧型的作家,两人不好论高低。
瘦:最近几年在国内的文坛边缘出现了一个被称之为“小女人散文”的创作群,她们在流行传媒上以日常生活为底色随意勾兑,据说颇有人缘,不知你有否耳闻?
王:“小女人文学”的一种小小的情怀有它表现的权利,但这些年来有一种铺天盖地的趋势,甚至“小男人散文”也很盛行,写些猫狗一类的东西。这些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时尚就值得注意了。1994年我曾就此现象撰文予以猛烈抨击,也曾惹恼了一部分人,我不是想把“小女人散文”全部驱赶出局。
瘦:前段时间我在广州与黄爱东西聊了聊。她说她的散文有人读贴近生活已经相当不错了,她不想去关心什么终极价值文化关怀。我想这个问题再展开,那就牵扯到普通老百姓的快乐与文学家的快乐观了,作为寻常的人从生到死,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的精神重荷,他们可能活得相对轻松些。
王: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问题被越位去理解,比如我们讲精神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每个人都去充当宗教徒,任何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纬度在那里,而我们最近面临的是一种更高的精神纬度被放逐的局面,即把世俗生活推向极致,一种标准化,打个比方,不是说森林中不能没有野花野草小动物,我们保护老虎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狐狸全部消灭掉,只是说在人类的生态环境中不能没有老虎,老虎倘若灭种灭绝狼成了最大的,狼灭绝后狐狸成了最大的,这样下去甲壳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了。现在我们强调张炜张承志并不是讲要把所有的黄爱东西全部灭掉。
瘦:当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谈论同一个对象时很容易失之偏颇。
王:任何一种观点如果“全面”就不成其为观点了。任何人提出某种观点只能站在他(她)的立场上。
瘦:你个人是不是相信所谓“绝对真理”的东西?
王:真理本身就有很多层面,从深刻的哲学范畴讲当然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全在一般道德伦理和日常生活层面当然有绝对真理了。比如“人不吃饭就要饿死”,它就是一个绝对真理。
瘦:但是一旦科学能够提供质的飞跃条件,从而改变“人不吃饭就要饿死”或者“太阳从西边出”这样的规则,我们曾经信奉的诸多真理(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会不会訇然坍塌?当然这只是个妄想。
王:人对自己所身处的世界还很无知,宇宙是个什么东西?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没有穷尽也就超出了人的想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