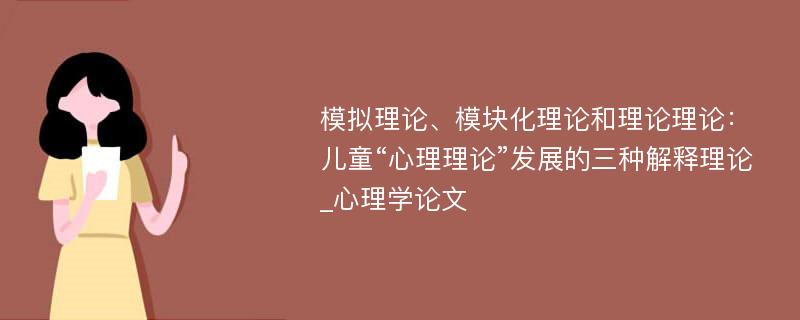
模拟论、模块论与理论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三大解释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三大论文,模块论文,儿童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个世界上,理解“他人”(Other people)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但关于我们对自己特别是“他人心理”(Other mind)的理解的研究,长期以来属于心理哲学家的研究领域。自80年代以来,发展心理学家开始对儿童是如何理解——有人称“发现”——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这一新的领域进行探究。一方面,他们发现并描述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大量观察与实验事实;另一方面,也试图对这些事实提供心理学解释。由于心理学家各自的理论假设不同,迄今为止已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解释理论,其中以“模拟论”、“模块论”和“理论论”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所谓“社会建构论”、“内省主义理论”等)。本文拭图在概述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观察与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三大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观点和存在的问题作出述评,以便推动和深化我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
一、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观察与实验事实概述
正如我们从当今发展心理学的现状中所看到的,心理学家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事实的“描述”,往往要多于——更确切地说是“优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这在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中就更是如此。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所谓儿童的“心理理论”,是指儿童具有一种按“信念”、“愿望”、“意图”等来解释人的行为的常识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儿童是“常识心理学家”。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儿童的这种心理理论并对此作出解释,就可以适当地称之为关于“儿童心理理论的理论”。
目前,已有一些不同学科在这一研究上合作。哲学家长期争论我们的心理理解——我们的常识心理学——的性质和起源。比较心理学家探索这种能力的进化。现今关于认知进化的一种流行理论认为,理解(并因而操纵)我们“同样”的能力,是人类智力得以发展的驱动力。他们还广泛进行关于灵长目理解心理状态的能力研究。临床心理学家提出,自闭症障碍涉及到“心理理论”能力的缺陷。社会心理学家探索我们如何理解像“人格特质的稳定性”那样的心理方面。人类学家则表明,关于“心理”的基本假定从跨文化方面来看是不同的。
然而,现今最广泛的心理理论研究是在发展领域。也就是说,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是最富有成果的。从近来关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大量观察与实验事实来看,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儿童似乎从惊人的早期年龄(可能从出生开始)便理解“心理”的重要性质,而且这种知识也随着发展而经历广泛的变化。80年代开始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3至5岁儿童对“信念”和“实在”的理解。大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和相关的变化。Perner发现,这个年龄的儿童,在理解事实上信念可能是错的方面有困难。在一个实验中,儿童看一个封闭的糖果盒。当他们打开它时,它显示在里面有铅笔而不是他们所预期的糖果。询问儿童:在他们打开之前,另一个儿童会认为盒子里原先是什么?3岁儿童前后一致地说,这个儿童会认为盒子里有铅笔。他们不理解另一人的信念可以是错的。有研究表明,当问及儿童他们自己刚刚过去的“误信念”时,他们往往犯同样的错误。儿童说,他们也曾认为在盒子里有铅笔,正像他们预测其他人将认为在那里有铅笔一样。Flavel等表明,3岁儿童在理解“外表”与“真实”之间的区分方面有相似的问题。例如,给被试呈示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岩石的海绵,儿童坚持认为,这个客体既真的是一个海绵,又看起来像一个海绵。最后,3岁儿童似乎在理解他们信念的来源方面也有困难。在一个实验中,儿童知道被藏在隧道下面的一个客体——或者通过看见它,感受到它,或者把它告诉儿童。虽然儿童能辨别这个客体,但他们不能辨别他们是怎么样知道这个客体的。以上研究表明,这些相互关联的发展暗示出,在3到5岁之间,儿童对信念的表征特征有新的理解。(注:J.Perner,(1991).Understanding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Cambridge,MA:Bradford books:MIT Press.)
一些近期研究表明,理解误信念的第一个信号是当儿童把这个问题置于他们早先对愿望或知觉的理解的语境中时,或者当他们面临着与他们不正确的观点相反的证据时,就可能出现。他们可能显示某些关于信念的内隐知识——在他们使得这种知识成为外显知识之前。然而,这种非常早期的理解,与4岁或5岁儿童所显示的对信念的健全而联贯的知识相比,似乎至多是脆弱的和不完全的。
更近期的研究既探索了大跨度的年龄又探索了多样的心理状态。有广泛的证据表明:在3岁前,儿童就理解愿望的重要性质。这包括如下事实:愿望可以是未满足的;愿望决定情绪;甚至愿望在不同的人那里可以不同。同样,甚至2岁半似乎理解视知觉的性质。他们理解,如果两个人位于一个屏幕的相反方向,则他们可能看到不同的东西。3岁也似乎理解假装和想像的重要性质,他们能用这种理解在心理实体和物理实体之间作出一般的区分。例如,他们理解,假装成为一只兔子不同于真实的兔子,或者一个想象的玩具是私有的和触摸不到的,而一个真实的玩具则不是这样。Wellman广泛研究过关于心理状态的早期自发谈话。他证明,18个月和3岁之间的儿童在实验室任务中的确没有显示出这些能力,但他们也自发地用这些术语来解释人的行动,并从愿望转换到信念说明。(注:H.M.Wellman,(1990).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Cambridge,MA:MITPress.)
随着心理学家研究越来越小的婴儿,要肯定他们对他人进行真正的心理归因,往往会变得更困难。然而,对非言语行为的研究表明,甚至婴儿也理解心理的某些性质。婴儿模仿的研究表明,在儿童对他人动作的知觉,与他们对自己内部运动状态的知觉之间有天赋的联系;看见他人作一种特殊姿态的新生儿,将作出那一姿态本身。同样,非常小的婴儿对人的面孔和声音显示出特别的偏好,并与他人从事复杂的非言语交流式相互作用。到9个月,婴儿开始跟踪他人的凝视,并把客体指向他们看。在著名的“社会参照”行为中,当婴儿面临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时,就转向查看成人的面部表情,与其相一致地调整自己的动作。这些非常早期的能力表明,我们的“心理理论”有着强烈的天赋成分。
然而,儿童心理理解的其他方面直到5岁后才显得成熟。例如,虽然非常早期阶段的儿童就理解情绪,但他们仅仅在大约6岁才能理解真实情绪与情绪表达之间的差别。同样,理解心理的推理特征似乎是相当困难的。能理解简单的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当问题涉及到对模棱两可刺激的多种解释或信息的更复杂的来源时,仍然有困难。最后,儿童在相当晚的年龄似乎才理解有关意识的现象学——如“意识流”的存在——的基本事实。如6岁儿童报告:人们在深度无梦睡眠的中间能有意识地决定翻个身,或相反,一个是醒着的但还坐着无所事事的人,就全然不会有思想或内部体验。(注:A.Gopnik and A.Meltzoff,(1996).Words,Thoughts and Theories.Cambridge,MA:MIT Press.)
二、模拟论:儿童用自己的心理资源来“模拟”他人行为
以上所概述的观察与实验事实,尽管不是所有研究者都公认的,但基本上还是可靠的。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解释这些事实。自6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解释应该说是“理论论”。就其一般的涵义来说,理论论认为,人们预测和解释人的行为这一日常能力,其起源应该是大量内隐的一般知识或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都需要使用它。但从80年代以来,理论论受到了所谓“模拟论”的挑战。具体说来,1986年,J.Heal发表了论文《复制与功能主义》,R.Gordon发表了《作为模拟的常识心理学》。随后,A.Goldman于1989年发表了《心理学化的解释》。这些论文标志着模拟论正式形成。“模拟”(simulation,或称“心理模拟”)论,是专门针对理论论所谓“一种理论构成日常心理能力之基础”这一假定提出来的。根据模拟论的说明,人类能够使用他们自己的心理资源来“模拟”他人行为的心理学根源。最典型的是在一个“假装”的意境内作决定。其共同的方法是“扮演角色”,或者“使自己处于他人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模拟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对于这一假设,模拟论者作了如下论证:
从理论来源上看,模拟论者追随的是笛卡尔常识心理学观。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享有特权地通达或存取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在笛卡尔看来,心理的内容对于我们主体是自明的(他称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人对“自我”的认识根本不成问题。倡导笛卡尔常识心理学观,就意味着要否定理论论的这样一个观点:儿童是从“第三人称观点”探索他们自己和他人心理的问题。因为理论论者坚持认为,在儿童推论他们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中,本质上不存在差异。无论是推论自己还是他人心理,都要求把像“信念-愿望框架”的某种东西(亦即某种理论)应用于所观察到或预测到的行为。与此相反,模拟论强调“第一人称意识”的至关重要性。因为我们直接通达我们自己的心理,没有必要运用一种所谓理论去理解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仅仅似乎是“在线地”(on-line)体验心理状态。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模拟论者认为,仍然没有必要使用像一种理论的东西来解释他人的思想和行动。我们理解他人心理的方式是通过一种“类比”过程: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经验,并模拟在某种情境下我们所做、所想或所感受到的东西。
而且,模拟是“加工导向”(process-driven)而不是“理论导向”的。这是用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设想模拟:人自己的行为控制系统,被用作其它这样的系统的可操作模型。首先是离线地(off-line)理解这一系统,以至于输出不是实际的行为,而仅仅是行为的预测或预期。输入和系统参数因此并不局限于那些调节自己行为的人。许多模拟论者认为,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控制系统被用于给他人建模,故而关于这一系统的一般信息就是不必要的。这样,模拟就被说成是加工导向而不是理论导向的。按Gordon的通俗说法,我把假想的信息输入我自己的决策系统中,然后让我的决策系统“离线”运行,即作出决定,却不产生任务行为。然后我接着说出那个作为“离线”运行之输出的决定,而这就是我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模拟是加工导向的。
最后,模拟是一种“内部建立的特殊化机制”起作用的结果。这是由近期模拟论的杰出代表人物Harris提出来的。为了解释儿童怎么样通过参照自己的心理状态来相似地理解他人,他提出,人类具有一种在发展早期就被启动的“内部建立的特殊化机制”,使得婴儿能从事像享有共有的注意,或者体验共有的情绪那样的“主体间活动”。例如,在发展早期,他人沮丧的显露将激发婴儿的移情反应。他们似乎把他人的沮丧体验为他们自己的。这种初期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致使婴儿首先通过直接地或“在线”地体验这些共有的意向状态,来关注意向性对象。
Harris进一步论证说,在第二年,儿童便开始理解像情感或知觉那样的意向状态,是指向于世界中的特定目标的。这致使儿童能“模拟”他人与目标客体的意向关系。他称这种模拟为“离线”模拟——其涵义是,儿童本身不必直接作用于目标以便模拟他人可能感到或思考的东西。在第二年初,儿童能使用这种能力指向他人的行为,如通过指向他人对先前没注意到的客体产生注意。这一年龄儿童也开始通过简单的嘲弄和欺骗的行动来操纵他人的行为。而2岁儿童假装的出现,是早期使用关于世界的“仿佛”模式——亦即不断地使用想像——的能力的证据。这种想像的能力与对意向态度的理解并行发展,直到儿童能超出他们自己的直接的心理体验,而仅仅想像他人的心理状态。这样,不断提高的想像能力与“理解性的意向”一起发展,就产生了在线地模拟他人的信念和愿望的极大力量。(注:P.L.Harris,(1992).From Simulation toFolk Psychology:The Casefor Development.Mind and Language,7,pp.120-44.)
根据以上论证,模拟论者认为,使用这种“心理模拟”的模式,就没有必要具有一种“理论”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儿童需要做的一切仅仅是想像:他们正在体验他人具有的信念和愿望。因而他们不必乞求于一种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行为。一旦从事模拟的能力得心应手,任何随后的发展都是逐渐更强有力的模拟的结果。随着儿童想像能力的提高,他们更能够根据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知识进行回想,以便模拟那些与他们自己渐渐不相似的心理状态。到4岁时,他们能解决“误信念”的标准测验,因为他们能模拟或想像那些他人会信以为真的虚拟事态。这样,在3岁与4岁之间的明显差别,不是被看作心理概念的某种戏剧性转换——正像理论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而相反是看作一种利用不断准确的模拟的能力。
三、模块论:心理理论发展中的天赋因素
与模拟论和理论论都不相同,模块论(module theory)试图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天赋因素提供说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Leslie。他提出,儿童的心理理论是作为一种“硬接线的”或天赋的处理机制起作用的结果才成为可能的。这种机制采取人脑中的一种“特殊的、封闭的模块”的形式——一种“心理理论机制”(TOMM)。心理理论机制的出现,为人提供了从事“元表征”的能力。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具体论证:
Leslie采纳的是“福多式模块”的标准理论。这一模块理论主张心理模块是天赋特化的、功能独立的。他特别强调福多式模块的两个特点:一是模块是天赋的或“硬件化的”,具有固定的神经构架(遗传上特化的);二是模块是“领域特殊的”(只关注与其特殊处理能力相关的信息)。
Leslie假定,人脑有一个作为模块的心理理论机制,在儿童大约4岁时——这是儿童时期的一个关键点,这种模块相对地突然打开。也就是说,一个预先设置好了的、用于理解他人心理的功能模块准时启动了。对于Leslie来说,大约18-24个月早期假装的出现,暗示着在意义与所指物之间作出区分的能力,以便理解作为表征的信念。于是2足岁儿童就已有了元表征能力。为了给Leslie的“元表征理解”怎么样起作用提供一个例子,请想像如下情境:一个学步儿童正在看母亲假装一个香蕉是一部电话。根据Leslie的观点,他并没有混淆地认为母亲握在耳边的黄色东西真是一个电话,因为他能把作为一只香蕉的真实香蕉的“初级表征”与作为一个电话的香蕉的“次级表征”分离开来。换言之,他能理解,这个香蕉不是一个真的电话而是在这一游戏情境中作为一部电话的表征。即是说,他具有对一个表征的表征即“元表征”,这就是所谓心理理论的标志。
如果在2岁的幼小年龄元表征能力就已经形成了,那么为什么要花很长时间儿童才通过标准的误信念任务?Leslie断定,在“心理理论机制”被启动之后,发展是相对连续的,在
3和4岁之间观察到的差异不是反映了一种极端的理论转换。相反由较大儿童表现的优越的作业成绩可以按儿童信息处理能力的更一般进展得到解释。
为了说明儿童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Leslie提出,除具有一种“心理理论机制”之外,为了在评估元表征理解的多样的任务(如标准误信念任务、误照片任务、误地图)上取得成功,儿童也必须具有一种适当发展了的“选择处理器”(SP)。正是这种选择处理器,使儿童能从事像抑制各种习惯性反应那样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在误信念任务中,要求儿童使用“选择处理器”来从事像抑制他们自己对客体实际上位于何处的知识——以便准确地报告他人的误信念——这样的执行功能。正是“选择处理器”的逐渐增强,导致了在3和4岁的心理活动能力之间出现明显差异。这样,标准误信念多样性任务,就不是测验信念的理解,而是反映了儿童推测那些信念的准确内容的能力。于是Leslie得出结论说:就3岁儿童的“心理理论机制”来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错误的东西。(注:A.M.Leslie,(1994).Pretending andBelieving:Issues in the Theoryof ToMM.Cognition,50,pp.211-38.)
四、理论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就是“理论形成”过程
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论”述评》一文中,作者就理论论所持的基本观点、它的理论解释力以及存在的迫切问题方面,作了初步的讨论。(注:熊哲宏:《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论”(The theory-theory)述评》,《心理科学》2001年第3期。)这里,我们根据新近所掌握的材料,就理论论的新进展、特别是理论论的某些新变式作如下分析:
首先,据理论论者对“理论”一词的不同理解,可把他们分成“弱”理论论者和“强”理论论者。前者是指他们把理论一词理解为一种“常识心理学”,即按信念、愿望、意图等来解释人的行为的理论。后者是指他们在与科学理论相类比的意义上使用理论一词。据这种用法,儿童对心理的认识或理解本质上是像理论的,具有与一般科学理论同样的基本特征。
其次,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是作为一个动力学系统的过程。正如Gopnik等坚持认为的那样,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不是静态的。理论按其本质是动力学的并向变化开放的。理论论者把科学理论的这些特征应用于在儿童思考心理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根据这种观点,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假设检验”过程。幼儿开始于简单的理论以预测行动。起初,儿童完全用他们已有的理论透镜看这个世界。当暴露出与他们的理论相反的证据时,儿童只是忽视或蔑视这种事实。然而随着反证的不断积累,儿童的思维的过渡便开始发生。一种转换的最初信号是,当面临特别突出的反证时,儿童开始发明一种企图把他们已有的理论坚持下去的辅助解释。当辅助解释渐渐地不再能说明累积的反证时,一种新理论的微光就开始出现了。起初这种新理解仅仅在非常有限的领域才看得到。最后的一步是充分成熟的革命——旧理论被思考世界的更适当的新方式所完全取代。
最后一个问题是,一种心理理论的标准或标志是什么?这在理论论者中极不一致。作为理论论的一个新变式(或者说一种主题上的变异),Perner同意Wellman等人的观点:儿童的确利用一种理论,发展的过程涉及到大约4岁时发生的戏剧性的理论转换。
然而,Perner不同于Wellman的地方是: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理论。对Wellman来说,心理状态的理解处于儿童用来预测和解释行动的理论框架的核心。一种成熟的心理理论,是通过开始把信念理解为表征并能在信念愿望心理学中适当地应用它们而标志出来的。与此对比,Perner把表征更广泛地解释为一种成熟的或“表征性的”心理理论的规定性特征。于是发展的东西就是对表征的理解这一更普遍的认知能力——或从事“元表征”的能力。据此观点,一种心理理论的基石就是这样的洞察:一种东西能与世界中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表征关系中。表征以许多形式出现,如图画、尺度模型(Scale model)、地图,或者信念全然是实在的表征。由于这种对表征的广泛理解,儿童才能使用某种像信念愿望心理学那样的东西。
在这种元表征性洞察之前,儿童心理知识的性质是什么?Perner提出,起初儿童只具有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的非常简单的能力。他把这种初始状态称之为一种简单的修改着的模型之一。如果现有的模型受到新信息的挑战,那么该模型就被修改,旧的信息被消除,这样旧模型被放弃而支持新模型。在第二年,儿童开始能拥有世界中的事物的多重模型。他们现在能一次思考一种情境以上的东西。例如他们能思考一个过去事件而记住现在。他们能从现实往回行进,并从事假装。Perner称这个年龄的儿童为“情境理论家”(situation theorists)。儿童也开始理解像思想、知觉和假装那样的心理状态,但这种理解是有限的。Perner坚持认为,在4岁前,儿童把心理状态和其他表征仅仅设想为与一种事态相符合的情境。例如他们理解:爸爸滑雪的照片正好是在另一境地或情境中的爸爸。具有情境理论的儿童所缺乏的东西,是把心理状态理解为事态的表征这样一种洞察。他们不能在意义(表征的媒介)与所指物(它所表征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这样,通达唯一一种情境理论的儿童就会在误信念任务上失败,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把信念和信念的内容分开(例如,麦克关于他的巧克力所在位置的“信念”和巧克力的实际位置)。
然而,根据这种模式,3岁儿童的失败不应局限于理解误信念这样的任务。如果3岁正是处于“把握”情境理论中,缺乏元表征的洞察,那么他们应该在获得表征的理解的任务上都失败。他们的困难应不只是限于那些涉及心理状态理解的任务上。对这一观点的某些支持来自Zaitchik设计的“误照片”任务上3岁儿童的贫乏作业。在这一任务中,一个照片代表一个特殊的客体或景象(或著名的芝麻街人物——伯特)。当照片在显影时景象变化了(如伯特离开了,他的朋友Ernie取代了他的位置)。然后问被试:当照片显影完了时它将会显示什么。3岁儿童不正确地报告:照片将描写新的景象。理解表征的性质具有的普遍困难,其近期证据是“误导的路标”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不正确的显示描写一个女王的位置的路标。尽管3岁被试本身知道女王的正确位置,却错误地报告,路标描绘了正确的事态。(注:J.Perner,(1991).Understanding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Cambridge,MA:Bradford books:MIT Press.)
五、对三大理论的初步评价
应该说,在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各种可能的解释类型中,模拟论、模块论与理论论是目前最具竞争力的三大理论。它们不仅比较系统(相对而言模块论要弱一些),而且各自对大量观察与实验证据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如果我们从中立的观点看(即是说,不站在其中任何一种理论的立场上),这三种理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纵观近20年的研究,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尽管这三种理论彼此之间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和批评,但它们似乎都过多地求助于各自所依据的观察与实验数据,而很少深究各自理论本身的缺陷。下面我们着重讨论这一点。
先看模拟论。首先,从理论来源看,模拟论不过是心理哲学中关于“他人心理”问题的传统解决方案的现代变种,严格说来其理论建树不大。早在20世纪初,罗素在解答笛卡尔他人心理问题时就提出了“类比”说。根据笛卡尔的心身观,如果心理是独立于身体的实体,那么我们又何以可能知道他人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中?我们何以确定他人或别的物种真会具有我们称之为“心理状态”那样一种东西?罗素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往往是通过基于自身情况的某种缄默的、未明确表述的推理,来获知他人在想些什么或感受到什么。我们知道,在我们自身的情况下,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通常导致某种身体事件。故当我们从他人那里观察到这样的身体事件时,就很自然地推论他是处于相关的心理状态中。显然,罗素是从心理事件与身体事件之间有因果联系出发,我们从自身的情况中得知这种联系,然后将其应用于他人的情境中。简单地说,我们是通过把他人与自身相类比而获得他人心理的知识的。应该说,这与现今的模拟论声称人用自己的心理资源来模拟他人行为,并无实质区别。
其次,模拟论在关于他人心理理解的获得机制上仍是基于心理学传统的“内省”观,这就使儿童推论他人心理的合理根据问题更加悬而未决。模拟论将儿童对他人心理的理解建立在“我”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相似性觉知基础上,这就使他人心理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且是一种令人可疑的可能性)。我有什么权力——更合适的词是“特权”——仅仅从一个单一(我自己的)情况来推论并知道任何他人的情况?这正如我此刻感到葡萄是“酸的”,就推知所有其他人也会感到是酸的。这显然极不合理。实际上,这种模拟观早就受到维特根斯坦的挑战:根据传统的内省观,我们是从自身内部印象或对于自己心理的操作的觉察来获得观念的,心理所能意识到的直接对象是其自身的“观念”。但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显然不是通过什么内省来了解知觉、记忆和思维的。因为如果我是从我自己的情况中获得“心理”的概念的,那么我又有什么根据来确信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他人的心理中?我显然需要有合理的根据来相信真的存在着他人心理。因为如果我只能直接了解自己的心理,那么“他人心理”对于我而言就只能处于推论的地位。这样,又何以能断言:婴儿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
最后,心理理论研究的不言而喻的假定是,儿童按其对心理的常识理解来预测和解释人的行为,但模拟论的倡导者又承认,模拟论的强项在于“预测”,而不在于解释。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解释当然是需要某种“理论”的,而一般性预测则可以不需要理论。尽管模拟论一般所说的预测是指预测他人将来的思想和行为,但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何以能够以自己的心理状态为资源或源泉来预测他人的行为?进一步说,“我”能够在任何意义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状态下——预测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吗?实际上,我们成人往往也不善于解释自己的行为。在人工智能研究中,“专家系统”的性能总是比不上人类专家那样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专家往往说不清楚他是如何从事“问题解决”的。近期关于“婴儿主体间性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主体间动机的有意识探测是非对称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意识到他人的情感和意图要比我们自己的内部状态多。”(注:Edited by R.A.Wilson,and F.C.Keil,(1999).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Scien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pp.416.)因此,尽管模拟论者说,随着儿童的想像能力不断提高,模拟的准确性也就越来越强,但仍然未能说明儿童心理理论的飞跃性发展(如3至4岁间的理论转换)是怎样发生的心理机制。
再看模块论。应该承认,模块论既有理论解释上的一定优势又有较多实验事实的根据。就前者来说,模块论(特别是福多式模块)关于“心理的模块性”能够解释许多事实或数据,例如领域特殊性、功能分解、自主性和强制性等现象。就后者而言,似乎模块论最强有力的方面之一,是有可能解释在自闭症儿童情况下发展在哪里出了问题。自闭症儿童似乎不能自发地从事假装游戏。他们也典型地不能完成误信念任务。正是根据这些发现,Leslie坚持认为,自闭症是“心理理论机制”的一种特殊损害。
但是模块论——至少在目前的解释状况下——有两大缺陷:第一,天赋“心理理论机制”的假设主要是建立在对自闭症儿童的观察与实验之上的。他们有大量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自闭症儿童没有这种能力,或者只处于很低的水平。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是否这种心理活动的缺陷就是自闭症的核心缺陷。自闭症确实以一些损害为特征,却只有其中的一些与“读心理”(mind-reading)有关。例如,自闭症儿童也能从事重复性行为,也有某种受一定限制的兴趣,以及识别模式有困难。还有人依据自闭症儿童不会说出完整的故事,就断定他们缺乏心理理论机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假定更多的“缺陷模块”来解释这些多样的损害。问题是,这种假定到底有没有尽头呢?
第二,模块论总是与天赋论有着亲缘关系,因而天赋论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总是模块论所不能解决的。模块论多少得到了认知科学某些成果的肯定,因而可以说它使得传统的“天赋论”在新背景下再次复兴。这是因为,模块论与天赋论有着内在的联系。有人指出:“天赋论与模块性在如下意义上是不同的:天赋论是关于认知怎样发展的一个主题(涉及到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经验输入这一观点),而模块性是关于认知加工是怎样被组织的事情。但这两个研究方案显然又是相互支持的。因为,同样细化的模块组织,应该仅仅通过普遍学习过程在多样的经验输入之上进行操作,就被复制在不同个体中,这一说法全然不是合理的。模块似乎是特殊化的、专门的认知机制,支持模块性的主要理论论证之一——至少相关于知觉输入模块——是,使得认知被结构化的方式有适应优势。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适应优势将需要通过对于模块系统的发展进行指令的遗传传递而被复制下来。”(注:G.Botterill and P.Carruthern,(1999).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56.)于是,人们经常对天赋论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模块论。
最后我们看理论论。我们已经指出了理论论至少存在三个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即与“科学”相类比的合理性问题;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问题;关于心理理论发展的机制问题。这里我们再从心理学解释的角度看看它的主要缺陷。当理论论者在解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事实数据时,有一个重大的概念上的误区,即他们在两个不同“论域”中使用“理论”一词: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心理理论中的“理论”,另一个是作为研究者的解释工具的“理论”。把这两个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的两个词混淆使用,就使得他们的解释显得过于牵强。当他们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理论”或心理理论一词时,是指儿童能按他们对信念、愿望和意图等的常识性理解——即儿童的常识心理学,来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心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儿童对信念、愿望和意图等常识性理解的发展。但是,当他们对这种“发展”作出他们理论上的解释时,却把这种发展解释为就像科学家的“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他们的解释给人的印象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就不再是对诸如信念或愿望的常识性理解的发展,而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理论的发展。难怪这种解释令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难以接受。他们反驳说,儿童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不是我们科学家用心血和汗水所构造的那种理论。说“儿童是小科学家”,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的;但要说儿童的理论与科学家的理论完全没有本质性区别——这正是强理论论者所断言的,恐怕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会承认。
从理论根源上说,理论论者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某种科学哲学的科学发展观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儿童发展的研究上。理论论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Gopnik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一直试图以一般方式指出,科学家和儿童可能利用了相似的认知结构、相似类型的规则和表征。我们能更详细地描述这些认知结构的特征吗?什么类型的规则和表征可能——既在科学家又在儿童中——被涉及到理论和理论变化?对于发展心理学家来说,这里是这个隐喻获得最有用和有价值的地方。我们的策略——至少起初——主要是纯粹采用科学哲学中关于理论和理论变化的详尽描述,把它们转译成认知心理学的术语,看看它们怎么样适合心理学的材料。”(注:A.Gopnik,(1996).The Scientist as Child.Philosophy of Science,63.pp.485-514.)且不说他们所选取的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合理,单就他们把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与科学理论发展相提并论,就会留下争论不休的心理学解释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