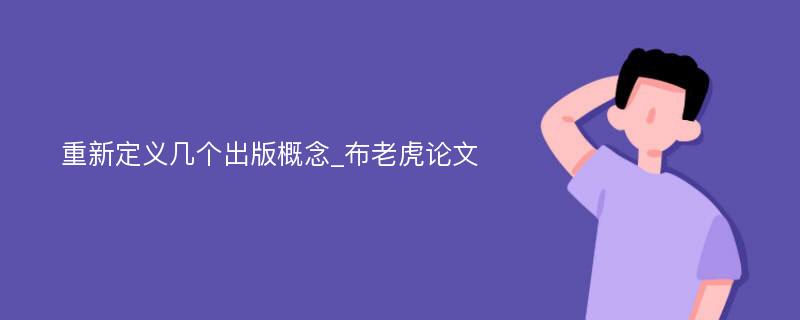
对几种出版理念的重新厘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要轰动一时,还是要存在永远
“我们的事业不可能轰动一时,但将永远存在”,时常想起马克思这句名言,然而对照抢热点、赶浪头、走马灯般纷纷攘攘的畅销书市场,我们毕竟要问:能有多少东西长期占据我们的书架?能有多少东西留给我们的后代,留给我们的民族?!我以为致力于长线而大气的标志性出版物开发是我们眼下走出市场疲软困境的理性选择。
怎样开发标志性出版物呢?这可能是令每一个出版者煞费苦心的事。
1.取决于出版者的政治意识。出版者在制定长效选题计划之前必须深刻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牢牢把握出版的“两为”方针,不能设想,一个在政治上出了偏差的“标志性出版物”是多么大的浪费和可笑!
2.取决于出版者的文化情结。这几年随着出版迈向市场,如何挣钱甚至如何卖书号:似乎成了一个编辑能耐大小、本事强弱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编辑人的“道”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曾云,“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这种“出世”思想就是一种对现实功利的超脱,对一种精神本体的形而上的追求。表现在编辑人心目中就是应该具备文化关怀的“道”的境界。这种貌似抽象却很实用的“文化关怀”,针对出版的决策者来说,似乎应当有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韧性追求;针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编辑人来说,似乎要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清苦。前者的优秀代表我们可以学学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后者的优秀代表可以看看三联书店迄今为止尚没有获取任何奖项但绝对有殉道精神的著名编辑许医农先生。如果遥想本世纪初如张元济、邹韬奋等灿若群星的现代出版家们,更是让我们高山仰止矣!
3.取决于出版者的平常心态。做标志性出版物一定要秉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平常心态,一开始就惊天动地、好大喜功,往往会事与愿违,而精耕细作、小心培育、逐渐扩大,一以贯之,坚持数年下来则不失为名山事业。这方面在80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与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可以给我们以良多的启示。在思想启蒙方面,《走向未来》是绝对功不可没的,我想每一个在80年代进入大学的青年人都曾受过这套丛书的嘉惠,而且这套丛书还是整个80年代唱响“文化热”的主角。就重大影响而言,《走向未来》应该算是标志性出版物了,但后来可能因为《走向未来》是80年代第一套有影响的丛书,所以在丛书的策划上显得经验不足,后劲不够,以致于后续的书目有很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不成熟的地方了。而钟叔河先生精心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虽没有大张扬但却是完完整整地留下来了。另外,标志性出版物的最高境界是品牌。
二、要创造特色,还是要创造品牌
这几年来“创造特色”这个词经常挂在社长老总们的嘴边,可能因为讲得太多,这个词的本身的语义定位往往就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显然,一个结果已经在告诉我们:数年过后这些秉持“创造特色”四字理念作为办社方针的社长老总们似乎并没有在自己的领地办出“特色”来。
我以为一味地强调“特色”,而不将“特色”如何准确地定位,或者再将这些富有“特色”的定位如期地付诸实施,然后再将这种有实际内容的“实施”进行理念总结识别,并上升到CI策划(corporation identity,即企业形象)的高度,那么这个出版社的发展将永无“特色”可言。因为没有“特色”定位也就无所谓大的发展。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社会里,一些具有现代眼光的著名企业已经很少抽象地提“特色”二字了,因为“特色”虽是一种对个性的描述,但“特色”本身固有的内容不发展、不定位,“特色”反而变得十分平庸或者变成遮护平庸的幌子。其实精明的商家早已将“品牌”二字取代“特色”二字,所以我主张在当代出版界当用鲜明准确的“创造品牌”来替代“稳重”平庸的“创造特色”。
那么如何去创造品牌呢?
1.调整出书思路,即长效书→标志性出版物→品牌书。
我不反对出版社尤其是人民出版社要经常出版一些时政类书,这些书可以给出版社带来一时的经济效益,但我以为重点还是应放在长线即长效书的出版上。有了长线打算就要扩展成标志性出版物,之后又要在横向上发展壮大再发展成品牌。在这点上胡守文先生强调的是由品牌发展成标志性出版物,我却以为顺序恰恰应当颠倒:由标志性出版物到品牌。品牌只是标志性出版物理性的成熟的发展结果,这一点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布老虎丛书》就可以明白。“布老虎”无疑已成为当代出版界一个成功的品牌运作了。起始的“布老虎”只是一套长篇小说,后来因为市场营销的成功,《布老虎丛书》开始得到广大读者尤其得到白领阶层的厚爱。春风文艺出版社当时没有陶醉于眼前的成功,而是将丛书继续扩大,在纵向上扩展原有思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标志性出版物;在横向上开发《小布老虎丛书》、《金布老虎丛书》,并同时注册“布老虎”商标,成立“布老虎有限责任文化公司”,将“布老虎”品牌资产进行正式评估,价值亿元。此时,“布老虎”这个概念已深入人心,其品牌地位也瓜熟蒂落矣!不难理解,是有了《布老虎丛书》这个标志性出版物才有“布老虎”这个品牌的确立。
2.培养一种出书策略:大“火箭”、小“排炮”。
关于这一点我在《出版广角》1998年第5期曾撰文讨论过。所谓“火箭”效应即是指在一本书或一套书推出之后一定要在前面逻辑范围内紧接着推出第二本或第二套。所谓“排炮”效应即是指规模效应,一套书最好能整齐推出,切忌“拉羊屎”。眼下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正在进行规范的品牌运作,首先是“三思”这个名字的策划就颇具匠心:“三思”一是指英文“科学”(science)的音译,二是指孔老夫子一句名言“三思而后行”,这个双关语等于将“科学”与“人文”的两种精神旨趣协调在简洁明了的“三思”二字里,在品名上为整个丛书将在科学文化里面开掘选题打下坚实基础。其次在“三思”这个总名确立之后马上又接着开发了“知识经济系列”、“科学与反科学系列”、“科学史系列”、“科学家传记系列”等子系列丛书,每个子系列之后还开发了若干个子选题,目前关于这套书的口碑越来越好。
3.明确目标,找准位置;突出重点,抢占高地。
前面两句是说以什么样的规模来明确在可以预期的时期内(5年或10年),在出版方面所要达到的怎样的整体水平,后两句要围绕已经确定的思路为中心,选好主攻方向,抓住有影响全局或者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大选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抢占文化制高点。关于这方面我想结合“三农”图书说几句。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中国最大的图书市场也将会在农村,有些省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去开发“三农”选题,并且将图书出版战略重点转移到“三农”图书出版上,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现在如果能抓住这个制高点,将会在5年或10年以后收到惊人的效益。有一些专业社上报的选题在策划上缺乏精心创意和长远眼光,在销售上居然说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挣不挣钱没关系,等等。这些就足以有理由让人担心将来的“三农”图书是如何模样了。我在这里斗胆建议:作为农业大省要么不做“三农”选题,要做就一定要做出品牌,并且一开始就要树立品牌意识。“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秉持“品牌”意识来做“三农”图书哪怕一开始就严重亏本也比目标模糊、盲目投入要高明得多。金盾出版社现在已成为全国出版“三农”图书的名牌社,在我们感叹农村没有市场的同时,他们保持每一种几乎都在几万册以上的发行量,原因就是如该社总编室主任肖健夫先生所言:一开始就有精心策划,就有品牌战略。因为金盾为社之初没有一分钱支助,全靠自己在创业阶段“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式的运作才有今日“金盾”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相对于我们有些人提出“无偿地送书”、“不计成本”的“三农”选题运作法,我们自身是不是显得有点儿幼稚和冬烘呢?刚开始可能挣不到钱,但“有意识地亏本”和“无意识地不计成本地投入”两者谁明智,便不言而喻了。不过,我还是坚信有地方出版局领导的英明决策和常抓不懈,有编辑同仁的戮力同心,必将催生一系列标志性“三农”出版物和品牌出版物。
三、要偏安一隅,还是要走向世界
有一种惯常说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几乎成了人们对文学艺术审美批评的一句经典,用在文艺批评领域则有相对恒久的价值,如果放之四海,振振有词地拿到今天作为知识生产的出版业里来,可能要作另一番审思明辨。作为出版业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总是强调出版的地域特性,似乎只要立足本省挖掘本地的地域文化优势,就可以旱涝保收、长治久安。在科技相对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是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但到了信息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知识产业化的20世纪末,出版业如果还拥着一方水土闭关自守、靠山吃山、自说自听,则难以持久了。
当前出版界的“偏安一隅”有两个突出特点:
1.主张靠自己的地域文化作为自己的出版特色;
2.各省教材教辅学生用书实行行业垄断、贸易壁垒,似乎有教材教辅的保护就可以抵挡住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上面两种出版人的善良愿望能否长期兑现,且先看一种现状:首先,我们正在面临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为重要特征,以知识资源的开发作为社会进步主要动力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其特点是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次,出版业又面临着高新技术的迅猛挑战:电子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这些不断提高的高科技含量正在迅速成为当代出版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从刚刚结束的200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外出版社大量买进中国大陆的版权,而中国大陆出版社则向海外出版社买进版权又创历史新高,一本儿童读物《哈里·波特》经过激烈竞争之后最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尘埃落定,这充分说明中国出版市场已成为全球出版市场的重要部分这个铁的事实。既然我们已无法选择地置身在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知识社会、经济全球化社会里,光靠一点地域文化来做为自身发展的特色,实在有点小鼻小眼、顾影自怜了,而且马上又会面临一个出版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不断吸纳现代先进科技文明才会有出版的大发展、大气象。如外研社李朋义社长明确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沟通世界文化,传承人类文明”。另外,靠行政命令,靠一些老关系来保证自己的教材教辅能在省内一统天下,恐怕正在被市场的一体化打破。事实上每个省的学生用书均在互相渗透,各省的教辅垄断正在被一些著名的品牌教辅打破。
我们的出版既然不能在一块小天地里小打小闹,那么又该如何进军大市场走向世界呢?
1.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加入WTO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出版物市场不可避免要成为世界出版物市场的一部分。当国外精品图书疯狂拥入中国市场时,我们自己的图书是被挤兑出局还是占有特色优势?
我以为中国出版物在进军世界市场时有三点可以做到:
a.先不奢求去国外拓展市场,先保证在国外图书进来时我们能保证固有的市场即是初战告捷。
b.炎黄子孙遍及全球,尤其是东南亚一带,我们可以开发一些初级华文读物,满足广大海外华侨的寻根之需。
c.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出版发行到欧美。这项工作中国近代一些来华的传教士曾做过,但当代的地方出版社也只是有湖南人民出版社开始关注这项空白,该社副社长伊飞舟先生曾撰专文谈过这个问题,颇为引人注目。
2.吸取国外文化精华,引进国外版权。事实上这几年我们有一些出版社不再迷醉于“地方特色”而走出国门买进版权,单1996年全国引进版权就达2515次,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品牌书《三思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汉译大众精品》,就是大型的版权购进举措。
3.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要善于发掘和积极推出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的体现“中国话语”的学术著作(下文将详述),只要学术水平能达到国际一流,西方的出版商自然会来主动洽谈版权。
四、要积累文化,还是要学术原创
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开始,到“编辑”二字第一次在《汉书》出现“编,所以联简次也;辑与‘集’同”,编辑的含义就是辑集校勘、审定编次,于是编集前人成果,积累前人学术文化便成为编辑天经地义的职业含义。在当代出版界“积累文化”更是有热闹非凡经天纬地之举;如各种古籍的整理,各种“大全”、“全编”的泛滥,各种“×××文集”、“×××全集”的流行。他们似乎在无可厚非地兑现编辑的元典意义:积累文化。但是我不禁要请教一句:如果我们20世纪后半叶的出版全是汇编前人学术文化成果,那么到下个世纪后半叶我们的子孙来“百年回眸”时,我们本身留下了哪些东西让他们去“积累”呢?如果没有,他们岂不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再重新做一次,既如此,下世纪只要保留古籍出版社就足矣;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让后人去整理,那么我们现在出版的意义还存在吗?我们以为“积累文化”的“积累”二字当有新的理解:即不仅仅是对前人成果的被动汇总,还应该体现知识的增量和学术的原创,这才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积累”,才真正体现作为以“积累文化”为天职的出版的现代意义。
从以下现状可以看出出版学术原创著作的前景。
1.我们作为跨世纪的出版者正在有幸置身于一个知识社会的学术原创时期。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呼吁中国学术的“中国话语”(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正在成为每一个学人的使命。广西师大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距世纪学人文存》已出版22卷,已经有代表性地向我们展示了当代杰出中青年家人的学术风貌:打通中西,出经入史,卓然成一家言。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期望有巨大学术创获的学术群体。如果漠视这种学术现状起码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不负责任。
2.从这几年社科人文学术著作销售来看,有思想深度、有学术价值的高品位专著正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改革的深入也促使人们对一些新问题要进行深层的学理思考。如三联书店出版的《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几乎每册销售都在10000册以上。北京四大民营书店就是专门销售学术文化著作的名牌书店,其生意兴隆,行情看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同样可以给出版社带来双效,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给复旦大学出版社、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给当代中国出版社均带来了极大好处。
如何开发学术原创著作呢:
1.耐住寂寞,守信长线。学术专著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同时在出版以后也不可能轰动一时,但学术专著的效果正如冷水泡茶慢慢浓——效果在后面。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至今还是那么耐读。
2.选题策划与作者的沟通。眼下在学术界和出版界有一点难以沟通:学术界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出版界不愿意出;出版界以为有市场的东西,学者们不屑于为。这种尴尬由来已久,且日益明显地昭示一种现实:学者们不轻易接受策划编辑的选题,学者们不愿意做命题作文,这说明一厢情愿的选题策划与学者的专题研究有大差距。一方面需要编辑与作者的进一步沟通,另一方面是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时不能凭主观臆测,要对你要实施这个选题的有关作者进行广泛仔细调查,看看他们手中正在做什么、能做什么。
3.编辑学术修养的提高。学术原创著作既然是一种学术创新,这就要求编辑自身有相当高的学术修养,能够鉴别有真正学术创造的著作,能与一流学者进行平等对话,至于平时多读书多钻研更是一种基本的素养了。
五、要适应市场,还是要创造市场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从来不愁一本书有没有市场——因为是卖方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卖方市场一下变成了买方市场,于是我们在召开选题论证会时常说一句话:“适应市场,开发适销对路的选题”。这是一句很“忠厚”的话,本没有什么错,但在“人情友谊不如商情”(张胜友语)的当代市场社会里,如果一味地去适应市场,你总有一天不再“适应”市场,被淘汰出局。
为什么要创造市场?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多说,至于如何创造市场倒是一个值得深研的课题。
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策划编辑严平先生曾对我讲过一件事:我想做100本原版英文经典学术著作。当时我一个本能的反应是:现在能看一般英文报刊的读者都极少,又去哪里找人来读你100本英文原版而又艰深的学术著作呢?他只是轻松一笑:这就是适应市场还是创造市场的问题了。当时这句话给了我很大震动。
1.市场是惰性的,只要有策划人的正确激发绝对有可能创造营销的奇迹。这方面最成功的莫过于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先生说过的一个例子:该社青年编辑蔡剑峰在90年代初期曾提出“90年代英文名著读物”丛书的选题构想,当时的英文读物至多是一些肤浅的语法、词汇知识的介绍,而出版英文原版文学名著在常人看来还要冒很大的市场风险,当时社里编委会一时还没有把握。后来蔡剑峰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及书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写出了长达30000字的选题报告,从各方面论证:原版英文名著肯定会有市场前景,而且还会填补当时英文出版的一项空白。其结果是每一种书均发行在50000套以上,创造了当时英文出版的一大奇观。
2.创造市场首先要发现市场的潜在需要,这其中需要出版者敏锐的市场直觉;然后将潜在需要变成现实需要,这其中需要出版者果敢的行动。
3.引进现代营销策划。现在谈选题策划较多而思考营销策划则少有。所谓现代图书营销策划不是简单的宣传造势,而是在对出版社、书店、内外部环境予以准确地分析并有效地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对一定时间内的图书营销活动的行为、方针、目标、战略,以及实施方案与具体措施进行设计和安排,是一项深谋远虑的系统运作过程,它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容。
a.营销现状分析:选题的可行性,同类选题的数量、出版社、发行量、竞争对手的状况,读者反馈情况,各销售商对该选题的反应,同类选题的运作情况。
b.营销策划的内容。整体营销策划:选题策划,图书包装策划,新书上市策划,培养市场与跟踪市场策划;局部营销策划:即对整体营销活动过程中每一局部的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