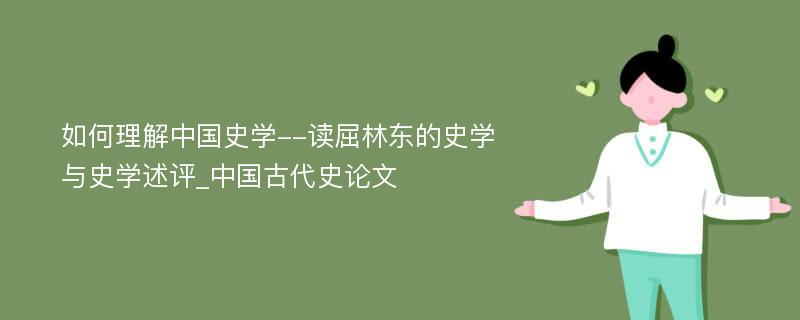
怎样认识中国史学——读瞿林东著《史学与史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瞿林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为什么研究历史、撰写历史、学习历史?这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会愈加深刻与丰富。如果你想进一步体味历史的魅力与底蕴,不妨走进一位史学家的内心世界与学术天地。
近读瞿林东教授所著《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深为其深刻、独到的学术见解所感染。
瞿林东教授习史、研史四十年,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他全身心地探索、思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并以史学家的责任与良知走进历史,凭其顽强的毅力和渊博的学识,拂历史尘埃,悟个中精义。《史学与史学评论》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许多认识弥足珍贵。笔者粗读该书,受益良多。
一、把史学研究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对待,这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读《史学与史学评论》,笔者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学术品格的力量。瞿林东教授在《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中充分肯定了这种责任感与求真、经世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的钥匙。
这种认识道出了中国史学家的历史责任,反映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基于这一认识,瞿林东教授提出了史家的社会责任在于求真与经世,并提出史家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和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史家的角色意识同史学的求真要求相关联,史家社会责任同史学的经世目的相贯通;而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家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
收入本书的文章无论是论史学、札记、短论还是书评、序跋,或是内涵深刻的史学的沉思,或是有关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启示,都给人们以教益。例如,七万多字的《论二十六史》显示了瞿林东教授对历代正史进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与宏观认识。
二、回答了中国史学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推动史学事业发展的自觉意识的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历史是一座宝库,那么,史学就是打开宝库大门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把钥匙就在史家掌中。史家的任务则应予以澄清、解释、说明。瞿林东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批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丰富的积淀与底蕴使他有勇气、有能力回答了其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如他对19世纪中期以来至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150 年来中国史学同中国历史的关系以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史学的本质和特点,关于中国传统史学之主体纪传体史书的整体面貌,历史、史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阐述。对“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理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反映了瞿林东教授的学识与功力。瞿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缺少发掘、整理、总结、研究。因为,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认识便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待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工作改进、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这个演变过程正是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这种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正是他致力于这一探索、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开创性成果。这一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三、重于通识,精于评论,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不断追求的目标。评论是史学自身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中国史学有重视评论的优良传统。评论的意义无庸置疑。不过真正做起来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评论者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评论者的理论修养、知识积累、认识水平、判别能力等等。笔者从《史学与史学评论》中,看到了一篇篇如抽茧剥蕉、似水银泻地的高屋建瓴之论。
史学评论并非是对评论对象的指手画脚;要取得评论资格,要求评论者有较高的通识素养。本书作者以治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见长,并在唐代史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唐代史学论稿》、《杜佑评传》就是作者唐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有了这种专门、精深的基础,他开始了“通”的追求。《中国史学散论》、《中华文明史》(十卷本)中所含史学各章即是瞿林东教授“通”的追求与成果。从《史学与史学评论》收入的23篇评论文章来看,涉及的评论对象,从时间上看有几千年;从领域上看,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还有专史;从特点上看,有宏观也有微观。如果缺乏“专”与“通”的结合,是很难涉足于这些评论的。瞿林东教授认为,对史学批评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这是由于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是因为人们自觉地关注不够,缺乏系统地发掘、整理、阐释,故这一宝藏尚未显露其光华。而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同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没有史学评论或批评,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他还从史学家与史学批评,思想家、教育家与史学批评两方面考察了史学批评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史学家和史学批评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批评,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
本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专著,但它的有些部分所收文章是按照发表时间先后编起来的;惟其如此,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艰难跋涉的足迹,看到作者是怎样在努力超脱本来意义上的专业的范围而把史学的视野投向历史、现实、人生的,有心的读者定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总之,《史学与史学评论》显示了瞿林东教授高度的历史自觉与理性精神,而这种历史自觉与理性精神恰是他几十年读史、治学道路的真实写照:“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做贯通的研究,从对历史过程的阐述走向对理论问题的探索,从当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作者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扎实而深入的道路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