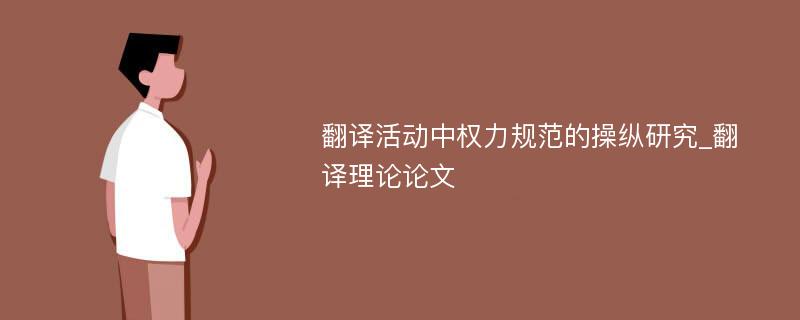
权力规范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翻译研究中,翻译的规范性研究既包括翻译过程的规范研究,也包括翻译作品的质量规范研究。译界学者最初将“规范”纳入翻译研究视野之时,认为翻译规范仅仅支配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所谓“规范”不过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对等。随着“翻译规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断有学者发表论文探究规范的本质以及规范与翻译关系,涉及翻译规范、规则、常规的本质、功能等一系列具体概念。毋庸置疑,学界对“翻译规范”的不同阐释对翻译的本体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角度各异的阐释也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混乱。要真正搞清楚一套理论的内涵,我们首先还得追根溯源。“翻译规范”概念滥觞于图里(Gideon Toury)的规范理论,图里本人对翻译规范定义如下: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把规范视为人们公认的普遍翻译价值和理念,如翻译的对和错,翻译的充分性和不充分性,并把这种价值和理念转化为适合某特定语境的翻译要求。同时,在特定的翻译活动中,明确提出译者需要遵守和抵制的要求以及译者需要容忍和许可的要求[1]54-55。
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翻译质量的标准主要涉及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如资深《圣经》译员约翰·比克曼(John Beekman)和约翰·卡洛(John Callow)提出“传译了原文意义和原文动态的翻译,称之为忠实的翻译。”他们进而解释,“传译原文的意义”是指译文对译文读者传达了原文对原文读者传达的意义或信息;“传译原文动态”是指译文应该使用翻译工具与自然的语言结构,且使译文读者轻松理解信息,译文与原文应该保持同样程度的难易度和自然度。此外,他们也认为翻译过程中,意义是第一位的,翻译者所要传达的是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或信息,而不是源语言的表达形式[2]。从上述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规范实质是译者权利的体现,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限于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研究重点已经从原文和译文的实质关系,转到了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针对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代理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代理人在有些翻译研究成果中也称为主体,他们自身的观念、兴趣等个人因素直接影响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从某种程度上预先决定译者的选择、策略、目标。作为基本的社会和文化现实,规范不仅仅与实际翻译操作过程有关,且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规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包括翻译活动中的预期、选择、决策、自查和结果评价[1]56-61。
古安维克(Jean-Mar Gouanvic)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行为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是译作在一个场域中通过关联性的权利制约实现译作本身和翻译过程的社会学[3]。这正凸显了以往翻译研究忽略的一个简单事实:翻译活动是一项社会活动,必然具有社会属性。以往的“翻译规范”研究仍然着眼于原文本与译文的关系上,因此不免落于“译文对等观”的窠臼。本文从翻译活动的社会活动本质出发,提出社会性翻译规范研究,将“翻译规范”研究纳入社会文化活动的范畴之内,还原其社会属性。社会性翻译规范的研究涉及翻译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惯习、影响翻译的社会权力、翻译活动发生的场域等领域。总之,社会性规范研究的本质是翻译权力的研究,包括代理人与翻译的操纵互动、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操纵互动和意识形态与代理人权力的操纵互动[4]28-29。
一、权力规范的相关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规约性研究(prescriptive study)向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的转变过程。对翻译规范性的探讨可以追溯到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的翻译理论,即严格规定译者该如何翻译。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之后,规约性翻译理论遭到广泛质疑。一些译界学者尝试用描述方法探讨翻译问题,他们重点研究支配源语与目的语文本生产和诠释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文化系统之中,认为翻译活动是受目的语文学系统中那些起规范作用的法则支配的。此时的翻译规约性研究已经从语言内部的规定性认识提升到外部的社会性规范研究上。
巴特(Renate Barts)认为“规范”是“正确概念的社会实现”[5]306。规范理论的任务是澄清规范的社会现实和梳理正确概念的客观性在一个社会中是如何产生、如何构建以及如何完成的,而语言规范理论是描写性的,主要探讨规范的种类和功能。语言规范是确立翻译标准的外部认识,翻译把语言规范引入就等同于把社会性规范引入到翻译的研究中来,在规范的制定和研究中,找到翻译规范发展的社会原动力。
第一位从翻译的角度系统地分析和研究规范的学者是以色列的图里(Gideon Toury)。图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翻译规范:期待性规范,此规范主要支配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方向性;伊始性规范,主要支配译者在译文充分性和接受性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在翻译过程中支配翻译决策和主流规范;主流规范指大家公认的翻译规范和要求。他认为,译者总是在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寻找妥协[6]73-76。在研究了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译学理论之后,他认为,规范理论旨在建立一套指导翻译行为的法则,包括标准化法则和冲突法则,规范是受目的语文化的制约和限制的,翻译的操作规范指导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1]61-62。
图里(Gideon Toury)之后,切斯特曼(Anderson Chesterman)(1997)等人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切斯特曼的规范理论涉及了社会、伦理以及技术等层面,他把规范划分为产品规范(期待性规范)和过程规范(职业规范)两大类。前者反映“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期待”[7]187,受目的语文化中主流翻译传统、目的语语类的语篇常规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切斯特曼(Anderson Chesterman)进一步提出了米姆概念,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7]5-6。切斯特曼还提出了超米姆的五种类型,他把翻译的规范界定为“完整的和全面的职业标准”[7]68。切斯特曼的规范理论更进一步证实了目的语文化的导向性和翻译规范对译文稳定性的制约。
赫曼斯(Theo Hermans)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规范理论。赫曼斯把规范分为“建构性规范”和“调节性规范”。建构性规范和调节性规范最初由诺德(1991)提出,她认为建构性规范“决定某文化社区如何看待翻译”[8]91-109,调节性规范处于建构性规范的内部,受建构性规范的制约,“总体上支配在文体层次下处理翻译问题的已接受的方式”。赫曼斯[9]25-51则认为,切斯特曼的产品规范和过程规范与诺德的建构性规范和调节性规范并无二致。赫曼斯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规范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其一,决定是否输入作品;其二,决定输入方式;其三,选择完成输入任务的途径,即翻译过程本身。必须指出,赫曼斯思考的并非翻译的心理过程,而是翻译作品的社会性和作品被接受或被排斥的可能性。
皮姆(Anthony Pym)(1998)认为,翻译规范的研究旨在探索翻译的稳定性,而忽视了权力和社会矛盾的变化,很少关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之间的矛盾。皮姆主要关注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关注译者的社会及其跨文化属性。他认为,目的语文化系统并不是对翻译过程、翻译职业道德或可译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唯一因素,处于文学系统核心地位的源语言文化对目的语规范的建构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译者总是处于两种语言文化相互交叉的位置。皮姆在规范研究中提出翻译伦理的讨论,他还认为切斯特曼的米姆概念观为翻译规范的伦理讨论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10]5-6。
上述描述充分说明了翻译规范研究是被提升到更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也说明了研究翻译规范社会属性的重要性。
二、权力规范的分类研究
翻译规范从社会属性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念和定义,图里(Gideon Toury)把规范分为伊始规范(initial norms)、期待规范(preliminary norms)、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和主流规范(mainstream norms)[6]73-76。在他的规范种类划分中,他从社会学研究方法入手,把翻译视为一项社会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翻译就有程序性特点和操作性特点。诺德(Christiane Nord)把规则(rules)、规约(conventions)和规范(norms)进行了详细的区分,他求助于言语行为理论,倾向于规约这一定义[8]94。诺德(Christiane Nord)之所以这样划分规范,因为他对翻译目的论情有独钟,在他的翻译理论和应用研究中,他从目的论中目的语文化制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规范研究。切斯特曼的米姆论,是把翻译活动放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来研究和探讨翻译规范,因此,他强调翻译规范完整性和全面性的职业翻译标准。从翻译的社会性规范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图里的规范划分标准,下文从主流权力规范、期待和操作权力规范、伊始权力规范的角度对规范展开讨论。
(一)主流权力规范
一般而言,规范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习惯,是社会化的结果。主流规范提供了一个可以保证顺畅交流的渠道,使译者可以预见译入语系统中的任何抵制因素。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主流规范有目的论的色彩,保证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特征。如果译者发现某些规范对自己是有利的,即有利于译本在译入语系统的语言和社会环境中的接受,则会采用这些规范。译者为了避免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即使不能很流畅地使用这些规范,也会尽量地遵守。对于译本的排斥和负面反馈,是对没有满足译入语中主流规范这一情况的反映。译文如果没有遵守翻译规范,必然会遭到惩罚,即受到译入语系统的排斥和拒绝。图里(Gideon Toury)认为,主流规范代表了“潮流”,同时伴随着“边缘和过时”,强调了翻译中的社会文化限定性对翻译效果的制约作用[1]54。例如,两个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交谈,一个来自异域的人,要想与主人进行和谐顺畅地交流,他必须遵守当地的交谈规则和禁忌。如果他对当地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人们的喜好和禁忌等都非常了解,那他就会使用当地的交谈习惯和语言习惯与主人进行交流,自然会得到主人的信赖和接受,谈话便能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期待和操作权力规范
翻译还有一种特殊的规范,是根据读者对翻译的期待而形成的,译者期待和读者期待有时会出现不一致,原因就在于操作规范。译入语文化中翻译的传统和译入语文化中流行的文本样式和模式决定了期待规范和操作规范的方式。如由于历史原因,源语言和译入语在话语权力上的不平等会形成某些翻译规范。由于译入语的读者总是有一种寻求异质感的期待,如果一个译本所体现的操作规范符合了读者的这种期待,读者会容忍译本中的某些内容与译入语系统中固定规范有所出入,因为这种出入会让读者读到具有异域色彩的内容。当然,读者的这种期待和容忍是有一定界限的,例如中国人用英语“long time no see”表示见面的寒暄,这种英语的表达方式现在中国人口语交流中较为认可,西方人也认可。
翻译的期待规范的形成是与主流规范有关的。虽然期待规范有时与主流规范有出入,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源语文化具有强势力量,源语和译入语在文化和话语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译入语的读者不得不接受。例如,文化强势民族翻译到文化弱势民族的译本,对于文化弱势民族的读者来讲只能一味地接受,满清末年中国国势衰弱,中国人只能接受英国人强加给的“西藏”翻译为“Tibet”,当然我们现在应该让西方人接受“Xizang”,而不是“Tibet”。另外一种可能是译入语读者认为源文本文化优于本土文化,因此会接受不同于本土文化和语言规范的异域文化规范。在图里(Gideon Toury)看来,期待规范体现了译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牵涉到社会因素下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期待规范反映了目的语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立场[1]61。
(三)伊始权力规范
伊始规范强调源语文化下译文的充分性和目的语文化下译作的可接受性,同时强调了译者在两个极端间的妥协[1]56。伊始规范是指译者在“异化”和“归化”之间如何选择的规范。这种理论认为在翻译中,译者要受到一定的实践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充分实现译者的主体性。伊始规范将“异化”和“归化”即“充分”和“接受”对立起来,并用规范进行固定,因而过于绝对化。伊始规范只是译者的一厢情愿,如果读者不接受伊始规范下的翻译结果,译者必须进行纠正和修改。伊始规范的应用与源语文本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强势程度有关,如果源语文本所处社会文化属于强势,则译者可以在翻译过程中用伊始规范,来达到理想的翻译结果,反之,则需要用期待规范来选择和决策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例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地主义的翻译理论都是对伊始规范的挑战,因为原来的翻译研究是在伊始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很多译本的产生都受此规范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一种惯习,在全球化的今天,惯习应该得到改变。惯习作为一种社会性翻译规范,必须适应全球化和世人对翻译的要求进行改变,从而实现翻译的文化社会性转向,这也印证了动态的翻译对等理论,所谓动态,必须考虑翻译的译本具有被读者普遍接受的要求,这种可接受性和充分性体现在译文对两个文化社会性的忠实程度。
三、权力规范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的实证研究
(一)意识形态权力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因素的一个方面,对翻译的影响包括选择、决策和评价,体现在翻译政策、经济政策、政治理论中。翻译现象与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权力可以被看作是影响翻译过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权力作用在翻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相当明显。例如,对于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和贺拉斯(Helasi)这种作家诗人而言,他们依靠罗马帝国强大的政治优势,通过翻译将古希腊文本的概念和篇章结构融入拉丁文本,这为罗马帝国的扩张打下了文化权力基础。这还意味着他们将文本解译并通过修正使它们适于目标文化体系。他们深信他们有解译和改写原文的权力,他们行使着绝对权力,没有谁拥有充足的文化资本能与之抗衡,争夺他们对解译的独家权力,各执一词的局面和唯一真理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1]39-51。
翻译政策是体现政府或相关机构的意志和意识形态,使翻译合法化的一个程序,从而将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置于经济、意识形态、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之下。历史与现实表明,翻译政策大多旨在对翻译现象给予财政、观念或精神支持。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政治条件或固有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国家与宗教相互作用的产物,对翻译的文本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作为政治管制手段的审查制度在当今世界屡见不鲜,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很畅销的书籍很可能在另一个社会或国家恰是禁书,这在媒体世界和出版公司的政策规定中都明确无误。出版规约一方面保障出版市场的有序化、合法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保护,是一种对于外国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行为的抵制。一般来讲,出版规约可以分为正式规约与非正式规约。正式规约往往是指那些由国家法律、政策等明确规定的约定,或是一些国际性的出版公约。例如,对于翻译作品的最为基础的规定是要求在翻译作品中有原作者的署名,以保护原作者的知识产权。而那些非正式的规约,虽然没有以法律条文等形式出现,但是它事实上是在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属性、道德规约、社会公德、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一种隐性的出版规约,而对翻译作品的出版起着很重要的监控作用。又如,一个有着国家宗教信仰的国家,是不能够接受宣扬无神论思想翻译作品出版的,而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翻译作品,更是被禁止出版,这是翻译作品出版的道德底线。弗米尔(Hans J Vermeer)和切斯特曼(Anderson Chesterman)对翻译规范的道德准则进行了讨论和研究[6]76-77。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性权力,对译作的选择和处理也有很大影响,有些翻译作品虽然没有触犯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宗教信仰等,但是遇到原作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译入语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不相符之时,如果译者在译本中对原作中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不加以处理,在出版时是不太容易被通过的。这就使得,一方面,译者尽量选择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与译入语系统相近或是相协调的原作进行翻译;另一方面,当译者遭遇到源语言系统和译入语系统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冲突时,通过“选译”“改译”“删译”“编译”等手法对原作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淡化处理,从而解决出版过程中意识形态审核上的障碍。谢天振教授认为,在《傲慢与偏见》的第34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初次求婚时的这段对白中的一句话:
I had not known you a month before I felt that you we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 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Austen,1972:224)
我还没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王科一,1956:227)
译者让她说出“天下男人都死光”这种粗话,不像原文那个有教养的女子应该说出的话。这种归化翻译既是归化于汉语的文学传统和语言习惯,也是归化于阶级斗争观,因此可以说是同时受到译语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12]229。
社会经济因素通常远比意识因素重要,经济危机时,翻译界乃至文化产业是最先受到影响的领域之一。在此背景下,指望任何形式的政府拨款或宣传行为以支持翻译活动都是空想。同时,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经常受到货币因素影响,往往体现在基于“文化政策”“出版政策”或单纯“经济原因”而采取的政策手段上,并且文本类型不同,采取的政策手段亦不同。基于此,具体翻译政策可以看作是影响翻译的重要的翻译规范的权力因素。
(二)代理人的“调解”权力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活动中的代理人包括个体和机构两类,个体包括读者、译者、作者和出版商等,而机构包括与翻译活动和翻译物出版相关的各个机构,两类代理人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属性,在翻译活动中,从预期到选择,从决策到质量评价的各个环节,代理人之间都会有冲突和不一致,这个时候就需要代理人按照社会规则来处理和协调达到一定的妥协,从而完成翻译的社会活动。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和译作主要取决于负责翻译作品的社会代理人。社会代理人本身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并且通过自身的活动辨证地对社会网络施加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具有显著的调解特征,翻译活动的代理人涉及译者、校对以及组稿商。巴哈(Bhabha Homi K)[13]29提出的“调解”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文化社会互动过程。在此语境下,可借用这一概念较为形象地阐明“调解条件”的必要性。在调解过程中,可以确定根据翻译选择和决策时制定的针对译者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自查和预期,以期在翻译之前和翻译期间预见其他相关代理人可能产生的反应,这包括校对人员和读者的反应。在翻译过程中的代理人受社会因素影响结束时,在印刷与发行这一层面,可以看出其它重要代理人也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出版商、系列丛书或杂志编辑等。据勒夫维尔(Andre Lefevere)的观点,他们属于“赞助人”系统的一部分。所谓“赞助人系统”可以理解为促进或者妨碍文学作品阅读、创作乃至重写的权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和机构等。赞助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宗教团体、政党、出版商乃至媒体[14]41-56。
翻译活动中的印刷和发行环节上的代理人也是翻译调解过程的一部分,不仅对译作的生产乃至翻译过程负责,而且还履行着实现翻译制度化的主体职能。换言之,他们发起翻译,并且使翻译行为得以实施。译者和出版商两者的权力虽不平等,但均是作用于翻译调解层面最为重要的代理人。译者是核心人物,与原作者一样,操作于某一社会环境之中。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经过了“信任,攻占,吸纳和补偿四个步骤”,使得翻译变成了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他认为不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了诠释,而且读者在阅读时也诠释了译文[15]142-143。翻译规范制约翻译,由于规范是预见性和既定的,因而往往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从既定的规范。规范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有积极的一面,译者如果无视翻译规范,任意跨越规范的话,则译文很难为译入语的读者接受。翻译规范为译者划定了一条译本被接受和认可的最低保障线,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避免了因没有标准和规范而漂移太远。有翻译规范的存在和支配,译者就不会轻易受惯习的影响而出现翻译质量的下降。
发行层面涉及的代理人和机构枚不胜举,发行代理人和销售代理人对译作的心态和辨识程度往往对译作的评价有很强的影响效果。翻译接受层面的代理人主要是图书市场,尤指广大读者。读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探究此范畴的立足点是全面研究读者的社会行为、政治觉悟以及社会环境。读者对译作的反映直接体现在译作的质量评价层面上,反过来,译作质量的评价也会影响到代理人进一步从事翻译活动时的选择和决策水平的提高。鉴于上述研究的复杂性,翻译研究人员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借鉴文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
宏观社会性因素影响下的代理人包括代表译者利益的机构或团体,在翻译活动中,这些机构的社会性使命体现在其为翻译立法过程中。立法的目的是保障职业译者的基本权利,这是社会性代理人的社会性体现。各职业翻译协会相互合作,促使有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以代表代理人利益为己任,试图建立职业翻译网络,将翻译过程关涉的诸代理人联系起来,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协会也是使翻译活动合法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们是翻译招标以及奖励、资助翻译宣传活动的关键代理人。
(三)文化知识权力对翻译的影响作用
文化知识权力包括各类与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相关的知识。1972年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学之名与实》的学术论文,堪称是描述性系统翻译理论的宣言。他提出了翻译的高度语境化问题,建议高度重视此类研究,促进翻译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包括所有知识都在无形中影响翻译活动。因此,要弄清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就首先要弄清翻译与知识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指出: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优势,而还要依靠知识;于是知识与知识的体现终于被理解成了权力的中心。翻译一直就是生产和体现这种知识的工具。[16]10
在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学之名与实》26年后,帕克斯(Gerald Parks)[17]25-35在讨论文化转换过程中译者的作用这一问题时,才试图“识别翻译社会学的可能内容,采用社会学方法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予以研究。”帕克斯依据的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形式理论及其范畴。他对从美国英语译人其它语种的众多翻译现象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译事,同时也隐约提到诸代理人的惯习以及“权力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等问题,并且认为就权力域而言,译品必须力争得到译语文化的认可。
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18]31详细探讨了“与文学活动相关的诸多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之间蕴涵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使其首先在文学活动中得以发挥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明显呈现文化社会学的取向,同时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近年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理论已成为翻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新近出版的众多学术文献足以证明这一点,出版的文献借鉴布迪厄的理论,或探讨某些范畴在翻译语境下的应用问题,或借用某些范畴对各种案例进行研究,以期对“翻译社会学”进行比较详尽地描述,从而挖掘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效果的评价。譬如斯密奥尼(Daniel Simenon)在“译者惯习的核心地位”一文中试图借鉴布迪厄的“惯习”这一范畴对描述翻译学进行拓展性研究,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译者似乎长期以来就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乐于对文化、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译者的这一第二性特征居然成为翻译活动评价尺度的一部分。”[19]1-39由此可见,译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其自身起码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另一方面,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20]159-168借用布迪厄的某些范畴知识对1945-1960年译介于法国的美国科幻小说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某一译本之所以在译语文化的文学领域得以流通,是因为它与原作有着相同的流通理据,并且特别指出译语文化的文学领域对译品的接受与欣赏享有绝对的权力,并对之施以具体条件。这些权力来自于译者自身知识的建构和知识能力的运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社会性翻译规范的角度考察权力规范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笔者在梳理权力规范的基础上,分别根据图里和布迪厄的学说,分类探讨和研究了权力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权力规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主导权、代理人支配翻译活动的权力、知识对翻译活动的操纵权力几个层面之上,同时这些权力因素交互制约能够保证翻译质量的稳定性。将“翻译规范”与社会学理论结合,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