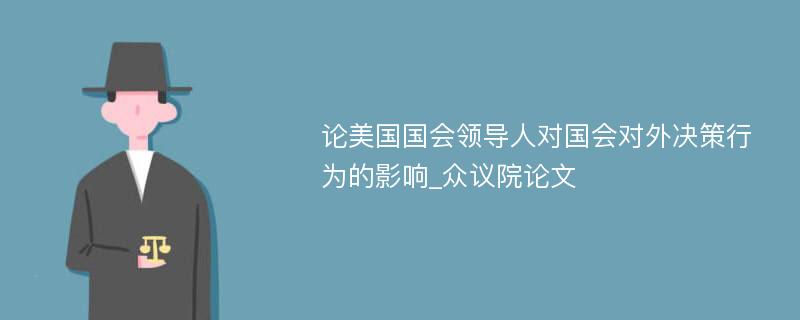
试论美国国会领袖对国会外交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国会论文,国会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领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越战后美国国会外交权力的复兴,国会开始越来越积极主动地介入美国外交政策领域,而作为两院议员中的领袖群体——“国会领袖”,对于凝聚两党共识、推动立法议程、左右国会立法和政策制定、影响总统、行政部门决策和国内舆论等方面无疑具有关键性影响。国会领袖的组织结构、国会领袖权力的行使、以及国会领袖对国会外交决策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始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结合对“国会领袖”概念的厘清、以及国会领袖权力和职能的分析,来研究其在国会外交乃至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概念的厘清:“国会领袖”及其构成
“国会领袖”(Congressional Leadership)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从狭义的定义来看,国会领袖包括参众两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注:参议院议长即为副总统,由于宪法地位以及历史发展沿革的特殊性,参议院议长一般游离于国会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只不过是一名负责主持会议的司法官员”,在立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而临时议长一职则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一般均由年高德勋的参议员担任,但是也并无多大实际权力,多数党领袖才是参议院真正的权力中枢。)、两院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多数党党鞭(party whip)和少数党党鞭。他们构成了国会两党领袖群体中传统的第一梯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政党在国会立法、政策制定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增强,参众两院中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成立和加强了一些指导性、协调性组织的权能,从而使这些政党组织的领导也跻身国会领袖的行列,其中包括参议院的民主党政策委员会(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主席、民主党党团会议(Democratic Conference)主席、共和党政策委员会(Republican Policy Committee)主席、共和党党团会议(Republican Conference)主席;众议院则包括共和党党团会议(Republican Conference)主席、共和党政策委员会(Republican Policy Committee)主席、民主党党团会议(Democratic Caucus)主席、民主党指导委员会(Democratic Steering Committee)主席等。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国会实施立法监督、议题设置、确定党派战略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国会两院两党的次级领袖团体。
为了加强国会领袖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性,近几年来国会领袖结构中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职位,例如1997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达施勒设立了一个新的领袖职位——“议场领袖助理”(assistant floor leader),任命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布赖恩·道根(Bryon Dorgan)担任该职,协助领袖进行议场协调。(注:Roll Call,Dec.3,1998,p.16.)而共和党也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多数党领袖助理”(assistant majority leader)。(注:Peter Stone,“Playing Second Fiddle,”National Journal,July 11,1998,p.1612—1616.)在107届国会中,参议院共和党增设“多数党党鞭顾问”(Counsel to the majority whip)一职,由缅因州女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Olympia Snowe)担任,以便争取本党女参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Richard Armey)也增设了一个与参议院同名的新的领袖职位——“多数党领袖助理”(assistant majority leader),任命纽约州众议员里奇·拉齐尔(Rich Lazio)和蒙大拿州众议员詹姆斯·泰伦特(James Talent)担任该职,以协助其“制订议场议程、确定立法和联系战略、进行领袖决策。”(注:CQ Monitor,Jan.21,1999,p.8.)时任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也在党内增设了“民主党领袖助理”(assistant to the Democratic leader)的职位,由康涅狄格州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担任,其职责就是“监督政策的协调、协助领袖进行信息沟通和研究、以及加强与新任议员的联系等。”(注:CQ Monitor,Jan.8,1999,p.4.)此外,格普哈特还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领袖顾问”(Leader Council)班子,其成员分别来自本党六个国会次级议员组织,即国会“黑人联线”(Black Caucus)主席、“西班牙人联线”(Hispanic Caucus)主席、“妇女联线”(Women's Caucus)主席、“新民主党人联盟”(New Democratic Coalition)主席、“进步联线”(Progressive Caucus)主席、以及保守的“蓝狗联盟”(Blue Dogs)主席,协助其进行利益协调和劝说工作,并加强对本党议员投票行为的统管。(注:Roll Call,Jan.7,1999,p.3.)
二、协调与管理:国会领袖权力的行使
国会领袖是国会制度结构中影响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国会领袖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两院的正常运作,针对各种不同的立法议题及优先顺序和管辖权问题进行不断的磋商和妥协,促使和保证重要法案的顺利通过,由此确保本党的政策取向和政治偏好得以实现。此外,国会领袖还要利用其影响力对国会内部各个派别、集团、以及独立色彩浓厚的议员进行协调和统筹。(注:DeAlva Stanwood Alexander,History and Procedur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16),pp.257—58.)
但是国会两院纪律的松散性和议员的独立性导致国会领袖既不能对本党议员进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也不能强制本党议员按党派划线投票行事,更缺乏对他们进行纪律制裁的手段,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依靠说服和诱导。两院两党领袖必须善于使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利益杠杆,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才能使国会这个松散而强调个性的立法机构团结一致并高效工作。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参众两院尽管业已形成了基本相似的层级化的领袖结构体系,但是由于两院各具特色的运作规则和程序,从而导致国会两院领袖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行使权力的行为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众议院,由于多数党严格控制着立法程序的安排,加之两党议员的纪律性也比较强,因此两党议员跨党投票的情况较少,即便有时发生这种情况,由于两党议员席位往往相差较大,因此即使有少数议员不依从本党领袖的意志,对于法案是否能够通过一般也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由此导致众议院领袖对本党议员的“控制权”,或者说影响力比参议院领袖要大得多。但是即便如此,众院领袖一般也不愿强制本党议员因遵从领袖的意愿而违背其选区利益,在工作过程中也主要是依靠说服和劝导,而不会对本党议员颐指气使,对于“跑票”的议员,也不会施加纪律惩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国内政治的)角斗场上,这一场争斗中的对手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场战斗中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任何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都不会关上同自己的那些敌人(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对话与和解之门。”(注:Barbara Sinclair,Majority Leadership in the U.S.Hous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40.)
尽管在众议院的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坎农这样的“沙皇式的议长”,但是随着1910年“反坎农革命”的成功,尊重议员的平等权利再次成为众议院运作的“第一法则”。例如在1940—1961年间担任国会议长的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就曾指出:“昔日敲桌子骂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领袖必须依靠说服、善意和最佳的理智来领导,这是他能实行领导的唯一方法。”(注:U.S.News and World Report,Oct.3,1950,p.30.)20世纪70年代,国会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众多资深议员退出参众两院,雄心勃勃、个人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的大批年轻议员进入国会,自由派民主党议员人数激增,加之委员会主席由议院党团秘密投票产生,以及数量多达100余个的小组委员会的兴起和职能的扩大,使国会权力进一步分化,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两党领袖的权力和权威。
此后,众议院领袖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绥靖”和安抚的手段,利用各种权力和利益杠杆,调和本党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的议员团体、派别,甚至个别议员之间的分歧,来促进本党立法议程的推行。例如,曾在1986至1992年间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汤姆·弗利(Thomas Foley)就曾慨叹:在众议院,两党领袖已经越来越难以真正实行所谓的“领导”,领袖必须时刻牢记议员在任何议题上都可能会反对国会领袖的意志。(注:引自笔者与汤姆·弗利在2002年3月12日的访谈记录。)现代的议长还不得不经常充当其党内冲突的调解人,一位国会领袖便曾无奈地指出:他必须随时注意努力平息党员之间的矛盾,防止党内的裂痕扩大,有时他还必须召集持相反观点的人,通过让他们彼此畅谈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以最终促使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在此过程中,任何强制性的“命令”手段都将毫无用武之地。(注:Barbara Sinclair,Majority Leadership in the U.S.House,p.38.)
与领袖权力不断遭到严重削弱的众议院相比,参议院历来是一个极为崇尚政治传统、注重惯例、信奉“无控制”原则的机构。对参议员个人意志的尊重和平等权利的高度强调,导致参议院个人主义倾向在参院建立之初便十分强烈,参议院也因此常常被描述为一个“由相互批评的人组成的集体”。(注:Guide to Congress,3rd.edition,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2,p.90.)曾在1981年至1985年间担任多数党领袖的田纳西州参议员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甚至在一次演讲中说:“担任参议院领袖就像是在管理一群猫(herding cats),你必须试图使99个独立的人采取一致行动。”(注:Congressional Record,105th Congress,2d Session,July 16,1998,S8375.)由于权力的高度分化,参议院两党领袖几乎从未拥有过对普通议员发号施令的“硬权力”,其作用的发挥只能更多地依靠平衡、协调和劝说等“柔性”手段,以期将本党议员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推动本党立法议程的实现。
例如,曾担任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多年的林登·约翰逊(Linden Johnson)便享有“妥协大师”的美誉,因为他深知:“党领袖唯一真正可用的权力就是劝说权。”(注:Malcoln Jewell,Samuel Patterson,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Random House,Inc.1986),p.125.)继约翰逊之后担任多数党领袖的曼斯费尔德则明确宣称:“我自己不相信受人逼迫有什么好处,我也从不逼迫别的参议员。”(注:Frank Mackman,ed.,Understanding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81),p.10)而在1977年当选多数党领袖的罗伯特·拜德(Robert Byrd)则这样描述自己的作用:“我没有权力,但我熟知条规,我熟知惯例,我熟知程序表,因此我处在为他人服务的位置上。”(注:彼得·沃尔主编:《美国政府内幕》(李洪、徐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35页。)107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也直言其必须采取“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的方式来进行领导,其原因在于“要100位参议员达成一致意见从来不是一件易事”。(注:James Barnes,“The Senate Broker,”National Journal,Dec 21,1996,p.2733.)
以107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为例。(注:2001年11月,由于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士·杰福兹(James Jeffords)退出共和党,原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斯勒接替洛特成为第107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参议院,达施勒一向以其行事低调和平易近人而著称,在两党议员席位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达施勒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轻触”(light touch)的领导方式。“他坐在办公室里,其他民主党各委员会主席或是重要议员不时来到这里,与他讨论下一次投票的战略战术。他耐心地倾听,从不试图仓促行事(rush things along)。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富有技巧地切换着话题,与不同的谈话者讨论,而且给每位议员都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只要他们愿意,他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同他们讨论。”(注:David Nather:“Power and Patience:How Daschle Picks Party's Battles,”CQ Weekly,December 8,2001,p.2886.)在普通参议员的观点意见与其相左时,达斯勒也“倾向于通过劝说和妥协,而非通过强制手段……来凝聚本党的共识。”(注:David Nather:“Power and Patience:How Dasclde Picks Party's Battles,”p.2891.)曾在1995—1996年间担任达斯勒的高级助理、后改任克林顿总统最后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翰·伯代斯塔(John Podesta)曾这样描述达施勒:“我从不认为他会走进房间,对其他议员大叫大嚷,发号施令,对于他所处的位置,他不能这样做。”(注:David Nather:“Power and Patience:How Daschle Picks Party's Battles,”p.2892.)对于绝大多数议员及其助手来说,达斯勒的这种“轻触式”的领导方式,是他的长处,而绝非弱点。正是借助这一“以谋求共识为取向的”领导风格,达施勒使两党众多参议员感到他们能够真正地“参与到决策中来”,从而成功地将惯于自行其是的同僚团结在一起。正如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所说的:“参议院不能依靠铁拳来进行管理,……我们永远都不能低估这一点的重要性。”(注:David Nather:“Power and Patience:How Daschle Picks Party's Battles,”p.2892.)
三、国会领袖影响国会外交决策的行为方式
尽管如上文所述,国会领袖无法对两党议员进行硬性的“统治”和“领导”,但是毕竟国会领袖手中握有一系列重要的权力和资源,国会两党议员在一般情况下,都不愿公然反对或违背领袖的意志,从而为自己在政治生涯的升迁道路上设置无谓的障碍。普通议员对领袖意志的尊重和服从在外交事务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会议员主要关注的都是国内事务,对于与本州或选区利益无关宏旨的外交事务并不十分关心,也缺乏必要的国际视野,因此,大多数对外交事务缺乏了解的议员往往愿意追随本党领袖的意见。此外,通过设立专门委员会、建议甚至要求常设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对总统和行政部门进行直接游说、发表公开言论影响国会和公众舆论等方式,使得国会领袖的态度和意志更易于被普通议员所接受,进而对国会外交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概括而言,其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会政策立场的“风向标”
作为国会的领导群体,国会领袖的言论和观点也更多地受到国会议员的尊重。每当面临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政策纷争,需要国会做出反应的时候,普通议员往往会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希望知道国会领袖的反应,以便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国会领袖的言行无疑起着“风向标”的作用,影响着普通议员的立场选择。与此同时,国会领袖所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向美国公众乃至全世界就国会的政策取向作权威性宣示,一旦国会领袖就某一政策议题发表见解或是表明立场,外界也都习惯于(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其视为国会整体的态度和取向而予以认真对待。
例如,1998年初,正当克林顿总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访华行程时,美国国内爆发了所谓的“卫星泄密”案,众院随即通过法案,禁止美国今后向中国出口任何商业卫星,而议长金里奇则与多位共和党国会领袖敦促克林顿取消访华计划,声称在查清事实真相之前总统访华“不合时宜”,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也将是“令人难堪的”。金里奇等人的言论立即得到了两院大批议员的呼应和支持,并被美国一些媒体大肆报道和炒作,给原本十分正常的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注:Steven Mufson,“Gingrich Tells China U.S.to Defend Taiwan,”Washington Post,March 31,1997,p.A17.)5月2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被迫出面明确批驳了这一无理要求,为克林顿如期访华进行辩解。在克林顿结束访华后不到一个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便发表讲话,表示对克林顿的“三不”政策表示“惊讶”,并认为克林顿的讲话“犯了严重错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注:美联社华盛顿1998年7月16日电。)7月7日,参议院通过了洛特提出的第107号共同决议案,重申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承担的义务,并敦促行政部门加大对台军售力度,要求总统敦促大陆承诺不以武力实现两岸统一。(注: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636页。)随后,在洛特的带动下,参众两院在短短的3个月内便出台了6项内容相似的法案,以对克林顿总统的对台政策表示不满。
2001年5月下旬,陈水扁“过境”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汤姆·迪莱便公开声称:“如果国会议员想同陈水扁总统会晤,并因他是作为美国盟友台湾的民选领导人而对其表示敬意,那么布什政府将会表示欢迎。这同克林顿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视台湾人为二等公民。”(注:“美报文章《美国向台北倾斜被认为是危险的》”,载《参考资料》,2001年5月24日,第3页。)随后,迪莱在其家乡得克萨斯州会见了陈水扁,并邀请陈水扁在他自己的农场中参加“牛肉野餐会”(Beef Barbecue)。由于迪莱在众议院中手握重权,甚至被美国舆论称为“众议院真正的领袖”,因此,此次会见被视为台湾又一次重大的“外交业绩”,此后,众多议员纷纷效仿,每逢陈水扁“过境”,总有许多议员前往与其会面,或是参加台湾当局举办的宴请或招待会,以展示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2、运用“议程设定权”,左右国会立法议程安排
立法是国会最重要的宪政职能,尽管每位国会议员都可以自由地向国会两院提交立法议案,但是在议案被登记编号之后,要由国会领袖决定应提交哪一个相关委员会进行审议处理。法案在经过委员会审议并送交两院全院大会表决之后,需要“排队等候”讨论的日程安排。如果是紧急或重要法案,参议院将由多数党政策委员会根据本党领袖的意见负责安排时间进行讨论,而在众议院则由规则委员会根据议长和多数党领袖的指令予以安排,而无法得到辩论安排的法案往往便将就此夭折。籍此国会领袖可以对国会两院的立法议事日程进行直接的设定和调控,进而对国会立法和政策制定施加举足轻重甚至“生杀予夺”的影响。
国会领袖对立法议事日程的控制权在众议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众议院议长为例,他能够利用职权控制议案的立法进度,“以他行使‘准许’发言的权力,断然决定什么议案可以允许个别议员超越由规则规定的或由规则委员会安排的正常程序去投票表决。”(注: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页。)也能“决定在何时、用何种次序安排什么法案给议员们讨论,这样他就能决定该法案的命运。对于一个有争议的议案,搁置一周可能会扩大或缩小其通过的机会。”前议长奥尼尔便认为议程设定权是他最重要的权力之一,甚至断言:“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就是决定议程的权力。”(注:Congressional Record,98th Congress,1st Session,Nov.15,1983,H9856.)
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手中也握有与议长相似的权力,只不过由于参议院的运作特性而显得更为“软性”一些而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可以帮助议员的提案得到通过,帮助组织对这些议案的听证会。多数党政策委员会很重要,它做日程,安排哪些议案要加以讨论,哪些不讨论,以及谁有得以行动的机会,谁没有。可以轻而易举地叫你靠边站,因此多数党领袖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注: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8页。)例如林登·约翰逊就不仅能够对“立法议程加以协助或组织”,而且还善于利用所谓的“认可的权力”(power of recognition),促使参议院按照他所设定的条件来进行立法表决。(注:Doris Kearns,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s(NY:Harper & Row,1976),p.105.)1971年5月11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讨论延长征兵制法案时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把美国驻欧兵员裁减一半。由于手握决定议事日程的大权,该修正案根本未经参议院相关小组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的审议和听证,便根据曼斯菲尔德的要求在第二天交付参议院全院进行表决。措手不及的尼克松政府尽管竭力试图推迟表决,以便争取时间赢得支持,但是却也只是争取到区区五天的时间。(注: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95—1196页。)
现在,议长、参众两院领袖、党鞭及其他领袖办公室之间都设有热线,各自的助手也频繁开会,讨论决定某项法案的提出时间,有时为了保证一项重要法案的通过要编排十余种议程,反复比较才能最后确定。对于国会领袖领衔提出的议案或是特别关照的议案,参众两院一般都会优先照顾,安排辩论,以保证其迅速通过。(注:George Rothewell Brown,The Leadership of Congress(NY:Arno Press,1974),pp.37—38;Judy Schneider,“House Leadership:Whip Organization,”CRS Report,Feb 12,2002,p.2.)例如,在1999年5月18日,106届国会众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提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HR.1838.IH),在迪莱和迪克·阿梅等多位国会领袖的积极推动下,该法案于1999年10月26日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得到通过,而规则委员会在2000年1月31日便优先安排在众议院全院进行辩论,辩论时间仅为1小时。第二天,该法案便在众院付诸表决并以341票赞成,70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而与众议院的高效相比,早在1999年3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等21位参议员便联名提出一项名称相同、内容十分相似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S.693.IS),但是该法案却遭到参议院两党多位领袖的反对,例如参院多数党领袖洛特便劝告同僚谨慎处理任何涉台法案,而少数党领袖达施勒则认为该项法案造成的破坏可能比好处更多。(注:“英报说美众院通过台安法法案使中美紧张关系加剧”,载《参考资料》,2000年2月5日,第7页。)因此直至106届国会闭会,该法案一直被参议院搁置,而最终没有付诸审议表决。
3、运用人事选择权,影响国会立法决策
人事选择权主要是指国会领袖决定政党组织、国会附属委员会或是次级组织成员人选的权力。根据两院内部规则,国会领袖有权根据需要设立一些非常设性委员会或是国会附属机构,并选择和决定上述组织的组成人员。例如在104届国会中,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便常常设立专案小组(task force),来补充甚至替代常设委员会的职能,而议长则有权决定是否设立以及任命其组成成员。1997年,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指示共和党议员约翰·波特(John Porter)和大卫·德莱尔(David Dreier)组织一个专案小组(task force),负责重新设计一套对华政策方案。该小组经研究提出放弃以通过对华最惠国待问题对大陆施压的手段,转而采取冷战时期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宣传等“软力量”,通过加强“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以期促成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这项政策得到了国会主张对华接触的多数议员的支持,并得到了采纳。(注:Karen Foerstel,“House Chairman:Gingrich Flexes His Power in Picking Panel Chiefs,”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Vol.52,November 19,1994,p.3326.另可参见刘永涛:《90年代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变化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第66页。)2000年10月30日,根据刚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国会成立了“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在12名组成人员中,由议长提名并任命的有3人,众院少数党领袖任命3人,参院两党领袖在与临时议长商讨之后各任命3人。又如根据美国106—286号公法,国会批准了对华PNTR法案,但同时设立了“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汇报大陆在人权、劳工待遇、宗教自由和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情况并做出年度总体评估,其成员也均由国会领袖选择并任命。这些负责向国会提供政策建议和立法咨询的国会非正式组织或附属机构,对于国会形成相关领域的立法决策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而国会领袖对其成员的任命则无疑可以确保上述组织能够贯彻国会领袖的意见和观点,其所提的建议和意见也能够与国会领袖的立场保持相当大的一致性。
4、直接影响普通议员,推动或阻挠议案的通过
国会领袖尽管无法对普通议员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但是为了保证领袖意志得到贯彻,国会领袖也有许多方式对议员施加影响,促使后者接受其政策立场。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提供资金支持。在美国“金钱政治”中,能够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为本党助选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能力。由于国会领袖一般都具有多年从政经验,在国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与社会各界交往也十分密切,因此在募集竞选资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金里奇在担任议长的四年期间,便为共和党至少筹集了2.5亿美元的经费,这一点“在共和党内无人可以替代”。(注:Leslie Wayne,“The Speaker:Gingrich's Midas Touch to Be Missed,”New York Times,Nov.9,1998,A26.)在108届国会中升任众院多数党领袖的汤姆·迪莱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0年则为本党候选人筹集了高达31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注:“美刊介绍美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50个风云人物”,载《参考资料》,2001年3月19日,第10页。)而108届国会众院民主党新任领袖佩洛西就是因为与加州财团关系密切,每年都能够为本党筹集到大量的竞选资金而得到本党议员的拥护,从而成功当选这一要职的。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会选举中,每一位议员无疑都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而国会领袖不仅拥有更为充足的财政资源,而且有权对本党及其本人所募集的竞选资金进行分配,以决定是否帮助某一位议员进行选举,因此通过对竞选资金的分配,国会领袖常常可以借机“诱惑”和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促使其充分尊重和考虑领袖的政策立场。(注:Stephen Gettinger,“Potential Senate Leaders Flex Money Muscles,”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Otc.8,1988,p.2776.)
其次是帮助本党议员宣传造势,提高声望。在国会历史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德就曾在本党候选人的募捐招待会上演奏小提琴,帮助其造势募捐。在108届国会选举中,参众两院领袖更是倾巢出动,到议员选区举办演讲,宣扬本党人选的政绩,为本党候选人或谋求连任的议员进行造势宣传。例如达斯勒就曾在其家乡南达科他州专程停留三天,为本党参议员蒂姆·约翰逊(Tim Johnson)助选,呼吁选民投票支持或是积极捐款。对于谋求选举胜利的候选人来说,国会领袖的强力支持是击败竞争对手的一个重要襄助。而为了在日趋白热化的选举竞争中得到国会领袖的支持,议员在日常工作中必然要注意倾听领袖的意见,建立良好的关系,以期在日后获得丰厚的回报。
第三,帮助或排斥议员进入重要委员会。能够进入一个重要的、令人尊敬的常设委员会,为选区谋取利益,从而争取连选连任无疑是每个议员梦寐以求的希望。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商业委员会、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便均属此列。国会领袖不仅拥有决定某位议员进入某一委员会或者小组委员会的权力,并可以定期对议员的委员会安排进行调整,而议员是否“听话”无疑是国会领袖在做出上述决定时的重要依据。例如,一位国会民主党领袖就曾直言:“我们设法把明白道理的人放在(重要的)委员会。有些想调换委员会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委员会,这些人从来不跟领导走,从来不帮助领导。不仅我和其他领袖这么做,指导与政策委员会里那些选举产生的委员也是这样考虑的。”(注:Barbara Sinclair,Majority Leadership in the U.S.House,p.96—97.转引自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232页。)
第四,国会领袖还可以运用上文所述及的影响国会立法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权力,对议员的某项法案表示支持,帮助其所提出的立法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协助其建立“政绩”,获得政治声誉,为连选连任或是在未来登上更高的位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不太驯服的议员,国会领袖则可以通过暗中阻挠其立法提案进入国会议事日程、长久搁置议案的辩论表决来对其加以“惩戒”。这样一个对选区无所贡献,或是毫无立法建树的议员则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激烈的选举竞争中败北,并就此结束其政治生涯。因此,国会领袖手中所握有的这一大权足可以使大多数议员对领袖的意旨俯首贴耳。
最后,国会领袖还可以通过支持议员在其选区的公共工程计划,帮助议员从政治“肉桶”中拿到一块“肥肉”来帮助其获得连选连任。除此之外,国会领袖例如议长还可以通过给予议员某些荣誉性的奖励,例如主持院会辩论或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来拉抬某位议员的声势地位,使之得到全院议员以及媒体的关注,提高其知名度,并以此作为诱饵来换取国会议员的支持。(注:Randall B Ripley,Party Leader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7),p.7.)
5、直接游说和影响总统以及政府官员。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国会领袖的职责与地位决定其必然要在府会沟通和互动过程中发挥桥梁和领导作用。(注:Roger Davidson & Walter Oleszek,Congress and Its Members,7th edition,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2000,p.164.)国会领袖不仅要积极与总统就立法议程和立法重点事宜进行沟通,而且还有义务向总统通报国会对于总统具体政策的反应,建议或是要求总统根据国会的意愿对其政策进行检讨甚至做出调整。在历史上,议长曾经权倾一时,享有“向总统提出决定国家政策及选战的方案”的巨大权力,隐隐然与总统分庭抗礼。(注:George Rothewell Brown,The Leadership of Congress,pp.37—38.转引自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而时至今日,国会领袖的支持对于总统立法计划的成功实施仍然不可或缺,因为“如果议长不想让某个议案通过,那它通常就不会被通过。”(注:Thomas O' Neill Jr.,Man of the House(New York:Randam House,1987),p.273.)
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降,美国历任总统均丝毫不敢忽视或低估国会领袖的作用,并都将保持与国会领袖的磋商和意见交流,努力获取国会领袖的支持视为影响其内政、外交政策成败的关键要素。总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国会领袖保持紧密的联系,如经常同本党领袖举行定期会谈;邀请国会领袖参加白宫聚会、国宴来拉近彼此的关系;与国会领袖交换对立法的看法,以便白宫确定在国会优先制订和协调立法项目的战略和战术等。例如艾森豪威尔在就职典礼后不到一周,就在白宫会见了参众两院领袖,并每周都会与国会领袖会面磋商。1988年总统选举过程中,老布什曾与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多尔对垒,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在当选总统之后,老布什立即与多尔会谈,以消释前嫌,然后又任命多尔夫人为内阁劳工部长,拉拢多尔之意显而易见。105届国会选举揭晓后,共和党继续控制着参众两院,克林顿在国会开幕后不久便专程前往国会山拜会议长金里奇、参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寻求双方能够达成妥协的议题。(注:Roger Davidson & Walter Oleszek,Congress and Its Members,p.186.)此后,克林顿每周都会抽出一天的早餐时间与国会两党领袖会餐,联系感情。现任总统小布什也深谙此道,并经常在其“西部白宫”——克劳福德农场邀请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度假休息。
通过与总统的直接交往和接触,国会领袖可以借机向总统说项,或是通过打电话、写信给总统,就自己关注的领域提出意见,影响总统的决策,甚至讨价还价,推动总统制定相应的内政、外交政策,或是要求总统对相关决策做出适当调整,以满足国会的利益需要。一般情况下,出于维护府会关系的考虑,总统往往也会对国会领袖所坚持的政策主张予以一定程度的采纳。例如在1994年6月21日,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少数党领袖多尔为首的54位参议员联名致函白宫,“强烈呼吁”克林顿从速改变传统政策,指派内阁级官员访台,与台湾展开高层官员的互访与交流。(注: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7月2日,参议院在审议《国防部授权法案》时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与台湾关系法》中增列:台湾的“总统”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如在任何时间访美,与联邦或地方政府讨论减少美台贸易赤字、防止核扩散和对美国家安全的威胁及保护环境等事务,美必须允许其入境。随后,参议院在审议《商务部、国务院和司法部拨款法案》时又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政策部分增加一款,说明美国与台湾“应派内阁级官员互访”。(注: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在国会的催促和压力之下,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出台“对台政策评估报告”,对美台关系做出调整,公然允许美政府官员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与台湾当局进行次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允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机构进行会晤;并允许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政府高级官员访台。(注:Winston Lord,“Taiwan Policy Reviow,”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October 17,1994,pp.705—706;Steven Greenhouse,“U.S.,Despite Critics,Is to Expand Taiwan Tie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1994.)2003年夏,又是由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积极游说和劝说,白宫决定将台湾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从而使台湾可以拒绝采购自己不想应用的美国军事装备,增强美台合作参与军事研发计划的力度,并加速对台湾的卫星相关技术出口的审查作业。(注:“中央社”(台)华盛顿2004年2月18日电。)
6、直接影响公众舆论
作为国会权力的代表,国会领袖时刻吸引着众多媒体的关注。每当面临重大的政策分歧,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备受瞩目。通过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接受媒体的专访、发表公开演讲等方式,国会领袖可以直接向选民宣示自己的政策主张,影响舆论导向,并进而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决策施加影响。近年来随着“媒体政治”影响的不断加强,国会领袖这一特权成为其手中一个重要法宝。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现在已不再是通过讨价还价赢得选票,而是通过影响公共媒体的方式来推动立法进程。”(注:New York Times,June 7,1984,B16.)1997年10月,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与另两位众议员在《华盛顿邮报》联合撰文,对克林顿政府批准的美中核合作计划提出批评,指责中国暗中向伊朗等国提供“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技术,而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则可能被用于帮助伊朗生产核武器,因此克林顿政府的这一行动是“极不明智的”,美中核合作计划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无法容忍的危险”。(注:Washington Post,Oct.29,1997.转引自陆曦:《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及其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3期,第43—44页。)随着该文的发表,国会上下旋即掀起一场调查大陆“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浪潮。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取得重大成功,布什总统针对陈水扁当局一系列推动公投、催生“新宪”的倒行逆施提出了严厉警告,但这却招致参众两院一些亲台议员的指责。12月底,众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发表声明称:“由于布什总统对陈水扁所主张的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自由人民通过投票表达观点的权利进行责难,他严重破坏了美国的传统,即美国站在希望获得民主和自由的人民一边。”为此,佩洛西敦促布什立即发表“一项与美国价值观相符的新的声明”来加以补救。此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主要媒体纷纷撰文,呼应佩洛西的声明,指责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华盛顿邮报》甚至发表社论,批评布什政府是在向大陆“叩头”,认为布什的讲话“不可容忍”,并迫使布什政府随后降低了对台湾当局批评的调门。
在国会权力结构中,国会领袖群体对国会立法议题设定、议事日程安排和议员政策立场选择等方面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注:Roger Davidson & Walter Oleszek,Congress and Its Members,p.164.)这不仅表现在内政决策领域,也在外交决策领域得到了日益鲜明的体现。随着越战后国会外交的复兴,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得到显著提升和加强,国会与总统争夺外交政策制定权的情形也愈演愈烈,为了努力获取国会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支持,总统在外交决策领域日益重视对国会领袖的争取和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为国会领袖与总统讨价还价,推动总统采纳国会所属意和坚持的外交政策立场,影响甚至左右美国外交决策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难得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