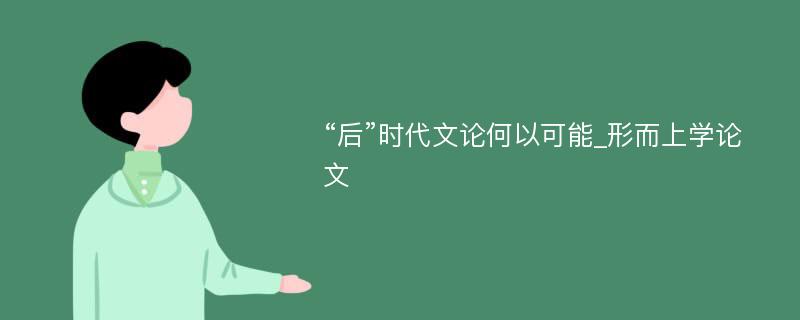
“后”时代的文学理论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开始至今,文学理论重构或重写的意动和构想一直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题域。这种诉求本身表明,人们对以往文学理论的叙事体系存有普遍的不满和多方质疑。同时,也表明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正在或已经发生着重大嬗变与转换。然而,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一嬗变与转换的真实内容,选择怎样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范式来完成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却始终模糊不清。此种状态造成多年来一些重构重写的作业并未有效地完成。所谓的重构重写往往成为新史料、新作品、新作家、新术语、新形式的添加、增补与组合。这种重构重写的文学理论表面上似乎也会给人一种“新”的印象,但这种“新”不过是表面上的翻新而已。重构重写之所以会变成表面的翻新,其缘由在于依然囿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之中。因为,没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重构重写依然只能是一种传统的叙事,一种似是而非的翻新。如此看来,要想有效地完成文学理论的重新建构、重新书写或重新叙事,就需要对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一番批判性的反思与清洗,而传统叙事方式乃是建立在传统思维方式与理论范式的基地之上,因此,对传统叙事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与清洗就与对传统思维方式、理论范式的批判性反思与清洗紧密地牵连在一起。
在全球化迅速蔓延的今天,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意义上说,我们都已经无可选择地被置身于“后”时代之中。“后”这一带有时尚色彩的前缀词,不断地前缀在一些词语前:后现代、后形而上学、后哲学、后工业社会、后革命、后历史、后发展等等。在此,我们暂不去梳理这诸多“后”的复杂歧义,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后”时代理论将成为一种何样的理论?如果理论一词也前缀上一个“后”字,那么,后理论将会是一种何样的理论?
后现代可谓是诸多“后”之中最具代表性涵盖性的概念。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并不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流派或思潮,后现代业已形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文化范式和理论范式,因此可以将后时代的后理论指认为后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正如美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注: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后现代理论范式与现代性理论范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后现代以极端的另类异质性颠覆和批判着现代性。
现代性在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理性法庭的建立完成了神话与宗教的祛魅。现代性确立自身合法化合理化的过程,是通过理性的系统化、体系化——即理性的理论化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另一个别名。理论的生产以及理论权威性的确立正是现代性合法化合理化的内在诉求。因此,后现代的理论范式在颠覆摧毁现代性的过程中,势必要颠覆摧毁理论的权威合法性。与现代性理论相对峙,后现代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反理论或非理论的理论。反理论或非理论的后现代范式对系统化体系化实证化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质疑,理论因此而进入到被解构的阶段。后现代理论话语彻底揭穿了理论身上披挂的科学权威性伪装,指出理论或知识话语背后隐藏着与某种权力相互共谋的关系。以往诸种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构件,诸如本质、概念、逻辑、体系等都被后现代理论话语拆解为支离破碎的碎片。在后现代看来,本质主义即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为此,形而上学的谵妄成为理论所固有的顽症。具有形而上学谵妄症的理论最终必将导致同一性和独断论,甚至导致恐怖、暴力和死亡。所谓概念的先验自明性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我镜像,一旦将其还原为语言问题,这些先验自明的概念所指涉的命题都不过是一些假命题,这些概念的言说都不过是一些滑动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语言游戏。体系的建构是理论的内在要求,然而,体系建构的种种设想和冲动,都不过是某种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和乌托邦幻像。总之,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拆解颠覆下,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已变成为一种可以分离解构的片断;指涉实在的理论概念已变成为一种话语方式;因果关联的理论逻辑已变成为一种延宕的隐喻。在后时代,在后现代,所有的理论都已成为一种反理论,成为一种非理论。至此,后时代的文学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在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时代,文学理论何以可能的问题。
在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时代去建构理论,这确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问题,同时它也意味着这是一个难解甚或是无解的问题。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地要进入这个充满悖论的怪圈。因为,在后时代,在后现代文化范式业已形成的今天,试图在传统理论的框架内建构一种新理论的追求已经成为不可能的谵妄。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理论重构重写的前提工作首先是对现代性传统理论观念的批判反思。由于缺乏对传统理论观念的前提性批判反思,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建构尽管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改写,其结果依然是旧瓶装新酒式的工作模式,依然难以突破传统理论的囿限。传统的理论神话依然成为理论创新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所说的传统理论神话是指以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为基础和核心所展开的理论建构,具体表现为:体系的神话、概念的神话和逻辑的神话。体系的神话表现为对建构体系的崇信;概念的神话表现为对基本概念的偏执;逻辑的神话表现为对逻辑演绎的痴迷。只要文学理论依然束缚在这些理论的神话之中,所谓新理论的重构重写,便终究跳不出传统理论的如来掌心。
理论的神话一经破解,传统的理论观念经过前提性的批判反思,新的文学理论才有可能逐渐浮出水面,并呈现出特有的谱系征相。显然,这一新的理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甚至用“理论”一词来表述它已有点不太适合,因为它是一种非理论的理论,一种反理论的理论。如果还要有体系,这种新理论的体系应该是一种非体系的体系,这意味着它应该是开放的、流动的、茎块状的,而不再是封闭的、凝固的、树状的;如果还要有概念,这种新理论的概念应该是一种非概念的概念,这意味着它是差异的、非透明的、隐喻性的,而不再是同一的、透明的、确定性的;如果还要有逻辑,这种理论的逻辑应该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这意味着它是断裂的、延异的、非线性的,而不是连续的、历时的、线性的。
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文学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范式。其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学理论是本质论或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新文学理论则应该是反本质论反本体论的后形而上学理论;传统文学理论是文学性或审美性的一元决定论,而新文学理论则应该是文本话语与解读叙事的多元决定论;传统文学理论是以经典文学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新理论则应该是以大众文化为对象的泛文学研究。
在传统理论观念中,本质论或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理论思维是最难祛除的传统理论范式。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本体论哲学一直被认定为“最高的知识”,被认定为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和前提,本体论哲学因此亦被称之为“元哲学”、“元理论”或“元知识”。后现代哲学转向以更加激烈、更加极端的姿态和策略,发动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彻底颠覆和摧毁。利奥塔正是在此意义上,以对“元话语”、“元叙事”的质疑来标示出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在勒维纳斯眼里,哲学中的本体论必然产生总体性,而总体性乃是一种同化他者、吞噬个性、取消差异的暴力体系。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乃是一种强权的哲学,一种中性的哲学,一种作为无名的非人的普遍性之状态的暴君。”(注:参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5页。)勒维纳斯向总体性开战,即是对强权本体论的抵抗,即是向暴力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暴力的挑战。福柯以其谱系学、考古学方法,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隐秘共谋关系,并从人的有限经验的限定性出发,宣布了无限之形而上学的终结,宣布了人之形而上学的死亡。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不懈的猛烈攻击。以“不在场”颠覆“在场”,以“边缘”颠覆“中心”,采取“延异”的文本策略破解任何本体论的确立和形而上学的建构。此外,后现代哲学所谓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深度模式等主张都可以视之为反本体论形而上学的不同表述。
虽然,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颠覆摧毁已呈崩解之势,但本体论理论思维的幽灵依然在不知不觉中作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已构成人们理论思维中挥之不去的怪影,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积淀着两千年历史的理论思维模式。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何以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才逐渐呈露出崩解的真实内容,也可以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诸多哲学转向从不同方位对其发动的全面围攻。表面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形而上学颠覆和拆解,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实质已经很容易被识破和揭穿,但是,本体论理论思维模式却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可以破除。在现今流行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本体论思维依然或隐或显地成为主导性的幽灵,以致于在许多人眼里,离开了本体论,离开了本体论思维,理论的思考和建构几乎就无法进行。当代文学理论多是以文学或审美的本体、本质、规律的追问,作为最基本的元理论起点,虽然,有些文学理论论著已意识到本体论思维的局限,并试图用文学创造、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创造等概念取代本体论或本质论的提问方式;但由于没能彻底摆脱掉本体论思维方式,经常会出现将文学创造、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创造等概念本体论化的倾向。在这种本体论思维作祟的理论模式中,本体论或本质论的理论观念始终统摄着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现代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始终成为贯穿理论建构的内在理论神话。因此,只有破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只有清洗掉现代性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的重构重写才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和展开。
也许会有人感到如此反理论非理论的文学理论是不是过于怪异?也许会有人提出如果文学理论不追问本质本体,不分析文学性或审美性,不研究纯文学,那它还是文学理论吗?保罗·德曼在《抵制理论》一文中回应了这些怀疑、抵制和反对的声音,并阐述了这种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文学理论所应该具有的谱系征相:“文学理论的什么东西这么吓人,以致于激起如此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它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倾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反对美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大哲学传统;它瓦解了文学作品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界限。”保罗·德曼认为这种充满悖论的文学理论,正因其悖论的充满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无论什么东西都无法克服对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己地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不过这种兴盛是一种胜利抑或是一种失败,却仍然无法做出定论。”(注: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第114页。)在反理论非理论的时代去建立反理论非理论的文学理论;在后时代,在后现代的文化范式中,去建立后理论的文学理论,将会是一种成功抑或是一种失败,或许正像保罗·德曼所说的那样,我们依然无法做出定论。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神话论文; 范式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