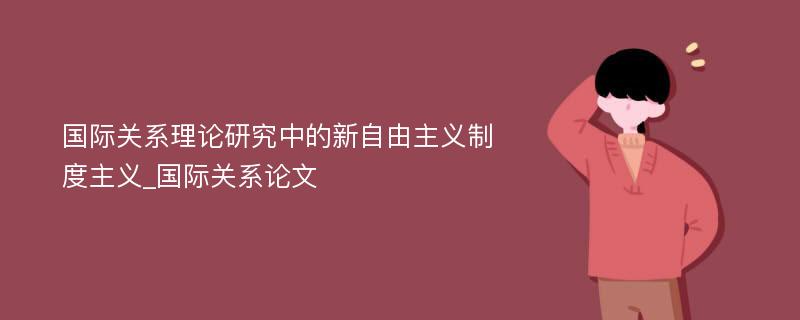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主义论文,制度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
近二十年来,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流派纷呈。自肯尼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后,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大行其道,影响至今不衰。不过,这二十年绝非现实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时代,其间也出现了诸如“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然而,在所有理论流派中,能够对现实主义“范式”构成挑战的,则非八十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莫属。
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个名称是在1987年后开始正式使用的,在此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制度主义等。(注: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Power,Westview Press,1989,p.2.)另外, 这个名称中的“新”和“制度”本身表明,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早期的自由主义如主张贸易和平论的“商业自由主义”、提倡民主和平论的“共和自由主义”和将国际一体化与跨国互动联系起来的“社会自由主义”是有别的。 ( 注: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p. 4; Joseph S.Nye,JR.: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January 1988,pp.245-246.)1983 年克拉斯纳(Stephan D.Krasner )教授以《国际组织》杂志关于“国际机制”的专辑文章为基础编辑的《国际机制》一书以及1984年基欧汉《霸权之后》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诞生;而1986年基欧汉编辑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则预示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始向传统现实主义范式提出挑战;1988年和1995年,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格里科(Joseph M.Grieco)和米尔谢默(John J.Mearsheimer)分别撰文《无政府与合作的限度》和《国际制度的错误假设》,(注:参见: Joseph
M.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pp.485-507;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4/95,pp.5-49.)这两篇文章是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还击,同时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处于反省、修正和重整阶段。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
1.关于无政府世界的特征以及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假定
与经典的现实主义范式不同,现实主义者是在“混乱”、“无序”这个意义上理解“无政府世界”的含义的,因此他们把世界看作是悲观的、对抗性的,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在“作为一种秩序”的意义上理解无政府世界的含义,因而他们把世界看作为可协调的、乐观的,就象艾克斯洛德和基欧汉指出的,无政府这个词就是指世界政治中缺少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但并不等于说作为一种秩序的国际社会是不存在的,“说世界政治是无政府的,并不因此就意涵着世界政治是完全缺少组织的”。(注: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David A.Baldwin,ibid.,pp.85-86.)而且,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是与国内社会的“有政府”相对而言的,如果“国际社会缺少中央政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话,那么理解无政府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什么叫“有”政府,什么叫“无”政府。如果“政府”是指“有效治理”的话,那么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领域,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对问题的管理就起着隐含或强制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国内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但是就问题解决的程序和规则而言,也并非如现实主义所想象的那么混乱和无序,它实际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而如果“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是判断政府的标准的话,那么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内部,政府也并不绝对地垄断着暴力,更何况在本无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了。(注: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现象的分析,最引人注意的是海伦·米尔勒的文章,其中详细探讨了合法性在国际社会里的意义。 参见: Helen 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Baldwin,ibid.,pp.143-169.)
因此,对于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命题,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都不否认,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对无政府状态含义的认识上。
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基本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是自利自助的假定,有所区别的是,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类似霍布斯眼中的“自然状态”,但又不完全是那种“国国为战”(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因为在这种自然状态中存在着“契约”的因素,这些“契约”就是下文提到的制度。因此,国家不是或不能无所限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利自助当然是国家行动的主要动力,但这种行动是受到国际制度限制的,是在制度框架下的行动。由此看来,与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约束国家行动的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着重的是制度对国家行动的限制。
2.制度的创设及其功能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是“制度”一词,主要指契约性质上的惯例、规则、条约、国际法等。克拉斯纳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较能代表这种看法,他认为国际机制是指“行为者在共同关注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 (注:Stepha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另外, 国际制度也指具有特定目标、由官僚机构组成、拥有一定行动能力的国际组织。
既然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里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国际制度是怎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过程而自发生成的;二是因为霸主(或主导的国家)的作用而强制规定的。
就第一种生成方式而言,国际制度的产生首先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进程有关。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是主权国家,单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从来不是孤立的、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在互动往来中,国家之间必然需要规则、条例乃至法律相互约束,国家对国际生活的参与也就是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另外,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因为信息的不完备,国家对外行动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往成本过高的问题,国家会主动地订立协议、规则、条约乃至设立组织,借助这些制度创新,将彼此的行为纳入到可预期的轨道中,以保证各方在稳定的环境中持续获益。
就第二种产生方式而言,国际制度是由一个权盖四方的霸主强制订立、推行的,这种制度创立过程,并不排除对暴力手段的使用。由霸主创设的制度,在道德上难免损人利己之后果,不过,因为这种制度作为公共(集团)物品,它们往往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合法性而被其他主体所接受。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一旦霸主衰落,那么先前由该霸主创设的制度是否也会寿终正寝?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此持否定看法,认为制度一经产生,就具有很大的“惯性”,有不会轻易消逝的功能性作用。“霸主衰落后的合作是可能的,这不仅由于分享的利益会导致机制的创设,而且维持既存国际机制的条件比要改变它们的条件少。虽然霸主的作用有助于解释当代国际机制的产生,但是霸主的衰落并不必然引起原有机制相应的弱化”。(注: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50-51.)不难看出,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霸主终结后的国际制度维持,解释较为主观和牵强,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论证。
制度一经产生,就会具有持久的功能价值。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对促进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以后,它至少具有下列两项功能,“第一,它使各方的需求汇聚在一个中心,为官员的合法行动以及决策者达成可行的一致模式提供了指南,并降低了行为的不确定性。长远来说,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政府在顺应机制的各种规则上,是如何界定它们的自我利益的;第二,制度可以通过禁止确定的行动来约束国家的行为”。(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utumn 1987,p.734.)
3.共同收益与国际合作
收益问题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对外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相对的收益”,也即在总收益中“我”能得到多少。当合作可以带来利益时,国家首先想到的不会是“我们俩都会获益”这样的效率问题,而是“我们俩谁会获益更多”之类的分配问题。(注:参见: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否认相对收益的意义, 但更强调共同收益的重要性。国家间博弈不全是“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很多情况下是“你得我也得”的正和博弈,而正是因为正和博弈的存在,为追求共同收益,国际合作才会出现。
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拥有共同利益的各方并不必然会自动走向合作。而且,所谓的共同利益也是因时因地而变的,一旦共同利益发生转向,原有的合作就会变得脆弱。那么现实世界中的合作又如何才能持久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还是从“国家行为自利自助”的假设出发论证的。我们知道,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动机假定与新现实主义并无二致,即国家行为总是自利自助的。根据一般的逻辑推论,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行为总和(集体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行为(后果)一定是理性的。国际关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全困境”。如果每个国家都“理性”地为安全缘故发展军备,其结果不会是每个国家因此而安全,而是整个世界因此而不安全。所以现实主义者振振有词地指出,国家自利自助的动机使得国际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存在国际合作,也是非常困难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他们从各国利益的相互性、未来的重要性、互惠战略、制度的意义等角度,论证了即使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国家)行为也会导致合作局面的出现。 (注: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A.
Baldwin,ibid.,pp.85-115.)
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评价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关系运行的制度化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大趋势。新自由制度主义撇开现实主义由内及外(强调追求权力的国家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由外及内(主张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的分析路径,认识到国际制度在组织国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并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将制度作用的广泛现象抽象化、理论化,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挑战是有限度的。一方面,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强调权力、安全、结构的现实主义范式自身存在着一些缺陷,它对处于合作大势中的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现实主义仍然不失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注:Ethan B.Kapstein:Is Realism Dead? The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Autumn 1995,p.773.)此话出自现实主义学者之口, 难免不带点偏见,但就现状而言,未必不是事实,因为能够完全取代现实主义的理论至今尚未出现;另一方面,就新自由制度主义自身来说,该理论的许多假设实际上源于现实主义,它对国际政治的解释与现实主义的不同只在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看到了国际关系中合作的一面,并认为合作是可能的、可行的而且是重要的,而现实主义则过分注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对抗的一面,认为冲突是永远的、绝对的而且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一位中间派学者在评论两派的辩论时,不无客观地指出这两派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注: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January 1988,p.238.)由此观之,所谓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挑战,目前看来只能是有限度的挑战。
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制度”一词的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而“定义一旦过于宽泛则失去分析的精确性和标的”,(注:参见郑端耀:《国际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之评析》,(台北)《问题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14页。)例如基欧汉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经典之作《霸权之后》一书中,就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制度”和“机制”两词的。另外,对于国际制度的创设及其功能,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目前主要停留在主观论述上,经验和实证研究不多,从而限制了该理论的解释和检验能力。不过近几年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正在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力图在案例研究上为其观点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
最后,新自由制度主义过多地纠缠在制度的“功能”上,未能跳出制度来分析制度,因而限制了该理论的增殖能力。据笔者观察,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产生,肯定部分受到当时风行的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影响, 实际上在基欧汉《霸权之后》一书中,诸如“公共物品”、“产权”、“外部性”、“交易成本”、“制度创新”等概念均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为什么后来的学者(包括基欧汉本人)偏离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向,不得而知。笔者的看法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注意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但是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更多地坚持这一研究取向的话,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创新能力可能更为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