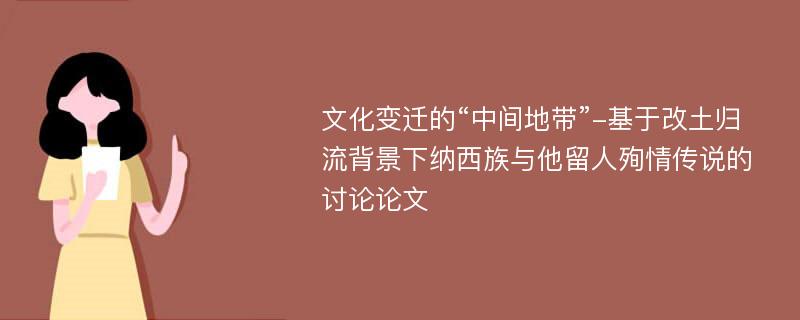
文化变迁的“中间地带”
——基于改土归流背景下纳西族与他留人殉情传说的讨论*
杨晓雯
(云南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文章在对中西方学术视野中的“西南”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中间地带”这一既涉及地理方位,又暗含族群融合过程的概念为视角,对永胜彝族支系他留人《一棵老梅树》和丽江纳西族《鲁般鲁饶》等“情死树”殉情传说进行了分析。作为具有“情死树”相同的母题的殉情传说,他留人借此解释了包办婚姻向自由婚恋转变的缘由,而纳西族的传说则正好相反。将传说与明清以来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背景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两个族群中存在的殉情现象均与强制性移风易俗政策造成的“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二元婚恋形态有关。相似的文本反映着族群之间,由于与汉文化关系的远近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格局。其中,他留人的地理及文化生境正是西南较大“中间地带”中生成的较小“中间地带”的典型。对族群间婚俗传说的对比研究,利于理解中间地带边界人群的文化在“夷汉融合”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与过渡性,也为“中间式”论述框架提供了更为具体、丰富的个案与可能性。
[关键词 ]中间地带;纳西族:他留人;殉情传说;改土归流
一 、理论视角 :“西南 ”研究与 “中间地带 ”
“西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小西南”仅指包括云贵、巴蜀在内的区域;“大西南”还包括西藏和广西与滇川相邻的一部分。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南”,远离中原,偏居一隅,因此潜藏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西南”相对“中原”而存在,没有“中原”,就无所谓“西南”。在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政治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中心主义形态下,“西南”逐步成为从“中心”俯瞰“边缘”,与“中原”形成鲜明的参照,从而凸显中国存在文化与地域差异的视角之一。
4.土地托管(返租)模式。反租倒包让贫困群众获得了租金、薪金和股金。宛城区老农经合作社把没有劳动能力贫困户的承包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除去成本,所有收入归贫困户所有,保证了每亩每年纯收入在1500元以上。淅川县福森集团金银花种植基地从农民手里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金银花,再分区包给农户管理,基地每亩收取400~500元费用,剩余所得归承包户所有,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贫困户参与生产的积极性。
作为学术语汇的“西南”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大学等知识生产机构的建立而产生;非汉语文本采用“西南”概念研究中国的潮流则盛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如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和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的研究。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西南”转向,表明其从华北、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趋势。无论是“中心”与“边缘”二分的“天下”体系,还是中西方学术语汇对“西南”的研究,都可以看出“西南”是在中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言说、定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藏彝走廊”“中间圈”“中间地带”“缓冲地带”等概念的提出,正是中西学者们出于打破文化中心主义,重新创造西南知识体系的尝试和表述。
高木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过去的五年里,不论是他洗澡,还是梨花洗澡,都避开对方;他在院子的井边洗澡,而梨花总是独自关上门,在房间里洗澡。他们绝无仅有的几次房事,梨花也必须先关了电灯,在黑暗中才让高木脱衣裳;至于她自己,上衣是不脱的,裤子也只脱出一条腿,草草了事。而此刻,他和梨花光了身子,滚作一团;梨花张扬地呻吟,如狼似虎;高木更是气喘如牛,翻江倒海,搅得床上天动地摇。
“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源于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对北美大湖区的印第安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开拓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他一反以往简单讨论美国人或欧洲人对印第安人所施行政策的研究,而是置印第安人于场景的中央,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厘清欧洲人与该区域的印第安人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理查德·怀特对“中间地带”界定如下:“‘中间地带’是地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地带,也是帝国与国家之外(nonstate)的村落世界之间的地带”。[注] Re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Great Lakes Reg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650~1815. 美国学者纪若诚(C.Patterson Giersch)采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西南社会,他认为,怀特基于美国大湖区族群关系提出的“中间地带”概念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有着帝国、土著、移民的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产生意义。他提出:“‘中间地带’不仅是简单的区域概念,更是看世界的一种视角,直入边疆研究中的几方面问题。有时它涉及地理方位,另一些时候,它又暗含族群融合的过程。有时,它又在表述着物质变迁或是基于边疆族际关系上的政治变迁。然而,这种多重含义却使空间与过程集于一身的‘中间地带’这一概念变得非常有力。”[注] 纪若诚.“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A].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38~177. 沈海梅教授以“中间地带”为文化视角来分析“西南”概念中的核心部分——云南,认为“云南不应当再是文化中心主义下的边缘,而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也是与西藏和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这里一直是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意味着多重关系的叠加,民族国家、族群、地域、性别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也同样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面孔。”[注] 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和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 比沈海梅教授的“中间地带”更早,受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提法的启发,王铭铭教授提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说”——由核心圈(汉文化圈)、中间圈(少数民族文化圈)和外圈(海外圈)组成。[注]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3~54.
无独有偶,笔者在研究丽江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的婚恋习俗时,发现其传说与同一地理单元中的纳西族的殉情传说有相似的母题,他留人的传说《老梅树》和《巴长马》对族群自由、简单的婚恋习俗以及男子串“青春棚”的由来进行了解释。结合婚恋习俗,分析其传说文本,可以发现,两个族群看起来差异较大的婚恋习俗中隐含着相似的文化记忆。笔者拟以“中间地带”为理论视角,将他留人与纳西族的婚俗及传说纳入其中进行考察,借永宁摩梭人为参照,探讨族群之间的婚俗文本记忆以及“以夏变夷”的进程中,不同族群在其地理和文化的“中间地带”所呈现的历史场景和互动关系。
历史上丽江纳西族以殉情而闻名,反映殉情现象的长诗、故事、传说在纳西族古典文学中独树一帜,代表作有《鲁般鲁饶》《放猪栽桃》《达勒·阿萨米》《游悲》《逃到美好的地方》等作品,塑造了开美久命金和朱古羽勒排、安朱拉来咪和朱补朱德若、达勒·阿萨米和长工等痴情、刚烈,敢于反抗,勇于殉情的青年男女形象。美国学者赵省华(Emily Chao)利用较早开展纳西族研究的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顾彼得、安东尼、杰克逊等人的调查资料,对纳西族殉情现象进行了研究。为了重构1723年以前纳西族的性别习俗,赵省华以丽江永宁摩梭人的资料作为参照,据此证明清王朝1723年后推行的“改土归流”是导致纳西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迁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丽江纳西族社会中的殉情、仪式及两性角色的转变。[注] 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90~214.
无论是“中间地带”“中间圈”,还是“藏彝走廊”,都与“西部”或“西南”相重叠,都指不同共同体交往的地带,它们体现的疆界不是线性的,而是块状的、带状的,具有高度的文化综合性、相互性与流动性。对“中间圈”里活跃的上下关系、族群相互性及流动性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中心-边缘”二分法的绝对性,为多民族错杂居住区域的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中间式”论述框架和视角。
二 、他留人的婚恋习俗与文本记忆
场地土层属于同一地貌单元,场地中地基岩土层分布稳定,总体上看层底面坡度<10%,除河沟地段地层有缺失外,各地基土分布相对连续,土体垂向压缩性相差较小,结合基础开挖深度及建筑物持力层情况,综合判断地基为均匀地基。
他留人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以“过七关”和串“青春棚”为核心内容。所谓“青春棚”就是未婚男女谈情说爱,选择伴侣的场所,与永宁摩梭姑娘的“花楼”有相似之处。按照他留人的习俗,少女月经初潮之后,家中女性长辈就给她举行以“换装”为核心内容的成年礼,由白裙改穿黑裙。同时,父母会在家中院子里为女儿搭建一间简单的房子,里边有一张木头单人床,旁边有一张普通的木桌子。“青春棚”用他留话来表达有三个说法:一是“查腊摩何格”,意思是年轻姑娘的棚子;二是“祖玛日喀”,即姑娘睡觉的地方;三是“何格夏喀”,意为“玩耍的棚子”。可见,从青春棚的空间布局及语汇来看,这是一种属于姑娘独占的、社交性的空间,具有比较明确的功能,用以谈情说爱,选择伴侣,进行社会交往。
20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姑娘在青春棚接待小伙子还是小伙子串青春棚,都必须首先取得一项资格认可,即“过七关”。所谓“过七关”,实际上就是在青年男女正式结交异性之前先交往七位异性,目的是考验他留青少年的机智与应变能力,并提供社交恋爱的机会和场合,积累寻觅结婚伴侣的经验。如小伙子必须连续七个夜晚在七位不同姑娘的青春棚中过夜,意为“七关”。姑娘亦然,则必须有七位不同小伙子连续七个夜晚前来串棚子,共度一宿者才算一关。没有“过七关”的姑娘没有人串她的棚子,没有“过七关”的小伙子也不会有姑娘接待他。
无论哪种习俗,都体现了他留人对自由恋爱与简单婚俗的重视,男女婚恋以是否“喜欢”为主要择偶标准,父母不会过多干涉儿女的婚姻。他留姑娘和小伙子如果两情相悦,决定在一起生活以后,婚事的准备——提亲、订婚和结婚仪式则非常简单、朴素。当地流传甚广的《老梅树》(又名《三个“一”》)和《巴长马》的传说解释了他留人自由、简单的婚恋习俗以及为何只能由男子串“青春棚”的由来。
(一)一棵老梅树的警告:他留人自由婚恋习俗的由来
为了说明汉族的介入对纳西人本文化造成的影响,赵省华(Emily Chao)和杨福泉都注意到了引入永宁纳西族摩梭人为参照加以比较。由于清代中央王朝施行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政策,永宁成为内域仅存的几个未实施“改土归流”的地区之一。因此,永宁的摩梭人以母系制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和暮合晨离的“阿夏”走访婚俗一直得以保留,男女交往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赵省华(Emily Chao)提到一个典型的事例:过去许多想逃避包办婚姻的纳西情侣用革囊渡过金沙江逃亡永宁。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有相当多的丽江纳西人陆续迁往永宁定居。从女性社会角色的转换来看,永宁摩梭少女的地位是随着她生理的成熟和开始成为族群再生产者的角色而提高的,而丽江纳西女性则完全相反,妇女地位的急剧下降始于婚姻生活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文化准则——纳西传统的准则和法定强迫的汉族准则的存在会在某种情况下导致青年男子的利益和青年妇女的利益发生冲突。一方面,青年男子为获得男子身份而需要情人,而另一方面,如果未婚女子怀孕了,她们就会丧失名誉甚至生命。”[注] 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06~207. 可以说,在1723年“改土归流”实施和汉族移民活动日渐频繁的背景下,地方土著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再创造。
Li 2013a: Li Xuezhu (李学竹), Munimatālakāra の梵文写本について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unimatālakāra], Mikkyō bunka 229.
后来,有一个名叫“嚓腊伯”的小伙子很不佩服这件事,他来到老梅树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也来试一试。”就用绳子拴住自己的大脚趾吊了起来,这时老梅树开口说话了,“小伙子,我不收你,你缺两个条件,第一你没有带女朋友来,第二你拴的部位不对,要拴在脖子上。”嚓腊伯大吃一惊,忙跑回去向酋长、头人报告:“不得了了,老梅树开口说话了。”酋长、头人等所有他留人纷纷来到老梅树下,大家商议说:“不如砍了这棵老梅树。”大家把任务交给了嚓腊伯。嚓腊伯走上前去,举起斧头准备砍倒梅树,斧头砍下去,老梅树却“哗哗”喷出血来,殷红的鲜血很快淹没了大地,刹那间黑云密布,雷电交加,峭壁上滚落下几块巨大的石头,现出一个大大的空洞,砸得地动山摇,似乎一场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
在针对初中生的作文教学中,部分教师还处于一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这也使得教学形式缺乏创新,这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制约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在实际课堂上,教师会对作文命题进行指导,为学生准备一个主旨让他们进行分析。并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利用几篇范文帮助学生理解命题。这种教学,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形式的枯燥以及内容的缺乏创新,会使得学生的创造思维限制在一个位置上,这种局限性是不利于培养初中生的作文创作能力的。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嚓腊伯首先醒悟了,高声说道:“一定是殉情自杀冲犯了务敌、务苏那些神灵,赶快烧香跪拜乞求老天吧。”大家恍然大悟,知道不能再让三个“一”逼死恋人们了,全都跪伏在地上恳求饶恕。这时老梅树又开口说话了,声音苍老缓慢,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废除三个‘一’,行自由婚恋,可免灾祸,不然……”他留父母们全都点头称是。瞬间,云开雾散,艳阳高照,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老梅树旁多出了几个巨大的石头永远警醒世人。
从此他留人实行自由平等的婚恋,让有情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现在他留小伙子只要带上两盒茶、两盒粑粑、两瓶酒就可以独自一个人把心爱的姑娘娶回家。“嚓腊伯”也就成了他留人对无所畏惧、有所作为的男青年的称呼。[注] 该传说由六德乡双河村委会二村他留人兰绍吉老人讲述。六德乡文化站他留文化研究中心杨如刚搜集记录。搜集时间:2001年1月5日。
这则关于他留人婚恋习俗来源的叙事文本由以下几个“事件”(fabula)构成:
1. 他留男女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父母、头人包办婚姻);
2. 一棵老梅树(殉情的地点及方式);
3. 男女殉情于老梅树下;
4. 老梅树发出凄厉的呜咽声;
当前,我国高校学风总体状况良好,多数学生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端正的学习态度。但长期以来,受社会、家庭、高校和学生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学风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际上,高校学风建设从来都是一项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不同时代,针对不同特征的学生群体,高校学风建设应该构建不同的模式。因为优良学风对个人、高校乃至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既是确保人才质量、参与国内外办学竞争的需要,也是学生实现顺利就业、参与人才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需求。
5. 嚓腊伯砍老梅树;
6. 老梅树流血;
他留人主要分布在丽江地区永胜县六德傈僳族彝族自治乡,1956年划归为彝族。自称“tha31lu55su55”,汉字表述为“他鲁苏”,即“外路人”之意。当地人认为祖先系外地迁徙而来。旧时他称为“他鲁人”,后统一为“他留人”。长期和汉族、傈僳族杂居。
7. 包办婚姻废止。
他留人认为最早的时候,不是男子来串女子的“青春棚”,而是女子选择中意的男子,主动串他的“青春棚”。在他留人中广为流传的《巴长马》以一个“难题求婚”而失败的悲剧故事解释了习俗转变的由来。
随着殉情现象的蔓延,情死树的传说逐渐增加了神秘性和怪异色彩。前面提到的大东巴和文质殉情未果的原因是因为正准备上吊,大杜鹃树突然倒了下来,于是遵从天意,放弃自杀。纳西族民间故事《放猪栽桃》讲了情侣安朱拉来咪和后生朱补朱德若殉情而死,从骨灰堆中长出来两棵连理树。杨福泉教授在《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一文中提到了中甸(今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流传着“情死树”的传说。据著名东巴久高吉的女儿(74岁)讲,传说过去有的年轻人在一棵树上殉情而死。人们在经过这棵树时,会听到男女哀哀的哭泣声。有一次,有人用斧子去砍这棵会哭的树,可里面竟流出血来。在拉市坝流传的“情死树”(山楂树)故事中也有砍树而树出血,然后人变疯的情节。当地民众认为这棵“情死树”是由殉情者——祖古羽勒排和开美久命金的生命和灵魂变成的,不能冒犯。大东乡也流传着类似的传说,相传鸣音乡一家人有三个儿子都在同一棵树下殉情而死,其父怒而砍树,树上忽现小蛇的情节。
这种生命、灵魂与树相关的“情死树”故事可能与东巴经神话中“生命树”(“含英包达孜”)的观念有关,是东巴教树木崇拜的典型反映。[注] 杨福泉.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J].民间文化,2000,(1). 纳西语称殉情为“游舞”(yeq vq),东巴字符为一片飘零的树叶,下面为舞蹈之人。根据李霖灿记录的美利董阿普的传说,生命树上黄叶的凋零意味着生命的逝去。[注] 李霖灿.么些经典译注九种[M].台北:中华丛书编委会,1978:246. “情死树”的传说,多少与纳西族认为生命寄托于树木的观念有关。
教师在针对现阶段初中生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应全面利用音乐产生情感共鸣的特性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引导教育,确保学生在接受音乐知识的基础上保证学生综合素质的建设。
纳西族的殉情传说因其现象之普遍,研究之深入而深为世人所知,而他留人的“老梅树”传说则往往让人忽略其“殉情”的情节。将他留人的“老梅树”与纳西族的“大杜鹃树”传说进行比较,可以判断两则传说均为“情死树”传说,且互为异文,是同一母题在不同时空呈现的变体,两个故事互为模仿,既同又异,也许有先后之别,却无高下之分,构成一种平等的位移(dislocation)关系,各自为其认同的习俗进行合理性话语建构以及文本支持。
(二)悲伤的巴长马:男子串“青春棚”的由来
在处于同一地理单元中的丽江纳西族中也普遍流传着“情死树”的殉情传说。载于《东巴经》的第一部殉情传说《鲁般鲁饶》中,女主人公开美久命金在一棵“埃刷本使孜”(黄栗树)上自缢,其情侣朱古羽勒排在一棵“美使孜”(藤科树)上自缢而死。杨福泉教授在其著作《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中记录了大东巴和文质为逃脱包办婚姻,试图以一棵用于祈神祭鬼仪式中的大杜鹃树作为“游孜”(殉情之树)自缢未果的事。在该书中还提到出版于德国的“纳西手稿”《哈拉里肯》(殉情者祭仪)中绘制的殉情者都是在各种树上自杀。[注] 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8. 殉情者准备殉情之前先要精心寻找“游孜”,黄栗树、松树、杉树、大杜鹃树、梅树、山楂树等都可以成为殉情树。寻找殉情树的过程叫“游孜果,游孜述”,意为漫游山间寻找游孜树。因此,民间产生了很多“情死树”或“殉情树”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是姑娘们串小伙子的“青春棚”而不是相反。有一个叫巴长马的姑娘喜欢上了一个叫起马巴的男孩,起马巴也喜欢她。可是路途遥远,巴长马挎上“次卡”(挎包),背上一盒粑粑,去串起马巴的青春棚。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对于巴长马的到来,起马巴非常高兴,但他的“青春棚”里还有另外三个追求他的姑娘,于是他们互相吟唱对答,各表心迹,各表爱慕相思之情。巴长马和起马巴真是一对人间情种,天造地设的一双,可是他们却是天生冤家,心投意不合的一对。黎明时分,起马巴故意对巴长马说:“你翻过九座高岭大山,淌过九条深箐大河,前来约会,可见你真心,可我还不相信,假如你能连续十晚上来,我就接受你的真爱。”巴长马起身回家去可还走不到家太阳就落坡了,只好急急忙忙返回。饿了就烧吃一点粑粑,困了就在路上的石头上睡一下,连续七晚上夜夜不落后,和起马巴约会吟唱“熟嘟”(对唱恋歌),真是两情相悦,心心相印,难分难离。只可惜良宵苦短,一忽儿公鸡啼鸣。第八天早晨,巴长马走回去实在是太困了,想休息一下,竟然在路上睡着了。不久,起马巴出来放牧,有牛、马、羊,还有猪,母猪闻到香味就把巴长马剩下的粑粑全吃掉了。巴长马醒后,知道自己没有粮食,又不好意思开口去借,再也无法坚持最后三晚上,挺不过这苛刻的考验了,就哭着跑回家去,回到家里,巴长马就病死了。她的姐妹们知道后十分悲痛,决心不再去串男孩子的青春棚,自己搭起了“青春棚”要让起巴长马之类的男孩子也来经历一番考验。从此以后,他留人就变成了由男孩子来串女孩子的“青春棚”了。[注] 该传说由六德乡三板桥村兰恒发、上朗者村兰兴旺、树柏佐村王俊国讲述,杨如刚搜集整理。
根据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对“难题求婚型”传说的分类[注] 伊藤清司.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A].辽宁大学科研处.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C].1983:1;在该文中,伊藤清司将“难题求婚型”传说根据发难者的不同分为A、B两种类型。A型是姑娘或姑娘的父亲向求婚的小伙子出难题,B型则是有权势者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或女儿而向该人或其父出难题。 ,《巴长马》属于典型的A型传说,即姑娘本人向求婚小伙出难题。傅光宇教授认为,“难题求婚型”故事起源于金沙江以北,其核心内容反映了“旱地杂粮农耕兼渔猎的经济生活”[注] 傅光宇.“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J].民族文学研究,1995,(2). 。在他留人这则传说中,女方对男方的考验内容虽没有涉及劳动生产的整个过程,但其中牛、羊、马、猪并存的放牧情节反映了他留人游牧与农耕并存的经济形态。他留人“过七关”的婚恋习俗实际上也是对男子进行考验的具体体现,其目的即为取得与姑娘恋爱的资格。每一关都有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名字:独木桥、夹筷子、锅庄石、织布架子、葫芦笙、纺车、秋千架。一方面这些名字与他留人的生活关系紧密,同时又包含着过关考验及婚姻生活中两性关系不稳定、婚姻生活不易的寓意。
高昂的代价使有情人难成眷属,山盟海誓,生死相许的恋人们誓要在另一个世界里结为夫妻。他们乘家人不备,成双成对地来到他留古城东侧的峭壁下,这里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其中有一片梅林,梅林里有一棵千年老梅树,情人们双双来到老梅树下,吃光喝光所带的东西,拥抱着哭泣,流干了眼泪,最后双双上吊殉情而死,化作蝴蝶、喜鹊,双栖双飞。天长日久,每到雷雨黄昏,这棵老梅树便发出凄厉哀号的“呜呜”声,叫人听得毛骨悚然,惊惧不安。
三 、比较视阈中的婚恋习俗与文本建构
把他留人的婚恋传说和传说反映的习俗相联系,女子串男子“青春棚”向男子串女子“青春棚”的转变,说明女子在婚恋关系中由主动择偶变为被动等待,可视为女子择偶主动权和自由度的丧失。刘亚虎认为这种“考验”原型“可能是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从夫居’代替‘从妻居’的过渡阶段里,母权制传统反对新出现的父权制婚姻的某种方式。”[注] 刘亚虎.神话与诗的“演述”——南方民族叙事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9. 黄大宏也提出此类故事正是“母系制度晚期婚姻制度、婚姻习俗演变的历史证明。”[注] 黄大宏.中国“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婚俗历史观——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制度的关系假说[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2008年以来,贵州省麻江县完成了5个年度(2008—2012年)的石漠化综合治理任务,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该县也因工作突出曾两度 (2009年、2012年)被评为全省石漠化综合治理先进县。及时梳理和总结前阶段工作,探索创新治理思路,对深入推进石漠化治理工作和提高治理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择偶主动权的转移与“改土归流”后妇女地位的降低不无关系。杨福泉教授在分析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时,注意到女性殉情者远远多于男性,他认为这种现象与清朝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有直接关系。流官政府以儒家礼教和内地汉俗为标准,对夷地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的移风易俗,包办婚姻制日益强化。强制性的移风易俗政策使得纳西族的婚恋习俗形成特殊的二元婚恋形态——“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这是造成纳西族青年男女殉情的关键因素。[注] 杨福泉.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J].民间文化,2000,(1). 赵省华(Emily Chao)的研究也表明,纳西族的殉情成为一种普遍习俗是1723年清朝在丽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尤其是1780~1949期间,殉情现象在纳西族青年妇女中快速蔓延,清朝的统治使纳西母系体制中相对平等的两性体制系统发生了转化。他认为,“纳西人的自杀是本土文化的‘剧本’和汉文化的‘剧本’的冲突而引起的”。而根据洛克和顾彼得的叙述,汉族统治丽江后,婚前性自由以秘密的方式得以残存,而且这不仅限于纳西族,是丽江区域内的通则。[注] 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90. 虽然没有更多资料证明他留人“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现象,但是根据其传说和洛克、顾彼得二人的调查,可以判断他留人在大规模的移风易俗活动中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古时候他留人的婚姻也是包办买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牢牢掌握在父母手中,没有丝毫自由。痴心的小伙子上门提亲,姑娘的父母就拦在门口说:“请你拿出三个‘一’来,否则请别再来打扰我家姑娘。”小伙子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而痴情的姑娘只能隔门抹泪,等待着另嫁他人的结局。所谓三个“一”是:一百盒粑粑(每盒36个)、一匹骏马、一百两银子。
滇西北地带番夷杂处,形成了南北高山纵谷的地理结构,其政治、文化体系既有固有的传统,又受明清帝国推动的相关制度的影响,地理及文化状貌极为复杂。丽江纳西族和永宁纳西族摩梭人作为处于同一地理和行政区域内的两个族群,成为学者们考察“夷汉融合”状态具有对比意义的群体。笔者认为,在当前已有的“纳西-摩梭”一个民族两个支系婚俗对比研究框架中,引入他留人为参照;或者在因殉情传说的相似性而产生对比意义的“纳西-他留人”研究框架中,引入摩梭人作参照,较之非此即彼的极端案例,应该更能反映长期“夷汉融合”带来的文化接触和变迁的“中间式”与“过渡式”的存在样态。
实现“三教融合”的有效路径就是通过农村普法教育的方式和途径,将自治教育和德治教育内容填充其中。这是因为,普法教育内容与自治教育、德治教育存在内容上的交集和方式上的共通。一方面,村民自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我国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外,一般是村委会自身制定的自治性章程规范,而后者制定的渊源是前者。德治教育的内容离不开法律这一最低的限度,法律既是实现道德的手段,也是衡量道德的标准。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普法教育,无论是传统的说教宣传手段,还是便捷先进的普法形式,在乡村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和固定的通道,利用成熟的媒介进行“三教融合”便利又高效。
杨福泉教授注意到,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远近,决定了土著族群受汉文化辐射并发生涵化的程度。永宁和四川盐源地区的摩梭人由于未纳入“改土归流”的范围,其婚姻古俗得以保留;而丽江纳西族和他留人则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以夏变夷”的政治文化运动中。“以丽江坝区为中心的婚姻性爱习俗的变迁是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渗透而产生的。越远离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丽江坝区,这种变迁就越显薄弱,形成一个类似由强趋弱的磁场辐射圈。而殉情则是集中发生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丽江。”[注] 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55. 丽江县城、坝区与边远山区受汉文化的涵化程度也不一样。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县城的殉情人数并不多,杨福泉认为这与丽江县城的居民大多是明清时期从汉地迁来的移民,不存在如其他纳西族地区一样的传统文化与清代输入的汉文化的冲突;丽江坝区和近郊的“殉情”现象就远远高于宝山乡、奉科乡、鸣音乡等边远山区。可以说,越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汉文化的辐射就越少,“殉情”现象也就少得多;反之亦然。依据封建时期汉文化影响的深浅程度,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格局。
除了转让子公司或孙公司保壳,卖房卖土地以求留A的上市公司也不在少数,上述*ST椰岛股权转让的同时也搭配出售椰岛综合楼。
连瑞枝在《山乡政治与人群流动》一文中指出,滇西北在整个西南具有“缓冲地带”的意义,“云南与吐蕃的缓冲地带经历了一段由大理往北漂移到丽江的过程,这主要和明朝的边区治理有关。”又“以丽江、永宁、北胜为厄塞”[注] 参见连瑞枝.山乡政治与人群流动——十五至十八世纪滇西北的土官与灶户,载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2016年12月14号. ;而北胜州位居蜀滇交界,不仅是大理北方之藩篱,也是边陲重地。清代永胜地方志书乾隆《永北府志》载:“永郡在金沙江以外,界接吐蕃。……南连宾邓,北拒蕃彝,东至元谋,西通鹤丽。作大理之藩篱,引控诸土司;为武姚之屏蔽,地交乎滇蜀。人杂汉夷,边陲重地,览兹图者,慎勿忽焉。”[注] 刘慥.乾隆《永北府志》(卷1)[Z].云南省永胜县地方志办公室翻印,1993:14.
可以说,他留人世居的北胜州处于滇西北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地带”;他留山作为北胜州的“东郊”,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属于“夷地”;从文化的“夷汉融合”角度而言,他留人又处于族群文化变迁的“中间地带”。因此,他留人不可避免受到“改土归流”影响,同时又保留了大量的土著文化因素。可以想象,“夷”与“夏”的互动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夷汉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实际上,对他留山实际的统治者——高土司的“改土归流”本身就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明洪武十七年(1384),永胜改府为州,就已设流官;但是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才彻底“改土归流”,由此带来的“夷”与“夏”互动则更为漫长而复杂。相对丽江坝区纳西族,他留人受“改土归流”的影响小一些,“夷汉融合”的结果最后极有可能就是“汉”融于“夷”,形成一个特殊的族群——他留人,如黄彩文教授关于他留人形成的看法:“他留人的形成就是物质发展程度较高的部分内地汉族,杂居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而融合于物质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的典型例子。”[注] 黄彩文.彝族支系他留人的历史源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可以说,融合了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他留文化具有杂糅性以及“以夏变夷”的不彻底性。笔者认为,他留人的婚恋习俗传说正是这种杂糅性与不彻底性的反映。
改土归流后纳西族中存在的“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二元婚恋形态同样符合他留人的情况。《老梅树》和《巴长马》的传说中体现出来的“抗争”“殉情”“妥协”等主题折射了他留人面对强制性的“以夏变夷”移风易俗政策的反抗与斗争的过程。不过,将纳西族和他留人“情死树”殉情传说作比较,发现其逻辑起点并不一样:纳西族的“殉情”传说认为,年轻人的恋爱、婚姻传统原来是自由、自主的,转变为封建包办婚姻后,才出现了“山楂树”下的殉情;而他留人的传说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古时候他留人的婚姻是包办买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牢牢掌握在父母手中,没有丝毫自由。高昂的婚姻成本使得男女相约于“老梅树”下殉情而亡,于是婚俗始变为今天后来所见的自由、自主的状态。在纳西族的传说中,“殉情”是结果;而他留人传说中的“殉情”则是条件。相形之下,纳西族的“情死树”传说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更具有逻辑性。不过,笔者认为,不能就此武断地判断他留人的传说缺乏逻辑性。传说是“历史的故事”[注]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9. ,其功能在于“阐释”——对当下不合理的、缺乏逻辑的、需要说明的现象进行解释。因此,纳西族“情死树”传说需要对严苛的封建婚姻制度中的“殉情”现象进行解释;而他留人“老梅树”的传说则需要对自由、自主婚恋风气的由来进行阐释,因此出现了其传说中最早的婚姻形态是包办婚姻这种不太符合历史逻辑的表述,但却暗合了传说的特点——传说总是为当下服务,其表述具有一定的情境性,总是处于选择性的建构中。
4.3 DNA疫苗 编码HPV的DNA不会在人体内复制,且通过电穿孔技术等方式可以进入靶细胞,并呈递HPV抗原,引起免疫应答。DNA疫苗性质稳定,且相对于病毒载体蛋白而言可以重复免疫,但是免疫原性较弱,且存在与宿主发生同源重组,从而导致DNA随机插入的可能,继而引发各类问题[14]。
除了从传说自身特点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联系当时“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笔者猜测,他留人不太符合逻辑性的“老梅树”传说却恰好反映了在“以夏变夷”“夷汉融合”的过程中,汉融于夷,封建包办婚姻最终未能取代传统自由婚俗的历史记忆。可以想象,这个过程一定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殉情”以及砍树而树流血等情节正是对这种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烈冲突历史记忆的折射。
从理论上讲,冲突的结果是自由婚恋传统最终在他留人社会生活中占了上风,未被封建包办的婚俗所代替,但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他留人的婚俗也一定会不同程度留下汉文化的影子。实际上,结合传说,对他留人的恋爱及婚姻家庭形态进行考察,笔者认为其婚恋习俗体现出的杂糅性和“不彻底性”正是在“夷汉融合”背景下,文化呈杂糅过渡中间状态的反映。1962年较早对他留人的婚姻、家庭做实地调查汪宁生教授对他留人的婚姻形态做了初步分析,他认为“他鲁人婚姻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偶婚极不稳固的结合”,而且在这种配偶婚家庭中,“由于有一部分妇女终身过自由性生活而永不正式结婚,以及离婚之普遍及离婚或夫死后子女必须随母回娘家的习惯,使得大量实行夫方居住和父系传递的家庭之外,还有一部分按母系传递的家庭,另有一部分家庭交替地实行父系和母系,这种父系和母系交错存在的情况,在他鲁人的亲属称谓中也有所反映。”[注] 汪宁生.云南永胜彝族(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C].2013:203. 汪教授在其论文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相同,周围汉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他留人的氏族也已瓦解,而他留人还保持原始的对偶婚制?为何他留人的对偶婚家庭又会出现母系和父系交错存在的情况?他留人的婚姻既不同于永宁纳人的“阿注”对偶婚和母系家庭,也不同于纳西族的一夫一妻制及父系家庭,它正好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从女子串棚子变为由男子串棚子,说明女性主体地位及独立性的丧失,在婚恋中主动变为被动;过“七关”但又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自由串“青春棚”,最终却又得确定与某一人结婚;与某人结婚,但离婚又很自由。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矛盾之处及文化的杂糅性都与他留人社会在“改土归流”运动中,“以夏变夷”的不彻底性有关,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夷汉融合”的历史过程复杂性与过渡性。
四 、结 语
早期的“羁縻”、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以及随之而来“改土归流”政策,都是“以夏变夷”长期的政治文化过程。王明珂先生提出以“边缘”漂移来界定“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反中心主义的努力,但仍局限于“夷夏”二分但身份及文化边界可变动的“天下”体系。[注]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实际的历史进程,历时久远,枝节横生,汉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能够充分反映文明等级之间互动关系的“中间式”论述框架——“中间圈”“缓冲地带”“中间地带”等理论对于西南研究意义深远。
以中央俯视“西南”,它处于远离中央王朝及文化中心的边缘;将其置于“中间式”论述框架中,它处于更大的地理及文化区域内的“中间地带”。既有隔离性又兼具中介性的功能使其具有区辨内外的政治、文化意涵。它与巴斯的“边界”和王明珂的“边缘”等不同,连瑞枝认为“它是由许多的‘点’所组成‘面’的区域,其由重重区隔、层层表里的人群与空间所组织而成。随着外缘历史条件不同,它的范畴也会随之扩大、缩小、漂移或是被重新定义。”[注] 参见连瑞枝.山乡政治与人群流动——十五至十八世纪滇西北的土官与灶户,载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2016年12月14号. 在该地带,中央王朝的力量、土著甚至是移民的力量均会在此交织,从而带来跨文化接触的复杂性。同时,“中间地带”还可以在任何疆界流动中生成,不断生长出新的“中间地带”。作为一种视角,“中间地带”不仅能让跨越中国西南与亚洲边疆的一些大区域的历史场景获得空间与过程的解读,也便于从微观式聚焦的社会文化场景中透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滇西北的地理及文化框架中,因与汉文化的远近关系,族群之间呈现出文化的过渡场景,而他留人的地理及文化生境正是西南较大“中间地带”中生成的较小区域内的“中间地带”的典型,对其所处文化系统内不同群体的对比研究,利于理解不同边界人群的行动性与主体性以及面对文化政治的游移与流动形成的文化状貌,也为“中间式”论述框架提供了更为具体、丰富的个案与可能性。如纪若诚所言,在文化的接触与变迁过程中,各方都是行动者,都是变革的对象,[注] 纪若诚.“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A].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西南边疆的某些文化接触,或许并不一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力量角逐,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在碰撞中出现,不同族群所处的空间与过程的差异,使得文化碰撞的结果呈现丰富的内容与样态。
The “middle ground ”of cultural change :A study of some legendary stories of martyred love of the Taliu people and the Naxi ethnic group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wer shift from local chieftain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YANG Xiao -w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researches on southwest China,and adopt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middle ground” that contains a geographical domain and implies the process of ethnic fusion.It analyzes such legendary stories of martyred love like An Old Plum Tree of the Taliu people (a branch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Yongsheng and Lubanlurao of the Naxi people in Lijiang.The two legendary stories have the same theme of “Tree Symbolizing Martyred Love”,but the Taliu's story gives the reason for the shift from arranged marriage to free marriage,while the Naxi's is vice versa.The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stories and the policy of “power shift from local chieftain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implement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in southwest China reveal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martyred love in the two ethnic group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cy of forc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stablished customs that led to the binary marriage pattern of “free love without free marriage”.The similar texts reveal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pattern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with Han culture.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Taliu people is a typical smaller “middle ground” in the relatively larger “middle ground” in southwest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marriage customs will reveal the complexity and provisionality of the historical fusion of the Hans and the ethnic groups,and provide better cases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iddle ground”.
Key words : middle ground; Naxi ethnic group; Taliu people; legendary stories of martyred love; power shift from local chieftain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作者简介 ]杨晓雯,女,云南永胜人,云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变迁视野中的他留人族群认同研究”(YB2016040)。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2-0140-08
[责任编辑 :黄龙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