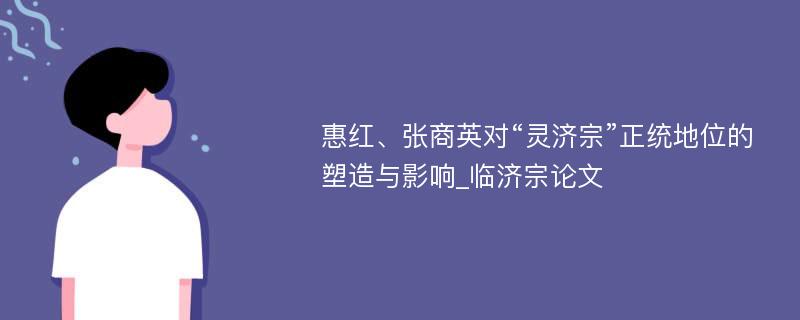
惠洪、张商英对临济宗正统地位的塑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统论文,地位论文,临济论文,惠洪论文,张商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45-8
宋人理性精神增强,普遍尊崇历史事实,这一风气在宋代的禅林世界之中亦得到体现。而就转生而言,宋代正统儒家学者往往视之为妄诞不可信之事。在禅宗内部,亦有禅僧怀疑神化事迹的真实性,或者认为随意转生是错误的,并不认同[1]。从宋代的灯录来看,也往往“有意识地消解掉僧传系统中神化性的色彩,把祖师和佛的形象人间化”①。不过,在宋人惠洪和张商英等人的笔下,仍然出现对禅师转生的叙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关系到临济宗系谱源流的“小释迦”转生再来一事。笔者将通过考察惠洪、张商英所运用的原始材料,来说明这一叙述的特质。以此为基础,笔者将考察惠洪、张商英这一叙述与历史语境、宗教观念、宗派立场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叙述所表露的意图、达到的效果,以及其在历史上造成的实际影响。
“小释迦”仰山慧寂转生再来一事最早出现在惠洪的《智证传》中:
昔黄檗尝遣临济驰书至沩山。既去,沩山问仰山曰:“寂子,此道人他日如何?”对曰:“黄檗法道赖此人,他日大行吴、越之间。然遇大风则止。”沩山曰:“莫有续之者否?”对曰:“有。但年代深远,不复举似。”沩曰:“子何惜为我一举似耶?”于是仰山默然,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风穴暮年,常忧仰山之谶己躬当之,乃有念公,知为仰山再来也。[2]
据《智证传》,慧寂预谶希运的法道将会“遇大风则止”,其法嗣年代深远。灵祐让他说出一人,慧寂便说:“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延昭害怕慧寂的谶记在自己身上应验,晚年得法嗣省念,知道他正是慧寂的后身。南宋禅僧惠彬在《丛林公论》中引述了《智证传》的这一记载,批评说:“《智证传》仅三万言,动谬佛祖之意。略举此数端,学者宜审之。”[3]认为《智证传》的记载违背了佛祖的意思,希望学者仔细审视。
从《智证传》来看,其中涉及到希运、义玄、慧寂、延昭、省念等禅宗史上重要人物的相关史实,距惠洪的生活时代已相去遥远。那么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惠洪采用了哪些史料?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的记载:“师又因栽松次……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沩山举前因缘问仰山:‘黄檗当时祗嘱临济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沩云:‘虽然如是,吾且要知。汝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谶风穴)。’”[4]从字句上看,惠洪《智证传》叙述的前半部分与此相似。
《天圣广灯录》接下来记录了另一次对话,说义玄将要离开希运,希运问他到何处去,义玄回答说:“不是河南,便归河北。”希运便打,义玄接住给了一掌。希运大笑,乃唤侍者,将怀海的禅板几案拿来。而义玄却叫“侍者将火来”,要烧掉怀海的禅板几案。这样看似激烈的行为表明,他已领悟不立文字、不落言诠的禅宗旨趣。希运便说:“虽然如是,汝但将去,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说明他对义玄未来的传法已有信心。后来灵祐问慧寂:“临济莫辜负他黄蘖也无?”慧寂认为并非这样,“知恩方解报恩”。灵祐又问:“从上古人还用相似底也无?”慧寂云:“有。秖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灵祐让他举出一人,慧寂便说:“秖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将此深心奉尘剎,是则名为报佛恩’,岂不是报恩之事?”[5]阿难这两句诗偈出自《首楞严经》卷三,按照北宋华严学者的理解,其含义是:发誓将以此深心承顺无量国土诸佛的教化,传法度生,这就是报答佛恩②。而慧寂举阿难的诗偈是为了说明:这一报恩之事与临济义玄的举动相似。
宋仁宗于景祐三年(1036)为《天圣广灯录》作序时说,该书“迹其祖录,广彼宗风。采开士之迅机,集丛林之雅对。粗裨于理,咸属之篇”[6],指出其史料来源包括禅门祖师的语录和机缘语句,而《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所涉及的正是临济宗、沩仰宗开山祖师。后来,收入《马祖百丈黄檗临济四家录》中的《镇州临济惠照禅师语录》中也有上述两节材料,文字基本一致③。杨杰于元丰八年(1085)为《四家录》作序说,“积翠老南,从头点检”,“诸方丛林,传为宗要”[7],可见慧南居积翠庵时曾点检道一、怀海、希运、义玄的语录,而此本在丛林中流传甚广。
惠洪乃临济宗黄龙派创始人慧南之法孙,他平生多称说上述四位禅宗祖师之语,曾撰写《临济宗旨》,阐述义玄、延昭、善昭等临济宗禅师的纲宗法要,在《题宗镜录》中又极力推崇道一、怀海、希运等禅宗祖师的语句[8]。另外,惠洪曾说自己手校《断际禅师语录》[9]。他还将道常重编的《大智广录》与当世所传者相互校对,指出后者多所讹略,可见他有《大智广录》的多个本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惠洪还提到“黄龙无恙时客”知琼为其“言黄龙住山作止甚详”,说慧南“尝手校此录于积翠”,与杨杰所说甚合[10]。除此之外,惠洪所编《禅林僧宝传》一书中,卷三《汝州风穴沼禅师》、《汝州首山念禅师》、《汾州太子昭禅师》,卷一一《洞山聪禅师》、卷一六《广慧琏禅师》的部分史料都可与《天圣广灯录》相互参证。惠洪《林间录》还记载说,临济义玄临终《付法偈》本为“离相离名如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而传者作“急还磨”[11]。尽管惠洪没有指明存在这处错误的文献,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正作“急还磨”[12]。
相互比对可知,《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或《镇州临济惠照禅师语录》虽在《智证传》中留下了痕迹,但却并未像《智证传》那样集中了上面两节材料,认为这是慧寂预言自己的后身。《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和《镇州临济惠照禅师语录》的小注中也说明了“遇大风即止”是“谶风穴”,但并没有像《智证传》那样,说延昭担心自己应慧寂之谶。
而据比《天圣广灯录》更早出现的灯史《景德传灯录》的记载,“黄蘖曰:‘吾宗到汝,此记方出’”,可知应谶之人乃临济义玄,但并未说明谶记内容。该句下小注云:“沩山举问仰山:‘且道黄蘖后语但嘱临济,为复别有意旨?’仰山云:‘亦嘱临济,亦记向后。’沩山云:‘向后作么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独坐震威,此记方出。’又云:‘若遇大风,此记亦出。’”[13]可见所谓“遇大风”是光涌对慧寂谶记的注解,但并未明确说明应谶之人,也未说是“遇大风即止”。延昭本人倒是在《临济慧照禅师塔记》中提到“师正旺化,普化全身脱去,乃符仰山小释迦之悬记也”[14],可见延昭知道此谶记的内容④,但这里所说的应谶之人并非他自己,而是义玄和普化和尚。另外像《汝州首山(省)念和尚语录》亦记载说,延昭担心“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于地矣”,可以与谶记联系起来,但按延昭的说法,却是觉得门下弟子“虽敏者多,见性者少”[15]。事实上,南宋时《联灯会要》的编撰者悟明就怀疑说,尽管“丛林皆以风穴沼禅师当是记”,但延昭与廓侍者一同坐夏,后者曾见到与义玄同时代的禅师宣鉴,因此延昭虽然不及见到义玄,但已致身禅林很久,“安得年代深远乎”?他推测说“吴越令行,遇大风而止”乃是预谶宗杲,因为宗杲“为临济十二世孙,可谓年代深远。先住吴之径山,后住越之阿育王,可谓吴越令行也”。不过悟明最后还是说,这是“贤圣谶记,故不可得而知”,可见其同样不敢确定谶记的含义[16]。
至于省念嗣法于延昭,这同样已经记载于《景德传灯录》卷一三《汝州首山省念禅师》、《天圣广灯录》卷一六《汝州实应禅院省念禅师》、《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一《汝州首山省念禅师》、《汝州首山(省)念和尚语录》等佛教史籍,却都没有像惠洪这样,以此来说明慧寂转生誓愿的实现。
因此,《智证传》记载的慧寂转生一事是有问题的——尽管《智证传》中这一转生事迹往往可以找到某些更早的、并非虚构的史料来源,但惠洪不是原文抄录,而是将记录不同时间、不同对话场景、不同事件的分散材料联缀在一起,又加入自己想象的运作,从而形成了本来并不存在的联系;凭借这种穿凿附会的联系,惠洪构造了与既有史料记载不同的禅宗史。
北宋时,不止惠洪一人提到仰山慧寂的转生神迹。据《罗湖野录》记载,张商英登右揆后,于政和元年(1111)二月为从悦禅师撰祭文⑤云,“昔者仰山谓临济曰:‘子之道佗日盛行于吴越间,但遇风则止。’后四世而有风穴延沼,沼以谶常不怿,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无遗恨矣。’……风穴得一省念,遂能续列祖寿命”[17],已将慧寂的谶记、延昭的忧虑和省念承嗣延昭三件事联系起来,并声称省念传得正法眼藏。张商英是从悦的弟子,而从悦与惠洪同为克文的弟子,同属临济宗黄龙派。惠洪大观四年(1110)、政和元年(1111)亦在东京,并且是张商英的门客,有证据表明他在这期间曾为张商英代笔撰文[18]。惠洪后来在宣和元年(1119)所作的《岳麓海禅师塔铭》中亦云:“临济纲宗,遇风则止。昭忧其谶,得念而喜。”[19]与张商英的说法完全一致,甚至文字也颇为近似。不仅如此,后来行秀禅师还引述说,张商英同样提到了慧寂的转生神迹:
师云:“无尽居士(按,指张商英)举临际辞沩山,仰山侍其傍。沩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他日法道大行吴越,遇风即止。’又问:‘其嗣之者何人?’仰曰:‘年代深远,未可言耳。’沩固问之曰:‘吾亦欲知。’仰云:‘《经》不云乎:将此深心奉尘剎,是则名为报佛恩。’居士曰:‘吾以此知风穴仰山之后身也。’”[20]
张商英讲述的转生神迹与《智证传》很相似,不同的是,张商英认为慧寂的后身是延昭而非省念。行秀在《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中对此说得更加简洁:“风穴应小释迦谶,无尽居士谓仰山后身,如投子为慈济再来。”[21]而惠洪在《蕲州资福院逢禅师碑铭》序中再度叙述了慧寂的这一转生神迹:“昔临济北归,仰山叹曰:‘此人它日道行吴越,但遇风则止。’沩山问:‘有续之者乎?’对曰:‘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故世称念法华为仰山后身。”[22]照此看来,既有史料为慧寂的转生神迹提供了依据,而到北宋晚期此事已流传于世,惠洪、张商英并非始作俑者。但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一转生神迹正是最早出现在惠洪、张商英二人的著述或言论中,并且他们又多次讲述此事,亦与二人的佛教观念相吻合。
北宋时期《首楞严经》“市工贩鬻遍天下”[23],讲家疏论亦多,已经成为盛行于世的佛典之一,而惠洪、张商英亦熟稔《楞严经》。惠洪本是主张“藉教以悟宗”[24]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祖师是佛弟子,若穷得佛语,祖师语自然现前”,曾撰写《楞严尊顶义》,通过笺释《楞严经》来融会禅教。不过,惠洪反对义学,对在他之前的讲家疏论并不满意,“倚恃宗眼,一笔抹杀,目为义解讲师”[25]。同样地,如果说《智证传》讲述了转生神迹的话,那么其中出现的“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两句《楞严经》诗偈就只能被理解为发愿转生,并且所去随愿。显然,这不是依文解义,而是与佛教所谓“愿力”的观念相关。事实上,“愿力”一词在惠洪《禅林僧宝传》、《石门文字禅》等撰述中多次出现,常被用来解释历史事件或禅师的身世,是惠洪经常运用的佛教观念之一。与惠洪一样,“无尽居士”张商英在《护法论》和文章中也采用过这一观念。
据柳田圣山分析,《天圣广灯录》卷一○《镇州临济院义玄惠照禅师》在记录希运和义玄的问答之后,又出现灵祐和慧寂,“这很可能是因为临济宗必须借重于比自己更早开宗的沩仰宗的权威而造成的结果。换而言之,很有可能临济宗当时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因此它仍然不得不仰仗于沩仰宗的盛名”[26]。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论断,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说,到北宋晚期张商英、惠洪对延昭或省念乃慧寂后身的叙述,固然将临济宗祖师的生平事迹神化了,但这种神化同样是借助沩仰宗的权威方才塑造起来的。
有证据表明,惠洪亦受到世俗正统史观的影响⑥。惠洪亦具有自居释门正统、排斥异端的倾向,其撰写《智证传》一书的原因正是在于“悯后生之无知,邪说之害道”。此外,《智证传》一书往往先举经论或先德公案,然后在“传”中加以诠释,这一体例显然是比附儒家经书《春秋左氏传》,以标榜该书的权威性和正统性。而为该书作序的许顗亦以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之语来说明《智证传》与《春秋》的关系,甚至认为“犹未若此书有罪之者,而无知之者也”,“宁使我得罪于先达,获谤于后来,而必欲使汝曹闻之”,极力称扬惠洪勇于护持正法的用心[27]。
上文所述慧寂的这一转生神迹出现在“传”中,而正文首先引述了省念在延昭法席下时师徒之间的机锋语句[28]。据正文,延昭升座,用佛陀“以青莲目顾迦叶”(即“拈花微笑”)的公案问学人:“正当是时,且道说个什么?若言不说,又成埋没先圣。”话还未说完,省念就下去。延昭知道他已经领悟,对侍者说:“渠会也。”第二天省念与真上座俱诣方丈,“风穴问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说说?’……(省念)对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省念的意思是说,一动一静都与大道冥合,不落任何心机。接下来,惠洪在“传”中对此进行了诠释。他首先引用了省念法嗣善昭的“一字歌”:“诸佛不曾说法,汾阳略宣一字。亦非纸墨文章,不学维摩默地。又曰:饮光尊者同明证,瞬目钦恭行正令。”然后评论说:“真漏泄家风也。”“拈花微笑”公案在北宋中后期甚为流行,据这一公案的说法,摩诃迦叶印得正法眼,后来被尊为禅宗初祖。惠洪的诠释无异于点明:不说而说、非言非默是临济宗风,破颜微笑(如摩诃迦叶)、瞬目钦恭等动作亦是临济宗风,而这在延昭、省念、善昭身上代代相传,都契证了佛陀、摩诃迦叶以心传心之旨。照此而论,临济宗自然为佛门正统。不仅如此,惠洪在《智证传》中“离合宗教,引事比类,折衷五家宗旨”[29],表现出会合、折中禅教和诸家宗风的倾向,并且常常援引类似故事,出现在“传”中的慧寂这一转生神迹就是如此:“仰山默然,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在他看来,慧寂的语句、行为与延昭法席下的省念是相似的,省念就是仰山慧寂的后身。鉴于宋代临济宗黄龙派禅僧和惠洪本人都清楚“小释迦”慧寂及其“沩仰宗枝不到今”的事实[30],这无异于为延昭、省念的法系传承寻求到一个神圣的渊源,而延昭、省念续佛祖寿命的意味同样是很明显的。
惠洪乃延昭七世孙,他正是通过领悟延昭、善昭的偈颂而发明大事,事在元符二年(1099),时年二十九岁[31]。惠洪后来编撰《禅林僧宝传》,卷三就为延昭立传,延昭也是该书中首位临济宗禅师,同卷还包括其法子省念、法孙善昭,灯灯相传的意味非常明显。在惠洪看来,正是延昭、省念、善昭的“哲人事业”使临济宗得以兴起[32],可见三人在临济宗系谱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惠洪亦再次叙述说,“风穴每念大仰有谶,‘临济一宗,至风而止’,惧当之。熟视座下,堪任法道,无如念者”,接着叙述了延昭、省念师徒之间的机锋语句[33]。同样将慧寂的谶记、延昭的忧虑和省念承嗣延昭三件事联系起来,与详言示人的《智证传》相比,这不过是没有直接说破转生神迹而已。
禅宗注重自身宗派系谱,作为从悦禅师弟子的张商英同样不例外。在他看来,“仰山、南岳及高山,佛佛同道无异化”[34]。慧寂生前多所神异事迹,驻锡仰山时,曾有山神让居,这也记载于张商英《仰山庙记》中[35]。张商英在《护法论》中还论述说,慧寂曾感罗汉来参,并受二王戒法,从此号称“小释迦”[36]。历来的禅宗系谱都追溯到释迦牟尼等西天诸佛,而“小释迦”这一称谓的由来表明慧寂证果于佛神,因此张商英在证明神迹不诬的同时,无疑也彰示了沩仰宗的正统性。其《祭真寂大师文》亦云:“师于念公为六世孙,于云庵为嫡嗣。住山规范,足以追媲首山。机锋敏妙,初不减风穴……今龙安诸子乃尔其盛,岂先师灵骨真灰烬无余耶?盖其道行实为丛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风,思有以发挥之。为特请于朝,蒙恩追谥真寂大师。”[37]这种追溯从悦以上临济宗系谱的做法,表明渊源有自,从悦对光大佛教、教化众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作为世俗政权认可标志的追谥,则被怀有“外护之志”的张商英视为最为有力的宣扬方式之一。沩仰宗本是最早开宗、最具盛名的禅宗派别,而张商英强调其师从悦乃是延昭、省念的法孙,延昭又以“正法眼藏”付嘱省念——这正是与“拈花微笑”公案中释迦牟尼以“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相类比⑦——又被视为“小释迦”慧寂的后身,因此临济宗(乃至临济宗黄龙派)的神圣性、正统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张商英与惠洪关系密切,相互影响,除了《祭真寂大师文》外,《护法论》的某些观点与惠洪亦有相似之处⑧。在对慧寂转生神迹的叙述上,张商英与惠洪所采用的材料也很近似。另外,惠洪本人还的确提出过“临济正宗”[38]的说法,而这一说法在当时已盛行于世(例如克勤的《临济正宗记》)。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沩仰宗与临济宗本就同出马祖道一法系下[39],因此可以理解,当宋代沩仰宗衰微、临济宗兴起之后,临济宗(包括张商英、惠洪所属的临济宗黄龙派)的正统性就可以从这一转生故事中找到更有神圣意味和更有权威性的根据,尽管张商英和惠洪都没有直接点明这一点。
这一转生神迹对后来的禅宗史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明清之际,临济宗内部圆悟与法藏一系的论争就关联到此事,并最终付诸于政治解决。法藏自称印法于惠洪,得义玄的真传,推崇惠洪《智证传》、《临济宗旨》等撰述。他后来为获得正宗师承而嗣法于圆悟门下,但二人对禅的见解大相径庭[40]。在《五宗原》中,法藏声称“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威音王佛作一大圆相,而诸佛之偈旨都不出圆相。圆相出于西天诸祖,早具五家宗旨,五宗各出一面,而临济宗为“第一先出”的正宗;沩仰宗圆相亦本于此,是所谓“无相中受圆相”[41]。在嗣法问题上,他声称“师承在宗旨,不在名字”,强调宗旨传承,不再看重师徒名分。又借助“沩仰自续风穴于首山,还归慧照”这一最早出自惠洪笔下的转生神迹,来说明临济宗囊括沩仰宗的关系[42];法藏还说,这一转生神迹是乘愿力之人“任彼遥嘱之法,宜其再兴于今之世也”[43],无异于宣称再兴临济正脉的人就是他自己。之后,弟子弘忍《五宗救》亦鼓吹法藏之说,声称“小释迦,果位中人也,发愿以续其断脉”[44]。法藏、弘忍死后,圆悟在《辟妄救略说》中叙述了从西天七佛到他本人的法脉传承(附法藏),并集中批判了二人的观点,认为“汉月瞒心昧己,自不觉羞。妄称仰山乘愿力再来,接续临济断脉”,“一味托仰山再来之名,诳惑天下后世,妄作妄说”,“但看首山,何尝有一字一言,自称仰山再来”,唾骂法藏是混入法门的野狐精,想要灭抹法门,故而自称是仰山再来[45]。
继圆悟之后,其弟子道忞等人亦加入攻击的行列。但法藏的弟子并未接受批评,仍然极力维护师说,并明确将法藏一系立为正宗。如弘储在《三峰和尚语录序》开头即云:“和尚乘仰山尘刹之愿,降神东震旦国,作天童长子。艰危百战,死任纲宗。”[46]认定法藏就是仰山慧寂再来,担负起纲宗重任。弘储另撰有《南岳单传记》,厘定了从始祖释迦牟尼到第六十九祖弘储本人的传法世系,并且记载了法藏“乃书《临济正宗记》付之(按,指弘储自己)”一事[47],其以法藏、弘储一系为佛门正宗的意味非常明显,至于圆悟的其他弟子则排除在外。弘储还在《临济祖塔重建碑》中叙述了达磨以下灯灯相传的系谱,认为“临济氏挺出,集十代之大成,出古今之独断”,“发灵山以来未发之妙”。其《临济祖塔源流序》又将“源流之见”追溯到克勤以《临济正宗记》付与宗杲,并再度讲述了从“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叶”一直到清初临济宗法系辗转相承的情况,指出“至有明嘉隆,山水微茫,仅存一线。禹门禀圆通法付四人。一曰天童圆悟……天童于天启甲子付净慈法藏,丁卯付大沩如学,次第付梁山海明……天童道忞……弘储为净慈藏和尚子”。弘储自称这是“依次序述”,从正法眼藏的付嘱和灯灯相传的系谱说明了临济宗的正统性,而在法藏,则特别说明时间是“天启甲子”,乃圆悟最先付法之人。弘储的弟子南潜又撰有《临济慧照祖塔重建碑后记》,亦提到临济宗的传承,认为“临济以下,自逆而顺,而及天童、三峰,至于老师。临济之道,大行吴越,使小释迦没而不食其言”,同样排除了其他法系⑨,而单提圆悟及法藏、弘储一系应了“小释迦”仰山慧寂的谶记,神化色彩和自命临济正脉的意味甚浓[48]。
南潜在《南岳单传表后序》中还再度讲述了这个“小释迦再来”的故事:
我临济氏,承南岳之明命,兼统五宗,以照耀南天下,于诸宗独尊。黄檗谓临济曰:“吾宗到汝,大兴于世。”沩山举问仰山:“黄檗当时祇嘱临济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祗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及沩固问,仰云:“一人指南,令行吴越,遇大风即止。”后风穴得念法华,成以为小释迦再来。此临济之统沩仰宗也。[49]
按照南潜的看法,临济宗承南岳怀让之明命,在诸宗中是最为尊上的,兼统禅宗五宗,而一统沩仰宗的证据就在于“小释迦再来”这一故事。既有西天祖师以圆相付嘱仰山之说,而法藏、弘忍、弘储等人又声称法藏就是“小释迦”仰山慧寂的后身,弘储的《南越单传记》亦已确立了法藏、弘储一系的正统性,因此南潜《后序》所讲述的果位圣人“小释迦再来”这一故事不仅为临济宗,也为法藏、弘储一系的正统性提供了具有神化色彩的“历史”证据。
圆悟和法藏之间论争的解决,最终来自于皇家的裁决。雍正皇帝撰写《御制拣魔辨异录》,驳斥了法藏、弘忍一系的观点。如该书卷八称,弘忍“若仰山者,悬应西天祖师付嘱圆相之记,实果位圣人”之说“良属梦呓”,“圆相既是西天祖师付嘱,仰山何以又焚却?若仰山平生只此九十七圆相是者,仰山则为疑误众生”[50]。雍正以帝王权威取缔其法系,禁毁其著述。这一举动不只是单纯清理禅宗门户,还针对法藏一系的影响力和反清扶明的倾向[51]。论争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而以“小释迦”转生再来作为法藏一系正统性之根据的禅宗史也便就此成为一部外道“魔说”史。
①龚隽《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57页。按,龚隽将禅宗内部有关禅者行传的资料一律称之为“灯录”,以区别于历代僧传系统。见该书343页。
②此处参照子璿的笺释:“上句同佛化。上求下化悲智二心,一一先悟妙觉明性。从深理生,故名深心。以此二心承顺尘剎诸佛化行,无二无别,故名为奉。下句结报恩。大论云:假使顶戴经尘劫,身为床座遍三千。若不传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见(宋)子璿集《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9册,第872-873页。
③后收入《古尊宿语录》卷五的《镇州临济(义玄)慧照禅师语录·行录》中亦记载了上述两节材料,文字亦基本一致。但据柳田圣山考证,该语录乃是南宋成淳三年(1267)方才新增入《古尊宿语录》。见(宋)赜藏主编集,萧萐父、吕有祥、蔡兆华点校《古尊宿语录》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页。
④据《古尊宿语录》,延昭所说的慧寂之悬记应是指:“但去已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此人祗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见(宋)赜藏主编集,萧萐父、吕有祥、蔡兆华点校《古尊宿语录》卷五《镇州临济(义玄)慧照禅师语录·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2页。
⑤按,《罗湖野录》云“公登右揆之明年,当宣和辛卯岁二月,奏请悦谥号”,误。宣和无“辛卯岁”,张商英登右揆、为中书侍郎,事在大观四年庚寅(1110),明年即政和元年辛卯(1111)。故“宣和辛卯”当作“政和辛卯”。见(宋)张商英《祭真寂大师文》注(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8-249页。
⑥曹刚华以惠洪《禅林僧宝传》中的纪年为证,指出惠洪谈到五代十国时,“冠后梁、后唐以‘伪梁’、‘伪唐’之称,可见他并不承认后梁、后唐的正统之说”。见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⑦张商英在文章中数次强调这一点。如其《东林善法堂记》:“其究竟也,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无相实相,正法眼藏,拨去文字,教外别传,嘱付欲光,宛转传授,以至今日。”《洪州宝峰禅院选佛堂记》:“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7、203页。
⑧按,南宋人俞文豹怀疑《护法论》乃惠洪假托张商英之名而作:“洪觉范假张无尽名,作《护法论》以排儒,谓居士乃佛称,欧公排佛,却号六一居士,正理在人心,未尝泯灭”。见(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上海: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年,第45页。
⑨小释迦之谶在当时同为法藏、弘储一系和圆悟、道忞一系所利用。如晓青、戒显、纪荫都称法藏、弘储一系应谶。而道忞《平江灵鹫寺十方僧田记》则称弘法于吴越之地的圆澄和圆悟、道忞一系应仰山慧寂之谶。不过,明清之际法藏、弘储一系盛行于吴越,道忞在《复灵岩储侄禅师》中也承认“闻郡将归心,台人戴德。令行吴越,在贤侄一人指南足矣”。见(清)道忞《布水台集》卷二八《复灵岩储侄禅师》,《禅宗全书》第98册,第5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