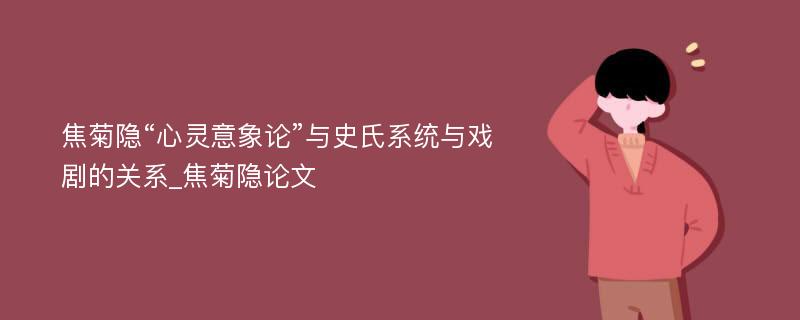
焦菊隐“心象说”与斯氏体系及戏曲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象论文,戏曲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焦菊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象说”是我国当代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在5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演员创造角色的重要理论,其要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1.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角色之前,应该首先在自己心目中创造出角色的形象(焦菊隐称之为“心象”);2.进入舞台表演之后,演员应该化身于角色,完全消除演员的自我意识。这也就是用焦菊隐本人在《导演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说的:“先要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焦菊隐提出的这一方法经过当时北京人艺于是之等演员的实践,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而且对于北京人艺表演风格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研究渐趋深入,焦菊隐的“心象说”开始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论焦菊隐导演学派》(1985)、《探索的足迹》(1994)和《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1995)等研究专著中,有关“心象说”的讨论都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焦菊隐的“心象说”是他融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理论、哥格兰表现派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理论和艺术理论而创立的新学说,因此应该看作是焦菊隐整个戏剧理论中最具光彩,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不过依我之见,肯定焦菊隐“心象说”对于中国当代话剧表演理论的特殊贡献,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对焦菊隐“心象说”的认识和评价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有些重要问题尚未真正得到解决,譬如“心象说”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关系问题、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理论的关系问题等。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直接关系到对焦菊隐“心象说”本身的评价。本文的写作,即是就上述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并略申己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一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焦菊隐的“心象说”与斯氏体系的关系。换句话说,“心象说”作为一种表演理论,其性质究竟是属于:(1)表现派?(2)体验派?(3)抑或综合二者而创立的第三种流派?
可以马上回答的是焦菊隐并不属于表现派。关于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争议,但对于后两种选择,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看第三种选择。
焦菊隐有没有可能在综合表现派和体验派的基础上创立“心象说”?显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确实可以综合表现、体验两派而创立第三种流派;第二,焦菊隐本人曾经以某种方式进行过这种尝试,或肯定了进行这种综合的可能。然而我们知道,就实际存在的表演理论流派而言,不是偏于表现,就是偏于体验,真正综合二者,既非表现又非体验的表演流派,严格说来是不成立的。这恰如文艺创作方法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样,所谓两结合,实际上不过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另一种方法而已。反过来说,表现和体验虽然分为两派,却并非彼此绝对排斥,而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因此,综合表现与体验创立第三种流派,至多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很难真正落实为一种现实的存在。
事实上,焦菊隐曾明确表示:体验派与表现派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他说:“许多人以为斯氏体系只讲体验不讲体现,提出应该让体验派和表现派合流,各取其所长来发展表演艺术。这是以局部代替全体的极大误解!”这就是说,在焦菊隐看来,体验派之长并非仅仅是体验,同时还包括了体现,因为斯氏除了讲体验之外,还有专讲体现的部分,只是我们了解得不够而已。既然体验派自身并无所短,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取表现派之长。焦菊隐接着又说:“至于‘两派合流’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因为除了他们的‘误解’外,还包含着戏剧观、美学观、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根本性分歧。这不像两杯水倒在一起那么容易地合流,水乳可以交融,水油就不大能交融了。”(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过程》,《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我们姑且不论体验派、表现派是否互有短长,姑且不论焦菊隐这一看法是否完全正确,单就焦菊隐认为两派不能合流来说,可以肯定,他不会有意识地去折衷两派而创立“心象说”。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焦菊隐吸收了某些表现派的观点,进而认为“心象说”是对斯氏体系与哥格兰表现理论的一种不分轩轾的综合,那并不符合事实。应该看到,焦菊隐始终是以体验派为本位去评判、借鉴表现派主张的,而且始终没有将表现派视为堪与体验派对峙的另一重要表演理论流派。
而从焦菊隐本人有关“心象说”的全部论述及他对体验和表现两派的认识来看,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焦菊隐的“心象说”是建立在体验论基础上的表演理论。无论是焦菊隐对演员形成心象过程中体验生活的强调,还是排演场上乃至舞台上要求演员完全化身于角色,乃至他用以建构“心象说”理论基础,都充分表明了焦菊隐的立场之所在,表明了体验是贯穿于整个“心象说”的一条主线。尽管焦菊隐确实接受、借鉴了表现派的某些方法和主张,尽管焦菊隐后来对其前期的某些观点有所修正,但这种接受、借鉴并未逾越体验派的基本原则,其所做的修正也十分有限,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心象说”的体验派表演理论性质。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焦菊隐的“心象说”完全照搬斯氏体系,而只是想说明,“心象说”在本质上还是属于体验派的,它与斯氏体系的差异,应该看作是体验派内部的、具体方法层面上的差异。
二
在我看来,焦菊隐“心象说”与斯氏体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心象与内心视象。
对于焦菊隐所说“心象”是否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内心视象”,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心象”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内心视象”。如同是北京人艺导演的欧阳山尊在其文章中便说:“焦菊隐同志所说‘心象’和斯氏体系中的‘视象’应该说是一回事,只是说法或译法不同。”(注:欧阳山尊:《〈龙须沟〉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见《〈龙须沟〉的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423页。)而中央戏剧学院张仁里教授则认为:焦菊隐的“心象学说”和斯氏的“视象”论似而不同,“‘内心视象’在斯氏体系之中是作为演员内部技巧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出来的,它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也仅仅是演员内部技巧中的一个项目,是演员自我修养中需要锻炼的某种素质。而焦菊隐先生的‘心象学说’则是从体验人物生活起,到演员内心建立人物‘心象’,再一直到创造出活生生的舞台人物形象为止的整套的、全面的演员创造形象的方法”。(注:《论焦菊隐的“心象学说”》,见《探索的足迹》,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推测张仁里先生的意思,“心象”当不同于“内心视象”,可惜他未对这两个概念作具体的比较辨析,因此其结论便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心象”一词首见于焦菊隐对丹钦科回忆录的翻译,则其并非源自斯氏著作中的“内心视象”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焦菊隐在50年代初提出“心象说”时,他是否在斯氏“内心视象”的意义上来使用“心象”这个术语。换言之,“心象”是否可以理解为“内心视象”的简称或缩写,如欧阳山尊所说,二者的差别仅仅是一个说法或译法的问题。
从翻译的角度来辨析“心象”与“内心视象”的异同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因为焦菊隐并非直接译自俄文,而他所据之英译本在今天已很难找到,所以我们无法肯定焦菊隐选择译为“心象”是否受了英译者的影响,也难以将三种语言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俄文的“обраэ”(形象)与“внутреннее эрение”(内心视象)显然不能用同一个汉语词汇翻译,因此,说“心象”与“内心视象”只是译法不同并不正确。另外,焦菊隐在《导演的艺术创造》一文中曾表示,有人把“心象”译作“意象”。(注:《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焦菊隐所说有人将“心象”译成“意象”,很可能是指郑君里。在郑君里所著《角色的诞生》一书中曾部分摘引了丹钦科《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我们对于演员的要求,正是不要他‘表演’任何东西,断然不是一件‘东西’;也不是感觉,也不是心情,也不是剧情,也不是词句,也不是风格,也不是意象。”(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这里最后一句中的“意象”,在焦菊隐翻译的《文艺·生活·戏剧》中,便译作“心象”。又郑著第二章《演员如何准备角色》单有一节,介绍“意象与形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心象”的原文不可能译为“内心视象”,它只可能是“обраэ”而不会是“внутреннее эрение”。
再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内心视象”的解释。在《演员自我修养》第四章讨论“想象”时,斯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只要我一指定出幻想的题目,你们便开始用所谓内心视线看到相应的视觉形象了。这种形象在我们演员的行话里叫做内心视象。”(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从斯氏对“内心视象”的解释和具体使用来看,它实际上就是演员通过有意识的想象而获得的一种心理表象,就此而言,它与焦菊隐所说“心象”确实不无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具体内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斯氏“内心视象”所指颇为宽泛,一切进入演员想象(“内心视线”)的对象——人物、场景、音响都包括在内,正如斯氏文集的编者在该书注释中所说,斯氏“把我们对事物的一切形象的和感性的概念都称为视象”,因此除了视觉形象之外,还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其他“想象的感觉”。(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斯氏将“内心视象”比喻为在演员内心放映的连续不断的电影画面。而焦菊隐所说“心象”的内涵要具体得多,它专指角色在演员心中的感性呈现。
当然这还只是外在的差异,但这足以说明,“心象”与“内心视象”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内心视象”一词也出现在焦菊隐笔下,如他在讲解“形体动作”时写道:形体动作必须从一点一滴着手,“先通过‘假使’推动想象,对规定情境、事件、情节、人物建立起一个大致的内心视象;然后结合直接与间接生活经验的回忆,设想出每个单位的形体动作的轮廓”。(注:《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但这显然是在斯氏本来意义上使用的。这也表明焦菊隐有意赋予“心象”一词特特殊的含义,使其区别于斯氏的“内心视象”。
二、体验生活与规定情境。
如果我们的考察再深入一步便会发现,“心象”与“内心视象”的上述差异并非偶然,它们实际上根源于焦菊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人方法上的分歧。
无论是焦菊隐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主张演员创造角色必须由体验角色入手,但在如何进入体验这一点上,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简而言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是从“规定情境”入手,先想象出角色生活的具体环境,然后置身其中,运用“假使”去获得角色的内在感觉,或者说,由此进入对角色内心的体验。用斯氏的话说,“只要你用内心视线看到熟识的环境,你便感到这种环境的气氛,于是和动作地点有关的熟悉的思想立刻在你心里活跃起来了。从思想产生了情感和体验,接踵而来的就是内心的动作欲求”。他之所以把内心视象比喻为连续不断的电影画面,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连续的视象会构成一条“不断的线”,有助于形成演员的贯串动作。“这些视象在你心里造成相应的情绪。它会影响你的心灵,并激起相应的体验”。而“不断地去观看内心视象的影片,一方面可以把你约制在剧本生活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经常而正确地指引你的创作”。(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99、100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4卷《演员创造角色》第85-104页,斯氏对创造外部情境和内部情境的具体描述。)不难看出,在斯氏体系中,内心视象作为激发演员情感体验的触媒,其实质是要求演员在想象中进入规定情境,与角色感同身受。同时,内心视象既然是演员发挥想象的产物,它在演员创造角色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便次于想象,如果说想象是斯氏所要求于演员的内部心理技术之一,那么内心视象不过是对这一心理技术的具体应用。严格说来,内心视象只是舞台上实存的、外在的规定情境的一种补充,演员通过它来填充剧本和舞台所遗留的空白,从而构成完整的规定情境。
至于焦菊隐“心象说”的方法,则是要求演员在阅读、分析剧本和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先初步形成一个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心象”,由此进入对角色的体验。诚然,演员对角色的把握离不开角色生活的具体环境,而且演员同样必须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弥补剧本没有写出的部分,但当演员这样做的时候,他更多地是一种外在于角色的、理性的把握。焦菊隐要求演员深入体验生活,一方面是希望演员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了解形成角色性格特征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与角色性格相似的类型人物,从而为形成角色的心象奠定基础。换句话说,对角色生活环境的了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角色。这也就是焦菊隐布置演员写人物小传的主要用意。在演员准备角色阶段,焦菊隐并不急于让演员进入规定情境,而首先是让演员在现实的生活体验中增强对角色的认识,通过对角色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考察,了解角色性格形成的历史,使这种认识由初读剧本时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这样,演员就有可能在自己心中形成角色的雏形,就有可能对角色的思想、情感和穿戴长相乃至动作特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焦菊隐看来,这才是演员得以进入体验的前提。
三、从外到内与从内到外。
由上述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途径的不同。在斯氏体系中(特别是其前期),演员创造角色的途径基本上是从内到外的。这里说的“从内到外”,首先是指从角色的内心到形体,即演员在规定情境中去体验角色的内心,获得与角色相同的情感反应,形成内在的心理动机,然后借助相应的形体动作将此体验体现出来。与此相联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从自我出发”,假设“我”处在与角色同样的环境中——亦即剧本的规定情境中,那我会怎么做?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设想,经过体系整个心理技术训练出来的演员,一旦置身于规定情境之中,他就应该获得与角色同样的心理体验,进而自然形成相应的外部动作,由“假如我是”必然发展到“我就是”。这实际上是要求演员直接进入角色的内心,先“有动于衷”,然后再“形之于外”;或者说,先是体验,然后才是体现。
而焦菊隐“心象说”所要求的,则是“从外到内”的途径。具体些说,就是演员先从外形上去把握角色,获得对角色若干形体特征的认识;然后再通过不断模仿角色的这些形体特征,感受、体验角色如此行为的内在动机;最后内外合一,达到生活于角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外在的形体动作。如果说斯氏体验角色是“从自我出发”,那么焦菊隐要求于演员的则是从认识角色出发。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焦菊隐并不赞成演员直接模拟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即使这个人物的经历、性格,甚至形体特征都与角色非常相似。他也不指望演员在体验生活时便能形成角色的完整的心象,而只要求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或一两个较为鲜明的形体特征。因为在焦菊隐看来,心象只是演员据以进入体验的凭借,而不是演员据以表演的范本。正是这一点使“心象说”有别于表现派的主张,而更符合体验派的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焦菊隐对于斯氏的“形体行动方法”予以特殊的关注。焦菊隐认为,从形体动作入手,并不意味着否定内心体验,因为这只是“创造角色的起步点,但绝不是说单纯的形体动作就是创造的全部”。由于“形体动作激发起心理活动,心理活动又反过来支配形体动作”,因此准确的形体动作便可能“激发起内在的思想情感”,达到演员体验角色的目的。所以,焦菊隐将斯氏“形体动作方法”视为演员“从外到内”创造角色的重要手段。同时,焦菊隐把动作划分为“人类的动作”、“类型的动作”和“典型的动作”三类,而“某一角色特殊的性格化动作”(典型的动作)必须建立在前两类动作的基础之上。(注:《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127、135、134页。)这恰与他主张由类型到典型的方法相对应。
必须承认,对于斯氏所说演员创造角色的方法和具体步骤,焦菊隐是十分清楚的。他曾多次提到斯氏将演员创造角色划分为五个环节:1.演员内心产生人物内心世界的视象;2.演员内心产生人物外在面貌的视象;3.演员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4.演员用自己的形体去体现人物的外在行动;5.演员通过他所创造的人物外在行动,把内心体验传达给观众。(注:《焦菊隐文集》第4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类似的划分,还见于该书第33页、115页。)显然,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虽然这个划分不无焦菊隐自己理解的成分,但指出由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入手,却是符合斯氏基本精神的。
那么,焦菊隐为什么不完全按照斯氏的办法,而要提出“先有心象”、“体验生活”和“从外到内”等一系列主张呢?这就不能不追问焦菊隐当时所面临的中国话剧表演现实,特别是演员自身素质的问题。
就反对表演中的公式化、刻板化等形式主义倾向而言,焦菊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处境是一致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面对的演员不同。斯氏手下的演员大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形体表现方面。其中不少演员来自丹钦科领导的戏剧学校,对于如何进行体验已有一定的基础。正如焦菊隐所说:“丹钦科不但以一生的辛苦,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预备了一个安心实验的环境,而且还给他训练好了内心表演体系所需要的演员。”(注:《焦菊隐文集》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而焦菊隐则没有这样的条件,与之配合的演员基本上没受过专门的培训,对于如何体验往往不得其门而入。在这方面,于是之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我如果不熟悉生活,决不是假使一下、积极动作,这人就可以演活了。比如光靠假使,假使你是阿巴贡,这成吗?第一阿巴贡,第二莫里哀,第三法兰西等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就假设我,这样的假设没有资本啊!”“当叫我演一个我并不深知其生活的角色时,我曾经这么‘假设就是我’过,但都收效甚微。弥补的办法,不是那‘魔术般的假设’,而是去生活。”(注:《于是之论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66、91页。)的确如此,没有相关的生活积累,凭空假设,那是任何人都难以进行的,也是任何心理技术难以奏效的。焦菊隐之所以主张演员先培植一个角色的心象,提出“从外到内”的方法,就是为了解决演员这种对体验的困惑。
另外,斯氏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按部就班的训练教程,按斯氏的设想,至少需要两个学年的时间来完成。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一种基础训练对于培养演员的素质无疑是有益的,但对于新中国剧院的演员来说却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他们希望有一个简捷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而不必等到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之后再从事舞台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焦菊隐一再强调要发展斯氏体系,将斯氏体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的根本原因。而且,他之所以选择了与斯氏不尽相同的方法,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在《导演的艺术创造》中,焦菊隐特别谈到了如何认识斯氏体系的问题,他指出:斯氏表演理论“是一个体系,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片断的、孤立的、技巧上的方法”。“要实践这个科学的体系,在苏联就有适用于苏联演员条件的方法,在中国也就应当有适用于中国演员条件的方法”。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寻求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方法,把它在中国的土壤里培养、发展、壮大起来,而不能从苏联生硬地、教条地移植搬运到中国来”(注:《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2页。)
三
事实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注意到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焦菊隐所说“心象说”的方法。他曾在一篇手稿中写道:
大家知道,有些演员在想象中给自己创造出规定情境并使其达到尽致入微的程度。他们在内心里看到他们想象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一切。
但也有一种有创造性的演员,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身外的事物,不是环境和规定情境,而是处在相应的环境和规定情境中的他们所扮演的形象。他们在自己身外看到它,注视着它,同时在外表上抄袭这个想象出来的形象所做的动作。
还有一些演员,他们所创造的想象中的形象对他们说来已成他们的alterego。他们的孪生兄弟,他们的第二个“我”。它不停不休地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也不(与它)分离。演员经常注视着它,但不是为了要在外表上抄袭,而是因为处在它的魔力、权力之下,他这样或那样地动作,也是由于他跟那个在自己身外创造的形象过着同一的生活。
斯氏在这里谈到了演员创造角色可能有的三种方式。第一种通过演员的内心视觉看到规定情境即是斯氏本人的方法;第二种接近哥格兰所说的方法,演员内心看到的不是规定情境中的一切,而只是演员所要扮演的形象;第三种看似第二种,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第二种演员从外表上“抄袭”他在内心看到的角色形象,而第三种演员则是去体验那个想象中的形象(与之共同生活)。而且斯氏还表示:“如果说抄袭外部的、在自己身外创造的形象是一种单纯的模仿、模拟、表现,那么,演员与形象的共同的、相互而紧密联系着的生活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过程,是某些具备创造性的演员所固有的。”(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3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558页。这段文字并非见于该书正文,而是由编者附录在“性格化”一章的注释中的。)
显然,斯氏这里提到的第三种方法,与焦菊隐“心象说”的方法非常相似。它既吸收了哥格兰方法的某些因素,同时又将其纳入体验的范畴——演员在内心想象出角色的形象并不是要从外表上去模拟抄袭,而是为了使之成为演员的第二自我。
然而斯氏在正式写作《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及《演员创造角色》时并未收入这段文字。是因为斯氏对这种方法尚未考虑成熟?抑或觉得其与从规定情境入手的方法相比犹有不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斯氏对它持肯定态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焦菊隐恐怕没有看到过斯氏的这段话,如果看到的话,他很可能会把它作为自己提出“心象说”的重要依据。但就算焦菊隐确实看到过这段话并从中受到启发,仍不会降低“心象说”结合中国话剧演出实践,发展斯氏体系的重要价值。道理很简单,尽管斯氏对上述第三种方法持肯定态度,却没有纳入其体系,至多是把它视为演员创造角色方法的一种特例,而在焦菊隐,则是当作演员创造角色的基本手段。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年视为特例的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价值也逐渐为人所认识。1975年,前苏联史楚金戏剧学校(即原来的瓦赫坦戈夫剧院附属学校)教师、普希金剧院演员尤·安·斯特罗莫夫出版了《演员创作再体现的途径》一书,对演员创造角色的不同途径(方法)作了比较分析。斯特罗莫夫认为,传统的方法——“从自我出发”和“从形象出发”都犯有停留在各自出发点上的错误,而前一种方法的错误尤不易被人察觉。很多演员只强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从自我出发,借助于假使而进入规定情境,却忽略了这只是斯氏处理角色的第一个阶段。这种误解直接导致了让角色屈从于演员和舞台上缺乏形象性的弊病。因此,斯特罗莫夫用了较多的篇幅探讨第二种方法的意义,其中有些见解与焦菊隐“心象说”的观点颇为接近,如:
要知道,很可能形象的视觉心象不能代替形象,只能促进对它的理解,从而使演员做出相应的动作,该动作反过来又唤起体验。
因此,演员在研究角色时,对未来舞台形象的视觉与感觉方面的心象会使他建立起行动的逻辑。在再体现的创造过程中,心象对于不同的演员个性是有不同意义的。有些演员几乎不考虑自己创作的结果,而是尽可能深刻地沉入人物的行动逻辑之中,把自己置于他的地位;而对另一些演员,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未来的形象总是清楚而鲜明地出现在想象的视线前,仿佛成了他们创作中的灯塔。对于那些在舞台上难以按“我在规定情境之中”这一原则行动的演员,形象的视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角色的最初视象绝不能当作是最后的。这只是初步的线条。还有大量的工作呢。因此,不必担心最初的视象有时带有抽象的性质,处于司空见惯的、有时甚至是老生常谈的概念之中。出现这样的视象甚至是有益的。它使演员可能拒绝某些东西,改变某些东西。重要的是给予想象以动力。(注:尤·斯特罗莫夫:《演员创造再体现的途径》,姜丽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1页。)
不难看出,斯特罗莫夫的这些见解所表述的,正是焦菊隐“心象说”前一个环节——角色生活于演员的意义。如心象可以促进演员对角色的理解,由心象获得的角色外部动作有助于演员进入体验,以及初级心象可以带有理性色彩等等,都与焦菊隐所说相吻合。而且,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受焦菊隐影响,译者也将相应的词对译为“心象”。斯特罗莫夫特别提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第三种方法的意见,并把它作为结合“从自我出发”与“从形象出发”两种方法的理论依据。他根据尼·巴·赫梅辽夫和鲍·瓦·史楚金等苏联著名演员的创作体会,说明他们都是结合两种方法而进入斯氏所说的“独特的体验过程”,并由此认为:“实际上,最自然和最有效不过的途径是结合两者,综合使用,把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注:尤·斯特罗莫夫:《演员创造再体现的途径》,姜丽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斯特罗莫夫的这部著作是苏联文化部审定的戏剧院校教材,其影响、地位于此可见。书前有苏联戏剧界权威鲍·叶·查哈瓦的《序言》,称作者对两种途径——从自我到形象与从形象到自我,或者说从内到外与从外到内,都“作了充分而清晰的阐释”;对结合两者而构成的第三种途径也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查哈瓦认为,斯特罗莫夫的著作,“对戏剧学中直接回答今天的需求并积极促进戏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那一部分,作出了重大贡献”。(注:尤·斯特罗莫夫:《演员创造再体现的途径》,姜丽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而根据我们前面对“心象说”方法和理论内涵的分析,早在50年代初,焦菊隐就意识到单纯“从自我出发”、“从内到外”可能产生的弊端,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斯特罗莫夫的大部分观点,实际上不过是重复焦菊隐说过的话而已。尽管那时焦菊隐在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困惑,甚至偏颇,但他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斯氏体系。对比查哈瓦对斯特罗莫夫著作的评价,我们可以说,焦菊隐的“心象说”不仅是针对五十年代中国话剧表演中存在问题的救弊良方,而且也是对斯氏体系本身的一个突出贡献。可想而知,如果斯特罗莫夫读过焦菊隐有关“心象说”著述的话,那么他必引以为异域知音,对焦菊隐先于他二十多年就关注这个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建树而感到惊喜。如果其他当代苏联戏剧表演理论家肯放下老大哥的架子,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综合两种方法创立第三途径方面,中国同行比他们先行一步,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方面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前苏联剧协主席拉甫洛夫在看了《茶馆》演出之后表示:“如果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有所发展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茶馆》中的精彩表演。”(注:转引自童道明《心象说》,见《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拉甫洛夫从《茶馆》的表演中看到了中国同行对斯氏体系的发展,而我们知道,《茶馆》在表演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心象说”的指导。
四
讨论过焦菊隐“心象说”和斯氏体系的关系之后,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即焦菊隐在建构“心象说”理论时,是否有意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理论,或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某些成分?是否受到二者的启发?
先看“心象说”与传统戏曲表演理论的关系。
我们知道,焦菊隐很早就对戏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由于他当时对戏曲所持的态度,因此他并不赞成将戏曲表演方式引入话剧。那么,在50年代提出“心象说”理论时,焦菊隐是否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呢?
恐怕首先应明确两点:1.在焦菊隐的话剧导演实践中,“心象说”的提出和话剧借鉴戏曲表演方式分属于两个时期;2.在50年代以前,对于话剧和戏曲各自的表演方式,焦菊隐倾向于看作是两种不同的表演体制。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基于事实作出的判断,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承认,当焦菊隐在50年代初提出“心象说”时,他尚未有意识地去借鉴传统戏曲的表演理论,尚未将戏曲表演因素纳入其方法。所以,对于焦菊隐的中国戏曲文化背景,我们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说实在的,焦菊隐“心象说”理论价值的大小,其对中国现代话剧表演理论的贡献,主要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接受了传统戏曲表演理论,而是它作为演员创造角色的一般方法所产生的实际效验,以及它对斯氏体系的发展与改造。
事实上,从焦菊隐有关“心象说”的全部论述中,我们很难找到他有意识借鉴或吸收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理论的证据,譬如说,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理论的引述,或戏曲演员的演出实例。而没有必要的证据,凭想象认定焦菊隐“心象说”借鉴戏曲表演理论,那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相反,从“心象说”的基本理论倾向来看,它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恰恰与传统戏曲表演理论相抵触。
例如关于演员与角色的关系问题,“心象说”和戏曲表演理论就有较大的出入。按照“心象说”的要求,演员应该尽可能化身于角色,消除表演意识,在舞台上活动的只能是角色的自我。而在戏曲表演中,却强调演员应该始终不忘自己的演员身分,既要能入,更要能出。戏曲表演界有一条流传甚广的口诀,叫做“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求演员“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另一方面又要求“像龙非龙,像虎非虎”。换句话说,戏曲表演中演员和角色的关系应该处在“似与不似”之间。
又如戏曲表演中程式化手法的应用,也和“心象说”的主张相悖。如前所述,反对话剧演出的程式化是焦菊隐提出“心象说”的目的之一,尽管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焦菊隐也反对戏曲的程式化,但应该看到,戏曲中程式基本上是一种预先设计的、非即兴表演的产物,这就和“心象说”的宗旨不符。焦菊隐所要求的,是演员通过对角色内心的体验自然产生外部的形体动作;而戏曲表演则是根据角色的性格特征去选择相应的程式,并在舞台上精确地表现出来。更何况程式自身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定和沿袭已久的惯例,演员虽然可以灵活应用甚至加以改造,却不能完全代之以生活化的动作。
诸如此类,都是中国戏曲表演所独有的特征,因此要讲吸收借鉴戏曲表演,恐怕主要应该是这些不同于斯氏体系之处。至于戏曲表演同样要求演员体验角色,要求在体验的基础上创造,那只能说是戏剧表演的基本要求,共同规律,而不是构成戏剧表演理论之中国特色的主要因素。
依我之见,与其说焦菊隐的“心象说”借鉴了传统戏曲表演理论,不如说焦菊隐后来在话剧表演上吸引了戏曲表演的若干因素。所以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从提出“心象说”到从事话剧民族化探索分属于焦菊隐戏剧思想发展的两个时期,而且还因为“心象说”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主要在于演员创造角色,或者说在于舞台演出前阶段。从表演理论的构成来说,演员创造角色虽然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但毕竟不是整个表演理论。同样,“心象说”固然是焦菊隐表演理论的核心,却不能等同于这个理论的全部。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心象说”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
五
再看“心象说”与中国艺术理论的关系。
应该说,将焦菊隐的“心象说”与中国艺术理论联系起来,始于于是之对“心象说”的领悟。而且不止于此,在某种意义上,焦菊隐“心象说”所以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和于是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于是之不仅作为“心象说”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以其成功证明了“心象”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且在80年代以后多次著文,结合自己的体会、经验对“心象说”进行总结、补充,从而扩大了焦菊隐“心象说”的影响。关于焦菊隐和于是之的关系,我另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人们在研究“心象说”时,往往把焦菊隐和于是之理解为一种理论与实践互为印证的关系,关注的是两人相同相合之处。确实,如果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原属必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看法上,于是之,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于是之与焦菊隐不尽相同。他在接受焦菊隐“心象说”的同时,还有所矫正,有所发展。既然我们讨论的是焦菊隐的“心象说”,而非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表演理论,那么我们便不能满足于一概而论,而必须有所区分。
在60年代初写作的《演员创造中的“我”和“他”》一文中,于是之提到了唐人符载的《观张员外副松石序》,认为其中所说张璪作画时“物在灵府,不在耳目”,与演员创造角色须有心象的道理相似;而在80年AI写作作的《焦菊隐先生的“心象”学说》中,于是之又引述清人郑板桥题画竹一段文字,说明“心象”恰如郑板桥所说“胸中之竹”,是一个主客观的统一。(注:《于是之论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3页。)正是于是之的上述见解,使有些研究者开始将焦菊隐的“心象说”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联系起来,进而认为焦菊隐选择“心象”这一词汇,“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我国民族美学的传统精神”。(注:参见《论焦菊隐导演学派》,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然而,类似的联系在焦菊隐的著述中却颇为鲜见。不错,他曾以齐白石画的茄子为例,说明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因此演员的表演应该是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注:《谈话剧接受民族传统的几个问题》,《焦菊隐文集》第4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但这已是60年代的事,而且主要是就舞台表演而言。
如果着眼于焦菊隐本人的有关论述,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焦菊隐在研习斯氏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而提出“心象说”。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文学家,一个熟悉文学史、戏剧史的文艺批评家,焦菊隐当然知道,在想象中把握表现对象并通过某种物质手段传达出来,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心象”并非只是演员的专利,其他艺术创作同样需要获得“心象”,只不过在别的艺术中,将“心象”转化为“形象”所需的媒介各有不同罢了。所以焦菊隐在谈到剧作家创作时说:“作家首先要在自己的内心视象中清楚地看见他的人物在什么环境里在想什么、做什么,然后再用概括的语言写成台词。”(注:《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4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剧作家的创作是这样,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也与此有相通之处。或许可以说,焦菊隐正是凭借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修养,部分地弥补了缺乏表演实践的不足,从而在表演理论领域也有所建树。而且,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心象说”的价值更在于演员创造角色阶段,而其失误多在舞台演出。
这也许不是偶然,在郑君里《角色的诞生》和斯特罗莫夫的《演员创造再体现的途径》这两部书中,都特别谈到了作家、艺术家对其创作“心象”的把握。譬如郑君里写道:“其实这一种创造的意象(即焦菊隐所说之“心象”)并不是演员所专擅,而为一切艺术家在着手创造之前所共有的。唐代王维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中国画家一向讲究‘竟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假使竹树的意象不是在苏轼的心版上长得那么葱茏,怎么能够在他一挥手之间便郁苍地从他笔底茁发,在水墨下生了根?假使巴山蜀水不是久已在吴道子的心胸中起伏奔腾,他怎能够在朝堂之间即席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假使歌德的迷娘的意象不是有机地再生于贝多芬的心坎中,那么后者怎么会自认‘这感受的印象刺激心灵去产生新作’,而写下了那不朽的《迷娘曲》的音乐?”(注:郑君里:《角色的诞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新版,第58-59页。)而斯特罗莫夫则认为:“对周围世界和人的性格的鲜明的心象,是任何艺术创作的前提。”他还引述了屠格涅夫、歌德、普希金等作家和俄国作曲家亚·季·格列恰尼诺夫的创作体会,进一步证明:“不仅演员,许多作家、作曲家和美术家,也是从自己主人公的视象和视觉心象中汲取创作的动力。”(注:斯特罗莫夫:《演员创造再体现的途径》,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9页。)
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这两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心象之于演员创造角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焦菊隐创立“心象说”的背景,较之笼统地讲法兰西和中国戏曲理论背景,恐怕更接近事实,也更具有说服力。
标签:焦菊隐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