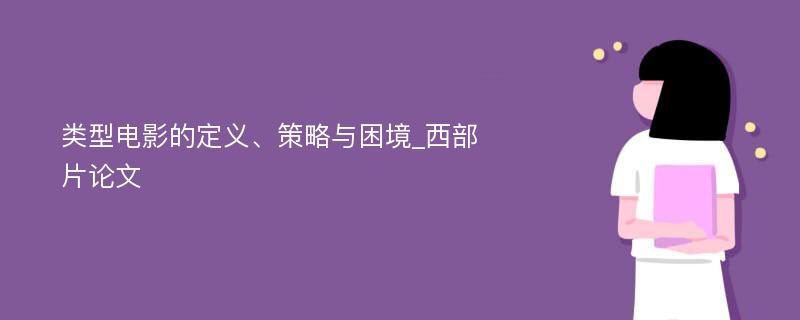
类型影片的定义、策略及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定义论文,影片论文,策略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类型通常指分类的方法,而类型片就是指那些根据分类原则给以不同命名的易于分类识别的影片。可以说,好莱坞电影是一种类型电影,尽管影都好莱坞的声名是以那些具有独特风格与美学倾向的影片、导演与演员而获此殊荣的,比如像格里菲斯、约翰·福特、奥森·威尔斯等等,但人们依然可以争辩说:他们的作品难道不是类型片的经典之作吗?因此,也有人据此得出结论:所有的影片都是类型片,影片只有在类型中才能被解读。而更为现实的是,在电影市场上,类型片是为预期的消费者提供一种选择的方式。可见在类型片研究中面临着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人们所依据的是何种分类原则?市场的还是美学的?文学的还是电影的?语言的还是影像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则是,类型思维本身是否可靠?
一、类型电影定义的困境
实际上,当“类型”成为一个可以不假思索、信口拈来的名词时,人们同时开始质疑“类型”一词的含混与多义,而“类型片”更是一个几乎被用烂了的,但又复杂矛盾、歧义丛生的概念。几乎所有关于类型片的重要论述都看到了类型片所存在的这种含混与歧义现象,都指出了类型片定义与影片实践所存在的差异问题:理查德·麦特白在论述到类型问题时,引用了博尔赫斯假借弗朗茨·库恩写作中国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的那个著名比喻:“在那些久远的书页上写有动物的分类:(a)属于皇帝的;(b)涂过香油的;(c)驯服的;(d)未断奶的猪;(e)美人鱼;(f)巨大的;(g)迷途的狗;(h)包含在这个分类法中的;(i)颤栗仿佛发疯的;(j)不可数的;(k)用非常精细的骆驼毛梳理过的;(1)其他;(m)刚刚打碎了花瓶的;(n)从远处看像苍蝇的。”① 博尔赫斯的原义显然指的是东西方人的不同思维方式,而借此质疑西方思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尽管麦特白忽略了这段文字的要义,但他还是在概念层面上解释这种混乱:“观众、制片人和批评家在讨论电影的时候都在用类型的概念,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使用这些概念的含义可能大不相同。”② 为了解决这种混乱,他提出了“联合类型”的概念:“大部分电影使用的类型元素是交织合并的。”③ 同时又借用安德鲁·都铎的话重申,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④
大卫·波德维尔和克莉丝汀·汤普生指出:“让人困惑的问题在于给类型片下一个定义。究竟是什么使得一组影片成为一种类型片呢?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没有一种简单而确切的方式可以用来定义类型片。”⑤ 有的从情节,有的从叙事方法,有的则从观众的特殊情绪效用出发,“显然没有在逻辑上严谨的特征可以将所有类型片的诸多要素都包括进来”。⑥
而莎拉·培理-费林特则不无悲伤地指出:“现在的类型片定义已经变得相当混乱了,‘叙事电影、经验的和先锋的电影,以及纪录片’都混杂在一起,相继集中在更为普遍的种类上。……同样的结果是,也将纪录片和虚构故事的叙事电影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了。这些及时反映当前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影片与电视片一样,既是社会制度的,也是政治的,这些影片建立在观众的再定义上,它们是将观众作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来对待的。”⑦
安东尼·伊斯欧普吸收了托多罗夫的观点,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划分难题,建议将一个特定类型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理论的、临时的结构,其结构本身又是不停地被一个新产品置换着,“对任何一个特定类型的研究,首先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可变动的模式”。⑧
爱·布斯康布认为电影研究所讨论的对象是一种视觉手段,因此他认为类型分类的标准是一系列“外部形式”,由于这些外部形式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它所内涵的主题有其确定性。但他更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的类型特征,如《卡萨布兰卡》;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影片的“外部形式”所包涵的象征意义则是反其道而用之的,为此,他提出了“反用这些惯例”的手法,比如美国导演佩金巴的影片《午后枪声》。⑨
针对这种类型变异现象,有研究者以“反类型”的概念来特指那些“颠覆和背叛了原来归类”的例子,⑩ 并进一步讨论了类型电影的“越界”和“移植”的现象,由此认为“电影类型的游动移植,可以运用本地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来讨论,本来是十分本地化的电影类型被移植后,也许会变成一个全球化的新类型”。(11)
从上述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意见都指出了类型电影定义与电影意义之间的矛盾,都极力在寻找一些更贴切的条件来确认类型的边界,但几乎没有人质疑“类型”本身是否成立;都力求在逻各斯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而没有人质疑这个逻各斯本身是否成立。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在《电影Ⅰ:运动—影像》中有一段极为耐人寻味的话:“使美国电影拥有优势的就是它生来没有令人窒息的传统加以限制,然而这个特点却在这时候破坏了它的优势,因为动作—影像的电影自己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传统使得它今后的发展常会朝向负面的解放,而这电影的几大类型,诸如社会心理剧、黑色电影、西部片及美国喜剧等等皆自毁殆尽,只剩下一个空壳子。”(12) 德勒兹这个“空壳子”的意见非常值得重视,他实际上跨出了狭义的“类型”概念,而回到了思维领域,重新审视电影所特有的现象。德勒兹在电影影像中看到了人类认知与思维的新路径与新命题,他说他谈的是哲学问题,不是电影问题,但他却给电影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考。
也有国内的研究专家将新好莱坞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继承和变革的转折点,如郝建先生在《影视类型学》一书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三种形态:超类型、反类型、混合类型。他认为:“新好莱坞之后,在类型电影的王国中,一切都还存在着,可一切都变了样了。”(13) 在该书最后,作者单列一章来讨论后现代电影的风格与特征,特别强调了那种杂糅、游戏、模糊、暧昧以及风格混用的效果,将它们看做是后现代电影特征。但有意思的是,行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后现代电影是一个独立的类型,还是一个类型的集合体,甚至回避了对后现代电影与类型电影之间关系的讨论,但该章的标题却是:“后现代状态下的类型电影”。(14) 因此不禁使人联想,该书作者与德勒兹似乎达成了不谋而合的共识,借助这种有名无实的处理方法,却使我们看到了“类型”是如何成为了一个“空壳子”的。
二、“类型影片”是如何“空壳化”的
确认不同类型就是确认差别,当各种“类型片”的概括性定义成为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时,实际上已经承认,影片间这种界限已经消亡或融化。为了寻找与确认新的差别,人们不断地提出新的类型定义来规范这些差别,于是又会有新的空壳化的类型片种产生出来。其结果是,这种空壳化的现象就成为一种常态。
如果我们将这种空壳化看做是“类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结果,是一种历时态的话,实际上肯定了该类型的定义在当初命名时是具有涵盖性的,这些所谓的超类型、反类型、混合类型的元素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每部影片本身固有的、内生的。但我们是否考虑过,当我们命名一个电影类型时,比如西部片,你是否已经确认构成这一定义的元素是决定性的、主导性的?而其他被排斥的元素是从属性的,是被忽略了的?而如果从另一角度重新来认定这些被忽略了的元素,难道不就是一种超类型、反类型、混合类型?为什么不能承认,确实存在不断增长着、积累着的元素,同时还有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些元素的可能性呢?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类型”空壳化的多种可能性,从而使我们重新审视“类型电影”定义是在哪里发生问题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03年埃德温·波特拍摄的《火车大劫案》。很久以来,这部影片一直被人认为是电影史上的第一部西部片。(15) 西部片一直被认为是最具美国特色的电影类型,也是美国类型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型。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当时的报章杂志、广告海报上,《火车大劫案》是被归入当时流行的“追逐片”、“凶杀片”或“铁路片”一类的,这个时候没有“西部片”这一说法,“西部片”这一术语的命名还是1907年以后的事。可见,一个类型的确定有大的不确定性与变动性。早期电影的镜头运用通常是采用全景拍摄的手法,《火车大劫案》基本上也是这样,绝大多数场景是全景,但在结尾部分突然出现了一个近景:一个强盗正对摄影机镜头开了一枪,引起了观众惊恐万分,纷纷夺路而逃,一时成为了一个轰动事件。这个近景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全景与近景的景别变化又会对影片的意义产生哪些微妙的影响呢?更有意思的是,按《爱迪生目录》一书的说法:“这个画面可以放在影片的开始,也可以放在结尾。”当然,也可以将它放在影片的中间部分,也就是说,每个段落位置的设定也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灵活度,而段落或镜头在影片中的位置变动将会产生很大的意义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效果。我们看到,正是由于镜头和景别的变化,使一部影片的意义发生了变异,斯坦利·梭罗门将这一段落镜头的变化看做是真正电影化的一个转折:“在他以前的人仅限于思考摄影技术的潜力,而没有一个人曾经把真正的电影概念付诸实践。鲍特不再用摄影机来摄制表现文学观念的影片,而是用摄影机表现电影观念的影片。”(16) 可见,在电影类型的确认中,我们面临着三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所讨论的对象是电影,而不是文学;镜头、景别、构图、光影这些影像元素是不断变动着的;类型的界定甚至是随机的,并不具有神圣性。
类型理论原本是一种文学思想,初期的文学分类着重体现在题材、体裁、表现形态、情感接受上,到了18世纪之后,随着理性主义思想的不断强化,文学类型逐渐成为艺术表达、模仿、接受、定义的最理想的形式,并成为了学术领域内的确定性原则,这种文学规范化现象在19世纪欧洲成为浪漫主义运动首先力图突破的对象。到了19世纪晚期,即电影出现的那个时期,类型文学已经成为地摊文学的主流,而它与大众出版市场的紧密结合使它成了一个“任何一个作者型艺术家必须与之斗争的污辱名誉的系统”。(17) 在中国,这种类型禁锢到了20世纪初也被“新文学运动”抛弃了。但这种被文学抛弃的类型思想却很快被好莱坞制片商接受,成为大力推进电影市场化的最有力的助推器。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类型影片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过电影批评家与研究者的视野之内。这种局面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改观,到了六七十年代,类型影片研究才真正得到重视。
最早对类型片进行理论层面研究的是巴赞,这位现代电影理论的开创者在对美国西部片研究后指出:“西部片的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青春的活力,它必定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奥秘:永恒性的奥秘。揭示这个奥秘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提示出电影的本性。”(18) 他反对“把西部片的本质归结为任何一项表面元素”,他认为:“我们通常是按照这些形式特征确认西部片的,其实,它们只是西部片的深层实际的符号或象征,西部片的深层实际就是神话。”(19) 而所谓神话,“实质上,第一个神话只是通过特定的戏剧性程式,具体阐明伟大的、史诗般的、抑恶扬善的摩尼教义”。(20) 因而,西部片所追求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具有确定性、永恒性和神圣性。
一种更为机智的理论是托马斯·沙兹提出的,他巧妙地将“二战”后在法国兴起的“作者论”思想引用到美国类型批评上:“我们注意到在美国电影中受到最高褒奖的必然是类型片导演——亦即主要在一两个主导叙事形式范围内进行工作的那些导演。”(21) 他在这里推崇作者个人的类型,暗示了类型是由作者个人创造的,从而将原本对立的两种批评理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他依然将类型归结为“神话”,并且是一种“大众神话”。他引用罗兰·巴特的话说:“神话的功能就是把历史转换为自然,亦即,把复杂的社会问题聚合成概念系统,从而使它们成为常识性的。”(22) 这种神话通过电影的仪式化形态表现出来。
英国人爱·布斯康布则明确反对一切东西概由作者个人负责的“作者论”,他认为“一些非常成功的影片得力于某一类型的传统,而不是什么导演的独特贡献”,(23) 他认为电影分类的标准首先是作用于视觉的造型元素,即“像型图谱”是主要的,情节是次要的,因此,电影类型的定义是“一个外部形式构成,其中包含着一系列作用于视觉的惯例”,(24) 他明确表示,类型研究就是研究它们的外部形式。其中最为激进的是劳伦斯·爱洛韦,1969年他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个犯罪片影片展的说明书上写道:我们所计划的电影批评就是为大多数观众乐于观看的那种电影写作的,而主流电影批评却是为业已退化的少数人而写作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对流行电影的描述,它们将那些“场景和反复出现的东西看得比单个的实体更重要”,(25) 可见,在他看来所谓类型片的定义就是那些“场景和反复出现的东西”,因此,就如沃尔肖所认为的“模式就是一切”。(26)
同沙兹的社会仪式化理论一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理论脱离了影像研究而转向外部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反映论”,他们将电影看作某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的媒介,但这种观点仍然将批评建立在文本决定论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情节剧与黑色片作为主要类型片,仍然以表达意识形态传统为叙事策略,但这种策略在现代性的对话中,逐渐“从‘传统的神圣性(教会)和它的核心制度(君主制度)’转向民主社会的纯粹道德的与个人的观念,以一种新的‘神圣性’……成为后神圣时代发现、展示、表达基本道德世界的主要方式”。(27)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无论其结论如何、方法怎样,是概括性的还是描述性的,是寻求图像的程式化,还是确认某一类型的演变,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是神话的还是社会的,其共同点都是为了找到或求出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稳定的文本模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已经普遍注意到类型影片的易变性,但都没有怀疑“类型”这一概念本身的可靠性,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稳定的、以统一性为原则的宏大叙事之上的,其终结点则是为了求证一个抽象的真理。所谓定义类型,就是提取诸多类似影片的共同性。这是一种寻找概念“在场”的过程,从一部或多部影片中抽取对象的形式、观念的意义,将原本并不在场的东西转移到“在场”,并以这种形式或意义作为影片的“中心”来界定影片的分类、归属,而作为影片存在物的影像则转换为杂乱的假象、干扰“中心意义”的外表,被舍弃、排斥、否定、忽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影片的能指成了附属物,而飘忽、丛生的所指则被固化下来,获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甚至被“神圣化”,成为对影片分类、归并的原则、标准。尼采说:“‘个体’和‘类’的概念统统是错误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类’只表示同时出现的一群相似的人,其发展和演变为时很长,且进展缓慢,以致很难发现细微的进展和生长。……形式、类、法则、观念——到处都在重复同一个错误,都把错误的现实转嫁到虚构的头上。就好像一切现象都含有驯服精神一样。”(28) 显然,所谓“形式、类、法则、观念”原本是缺席的,它们的“在场”是虚构的,类概念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在场”将现实存在固定下来,而最后固定的其实是假象,是虚构的“形式、类、法则、观念”。所以尼采说:“人们不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一个同等状况的世界)等的必需,理解为似乎这样我们就真能固定真实的世界;而应当认为是这样一种必需,即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我们要就此创造一个对我们说来是可以测度的、简化的、可理解等等的世界。”(29) 显然,在类型电影中,类概念的“在场”将电影影像存在虚构化,影像最后以类的形象出场,电影审美的感性力被抽干了,影像成为一个干瘪的空壳。
三、类型空壳化与影像本位
类型空壳化的失误有其认识论上的必然性,类型思维将概念虚构为实体,成为“在场”,而将影像退化为幻象,反而“缺席”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影像本位与视觉本位。类型理论并没有怀疑从影像出发的研究方式,但他们的影像联系方式同好莱坞策略所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将影像本位与视觉本位看做是同一体,以致将影像与观众混为一体,将指涉物与被指涉物混为一体,影像失去了独立性。这就是以理性主义中心论为核心,将影像研究滑入到视觉本位的表征研究,而“表征研究必须考虑到文化现象、哲学视角和意识形态规划的广泛的多样性”,(30) 在以视觉本位取代影像本位的情况下,那些“其他的指示系统”的方法,如文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方法将会取代影像的方法成为电影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就是上述引文中德勒兹提到的“运动—影像”传统,是造成类型电影空壳化的直接的内在原因。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类型电影与观众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为预期的消费者提供一种选择的方式。可以说,类型电影的生产、推广、宣传、研究是好莱坞的一项策略,是好莱坞机制借助理性主义中心论的产物。当作为晚期资本主义产物的后现代思潮瓦解了理性主义中心论之后,类型电影也同时瓦解了,因此,好莱坞的后现代电影根本不是类型电影,好莱坞决定了类型电影的“看”的方式。
德勒兹将影像看做是思维对象,强调影像本位,就是确定影像居先,确定影像的时空联系的,使影像同思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直接的联系,从而确定直观感觉为“看”的方式。(31)
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到站》,“站台”是一个空间概念,但这个单镜头作品其实是一种时间表述,它所表现的是人在某个特定场所的存在状态。在同一个空间里以不间断的方式表现了火车的运动、上下火车乘客、站台上来回走动的人群的随机性,他们是变动的、多向度的。而7年后埃德温·波特的《一个消防队员的生活》,出现了一组剪辑而成的影像,其中一个影像中出现了“救火会”前的门铃,门铃下出现一张“有火警请拉铃”的告示,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是一只拉铃的手,再接下来是消防队员寝室……镜头间出现了意义传递,这就是电影叙事的雏形。在这里,影像组接的根据是空间,上面提到的《火车大劫案》中匪徒开枪的独立镜头也是一种空间组接。这是一种瞬间影像,即运动的固定切面。从这些最简单的早期镜头中我们发现,一个单镜头所展示的影像作为一个独立能指包含着无数潜在的所指,叙事在选取组接镜头时,总是一种空间选择,而同时也决定了其所指,这种组接的过程就是删除、归并、命名所指的过程。在这类镜头中,时间表现为抽象时间,是被边缘化的。早期类型电影出现了大量这一类影片,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叙事技术的发明集中在“视线吻合”上,如连续剪辑、平等剪辑、逆向剪辑、特写镜头、景别变化、正反打、中轴线等,其思路都是以视线在空间的平滑流畅的转接为轴心变化;另一方面,好莱坞商业机制决定了类型电影必须以故事为核心,以情节的因果链吻合为核心来展开。这样,情节线索的单一、清晰与紧凑决定了镜头、影像的选择必定是排他的,必定是以空间为中心展开的。在这过程中,时间被削弱了,“‘固定切面+抽象时间’所投射的是一种闭锁性,其中所有组成部分就是固定切面以及在抽象时间中被计算着的接续状态”。(32) 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好莱坞“运动—影像”电影的传统,但德勒兹又指出,好莱坞传统中还包含着另一种传统,即不断突破传统、走向其反面的传统,“运动—影像”同时还内生着一种“时间—影像”的生长力,时间的多义性不断地使影片回归到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表现,首先形成这种冲击力的是奥森·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它通过5个凯恩生前盟友的不同视角,从不同角度叙述了一个多元的人物,用这种扇面的记叙方式取代了直线因果式的叙事方式,在空间流动的同时,时间也成为了实在的存在。
德勒兹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出现看做是这种转变的最后完成。在新现实主义影片中场景与情节常常表现为随意的片断、瞬间、零散、失败、偶然的相遇,德勒兹以《温别尔托·D》中女仆在厨房里无意识走动的著名段落为例指出,由于这种时间性的被肯定,新现实主义以后的影片看上去是随意的、片断的,有的场景是“假”的,有的冲突的形成甚至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是真实的;而好莱坞的类型影片,场景与冲突都是真实可信的,但却是虚假的。显然,类型影片是一种追求意义的深度模式的思维方式,它建立在传统的抽象理性思维基础上,试图越过影像画面的能指符码,寻求在其底下的固定的所指。而新现实主义以后的电影突破了单向的时间性与事件的直线因果联系的虚假陈述,将电影看作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类型电影的“空壳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突显出来的,后现代电影的强调图像感受性优于语词感受性,突出多元混杂,取代抽象意义,都表现为类型电影的瓦解与溃散,因此将后现代电影划入新的类型电影,是将已经被解放的电影影像重新关入词语的牢笼。而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提倡“新感受力”不仅是对类型电影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影像本位的真正回归。(33)
注释:
① 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吴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②③④ 同上书,第69页。
⑤ 大卫·波德维尔、克莉丝汀·汤普生:《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⑥ 大卫·波德维尔、克莉丝汀·汤普生:《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⑦ Toby Mill/Robert Stam,Flim Theor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UK,2004,P40.
⑧ Pam Cook/Mieke Bernunk,The Cinema Book,British Film Institute,London,1999,P138.
⑨ 爱·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闻谷译,载《世界电影》,1984年第6期。
⑩ 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1) 同上书,第24页。
(12) 吉尔·德勒兹:《电影Ⅰ:运动—影像》,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第342页。
(13) 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8页。
(14) 参见郝建:《影视类型学》,第十八章。
(15) 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第27页。
(16) 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17) Toby Mill/Robert Stam,Flim Theor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UK,2004,P25.
(18) 安·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19) 同上书,第232页。
(20) 同上书,第237页。
(21) 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22) 同上书,第10页。
(23)(24) 爱·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邵牧君译,载《世界电影》,1984年第6期。
(25) Toby Mill/Robert Stam,Flim Theor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UK,2004,P25.
(26) 同上书,第30页。
(27) 同上书,第37页。
(28) 尼采:《权力意志》,载吴晓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9) 同上书,第238页。
(30)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31) 参见拙作:《电影研究中的影像本位问题》,载《社会科学》(上海),2007年第6期。
(32) 吉尔·德勒兹:《电影Ⅰ:运动—影像》,第38页。
(33) 参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