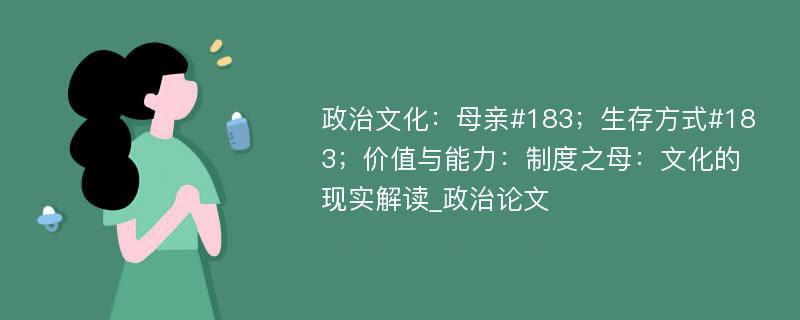
政治文化:母体#183;存在方式#183;价值与能力——兼对“体制之母”:文化的现实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母体论文,之母论文,体制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回原:“文化为体制之母”的现实解读
长期以来,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偏差。一是政治文化建设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各种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和政治教育与宣传的捣鼓;二是将政治文化建设等同现实政治文化的完全重建。当前重构市场经济下政治文化目标的提出,同样地至少在理论认识上仍存在着这种看法。立足于经济建设成就和繁荣的社会发展基础上,政治文化建设似乎是一项崭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一个崭新的平台上重新筹划。笔者认为,政治文化建设目标从来就是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的核心目标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从未忽略过政治文化在全局工作中的分量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但在实践的理解上,政治文化的割裂并非偶然,这不仅指传承着的传统,而且指各种政治文化资源。认为当代政治文化是市场基础上的完全重建过程。对此,有必要从理论到实践廓清一些基本问题。在此主要讨论这两种认识偏差中的后一个问题:政治文化建设不等同于政治文化完全重建以及两者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因此这里对“文化为体制之母”做一解读,对于回原到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上理解当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似乎更有其必要性。
“文化为体制之母”系喀麦隆著名思想家伊彤加·曼格尔勒·丹尼尔(Daniel Etonuga Manguelle)首先提出的,他本人是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的创办人和会长,曾任世界银行非洲委员会委员,他主持的协会参与了非洲西部、中部和南部的50多个项目的开发,因此发表于1998年的《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的报告就具有现实的说服力。该报告以数据为依据在分析了非洲触目惊心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与变革计划:“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存非洲文化,这一现存的最富人情味的文化之一。但是它必须得到新生,要从它内部发动这一过程,让非洲人既保持为非洲人,而又同时跟上时代。……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文化为体制之母’。较有效和公正的非洲体制有赖于我们文化的变革”。[1]在这里,他似乎论述的是文化与政治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只要对他全面论述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就不能不承认他实际上提出了“文化母体”这一根源和内核问题。首先,文化是内生的、不可割裂的血缘和生命联系,这是民族生命的源泉和根本;其次,文化的变革是最深层的变革,只有触动文化这一神经,才能实现全局的摧枯拉朽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他的个体发现,只不过他论述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情况有类比的可能,笔者愿意引入这一论述展开讨论并就教于方家同仁。
就笔者的理解来看,“文化母体”的设定建立在如下的基本假设与思考上:一是文化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二是文化是一种对价值意义追问的能力——文化力,是一种情感关爱;三是只有文化才堪为跨越时空和一切人为因素的成功和有效的连接链扣和交流平台。即能“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的观念和准则。”[2]回到政治文化的概念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政治生活方式与政治行为模式,是一种对政治目标与价值意义的迫问能力——政治文化力,是一种政治情怀;同时只有政治文化才能够跨越一切政治心理和政治时空界限而搭建成功有效的交流平台。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公民政治行为方式、政治目标与价值的总和。从现时我国的政治文化建构问题来考量,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文化模式、能力与价值是彻底“重建”,还是回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母体的本原上来培养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培养大众的政治情感,同时为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出公民民主交流的政治平台。
二、政治文化:实在的政治行为方式
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行为模式,“文化”从来都不是架空和虚无的。但在整个20世纪,对文化所作的各种定义都倾向于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视为纯粹文化的形式,即人类的行为就是“文化的行为”,而文化的行为就只有模式和形态上的差异而没有行为能力和价值目标的差异。这里谈的行为目标和价值是指人类的文化行为就是指为了提升人本身的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所作的一切努力。政治文化行为和模式的能力目标与价值就是提升民众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综观20世纪,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果就是展示人对物质的改良和对民主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把政治文化仅仅视为精神产品和上层建筑的附属品,显然是狭隘和不合理的。在当今,文化作为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无疑也使政治文化显示出“物化”的趋势(如西方强势政治文化意识的输出)。那么,有助于本文讨论的是,政治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我们习惯上所认同的是民主精神层面的“提升”与“美化”了。既然它是人们政治行为方式和目标的总和,那么,它就有可能和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建构能力——自始至终就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标,更直接地说,鉴于政治文化以人为本,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就可设计为对人们政治生活与政治行为品质的提升和政治情感的培养。
但是,在近20年间一直实践着的(至少现实情况如此)“先经济建设,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式,甚至被典型化为“搭台与唱戏”的关系,这一种“顺序”实际上模糊了两个事实:政治文化是一种本然的存在,不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经济状态,政治文化脱离了他们的深层根源;虚化了政治文化本来的功能及其社会价值目标。因此,要使经济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得到真正实现,首先得从政治文化上还原这种认识,才是极其必要的。
(一)政治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存在——以阿昌族群体政治心理研究为例(注:阿昌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较为神秘的少数民族,阿昌族是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约3.9万,主要分布于云南西部德宏州陇川县和梁河县以及中缅边境地区。云南大学于1999年组织了大型民族调查活动,对全省25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后民族经济、文化、政治认知和心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特别是民族政治心理状况的变化过程做了深层次的研究。本人作为阿昌族调查组组长有幸参加了这次调研活动,并刘阿昌族社会政治历史的变迁做了详尽的考察,对过去和现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做了一定的比较,以详尽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既有的研究成果中的不实,特别是有关本民族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变迁做了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民族政治文化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民族心理文化模式着手,结合中华政治文化历史发展,以文化整体观的态度来看待民族政治文化形成与变化,才能对其作出完整的表述和解释。)
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贯彻其中的理论灵魂是“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对于“文化整体观”,弗兰兹·博厄斯在该书的序言写道:“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一种文化的意义这种愿望,迫使我们设法把标准化行为的描述也仅仅当作迈向其他问题的垫脚石。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予其生命的文化。”[3]在此,文化整体观被视为文化研究中最基础的背景,它提供了完整理解“文化方式”存在的土壤。该著作对整体观的考察和描述包括了文化血缘的沿续、历史的传承和变异、个体与整体的模式选择等,这也是基于文化平等基础上人类平等的观念的完整表述。总括而言,从整体观来考量“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是之结论是易解读的。它告诉我们,只要循此道而行,文化是有根的并且隐藏无可限量的力量。
近年来致力于民族地域差异性的阿昌族政治文化心理研究恰恰在整体观上出现了方法上的偏差。这一研究试图整合政治文化形态上的诸种特色,建造一个独立模式的“民族政治文化”。但显然,特色的寻觅和整合并不能必然地展示阿昌族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这里,借用“模式”一词,可能更方便地表述阿昌族政治文化不过是对无限种生活方式做出政治心理选择的结果,而选择的条件是已经被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广泛认同的如地理、风俗、价值观等普适性原因,这些特性、差异造就的个体化应该使政治文化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得到有力的支持,但现实却并不如此。
首先,试图使“阿昌族政治文化”以独立模式发展的研究着力的是地域民族个性为基础,由于整体观的忽视,造成了与整体政治文化的本源的分割;其次,地域民族特色的研究中,分散的材料并不服务于对阿昌族政治文化的起源的追溯。但是,“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已经为人们的寻根提供了深远的背景,政治文化正如《文化模式》里指出的:“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文化之中,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探索每一文化整体的兴趣。人们愈来愈感到,脱离了一般背景,就无法理解文化的一般特性……这种整体化的思考方式把地域特色作为背景而不是主体。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它避免了分离——因为分离造成了文化史的多种源头,这不是科学的结论。”[4]显然,阿昌族民族政治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昌族政治文化不可能独立于中华政治文化之外,尽管研究成果可以表明其发展形态的多姿多彩,但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制约了对阿昌族民族政治文化本质归属的认同。整体与个体关系的分离、前提与目标的倒置,使阿昌族政治文化的研究并不是回到其本原上。为什么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阿昌族并没有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之美呢?为什么文化的“无根之论”依然存在?仅仅用所谓的民族特质解释这一切显然是不足的。进化论和地域文化分析的方法虽然都致力于阐明政治文化行为模式的顺序,但不可置疑的是,最终的目标还是回到本原——承认政治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并积极地发挥作用。鉴于此,研究方法应该致力于呈现它的本然状态:政治文化的内生和传承方式。
(二)回到文化方式中:政治文化的能力、解释和选择
19世纪以来,文化学的研究不仅沟通了与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联系,更融通了与政治学的关系纽带,各学科之间已经不是作为彼此的辅助和支持,而是为政治学(包括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或者是更新了方向。这种方法上的发展,已经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景,联系和合作更成为必要。可以认为,“回到文化方式”中,既是一个综合的理论概念,更是一个有效的认识手段。这里谈及的所谓“政治文化的方式”就是首先承认一切政治文化现象就是社会文化现象,一切社会的政治文化模式都是文化类别的一种,包括了远离人文的科学技术。
如果我们认识或者承认文化方式自始至终地存在这一事实,承认政治文化重建只是政治文化改革社会的力量的重新组合,那么,回到政治文化方式中就显得更直接和简单了。笔者认为,它的逻辑顺序是:政治文化能力的培育、政治文化解释系统的建立和政治文化选择的进行。
英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查里斯·帕希·斯诺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一书,是他两次重要演讲的整理合集。文章中他提出了“科学文化”这一概念,论述了目前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在《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这一著名演讲中,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它们彼此的分裂造成了社会的损失,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只了解一种文化,因此会对现代社会做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未来做出错误的选择与估计。“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最不寻常的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最根本性的选择不得不由少数人秘密地、可还是以合法的形式做出。然而,做出这些选择的人不可能对做出这些选择所根据的因素或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具有第一手的知识。”[5]这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危险,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和分离就是错误判断的前提。因此,这里就提出了我们在判断之前,必须了解全部,这就是文化的能力。政治文化作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也有其政治文化能力。本文同意“文化能力”是对社会的判断这一观点。事实正是如此,如果决策人在决策时仅仅依靠的是政策权力和专业知识,不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根源可能导致的各种态势,是危险的或者是冒险的。政治文化能力对决策的帮助不是停留在“全面情况上”,而是像斯诺认为的,是在过去与未来中寻找现实的通道,倡导培育“政治文化能力”具有确切的现实性。
在对社会现象的诸种解释中,文化的解释方式总是徘徊在精神层面上,是最宽泛的,因此也似乎是最虚无的。建立文化解释系统,如果仅仅停留在学术范畴上,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解释系统”而非社会运作方式。鉴于人类的行为从来就具有诸种意义,而文化的意义就是改变程式和消除各种理解的鸿沟,在相互的理解上协调平衡发展,正如消除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分裂程式一样。所以,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行系统。相应地,政治文化的解释功能就在于其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符号解密系统而存在。
政治文化的选择主要是涉及到由政治文化建设目标而设置的政治文化评价标准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论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文化经济学的挑战,这并非针对民族主义而言,而仅仅是人性的发展和需要而言。如果在这时候,我们仍充满幻想地相信某些地区、族群的野蛮礼仪风俗是文明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的话,这不是对文明的逃离,也是对文化观念的狭隘的思考。“饱总比饿好”,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公理就可指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论中文化评价使用的“适应”论的偏颇。对于政治社会而言,更优的政治文化可以造就更优的政治社会结构。没有什么比能提升人的政治生活品质更重要的选择标准了。这是先进政治文化的核心。究其实,政治文化评价是社会政治评价的总和,政治文化的失衡是政治文化评价标准的失衡,谁可以在标准的范式外发展?犹如没有人可以活在他从属的文化模式之外是一样的道理。
三、政治文化:目标与能力
政治文化不是一个自全系统,它既是政治变化中的因素也是政治变革的力量。笔者把政治文化建设与政治文化重建间的关系拟表达为政治变革社会力量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变革就没有停止过,改变的仅仅是形式和方法而已。但是,政治文化变革的道路至今尚未通畅,这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性难题。恰是“几乎不曾有人费心去设法倡导文化的改变。实际上,倡导改变文化的整个概念成了一个禁忌。”[6]
政治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与选择一样是两难的。但这并不说明没有选择的可能。在当前政治文明的建设旗帜下,怎样的和可能的政治文化现实可以被呈现和应该被反映在政府的政治规划和设计中,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变革社会力量的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的核心概念。
(一)民主共享:政治文化实践的最终目标
民主共享是指各种政治文化差异的个体或地域群被选择作为共同的政治行为方式。这是对不同政治文化理解、尊重和实践的结果。基于人类平等的趋同性,民主共享是必须的。共享如何选择路径呢?20世纪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把文化视为一切行为的初始而非结果,这肯定了政治文化实际上是政治行为方式。既然人的政治行为方式就是政治文化方式,既然政治文化的起点已被大量的原始文化研究成果证明实现了共享,无疑,政治文化就是一切政治行为的起点。这就是回到内核的有效途径。这里有两个正相关的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现今时代没有人可以否认,政治文化的本质源于人而归于人这一意识主体。人类民主进步的所有努力无一不是为了提升大众政治生活的品质,因此,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在此,政治生活方式是一种泛涵解释,包括政治生活态度、政治行为意义的追寻、政治文化目标的设计等等。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宏大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把政治文化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标签和政治文明的口号,标签化、象征化、符号化,等等,忽略了政治文化作为人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根本意义,也就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为了提升人的政治生活品质。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否认个人的政治文化贡献——离开人本身、离开生命意义本身讨论政治文化问题,无疑都将是缘木求鱼。政治文化的大而无当正是由这些政治符号效果造成的。在今天建设政治文明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朴素地回到本原中考察一切政治文化问题,正是由于人本身的要求和发展,才产生政治文化讨论的必要和政治文化建设的客观必然。
第二,讨论政治行为方式存在不仅涉及到个人、个人与他者的关联,以及在这关联中呈现的生命状态,最关键的是要关注大众——组成某一政治文化形态的基础人群对政治行为意义和价值的认知。
以关注少数人的、精英的、金字塔尖为主要取向的政治文化观念和倾向,就当前的社会条件而言,只可能是一种政治文化远景。所有的政治文化选择在表象上是政治市场问题,而实质上是历史的选择和公众的文化惯性选择。这也需要回到本原上才更具有说服力。民主实践过程中的地域特色被看作政治文化的差异,它的传承结果已经显示了它被选择的原因和可能。就一种政治文化惯性而言,它当然是大众习惯和接受的结果——所有有悖于这一规律的政治文化行为的命运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改造。因此,与政治文化的本质一致,以民主共享为起点也应以共享为归宗。而且共享也意味着不同人群可以交流与合作的最佳途径,这正是当今政治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此问题上,要加以澄清的是,通常说的“大众政治文化”这一看法实在与现实着实不符。就我国政治文化现状而言,“大众政治文化”至多是流行文化部分而非大众可以共享的政治文化成果和产品。我们要关注的是,假定社会可以建立一个政治文化系统,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大众到底可以享用到什么?在商业化的市场运作中,政府对政治文化设施的投入建设,如何充分考虑民主共享中的合理设计。只有民主文化的共享才能真正实现政治文化目标的一致性。
(二)价值能力的追问:政治文化情感的培养
政治文化情感,笔者指的是以个体精神关注和考察人与整个世界的政治行为方式,这一方式首先赋予人以关怀世界与家园的政治情感意识。政治文化的平等是生命的平等。再进一步地说,政治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政治情怀——关于政治价值意义追问的能力和基本功能。
就政治文化建设而言,毫无疑问,政治运作的灵魂不是物化的一切,而是物化背后的政治生命价值和政治文化的能力。政治文化塑造政治人,对一切政治价值意义的追问都是政治文化问题。显然,对政治文化问题的解答需要的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专业知识与政治符号象征,更是需要一种政治情怀,这可以是本尼迪克特追随的人类平等观念,也不拒绝呈现查里斯·帕希·斯诺对两种文化分裂局面的忧虑,它仅仅关乎价值意义,统括全面的能力的价值意义——一切政治问题其实都是人类的政治文化问题。与原始时代所有与生存相关的努力都被视为当然和必然相类似的是,今天人类的任何政治行为方式都有被关注的必要,只不过,对政治文化价值和能力的判断标准使我们做出更优的选择。二元价值观面对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已经无能为力,与其以“对错”来判断不如以“合适”与否来选择,正如政治行为与人的政治情感同体生存、协调发展一样,政治文化的价值意义首先在于公民政治情感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