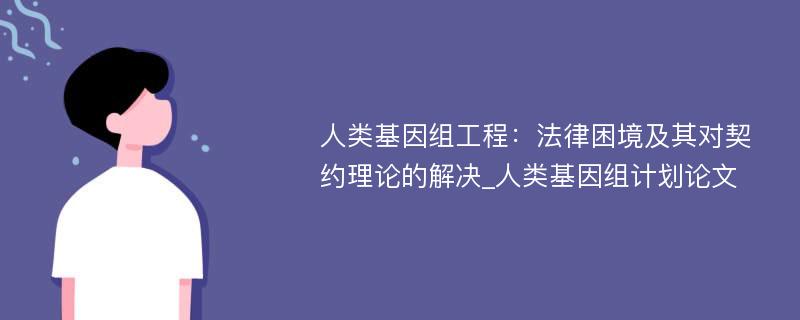
人类基因组计划:法律的困境及其契约论解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困境论文,人类基因组论文,计划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及诸多问题的产生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是迄今为止人类生命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它与“曼哈顿工程”(制造原子弹)、“阿波罗计划”(人类登月)一起被誉为21世纪科学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从合作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看,HGP的确是一项跨世纪的世界工程(注:HGP主要由美、英、日、法、德与中国等参与完成。参见余焱林、徐永华:《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与人类文明考查》,《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7期。)。
依据理论上的预测,人类基因组计划有可能揭示出人类的所有遗传信息。这意味着,随着HGP的完成,人类将在当今生命科学的话语体系下,解构出决定着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人类性状(包括健康的与疾病的)的遗传信息。现在人们所无知的许多遗传信息,其中尤其是许多遗传疾病的信息等,都有可能随着HGP的实现而被人们所认知,如白血病等。易言之,决定着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生物学程序都可能被人类自己理解。可以认为,这正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但事情也许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人类在面对如此宏大的计划时,毕竟有诸多顾虑:人们不由得怀疑遗传学家乃至整个人类是否要“扮演上帝的角色”(playGod)(注:参见Richard N.Osting,Scientists must not play god,Time,June 20,1983,v.121.p67.)?正如80年代后期关于HGP本身是否可行及是否应该的激烈争论所显示的,人类对HGP所能带来的“美好前景”和“灾难性后果”都是同样地敏感与清醒!而事实上,这种事先的警觉与认识是正确的,因为随着HGP的实施,已出现由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也正是HGP的一个子计划,即HGP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ELSI)研究的任务(注:参见邱仁宗:《人类基因研究和伦理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1期。)。尽管由HGP所揭示的遗传信息本身是中性的,并未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在其中,但是,由人类基于这些遗传信息而做的许多判断和决定乃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的产生。大致来说,这些问题至少包括:
(1)如何保护HGP成果的问题。这涉及到DNA序列的可专利性问题、DNA数据库的保护问题等。
(2)基于基因缺陷而造成的“遗传歧视”(亦称“基因歧视”,genetic discrimination)问题。这涉及到如何制止劳动单位(雇主)或保险公司因某些基因缺陷而拒绝雇佣此缺陷基因携带者或拒绝为之提供保险的问题。
(3)与上述遗传歧视相关,对缺陷基因的遗传普查和相应的基因治疗问题。这包括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问题、在涉及未来世代利益的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中的决定权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于优生学问题的忧虑等。
(4)对个人遗传信息如何保护和如何合理利用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是否有必要重构人权保护体系?
(5)“基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冲突问题。因为“自由意志”(free will)正是法律——其中尤其是刑法——运行的基础,若“自由意志”最终被“基因决定”取代的话,法治运行体系遭受的冲击则可能是毁灭性的。
(6)如何保护一个种族或地区的基因资源即遗传多样性的问题。这主要涉及到少数民族与欠发达地区基因资源的流失问题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对他们的不利影响。
(7)生物安全性的评价问题。即人类的基因操作是否是安全的?它能获得科学与伦理的论证吗?人们又如何运用法律来控制这种操作以保证整个自然界的安全?
可以认为,这些问题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将对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社会各界其中尤其是法学界等极为关心的事情。
二、HGP法律问题的契约论理解
笔者认为,同以往任何一次科学革命相比,HGP给人类带来的冲击是更为深刻与全面的:它的影响已遍布到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各个角落,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伦理、法律到环境、食品、卫生、健康、家庭等,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HGP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人们对于HGP的认识或接受程度亦有很大区别——这可理解为基于宗教、文化、种族、伦理甚至经济等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反应。易言之,正如不同文化等对于试管婴儿、体外授精等生殖技术和安乐死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与态度一样,人们对HGP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亦有多种不同反应。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的“知情同意”问题,在个人主义或自然主义占主体的西方文化中和在集体主义或家族主义占主体的东方文化中或在不同的宗教中就可能有根本不同的理解。
这种多样化的理解和随之而采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态度,虽然在有些情况下是基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的相互冲突而引起的,如基因工程公司或医疗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有可能不经病人的知情同意而窃取某些有市场价值的基因,但在许多时候,这种理解的不同则可能是完全基于不同的道德背景(如文化、宗教等)做出的。易言之,这种理解的多样性,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也许是由于非经济因素造成的。
在此我们就可看到问题的矛盾所在。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体系下,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种族或宗教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都应该表现出尊重,因为这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亦是世界文化保持繁荣的理由。另一方面,HGP合作的广泛性,和其结果对世界的公开,就使世界各地基本同时地面对HGP的最新成果,也因而基本同时面对由HGP所带来的诸多社会、伦理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因而就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这种必要性亦由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逐渐全球化而带来。如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相关的贸易问题、税收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基本上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在文化上与政治上亦有同样的趋势,如对人权问题和环保问题的普遍重视等。这些方面的趋同亦会影响与要求在对待由HGP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的相对统一。
这种标准的相对统一是必须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商业势力进一步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单独采取严格的标准都有可能导致商业公司将其主要活动转移到标准较为宽松、限制相对较少的国家或地区,以规避相应的法律制约。对于科学研究亦是如此。可以想见,局部的限制是很难获得普遍控制的。
在此,我们看到了解决由HGP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如何在相互尊重各自道德观的情形下获得相对统一的法律标准呢?笔者认为,诉诸于契约论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契约论是人类理性的创造。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到罗尔斯等,契约论被用作一种论证工具来证明人类社会的由来和自然法的必要。在诸位契约论大师中,虽然各自的观点与论证不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类初始状态的假定,尽管他们假定的初始状态亦是不同的。罗尔斯在这种假定的原初状态中抽象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概念,认为人们正是在这种“无知之幕”之后才可能通过制订理性的契约来达到公平和正义(注: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136页。)。罗尔斯假定人们不知道关于他们自身的某些特殊事实,如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天赋等,因此为避免将来可能造成对自己的不利,人们便通过订立契约以“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注: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136页。)。即,人们正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状态的无知,才诉诸于通过事先的相互同意而达成契约,以免自身的利益在未来受到损害。对于这点,亦可进一步理解为: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便在对某些信息相对无知的前提下达成契约,以维护(或理解为客观上维护了)“公平的程序和正义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了契约论的人性基础,亦看到了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契合点(注: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4页;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136页,译者前言第12页。)。此亦如休谟所说:“只是从人类的自私与有限的慷慨,和自然提供的稀少资源中,正义才找到了它的根源(注:Peter Stein,Legal Evolution-The Story of an lde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13。)。”
基于“无知之幕”的假定,罗尔斯论证了“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做为“平等原则”(equality principle)的第一原则和由“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a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组成的第二原则(注: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1页。)。认为通过这两个原则(其实是三个原则)的依次运用,就能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
如上所述,以HGP的实施为标志的生物学时代,已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人类在共同面对困扰自己的诸多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另一方面,道德观的多样性又使人们难以在众多的道德标准之间做出选择。笔者认为,在此困境下,借助于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理性立约不失为一条相对完善的解决途径。
可以认为,在HGP所带来的“基因时代”到来之际,相对于罗尔斯“无知之幕”的理性假设,在此我们却看到了真正的“无知之幕”:在HGP能揭示出大量的基因缺陷之前,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事先知道他或她的基因组中是否含有或含有多少缺陷基因,因而便不可能事先知道自己的遗传命运!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人类在基因时代需要达成理性契约的充足理由:在每个人都因为面临着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各种基因缺陷而表现出的不可测的恐惧中,人们就期望能达成一种事先的契约,以制止一些行为或容许一些行为,以使这种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基因歧视不会或尽可能少地给人性的尊严与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不可测的扰乱。
三、HGP法律问题的契约论解答
如上所述,基于“初始的无知”(primary ignorance)假设,罗尔斯抽象出人类社会“无知之幕”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正义原则,以期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而事实上,人们不仅在原初的状态下是无知的,在现代的社会状态下亦是同样地无知:他或她不知道自己的基因组内是否有缺陷基因存在,不知道这种缺陷基因有多少,亦不知道现在被认为是正常的基因是否在将来的某一天又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或者现在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基因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又被证明是正常的或者具有某种重要的生理功能。这种个人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或说不可预测性,其实也正如社会未来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一样,是强烈地受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影响的。即相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人类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知的个人信息或社会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就决定了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无论是对于个人命运抑或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命运都是相对无知的,即人们永远处于一种“无知之幕”的笼罩之下。
而契约理论对于“基因时代”诸多问题的解答,至少可从概念、原则与规则三个层次获得答案。
首先是概念。概念是人们认知的基础,亦是人们达成契约的先决条件。可以想见,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要达成一致的契约是不可能的。但有趣的是,即使是某些概念的形成,亦必须由人们通过共同的同意或认可——也因而是一种契约——来达成。这看似一种循环的论证,但其实却正是契约在不同层次应用的体现。例如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诸如“人”、“死亡”、“尊严”等概念,无不必然或者应该通过人们相互间的契约来达成一定的内容。举例来讲,什么是“人”?“人”的内涵都有哪些?他或她从何时开始可被认为是“一个人”?是从受精卵开始,还是从胚胎期,抑或从母体中产生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对此概念的精确理解或说约定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关系着一系列重要的权利归属:例如,何时堕胎是允许的?当母亲的利益与胎儿的权利相冲突时如何权衡两者?胚胎、胎儿与婴儿的权利是相等的吗?这些概念的不确定或内容的不统一,就会势必造成权利冲突的激化。对于“死亡”的定义亦是同样的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死者”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可能关系到“生者”的利益如器官移植等,也是当今世界讨论异常热烈的问题。对于人的“尊严”、“唯一性”(uniqueness)等概念亦可从同样的思路做出解答。
其次是原则。这既包括诸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自主、有利、安全、知情同意和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等原则,亦包括当这些原则相冲突时的平衡原则及其对相关原则的取舍(注:Tom L.Beauchamp & James F.Childress,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4th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50~262。)。例如,当“自由意志论”和“基因决定论”相冲突时,为社会利益考察,人们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舍弃“基因决定论”而采取“自由意志论”。这正如一位社会生物学家所说:“纯粹的(基因)决定理论不能被任何社会所接受——即使它们是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罪犯也许都是一个受害者——他的基因、他的教育、他的环境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受害者。然而,法治系统一定要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面,即一个成年的健康人和正常人能够和必须为他或她所做的负责——否则,在社会中的和谐共存将是不可能的(注:Georg Breuer,Sociobiology and the Human Dimen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44。)。”这种对各种原则的确定和当原则相互间有冲突时对平衡原则的掌握,则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共同的约定即契约而实现。考虑到人们在地域、文化与种族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共同的约定是必要的,否则就可能出现相互间的不理解与不合作。
最后是规则。在通过契约达成相对统一的概念和原则之后,人们就可以进一步通过契约来达成可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规则可以是法律、道德与伦理等。一般而言,在这三者之间,法律的强制作用要大于道德与伦理。但在有些情景下,三者之间的界限却是模糊的,如在国际法范畴之内。与概念和原则相比,契约的意义在规则的层次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与直接。如前述DNA的可专利性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信息等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基因治疗中的知情同意问题、基因资源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及基因操作的安全性问题等,都可通过人们共同的协商,以达成必要的契约,供大家共同遵守。例如,基于HGP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共同认识,人们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认为有必要在实施HGP的同时,开展此计划对于社会、伦理与法律等方面影响的研究,以期能通过尽早与尽可能全面的共同防范措施避免它对社会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针对上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7年通过了《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权问题的世界宣言》,欧盟于1997年通过了《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于1996年发布了《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的声明》,HUGO伦理委员会于1997年和1999年分别发布了《关于DNA取样:控制和获得的声明》和《关于克隆的声明》。这些理性的立约无疑为世界范围内的HGP实施及其他生物技术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指导与限制。
以上分析了契约理论在解答由HGP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时可能具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种作用是有益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当人们尚未达成一致的契约时,便处于一种“前契约”状态,此时契约理论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其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仅有契约理论是不能完成相关判断的,而必须借助于其他理论如功利主义的判断;(注:参见李一平:《关于道德的多元化——就〈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与恩格尔哈特的对话》,《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8期,第428~431页。)其三,出于社会成本的考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功利主义等的补充便是必需的。但尽管如此,契约理论仍不失为解决基因时代诸多问题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