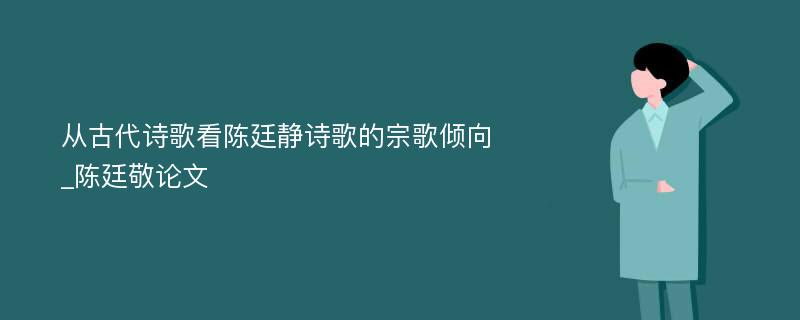
从古体诗看陈廷敬诗歌的宗宋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体诗论文,诗歌论文,倾向论文,看陈廷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275(2007)01-0012-04
将陈廷敬与王士禛的行迹与事业相比较,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相近似之处。二人年寿差不多:陈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去世于清康熙五十一年,享年73岁;王出生于崇祯七年,去世于康熙五十年,享年77岁。二人中进士的时间相近:陈在清顺治十五年,时当21岁;王在顺治十二年,时当22岁。二人仕履相仿,都长时间在康熙朝作京官:陈从康熙四年起,直到康熙五十一年,除了父、母亲去世,按照礼制回乡各守丧三年外,在京任职长达四十余年;王也是从康熙四年起进京为宦,直到康熙四十三年,作京官四十年,并且这期间,也曾经历过父、母亲之丧。他们都曾经担任过翰林院侍讲或侍读,都在国子监任过职,一作司业,一作祭酒,都作过詹事府少詹事,作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和刑部尚书,都曾深得圣眷,充当过经筵讲官,并且于康熙十七年一起入直南书房。在文化与文学事业上,二人也桴鼓相当,他们曾一起担任了《明史》、《三朝国史》等大型书籍的纂修官,一起参与编修《御制文集》。他们都能诗善文,创作甚丰,陈当时“咸以大手笔推之”[1] (集部七《午亭文编》提要);王则为一代文坛领袖,“海内宗仰如泰山北斗”[2] (P580宋荦《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
陈廷敬与王士祯共同立朝数十年,常一起游观宴享,一起“砻砺切靡为学”[1] (集部七陈廷敬《午亭文编原序》),彼此频繁地投赠唱和。他们惺惺相惜,有一次康熙帝询问朝臣中谁最能诗,陈廷敬举荐了王士禛,而王士禛亦甚奇陈廷敬之诗[1] (集部七《午亭文编》提要),可见,他们彼此知心,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不过,尽管他们在文学上互相欣赏,可是其诗学主张却并不相合,可以说差异很大,陈廷敬坦言:“新城王阮亭方有高名,吾诗不与之合。王奇吾诗,益因以自负,然卒亦不求与之合,非苟求异,其才质使然也”,“始吾于汪(指汪琬)、王(指王士禛),顾颇自得,不欲苟雷同,岂唯才质乎,将以力之所近者,求至于吾道焉已耳。”[1] (集部七陈廷敬《午亭文编原序》)由这些话,可知他们的不合,是由不同的才性造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他们所追求的不同的“道”造成的,也就是说,是源于见解的巨大差异,带有根本性,无法苟求雷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廷敬和王士禛都是襟怀宽广、识见融通的达人,“君子和而不同”,诗学观念的不同,并没有损伤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妨碍他们惺惺相惜。
陈廷敬用颇有些自负的口吻所表白的与王士禛不能相合的诗学主张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诗学观的不同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王士禛的诗学主张是众所周知的,其核心为“神韵说”。他倡导诗歌应该达到严羽说过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那样一种境界[1] (集部·总集类五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序》),推崇清简淡雅、超然玄远的风格。他宗尚、取法的对象并不宽广,主要为在创作上符合其审美理想的王维、孟浩然这一诗歌流派。
陈廷敬并不是像王士禛那样的一个诗歌理论家,没有提出过一套系统而明确的诗学理论,因此我们只能从他的创作和别人的议论来探察其诗学观,以比较其与王士禛诗学主张的差异。
先来看别人的议论。我们举三段话,一段是王士禛所言:
陈说岩廷敬相国少与余论诗,独宗少陵。略记其一云:“晋国强天下,秦关限域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3] (P200)
再一段话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陈廷敬)喜为诗歌,门径宗仰少陵,颇不与王士禛相合。
还有一段话是著名诗论家沈德潜所言:
予少时,尤沧湄宫赞以午亭诗见示。读《晋国》一篇,爱其近杜。后读《渔洋诗话》,亦谓其独宗少陵,前辈先得,我心不胜自喜。[4] (P88)
以上议论,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意,无一例外地说陈廷敬以老杜为宗。这些议论都出自眼力不凡、识见超人的评论家之口,自然是发言有据,当应令人信服。
再从陈廷敬的诗作来看,翻阅《午亭文编》,像王士禛、沈德潜所举的《晋国》那样一类呈现出沉雄阔大的意境、可谓深得老杜之神的篇章甚多。联系陈廷敬特地为解说杜甫的七言律诗而作《杜律诗话》,可知他下过苦功学习杜甫,“近杜”之说,确为不刊之论。
可是,王士禛诸人的议论太过简略和笼统,太过简略就难以精当,太过笼统就易生误解。我们知道,清代早期的诗坛是分成“宗唐”和“宗宋”两大派别的。按照上述说法,想当然地就会把陈廷敬归入“宗唐”派。也就是说,陈廷敬与王士禛其实都属于“宗唐”一派,其不合处仅在于取法对象一为老杜,一为王孟诗派而已。
然而,稍有些诗歌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是一位处于我国古代诗歌发展转折关头的诗人,他的创作既融会和发展了唐朝诗人已经取得各种艺术经验,形成最典范的唐音,充分展现出“盛唐气象”;同时通过其不凡的艺术才力,刻意求新求变,在题材、艺术形式、语言上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宋代诗人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都是由他发端的。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一头连接着“唐音”,一头连接着“宋调”。
所以,笼统地讲陈廷敬“门径宗仰少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辨析清楚其创作究竟接受了杜甫那些方面的影响并呈现出怎样的艺术风貌,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陈廷敬诗歌的特征与成就,才能更确当地为其诗歌创作“定位”,认识清楚当王士禛的“神韵说”笼罩诗坛的时代,其创作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陈廷敬的《午亭文编》的诗歌部分是按照诗体编排的,而《午亭山人第二集》是按照时序编排的。然而不管哪一种编排,阅读其古体诗与阅读近体诗给我们的感受却并不一样。
陈廷敬的近体诗,大多数与上面提到的《晋国》诗一样,格律严谨,语言凝练,意境雄阔,格调健朗,酷肖老杜那种最能体现唐音的典范之作。
再比较着读陈廷敬的古体诗,感受就不同了。在这种古老的诗体形式领域,很明显,他是沿着老杜所开辟的通向宋代诗风的道路前行的。其大量的古体诗作,无论五古还是七古,都鲜明地呈现出宗宋的倾向。我们从陈廷敬所喜爱并一再模仿的诗人就不难窥见此中消息。
明显的宗宋倾向,恐怕才是陈廷敬与王士禛诗学主张分歧的根本所在。
陈廷敬所喜爱并一再模仿的诗人一为韩愈,一为苏轼。
韩愈是比杜甫对宋人影响更为直接和巨大的诗人。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方面,较之杜甫,他可谓变本加厉,杜甫只是开个头,他则专以此求胜,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地身体力行。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在创造有宋一代的诗风时,即把选择典型的目光对准了韩愈。其后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更是从韩愈那里多方取法,正如清人叶燮所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3] (P570)陈廷敬对韩愈创作的推尊与喜爱,正是其宗宋倾向的明白无误的表白。他曾说:“不学西昆学杜韩。”[5] (卷一《自嘲兼简内直诸公》)又说:“杜韩郁崩腾,回风激泷湄。”[1] (《午亭文编》卷五《题东坡先生集》)将杜甫与韩愈相提并论,其着眼点恐怕即在于杜、韩共同具有的影响到宋朝一代诗风的那种力求生新夭矫、不落腐庸艳绮俗路的风貌。这里需要略作解释的是,“学杜韩”的“韩”,不专指韩文,也应包括韩诗。他对韩诗不仅喜爱,而且非常熟悉,写诗曾一再用韩愈诗原韵,在《午亭山人第二集》中便有这样的诗作十三首:《秋日述怀次用昌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韵》、《秋怀诗次昌黎韵十一首》、《虾蟆石诗》(诗序中说是用昌黎〈答柳州虾蟆诗〉韵)。这些诗学韩不仅仅在用韵,其语言、结构、命意等等也都努力逼肖韩愈。这一点,下文再加以讨论。
对苏轼,陈廷敬就愈加景仰,其《题东坡先生集》诗云:“苏公天上人,万丈银河垂。举手扪星辰,足蹋龙与螭。”[1] (《午亭文编》卷五)表示了无限的企慕。对苏诗,也就更加心摹手追,频频模仿。其用苏诗原韵的古体诗即多至十八首,如《忆樊川梅花用东坡〈松风亭梅花〉韵》、《和子瞻饮酒四首》、《十二月二十六日湘北、贻上、幼华、蛟门见过,用东坡〈馈岁〉〈别岁〉〈守岁〉韵三首》、《同南溟、湘北春宿左掖,闻贻上将至,用坡公〈喜刘景文至〉韵迎之》、《人日雪宿左掖用坡公〈聚星堂〉韵》等等。从这些例子足以看出陈廷敬对苏轼诗歌熟悉的程度,许多诗他是背诵如流的,例如他在掖垣值宿,不可能随身携带着东坡诗集,而像《喜刘景文至》、《聚星堂》这样的诗他必是烂熟于心,能够随口吟诵。像学习韩愈一样,陈廷敬的这些诗,当然也不仅仅在用韵上追步苏轼,而是全方位地学习,从苏轼那里获得多方面的滋养。
陈廷敬有时还用韩愈、苏轼原来的诗题来写作,例如韩、苏都写过《石鼓歌》,他亦用同题作了一首,自嘲说:“石鼓歌者韩与苏,我今捉笔捋虎须”,但又不无自豪地说:“我歌石鼓排郁纡,韩苏歌后补所无。”[1] (《午亭文编》卷三)韩愈作有《秋怀诗》十一首,他也用同题作了十一首。苏轼有《和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他便也学着写作和诗十三首(《午亭文编》卷六有诗《东坡〈和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谓其七首皆仙语,读〈抱朴子〉有感,和之。余尝欲作游仙诗,因次其韵》)。没有发自内心地向慕和学习的愿望,是不会这样亦步亦趋地照样做的。
次韵也好,使用同样诗题也好,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当然还应该从具体写作的各个角度细致地分析陈廷敬诗歌的宗宋倾向到底有哪些表现。
“以才学为诗”是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受杜甫、韩愈影响而形成的。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等作品肇其端,韩愈继往开来,他用恣肆开张的笔法大谈“金石学”的《石鼓歌》就是一个显例。至宋代,此风愈盛。如苏轼,除了《石鼓歌》,还写下诸如《诅楚文》、《题王逸少帖》等等篇章。担任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大清一统志》等等大型典籍总裁官的陈廷敬,是一个精通文史和文字学的大学问家,在“以才学为诗”方面,他步武前贤,也一展身手。尽管有韩愈、苏轼之名篇在前,他仍能游刃有余地写下能够补韩、苏“所无”的《石鼓歌》,特别是后半篇将宋徽宗之后石鼓的命运娓娓道来,显示出其学问的渊博。《右军书乐毅论真迹歌》则是一首讲论书法史的诗歌,诗中将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的由来以及这一法书后来在历朝的隐现浮沉,一一道来,像是一篇专门的书法史。此外,《万寿寺华严钟歌》讲述永乐大钟的铸造与命运,《开元钟》述说后唐李嗣昭铸造铜钟始末,《焦山古鼎歌赠林吉人》描述古鼎流传,均在诗中谈文说史,显露才学。至于在其他诗作中引经据典,更是随处可见。
“以文为诗”是宋代诗风又一个重要特征,它同样是滥觞于杜甫,中经韩愈发扬光大,至宋人而蔚成风气的。“以文为诗”,主要指在诗歌中容纳进古文的元素。陈廷敬在古文的写作上造诣很深,足以与同时代的古文家汪琬相媲美。所以他对于宋人的“以文为诗”理解既深,把握也准,不仅接受起来没有什么障碍,运用起来也是优游自如。
“以文为诗”,具体说来,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以习见的古文句法入诗;表现在结构上,就是运用古文章法。
先说古文句法入诗。我们知道,传统的五七言诗形成以后,特别是近体诗形成以后,虚字虚词基本上退出了诗歌,省略句子成分、语序倒置等等手段成为司空见惯的构句法。所以当我们诵读那些合乎常规的诗歌时,会产生意象密集、诗意浓缩的强烈感觉。就每一句诗而言,语言凝练到无以复加;就句与句的关系而言,往往是通过“意合”的方式来衔接,句与句之间,意思常常是跳跃的,有相当大的“间隔”,容易造成多义性。而习见的古文句法恰恰与之相反:语序合乎规范,句子成分完整,大量使用介词、助词、感叹词等等虚词,以标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传达出明确的意义指向和鲜明的感情色彩。用这样的句法写出来的诗句因此也就显得平直,简截,浅白。宋诗的味道与唐诗不同,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大量运用了古文句法。
翻开陈廷敬的诗集,你会看到,运用古文句法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南旺分水行》:
导淮桐柏会泗沂,东流于海禹所治。赵宋黄河决而南,淮与泗沂兼并之。河于中土一大物,况挟众流行恣睢。尔后六百有余载,多为世患违津涯。吴艘越舶亘天来,神京陆挽人驴疲。伟哉潘生伏下职,建言为国陈良规(原注:济宁同知潘叔正建言开河通漕运)。宋公举事不漫浪(原注:宋尚书礼),下采群策褒参裨。是何老人白其姓,厥名曰英超等夷。铜壶倒影测累黍,玉尺量地穷四维(原注:老人白英建策分水)。河湾接流二十里,北走千里诚一奇。我行南旺分水处,此岂地利皆人为。……[1] (《午亭文编》卷七)
这一段一五一十地讲述南旺分水处的由来,不见紧缩的句法,不用密集的意象,平平道来,诗意简单而明确,不会产生歧解,没有一唱三叹的余蕴。像“河于中土一大物”、“是何老人白其姓”“我行南旺分水处,此岂地利皆人为”这样的句子,全是大白话,有些句子虚词可用可不用,他却故意使用,以造成一种别样的感觉。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正是在运用古文句法这一点上,陈廷敬的诗歌明显呈现出“宋调”特征。
再说运用古文章法。古文是长于叙事、议论的文体,其结构特点正与它的这一功能密切相关。无论它如何转折顿挫,曲折盘旋,一定要做到文气、思绪丝毫不乱,层次分明,井然有序。韩愈、苏轼的古体诗常常借鉴的便是古文这种善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极其明晰的结构方式。陈廷敬受前贤启发,也向古文结构取法。例如前面提到的《右军书乐毅论真迹歌》(题下原注:观于张吏部家):
刻石多有乐毅论,风格独让快雪堂。摩挲卷帙老将至,想像用意分豪芒。藤荫别馆见真迹,得此令我书传香。昔者晋室遘丧乱,南渡士民何仓皇。兵革未偃盛文藻,风流墨妙传两王。大令学书特从横,右军作此严其防。庖丁游刃中肯綮,东野钩百看腾骧。金绳玉锁不受缚,天马脱辔群鸿翔。神光陆离势欲动,洛灵容与骖鸾皇。又如大海回波澜,珊瑚碧树枝柯长。夏瑚周鼎历世宝,法墨直欲与颉颃。展转六朝谁所得?漂零百战同兴亡。晋阳之甲杂儒翰,贞观御府亲收藏。太平主家借摹写,明珠翡翠罗缥缃。如云宾客一朝散,丹青豪素空籯箱。大索十日闭朱邸,老妪衣缝潜携将。投之爨下实虚语,人间那得知其详。世上小儿学解事,诋诮正士嫌锋芒。蛟龙岂无角牙厉,雷霆变化谁能量。岐阳石鼓久漫灭,昭陵茧本沉芬芳。我贫讵有千金直,过眼矜燿神扬扬。是日聚观如堵墙,击撞抵触头低昂。檐花正落飘不入,燕泥欲下能禁当。心记指画争俄顷,焉得常置几案旁。默嘱鬼物善呵护,干戈时代遥相望。断行短纸人爱惜,晋家陵土今荒凉。对此涕泪翻淋浪,人寿几何徒羡女,日斜掩卷魂暗伤。[1] (《午亭文编》卷三)
此诗由在张吏部家观赏王羲之《乐毅论》真迹写起,几句简单的交代之后,便转入到对历史的回顾,先写王羲之何以书写《乐毅论》,并顺带评论其书法之妙,然后像讲故事一样记述六朝时特别是唐朝时这件法书的流传经历,其后又回到开头,写观赏这一件稀世墨宝之时众人喜不自禁的举止和自己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最后是抒发感慨。通篇或叙事,或议论,或抒情,掌控自如,处理得起伏跌宕,曲折盘旋,同时又历历落落,井然有序,显然得力于古文章法。我们再读读《石鼓歌》、《开元钟》、《书刘西谷白渠举锸图》、《秋日述怀次用昌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韵》诸篇,也都体会到其运用古文章法之妙。
至如宋人好“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在陈廷敬身上一样表现得非常鲜明。其大多数古体诗都有议论,无论是针对历史,针对时政,还是针对人生,陈廷敬都喜欢发表见解。由于他是一位身处高位的政治家,眼光远大,思虑深沉,见解也就每每不同凡响。《书刘西谷白渠举锸图》由白渠的前身郑渠写起,转到白渠之兴,与之相联系,说到秦祚之短与汉武帝王朝之盛,顺势总结出这样两句:“富强要是人所为,陵替何曾关水土”。之后,讲到汉以后关中地区之兴亡,讲到成周八百四十载此地人民之纯朴安乐,讲到对包括画家在内的时人的期待,无不与那两句精辟的议论相呼应。这两句议论,蕴含着作者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刻思考,蕴含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显得分量很重,成为全诗惊警的点睛之笔。《秋日述怀次用昌黎〈此日足可惜赠张籍〉韵》是写人生的一段经历,一上来就是一大段议论:“此日足可惜,一试安可尝。百年曾几何,枌榆冀末光。人生不自保,为乐须有方。……荣途旦暮耳,何可为故常。旧时堂中人,恻怆悲存亡。进止势各异,修短理则长。人怀千载虑,一夕鬼在旁。譬彼沟浍水,绝流不入江。又如早燃烛,焰尽烬不明。谁能系长绳,续此一寸光。”这首诗具体的写作背景不清楚,这段议论究竟针对什么而发也不能明了,但那种饱含人生经验的深沉感慨,却让每一位读诗人都会心有所动。假如抽去了这一大段议论,仅剩下后面叙述个人经历的一部分,全诗就会显得比较一般,不会让人深长思之了。陈廷敬这一类因为有了议论而显得力大思沉的古体诗,明显更接近“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而同“多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味道有别。
综上所述,无论从陈廷敬喜爱、推重并一再模仿的作家来看,还是从其具体的作品来分析,其古体诗的“宗宋倾向”都是毋庸置疑的。
王士禛其实也有过“宗宋倾向”,他晚年自述一生创作历程时说“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3] (P163)。但是时间不长,早年的他专操“唐音”,中岁之后,又回到原来的祈向。他于55岁编辑《唐诗十选》,56岁编辑《唐贤三昧集》,重新强调了他的诗学主张,更坚定地打起“神韵”的旗帜。由于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很高,再加上康熙皇帝“宸语”褒扬,“神韵说”风靡一时,形成占绝对主流地位的诗学主张和创作倾向。
当一种风气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人容易随风倒,只有那些真正有主见、有胆识的人才敢于坚持己见,不为所动。陈廷敬就属于这样的特立独行之人。从上面所引的《午亭文编自序》那段话来看,他认为自己的“才质”与王士禛不同,无法与之相合。这就是说,他认为诗人各有各的禀性、才能、气质,因此,创作倾向、创作风格应该因人而异,一个诗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个人的追求,在诗学主张上不必强求相合,也无法强求相合。在我们看来,陈廷敬是一个性格沉毅持重的辅弼大臣,一个时刻关注现实的政治家,一个务实求真的学问家,在个性上与更富于文学家气质的王士禛有很大差异。料想陈廷敬自己对此也是有清楚认识的。他正是依据自己“力之所近者”确立了个人所追求之“道”,并且始终不渝、身体力行地去争取达到这一境界。
也许陈廷敬诗学观和创作上的“宗宋倾向”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是,他这种不为风气所囿、自主自觉地选择适合自己“才质”的诗歌创作路数,自主自觉地追求个人独特风格的思想与做法,却无疑是非常可贵的,极具启发性和积极意义。
考虑到陈廷敬在政坛上受人尊仰的地位,考虑到他在一代文化事业上的崇高地位,考虑到他的交游之广,其诗歌创作的“宗宋倾向”,特别是其特立独行的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一定在当时的文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需要做细致的考证,不是本文所能容纳,只能俟诸另外一篇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