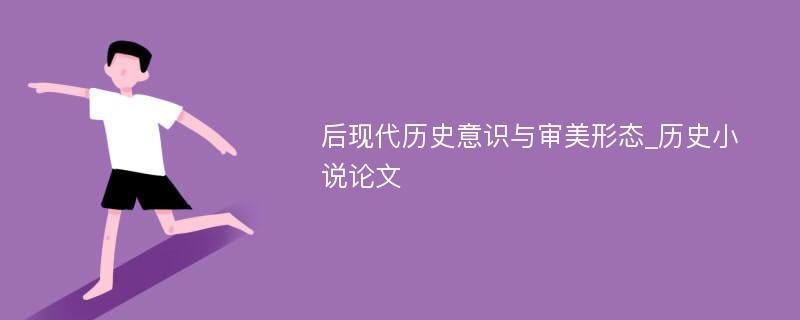
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形式论文,意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历史小说的理论问题是纠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面对当代历史小说的风起云涌与不断风靡全球的阅读狂欢,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历史意识和审美形式的当代融合如何可能?历史小说是否会走向终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通过对历史意识及其表达形式的诊断回应了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她在东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中不断推进与更新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在文学伦理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关联中,建构了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为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的融合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悖论的是,赫勒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扎根于东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潮流中。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将,赫勒在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的直接影响下展开小说研究,揭示主人公人格的道德伦理、情感现代性等问题,为其历史小说理论奠定了后现代性或者“现代性的异质性”基石。 20世纪50年代,赫勒对果戈理、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在卢卡契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观》。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的迫切性问题,通过对《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主人公的人格伦理与作者的伦理学的内在联系。《怎么办?》对浪漫主义的虚假幻想进行反讽性再现,触及“生活”与“存在”的悖论性命题,揭橥了作者的人类学原则,“人的每一种质性以及道德性都来自人的自然建构。人类学原则的起点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也是对宗教的批判。宗教把人割裂为身体和心灵两部分”,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活动是由外部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内部自然规律相互决定的”①。虽然经济和历史决定着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但人是有理性的自由个体,当一个人的激情成为主导时,就会导致伤害或毁灭,因而应该注重人自身与环境的和谐,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自由许可理论”。在小说中,女主人公韦拉爱上了把自己从小市民家庭环境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男主人公洛普霍夫,婚后又与洛普霍夫的朋友基尔萨诺夫相恋。在矛盾的纠葛之中,洛普霍夫以假装自杀的方式选择离开,从而成全了这对恋人,后来他与韦拉的朋友卡捷丽娜结婚,两对情侣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摆脱了悲剧的救赎性。在赫勒看来,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伦理生活选择,正是自由许可理论的文学化,在理性的自由选择中构建和谐的生活方式,在认识与自由之间达成康德式的审美和解。这种融合美和善的道德人格的理性建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劳动分工的批判,消解了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割裂,彰显出个体存在的丰富性,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极为接近。在70年代,赫勒从青年马克思关于人之存在的视角,以类似于雷蒙·威廉斯所言及的“情感结构”的小说批评方法,检视现代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转型与情感操持的危机。处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四部代表性小说作品,即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萨德的《瑞斯丁娜》和奥斯汀的《爱玛》,透视了现代初期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情感建构的积极性与自发性:情感在优雅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形式,美的心灵和罪恶的心灵皆自然流露,阶级性与个体的情感获得了内外的统一。20世纪20年代左右,卡夫卡、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的创作反映了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转型及其危机,主人公的情感日益抽象化与异化,只剩下空虚的躯壳。在一些小说中,人的情感转变为色情关系,难以获得人格的自我实现,“只有未实现的色情主义具有内容,然而实现了的色情主义又立即掏空了内容。生成性的外部因素导致了情感的毁灭,‘内在因素的维持’又导致了人格的毁灭”②。对此,赫勒通过情感现象学和资产阶级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明确提出超越资产阶级情感结构危机的新趋势,即具体的热情主义所蕴含的人格情感的丰富性,逐渐摆脱了卢卡契“悲剧形而上学”式的历史哲学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中,赫勒在小说批评中延续卢卡契主人公类型研究的路径,还不时戴着总体性的镣铐,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伦理观和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影响下,寻觅到人类新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初见端倪。 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卢卡契30年代所作《历史小说》的批判性阐释,是赫勒历史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赫勒以解构主义者德·曼的小说时间观和晚年卢卡契为《小说理论》所写的《序言》为视角,探究被她视为卢卡契文学理论最优秀的杰作《历史小说》的贡献与理论困境,鲜明地表达了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的立场。 德·曼在《盲目与洞见》中谈及《小说理论》所信赖的进步主义时间观。卢卡契在1962年的《序言》中否定了《小说理论》与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小说理论的实质联系。以赫勒之见,《历史小说》和《小说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历史小说》延续《小说理论》的历史分期,遵循小说主人公类型学的逻辑框架,挪用史诗与小说的比较方法,赞赏史诗文学价值的规范性意义。另一方面,《小说理论》的解释模式为《历史小说》的表现性反映方法所取代,用德·曼的话说,这是“从作为解释的艺术理论到作为反映虚构的艺术理论”的发展。③虽然卢卡契频繁地使用反映概念,但是小说表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左派立场是一致的。赫勒颇为重视卢卡契关于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样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论辩。在卢卡契看来,历史小说的审美艺术结构原则是从古典历史小说创作中所形成的“中间人物理论”:作为普通人物的主人公处于社会冲突力量的平衡点上,“其任务是把小说中的极端性的斗争力量,把艺术表现的社会巨大危机性冲突彼此联系起来。这个主人公处于情节的中心。借助于这种情节,就可以寻找到并建立起中立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斗争力量的各个极端可以被引入到人类关系之中”④。中间人物是旁观者、参与者、历史意识的洞察者,能够把握历史的总体性,他在形成历史之后能够回到日常生活,调整到黑格尔所谓的现实性中,散文化的时代诗意地来临。在赫勒看来,中间人物理论是一个完美的构形原则,这种具有史诗性的艺术原则为了适合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又引入了人民性概念,从而拯救了历史小说的困境,建立起审美结构形式与左派意识形态的联系。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对经典历史小说作品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但是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主要问题在于伦理元素的缺失、人民性概念的坚守,以及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无法克服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与绝对拒绝的现代主义伦理之间的悖论。对现实主义小说观念的坚守导致对现代主义小说的激进拒绝,而其激进的伦理现代主义又抛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伦理品格。基于此,卢卡契既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历史小说,又忽视了从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的女性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审美上与现实主义审美符码一致,但不符合“悲剧形而上学”的伦理镜像。卢卡契把中间人物和人民性联系起来,似乎解决了历史小说与左派意识形态的困境,但人民性在现代历史小说中遇到了挑战,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它不再是真正的人民性,而是沦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民性对艺术质性带来了伤害,在强烈的民众主义偏见中创作的历史小说只能是二流的作品和廉价的神学。倘若如此,那么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也就沦为意识形态的神话,无法触及现代历史小说本身,对历史小说乃至小说本身抱着失望的态度。赫勒揭示了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的悖论性及其运用,认为他对历史小说的理解最终只是一种误解,“虽然卢卡契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皆过时了)能够适用于古典历史小说的细致分析,但是在后经典的现代历史小说的分析中,它根本不起作用”⑤。 赫勒对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的批判可谓切中肯綮。她深入洞悉《历史小说》文本中的内在肌理,不论对审美形式的分析还是对民主伦理政治的考量,都不乏启发性。她在肯定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的同时直击其悖论和现代困境,在批判中透视出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的可能性。不过,她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意识到他的历史小说理论的企图,即第一次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样式理论(Marxist genre theory),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反映论运用到文学样式分化的问题中。事实上,卢卡契关注的焦点不是历史小说具体的历史流变,而是把握最重要的理论及其普遍的文学原则问题。对此,詹姆逊审视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时,强调了形式与意识形态融合的意义。他认为,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关于内容的讨论也是形式的分析,对中间人物的分析属于结构主义对人物叙事功能的思考,因而他的文学批评文本都是加密的作品。历史小说作为新的形式和新的历史意识的中介,构成了一系列进一步的中介和转码,成为走向历史、政治、社会变化的中介,进而涉及经济本身,获得总体性的把握。詹姆逊的符号学分析不乏洞见,但他对历史小说的认识是盲目的,他未加反思地接受了卢卡契关于历史小说的非独立样式及其终结的观点,认为,“历史时刻中的每件事情如果都互相连贯的话,那么,历史小说本身作为一种形式也必然最终消失,因而历史小说在其逐步追求具体的总体过程中,冲破了艺术自身生存的界限”⑥。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小说》与《小说理论》都包含最后救赎、终结论式的大写的历史哲学观。 虽然卢卡契对历史小说包括小说的远景预测是最终消亡,但这种预测并未最终实现,而是预示了历史小说范式的转型。赫勒回应了纠缠卢卡契的“历史小说是否是一种独立样式”的理论问题。虽然她和卢卡契皆反对纯粹形式主义的历史小说观,但拒绝后者关于历史小说与普遍意义的小说毫无本质区别的认识。她对历史小说、普遍意义的小说和史学做出了相对清晰的区分,认为这三种样式都是虚构的,但是各自包含不同类型的虚构真理。普遍意义的小说作为艺术样式,并非必然在艺术的揭示性真理和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建立联系,当我们阅读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时,并不追问小人国是否存在,这种追问不关乎小说的真理。历史小说作为法国大革命之后兴起的文学样式,建立了历史现实与小说揭示性真理的某种联系,但其人物和故事大多是虚构的,所以历史小说的真理仍然是艺术的揭示性真理,而史学拥有的是逼真性的真理意义。因此,历史小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不是走向史诗,而是在后现代找到新的历史意识和表达形式。 以赫勒之见,后现代历史小说具有传统历史小说的某些特征,仍然实践着中间人物理论,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时代错误,对人民加以描绘。但它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呈现出后现代的历史意识和人类条件,拥有独特的审美形式。历史小说不同于诞生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喜剧小说,它是随着宏大叙事一起诞生的,司各特、托尔斯泰等传统历史小说家追求历史的必然性,体现现代性的求新意识,“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宏大叙事的视野,传统历史小说讲述着极为类似的关于现在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的故事”⑦。当代历史小说展现了不同的景观,它追求多元主义文学观念和偶然性、异质性的人类条件的表达。我们可以把赫勒关于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分析概括为五个主要方面。第一,当代历史小说捣毁了黑格尔关于理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理解,怀疑他所谓的世界历史个体的设想。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只有三个主要的世界历史个体即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他们通过征战把当时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当代历史小说家对善和罪恶的看法都脱离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视角,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不是军阀,而是艺术家、商人、绘图员、哲学家、学者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群。最重要的事件不是战争,而是冲突、输血技术、南海金融风暴等。第二,当代历史小说呈现出不同类型的人的图像。匈牙利历史小说家斯皮罗流露出一种阴暗的哲学人类学,他所描述的人不是有病就是天真的傻瓜;在美国历史小说家珀尔的世界中有着正派的男男女女,也有忏悔的人群;在美国作家利斯的宽恕世界中,人是最脆弱的,人的理解也是有限的。这些小说创作在类似的后现代历史图像中呈现出不同的人之图像。第三,当代历史小说抛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注重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叙述视角。譬如,利斯的《纸币阴谋》、英国小说家哈里斯的《庞培》、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玫瑰之名》等作品由第一人称单数“我”来叙述故事;英国小说家皮尔斯的《指路牌》从四个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西皮奥之梦》以古老的手稿对故事进行解码;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由一匹画中的马或颜色来讲述故事。第四,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封闭性世界不同,当代历史小说的文学世界是开放的。作为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它通过偶然走向结局,无论是悲抑或喜,都只是一种特有叙述的结局。因此,读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可以不接受现有成见,事实上时刻处于批判性阅读与解谜之中。不少当代历史小说具有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等流行文学元素,这些元素不仅吸引读者眼球,而且具有加密符码的深层的象征意义,“侦探故事用心理学语言来说是作为一个移置,用文学语言来说,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⑧。这些加密的象征符号期待着读者来解码,因而故事的叙述没有封闭性,没有最终的确定意义。第五,当代历史小说在历史时期选择、暴力理解与主人公类型方面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它有意识地而不是天真地反思时代错误,区别了现在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的叙述,把遥远的过去的叙述视为当代历史小说的重要选择,这主要体现在罗马帝国最后崩溃的时期和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这一段现代世界诞生时期。这两个时期显示出在暴力中崩溃、在暴力中诞生的特征,符合历史小说的题材与形式的类型特征,因为没有暴力就没有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突显战争的暴力、男人的勇敢、女性的无用,是宏大伦理政治的表征。而当代历史小说表明,暴力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它对主要叙述而言只是外在的,对主人公人格的道德价值也无足轻重,但是暴力无处不在,深深地铭刻在妇女、犹太人、异教分子等主人公的身体上,惊悚元素不仅是技巧,而且成为故事本身的内容。当代历史小说在后现代条件下对微观权力进行探索,表达了后现代政治条件下的形式意识形态意义。 赫勒认为自己的分析不是审美的视角,但她对当代历史小说的理解整合了后现代偶然性的历史意识和多元化的审美形式,显示出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的特质。就历史小说而言,赫勒与安德森有相同旨趣,后者认为传统历史小说主要是民族身份的建构,但二战之后兴盛的当代历史小说使得卢卡契的理论框架不再适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突变,“新的形式标志着后现代的来临”⑨。虽然赫勒批判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并肯定后现代历史小说的辉煌,但她并未完全拒绝其对传统历史小说的洞察力以及对当代历史小说阅读的某些启示,而且她不同于安德森仅以詹姆逊的“形式意识形态”理论审视后现代历史小说的本雅明式的寓言批评。她从人类存在的后现代条件及其后现代历史意识的角度,思考当代历史小说的存在方式和人类学意义,为当代历史小说存在的合法性辩护,否定历史小说终结论,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正如她所说,“我所提出的历史理论能够被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形式”⑩。 面对当前国内外相对薄弱和陈旧的历史小说理论,赫勒的后现代建构透视出创造性的活力与当代阐释的合法性,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可能催生历史小说讨论的热潮。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独特地位,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也展露出多元化态势,网络历史小说亦别具特色,历史穿越我们也耳熟能详,但历史小说理论相对落后,远远赶不上创作的步伐,这严重地限制了历史小说的研究。赫勒的历史小说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理论思考与文学批评。但是,她对历史小说作品的选择主要考虑后现代哲学思想的适应性,她对侦探小说酷爱有加,并吸纳科林伍德关于侦探小说反映历史意识的观念,但不得不放弃柯南道尔、克里斯蒂等人的小说作品研究,因为当代历史小说更适合其理想的历史图像和人之图像。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同化了她所批判的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和现代美学不可根除的悖论。而且,她揭示的当代历史小说特征,大多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所具备。倘若如此,历史小说的独特意义何在?这似乎退回到了卢卡契的思考之中,只是绕了一个历史之圈而已。或许这是理论演进的荒诞,是后现代人类存在条件所无法逾越的悖论。尽管如此,只有通过卢卡契和赫勒的范式融合,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窥见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的复杂机制。 ①Agnes Heller,Cserniservszkij Etikai Nézetei,Budapest:Szikra Kiadó,1956,p.133. ②Agnes Heller,A Theory of Feeling,Assen:Van Gorcum,1979,pp.196-197. ③ Paul de Man,"Georg 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in Blindness and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59. ④Georg Lukács,The Historical Novel,trans.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3,p.36. ⑤Agnes Heller,"Historical Novel and History in Lukács",in Agnes Heller,Ferenc Feher,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0,p.286. ⑥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第31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⑦Agnes Heller,"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in John Rundell ed.,Aesthetics and Modernity:Essays by Agnes Heller,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10,p.93. ⑧Agnes Heller,A Short History of My Philosophy,Lanham:Lexington Books,2011,p.135. ⑨Perry Anderson,"From Progress to Catastrophe:The Historical Novel",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33,No.15,28 July,2011,pp.24-28. ⑩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2,p.316.标签: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