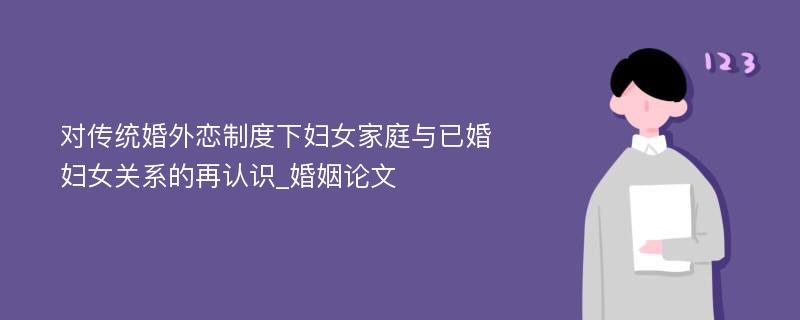
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问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娘家论文,传统论文,关系论文,外婚制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1)05-0017-10
一、前言
学界对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问题的理解,嵌入到对姻亲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一种是宗族模式的分析路径。它将姻亲关系作为相对于父系继嗣关系的“副关系”来分析,主要关注它与父系集团和父系原则的关系(李霞,2005)。该研究倾向于认为,姻亲关系对父系原则具有潜在的冲突。弗里德曼(1989)认为,婚礼这一仪式表明新娘的身体、生育力、家务服务向丈夫家庭的转移,她从此在财产关系和法律意义上都与娘家没有关系,而且娘家就丧失了对她的大部分权力,她如果成为寡妇,她的再嫁也由婆家决定。
但一些学者通过观察农村亲属制度的实践而非制度层面,从而对弗里德曼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可概括为实践主义的路径。植野弘子(2000)认为,出嫁女这种向丈夫宗族的转化与同化并不完全,即使在作为象征转换结束的婚礼上,一些礼仪也仍然标志着新娘与其出身家族继续联系的纽带。Ahern(1974)发现,娘家对出嫁女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一些仪式上得到象征性的表现,譬如娘家在女儿夫姓宗族的一些礼仪场合具有较高的地位,在妇女做寿和她的葬礼上娘家人的尊贵地位更是体现了娘家的权力。
朱爱岚(Judd,1989)通过论述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认为情感因素对于“娘家”而言,较成员资格和财产更为重要。古迪(Good,1990)认为,对出嫁女来说,亲属制度并不完全是父系的,不能忽略妇女与娘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力量。李霞(2005)则干脆认定娘家是出嫁女建构小家庭不可或缺的可利用的关系资源。刁统菊(2007)认为姻亲关系是对婆家、夫姓家族的离心力。阎云翔(2006)发现,农村家庭分家之后,姻亲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甚至许多人将姻亲看得比宗亲还重要。李银河(2009:135)也注意到,由于男权制残留的结果,仍有六成以上的农民认为宗亲关系重于姻亲关系,但出嫁女与娘家的联系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
实践主义分析路径看到了出嫁女与娘家关系在实践和行动中的复杂性、灵活性,以及它与制度层面表达的不一致性;却未能揭示出这种关系特性背后的动力因素,即出嫁女的归属。
根据笔者在湘南传统村落调查的经验,女儿出嫁之后,跟娘家的关系在制度层面是亲戚与亲戚的关系,在生活层面则因为情感的联系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出嫁女如何把捏与娘家、婆家的关系及各自的轻重,以完成自己对夫姓家族与村落的归属;同时,出嫁女在归属婆家的过程中,娘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文章要考察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在传统外婚制下,娘家在处理与出嫁女的关系上,并不是被动的,而存在积极主动的层面,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娘家是出嫁女归属婆家的坚强后盾,娘家针对女儿及其婆家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诸如督促和支持女儿归属婆家,敦促婆家接纳女儿,无疑都是为了女儿更好地在婆家立足,更好地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
本文基于2006年7-8月和2009年4-6月对湘南地区两次参与式调查的材料写作而成。湘南位于南岭山脉的湘赣粤交界处,自然条件封闭,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家族社会结构(杨华,2010)。笔者主要调查的村落是水村,同时还走访了该区域内其他村落,总计访谈60名16岁至89岁的妇女,20名18岁至85岁的男子。水村地处湘南最南部,地势较低,共有338户,1760人口,户均5.2人,辖12个组,分布在8个自然湾,其中5个自然湾为杨姓村民居住,其余皆为曾姓自然湾。杨姓与曾姓人口对半,两个姓氏即为两大宗族,自古有通婚和竞争的习俗。
二、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的制度规定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叙述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一个是娘家如何对待出嫁女,二个是出嫁女如何看待和体验与娘家的关系。
妇女在婚姻仪式中,已完成了在身份与角色上对娘家“外部化”,脱卸娘家色彩进入婆家,便因此携带上了丈夫家族、村落的印记。因此,对于娘家而言,出嫁后的女儿就是外姓家族的人,在信仰层面就具有外部人的危险特质(李霞,2002)。这一点在妇女生育上体现得很明显。
按照水村当地的风俗,妇女生小孩必须呆在婆家,在娘家生小孩会带来各方的恐慌。娘家人认为,小孩是妇女婆家的人,到娘家出生自然就将婆家的邪气带到娘家来了,这样会给娘家、家族和村落带来晦气,不仅娘家父母不会答应,娘家村落里的人也不愿意。婆家则认为,在妇女娘家生下的小孩,不可避免地粘带上了外族人的邪气,这对于婆家来说是危险的。
避免的措施很多,其中一个是快到临产的那段时期,婆家、娘家都会让妇女少回娘家,以防意外。如果妇女在娘家“发作”①,且娘家与婆家相隔不是很远的话,即便是深更半夜也会把她送到婆家。而若实在送不回婆家,必须在娘家生下的话,也得在侧房或医院接生,且生小孩后,母子在一个月内不进娘家的堂屋。这些措施无非是要将外人连同邪气挡在家门之外。如今,由于外地婚姻,或未婚先孕,在娘家接生的越来越多,而将一月内不登娘家堂屋的规矩展演得淋漓尽致。
在制度层面,娘家也不再把出嫁的女儿当自己人看待。娘家与出嫁女的实质关系,不再是因为出生、养育而自然天成的父母与女儿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连接纽带也不再是做女儿时的血缘亲情,而是“亲家”。娘家之所以还能与出嫁女有关系,完全是因为娘家与婆家结为“亲家”的关系。而且,娘家这个亲戚还不是妇女的亲戚。在与公婆没有分家前,妇女与娘家的关系嵌入于公婆与娘家的关系中,是婆家众多亲戚的一门亲,且不摆在重要位置;分家之后,小家庭最重要的亲戚是妇女的娘家,但也仍不是妇女的亲戚,而是丈夫的岳父岳母,妇女依托丈夫与娘家父母有亲戚关系;等到年老,妇女与娘家的关系,变成了儿子与娘舅家的亲戚关系。
因此,在与自己娘家的亲戚体系中,出嫁女本身不是自主的行动者和主体,她需要依托他人的名分才能与娘家建立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她本身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已经“结亲”,妇女作为中介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重要。事实上,在农村,人们之所以在女儿出生后,无论是不悦还是欣喜,都会接受,通常说的是,“多一个女儿,多一门亲戚”。
娘家把出嫁女当做亲戚,妇女更要把娘家当亲戚。“过人家”在湘南水村,意思就是“走亲戚”,对于妇女而言,一辈子所“过”的“人家”只有娘家。因此,妇女回娘家,就是走亲戚,把娘家当亲戚来走,也就是只能在年节时与娘家有些仪式性的往来,而不能再将娘家当家来住。
在婚后的前两年,妇女除“过人家”外,还有事没事就往娘家跑,有时一次住上十天半个月,还没有把婆家当家,一年大半时间在娘家住,这与妇女从做女儿向做媳妇的过渡期有关,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种状态显然被人们所理解。但有两点已经改变,一是此时频繁地走娘家,必须经过公婆同意,在分家之前尤其如此,她的行动并不是十分自由。另一点是,妇女回娘家的心态已经改变。做女儿时,就已经深感父亲的家不是自己的家,出嫁之后,这种感觉就更甚。如果家里只有弟妹的话,尚可毫无顾虑地在娘家吃住,没人会有意见,但如果有兄嫂、弟媳,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会有被监视、被排斥的感觉,并可能因此造成娘家的婆媳不和。
妇女对娘家村落的感觉也逐渐淡漠。虽然在口头上,婚后前几年还将“我们湾”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娘家村落,但许多受访对象称,虽然回娘家村落有亲近感,但每回一次就增加对村落的陌生感。特别是,当妇女生完头胎以后,还频繁回娘家,娘家村落的妇女就会用异样的眼光审视你,会被认为是没有将婆家当家,这是有问题的。因此,随着妇女在婆家逐渐适应,将婆家当家以后,娘家的村落在她们的口头中就不再是“我们的湾”,而是“你们的湾”或“他们那个湾”。如果一个结婚五六年的妇女,依然将娘家村落称为“我们湾”,若被娘家村落的人听到会很别扭,碰到好事者会给予纠正。这时,妇女回娘家的次数也会明显减少,除了年节、父母生日及其他事由,妇女一般不回娘家,即便回娘家,也不会住得太久。如果娘家娘过世后,女儿几乎没事就不上娘家了,即便是年节要过人家,也多差儿女去。
妇女尽管在感情上要与娘家父母、兄弟更亲,但也不能因此一味地顾着娘家、向着娘家。“千百年家门,六十年亲戚”,娘家再亲,至多一两辈人的往来,而家族、村落的家门关系则是永无休止的;“人死人埋,靠家门”,村落的主要生活还是在家族、熟人社会中展开,妇女需要掂量关系的轻重,在娘家、婆家(家族、村落)中选择自己的归属。
妇女要归属于丈夫的家族和村落,就不能依照自己的情感偏好来行事,而须遵循村落既定的行为法则。比如在平常,若非特定“过人家”的日子,妇女从集镇上买回“新鲜”,若只顾着孝敬自己的亲爹娘,而忘了公婆,后者及村里人就会有意见,她们会说,“人家那边有媳妇,要你买什么?”懂道理的娘家娘也会教导女儿,不能冷落了公婆、坏了规矩。若有妇女能将娘家娘接到家里常住,在对待公婆上至少也要“大面上过得去”,才不会遭惹闲话。
在八九十年代,水村与周边村落常常因争夺灌溉、山林、坟地、地界等发生纷争,因不可避免会涉及妇女的娘家与婆家的关系问题。此时,妇女及家庭能回避则尽量回避,能从中调解、化干戈为玉帛更好,倘若不幸,冲突激化到需要妇女及其家庭站队时,明智的选择是,公然站在夫姓村落一边,与娘家划清界限。此举很可能会断了与娘家的亲戚往来,但换来的是,妇女更能被夫姓家族与村落所接受。
虽是亲戚关系,却并非意味着妇女与娘家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更不意味着她们的情感纽带被完全否定。一方面,娘家还要承担女儿在夫家某些行为的责任,这与娘家在妇女做女儿时的教导连在一起。女儿在婆家会不会做媳妇,会不会为人处事,遵不遵守妇道,婆家村落对女儿的评价如何等,很大程度被认为是与娘家的“操教”有关。婆家评价好的,娘家有“名气”(声誉),婆家人(家族、村落)到哪都说娘家的好话。若是妇女做得不好,特别是在两性上出现问题,娘家更是摆脱不了干系,主要的责任和骂名都由娘家来承担。因此,娘家仍然对出嫁女儿有操教的责任。更何况,婆家对女儿的任何评论,最终都会影响到女儿在婆家的归属问题,娘家对此不得不操心。所以另一方面就是,娘家出于对自己女儿的情感所依,在日常生活中会操心女儿在婆家的归属问题。父母常念叨,“养个女不指望别的,就指望她能够在婆家好好过日子,不要让做老子老娘的操心。”
三、娘家督促出嫁女归属婆家
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有着情感和价值上的期待,对儿子的期待是成家立业、传递香火,这些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情感方面不是很彰显。父母对女儿则完全是情感层面的期待,没有其他的奢求,只希望她有个好归属。对于尚未完全归属,或归属不好,或难以归属的女儿,父母则需要督促女儿完成对婆家的归属。
对于新出嫁的女儿,操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儿每次回娘家,父母首先要问的总是“跟家娘(婆婆)还说得来吧”、“跟家娘相处得怎样”等问题,对于父母而言,这些是他们最急于了解的,他们希望尽快掌握女儿在婆家的状况,当然他们还会从侧面了解或证实相关情况。无论情况如何,父母尤其是母亲,都会有一番新的操教。母亲在这个时候的操教非常奏效,一方面是缓解女儿因为身份、角色调整带来的紧张和不适应,给予心理调适;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学会如何处理在新环境中遭遇的种种问题。
在处理与公婆的问题上,远不仅仅限于在婚后一两年的教导,这始终是母女会面的话题,在多妯娌的家庭,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因为这涉及如何对待老人、分配养老,以及处理妯娌关系的问题。若与娘家嫂子相处较好,嫂子也会扮演传授经验的角色。在娘家眼里,女儿在婆家与近亲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她能否在婆家过得安心、幸福,关切到她在婆家的归属。若这些关系处理得当,则可能尽早地融入婆家,完成角色的转变,否则就会推迟她在婆家的立足。
随着女儿在婆家呆的日子的增长,娘家也会越来越关心她与家族、村落熟人社会的关系。女儿在婆家村落过得如何,可以从她回娘家的次数看出,若在女儿生了头胎孩子后还频繁地回娘家,娘家娘及其他妇女就会生疑,认为要么两口子不和,要么与公婆、妯娌关系不好,或者在湾子里没有“夹”到人,总之是没有把婆家当家。这对于一个出嫁女来说是大问题。因此,在村落习俗中,一般不会让出嫁女隔三差五地回娘家,认为女儿有事没事回娘会影响娘家的声誉。
笔者访谈的水村平屋里湾就有一两个外嫁女结婚后若干年仍然在娘家—婆家来来回回,给人的印象好像没有成家一样,这被很多妇女看不惯。娘家家族里的人很生厌,见了她们只是象征性地招呼一声,懒得多理会。不少妇女跟我说,“要是我的女儿也这样(常回娘家),老子们会放她的手?用鸡子板来赶。”村落的这种风俗及人们对待常回娘家女儿的态度,会让许多女孩自觉地放弃对娘家的情感依赖,从而强迫自己更早地适应婆家生活。
懂得事理的娘家娘也就不会感情用事,即不把女儿天天拽在手心,而是操教女儿如何在婆家安家、打点村落里的关系,首先就是要“夹人”、“从人”②,多去串门、聊天,与人建立关系,湾上有什么事要多去“凑热闹”(即搭帮手),而不是有事没事就回娘家。老人跟我讲,“女仔儿跟娘家老子老娘再亲,也是亲一时半会,不会亲一辈子,该亲的还是婆家湾上的人。”
有这么个案例,青梅是水村平屋里湾的媳妇,与各家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在湾上也是“有说份”的妇女。她的一个小姑子嫁到另一个乡,公公是个老封建,还保守着妇女不应该到处抛头露面的老思想,因此她与村落其他妇女的交往就受到限制,于是跟娘家嫂子讲这个事(娘家娘早已过世)。青梅跟小姑子说,“一个妇娘人,嫁到哪里,就是哪里的人,就要‘从’哪里”,她鼓励小姑子不仅要多去串门露脸,而且在湾上还要积极地帮忙做事,只有这样才能落得下脚,别人才不会挪孽你。
有些冥顽不化的妇女,一般由于个性太强,不容于婆家,也难以融入婆家,那么娘家就会采取强硬措施,不再是软绵绵的说教了。平屋里湾出嫁女的外梅就有此遭遇。该女子书没读几年,脾气还特犟、个性要强。一到婆家就跟婆婆、兄嫂关系搞不好,经常吵得整个湾子都乌烟瘴气,也不会在湾子里“夹人”。因此出嫁七八年,在湾子里还没有个要好的人,平常基本上没有人跟她搭讪、玩耍,她只好没事就回娘家。娘家娘心疼女儿,舍不得说重话,马花等人给脸色看也不多顶用。对于自己女儿的这些情况,外梅的父亲不是很清楚,一日,马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对外梅的父亲说了真实情况。听后,外梅的父亲连夜赶往女儿家,没说一句话,开头就是一巴掌打将过去,然后才告知被打傻的女儿为什么挨打。此后,外梅就不多回娘家,实在有事要回,也选择在晚上不被人瞧见的时候,并且开始收敛自己的个性,搞好与湾上人的关系,融入妇女圈子。外梅对我形容说,“之前看到老公跟人打牌、不做事,自己就气得要死,几次还拿他们的牌给撕烂,弄得人人都对我有意见,讲我太不会做人,现在我自己有时也上人家家里打牌,跟湾上人的关系还蛮好。”
个性要强、脾气古怪且不会做人的妇女,不仅自己难以融入婆家,无法从中获得归属感,同时还因她们的“强势”而侵害他人的归属,使人家感觉不到安全。对于她的婆婆和妯娌来说尤其如此。现在农村普遍出现媳妇比婆婆厉害的局面,若关系处不好,更加剧了婆婆对自己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敏感和担忧。如果媳妇确实特别厉害,婆婆又制服不了,在水村,婆家就会出一招比较狠的,“待外世”,意思就是将媳妇的“厉害”捅到她的娘家那里,让娘家到婆家来处理事情。这是“以夷制夷”的做法,一般比较凑效,当然出手时要谨慎。娘家(包括家族)因对女儿归属及自身名誉的重视,而会对罔顾自己与他人归属的女儿施加压力,使婆媳关系趋于缓和。且娘家的家族越大,“待外世”的效果越明显③。
为了督促女儿对婆家的归属,有时娘家会以断绝关系相威胁,这种激烈对抗通常发生在女儿婚变之时。女儿因故要与丈夫离婚,而娘家则不希望她的婚姻破裂,从而引发对峙。在娘家看来,女儿的离婚,不单单是娘家要承担部分责任,更重要的是离婚时女儿失去了原来的归属。从而使其最终归属成为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尤其是那些年龄较大、已结扎的妇女,要想再找户靠得住的人家安度晚年,着实比较困难,即便能与人结婚,没有亲生的儿子亦无法在后夫村落安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什么天大的理由,也大不过“过日子”,不值得、也不应该离婚:因此,为了保证妇女的归属,无论婚姻、家庭乃至村落、社会发生什么“病变”,只要不到迫不得已,妇女就不应该提出离婚。前提不论,一旦妇女提出离婚,娘家就会向自己的女儿动刀子。
水村杨姓近三十年有5例出嫁女主动提出离婚的个案,其中1例的妇女是被丈夫虐待。跟娘家商量离婚事宜,未允,娘家家族人去了出气后,两口子分居未离婚;还有3例夫妻不和,妇女提出离婚,被娘家及婆家说服而没离成。唯一主动提出离婚且离成的是平屋里出嫁女秋风。这几个妇女都在35岁左右,都生育了子女——即是说她们能安身下来。
秋风嫁至邻乡,夫家在省道旁边,交通便利,做小生意发了财,夫妻俩和两女一儿生活了十几年,相安无事。到九十年代中期,秋风的男人在外边找了个女人,并在镇上租套房子过着同居生活。秋风不让,于是矛盾闹得厉害,娘家一大帮人还向女婿兴师问罪了。调解的结果是,她的男人继续跟外边的女人住在一起,但秋风与丈夫仍然是合法夫妻,不离婚走人,在家看孩子,男人答应每月给秋风及孩子生活费。对于这样的结果,娘家人是满意的,因为终止了离婚。一开始,秋风也听娘家人的话,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如此生活一年半载之后,秋风总觉得不甘心,认为自己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提出离婚,娘家人百般阻挠也无济于事,甚至提出只要她离婚,她就不要再回娘家了。但秋风义无反顾。她的娘家娘为此受不了打击很快病倒去世。
马花是秋风娘家的叔伯嫂子,她全程参与了这个事,她认为离婚错在秋风,因为,“人家男人还愿意上你的房门,说明还愿意跟你过,你提出离婚,就是你不‘过日子’了。”马花的逻辑是归属的逻辑,只要归属还有一线希望,妇女就不能主动放弃归属。在她那里,“过日子”就是在婆家立足、安生,不安心“过日子”,就是妇女不“本分”的表现,因而过错在她自己。
四、娘家支持出嫁女归属婆家
女儿能否在婆家站稳脚跟,她在婆家有没有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娘家对女儿的态度有关。娘家对女儿足够重视,在婚前婚后给予女儿各方面的支持,那么婆家对这样的媳妇也不会过于怠慢,相反,若娘家不将女儿当回事,那么婆家也就不会将这个媳妇当人待。这是农村一般的逻辑,说明娘家的支持在女儿的归属中占很大的分量。娘家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仪式性支持,一个是物质生活层面的日常性支持。
仪式性支持主要表现在女儿出嫁、看月婆、公婆丧葬等具有仪式象征色彩的事件上。在这三个事件中,娘家的不同行为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儿在婆家(包括家族、村落)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如此。
首先在女儿出嫁时,有两个细节具有决定性和象征性作用,一个是嫁妆的丰厚与否。嫁妆越多,代表着娘家对女儿越重视,因此意味着娘家在以后日常生活中,对女儿的照顾与支持也会不遗余力,此一点婆家不敢轻视娘家之力量④。另外,嫁妆的多少,决定了婚后对财产的决定和支配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在婆家的地位(阎云翔,2006)。一个在女儿婚姻中支不起嫁妆、甚至还想从彩礼中捞一把的家庭,对女儿归属的支撑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湘南农村,无论家庭境况如何也要为女儿准备嫁妆,也就使得嫁女儿永远是亏本的“买卖”⑤。
嫁女儿中的另一个细节更具象征意义,是出嫁当天有没有“上客大元”陪送,即女儿的父亲有没有送女儿出嫁。若父亲早亡,也须有家族里的长辈替代。上客大元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拜会亲家,意思是从此两家结为亲戚,而它的象征性也是表示娘家对女儿的重视。上客大元此行就是要告知女儿的婆家:我们娘家既然把女儿摆在如此之重的位置,那么到了你们婆家,就看着办吧。因此,无论有没有婚姻的仪式,在结婚当日,父亲都会陪同女儿到婆家,女儿嫁至外地,按惯例也如此。否则,婆家会看不起这个媳妇。另外,上客大元若不亲自来结亲,那么亲家也会感觉到对他们的低看,也会有意见,并可能最终将气撒到媳妇身上。
正因为“上客大元”在婚姻仪式中对女儿归属的象征性,在八九十年代,许多父亲为了反对,或者表示对女儿自谈婚姻的不满,就刻意不出席女儿的婚姻仪式。
第二个仪式是看月婆。娘家“看月婆”,就是探望生完孩子之后的女儿,尤其是头胎之后,娘家(及家族)的这一行为十分重要。对于娘家来说,看月婆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女儿给你婆家生儿育女,看你如何对待她,若善好则加勉,若不满意就要敦促婆家善待女儿。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娘家的上客大元因故没有出场,女儿因此被婆家瞧不起,那么看月婆就是一个直接的弥补机会,它同样起到娘家对女儿支持的象征作用。
上文提到的外梅,她现在的老公当年是个小混混,两个人自谈,父亲杨广生不同意这门婚事。且因为是未婚先孕,因此女儿出嫁既没有仪式,也没有嫁妆,只是拿了个证,他也没有去做“上客大元”。婆家自然是看不上这个媳妇,婆婆甚至还辱骂外梅是“吊块腊肉”自己送上门来的烂婊子⑥。待到女儿生了头一胎,杨广生的气还没有消,他甚至阻拦妻子去看月婆。后来,一些叔伯兄弟媳妇对他说,“本来人家就看不起(你家女儿),你还不去看月婆,人家更加会瞧不上”。这样,一个家族的妇女才提着礼品去看月婆,以此给外梅在婆家打气。
娘家真正给女儿壮声势,是在女儿公婆的葬礼上。女儿公婆的葬礼,娘家客人(父姓家族的人)来的越多、声势越浩大,给婆家的震撼就越大。这个样子,主要是做给两类人看,首先是女儿的妯娌、夫家兄弟,他们是女儿在婆家生活的重要关系;另一类人是婆家的家族和村落,女儿能否在婆家立足生根,这些人是关键。因此,娘家的声势是要告知婆家的人,我们家的女儿是不可欺的。受访人一致宣称,“家娘(婆婆)、家元(公公)老了,娘家人都要去,去的人越多,挂孝的越多,随的礼越多,闺女在婆家的地位就显现出来了。”
娘家在仪式上对女儿的支持,更多的是给予女儿精神力量,一方面它们象征着娘家对女儿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它们公开展示了娘家作为女儿后盾的力量,从而使女儿和婆家心里都有个底,即娘家并没有舍弃自己家的女儿。这样,女儿就可以更加从容、更有底气地融入婆家、介入婆家生活,而婆家(家族、村落)需要以更加宽宏的心胸予以接纳和包容。
当然,正如上文提到,有时候女儿会仰仗身后有强大的娘家,在婆家会过于嚣张,从而引起婆家(家族、村落)的不满。遇到这种情况,婆家只好“待外世”⑦。
娘家除了上述仪式性的支持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对女儿家的支持,也是构成女儿更好地归属婆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当分家所造成的原来大家庭的合作终止之后,娘家成为小家庭最重要、也是最可能提供支持的关系资源(李霞,2002)。这种支持具体包括在农活时帮着干活、盖房时来帮忙、帮女婿介绍活干,以及钱物方面的给予与借贷。
日常性的支持,目的在于使女儿在夫家的生活更加顺意和体面,也更加安心,但娘家的支持须保持一个度,不让女儿过于依赖娘家,而荒废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延误了她对婆家的归属。而且,娘家对女儿各方面的支持,是出于情感,而非制度性的规定,因此是有限度的。另外,娘家支持的限度还表现为它的间歇性,而不是时刻体现于日常生活中,这也使得妇女不能过分依恋娘家而忘了自己的真正归属,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妇女更早地融入婆家,在婆家寻求生活上的支持资源。
五、娘家敦促婆家接纳出嫁女
除了上面讲的督促和支持之外,在女儿的归属问题上,娘家还会直接与女儿的婆家打交道,给婆家施加压力,敦促他们接纳自己的女人,为女儿在婆家营造一个相对宽松、温馨的归属环境。督促的方式是,娘家直接派人到婆家“商讨”问题,人数的多少视问题的性质、程度而定。
上面叙及婆家“待外世”以理顺与媳妇的关系,其实当媳妇在婆家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遭人欺负,也极易“待外世”,在娘家倒苦水,希望娘家出面解决自己遇到的麻烦。但多数时候,娘家并不愿意掺和女儿在婆家的事,尤其是与丈夫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每当女儿为了这些事向娘家倾诉时,往往是自讨苦吃。因此,为了眼不见、心为静,父母一般不会把女儿嫁得太近⑧。只有在感觉自己女儿真正受到了欺负,威胁到了她在婆家地位,或者婆家表现出对女儿娘家的蔑视时,娘家才会有所行动。
在女儿与婆家的矛盾中,不同的关系,娘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与策略。在与村落熟人社会的矛盾中,如果女儿觉得受到了欺负,而婆家及家族却没有为她出气的话,她就会“待外世”。但娘家在这个关系中不会强出头,因为涉及到的是女儿婆家与另一个家族的事情,娘家一般是隔岸观火,即自己不出面,而将女儿“待外世”的事以适当方式“通告”婆家,以此使婆家感觉到压力后采取积极措施。这就是说,女儿在婆家的主要保护网——家族没有起到给予女儿安全感的作用,娘家只是略施点压使其运作起来而已。下面的案例具有典型性:
曾莉香是平屋里二房的媳妇,很早就守寡了,夫家兄长后来也去世,因此她遇到困难多半是求助于娘家。2008年下半年,她与本湾香高的老婆秋雨一起在邻镇打工,期间她知晓秋雨还与之前的男朋友有暧昧关系,并口无遮拦地说了出去。话被传到香高耳边,香高说莉香散布谣言,给她扇了几个巴掌。莉香觉得受了委屈,就将事情捅到娘家兄弟那里,希望能出口恶气。但娘家兄弟并不鲁莽,而是打电话给莉香夫姓家族里的一男子,并明确地说,这件事是他们“屋里”的事,娘家是无权干涉的。对方清楚亲家的意图,很快纠集家族十余名男子找香高理论,以香高请客吃饭了结此事。
若是与家族内的关系,如涉及到堂兄弟、叔伯兄弟、兄弟及丈夫、公婆,娘家就更可能插手此事,理由很简单——这显然是家族内部对女儿的排斥,女儿在夫家村落已无求助之对象,娘家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出面。妯娌或兄弟家庭之间的矛盾最频发,妇女也最容易感受到在大家庭里的欺辱、轻视,也就容易“待外世”,并可能引发各自娘家的对峙。妯娌之间的争吵,在娘家看来是女儿的地位之争,也是娘家的气势与名誉之争。因此,任何一方只要感觉到对方在小看自己,娘家的反应都很大,出头的几率在各类关系中是最大的。
妇女在与丈夫、公婆发生矛盾后“待外世”,娘家会相对谨慎些,没有像针对兄弟、家族那样无所顾忌。顾虑之一是,妇女与丈夫、公婆是最近的人,尤其是丈夫,要与之生活一辈子,若将关系闹僵,女儿以后更无法在婆家立足。所以,娘家在敦促婆家接纳女儿时,总是要秉持一条原则,即归属的原则。也就是说,娘家出不出头,采取什么方式出头,最终都是为了女儿在婆家的归属,而不是仅仅出气、争脸。水村的老人就讲:
女儿,跟人家了,有矛盾那也是人家的家庭事务,用不着其他家庭介入。如果这个女儿,在家里头受了欺负了,娘家的兄弟哥,替姐妹出气。像这样出气,就容易闹出更大的纠纷。都没有好结果。亲家是一刀切不断的亲戚,不到闹翻脸的时候不能闹翻,一闹翻脸(女儿)就没法在这里生活了。
因此,为了归属,有时娘家前往婆家不仅不能出气,反而还要忍气吞声,特意长婆家的脸、灭自己人的威风,且这被看做是娘家为女儿出头的最高境界。笔者调查到,凡是娘家年轻人多,而又不听老年人言的,容易冲动地纠集一起去婆家找茬,最后无一例外都是两败俱伤,最为严重的是妇女因此无法再在婆家呆下去,不得不离婚。水村前几年就出现过两例这样的情况:
案例1 水村老屋冲湾曾二清有个二女儿,嫁在水村西边的柳湾,在那生活很不顺畅,婆家看不起。尽管生了个儿子,人家仍然不当回事儿,老公懒散,还有外遇,对她爱理不理。这边娘家知道情况以后,就想替女儿出气,领了身强体壮的兄弟哥、叔伯上十人,想逮住女婿打一顿。结果对方也是大户人家。到人家湾里出气,人家也一呼百应,结果没有打到人家,还被轰了出来。之后,男人对女儿更加不好,女儿没法再在那生活,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只有离婚。
案例2 大屋里的杨香歌,嫁到邻村,离娘家只有几里的路程。结婚时间不长,还没生小孩。在家过日子,男人发现这个妇女有很多毛病,就看不起她,两口子经常生气。娘家人去了一班子人,把家里东西砸了个稀巴烂,随后扬长而去。气是出了,女儿在那怎么生活?男人进一步看不起她,最后离婚。
有经验的老道做法是,娘家父亲或家族会办事的人亲自“拜访”婆家,在婆家不动声色,首先劈头盖脸地把自家的女儿猛批一顿,然后检讨自己操教无方,望亲家见谅,同时也请亲家帮着自己操教。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婆家有了面子,女儿在婆家可以更稳地立足,而娘家则松了口气,也会得到通情达理的好名声。娘家的另一个顾虑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底气”去兴师问罪,这个底气就是自家的女儿有没有为亲家生下一儿半女,特别是儿子。若没有这个底气,即便女婿、亲家对女儿有着明显的欺负、虐待行为,娘家也爱莫能助,只能看着干着急。甚至要讨女婿、亲家的好,以期女儿在夫姓家庭、村落立足。下面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水村杨云华的女儿不会生孩子,先嫁一家,因不能生育而离婚。云华对外宣称是女儿没有跟女婿“睡觉”。嫁第二家又过两三年,仍不见下蛋,外边也就都知道实情了,“不可能又不睡觉吧,你这父母怎么教育的?不可能不睡觉,你生闺女就是给人家生育的。”于是婆婆很看不起她,经常叫儿子再找个女儿,然后与她离婚。而娘家这边则说给他们抱养一个儿子,由娘家来抚养,婆家不愿意,两亲家的关系不好。云华希望维持女儿的婚姻,因为再离就嫁不出去了,于是对女婿就不好发脾气,更不能动手打,“一打就打掉了,更生分,日子没法过,只能离婚”。便把女婿叫过来说好话,好好招待,从感情上开导他,说这是女婿的命,叫他认命。现在关系还在僵持着。
所以,对于女儿的归属以及娘家对婆家的敦促权力而言,有没有“外孙(甥)”是关键。有外孙(甥),女儿就有很好地归属婆家的基础条件,娘家则有敦促婆家接纳女儿的底气,不至于使女儿的婚姻过于不稳定及生活过于不如意。这样,在这方面,娘家既有责任督促女儿生育儿子,并承担不能生育带来的后果,又有动力督促女儿生育儿子。当然,若是在结婚后的一年半载遭遇此等事,也就不存在底气的问题,因为此时还没有生育的问题。
女儿的婚姻问题是归属的重头戏,婚姻若不稳定,也就无所谓归属。因此,有外甥(孙)的娘家会对女婿看得很紧,若女婿嫌弃女儿或有外遇要与女儿离婚,娘家大动干戈就在所难免,且有当地的舆论支持。若是妇女在婆家自杀而亡,娘家就会来“打人命”。打人命后的归属,是打出来的归属。
六、结论
透过上文的叙述与论证,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妇女出嫁后,与娘家的关系在实质上已经从做女儿时的亲子关系,转变成了制度层面的亲戚关系,出嫁女在心态、行为原则上都较做女儿时有很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如同宗族模式的分析路径所认为的那样,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并不重要,或者说姻亲关系是与父系原则、父系集团相矛盾的,有着潜在的冲突。出嫁女依然与娘家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她顺利地归属于夫姓家庭、家族和村落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妇女出嫁后,娘家并没有断绝与出嫁女的关系,而是依然与她及其家庭、家族和村落发生着频繁且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如实践主义的分析路径所认为的那样,娘家是出嫁女为建构小家庭可资利用的一支力量,姻亲关系是妇女对婆家、夫姓家族的分离力量。娘家针对出嫁女的所有行为,都不是为了将出嫁女牢牢地拽在手心,也不是要将出嫁女及其小家庭从其夫姓家族、村落里剥离出来,更不会为了出嫁女小家庭的利害而要与其夫姓家族、村落做生死斗争;无论是督促出嫁女归属婆家,还是支持出嫁女归属婆家,抑或是敦促婆家接纳出嫁女,娘家的一系列行为无不是直指出嫁女的归属,只要是有利于出嫁女尽早、尽快、尽善、尽美地归属于夫姓家庭、家族和村落,娘家就会尽拳拳之心而为。
第三,所谓出嫁女的归属就是要在夫姓家庭、家族和村落里立足和安身,获得稳定的社会位置和扮演相应的角色,从而拥有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能够充分地享受和体验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娘家是妇女获得稳定的归属的坚强后盾。
第四,在传统外婚制下,娘家在处理与出嫁女的关系上,并不是被动的,而存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层面,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其内在的基本逻辑是出嫁女的归属。
总而言之,从出嫁女的人生归属的角度,去探讨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妇女与娘家、夫姓家族和夫姓村落的关系状态,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避免了宗族模式和实践主义两条分析路径的片面性,从动态、多维的角度去透视娘家行为的本质——它非表面的是非利害,而是涉及到出嫁女一世人生幸福的“归属”。
[收稿日期]2011-08-03
注释:
① 当地用“发作”来形容妇女临产前的身体反应。
② “夹人”的意思是交结朋友、上心的人,在村落里就是要多去跟妇女圈子中的人交心做朋友;“从人”,就是湾上有红白喜事或者人家要帮忙的事,要去搭帮手,去凑个数,即便是露个脸也行,总是把夫家湾上的事当事。
③ 其实,媳妇在婆家之所以会如此放肆,也与娘家是大户人家有关系,因此娘家家族大是双刃剑。
④ 随后将要讲到,娘家家族对女儿的后盾作用与对婆家的威慑力,从嫁妆中可以窥探一二。嫁妆越多,说明家庭本身的富有,也意味着娘家的家族成员将更可能支持这个家庭的行动,在家庭支持女儿归属的事情上亦如此。
⑤ 想从嫁女儿中渔利的家庭被人戏谑为“卖女儿”。
⑥ “吊块腊肉”,意思是女孩嫁不出去了,还陪送东西赖着人家接受。
⑦ 水村最出名的三个厉害女儿是外梅、简练、桂梅,三人是同一个亲房的堂姐妹,他们的父亲共11叔伯兄弟,而她们这一辈的男子有多达二十几个,因此在当地十分显赫。且桂梅的父亲曾任村支书。由于有这些背景,这三人在婆家均气焰过人,与婆婆闹得厉害,甚至桂梅还拿扁担打婆婆,影响十分恶劣;而简练则结婚七八年,多在外打工,回来就跟婆婆吵架,跟邻里基本上没有多少来往,笔者访谈时,邻里对她的印象很坏。为此,三人的婆家,都在不同场合“待”过外世。简练的婆婆跟马花诉过苦,桂梅的婆婆则跟桂梅的娘家兄弟媳妇谈过媳妇的事,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作用。
⑧ 那些女儿嫁得近的家庭,耳边总会传来刺耳的声音,弄得心神无一刻安宁。听到了女儿与女婿的争吵你不去管管,心里放不下,去了又给自己找麻烦。而且有时候小夫妻吵闹,口无遮拦,往往会把双方的父母都牵扯进来,骂到父母头上,父母听了会怎么样呢。所以,还不如不听见为妙,将女儿嫁在适当的空间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