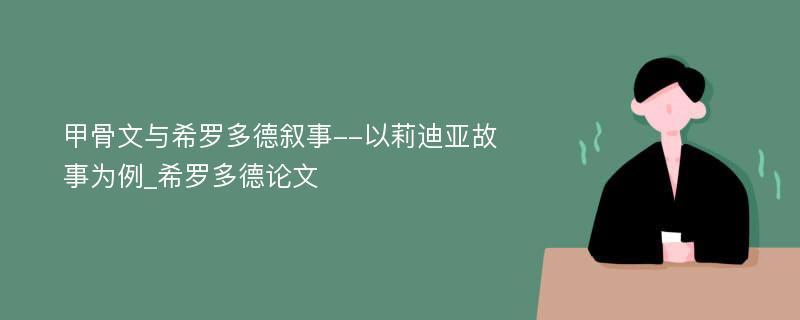
神谕与希罗多德式叙事——以吕底亚故事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谕论文,为例论文,多德论文,希罗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多次援引神谕①,这些神谕往往与其所述的本族或异族的诸多过往故事密不可分,这就给读者和研究者提出了问题:神谕在他的叙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更为深层的问题是,融合神谕的叙事是否可以称之为“真实的”或“历史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作出阐释。鲍登和金特都从神谕本身出发,指出它们可以增加叙述的重要性或权威性。②伽拉姆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话语产生”的复杂进程,强调神谕在希罗多德的文本中起着引导叙事的作用。③帕克、沃尔梅尔和冯腾罗斯等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考察了现存的德尔斐神谕,指出其中大部分为伪神谕。④哈里森则从宗教的视角,分析了各类神谕为当时希腊人所接受的原因,并认为人们相信神谕是真实的。⑤笔者认为,新近引起国际史学界重视的叙事学研究中的“叙事时间”理论。⑥对我们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著述具有启发意义。本文试图围绕《历史》中的一段著名叙事即吕底亚故事(Lydian logoi),应用叙事学的概念分析神谕在他对过去的记述和认识中所处的位置,以期深入理解他所开创和撰述的历史。
一、“叙事时间”与神谕的应验
按照叙事时间理论,事件及其发生过程被预先叙述,则为“预述”(prolepsis)。与之相反,通过回溯来展现事情的始末,则为“倒述”(analepsis)。⑦与一般的预述和倒述不同,希罗多德在叙述与神谕相关的故事时,大多不是由他本人来告知事件的走向,而是借神谕来预测或印证事件及其发生过程。⑧
希罗多德记载的吕底亚故事,发生在美尔姆纳达伊家族统治时期。其中有三位国王的诸多事迹与德尔斐神谕有关,初代国王巨吉斯巩固王权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在描述了巨吉斯如何杀死他的主公坎道列斯并夺取王权之后,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后来他(巨吉斯)之所以能够稳稳地统治了全国,乃是由于德尔斐的一次神谕。”⑨根据此预述,希罗多德讲述了吕底亚人起初如何不愿意承认巨吉斯为王,后来却因神谕而认可了他的王位。紧接着,希罗多德引用了该神谕的后半部分:“来自海拉克列达伊家族的报复会落到巨吉斯的第五代子孙身上,”⑩这构成了下一个预述。待到叙述完整个吕底亚故事以后,希罗多德才借皮提娅女祭司之口,说明克洛伊索斯的不幸遭遇证实了神谕的应验。克洛伊索斯之所以受到惩罚,正是由于五代之前的祖先所犯下的罪业。(11)
在吕底亚第四代国王阿律阿铁斯的故事讲述中,希罗多德也曾以神谕来构成预述。阿律阿铁斯的军队进攻米利都时,意外烧毁了阿赛索斯的雅典娜神殿。之后,阿律阿铁斯病倒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于是,他派人到德尔斐去咨询神谕,请教怎样才能病愈。皮提娅说,如果他们不重建被他们烧掉的雅典娜神殿,便不能得到神谕。(12)此时,皮提娅的话构成预述。而后,希罗多德详述了阿律阿铁斯与米利都人休战的经过和重建神殿的细节。于是,阿律阿铁斯痊愈了,还继续统治了吕底亚达57年之久。
随后,希罗多德对吕底亚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克洛伊索斯展开叙述。这位国王曾五次派使者去德尔斐请示神谕。起初,他并不确定是否应当信任神谕,于是他分别派遣使者去希腊和利比亚的多个神谕所测试神谕。当使者来到德尔斐询问神谕时,皮提娅女祭司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知道沙粒的数量和大海的尺寸,我理解聋人之意,也听到无声之语。硬壳龟的味道触动了我的感知,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煮着,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13)
据说,克洛伊索斯一看到来自德尔斐的神谕,就表示满意和信服,并认为它是唯一的神谕,其他的神谕则完全不能令他满意。但此时,读者却无法通过德尔斐神谕的内容而理解国王的行为。“沙粒的数量”(psammou t’arithmon)和“大海的尺寸”(metra thalassēs)都是谚语式表述方式,(14)体现了神的无所不知。“听到无声之语”(ou phōneuntos akouō)可暗指阿波罗的预言能力。(15)后三行诗则令人无法理解。尽管多布森认为它们是谜语,甚至还对其作出解释,(16)但这极可能只是“预言解释家”的一家之言,正如“木墙神谕”会引起雅典众多预言解释者的解释一样。(17)结合故事的后文来看,其实是希罗多德在此处运用了倒述的手法。原来,早在国王遣使者们去往不同的神谕所时就在想,什么是最不可能被猜到的事情。他想到了在青铜锅里同时烹煮龟肉和羊肉,并在与使者们约好的那天实施。(18)结果,只有皮提娅的回复与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一致。
当克洛伊索斯相信了德尔斐神谕以后,便再次派人去德尔斐,咨询他真正想要问的事情。他的问题如下:是否可以与波斯作战,以及是否需要联合一支盟军。皮提娅向他预言,如果他进攻波斯人,他将灭掉一个大帝国,并且忠告他考虑和希腊人中的最强者结成同盟。(19)在此处,希罗多德又一次借皮提娅之口作出预述。随后,希罗多德讲述了克洛伊索斯寻找同盟,以及最终与斯巴达结盟的历程。但“灭掉一个大帝国”的意思却含糊不清。(20)希罗多德没有在此时急于交代,而是在故事的结尾才借皮提娅之口给出解释:克洛伊索斯要摧毁的帝国正是他自己的吕底亚帝国。(21)
希罗多德在谈及克洛伊索斯又一次咨询神谕的故事中,所用的叙述手法与前一次相似。当克洛伊索斯派人询问他的王国是否长久时,皮提娅回复如下:“一旦在一匹骡子变成了美地亚国王的时候;那时,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啊,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吧,不要停留,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吧。”(22)其中,“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是毫无保留的命令;“不要停留”是对上述命令的强调;“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是以劝说的口吻再次强调撤退的必要性。此外,神谕中还称呼克洛伊索斯为“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而“两腿瘦弱”不便于快速逃跑,给人一种无法逃离之感。因而,本神谕的意思基本清晰,它预示吕底亚将会战败,命令克洛伊索斯赶紧撤离。但是,这位国王不明白“骡子”的含义,还“误解了神谕的意思而把军队开进卡帕多启亚”(23)。接下来,希罗多德叙述了吕底亚—波斯战争的经过,以及吕底亚战败的结果。至于“骡子”,则在皮提娅给克洛伊索斯的最后一个神谕中才得到解释。“骡子”指的是波斯帝国国王居鲁士,因为他的父母分别属于不同的“种族”:母亲是原美地亚王国的公主,父亲却是这个王国当时的臣民波斯人。(24)
可见,希罗多德在叙述与神谕相关的事件时,常以神谕来构成预述,(25)偶或构成倒述。(26)除此之外,他还偶尔用到了其他叙事手法。在叙述了波斯军队攻陷吕底亚都城撒尔迪斯之后,希罗多德便着手讲述克洛伊索斯本人当时的遭遇。但希罗多德没有立即陈述这个国王被俘的经过,而是先插入一段神谕:“吕底亚人啊,众民之王啊,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啊,不要奢望和请求在你的宫廷里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吧。对你来说,你的儿子若像先前一样将会更好;他第一次讲话的那一天,将是不幸的一天。”(27)实际上,克洛伊索斯没有在此时派人求问神谕。希罗多德也称此神谕的咨询时间在“克洛伊索斯以前的全盛时代”(28)。换言之,希罗多德“缓述”(delay)(29)了这一神谕咨询的过程,将其安排在神谕实现的那一刻。“不幸的一天”对应克洛伊索斯被俘虏的当天。至于希罗多德为何采用缓述,则是出于叙事安排的需要。从称呼来看,“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啊”(mega nēpie Kroise)比上个神谕中“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啊”(Lude podabre)的语气要强烈得多。假设希罗多德把此神谕放在前面讲述,就会破坏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情感渐变进程。
当战事结束以后,克洛伊索斯成了居鲁士的幕僚。他又派人去德尔斐质问神何以出现当前的结果,而皮提娅的回复则成为迟来的解释。她复述了巨吉斯的故事,告知他的失败是为了偿付祖辈的罪业。她也揭示了克洛伊索斯对神谕的误解,前两个神谕中的“灭掉一个大帝国”和“骡子”都不是他所理解的含义。(30)换言之,希罗多德借皮提娅的回复形成“重述”(repetition),(31)使得故事前后呼应,也让叙事更加完整。
从以上分析来看,希罗多德将神谕贯穿于他的叙事之中。他经常以神谕对未来的预言来达成预述;时而以期待印证的谕示来构成倒述;偶尔以叙述神谕时间的推迟来形成缓述;偶或以神谕给出的解释来造就恰当的重述。这些都离不开神谕的应验。
二、“真实”与历史语境
鉴于希罗多德直接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那么他是否相信自己记载的这些神谕故事呢?尽管他曾宣称他的职责就是把所能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没有任何义务相信每一件事情;(32)但我们仍能从他的叙述中看出他对神谕的态度。
他在叙述那些实现过程比较简单的预言时,大多平铺直述,几乎不插入评语;但偶尔也会指出:“因此预言得以应验”,“正如神谕的预言”或“预言中的一切得到应验”。(33)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神谕所流露出的信任。此外,通过评价故事主人公在得到神谕以后的反应,希罗多德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在陈述了皮提娅给巨吉斯的回复后,希罗多德作出以下评论:“吕底亚人和他们的国王自身都无视这句话。”(34)而后,他在叙述中向我们证明了这则神谕的应验。在讲述阿尔凯西拉欧斯的故事时,希罗多德在引用神谕后随即感叹:“他忘却了神谕的话。”(35)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希罗多德向我们揭晓,“在他(阿尔凯西拉欧斯)这样做了之后,他才认识到这正是神谕指点给他的意思”(36)。在故事的结尾处,希罗多德又对此作出评论:“不管阿尔凯西拉欧斯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听从神谕的话,他没有逃出他本人的命运。”(37)可见,希罗多德认为人们应该遵从神谕的嘱咐。
事实上,希罗多德也常指出,不是神谕出错,而是人们误解或不懂神谕。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与波斯的战争时,曾四次提及克洛伊索斯对神谕的误解。第一次出现在发动进攻之前,那时他误解了神谕的意思而把军队开进卡帕多启亚。(38)第二次出现在他发动战争的几个动机之中,其中之一就是他极为相信自己对神谕的理解。(39)第三次出现在跨过哈律司河之前,当他接到含糊不清的神谕时,却误认为神谕对自己有利。(40)第四次出现在战败之后,当皮提娅解释了所有谜语之后,克洛伊索斯承认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神。(41)另外,通过拉凯戴孟人出征铁该亚的故事,希罗多德也告诉我们,不是神谕出现失误,而是拉凯戴孟人误以为自己必将获得胜利。(42)此外,希罗多德还在讲述昔普诺斯人的故事时指出,不论是获得神谕的时候,还是萨摩司人入侵的时候,昔普诺斯人都不懂这个神谕的意思。原来在古时,所有的船都被漆成红色,这才是皮提娅要他们小心木头伏兵和红色使者的真意。(43)
希罗多德甚至还会用神谕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为了证明伊索是雅德蒙的奴隶,希罗多德列出的证据来自神谕。当德尔斐人遵照神谕的命令,邀请伊索的主人来收取这个奴隶的死亡赔偿金时,来的人是雅德蒙的子孙。(44)在解释提洛岛为何会发生地震时,希罗多德给出的补充性证据是一则神谕:“我要使从未震动过的提洛发生震动。”(45)此外,希罗多德在陈述了对埃及领土的看法之后指出,阿蒙神殿发出的一则神谕证实了他本人的这一看法。(46)
据此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呈现的是相信神谕的态度。(47)但是,现代学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希罗多德在吕底亚叙事中所引神谕的真实性都遭到质疑。(48)不仅如此,现存的大部分德尔斐神谕几乎都被如此看待。冯腾罗斯的统计是其中的典型,他将德尔斐神谕分成四类:历史、准历史、传说、伪造,数量分别是75、268、176、16。第一类中真实的神谕有48个,应该真实的25个,不真实的2个;第二类中应该真实的16个,可能真实的8个,部分真实的1个,受到怀疑的2个,不真实的241个;第三、第四类则都不真实。(49)但正如毛里兹奥所言,冯腾罗斯检验神谕是否真实的标准,其实就是判断它们是否出自皮提娅之口。然而,即便是那些被他断定为真实的神谕铭文,本身也带有模式化语言,它们不会精确地记录皮提娅的回复。那么,冯腾罗斯鉴别神谕是否真实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50)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会发现皮提娅发布的神谕本身会经历解释和流传的过程。当人们去德尔斐求问神谕时,皮提娅女祭司会用变化了的声音和含糊的语言说出阿波罗的神谕。(51)接下来,德尔斐圣所的专职人员负责给皮提娅的言语进行修饰,甚至改为六音步诗体形式。(52)至此,德尔斐神谕已经或多或少经历了一次由他们带来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获得神谕之后,还常需要从事神谕解释的专职人员来对其进行解释。许多希腊作家都曾提到,神谕需要由专门的解释者进行细致的释读。(53)此外,从事这一事务的人还被给予固定的称谓。希罗多德称神谕解释者为 khrēsmologs,(54)色诺芬在提到神谕解释者迪奥佩特斯(Diopeithes)时,也称他为khrēsmologs,(55)阿里斯托芬在《和平》中也称,擅长解释神谕的希耶罗克勒斯(Hierocles)为khrēsmologs。(56)虽然有些作家不喜欢使用这个单词来称呼神谕的解释者,(57)甚至将这个单词的意思另作它解,(58)但证明了在古希腊社会中,神谕是允许被解释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希腊人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神谕可被重新解读。当雅典发生瘟疫时,人们回忆起一则神谕:“和多利斯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将与之俱来”,并认为它预示的就是此时所发生的瘟疫。但修昔底德认为,如果以后再发生一次与多利斯的战争而引起饥荒,那么,人们会重新释读这句预言,并认为它预示的就是彼时所发生的饥荒。(59)虽然修昔底德道出的只是假设之词,但也说明重新释读神谕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现象。希罗多德的文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许多年前,雅典的一个神谕解释者吕西斯特拉托斯曾预言:“科里亚斯的妇女也将要以桡为薪来烧饭。”(60)当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受创时,人们认为这则预言应验了,即希腊战舰的损失是预言在希波战争中应验的结果。据此,这个多年前的预言,在新的情景中被重新释读。
因而笔者认为,与其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去检验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是否真实,不如把他记载的神谕故事放入古希腊的语境中进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出生较早于希罗多德的吕底亚作家克桑托斯(Xanthus),曾用希腊语写下四卷本的《吕底亚志》(Lydiaca)。由于这部作品只以残篇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无法了解作品的全貌。但埃弗鲁斯(Ephorus)对其作出了评价,即克桑托斯给了希罗多德“起跑点”。(61)这表明克桑托斯所记载的事件应都发生在巨吉斯的时代之前。(62)于是,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故事时便没有多少书面资料可参考。(63)尽管如此,但我们仍能得知,这故事是当时人们所熟知的故事。早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克洛伊索斯的故事已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广泛传播。约在公元前520年,一个富有的希腊人为他的儿子取名为克洛伊索斯。不久之后,雅典的陶瓶画家在一个红色陶瓶上绘制了一幅画,其中展现的正是克洛伊索斯在火葬柴堆上的场景。(64)公元前468年,希腊诗人巴库里德斯(Bacchylides)为叙拉古僭主希耶隆(Hieron)创作了一曲胜利颂歌。诗人在歌颂敬神之人时,举出的例子就是克洛伊索斯的故事。他在将被烧死之时得到了神的援救,便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神的虔诚信奉。(65)由此可见,克洛伊索斯的故事是如此广为流传,以至于希罗多德认为不必特别指出其资料的来源。于是,希罗多德在介绍克洛伊索斯时说,“据我们所知”(hēmeis idmen),他是异邦人中第一个制服希腊人的人。(66)此外,希罗多德在提到巨吉斯时也说,“据我们所知”(hēmeis idmen),他是异邦人中第一个向德尔斐神殿奉献礼物之人。(67)在谈及吕底亚人时也说,“据我们所知”(hēmeis idmen),他们是最早打制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也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68)换言之,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故事,正是当时的人们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
三、历史性叙述与分析
既然希罗多德相信神谕,又以预述、倒述等叙事手法来表现神谕应验的故事,那么,他是否只是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69)他是否只知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人类事件与行为的神话叙事方式,而不知以人和人类社会为中心来解释事件与行为的历史性分析?(70)从表面看来,确实如此。他从未给出任何反驳神谕的言论,还常以神谕的应验来构筑叙事。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叙事话语中发现诸多历史性叙述和分析。
就克洛伊索斯为何率领吕底亚人对波斯人作战来看,希罗多德没有过分强调神谕在其中的作用,而是解释了克洛伊索斯发动战争的多重原因。在他进攻卡帕多启亚之前,希罗多德指出了他发动战争的三个动机:一是扩张领土,二是信任神谕,三是打败居鲁士来给阿斯杜阿该斯复仇。(71)但在第一次询问神谕之前,克洛伊索斯了解到波斯帝国的发展壮大,他想要阻止那日益增强的力量。(72)那么,阻止波斯的强大是他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动机。
实际上,不少学者在研究希罗多德如何解释事件时已发现,他使用了多重解释的方法。拉特内尔认为希罗多德主要采用了五种解释方法:神的嫉妒、命运、神意、报复以及历史的分析。(73)米卡尔森注意到宗教因素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它是对事件的唯一或最重要的解释,而只是几个解释中的一个。(74)哈里森也表明,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类动机和神性因素并不矛盾。(75)结合学者们的论述来看,克洛伊索斯发动吕底亚—波斯战争有四重原因,误解神谕只是其中的一个。尽管伊默瓦尔把这些原因进行主次分析,(76)但实际上,希罗多德在说明多个原因的时候用的是并列连词kai...kai...kai...(77)可见,希罗多德在面对多个原因时,并没有特别强调哪个原因最重要。
根据与克洛伊索斯相关的第四个神谕,希罗多德引出了克洛伊索斯被俘的经过。但仅限于此,其他叙述都遵循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起初,克洛伊索斯跨过哈律司河,来到卡帕多启亚,攻占了普铁里亚人的城市。然后,两军在普铁里亚激战,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克洛伊索斯带兵返回撒尔迪斯,打算来年春天再向波斯发动进攻。但是,居鲁士却突然率军向吕底亚人出战,于是双方在撒尔迪斯城前决战。吕底亚的援军斯巴达人未及时到达,结果,吕底亚人败北,撒尔迪斯被攻陷,城市被洗劫,克洛伊索斯被俘虏。
战争结束以后,皮提娅解释了克洛伊索斯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即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既定的命运,克洛伊索斯偿付了五代以前的祖先的罪行。尽管希罗多德没有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称自己赞同皮提娅的说法,但这是希罗多德所列举的唯一解释,而此神谕又与早年巨吉斯所获得的神谕相呼应。这似乎表明,希罗多德完全依赖德尔斐神谕来解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本人的理解蕴藏在他的叙述之中。
他多次暗示克洛伊索斯的过度自信。khraomai和manteuomai与名词manteion和khrēstērion一起使用,表示“咨询神谕”的意思。(manteion指皮提娅在灵感状态下说出的神谕,而khrēstērion则是祭司解释的神谕)但是,在叙述克洛伊索斯咨询神谕时,他却七次用了另一个动词peiraō的相关变位形式以及名词形式。这个词本义是“尝试”,与神谕一起使用有“测试神谕”之意,即就自己原本知道的事情去测问神谕。希罗多德在记载克洛伊索斯第一次派人询问神谕时,已五次用到这类词汇,它们分别是apepeirato tōn mantēiōn,peirōmenos tōn mantēiōn,tēn diapeiran tōn khrēstēriōn, epeirōtōntas ho ti poieōn tunkhanoi ho Ludōn basileus Kroisos ho Aluatteō,epeirōtōn to entetalmenon。(78)前两个是动词短语,意思是“测试神谕”;第三个是作宾语的名词短语,意思也是“测试神谕”;第四个是“测试吕底亚国王、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正在做什么”;第五个是“测试被命令要做的事情”。希罗多德对测试神谕的强调,无疑表现了克洛伊索斯的过度自信。多布森在分析神谕的内容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克洛伊索斯正在做一个亵渎皮提娅的恶作剧。(79)冯腾罗斯也指出,克洛伊索斯测试神谕的行为极为专横和不敬神,这将促使他走向厄运之路。(80)此外,希罗多德还两次用到了“测试”一词,出现在克洛伊索斯所获得的“骡子”神谕和最后一个神谕中,分别是 epeirōta和epeirōtān。(81)前一个“测试”表明,他心中早有答案,只是检验一下皮提娅女祭司能否给出他心中的那个答案;后一个“测试”则体现了他对神的质问,足见即便是在战败之后,他也继续保持着过度自信的姿态。
过度自信也就成了克洛伊索斯率领的吕底亚军队被打败的原因之一。当他从德尔斐神谕得知他会“灭掉一个大帝国”的时候,他“大喜过望”(huperēsthē),深信自己一定可以摧毁居鲁士的王国。(82)那时,德尔斐神谕警告他:“在一匹骡子变成了美地亚国王的时候赶紧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然而,克洛伊索斯非但不受任何影响,反而“高兴得无以复加”(pollon ti malista pantōn hēsthē),他认为骡子绝对不可能代替人做美地亚国王。(83)拉特内尔认为希罗多德笔下的“笑”出现在三种类型的人身上。第一种人在严重的过失面前是无辜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脆弱,以克洛伊索斯为代表。第二种人做了邪恶的行为,他的欢愉只能在疯狂中得到解释,以冈比西斯为代表。第三种人傲慢地自信于他们的权力,以薛西斯为代表。(84)尽管拉特内尔将克洛伊索斯作为第一种人的典型,但是从“大喜过望”到“高兴得无以复加”来看,希罗多德都在刻画一个自信过度膨胀的角色,尤其是“高兴得无以复加”把克洛伊索斯的高兴程度描写到极致。此外,希罗多德还两次谈及克洛伊索斯那满溢心中的自信:一次是在桑达迪斯警告之前,克洛伊索斯满以为自己可以摧毁波斯的军队;(85)另一次是在进攻卡帕多启亚之时,他坚信自己可以为阿斯杜阿该斯复仇。(86)克洛伊索斯在获得神谕之后的过度自信在这里得到呼应。希罗多德不停地暗示:克洛伊索斯非常高兴,但实际情况不如他想的乐观;克洛伊索斯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其实他不能做到。
此外,希罗多德还叙述了吕底亚军队如何在作战策略上败给波斯军队。在军队实力上,两军不相上下,这从第一次战斗中便可看出。那时,两军在普铁里亚拼死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结果却未分出胜负。然而,在后来的战斗中,吕底亚人的作战谋划处处不如波斯人。当第一次战斗结束以后,吕底亚人的策略是请求盟友(埃及人、巴比伦人和斯巴达人)的援助,并打算来年春天再向波斯人发动进攻。波斯人却棋高一筹,先打听到吕底亚人的作战计划,而后决定迅速出兵吕底亚。波斯人不仅知己知彼,而且掌握了作战的先机。相反,吕底亚人根本没料到波斯人的到来。第二战,两军相会在撒尔迪斯城前广阔的平原。初时,吕底亚的骑兵占据地利优势。但随后波斯的军队中有人献出良策,用骆驼与吕底亚人的马对峙,让吕底亚的骑兵优势无法发挥。于是,吕底亚人被击溃,都城撒尔迪斯被包围。由于撒尔迪斯城内的坚固防守,波斯军队的围城行动进行得很艰难。但在第四天,波斯人找到了对策,成功地翻越防守松懈的峭壁,从而攻陷撒尔迪斯。实际上,希罗多德在叙述中多次强调吕底亚人的勇敢善战。因而,吕底亚人战败的真正原因是:在战争策略上三次败给波斯人。
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是否存在历史性叙述和分析,这已不是新鲜话题。(87)但本文主要针对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故事,并在此处以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故事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分析。一方面,神谕解释了克洛伊索斯对波斯开战的动机、被俘的经过和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希罗多德的理解并不限于神谕的解释,他的文中还包含诸多历史性叙述和分析。
在叙述吕底亚故事时,希罗多德常用皮提娅口中的预言来构成预述,或通过追溯神谕的应验过程来形成倒述。此外,他还曾推延神谕的叙述时间而做出缓述,也会在故事的结尾以神谕的解释来造就恰当的重述。可见,他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才在文中形成预述、倒述、推延和重复等叙事手法。这也是他在叙述众多神谕故事时的特色,其中,预述是他在讲述神谕故事时的主要方式,因为它更为便利地体现了神谕的应验过程。
当今一些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指出,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这些神谕如何应验的故事,也就只是不真实的传说。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是当时的人们所相信的“真实”的过去。同时,希罗多德并没有因为相信神谕和认可它们的解释,而在叙述中完全倒向神话叙事。透过他的叙述话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在对战争原因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而,即使叙述的是神谕故事,希罗多德也充分传达了在《历史》序言中所宣称的宗旨,即他的叙事是“为了使人类过去的事迹(ta genomena ex antrōpōn)不因时间而流逝,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ta men Hellēsi,ta de barbaroisi)那些令人惊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荣耀,特别是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aitiēn)给记载下来”。
注释:
①希罗多德共引用神谕85次,涉及43个故事,其中大部分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有关,也有少许与来自多铎那、埃及、埃西欧匹亚等地的神谕有关。
②H.鲍登:《古典时代的雅典和德尔斐神谕》(H.Bowden,Classical Athens and the Delphic Orac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J.金特:《德尔斐神谕故事和史学的开端:希罗多德的克洛伊索斯故事》(J.Kindt,“Delphic Oracle St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ography:Herodotus’ Croesus Logos”),《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101卷,2006年,第34—50页。
③C·伽拉姆:《古希腊的神话和历史》(C.Calame,Myth and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
④H.W.帕克和D.E.W.沃尔梅尔:《德尔斐神谕》(H.W.Parke and D.E.W.Wormell,The Delphic Oracle)第1卷,牛津1956年版,第49—283页;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J.Fontenrose,The Delphic Oracle:Its Responses and Operations),伯克利1978年版,第241—429页。
⑤T.哈里森:《预言和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T.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258页。
⑥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意识到,原始的故事时间是事件之中的自然时序,而叙事的话语时间却不一定总是如此,S.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叙事结构》(S.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系统地阐述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提出了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重要概念。根据叙述时序和故事时序的差异,可将叙事方式分成预述、倒述等;根据叙述时距与故事时距的长度比量,可将其分为概要、场景、省略和停顿等;根据叙述频率的不同,则分为单述和重述等,G.热奈特:《叙事话语》(G.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50页。近年来,叙事时间理论也被学者用来分析古典文献,可参考I.J.F.德容和R.努恩里斯特主编:《古希腊文学中的时间》(I.J.F.de Jong and R.Nünlist,eds.,Time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莱顿2007年版,第1—522页。
⑦G.热奈特:《叙事话语》,第24—30页;G.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叙述学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⑧一般而言,预述与倒述的形成,是由于叙述者提前或推后故事的讲述。此叙述者既可以是作者本人,也可以是故事中的人物角色。T.路德:《希罗多德》(T.Rood,“Herodotus”),I.J.F.德容和R.努恩里斯特主编:《古希腊文学中的时间》,第116—117页。但希罗多德在叙述神谕故事时,还借助神谕来构筑预述与倒述,这是他不同于前代作家的地方。后文中提到的缓述、重述也具有以上特征。
⑨希罗多德:《历史》,Ⅰ.13.1。本文所引用的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希腊文原版为“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中由C.胡德主编的1927年版的《希罗多德的历史》(C.Hude,ed.,Herodoti Historiae),而中译文主要参考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的王以铸的翻译,并在需要时略作改动。
⑩希罗多德:《历史》,Ⅰ.13.2。
(11)希罗多德:《历史》,Ⅰ.91.1。
(12)希罗多德:《历史》,Ⅰ.19.3。
(13)希罗多德:《历史》,Ⅰ.47.3。
(14)A.Y.坎贝尔:《希罗多德Ⅰ.47和忒奥克里托斯:(牧歌).XVI.60》(A.Y.Campbell,“Herodotus Ⅰ.47 and Theocritus Id.XVI.60”),《古典学评论》(The Classical Review)第45卷,1931年,第117—118页;A.S.F.高:《大海的尺寸》(A.S.F.Cow,“Metra Thalassēs”),《古典学评论》(The Classical Review)第45卷,1931年,第10—12页;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第113页。实际上,与它类似的词句也出现在其他古典文献中。品达在形容阿波罗的全知形象时,赞颂他“知道大海和河流中有多少沙粒会被风浪所击打”,品达:《皮提亚颂歌》(Pindar,Pythian ode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Ⅹ.44—49。赫西俄德也将“神的知识”称为“大海的尺寸”,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Hesiod, Works and Days),洛布古典丛书,剑桥2006年版,648。
(15)在《给赫尔墨斯的荷马颂歌》中,赫尔墨斯认为,只要阿波罗“看不见已看到的事,听不见已听到的事”,便不会发现他作的偷盗之事。但最终阿波罗还是看见了原本看不到之事,听到了原本听不到之声。阿波罗多罗斯在《神话宝库》中将阿波罗的这种本领称作“预言能力”,见阿波罗多罗斯:《神话宝库》(Apollodorus,The Librar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1年版,Ⅲ.10.2。哈里森认为,此神谕的第二行诗中透露出阿波罗拥有预言能力,T.哈里森:《预言和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第41页注30。
(16)M.多布森:《希罗多德Ⅰ.47.1和给赫尔墨斯的颂歌:对测试性神谕的解释》(M.Dobson,“Herodotus Ⅰ.47.1 and the Hymn to Hermes:A Solution to the Test Oracle”),《美国语文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100卷,1979年,第349—359页。
(17)希罗多德:《历史》,Ⅶ.142—145.
(18)希罗多德:《历史》,Ⅰ.48.2
(19)希罗多德:《历史》,Ⅰ.53.3.
(20)卢奇安:《宙斯唱悲剧》(Lucian,Zeus Rant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5年版,43;O.穆雷、A.莫雷诺主编:《评注希罗多德:第1—4卷》(O.Murray and A.Moreno,ed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Books Ⅰ-Ⅳ),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第114页;H.W.帕克和D.E.W.沃尔梅尔:《德尔斐神谕》第1卷,第40页。此外,金特认为神谕的含糊不清很正常,因为神的语言不易为凡人所理解,J.金特:《德尔斐神谕故事和史学的开端:希罗多德的克洛伊索斯故事》,《古典语文学》第101卷,2006年,第34—50页。
(21)希罗多德:《历史》,Ⅰ.91.4。
(22)希罗多德:《历史》,Ⅰ.55.2。
(23)希罗多德:《历史》,Ⅰ.71.1。基尔希伯格认为克洛伊索斯自己在做了开战的决定之后,才求助于神圣机构,J.基尔希伯格:《希罗多德著作中神谕的功能》(J.Kirchberg,Die Funktion der Orakel im Werke Herodots),格丁根1965年版,第17页。但他过于强调战争意图与求助神谕间的先后顺序,而将神谕在事件中的作用降至附属地位。
(24)希罗多德:《历史》,Ⅰ.91.4。起初,波斯人是美地亚人治下的臣民。后来,居鲁士率领波斯人推翻了美地亚人的统治,建立起波斯帝国。希罗多德:《历史》,Ⅰ.107—130。
(25)更多此类预述,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Ⅰ.167;174;Ⅲ.57—58;Ⅳ.15;155—164;Ⅴ.43;81;114;Ⅵ.34—35;52;139—140;Ⅶ.140—145;178;Ⅷ.20;36—37;64;77;114;133—136;Ⅸ.33;42—43;93。
(26)更多此类倒述,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Ⅰ.65—67;Ⅱ.134;Ⅴ.92;Ⅵ.76;77;86;98;Ⅶ.197;Ⅷ.20;96。
(27)希罗多德:《历史》,Ⅰ.85.2。
(28)希罗多德:《历史》,Ⅰ.85.1。
(29)缓述,即延缓叙述某事。可参考S.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中的叙事结构》,第72页;T.路德:《希罗多德》, I.J.F.德容和R.努恩里斯特主编:《古希腊文学中的时间》,第123页。更多与神谕相关的缓述,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Ⅴ.81;Ⅵ.19;Ⅶ.220。
(30)希罗多德:《历史》,Ⅰ.91。
(31)重述,又称重复性叙述,即数次讲述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可参考G.热奈特:《叙事话语》,第113页;G.普林斯:《叙述学辞典》,第192页;T.路德:《希罗多德》,I.J.F.德容和R.努恩里斯特主编:《古希腊文学中的时间》,第118—119页。更多与神谕相关的重述,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Ⅴ.90—91;Ⅷ.141;Ⅸ.64。
(32)希罗多德:《历史》,Ⅶ.152.2。
(33)希罗多德:《历史》,Ⅷ.96.2;Ⅸ.64.1;Ⅵ.19.3。
(34)希罗多德:《历史》,Ⅰ,13.2。
(35)希罗多德:《历史》,Ⅳ.164.1。
(36)希罗多德:《历史》,Ⅳ.164.3。
(37)希罗多德:《历史》,Ⅴ.164.4。
(38)希罗多德:《历史》,Ⅰ.71.1。
(39)希罗多德:《历史》,Ⅰ.73.1。
(40)希罗多德:《历史》,Ⅰ.75.2。
(41)希罗多德:《历史》,Ⅰ.91.6。
(42)希罗多德:《历史》,Ⅰ.66.3。
(43)希罗多德:《历史》,Ⅲ.58.1—2。
(44)希罗多德:《历史》,Ⅱ.134.3—4。
(45)希罗多德:《历史》,Ⅵ.98。
(46)希罗多德:《历史》,Ⅱ.18.1。
(47)希罗多德记载了三起伪造神谕的案例,可参考希罗多德:《历史》,Ⅵ.66;Ⅴ.63;Ⅶ.6。他对伪神谕的记载表明,他不会无条件地相信任何神谕,但不表示他怀疑神谕制度本身,参见T.哈里森:《预言和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第140—143页。而且,他称皮提娅说出的是“克列欧美涅斯要求她说的话”或“这些人想要她说的话”,称奥诺玛克里托斯的做法是“擅自在穆赛欧斯的神谕插入了一段话”。可见,他怀疑的不是神谕制度,而是“神谕”本身是否真的来自神。
(48)J.A.S.伊文思:《历史之父还是谎言之父:希罗多德的名声》(J.A.S.Evans,“Father of History or Father of Lies:The Reputation of Herodotus”),《古典学杂志》第64卷,1968年,第11—17页;H.W.帕克和D.E.W.沃尔梅尔:《德尔斐神谕》第1卷,第132—133页;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第113、301页;J.基尔希伯格:《希罗多德著作中神谕的功能》,第19页;W.W.豪和J.威尔斯:《评注希罗多德》,(W.W.How and J.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第1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O.穆雷、A.莫雷诺主编:《评注希罗多德:第1—4卷》,第84—140页。
(49)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第245—416页。目前有两部学术作品对德尔斐神谕作了统计,帕克和沃尔梅尔在《德尔斐神谕》中统计的数据是615个,冯腾罗斯在《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行》中在此数据基础上删去95个,增添15个,总数据成为535个。由于冯腾罗斯在列举数据时作出了真实与否的判断,本文在此借用他的数据。
(50)L.毛里兹奥:《作为口述表演的德尔斐神谕:真实性和历史证据》(L.Maurizio,“Delphic Oracles as Oral Performances: Authenticit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16卷,1997年,第308—334页。
(51)普鲁塔克:《不再被颁发为诗体形式的德尔斐神谕》(Plutarch,“The Oracle at Delphi No Longer Given in Verse”),《道德论集》(Moralia),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405c;H.鲍登:《古典时代的雅典和德尔斐神谕》,第13页。但毛里兹奥和普莱斯都更强调皮提娅与阿波罗的精神融合,可参考L.毛里兹奥:《人类学与精神占有:重新解读皮提娅在德尔斐的作用》(“Anthropology and Spirit Possesion: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ythia’s Role at Delphi”),《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5卷,1995年,第70页;S.普莱斯:《德尔斐和预言》(S.Price,“Delphi and Divination”),P.E.伊尔斯特林和J.V.穆尔编:《希腊宗教和社会》(P.E Easterling and J.V.Muir,eds.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52)据普鲁塔克,诗人给皮提娅的话添加了一些华丽的辞藻和悲剧性的表述,见普鲁塔克:《不再被颁发为诗体形式的德尔斐神谕》,载《道德论集》,407b。据斯特拉波,皮提娅口中的神谕包括诗体和散文体,而某个为圣所工作的诗人则把散文体也修改成诗体,见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Geography),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Ⅸ.3.5。麦克劳德分析了德尔斐诗体神谕中的史诗式模式用语,进而证明负责修改皮提娅语言的是口述游吟诗人,可参考W.E.麦克劳德:《德尔斐的游吟诗人》(W.E.McLeod,“Oral Bards at Delphi”),《美国语文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第92卷,1961年,第317—325页。帕克和沃尔梅尔却认为,把皮提娅的话改写成六音步诗体的是圣所中的男祭司。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男祭司们也将神谕改写成三音步诗体。可参考H.W.帕克和 D.E.W.沃尔梅尔:《德尔斐神谕》第1卷,第33—34页。
(53)品达:《奥林匹亚颂诗》(Pindar,Olympian Ode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Ⅻ.10—18;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Aeschylus,Agamemnon),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26年版,1255;欧里庇得斯:《美狄亚》(Euripides,Medea),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674;H.迪尔斯和W.克朗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H.Diels und W.Kranz,eds.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柏林1961年版,22 B 93。
(54)阿姆披亚拉欧斯、吕西斯特拉托斯、奥诺玛克利托斯都被希罗多德称之为khrēsmologs anēr,希罗多德:《历史》,Ⅰ.62-4;Ⅷ.96.2;Ⅶ.6.3。
(55)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18年版,Ⅲ.3.3。
(56)阿里斯托芬:《和平》(Aristophanes,peace),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52—1119。
(57)悲剧家和柏拉图都不太喜欢使用khrēsmologs这个词,可参考H.鲍登:《售卖的神谕》(H.Bowden,“Oracle for Sale”),P.德洛和R.帕克主编:《希罗多德和他的世界》(P.Derow and R.Parker,eds.Herodotus and His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58)柏拉图提到khrēsmologs时,都将他们与献祭相连,参见柏拉图:《理想国》(Plato,Republic),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364b—e。此外,阿里斯托芬也不区分mantis与khrēsmologs,阿里斯托芬:《鸟》(Aristophanes,Birds),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60—961。
(59)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Ⅱ.54。
(60)希罗多德:《历史》,Ⅷ.96。
(61)F.雅各比编:《希腊历史学家残篇集成》(F.Jacoby,hrsg.,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CD-Rom,莱顿2004年版,70 F 180。
(62)J.玛林科拉:《希腊历史学家》(J.Marincola,Greek Historian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63)关于希罗多德写作的口述背景,可参考吴晓群:《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64)名为克洛伊索斯的雕像现藏于雅典国家博物馆,而描绘火堆场景的红像陶瓶现藏于卢浮宫,可参考J.古尔德:《希罗多德》(J.Gould,Herodotus),伦敦2000年版,第34—35页。
(65)巴库里德斯著,R.菲格尔斯译:《胜利颂诗》(Bacchylides,Epinician Odes,transl.by R.Fagles),Ⅲ.21—63,纽黑文1998年版,第7—10页。
(66)希罗多德:《历史》,Ⅰ.6.2。
(67)希罗多德:《历史》,Ⅰ.14.2。
(68)希罗多德:《历史》,Ⅰ.94.1。
(69)费尔班克斯认为,希罗多德是德尔斐神谕的辩护者,可参考A.费尔班克斯:《希罗多德和德尔斐神谕》(A.Fairbanks,“Herodotus and the Oracle at Delphi”),《古典学杂志》第1卷,1906年,第37—48页。
(70)神话叙事方式总是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人类的事件和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想;而历史的叙事方式则采取的是历史性的分析,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本来解释事件与行为,可参考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金特认为希罗多德在对神谕的使用中缺乏批判性分析,可参考J.金特:《德尔斐神谕故事和史学的开端:希罗多德的克洛伊索斯故事》,《古典语文学》第101卷,2006年,第34—50页。
(71)希罗多德:《历史》,Ⅰ.73.1。
(72)希罗多德:《历史》,Ⅰ.46.1。
(73)D.拉特内尔:《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D.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多伦多1989年版,第197—204页。
(74)J.D.米卡尔森:《希罗多德和希波战争中的宗教》(J.D.Mikalson,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5)T.哈里森:《预言和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第235页。
(76)复仇是附属的动机,扩张是更深入的缘由,神谕中预言的命运和他因误解神谕所带来的冲动是最主要的原因,可参考H.R.伊默瓦尔:《希罗多德中的历史原因方面》(H.R.Immerwahr,“Aspects of Historical Causation in Herodotus”),《美国语文学会学报》第87卷,1956年,第241—280页。
(77)希罗多德:《历史》,Ⅰ.73.1。
(78)希罗多德:《历史》,Ⅰ.46—47。
(79)M.多布森:《希罗多德Ⅰ.47.1和给赫尔墨斯的颂歌:对测试神谕的解释》,《美国语文学杂志》第100卷,1979年,第349—359页。
(80)J.冯腾罗斯:《德尔斐神谕:它的回复和运作》,第113页。此外,巴尔克尔也认为,克洛伊索斯意图挑战神谕的权威,可参考 E.巴尔克尔:《标注神谕:希罗多德历史中的解释、特性和表演》(Barker,“Paging the Oracle:Interpretation,Identity and Performance in Herodotus’History”),《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an)第53卷,2006年,第1—28页。
(81)希罗多德:《历史》,Ⅰ.55.1;90.4。
(82)希罗多德:《历史》,Ⅰ.54.1。
(83)希罗多德:《历史》,Ⅰ.56.1。
(84)D.拉特内尔:《非笑素材:希罗多德中的文字策略》(D.Lateiner,“No Laughing Matter:A Literary Tactic in Herodotus”),《美国语文学会学报》第107卷,1977年,第173—182页。
(85)希罗多德:《历史》,Ⅰ.71.1。
(86)希罗多德:《历史》,Ⅰ.73.2。
(87)J.古尔德:《希罗多德》,第63—85页;D.拉特内尔:《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第189—228页;J.L米列:《希罗多德:历史之父》(J.L Myres,Herodotus:Father of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0—88页;J.玛林科拉:《希腊历史学家》,第19—60页;A.莫米亚诺:《史学研究》(A.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96年版,第127—142页;D.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0页;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63页;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