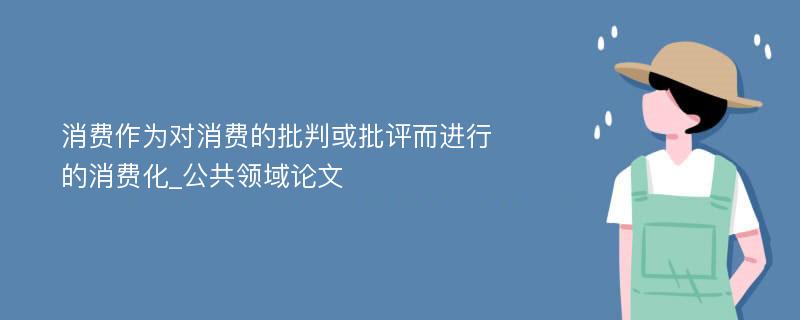
作为消费的批判或批判的消费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4-0017-07
一
批判是一种否定的理性。正是在批判中,人们摆脱了事物当下、表面的束缚,引向改变了的、更新更深刻的可能性空间。就一个群体而言,批判是人们活力、创新、超越之源。就整个人类而言,批判是其历史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当然,从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开始,批判就成为哲学、哲学家的代名词或图腾。近代的启蒙运动则唤醒了民众怀疑、批判的勇气,批判及其能力成为主体性的重要表征,公开地进行批判的自由也逐渐成为公民普遍的权利。公众的批判汇集在一起,既超越了各自的私人领域,也区别于公共权力(国家),形成了所谓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明确地把起于17、18世纪欧洲的公众舆论定义为“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1](P108)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看来,舆论与良心等同,公众舆论的法则等同或代替了哲学的批判法则。康德甚至认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共识具有检验真理的实际功能。
正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和传媒的日益发达,以批判为己任的公众舆论奠基了所谓现代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公共媒体展现自己的观点,彼此交换意见,从而形成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批判或共识。理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公开批判空间。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精髓。公共领域的批判当然指向公共权力,虽然通过批判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1](P28)但是,成熟的公共领域能以批判的方式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并把社会的需要成功地传达给国家。而成熟的国家、政府也应该将公共领域视为自己反思性监控体系的重要甚至是核心部分,从中吸取营养,及时把公众、社会的需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对自己的方针、政策进行适时修正。惟此,现代统治阶级才能持续确保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公共领域的批判也指向社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文化批判(也包括对公共领域自身的反思、批判),对舆论导向、社会风尚、个体趣味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对于社会而言,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教化的功效,也是开掘生活的多元可能性,避免“单向度”生存的保障。总的来说,无论是对公共权力的批判,还是社会私人领域的批判,就像阿伦特所理解的那样,这既是个体展现、实现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集体永续共存的需要。吉登斯则把自觉运用反思、批判,将反思、批判体制化的现代性阶段称为反思性现代性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说,批判是当代社会在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之后的世俗救赎。
社会自由的增进、公民能力的提高和大众传媒的兴盛使得当代社会的批判十分发达、蔚为壮观,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时代的批判更多、更广泛。在多元、差异性的生活中,论争、批判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格。不过,当代公共领域的批判却面临着两个相互“辉映”的问题:一方面,在众声喧哗中实质性的批判有萎缩、淡出的迹象,文化批判的公众(the public)正逐渐演变为文化消费的大众(the mass);另一方面,依然保存的,甚至是很红火的批判自身成了一种消费品,也就是说,在众多消费中,新增了一种消费——批判——作为消费的批判。就批判的超越性而言,批判具有生产的性质——当然是就精神生产而言,其“生产”的形式主要是理性的,其“生产”的目的主要在于真理。但是,在现时代,批判及其活动本身已经被对象化,成为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殊活动。这种满足是一种“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也就是消费。在当代中国,公共领域还处于吁求、发育的阶段,远未成熟。就像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一样,公共领域也共时态地呈现着现代化历时态的问题。在公共领域刚刚诞生,公众批判还远未得以展现其历史力量的时候,就面临着异化为一种消费的危险。这不能不让人警觉和深思。
归结起来,当代公共领域的批判逐渐消费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的休闲化。与本真批判的理性形式、真理目的不同,在“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2](P20)的现代社会,批判活动正渐化为感性的形式和审美、娱乐的目的。批判活动成为对我们的休闲快乐极有益的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至为激烈、深刻的批判活动也可能吸引很多人的参与,但不少人只是将之理解为“视听盛宴”、“精神桑拿”,效果就是“很爽”。参与者可能颔首于批判中某些真理性的洞见,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真理”是外在性的,他们并不打算在世界观或行为上因之有所改变。对于现代社会的大众来说,批判、真理不是不重要,而是发笑、快乐更重要。哈贝马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为了迎合大众的休闲诉求,“新闻和报道,甚至编者评论,都以休闲文学的行头粉饰起来”。[1](P196)其实,许多批判者自身何尝不是日益将批判理解为一种可以带来愉悦的休闲!更进一步的是,当人们对“批判的武器”的鉴赏的边际效益递减之时,就会渴望着“武器的批判”。换言之,如果说现时代的大众对批判活动做了休闲、审美化的处理,那么现在还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还形成了一种暴力美学的心理渴望机制——从纯粹娱乐的角度渴望一种极端的对抗。这样,极端、出位就成为一种可以带来审美或娱乐剩余价值的资本。就批判活动而言,越是激烈的论辩对抗越是具有观赏、休闲的价值。
第二,批判的商业化。在现代社会,有供求关系的地方就可能被商业化。对于商家和大众传媒来说,批判活动便是其预期的生财之道,具有商品和消费品的形式。哈贝马斯追溯过去认为,尽管文化商品的商业化在过去曾经是批判的前提,但批判本身却根本不处于交换关系之中。在那时,批判是私人财产者作为“人”,而且仅仅作为“人”的交往领域的中心。但是,“今天,讨论本身受到了管制:讲台上的专业对话、公开节目讨论和圆桌节目——私人批判变成了电台和电视上明星的节目,可以圈起来收门票,当作会议出现,人人可以‘参加’时,批判已经具有了商品形式。讨论进入‘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个人摩擦层面……文化商品市场成为不断扩大的消闲市场”。[1](P191)事实上,现时代的很多批判活动是按照大众的口味策划、组织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基于对消费市场的考察而批量化地生产出来的。这与我们所在的这个商品社会中其他商品的生产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那些具有批判能力,甚至善于批判的人,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所谓文化资本,目我包装为职业的批判者——严格地说是职业的批判表演者。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本是交往行为的批判活动就演变为戏剧行为了,其目的则基于商业利润。这样,批判意识就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文化批判从总体上成为不断扩大的消闲市场。
第三,批判的私人化。就公共领域而言,真正的批判是建立在生命、生活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具体的私人活动是作为隐私而存在于私人领域的,除非作为一个总体,私人生活是不应该被批判所涉及和照亮的。但是,吊诡的是,现今许多人们一方面强调对隐私的尊重,另一方面以窥探、讨论别人的隐私为趣,即使在所谓的批判中也是这样。由于对宏大叙事集体无意识的告别,生活细节就成为批判活动关注的焦点,批判消费者的心理需要更是成为批判消费品提供者的生产逻辑。这样,在大家的合谋下,批判下降为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则上升到批判层次。结果,表面上是私人领域似乎被公共领域所殖民,本质上是公共领域为私人领域所颠覆。由于人们“囿于自身单一经历的主观性之中”,“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3](P45)因此,在热闹批判的表层下,可能实质性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在同一个圈子中,“所有人突然变得循规蹈矩,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每个人都在延伸和加强其周围人的观点”。[3](P45)而与其他圈子的人的观点却丧失了基本的可公度性。正是由于批判的私人性的极度增长,我们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怪异现象,即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批判比任何时代都多、都广,另一方面则是实质性的批判在萎缩、淡出。窃窃私语以众声喧哗的方式出现,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
二
批判成为一种消费活动这一现象,总体上是由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逻辑所造成的。但是鉴于关于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论说已经汗牛充栋,笔者更愿意去探讨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具体的、最简单的生产—消费活动是如何可能的——其实也就是探讨批判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他们共同的命运。
在理想的公共领域中,公众虽然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私人身份,但都以平等的方式交流意见,切近真理和人性。不过,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西方现代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1](P200)中国既然没有过成熟的公共领域,也就无所谓明显的公众分裂,而只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继续着传统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分层。确实,他们中的大多数秉承“价值中立”原则而成为“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用鲍曼的话来说,如今的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他们从批判地改变世界重归于解释世界。另外,依然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大众眼中的专家——继续进行着批判,但由于过于学理化,并不能真正进入到公共领域为人所见所闻,而只能在少数专家组成的圈子里“自产自销”,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批判性消费的一种特殊表现吧。当然,确实有部分知识分子借助媒介发挥着批判的作用,但他们的批判是否“有市场”越来越取决于民众的消费趣味和媒介的操作方式,而不单纯是真理、正义与人性。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在其不合乎大众趣味的时候,卷入了专家与大众的矛盾,专家自身成为围攻的对象;在其合乎大众趣味的时候,专家变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提供者。当然,从更大的尺度上看,即使那些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成为大众围攻对象的专家,在客观上也成了批判性消费的提供者,因为正是在“围剿”这些专家的过程中,大众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酣畅快感。
大众文化的崛起导致了大众趣味的权力化。[4]在当代,“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而在过去——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却从未被人注意过,它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一点儿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却越过舞台的脚灯,摇身一变成了主角”。[5](P5)作为登上历史舞台的强大力量,大众以热情关注和货币方式投票使自己成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当他们对别人,尤其是所谓专家的批判进行围观时,更多的是以观看“节目”的心态进入的,甚至把对批判的观摩当作一种休闲活动,正面的评价是“好玩”、“有趣”、“有意思”。相对于批判指向的事实而言,更关注于叙述方式和修辞方法,“怎么说”远比“说什么”和“谁在说”更为重要。当大众决意通过媒介(网络论坛、博客)表达自己的批判时,在其旨趣上与看电影、唱卡拉OK、蹦迪,健身没有原则的区别,成了一种休闲的爱好。正因为批判的私人化,专家与大众的界限也在分化中消弭(专家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也就会成为大众),大众随时可能卷入批判,成为批判的主角,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主角。但由于他们批判的当下性、感性、情绪化特点,自身就消解了批判的力量。[6](P418)而且,在多少有些精神分裂式的、无法透视和公度的众声喧哗中,大众更着意于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精神放松的惬意。当消费和休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时,批判也无处逃亡。乃至对于消费的批判,或对于作为消费的批判的批判都可能宿命地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与资源。
把批判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的是大众传媒,或者说,大众和专家都是以大众传媒作为展现自己存在的平台。但是,大众传媒首要的功能可不是连接专家和大众,而是把包括专家、大众在内的所有人与世界连接起来。在大众传媒时代,所有事件都首先作为媒体事件而发生,人们通过媒体而感知这个世界。但是,现代传媒对世界的“转播”决不是一一映射的,媒介总是“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7](P8)而从个体的角度看,“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与暴力,条件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7](P10)个体与媒体情投意合的结果——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7](P9)哈贝马斯也表达了与鲍德里亚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最终,新闻报道不得不装扮起来,从形式到风格都近似于故事叙述(新闻故事)。事实和虚构之间的严格的界限日趋消失了”。[1](P196)同时,大众传媒戏剧性传播的只是碎片化的世界图景。这样,人们在失去对世界的真实性把握的同时也失去了整体性的把握,在没有真实性和整体性保障的基础上的批判当然就只剩下游戏的性质。如果说,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传媒“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的话,[7](P9)那么,我们在批判、论辩的交流中获得的就是“现实所产生的眩晕”的眩晕,而且是碎片化的多重眩晕。正是在碎片化的多重眩晕中,我们产生了安全的幻觉与闲适的愉悦。
现代社会的景观化本质从总体上消解了批判。作为哲学概念的“景观(spectacle)”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提出的,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世界已经被拍摄”的影像社会,即景观社会。不过,“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转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的世界观”。而且,“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8](P3)也就是说,景观化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本体性的,人根本不能外在于景观。景观“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魇”。[8](P5、7)这样,所有活的东西都只是一种表征、显现而不是存在或占有成了生产、生活的最终目的。景观社会是一个“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8](P4)景观在造成一种娱乐的迷惑的同时,“使人们保持一种无意识状态”,人们只要去看,不要去思考和对话,因为“景观是对话的反面”。[8](P8、6)没有思考和对话,当然就做不到对它的本真性批判。景观社会中的人们宿命地趋向了一种单向度默认的状态,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沦为权威景观的奴隶。一句话,按照德波的说法,在景观社会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8](P8)
现代社会的符号化、景观化对于批判的消解更为重要地体现在对批判所需要的距离的剥夺。正如“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样,真正的批判是以对对象的间距化为前提的。没有恰当的批判距离,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整体的立足点去批判。由于高度现代性复杂的纵横编织——包括大众传媒的戏剧化、符号化、碎片“转播”和整体的景观化,我们今天都浸染在社会的大染缸中,匍匐在现代性结构的丛林之中,谁也不能置身于外(符号化、景观化使我们远离真实的世界的同时使我们深陷于暧昧的世界)。确如詹明信所言:“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屑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6](P505)高度现代性的反思监控系统更是巧妙地把一切事实上或可能的批判作为自己修正的营养。“总之,在不同的境况中,我们都隐隐感到不论是以局部实践领域成为策略基地的反文化形式(包括抗衡和游击战争等形式),或者是明目张胆地干预政治的创作形式……其反抗力量都难免被重新吸纳,而一切干预的形式都难免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除武装,取消了抗衡的实力。而实际上,反抗形式本身正好隶属于反抗形式加以吸纳的体制系统,原因是对抗的形式始终未能于其自身和所对立的体制系统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批判实力的距离。”[6](P505-506)没有批判距离的批判本身就是伪的,在这种批判中人们不可能“在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光辉中看到现实事物”,而只会“在幻觉和专擅之迷人的假象”[2](P20)中郑重其事地娱乐;而且,这种批判的郑重、严肃程度与其喜剧效果成正比。
三
从发生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批判活动本身就具有超越真、善的价值,它的过程与形式就可能造就一种特殊的审美氛围,让人领略到似乎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愉悦。也可以说,批判不仅对于有批判能力的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自我享受,而且对于围观和参与者来说也可以是一种享受。即使是在大众文化时代,批判的消费化倾向首先也要被积极地理解:这是大众对于理性化、抽象化的现代体制的一种造反,他们试图以解放感性自我的方式为生活“加魅”,对现代性的焦虑进行自我治疗和救赎。[4]因此,现时代的批判活动遭遇的问题不在于简单地突出了批判的美学功能与价值,而在于存在这样一种真切的倾向:消费以一种总体性的压倒方式,将批判彻底休闲化、商业化和私人化。因此,我们不得不重视批判的消费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批判的消费化使得整个文化生活水准下降。以往,商品、市场对于文化来说可能是形式的和外在的,但如今由于市场规律已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在消费文化的广阔领域,不再只是作品的传播和选择,作品的装潢和设计,甚至还包括作品的生产都依据销售策略进行。当公共交往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之时,确保公众的获取能力成为现代批判性活动的首要问题。如果不能为大众所感知,一切批判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根据。正如詹明信所明确指称的,现代大众文化生产的核心理念是“美感上的民本主义(aesthetic populism)”。[6](P423)由于大众的惰性,市场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从而从心理上增强各个阶层民众的获取能力。这就是“将获得文化的商品的条件降低至休闲水平。当文化不仅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变成商品的时候,它就失去了一些只有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掌握的因素,这里,‘获取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P192)把大众的获取能力作为第一要务乃是所谓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大众文化在本质上“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增加销售,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1](P191)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实质上消平了文化的等级性、垄断性。正因为批判成为一种消费,批判的门槛就极度降低,外行的批判、批评也得以制度化,以往无形中形成的文化准入条件荡然无存。这是一个“谁都可以是作家、批评家”的时代。批判者的水准和消费批判人的水准就决定了整个文化生活的水准。在大众文化的繁荣中,大家感受到亲切、时尚,但从历史的高度看,这种文化只是在一个较低层次上的循环,文化的民主性、开放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高质量的文化批判性。
批判的消费化使得批判所能开启的可能性被窒息。从应然的角度说,公共领域中人们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就建立在专家和大众的批判意识与能力的基础上。但是,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的逻辑却“和民主制度歌颂人民是为了让它待在原地(就是说让它不要参与社会政治舞台)一样,人们承认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是为了叫它不要像这样在社会舞台上进行表演……公众和公众观点,就这样受到了诅咒,成为了仅仅满足于消费的消费者”。[7](P56-57)把大众锻造成普遍的接受者,也就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出市民私人性的假象”。[1](P188)消费者感到一切都是人性化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其实不过是一种主体幻相。各种可以选择的批判也充当了个性化心理按摩的作用,而自己卷入的批判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1](P191)“说说而已”成了现时代很多人的口头禅。就其实质而言,批判的消费化形成的是貌似个性化的普遍人格。多元、极端、出位、酷、炫的背后具有一种深刻的同一性,那就是批判的私人化使得大众满足于单向度,丧失了或关闭了本来可以由公共批判开启的其他可能性。世界是我们生命之诸多可能性的总和,对可能性的窒息就意味着我们在实质上有失去世界的可能。“当人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当人们只允许世界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公共世界也就走到了尽头。”[3](P45)我们的生命将根本受损,我们的生存将遭受危机。
批判的消费化最终使得批判与资本妥协,成为资本的帮凶。就现代性的社会批判而言,其核心无疑是指向资本逻辑的。但是,当批判出现消费化倾向时,事情就发生了荒谬的逆转。消费的逻辑不仅体现在批判性文化商品的流通中,而且已经进入批判的发生之中,批判从主体在场向他者——尤其是作为批判的消费者的他者——在场转变。为了具有消费的价值,态度、形象、选题、叙述方式变得格外重要。所有这些都成为批判生产者反思性地建构自己形象的强烈暗示和重要资源。真诚、真实逊位,表演在所难免;戏剧行为粉墨登场,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如火如荼。尤其是当批判生产者意识到自己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时,他们不仅倾向于以一套二元对立的符号系统与大众区隔,标识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会将文化资本、符号资本预期为或直接兑换为货币资本。当然,这一切都与大众传媒分不开。因此,当批判作为消费品出现时,批判妥协了,直接地是与大众传媒妥协,但这种妥协是以与大众妥协为借口的;在本质上,批判的妥协是对资本的妥协。在资本统治的时代,批判只是再现,甚至是再生产了资本的逻辑,对资本逻辑似有还无的批判充其量只是发挥着合目的的“牛虻”作用,使资本更为健硕。这样,现代社会中的批判性活动以对资本的批判始,以与资本的妥协终。怎不令人唏嘘之至!
从总体上说,现时代批判活动的消费化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对批判消费化倾向的批判自身也不例外。但是,问题一经揭示,思想就会意向于对这一状况的超越。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于或多或少从事着批判活动,甚至还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学者来说,能否谋求整体解决方案可以存疑。但是,在似乎是命定的批判的消费化倾向中,凸显和坚守自己的真诚是有可能做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7-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