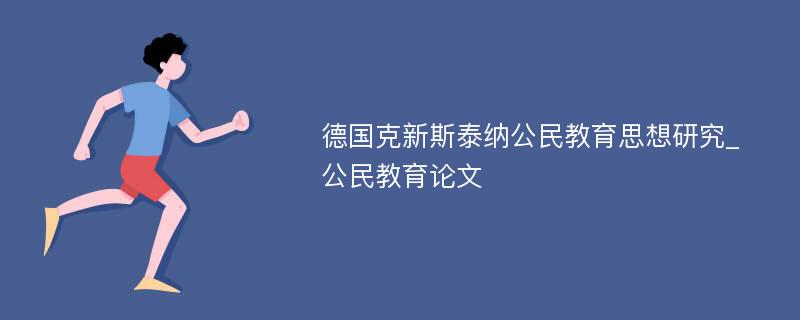
德国凯兴斯泰纳公民教育思想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公民论文,思想论文,凯兴斯泰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新教育运动中,乔治·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育家。他的公民教育思想循着费希特开辟的道路,将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并不同于在国家统一与崛起过程中产生的傲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的劳作教育思想,适应德国当时生产力发展对人发展的需求,将教育与生产劳动、职业技术结合起来,与只注重读书教育有别,当然也有别于当时西欧新学校注意从游戏中学习的普遍趋势;他将“劳动教育”纳入“公民教育”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培育“有用的公民”的观点,较辩证地反映了科技进步、政治民主、国家富强三者统一的关系,更加符合魏玛共和国的进步要求,不仅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产生了积极的现实作用,而且对二战后德意志民族教育的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
一、关于公民教育
凯兴斯泰纳指出:“国民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1](P220)公民教育是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主题与主体,此处重点阐述公民教育的性质、概念、目的任务和部分内容。
(一)公民教育的性质
凯兴斯泰纳指出:公民及公民教育的定义前提是立宪国家,但在专制立宪的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国家公民”,“国家公民的概念和民主立宪国家的概念是相互交替的”[1](P214),当且仅当民主立宪的国家才有公民及公民教育,因为“旧的专制国家在必要时可以抛弃不要的东西,而在新的人民国家里则必须保留,那就是对人民的最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对人民进行国民教育”;“民主的国家宪法要求具有高尚稳健的精神状态”,“凡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地方,在那里,只有当全体人民都学会以国民的身份去感受、去思维并且去行动时,才会有一个健康兴旺的国家出现”[1](P213)。也就是说,凯兴斯泰纳认为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民族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怎样理解凯兴斯泰纳的民族观和民主观呢?凯兴斯泰纳经历了德意志民族的分裂、统一与崛起,和大多数德意志人一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强调教育的民族性,指出教育者的全部教育必须具有民族精神的特征[1](P190),“真正代表民族特色的东西,那些出现在我们的歌颂伟大祖国的歌曲与诗作,出现在我们为表现伟大男性或女性人物……而创作的书画与戏剧中的真正代表民族特色的东西,必须得到最精心的培育。”[1](P191)但他对当时德国蔓延的民族主义情绪持批评的态度,称其为一种病态的、十分愚蠢的自负,要求清除课外读物、历史书籍、歌曲选集中的民族主义“杂草”。可见他的民族观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别,是健康的、开明的。他热烈歌颂魏玛共和国,称其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制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国家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1](P213)。魏玛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见凯兴斯泰纳的民主观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概而言之,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观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公民教育。
(二)公民教育的概念
凯兴斯泰纳所谓公民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国家意识的公民。这一概念又以国家、国家意识、公民三个概念为基础,要正确理解公民教育的概念首先就必须正确理解这三个概念。
凯兴斯泰纳认为,国家是一种道德集体。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人总是要不时地相互打斗,而且又不时地互相调和,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这种争斗越来越人道一些,让这种调和越来越自愿一些,于是道德集体的轮廓便在知识者心目中慢慢地形成了,这就是国家图像;在国家这种道德集体之中,利益与不同观点的斗争在寻找着以越来越具有人类尊严的方式去解决不断出现矛盾的方法,而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始终与所有其它各种均衡了的利益相一致。由此,知识者便会领悟到各种国家文化都是建立在斗争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法制”与“文明”就产生了,成为国家伦理概念。“文化,特别是国家生命就是在这种不断地斗争与调和之中向前发展的”[1](P241)。由此可见,凯兴斯泰纳的国家概念,实指人与人之间秉持“法制”与“文明”伦理概念的道德集体。这一“法制”与“文明”完善结合的集合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体,在这一集体中,国家的法律制度将被自觉遵守,而不再需任何强制的措施,为了实现此种理想,公民教育就有产生的理由。
国家既然是道德集体,在凯兴斯泰纳那里,国家意识其实就是道德意识,就是“某个个人道德自律性”[1](P242),“是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觉权和由此产生的自愿参与社会伦理发展的个人责任感。”[1](P306)。他认为这种意识不同于单纯的法制意识,也有别于纯集体意识(或者叫社会意识),因为这两种意识是以法制为基础的,而道德的国家意识虽然屈从于积极的法制,却始终关心着这种法律制度必须按照国家集体道德化的标准,越来越道德化。换言之,凯兴斯泰纳的“国家意识”就是法制意识与文明意识的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外在的道德意识内化为自觉的文明意识,同时法律制度文明化,合乎多数人的利益。
凯兴斯泰纳认为,在理想的国家集体中,公民必须具有三种美德即:“公正”、“合法”及“劳作”。首先,公民必须具有“以公正为内容的道德勇气和受合法情感支配的忘我友爱的精神”[1](P251),学会从公正与合法性的角度去解释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对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公民的关系,一方面为社会公正具有“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高度负责”的“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遵守集体法律,时刻准备着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集体命令。其次,“公正”、“合法”并非凭空产生,是在集体生活尤其集体劳作之中产生的,集体与个人的文化财富的建设也需要脑力的和体力的劳作,故劳作也是公民必备的美德。具备“公正”、“合法”与“劳作”的品德服务于现有的国家的人,凯兴斯泰纳就称之为“有用的国家公民”[1](P15)。
(三)公民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凯兴斯泰纳认为,公民教育终极目的是教育公民“获得”国家意识。他指出:“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1](P243),也就是说使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通过教育而获得自觉地参与国家生活的习惯,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而逐渐向着法制与文明国家的理想迈进。可见,道德的国家理想是国民教育的起点与归宿。至于“文明与法制的国家理想”,他具体解释道:我们说它是法制国家的理想,其条件是,经过奋斗得来的集体应该能够按照正义与公理的准则,调理全体公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它是文明国家的理想,其条件是,这样的集体必须保证每一个公民无一例外地能根据自己才能的大小,为伦理的文明价值而服务[1](P241)。
根据公民教育的目的,凯兴斯泰纳确定国民教育的任务。其二,建立学校各种学生联合组织,劳动场所和采取正确的劳作方法,教育学生习惯于为集体服务、尽义务,在自愿参与、服务、相互关照及自愿奉献的情况下,从道义上促进这一集体的发展;其二,通过共同劳动来唤起对一切行为极端负责的责任感;其三,必须锻炼学生学会按照正义和公理的准则,去解决劳动集体中出现的利益争端问题;其四,通过某些具体事例,培养学生将服从全体利益变成一种自觉的想法[1](P140-214)。总之,国民教育的任务是创造具体的条件,通过实践磨练,培养公民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及各种具体的能力,使其能切实地服务于现有立法国家,使之越来越接近于道德集体这一理想。
(四)公民教育的内容
凯兴斯泰纳认为公民教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进入职业社会承担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进行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这种教育,在由近及远的多种层次的集体组织中进行,近如身边的小集体远如国家大集体。
关于小学公民义务与权利的教学任务,必须使孩子懂得下述问题:
(1)集体通过公共福利给我们提供了些什么?
(2)对于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由此产生了哪些义务?
(3)据此,集体与其全体成员道德关系中,存在着哪些相互的影响和作用?
(4)什么叫做集体的公民,如家族、学校、地方、国家集体的公民?公民可以提出哪些要求?他们必须对哪些要求感到满足,以及他们必须全力地保护哪些机构?
至于高年级或者大学内,他认为可以保留“通俗国家学说课”即公民政治课,以使学生了解国家的任务,激发他们产生历史责任感及对祖国的热爱。
第二,进行集体观念的教育。个性的形成离不开集体,离不开实践锻炼。通过为那些小范围的联合组织如家庭、学校、青年联合会等服务过程中,培养学生为某一道德集体服务的习惯,进而培养学生为国家劳动集体服务的习惯。具有这种社会习惯的人,方有可能成为以正义与合法为原则具有道德勇气和忘我精神的“自由公民”。为此,学校能够而且必须做的是,用理想的国家集体的思想和为实现、为保卫理想的国家集体而献出自己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人物的尊敬与爱戴,充实学生的心灵,唤起在国民义务活动中必要的奉献精神。
第三,进行权威感教育。他说,对人类天性的缺陷来说,没有权威,便很难有真正的文化。他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国家事务中,总得有出类拔萃的人当领导,成为“高价值的承载者”,其他人必须承认并自觉自愿地服从他们的领导,否则国家将会陷入无政府的状态。如果缺少权威感教育,则永远解决不了秩序的混乱。他认为权威教育是充满道德勇气的权威教育。一方面,必须对那些因其精神与道德能力而被任命的权威承载者的人们进行必要的国民教育,使其完全具备公正与合法的思想意识以及一丝不苟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教育公民不仅崇敬、服从权威,而且要敢于谴责那种无能的或者已经忘记自己职责的权威承载者并与之进行斗争;此外,一切权威的概念都随时代变迁和文化进步而不断更新,故公民教育应该更新文化观念及权威概念。
第四,进行民族感教育。民族感是“一种集体主义情感”,以集体为出发点,或来自共同的以外在事物为目标的成功抱负,或产生于完成共同的劳动任务。他分析并评价了三种类型的民族情感,一是从高于其他民族的臆想中或者从真正的“光辉形象”的“觉悟”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二是在其他民族为它们施放的真香或假香的烟雾中探寻其价值。前者自高自大,后者自欺欺人,凯兴斯泰纳对这两种民族感皆持否定态度。他肯定地提出第三种民族感,这种民族感不是在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而是致力于自身奋斗,履行自己的道德职业。这种民族自力更生,有自知之明,只有当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或别的民族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时,他们才感觉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充满着文化使命的觉悟。他称赞英国人的民族观在不小程度上是立足于这种觉悟的;认为德意志民族过去具有,现在也应具有这种自觉、自省、自立、自奋的价值观[1](P299-302)。为培养这种价值观,一是教育本民族尊重真正的价值及其承载者,也就是尊重优秀的文化及其创造者、领导者的权威;二是教育公民在为集体服务、为国家理想服务中,同甘共苦,无论失败或成功皆怀有希望,这样才能帮助德国人在我们心中培养起与多数民族一样合理的民族情感的堡垒。
第五,劳作教育。劳作教育不仅是凯氏公民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是他公民教育思想的现实基础,同时是他教育实验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在下面专门展开论述。
二、关于劳作教育
1908年1月12日,凯兴斯泰纳应瑞士苏黎世之邀,在苏黎世彼得大教堂举行的纪念裴斯泰洛齐诞辰162年会议上提交“按照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建立起的新型学校”的论文,提出“劳作学校”的概念,此后,他不但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而且将之化为实践,遂产生广泛的影响。那么,劳作学校有何意义,其原则、任务有哪些?下面我们逐步来作探讨。
(一)劳作学校的意义
德语“arbeitsschule”汉译“劳作学校”或“劳动学校”;其中“arbeit”一词,汉译为“劳动、工作、劳作”,德文原意指从事农业的“苦工”、“贱役”,含贬义,后来词意的外延逐步扩大,兼含有手工技术劳作及一般需要体力的劳动,渐含褒义;到了近代,该词也应用于脑力劳动方面,即所谓“精神的作业”[2](P116)。凯兴斯泰纳虽未直接阐释“劳作”含义,但从其著作可知,凯氏不仅赋予该词体力劳作与精神劳作两方面含义,而且热情赋予该词人类文化的创造性的积极意义。凯兴斯泰纳正是从劳动与人类文化财富的关系中来理解“劳作”的意义及劳作与教育的关系。
他指出:人类通过劳动创造文化财富;而人类的文化财富,也都打着其创造者的精神烙印,内含着其创造者的独特的精神结构,具有其创造者的独特个性。既然劳动创造文化,既然每一种文化财富都会有一种精神结构,那么,只是具有同样的,或者说,近乎同样的精神结构的人,才有可能接近它;而且这一文化财富只对于“接近”它的人,才会变成精神财富。“接近”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创造性的劳动”。靠记忆知识结构、艺术形式、道德观念,构不成教育:教育不能不劳而获。只有通过受教育者有个性的活动也即劳动,受教育者的精神结构才能与文化财富的精神结构同化于一体并不由自主地受其感染,文化财富才能发挥其教育价值,因此说:“教育需要靠劳动获得”,“因为,只有通过劳动,精神作用才全部形成,而且更有创造力……只有在劳动活动中,思想与道德修养才得以锤炼和提高。”[1](P40)他把“储存于文化财富中的精神结构”称为“文化财富的内在教育价值”,认为要使内在价值产生就必须靠学习者的劳动。基于此,他给劳作学校下定义:“劳作学校正是这样一种学校,她通过她全部办学的方式和方法,达到其教育财富和教育价值的产生。”[1](P42)
(二)劳作学校的原则
“劳作学校”,顾名思义,其总的精神就是“劳作”二字,但是又怎样具体理解“劳作学校”的“劳作”二字呢?当时德国“劳作学校”成为时髦名称,某些学校只是在教学时设法让学生动动手或点缀些生产课即名之曰“劳作学校”;对此凯兴斯泰纳不以为然。因为在凯氏那里,“劳作”是文化的创造,不是指简单的体力活动,也不是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的简单相加,其本质是“创造性”,离开“创造性”的所谓“劳作”充其量只是“活动”而已。把握“创造性”这一本质的教育与教学活动就是“劳作”,否则只是一般活动。教育与教学的“创造性”就是体现在能“启发”学生主动积极思维,使学生成为具有创造力的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启发性”是“劳作”在教育与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劳作学校”的总原则。劈柴担水都是道。当且仅当贯彻“启发性”总原则,一所国民学校方可称之为劳作学校,而不是看其是否贴上单纯手工操作的标签;一个教育者方能在各种教育与教学活动中恰当、自如地选择、组织、使用“方式与方法”,使“劳作”精神具体、生动、深刻地得以体现,发挥出现实的生命力。
本着“启发性”这一总原则,凯兴斯泰纳具体阐释手工劳作课和文化课教学原则。
手工劳作课的原则有三:即模仿、准确和灵活。学生手工劳作起于模仿,“几乎所有领域都始于以模仿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表达手段。甚至那些在表达能力上具有最深造诣的人,如那些杰出的艺术家们,在他们起步创作时,基本上是模仿者……待到学生在运用表达手段时,感到有足够的把握,这时教育者才可以逐步给他们提供自己独立创作的机会。”手工劳作不是游戏,是培养劳动者,不是业余爱好者。必须将那些仅为爱好艺术而劳动的有害思想排斥掉,严格要求他们一丝不苟地对待他们自己的劳动,培养学生的“准确性”习惯。凯氏认为德意志民族正是依靠“准确性”的民族习惯才取得了最根本的成就[1](P49-50)。建立在“模仿”与“准确”的基础上的“灵活性”,这是创造性的最终体现。
至于文化课教学原则,不是填鸭灌输、死记硬背,而是吃透教材,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引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感悟。他说:那些教育人们从同代人的描绘和其它原始材料中,或从当代历史作品读物中独立获取历史知识的人;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各类遗留作品进行戏剧表演,使学生对创作内容的体验和理解变得更加深刻的人;那些在劳动集体中,为培养学生在社交活动中的洞察而创造机会的人;那些引导学生参加的各种实验而把握物理、化学、生物学规律和要点的人,他们会按照创造性的劳动原则组织课堂教学[1](P39)。
(三)劳作学校的任务
根据培养有公正、守法之心和能劳作的、有用的国家公民的公民教育目的观,凯兴斯泰纳认为,劳作学校的任务有三项:(1)职业教育的任务,或者就业前的预备教育任务;(2)职业教育的伦理化教育任务;(3)人们在其中从职的集团的伦理化。
凯兴斯泰纳说:对于国家里的个人来说,第一个要求是,他应该有能力而且愿意承担这个国家里的任何职务,也就是说有能力从事任何职业活动,并因此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国家目标的实现,所以国民学校的最初任务就是就业前的预备教育,即职业教育。为说明其合理性,他引证裴斯泰洛齐观点:人类智慧建立在对其最直接的人与事的了解的牢固基础上,基于对身边事物处理能力的大小;职业教育是教育人的大门。他强调职业教育要手脑并用,心智技能与动作技能要紧密结合;要以激发学生实践兴趣为中心再过渡到纯理论兴趣,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要培养严谨的习惯和劳动热情,这都是未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必需的准备。为此,他认为配备专业教师开手工专业劳动课,要配备实习劳动场所,如工厂、苗圃、学校厨房、缝纫间、实验室等。
如果说第一项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那么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则在于思想品德教育。第二项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具体包括从事本职的自觉性、责任感和对同事的关心体贴;第三项任务是“指导学生为实现他们在其中生活谋职的大集体的道德伦理化而共同努力”[1](P32),也就是说要培养学生公正与合法之心。为此,凯兴斯泰纳根据费希特“经济劳动集体作为对下一代人进行教育的要素”的观点[1](P28),指出关键要建立健全“符合劳动集体精神的学校管理组织”,让学生在劳动集体学习生活。
三、对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的评价
凯兴斯泰纳是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教育家,作为历史人物,欲对其评价,首先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
尽管凯兴斯泰纳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认为公民教育不存在于专制国度只存在于民主共和国,但客观地说,德意志历史上的公民教育思想大体有两条道路可循,一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公民教育,一条是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公民教育。第一条道路的开拓者是费希特。费希特为德国思想界变化之枢纽。1806年前,他崇奉康德大同主义,视欧洲为全体欧洲人的基督共同体,并讲若能持此观点,我们对历史上的分合盛衰则安之若素。但是,1806年耶纳(Jena)之战,普军土崩瓦解;1807年《特尔锡和约》(Peace of Tisit),普鲁士丧权辱国。这对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朝野尤其思想界触动很大,民族感陡增。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发表《告日耳曼民族》演说,认为:日耳曼全体与欧洲其他各国之区别,乃本诸先天;日耳曼民族之惟一使命乃在于推翻征服者、统一全民族;基于此,形成自己的公民教育思想。费希特虽然由大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希望民族统一与独立,但他政治上仍倾向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教育思想仍汲取了康德民主的精华,其公民教育思想熔民族性和民主性于一炉,不失始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主色彩仍十分鲜明,代表着德意志民族公民教育的正确方向。但普鲁士乃至以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实际制定并采用的国家主义教育政策则是基于保守主义的立场,这种保守的国民教育到俾士麦时期则演变为军国主义教育,这与费希特开创的民主的公民教育道路有主要区别。
凯兴斯泰纳一生亲历祖国的分裂、统一及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作为教育家和思想者,他的思想首先体现着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公民教育成了他教育思想的主题和主体。他的公民教育思想虽未必完全像他自我标榜“立足于真正的人爱和对真正人类尊严的崇敬”[1](P215),但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的,若追根溯源,他的公民教育思想根源于费希特。他说:“近百年来,我们始终遵循着费希特在他《告德意志民族书》所提出的建议。”[1](P28)这里的“我们”至少包括凯兴斯泰纳本人,并非断章取义。他们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公民教育思想体系一脉相传,与狭隘的德国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有本质区别。这可从三点分析。首先,费希特与凯兴斯泰纳的立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德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讲究铁腕专制。其次,费希特与凯兴斯泰纳有清醒的民族自觉意识,能看到其他民族的长处与自己民族的不足,有一定的人类情怀;而德国狭隘民族主义者狂妄自大、自欺欺人。第三,德国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公民教育单纯起自民族战争,带有歇斯底里的民族复仇情绪,后来发展成法西斯教育,助纣为虐,对法西斯侵略战争负有难辞其咎的罪责;费希特与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及民族战争中形成的免于征服要求独立的正义民族感,富于理性,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对德国社会进步尤其二战后德国教育民主化改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战后,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反省比较诚恳与深刻,民主化进程比较彻底与合理,是与他们本民族就具有一条富于理性和民主的民族观的优秀传统是分不开的。
除继承费希特外,凯兴斯泰纳还继承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的劳作教育思想,并把它和费希特的公民教育思想传统及当时德国具体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形成将职业与伦理、劳动与发展、个人与集体相统一的独特的劳作教育思想,对当时魏玛共和国尤其二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开辟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具有现实意义的劳作教育之路。
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不是两张皮,毫不相干,而是有着血肉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相互印证,相互实现。公民教育是劳作教育的目的与归宿,劳动个人离开集体及集体理想难以成长为公民。离开了公民教育,劳作教育就成了单纯的个人谋生教育,难以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公民教育是通过劳动教育来实现的,国家公民离开集体劳动难以成其为公民,离开劳动教育,公民教育就成了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并非是与“国民学校”有别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学校,它仍然是“国民学校”,就是说,只有具有“劳动集体精神”并且能“启发学生创造力”的国民学校才是劳作学校。
凯兴斯泰纳的教育思想虽然以其民主性和开明的民族观而显示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仍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借鉴凯氏教育思想时还应有阶级批判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