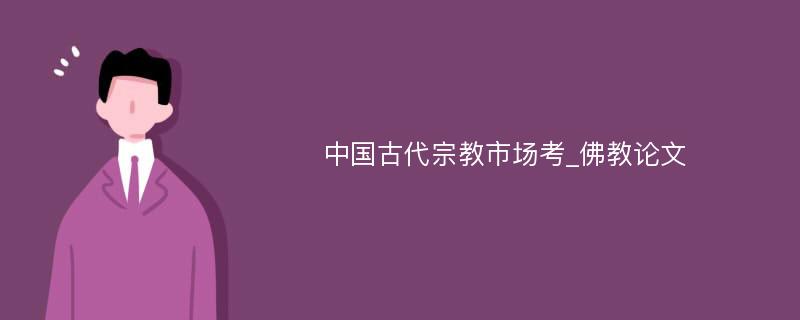
中國古代宗教圖書市場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古代论文,圖書市場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宗教信仰領域裡探討市場與交易,似乎有些褻瀆。正是這一成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真實。實際上,人們因為信仰宗教,需要經書,需要催生了宗教圖書市場,神聖的信仰與世俗的功利奇妙地混雜在一起。本文擬鈎稽相關材料,對中國古代的宗教圖書市場作一全面考述。 一、宗教信仰帶來的圖書細分市場 就中國古代而言,因為宗教信仰不同帶來的圖書細分市場主要有佛教類圖書市場、道教類圖書市場以及善書市場。 與人們一般的圖書需要不同,對於佛、道而言,不僅識字的信徒需要經典持誦講讀以明教義、除罪孽,甚至不識字的信衆也需要通過供養經書來求得福報。佛、道都有供養經書祈福消灾的說法,即不需要閲讀經書,只要存心禮敬、予以供奉也是在做功德。除了供養某一部或幾部經書,還有供養整部佛藏或道藏的轉輪藏。 所謂“轉輪藏”,宋代李綱《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云: 有大導師善慧大士以方便智設妙圓機,創轉輪藏以貯佛語及菩薩語,關機斡旋,周行不息,運轉一匝則與受持誦書寫一大藏經教等無有異。夫一藏教,其數五千四十八卷……① 文中的善慧大士是南朝蕭梁時的傅翕,《五燈會元》卷二有傅,據說輪藏是由他發明的。而在宋代羅願《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裡有關于轉輪藏更具體的描述: 傅氏鑄銅以為式,其植若箸,橫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為昆侖海水,仿百物以為飾。② 推動輪藏轉一圈,就等於把藏在其中的佛典持誦一遍,這無論是對識字還是不識字信衆來說,都絕對是方便法門,但不識字者對此尤有需要。有別於一般藏書樓“藏”與“用”的結合必須經由“讀”,宗教利用人們虔誠信仰的熱情,居然巧妙地將大藏的“藏”與“用”脱離“讀”這一環節,簡捷到只需輕輕一轉。在輪藏《大藏經》之外,寺院當然也藏有其他佛教圖書與非佛教圖書,其中其他佛教圖書主要包括“大藏之外的單本譯經、大藏之外的中國僧人撰著、疑僞經、宣教通俗文書、一般寺院文書、其他文字佛教典籍等等”③。就寺院藏書而言,顯然與中國藏書文化傳統有關,但寺院之所以建輪藏,則更多是受宗教因素影響:一方面是因為佛經裡包藴著佛法,信徒禮敬三寶,以此來供養藏經是虔敬之心的表現;另一方面是因為信衆相信轉輪藏可以修福積德,無論僧俗都對此有極大熱情。 宋代不少寺院都造轉輪藏,葉夢得(1077-1148)《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提及:“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來,所至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六七。”④據此,當時一半以上的寺院都建轉輪藏。而宋人文集中多有為寺院造輪藏所作記文,例如黃庭堅《山谷集》卷十八有《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山谷別集》卷四有《普覺禪寺轉輪藏記》等,這些均可佐證寺院造轉輪藏盛行一時。 轉輪藏中所藏佛經,有朝廷頒賜的,但大多來自于信衆印施或寺廟購置。例如,上述羅願文中提到:“先是,紹興中里人餘聰買其書,號四大部,置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⑤再如,宋代孫覿《崇安寺五輪藏記》提到該寺輪藏造成後,“右承直郎高鳳印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匭中”⑥。又如,宋代楊萬里《興崇院經藏記》提到,江西安福縣興崇院僧海睿“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於開元寺以歸,為卷五千四十有八”⑦。又如,金代趙渢《濟州普照禪寺照公禪師塔銘》裡提到智照為了充實輪藏,聽說京師宏法寺有藏板,於是前往印造,“凡用錢二百萬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歸”⑧。顯然,各寺廟造轉輪藏的需要構成了整部《大藏經》售賣的主要市場。值得一提的是,有時轉輪藏反過來也能為寺廟帶來收入。例如,宋代費衮《梁溪漫志》卷十“惠歷寺輪藏”條載:“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⑨而南宋劉一止《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也提到:“而轉輪藏施利之人未嘗有虚日。”⑩ 與佛教一樣,道教也極為重視道經的保護與供奉,宣揚供奉經書可以得無量福報,在《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二“寫經品”中還專門談到如何作經藏(11)。從宋代開始,道教也有轉輪藏。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下詔訪求道書,第二年,福州知州事黃裳即上奏請求建輪藏以藏道經。(12)徽宗時,西京登封崇福宫、南宋時鄞城蓬萊觀、臨安延祥觀、宜興通真觀、新建建德觀、奉新昭德觀等都建有輪藏。(13)而《四川通志》卷二七載江油縣寶圌山有淳熙八年(1181)所建“飛天藏”(14),亦即轉輪藏。道教造輪藏具體方法,據元代虞集《龍虎山道藏銘》所載(15),與羅願所述佛教造輪藏法無異,道教規摹佛教處頗多,或即是受後者影響亦未定。入藏轉輪的道藏,有的道觀是來自於頒賜,有的則是由道觀募款購置或由信衆購施。能够得到官方頒賜的道觀畢竟數量有限,衆多道觀恐怕主要是通過購買建立起自己的經藏,這對於道教類圖書市場無疑有刺激作用。 有别於人們一般的圖書需要,在供養經書可以祈福消灾這一信仰的影響下,信徒無論識字與否,都有可能供奉經書,“用”與“讀”的剥離會直接導致信衆對于經書總體需要量增大,這對於佛、道類圖書市場的繁榮是有促進作用的。 在中國古代,除了佛、道二教,人們普遍相信,行善能够給行善者自身或其家族後人帶來福報,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宗教信仰。行善信仰的來源很複雜,儒、釋、道三家對此都有貢獻。為了勸人行善,中國古代從宋之後産生了以《太上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為核心的一批書籍,這些書被稱爲勸善書,簡稱善書。明清時期圖書出版已經嫻熟運用插圖技術,為了更廣泛地勸誘人們行善,這一時期的善書也普遍以繪圖解說相關觀念,以便即使是不識字的田夫村婦及童孺等也能由觀圖而興起善念,因此出版了諸如《感應篇圖說》、《陰騭文像注》、《陰騭文圖證》、《陰騭文圖說》、《覺世經圖說》等圖說善書。(16) 因為人們信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産生了對於善書的需要,但“因為是解說勸善的書,而不是為了贏利而出版的,很多情况是無償地施于他人”(17)。不過,善書的流通雖然以印施為主,但也有印賣的。清光緒間刻《太上寶筏》附有“善書流通十四法”,其中就有“貿易流通”一法:“書坊刷印善書,或發兑于鄉會大比之年,或發兑于文宗按臨之地。”(18)可見,因為人們行善的信仰,帶來了圖書細分市場中的善書市場。 二、功德觀念背後的宗教圖書市場 由於經書載述了教義,因此經書的流通就關乎教義的傳播。出於傳道弘法的考慮,不同信仰的宗教都把積極參與經書流通視為信徒的另一重要功德,以此勸誘信衆複製、傳播經書。為了做功德,信徒們熱衷於寫經、刻書,但因種種因素制約,不可能每個信徒都直接去寫經、刻書,這種宗教熱情客觀上就為專門製作出版經書的圖書出版商提供了掙錢機會,宗教信衆只需要奉獻錢財,就可以在圖書市場中獲得需要的功德,可謂各得其宜。 我們先看佛教。《法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中釋迦牟尼說:“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19)寫經造藏有功德,甚至像唐代顧况《虎丘西寺經藏碑》裡所說可以成佛(20),這個誘惑對于佛教徒來說是難以抵擋的。在這種功德心理影響下,歷代佛教徒虔誠寫經、刻經以及造藏。我們從現存的很多佛經上,都能看到信徒發心寫經的題記或施捨資財刊雕經板字樣,而戲曲小說中對此也多有記叙,例如《紅樓夢》第88回就提到賈母發願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一部《金剛經》,又要家中女眷寫三百六十五部《心經》,其中《金剛經》是“發出外面人寫”(21)。顯然,信徒為了消灾祈福積功德,可以自己寫經或刻經,也可以捨財由別人代勞,後者就為佛經類圖書造就了一個需求極大的市場。另外,像《太平廣記》卷102—116總共有十五卷故事講述持誦、書寫佛經以及因為對經像的態度導致的報應,其中102—108所録故事與《金剛經》有關,卷109與《法華經》有關,卷110—111與《觀音經》有關,卷112—116與“崇經像”有關。卷116《僧儀孚》云: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賫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户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羡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舍財修功德,以孚為鑒戒(出《冥報録》)。(22) 這個故事意藴很豐富,從我們的角度看,至少從中可以看到佛經市場客觀存在,甚至佛教徒中也有販賣經像以牟利者。而故事的本意,除了道德警戒之外,格外强調的是不能將神聖的佛經作為牟利對象,否則會招致慘酷報應。也就是說,對於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來說,自覺、積極傳播佛經是修行中的一種功德,但若從中獲利,則反而成了罪過。因此,佛教信徒刻經一般不以牟利為目的,多為施送以弘法,即使出售也僅僅按紙墨印工核算成本價,例如晚清著名的金陵刻經處就為此常常陷入入不敷出之境(23)。不過,如下文我們將看到,有些一心牟利的經坊主將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置於腦後,印售經書時也索要高價。 中國古代佛教經書的製作,與其他圖書製作一樣,包括抄寫與刻印兩種方式,元人張之翰《普照寺藏殿記》就提到,“初經之未廣也,或以銀,或以金,或以血寫者嘗多;及經之既廣也,印於福,印於杭,印於蘇”(24)。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内地,但在唐以前,雕版印刷術尚未發明,佛經主要通過抄寫的方式傳播。唐初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之後,逐漸采用刻印的方式傳播佛經。但需要注意的是,信徒們為了表達心中的虔誠,仍有不少人會選擇抄寫方式,“從現有資料看,直到明清,依然有人修造金銀字大藏經。到了現代,雖然已經無人修造完整的金銀字藏經,但依然有人爲了功德而寫經、寫金銀字經乃至寫血經”(25)。 信徒自寫、自刻之外,信衆對於經書的大量需要帶來了活躍的佛經圖書市場。早在寫本時代,除了官方有專門機構抄寫佛經外,民間也有人以替人寫經為生。例如,《魏書》卷五五《劉芳傳》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26)寫經職業的出現,說明其時捨財寫經的人很多,有一定的市場需要,《陳書》卷二六《徐孝克傳》就提到徐孝克把陳後主賜給他的石頭津税錢“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27)。 在唐代,民間寫經由個體行為發展到開鋪設肆,規模更大,開元二年(714)唐玄宗《禁坊市鑄佛寫經詔》裡就提到“如聞坊巷之内,開鋪寫經,公然鑄佛”,以致“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饑寒”,寫經造像求功德的狂熱信仰已經危及信徒的正常生活,唐玄宗因此下令:“自今已後,禁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為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禮。須經典讀誦者,勒于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寺觀并准此。”(28)這道詔令等於宣布民間寫經違法,只允許僧人寫經供應。不過,在狂熱的宗教信仰以及猶如宗教一樣令人發狂的金錢欲望的聯合衝擊下,這道禁令能堅持多久很令人懷疑。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因為能够更快捷地複製圖書,也被人們用來雕印經像,例如,《僧園逸録》載玄奘曾經“以回鋒紙印普賢象,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29),而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就是佛經《無垢淨光大陁羅尼經》。最晚到了唐末,坊間已經有專門印售佛教經像咒語的店鋪,例如成都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西川過家雕印佛經等。(30) 宋代雕版印刷術成熟,官方刻有《開寶藏》,這是中國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朝廷專門在太平興國寺設立印經院印刷流通藏經,後來經板轉到顯聖寺,由該寺負責印造流通。除非皇帝下令頒賜,否則要想得到藏經是必須購買的。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日本僧人成尋三月廿四日記載了顯聖寺印經院準傳法院札子,其中提到:“切緣所管經版萬數浩瀚,逐時印造。每一歲并新譯成經共五千四百二十五卷,并系一依自來舊印經院條式内數目出賣。”(31)在該年四月六日,成尋又記道: 五臺副僧正來坐,京中僧多以群集。華藏大師、慈照大師等稱“九地菩薩”。依路次寄印經院買取《千鉢文殊經》一部十卷、《寶要義論》一部十卷、《菩提離相論》一卷、《廣釋菩提心論》一部四卷、《圓集要義論》四卷、《祥符法寶録》廿一卷、《正元録》二卷,與錢一貫五百文了。(32) 除了官刻《大藏經》印刷出售外,宋代寺院刻有《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磧砂藏》等大藏經,其中《磧砂藏》實際上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刻成。由于官刻大藏請印相對不易,一旦有私刻大藏,自然會受到請經信衆的青睞,因此從元代開始一直到明代,頗有請印《磧砂藏》者,一些民間經坊如杭州衆安橋楊家經坊等因為承擔《磧砂藏》的印刷裝幀而隆興一時(33)。 關于明代佛教類圖書刻印情况,明弘治五年(1492)四月十日丘濬在《論厘革時政奏》中站在儒家立場上很不滿地說:“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之曰:本朝於佛、道二教各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刻、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別刻新本為哉?”(34)他提到明代除了官方刻有大藏經外,民間經廠、書肆中還有佛經刻售。其實,和宋代一樣,明代官刻《大藏經》也是印刷售賣的。《洪武南藏》刻成之後,板藏南京天禧寺,該寺永樂間賜名為報恩寺。《金陵梵刹志》卷二載: 永樂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時,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錦衣衛指揮趙曦于武英殿題奏:天禧寺藏經板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聖旨:問他取些個,欽此。(35) 但這副《大藏經》經板永樂六年(1408)毀於人為縱火。後來《永樂南藏》刻成後,經板仍藏於報恩寺。在《金陵梵刹志》卷五○“各寺租額條例”裡,記載了取施利的具體數目:報恩寺禪堂“藏經板一副”,印經一藏獲板頭銀十二兩,“每年約二十藏,銀二百四十兩”(36)。在實際請經過程中,請經者除了支付板頭銀之外,還得支付經坊紙墨印刷工價,當時報恩寺附近的南京城内聚寶門外彙聚了大量經坊,為請經者刷印大藏。為了牟利,有些經坊可能會索要高價錢,例如《金陵梵刹志》卷四九所附《請經條例》就提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請經僧本宗投訴“經一藏多索價至四十餘兩,紙絹仍濫惡不堪”(37)。 《大藏經》外,官刻其他佛教類圖書也刷印售賣。例如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南京僧録司刻《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目録後刻有: 板貯僧録司。印行每部太史紙兩裁計九百七十七張,連刷印銀一錢五分五厘。栗殼面,太史雙副葉,綫訂,六本連絹套銀五分。管板僧銀二分,共銀二錢二分五厘。(38) 這和其他圖書一樣是明碼標價出售。 清代官方印售佛經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藏族地區的德格印經院,該印經院刻有藏傅佛教經典甘珠爾部與丹珠爾部等,前來請印的人們不僅有藏族佛教信徒,還有鄰近其他國家的信徒。(39) 由于不少單本佛經乃至整部大藏經都是由寺院刊刻的,因此寺院除了向經坊出租印板外,有的自己也印造佛經出售。例如,明人胡應麟在談到杭州的圖書市場時說:“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40)當時昭慶寺專賣佛教類圖書,僧人充當書商。再如,《徑山藏》刻成之後,無論僧俗,均可到嘉興楞嚴寺請經。 宋代以後,民間經坊、經鋪等也會刊刻佛教類圖書出售。例如,在一本王蘭亭侍郎施捨給寺院的《妙法蓮華經》卷七末頁有宋代杭州沈二郎經坊廣告: 本鋪將古本《蓮經》一一點句,請名師校正重刊。選揀道地山場鈔造細白上等紙札,志誠印造。見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新雕印行。望四遠主顧,尋認本鋪牌額請贖。謹白。(41) 該廣告商業營銷味十足。沈二郎經坊外,宋代臨安王念三郎經坊、王八郎家經鋪等以及金代的衛家經坊等均刊有佛教類圖書出售。(42)明代,杭州楊家經坊刻有《金剛經》等數種佛教類圖書,此外北京京都高家經鋪、杭州沈七郎經鋪等也刻佛經出售(43)。 我們再來看道教。道教同樣重視經籍的複製,《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一“置觀品四”提到:“凡在觀中,皆須先造寫經坊,當別立一院,勿通常人。”(44)該書卷二“寫經品”又稱:“廣寫供養,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條軸,函笥藏舉,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45)寫經與供養經書都是在做功德。與佛教一樣,道書的製作方式,最初是抄寫,後來則是寫、刻并用。而在功德觀念鼓舞下,道教信徒也是紛紛刻經施送。例如,宋人衛涇《(度人經〉後跋》提及練使平喬梓刻《度人經》“以散施四方持奉之衆”(46)。類似的,元人陳旅《道藏經跋》裡也提到“廬陵真常觀道士李俊迪刻道藏經若干卷,以廣其傳”(47)。而在明代,信徒印施諸如《三官經》之類道經動輒上千卷。數量如此巨大的道經,信徒往往是出資由專業的書坊來完成刻印,例如明代北京崇文門裡觀音寺胡同黨家為信徒陳文英夫婦印《三官經》一藏、太平倉後崇國寺單牌樓張鋪為太監李志惠印《真武妙經》五千零四十八卷等(48),這實際上形成了道教類圖書市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道教經書有不少來自于道家、陰陽五行家著作以及醫學、方術、讖緯等圖書,這些圖書在圖書市場上一直作為子書售賣,我們不能籠統地把這些也視為道教信仰帶來的圖書市場。 善書市場的形成與佛、道類似。清嘉慶間成書的善書《暗室燈》說:“刻揚善書,為行善第一功德。”(49)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太上感應篇圖說》卷首記載杭州汪源繼承父志捐資刻成該書,“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結果不但其父“超生天堂”、其母得享高壽,他與衆善人均“名著善籍”(50)。類似說法和故事與上述《太平廣記》中“報應”類所載與佛經有關故事性質一樣,其目的是為了勸誘人們翻刻流通善書。 受功德觀念影響,明末清初善書的刻印興盛一時,其中多為善人或善堂印施,但也有圖書出版商發現其中存在商機。例如,康熙間出現的《感應篇直講》一書,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刊之後,有清一代,曾經十五次重刻(51),除了一些善人、善堂、善書坊翻印施送之外,一些圖書出版商如蘇州青霞齋刻字店、青雲齋刻字店以及北京篆雲齋範刻字鋪等也看到該書巨大需求背後的商機,積極加入到該書翻刻的行列中去。由於善書需求量大,清代琉璃廠裡很多刻字鋪都刻有善書,例如《陰騭文圖說》四卷,有會文齋刻字鋪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及晋文齋刻字鋪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而龍雲齋刻字鋪光緒十六年(1890)刻有《太上感應篇圖說》八卷,永盛齋刻字鋪光緒二十四年(1898)刻有《玉曆至寶鈔》一卷等。(52)顯然,這些圖書出版商承印善書和善書坊因為信仰專門印送善書不同,他們是沖著牟利去的。 正因為圖書出版商有牟利動機,所以尤其重視廣告等營銷手段的運用。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刻的《繪像丹桂籍二編》一書於“樂捐姓氏”之後,列有自辛巳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開始至辛丑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印施該書的善人姓氏及每人印施的數量,據此統計,僅乾隆四十三年一年印施的數量就達一百七十餘部。為了吸引想印施該書的信衆,該書書名頁左下角有長方形牌記道:“好善君子印施者,板藏蘇州閶門内專諸巷西首緑蔭堂書坊。”與此類似,道光十六年(1836)西安唐榕刊刻的《丹桂籍》一書,後附告白: 此版照蘇州原版重刊,校正無訛。凡樂善君子發心印送者,版存陝西西安府城内鼓樓什字街西邊南紙店内唐家刻字鋪便是。其紙墨工價、裝訂,每部來小鋪面定商議,實無錯誤。告白。(53) 有的書坊還將善書書價在告白中說得很清楚。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刻《戒士圖說》一書封面刻有告白: 是書足錢頭號毛太紙二百文,次毛太紙每部足錢一百六十文,加布套四十二文。凡好善信士發心印送者,向嘉定縣南翔鎮東街漱芳齋范綬章刻字店承辦,庶不致誤。特此謹白。(54) 以上這些都是吸引信衆前來印書的商業廣告,我們不難從中看到圖書出版商牟利的企圖。清代圖書出版商其實并不諱言自己從事善書刻印的牟利動機,他們對此有獨到的解釋,例如清代中葉蘇州三經堂題識云: 佛經善書,貴乎流通,流通必使長久。若概施送,不可常繼,得者易或忽而不讀,是以斟酌紙本、印訂工價,貯資續印。庶使讀者慎重,以冀永遠流通。道光甲辰(引者按,1844年)夏三經堂謹識。(55) 三經堂除了刊刻佛書外,還刊刻了不少善書,例如刻《欲海回狂》等七種售與婁門善慶庵,刻《感應篇說定》等售於乍浦沈義豐,刻《陰騭文廣義》等售於常州吴氏,刻《關帝聖迹圖》等售於盤門張義芳,刻《訓俗遺規》等售於上海唐恒美,刻《勸孝編》等售於江西徐白舫,刻《雷霆顯警録》等一百種售於南翔甘氏。(56)三經堂說自己之所以不像一些善書堂那樣無償贈送,一是因為這樣做難以持久,二是因為適當收錢能够讓讀者重視該書,不至於因為得來輕易而弃置不讀。這則識語真可謂巧舌如簧。 佛、道經籍與善書市場外,基督教進入中國後,為了傳播教義,就像《新約·馬可福音》耶穌對門徒所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傅福音給萬民聽”,傳教士與教徒們也會積極翻譯、刻印基督教經書,例如1610年來中國的耶穌會士金尼閣就曾“先後在絳州、西安、杭州創辦印刷所,每年印書甚多”(57),明、清時期因此刊刻了大量這類讀物。由於基督教是外來宗教,受到中國各種原有思想信仰的抵制,再加上中國政府一度還禁止其傳播,傳教極為不易,基督教義相關讀物因此基本上是免費散發。在這種情况下,中國的圖書出版商一般不會像刻佛經、道書以及善書那樣積極主動地投身到基督教類圖書的印售中去,只會被動地應教會人士的要求為他們刊印相關圖書。 除了上述宗教信仰外,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有其他民間信仰會帶來相應圖書需要,例如陸游就提到“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58),只是文獻不足徵,我們不清楚是否有圖書出版商投身到這類圖書市場中去。 總之,在佛、道信仰的影響下,信徒們相信供養經書是在做功德,可以得福報,這導致了對經書的大量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受宗教觀念影響,信徒們把積極參與經書流通也視為重要功德。信徒從宗教信仰出發,或寫或刻,多為施送,其中幾乎不沾染任何商業利益的考量。但對於無暇或無力自寫、自刻的信徒來說,要想通過流通佛、道經書或善書來修善積德,圖書市場上出售的這類圖書就成了便利且成本相對低廉的選擇。於是,就像葉夢得所說,“施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59),精明的圖書出版商利用宗教信徒做功德的心理牟取利益。無論是供養經書還是流通經書做功德,這類宗教觀念背後本來就潜藏著信徒對福報的功利訴求,而被圖書出版商利用後則更直接地與商業利潤聯繫在一起,功德與功利就這樣密不可分。 ①李綱:《李網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第1280頁。 ②羅願:《羅鄂州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2頁。 ③徐建華:《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若干問題研究》,黃建國等编:《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89頁。 ④葉夢得:《建康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册,第616頁。 ⑤羅願:《羅鄂州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2冊,第492頁。 ⑥孫觀:《鴻慶居士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5冊,第241頁。 ⑦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031頁。 ⑧張金吾:《金文最》卷56,《續修四庫全書》第16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1頁。 ⑨費衮:《梁溪漫志》,《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41頁。 ⑩劉一止:《苕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2冊,第119頁。 (11)《道藏》第24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749頁。 (12)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36頁。 (13)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140、148、149、152頁。 (14)《四川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0冊,第487頁。 (15)虞集:《道園學古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7冊,第636頁。 (16)參看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第二章第四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17)酒井忠夫撰,劉岳兵等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頁。 (18)轉引自游子安:《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1頁。 (19)王彬譯注:《法華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07頁。 (20)顧況:《華陽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2册,第557頁。 (21)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257頁。 (22)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814頁。 (23)羅琤:《金陵刻經處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 (24)張之翰:《西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第489頁。 (25)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頁。 (26)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19頁。 (27)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338頁。 (28)《全唐文》卷26,《續修四庫全書》第1634冊,第411—412頁。 (29)馮贄:《雲仙雜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第666頁。 (30)張秀民撰,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頁。 (31)成尋撰,白化文、李鼎霞校點:《參天台五臺山記》,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59頁。 (32)成尋撰,白化文、李鼎霞校點:《參天台五臺山記》,第277頁。 (33)楊家經坊刊經活動從元代一直持續到明代,詳參李際寧:《杭州衆安橋楊家經坊與〈磧砂藏〉》,《佛教大藏經研宠諭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34)丘濬:《重編瓊臺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8冊,第138頁。 (35)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762頁。 (36)葛寅亮:《金陵梵剁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4册,第257頁。按,張秀民先生在其《明代南京的印書》一文(收入《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147頁)中說“每印一部,須付報恩寺板頭錢二十兩”,李際寧《佛經版本》一書襲用了張先生這一說法。《金陵梵刹志》卷49所附《請經條例》有“每印經一藏有板頭銀一十二兩,藏内缺續藏四十一函,合扣銀八兩刻補經板”,張先生或是將這裡兩個數目相加得出二十兩板頭錢。但至少在該《請經條例》頒布之時,所缺續藏并没有全部刊刻完,此時請經者無法得到續藏全部四十一函。 (37)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4册,第219頁。 (38)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3冊,第715頁。 (39)張秀民撰,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第494頁。 (40)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56頁。 (41)丁申:《武林藏書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92頁。 (42)戴蕃豫:《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4、25、82頁。 (43)張秀民撰,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第254、258頁。 (44)《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道藏》第24册,第745頁。 (45)張秀民撰,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第749頁。 (46)衛涇:《後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9册,第710頁。 (47)陳旅:《安雅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3冊,第168頁。 (48)張秀民撰,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第255頁。 (49)轉引自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第6頁。按,類似的說法,在清同治八年(1869)刻《得一録》書前《募捐刊布善書章程》中也有:“作善無窮,此願先從刊布善書起。”書影見酒井忠夫撰,劉岳兵等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第604頁。 (50)引文見酒井忠夫撰,劉岳兵等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下卷卷首所附該書書影。 (51)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第36—37頁。 (52)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7頁。 (53)轉引自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19頁。 (54)轉引自袁逸:《清代書籍價格考——中國歷代書價考之三》(上),《編輯之友》,1993年第4期,第73頁。 (55)轉引自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171頁。 (56)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170—171頁。 (57)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第363頁。 (58)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25頁。 (59)葉夢得:《建康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第6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