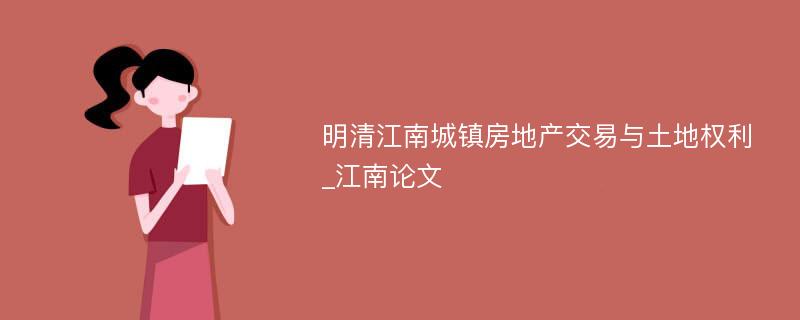
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权论文,江南论文,明清论文,城镇论文,房地产交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田地房产及其契约文书,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石,我国学术界一向予以高度重视,出过几部极具价值的专著。或许因为认定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仅为政治中心,在经济上则依附于乡村;历代王朝重视的是国家田地以及小农地位,强调确保农业生产,保证国家赋税。所以,有关研究土地制度的著述几乎都是探讨“农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尽管,传统的一体化社会中,中央颁发的政策法规或能保持高度的统一,然而,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系统、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组织体系有着明显差异,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城乡间有关田地房产在转让现象上存在诸多类同,这固然可当作一般的、普遍认识,但彼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似更有探究的必要。这里,以江南地区作为考察区域,着重对明清时代城镇的房地产交易及其地权形式作一描述与解析。
一
要讨论明清时代江南城镇的房地所有制问题,如果仅仅选定其中的某一特定时段,则未免会流于偏颇。如明初作为朱氏王朝国都的南京,迁豪富,徒军匠,人口遽增。洪武二十四年,京城人口竟达47万余。当时,“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1〕房地尽由政府提供,自然不许民间自由转让。明代初期,江南土地占有形式上出现的“反潮”,不只表现于国家权力中心的京城,就是其它城镇及其广大农村,新兴王朝动辄以国家名义籍没了大片原属私人财产的田地宅地。“及张士诚据吴,所置平章太尉等官,皆负贩小人,无不志在田宅,一时买献之田,遍于浙西。明初既入版图,按其祖籍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以事被籍没,而浙西之官田愈多矣。”〔2〕另一方面, 朱元璋严格户籍制度,“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毕以其业著籍。”〔3〕把人与地牢牢捆绑在一起。人少有流动,地鲜有转移, 房屋也难以租赁转手。国家强权在深深地箝压着社会经济运行秩序。
权力至上,但权力并非能统管一切,更不会维持长久。约至宣德年间,继明王朝开国也不过五、六十年,江南各地官员就纷纷奏报流民四起。其中一部分“冒匠窜两京”。在南京城,一批非法的“黑户口”移民营造房屋,或开张铺店,做起买卖生意。这类现象的出现,是城镇严格的社会组织系统开始紊乱的信号。明代中叶始,江南城镇中民房的租赁已是普遍之事。苏州城的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开创人孙春阳,原籍宁波,明万历时期初来姑苏。在吴趋坊北口租觅临街房屋,开出小铺。后店面生意做大,遂购地扩房,发展为“铺中之物亦供上用”的综合南北货商店,以至“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4〕孙氏从租赁房屋起步,而后发财致富。严格说来,租与赁是有区别的。所谓借地者曰“租”;“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宋人王禹偁《书斋》诗),这里的“赁”,显然指借房屋。租地与凭屋这两种现象都说明房地业主对自家的产业拥有支配权。如苏州木商在紫阳地起造正堂三间,后厢两披壹间。但这一地基并非买下,而仅是租地借造,需向业主交纳、出租地基费。东越会馆在苏州初因“择地维艰”,暂于金阊南桐子门外借房,以为“朝夕商酌地”。〔5〕这是明显的赁居了。颇有意味的是,当英国驻上海的首任领事巴尔福(G.Balfour)抵沪时,也是经人介绍,在城内东西门之间西姚家弄租了一处住宅,上下共52间,租金每年400元。英国领事馆就设立在这座租赁来的房屋内。
当时,更多的情况可能就是买卖房地。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6〕开埠前的港口城市上海,“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 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尤多大户,立别宅于上海。”〔7〕明万历间广游大江南的谢肇淛曾如斯评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8〕言外之意,南方人讲究起宅盖屋。事实确实如此, “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9〕明清江南住宅消费及私家园林之发达,早为时人所叹止。然而,由于经济的杠杆作用,华宅园林频繁易手速度之快也同样让人惊诧。往往前辈苦心经营,未及数代遂改他姓。
以同乡会为基础的会馆及以同业会为核心的公所这两种组织出面筹措资金,购置房地,在明清江南城镇的房地交易中尤为注目。会馆是侨寓一城一镇的同乡为共同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它们经营的房地规模都较大,主要用于议事、存放贷物、留宿以及举办一些慈善事业。苏州、杭州、南京等工商都会城市,会馆遍布。“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新安在马府街,洞庭在徐家巷,崇明在江东门。”〔10〕据统计,明清时代苏州有各地商人所建会馆40余个。其中,买置房地数额较大的有钱江会馆、吴兴会馆、江西会馆、潮州会馆等。特别是潮州会馆,仅康熙四十七年,买下许昭远一所房屋,竟花银4850两。该会馆曾专设房产册簿,“存馆契卷,递交董事收执”。〔11〕公所,则基本上一业一所,不跨行业。其时,江南城镇公所之设,也似成时尚。然比较而言,在房地置办规模上,公所普遍没有会馆实力雄厚。一些小行业更因资金短缺,生意清微,劝助数载才勉强足数买一小块房地。这还远不及县级以下市镇的会馆基地范围。明清江南的重要市镇,可谓客商云集,“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12〕这些商人或租赁房屋暂居镇上,有的干脆购地筑室长期定居。同乡一多,遂有会馆之设。与苏、杭中心城市相比,市镇的房地价自然要便宜一些。丝绸巨镇盛泽早有会馆设立。康熙年间,山东济宁州众商先后六次购买民田近30亩,用价仅294两,以此作为济宁会馆的基地。〔13〕
土地交易之盛行,刺激了城镇的拓展,不少地区由此出现新兴工商区。苏州的金门、阊门,因有运河流过,物流频繁,形成了一个新的商贸区。大量本地或外乡的工商户均纷迁居此。他们置买的房地实际上就是以前的乡村田地。房地的自由买卖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这在非政治中心的江南市镇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嘉兴府濮院镇,原为濮氏南迁聚落,元大德间,濮氏构屋开街,召民贸易,又名永乐市。“自万历间机杼渐盛,绸遂行而街衢日扩。”〔14〕该镇落迁居民多为四乡织工绸户,或为行销的商贾。人们都习惯认为房地产只是发展到近代才成为城市经济的“晴雨表”。其实,明清的江南城镇,房地交易也能反映城市的发展状况。自明代始田地已有阶差之说,所谓“凡亩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15〕明代苏州南濠一带货物如山,然终究仍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入清以后,“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16〕时人顾公燮感慨于当时的地价,因记下“南濠地值千金”〔17〕。同样,从前素称清净的盘、葑两门周围,好房子即使减价出售,问津者也寥寥;但到乾隆后朝,这里人口集聚,房地随即“求之不得了。”〔18〕明清时期,江南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重要街巷已能体现一定的地价差,这是城镇经济发展与房地交易发生关联的必然反映。城镇的房地经营中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在两方的房地转手、租借之间会由中间人牵线撮合,从中收取酬金。然而,由于受地权约束与城乡经济运转结构的限制,在江南林林总总的行业里房地经营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
二
房地交易离不开土地。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这是它的自然属性。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分析土地的社会属性,这便由社会的地权制度集中反映出来。地权,主要指土地归谁所有,由谁使用或经营,亦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地权制度体现了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因土地的分配和利用而形成的权力与经济关系。我国学术界从50年代起对封建社会的地权制度进行过广泛热烈的讨论。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在于土地的私有与买卖。这一判断主要是针对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依据农村社会的土地占有及其经营状况得出的。如同功能多样的城镇社会房地的使用、买卖远比乡村复杂一样,城镇的地权形式也具其独特之处。
明代土田之制,分二类:官田与民田。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民田则为“民所自占得买卖之田”。〔19〕官、民田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区分似较清楚。然一一考辨《明史·食货志》中所指的官田范围,就会发现这种类分例举完全是为赋税征收的需要。对于近城或城下之地虽称也属官田范围,但就城市中的土地属性而言,却并没有一个明确说法。因之,如何分析江南城镇的地权形式,就需综合各级城镇的功能类型,城居人员的职业、身份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组织体系诸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明清时代,江南城镇工商繁荣,商人及商人资本相当活跃。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概括。但在这一地区,省、府、县级城市从来都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功能而首要存在,只不过由于时升时涨的商业氛围笼罩,这一功能的表现变得或浓或淡而已。朝廷要统治江南,必先控制中心城镇,因此江南省、府、县级城市都保留着相当面积的行使政治功能的“权力核心区”。一般以省、府、县治衙门所在的街、市为中心,由此而集聚了一片官衙、府第,以及园林建筑。这些房地主要供官员、吏役居住,通常属于官府财产。有时官员调任,而地产传留。当然,该小区有街巷,因消费需要也有热闹的小市,而且房地也可自由买卖。但相对而言,身份、职业、等级更为强调,并非所有的有钱之室都可置买这里的房地,随意落迁。这是城市职能分化因素造成的,如苏州的胥门、盘门,接近府衙、县衙,故官员、吏役相对集中居此。
与行政统治需要而集中一批房地不同的另一种情形:国家和官府还掌握及经营了大量土地,也称官庄(有些地方有皇庄),遍布各大城镇;同时也掌管一批店铺,即官店,在江南的苏、杭及南京,还创设了官营织造局,这是资产雄厚的大型丝织工场。明初,南京设有官店,保障京城供给,并在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20〕隶属国有的江南织造局,历年都要置地购屋。如清初,陈有明建苏州总织局,曾多次“别购旧屋”, 竟使织局拥有各类房屋200 余间, 围墙160丈。〔21〕后工部侍郎周天成又扩筑到187丈。
随着江南城镇经济力量的壮大,在城镇政治功能继续保持的前提下,其工商业中心功能则日益加强。这时,城镇的规模、布局,政权的行为再也不是有效的唯一抉择。市场的因素,城镇的发展也要体现经济生活部门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伴随这种需求趋势的扩大,私人土地所有权逐渐成为江南城镇土地所有权构成的主体。私人的土地权利,诸如对于土地财产的继承权、典质权、让渡权、买卖权以及土地经营上的出租征租权,明清时代都已受到国家立法的承认与保障。“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22〕这是法律认可因土地私有而发生的分家析产。租地赁房的普遍,以至江南一些地方为此专门设项收税,嘉兴府秀水县曾贴出告示,记载了嘉兴、秀水二县上报的在城房屋的租金及征收税额。〔23〕同时,可作援引的国家税法也作了明确规定:“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即别纳纸价。”有学者为契本作注,认为契本指买卖田地房屋家畜的契约税。〔24〕国家只要收到税银即可,完全承认私人土地在经营上拥有出租征租权。
房地产在传统社会早被当作不动产,视为“恒业”。民间房地交易,全凭契约。每有房产民事纠纷,动辄告至官衙。苏州尚始公所成立之时,商人陆既通曾捐助基地一间入公所。基地之契券也由陆既通儿子陆惠卿交出。后陆家“持蛮”,意欲收回所捐之地。尚始公所坚持不让,双方僵持,遂诉讼至官府以求公正。苏州府吴县衙门经查实,认为地既已捐入公所,当属公所之产。但虑及陆家这时景况艰难,判尚始公所“念其父旧情”,贴银60元,补作基地之价,此后“陆姓子孙不得再有纠葛。”〔25〕房地转让,所有口实皆出契文。鉴于此类契券的重要,各地政府明文告谕百姓,如浙江省于乾隆三十八年贴出相关文告:
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其契载银数或百十两,或数千两,皆与现银无异。是以民间议价立契之时,必一手交银,始一手交契,从无将契券脱手付与他人收价之事。……盖有契斯有业,失契即失业也。”〔26〕江南城镇日常使用的土地契约文书,作为研究土地制度和反映实际社会经济关系的最重要资料,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分产、赠予、买置房地等契约文书的大量存在,这是明清城镇居民拥有房地财产处理权之极好证明。有关房地财产处理权的契约,此间着重分析“买置房地”。
买置主要是通过买卖自置房地,这是一种产权转让,必立有买卖契约。明清这种契约的样式,我们在苏州府“吴兴会馆房产新旧契照碑”与“纸业创立两宜公所购置房基文契碑”中均可看到。〔27〕由此发现,房地买卖的契约规定已很严密,契文中包括土地买卖关系的基本要素(立契人、房地来源证明、坐落位置与面积、出卖原因、买主等)、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都作了规范,并对上手契的处理也有详细说明。此外,还有凭中、担代人的附证。随后一些契约还交官府验明,给发印照。但在明代及清前期,绝大部分房地契约则据民间的乡规俗约签立,而毋需官府参与,完全属私家文书档案,只是在发生民事纠纷后才不得已去衙门解决。明清江南城镇的契约文书表现出来的习惯与形式,日显成熟,这是较长时间凝炼的结果。并且,这种制式还具一定的继承性。近代上海发出的著名“道契”,〔28〕经分析对照,发现它与明清江南城镇的地契文式大致相通。这说明上海开埠前后,其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与江南其它城镇存在相当类似,来华的西方人(包括租地人乃至驻沪领事)对这种社会氛围以及习惯有个熟悉的过程,在确与中国地方政府与原土地业主会商协议后,才共同出台道契——这一深刻影响到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土地制度。
形式与内容互为表里,但研究房地契约文书,最重要的还是关注其中体现的法权关系。从契约上看,明清江南城镇中,“活卖”与“绝卖”两种方式都有,而绝卖趋势明显。所谓“活卖”,系指房地交易时,留有回赎、找贴等权利。绝卖,顾名思义,在成交以后即杜绝一切干系。绝卖的房地契约往往写明:“自绝之后,永为某某世业,与原始无干,再无异言。尤恐无凭,立此杜绝契存照。”或者在议价绝卖后,干脆在契上注明:“欲后有凭,立此永远割藤拔根杜绝卖屋文契,永远存照。”〔29〕绝卖形式在法权关系上体现得更加一目了然。
在地权问题上,比较复杂的倒是公所、会馆所置买的房地产权。明清江南会馆、公所遍布各大城镇,而尤以苏、杭、南京以及后来的上海城为多。会馆、公所“所有产业契据等项,皆因公产”,所以“系轮替经管”。〔30〕可见,这些房地财产不属于个人所有,一般为各方人士集体募得。但它们由于皆系官宦、商人操持,分轮执管,辗转交替,“恐难一律慎密”,是以一些公所、会馆竞相出现贪婪小人盗卖集体公产的地基屋宇。也正因为这种现象的屡有发生,一些城镇采取把会馆、公所的房地产业契据全部禀缴县库存储,“另录置产簿二本,呈请盖印,一存县档,一存会馆,永远执守”,〔31〕杜绝不断出现的公产流失,变相成为私人房地产的恶习。其实,明清江南城镇中,属于公共土地的远不止会馆、公所,还有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佛教、回教、道教寺庙观所有的土地——这些或可代表城市中族权、神权的“物质基础”。
据此,对明清时代“江南城镇的地权形式应作具体分析。与乡村比较而言,由于城镇政治功能的相对强化,在房地置买上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苏、杭一带的花园别墅时落显宦权贵之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名园如苏州拙政园,在明为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的别墅,后归太仆卿徐时泰,继之,园东部又成侍郎王心一的归田园居;清初,属大学士陈之遴所有,康乾时期园先后为吴三桂之婿王永宁及太守蒋诵先、叶士宪等占据。几经移手,园主尽为当政的权宦。虽家有百万巨资的商贾也难以染指这些丽园豪宅。在城镇中,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官宦依势恃权侵占居民房地。乾隆三十九年,苏州吴县县令孙某借居钱江会馆,一月后迁出。次年,复有署苏督粮厅刘某来会馆借房,强占房屋30余间。迫使钱江商人将寄存货物搬出,以致贮货无所,蒙受一定损失。〔32〕在松江府城,普照寺西界有林太守第,林家世代居住。清初为一将领高谦占居。后籍没入官,又被松江驻军的一位长官假惺惺“偿价得之”,成了他的合法私产。对于这种转弯抹角的霸地占房行径,林氏子孙竟“莫敢过而问矣”。〔33〕平常百姓的基地、房屋为强权侵占往往投诉无门。城镇居民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与居住权时遭践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房地交易仍是不完全的。
来自政治的特权,乃至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传统习惯势力之干扰固然给城镇的房地交易带来了一定障碍;然而,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内在矛盾的运作,又使房地的买卖、出租征租仍具相对的运动性。个人对土地房产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决定了城镇房地在一定条件与范围下可以频繁转移。如松江府林太守第被那位官员以手段侵吞,成了他的房产。后该官员调任松江,便“赁为商店”,他即可从中收取房租。明清江南城镇房地租赁之自由、买卖的灵便,给以靠地区差价谋取利益的商人带来了方便。各地行商云集江南城镇,积累了一定资产,或成坐商,租房置屋,开设店铺,繁荣市镇经济,壮大商人力量。同时,具有活性的地权形式,能使一部分闲置劳动力从一个环节上突破专制政权严格的户籍束缚,而流向江南城镇。商业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结合,便可催生崭新的事物。这一时期江南城镇时有新气象涌动,部分导因即源于此。众多城镇的拓展,或谓乡村城市化,本身就是乡村田土不断转移到一部分工商业者那儿的直接结果。
考察传统社会的运行结构,我们常常觉得城乡一体化有其深厚的基础、凝重的氛围。地可转让,房可租赁,作为江南城镇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唯官宦、文人,乃至四乡富室也纷纷前来城镇涌居。苏州齐门外钱槃,田跨三州,每年收租97万。〔34〕既置田产于乡间,而举家却居于城镇。明清时代,乡村地主跃变为城居地主,似乎成了江南的一种时尚。与此相向,一批居城为官及在城镇的工商户,则集聚一笔余资去购置乡间田土,求田间舍一直是这部分人追求的理想。豪右富室都把田土的买置作为最安全的货币储藏手段。乡村人来城镇置地构屋,居城者买田于乡间,乡村与城镇始终保持着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城乡互动,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彼此界限模糊。商业资金、土地资金与高利贷资金等混沌一片,从乡村田地征收来的租赋成为地主来城镇挥霍的“聚宝盆”,江南城镇的消费功能、娱乐功能在肆意膨胀。明清时代中国最有希望的江南地区,却终于没有诞生出独立的工商业及其它们的中心——健康向上、富有进取的城镇。
注释:
〔1〕〔3〕〔15〕〔20〕〔24〕分见《明史·食货志》,转引李洵校注:《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0、5、22、 240、236—237页。
〔2〕〔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
〔4〕〔清〕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5〕〔11〕〔13〕〔25〕〔27〕〔29〕〔30〕〔31〕〔32〕分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269、48—52、327、351、86、48—52、51、96、168、178、21—22页。
〔6〕道光《黟县续志》卷一五,转引《十大古都商业史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7〕〔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第二《中衢一勺》卷下《海运十宜》。
〔8〕〔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等。
〔9〕〔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10〕甘熙:《白下琐言》。
〔12〕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
〔14〕《濮院琐志》卷一,转引浙江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89页。
〔16〕〔清〕余金:《熙朝新语》卷十六。
〔17〕〔18〕〔清〕顾公燮:《丹午笔记》卷一一三。
〔19〕分别为顾炎武、王原的解释,见李洵校注:《明史食货志校注》第18页。
〔21〕〔清〕孙珮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三。
〔22〕《大清律例》卷八。
〔23〕嘉兴府《秀水县告示》:“止派在城、不派在乡,止照门面、不论住宅,止□租价□征,不……。嘉兴县开报房屋租价壹万陆千捌拾肆两贰分,旧额每两征……本县(即秀水县)房屋租价,银叁万叁千壹拾肆两贰分,每两征银伍分捌厘……总计银壹仟肆佰捌拾余两;今止征银壹仟壹佰玖拾叁两”。转引浙江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第413页。
〔26〕《治浙成规》卷一,转引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28〕所谓“道契”,即在近代上海,外国人向中国人租赁土地而由中国官厅上海道台衙门所发给的一种契纸。
〔33〕〔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十。
〔34〕〔清〕钱泳:《登楼杂记》,转引自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