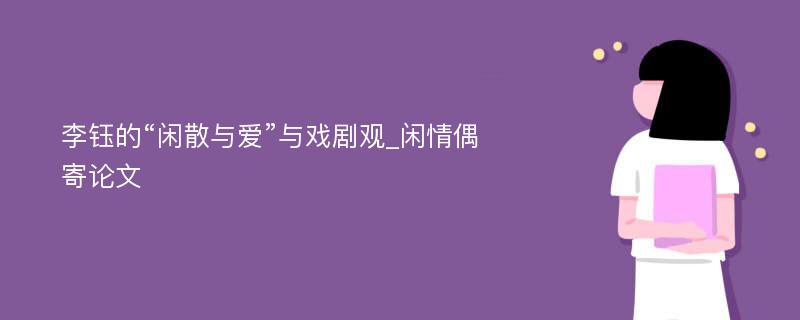
李渔《闲情偶寄》和他的戏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闲情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渔(1611—约1697年),是我国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理论家兼导演,是我国戏曲史上之集大成者。他的《闲情偶寄》对我国古代的戏剧艺术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总结,在戏剧理论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渔的《闲情偶寄》共六卷,包括两部(词曲和演习)二十一章五十三小节,自成体系。其中除编剧和导演理论之外,还涉及了声容、居室、饮馔、颐养等有关化装及演员的生活环境、营养和锻炼的事项。本文专就其编剧和导演理论作些评价和粗浅的论述。
一、有胆有识的戏剧观
在封建社会,填写词曲(实指撰写剧本)是如同创作小说一样,不受重视的。李渔一反世俗之见,开宗明义地指出那种认为“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宣称:“技无大小,贵在所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供复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
他以王实甫和汤显祖为例,说他二人如果一个不写《西厢记》,一个不写《牡丹亭》,那么后世之人,谁复知其姓字?他断言“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这一论断是具有非常之胆识的。他指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他不但在思想上重视剧本之创作,而且在行动上全力投入戏剧活动。他一生以戏剧为职业,带着以自己家姬为主要演员的家庭戏班子,“遨游天下”达40年之久,成了明末清初剧坛的盟主之一。在海内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他自编自排,不断演出自己的剧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致“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说明了他所作出的贡献决不低于史传散文之作者。他那长达40年的编导实践,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写出自成体系的戏曲理论专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戏剧的功能,李渔的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有裨风教”、“点缀太平”。前者偏重于劝善惩恶,因此他认为戏剧可以“代木铎”,“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后者则着眼于通过戏剧的娱乐性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即所谓“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他一生专写喜剧。其所写的《风筝误》的收场诗:“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买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皆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可作为其上述观点的活的注脚。虽然他以戏剧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有力工具这种封建文人的立场十分明显,但他对于戏剧的教育性和娱乐性的特点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则确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戏剧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他认为“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过与裂缯、毁璧等也。”这一提法正是既重视剧本创作,又重视表演和导演艺术的表现。他是深谙戏剧三昧的行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未曾明确提出戏剧是以演员的表演艺术为中心的综合艺术,但“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戏剧观念确已分明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剧作的舞台性以及观众需求的不可须臾忘却。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欣赏那种“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剧作。他认为金圣叹批点《西厢记》尽管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有很高的水平,然而对戏剧的舞台性却茫然无所知:“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而,“圣叹所评,乃文人把弄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学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也。”
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这一核心的观念出发,李渔要求剧作者“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则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样就把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实际密切结合了起来,从根本上揭示了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
二、专为登场的剧作论
李渔深知戏剧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舞台性,所以他的编剧理论就以此为出发点和依归。李渔的剧作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专为登场的剧作论,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曰结构论
李渔论剧本创作,首重结构。他指出“至于结构二字”,“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继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栋须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就是说写作剧本之前,要有一个通盘的思考。
李渔之首重结构,有别于他以前的戏曲理论家如王骥德等辈之首重音律。他突破了前人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戏曲毕竟不同于一般诗文,不是专门摆在案头供阅读的,而是要拿到舞台上演出的;如果没有能适应舞台空间与时间限制的结构艺术,就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结构论上,李渔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等一系列使剧本结构严密而完全的要求,其所包含之内容颇能体现戏剧艺术之真实的原则与方法。
李渔强调每本戏必须“立主脑”,以一人一事为全剧之枢纽。“如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他人物,“俱属陪宾”,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这对于分清主次、贯串情节、展开冲突、刻划性格都有明显的好处,是他深入钻研前人的名作,加上他自己“填过数十种新词”的体会的结晶。立主脑则需减头绪,所以他强调指出,要做到“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
他觉得“编戏有如缝衣”,所以又提出“密针线”的要求,说道:“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并指出:“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这样使全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无懈可击。
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核心观念出发,他又强调“脱窠臼”。他从古人呼剧本为“传奇”入手,指出“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这种追求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但为防止刻意求新而杜撰出脱离生活真实之情节,所以李渔又提出“戒荒唐”的原则。指出:“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很明显,他主张剧作之题材应源于现实。为了防止人家借口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因而一味猎奇,他特意指出:“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性之所发,愈出愈奇,尽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后人。”所以从发掘人性美和体现人情味来看,是不愁没有题材来提炼加工的。当然,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味趋新,因为艺术创作中总是既有“可变者”,亦有“当仍者”;另外,创新不可满足于外表的新奇,因为“文学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这些,李渔对剧作家都有所点破和提醒。他告诫剧作家要认真地“审虚实”,要用“姓名事实,必须有本”和“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相结合的方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达到“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
二曰语言论
李渔在前人关于戏曲语言的论述之基础上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完备的看法,概而言之,叫做“一贵四重”。则:“贵显浅”和“重机趣、重宾白、重性格、重科诨”。
所谓贵显浅,李渔从剧作与诗文所用语言的比较论述说:“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他又从剧作必须适应广大观众之欣赏水平着眼来论述:“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这些话都是十分中肯的。
所谓重宾白,即谓一反前人只重曲词的传统。李渔指出:“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宾白为末着。……予则不然。”“宾白一道,当与曲文同视”,这正是戏剧行家的持平之论。后来京剧界流行的“千斤话白四两唱”的说法,也正是承接李渔上述观点作出的对宾白重要性的强调和肯定。
所谓重机趣,是李渔从戏剧的娱乐性和必须取得应有效果出发而特意提出的。他认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正因为他觉得机趣之有无,关系到剧作之有无生命力,所以他很看重这一内在因素。他认为填词务必做到“勿使有道学气”,不来板起面孔讲大道理的枯涩无味的话。
所谓重性格,即我们常说的剧作语言必须充分个性化。李渔的具体要求是“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欲代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他说的“心”就是性格。而要做到充分个性化,就必须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他说:“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立心邪僻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僻之思。”这实际上已不只是语言运用的问题,而更是与人物塑造直接相关的要义了。
所谓重科诨,是李渔独到的体会。这是他替观众着想,从看戏之效果出发而予以强调的。他说:“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事,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只消三两个瞌睡,使隔断一部神情。瞌睡醒时,上文下文已不接续,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断章取义,作零出观。若是,则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之人参汤也。”古今中外有实践经验的剧作家,莫不有此体会,但是将这个问题提得如此重要,如此鲜明,在我国戏曲史上,李渔实乃第一人。
三曰音律论
李渔的音律论不及其结构论和语言论那么精到,今天已无太多的指导意义,而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了。李渔认为作曲(写剧本)比作任何文体都要难得多,因为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他要求剧作者“恪守词韵”、“凛遵曲谱”。在词的方面他还认为必须严格按照《中原音韵》的规定,这在当时是正确而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词曲的和谐,从而显示其音乐美。李渔还曾强调曲谱的规范性,指出:“曲谱者,填词之粉本,犹妇人刺绣之花样也。”“情事新奇百出,文章变化无穷,总不出谱内刊成之定格。”他认为凛遵曲谱固然受到一定限制,但如果熟练地掌握曲谱,就可以获得有规则的自由,问题不在于“依样画葫芦”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你“依样”的功力磨练得怎么样。
在音律论方面李渔还有一些见解。如在曲韵上,他认为“寒山”和“桓欢”,“真文”、“庚青”和“侵寻”都不能混押;在曲律上,他反对集曲,认为“串旧作新,终是填词末着”,等等。至于他所说的“慎用上声”和“少用人韵”,则是有自身的经验的,因为就押韵来讲,上声是较低的,入声则较难押。再有“拗句难好”和“合韵易重”之说,亦自有其可取之处。
三、以剧作为本的导演学
《闲情偶寄》的演习部实际上是一部以剧作为本的导演学。
李渔的导演理论,虽然不像现代导演学那么完备,但也称得上是已具雏形的戏曲导演学。其具体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选剧
李渔论演习,首重选剧。他说:“吾论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者,诚恐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使观者口虽赞叹,心实咨嗟,何如择术务精,使人心口皆羡之为得也。”他深知“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所以从演出的社会效果着眼将选剧列为首要。
那么该如何选剧呢?他具体指出了两点:别古今和剂冷热。
“别古今”涉及到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是继承古本:“选剧授歌童,当自古本始。”因为“古本相传至今,历过许多名师,传有衣钵,未当而必归于当,已精而益求其精,……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动笔者也。”这么说,李渔是厚古薄今否?非也。他认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创新。并指出:“旧曲既熟必须间以新词,……盖演古戏如唱清曲,只可悦知音数人之耳,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这和他一贯追求艺术创新的指导思想及其处处为观众考虑的戏剧观念有着直接之关联。
“剂冷热”也是李渔的经验之谈。他所着眼的不在外表之冷热,而在剧情是否符合人情。这就是,只要所选之剧本内容符合人情,则自然不会出现偏冷和偏热的问题。所以他说:“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可谓一语破的。
二是变调
讲的是如何对原剧作进行必要的导演处理。李渔既尊重前人的劳动,又不泥迹守古。他说:“变调者,变古调为新调也。”“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这种反对墨守成规的思想至为可贵。在变调的艺术处理中,他创造了“缩长为短”和“变旧为新”二法。前者是根据观众之需要灵活掌握演出之长度,在减省数折的情况下又能保持剧情之完整性或连贯性;后者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点铁成金,补其漏孔。”关于后者,李渔曾以其导演高则诚《琵琶记》的经验为例,作了极令人信服的论证:《琵琶记》中赵五娘千里独行,上京寻夫,即使能自保无他,也难免当时物议。原作在此处确有疏漏。正所谓“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李渔改成以张大公之使婢小二伴送,这一导演处理,巧妙自然,确实优于原著。
三是授曲
就是教唱。中国的戏曲本来就是“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剧,所以授曲自然离不开声乐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技法。李渔认为“声音之道,幽渺难知”,他发出慨叹:“噫,音岂易知者哉!”尽管他感觉到“音实难知”(刘勰语),但也强调实践:“术疎则巧者亦拙,业久则粗者亦精”。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他分六款阐述了他自己的授曲之体会,即:解明曲意、调熟字音、字忌模糊、曲严分合、锣鼓忌杂、吹合宜低这二十四个字。
解明曲意。李渔首先强调指出:“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中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销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他要求授曲者必须讲解曲义,指出有的演员终日甚至终年唱某曲而始终不知该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者,这种“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的,“虽腔板极正,喉舌齿牙极清,终是第二、第三等词曲,非登峰造极之技也。”因为“得其义而后唱,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若是,则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转腔、换字之间,别有一种声口,举目回头之际,另是一副神情。”这些话至今看来,犹觉其熠熠生辉。这不仅要求导演必须吃透剧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而且要求演员提高其文化素质。对曲意领会得深透与否,的确是演唱能否成功之关键。
调熟字音,则是李渔根据汉字的特点而言的。他按照汉字切字之法,指出咬字吐音的诀窍在于注重出口与收音。他提出每个字在发音时应分字头、字尾及余音,并以“箫”字为例,指出其字头为“西”,字尾为“夭”,尾后余音为“乌”。把汉字的声母韵母相切的办法用之于演唱时的发音吐字上,这的确是李渔在导演实践中的重要发现。
字忌模糊,这也很重要。李渔指出:“常有唱完一曲,听者只闻其声,辨不出一字者,令人闷杀。”可见吐字不清,直接影响表演效果。李渔指出吐字忌模糊,不愧是行家。
至于曲严分合,则是要求正确处理独唱与合唱应注意之事项,而锣鼓忌杂、吹合宜低二者,则是指打击乐及箫笛之伴奏不宜压住演唱者之声音。这些也属经验之谈,无须多说。
四是教白
在这方面,李渔又有其独到之见解。他从实际观察中发现梨园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善说白者,百中仅可一二。”因此他深感那种认为唱曲难、说白易的一般看法有问题。他说:“歌曲难而易,说白易而难。知其难者始易,视为易者必难。盖词曲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谱载分明,师传严切,习之既惯,自然不出范围。至宾白中之高低、抑扬、缓急、顿挫,则无腔板可按、谱籍可查,止靠曲师口授。……故曲师不可不择。”这就又对导演之文化素养提出了高要求。
在教白这个问题上,李渔只分两款来阐明他的体会。一是高低抑扬,一是缓急顿挫。
李渔强调白有高低抑扬。“何者当高而扬?何者当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衬字。每遇正字,必声高而气长;若遇衬字,则声低气短而疾忙带过,此分清主客之法也。说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衬字。其理同,则其法亦同。一段有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之主客。主高而扬,客低而抑,此至当不易之理,即最简极便之法也。”这讲得何等明朗和易于为人接受。他在举例详说这条的基础上,又传授后代优师一个简便可行之法:即“于点脚本时,将高宜长之字,用硃笔点之;凡类衬字者,不圈;至于衬中之衬,与当急急赶下,断断不宜沾滞者,亦用硃笔抹以细纹,如流水状。使一一皆能识认,则于念剧之初,便有高低抑扬,不俟登场摹拟。”
在强调分清高低抑扬的同时,李渔又指出注重缓急顿挫之必要,因为“场上说白,尽有当断处不断,反至不当断处而急断;当联处不联,忽至不当联处而反联者,此之谓缓、急、顿、挫。此中微渺,但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能口授,不能以笔舌喻者。”李渔认为说白之能有缓急顿挫,较之有高低抑扬,要求是更高的。他打比方说:“妇人之态,不可明言;宾白中之缓急顿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轻盈袅娜,妇人身上之态;缓急顿挫,优人口中之态也。”李渔以此为喻,是要求宾白达到引起美感的高标准。
五是脱套
李渔认为“戏场关目,全在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而“戏场恶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纪”,因此必须扫除某些恶习。这是他从演出效果着眼提出的要求,并非单纯地防止出问题,而实有其积极意义。不过他所指的什么“衣冠恶习”、“声音恶习”、“语言恶习”以及“科诨恶习”,在今天看来这些或者早已革除,或者不难防止,这里就不加具体说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