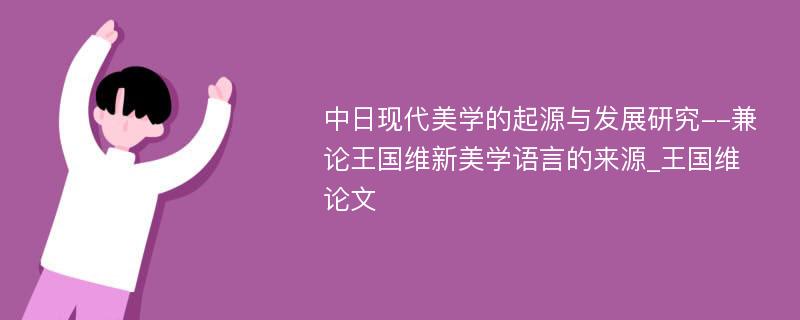
中日近代美学学科生成源流考——兼论王国维美学新学语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源流论文,近代论文,中日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3-0114-05
聂振斌先生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讲道:“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理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而这一点是从美学新概念引进时开始的。”[1](P56)但在不同的学术场合,总是有学者发出疑问:“美学”新概念的“引进”是开始于王国维吗?中国的近代美学学科之创始与完备始于何时?“美学”观念及其范畴系统首先出现于何时并于何人手中固定下来?王国维是始作俑者吗?如果是,王氏是从日本转译,还是直接译自西语?等等。这是美学考古学的问题,也牵涉到对王国维作为美学家地位的评价。而要弄清这些问题,则非要回到中日两国的美学发展史不可。此前,笔者曾见到李心峰先生的《Aesthetik与美学》、黄兴涛的《“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和刘悦笛的《美学的创建与本土传入的历史》①等文,对“美学”概念之出现进行了考古式的发掘,居功甚伟。然而,这些研究并不全面,尚缺少比较的视野,也没有进而解答学术界的上述疑问。
本文试图解决两个关联问题:其一,在上述诸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日本学者神林恒道的《美学事始:艺术学的日本近代》一书,并大量检索中日美学诸多淹没不闻的文献,对中日两国近代美学的生成历史作出系统的考证与分析,厘清中日美学的各自源流与相互关系。其二,对长期争讼不已的“王国维的‘美学’范畴来自何处”问题,予以细致论证与说明。
一、中日美学源流考暨王国维的美学知识背景
梳理汉字文化圈中中日两国“美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把王国维嵌入其中,一方面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中国近代美学学科生成过程中各种资源错综复杂的关系,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美学学科作为外源式文化事件的特性,观察中日两国美学学科生成过程里中、日、西三方的学术关系;另一方面,还可藉以观察王国维的知识背景及其学术资源,从而给我们认识王国维的美学贡献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平台。
毋庸置疑,面对西方所有而东方所无的“Aesthetics”,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探索性的试译。186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词典》(第一册),列有“美学”一词,该辞典将此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这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有关“美学”术语在华出现的材料。1867-1872年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兼翻译家西周曾尝试以“善美学”、“佳趣论”、“美妙学”、“佳趣学”来翻译“美学”[2](P7)。1873年,德国来华著名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1875年复著《教化议》一书。花之安提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二者皆美学,故相属)。”[3](P6)有学者认为,由此“美学”“大体已经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4],“首度译创了‘美学’一词”[5]。但是据我所看,此“美学”并非我们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其意系指“丹青音乐”之类“有关于美的学问或技艺”,不过是偶然的文言用法的二词连属。所以,花之安的“美学”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875年,在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辞典》里,译Aesthetics为“审辨美恶之法”。1879年,罗存德的《英华词典》被日本人改题为《英华和译字典》翻刻发行,后来又在日本出现了几次增订本,流布相当广泛。这对日本创译新名词产生过影响,但它究竟对日本“美学”学术名词的创译有无影响,则是查无根据,很难论定。
1879年以后,日本美学学科的生成进入加速运行阶段。此年,菊池大宽翻译了《修辞及华文》。“修辞”属于修辞学范畴,而“华文”即“美文学”属于文学范畴,换言之,菊池大宽这本书是就“西欧的文学之究系何种东西”这一论题进行体系性论说的最早的文学论。该书是日本文部省组织的国家出版行为,是系统地翻译西学、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新学问的一个环节。日本于西方学术的借鉴始于文学论而不是美学,颇有象征意义。自1882年始,以森欧外、高山樗牛等为主的教师在东京大学就以“审美学”的名称来教授美学[6],高山樗牛后来也接受了“美学”的译法:“美学者,研究美之性质及法则之科学也。”[7](P2)所以,“日本的美学”同样始于对外域的“美学”的发现,而且是由外国人推动的。
这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1882年,居留日本的美国东方美术史家、后来与冈仓天心共同推进“新日本画运动”的芬诺洛萨所著《美术真说》,比较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并且真正接触到了日本艺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成为日本美学与艺术学的开端。从幕末到明治初期,随着日本与西方接触的日益频繁,“和风潮”在西欧风起,原本已堕落为日本人消遣品的“浮世绘”重新被视为日本美术精华,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浮世绘”的研究著作。芬诺洛萨在人们认为不值一提而被到处扔弃的古佛像中,发现了日本传统艺术中“希腊式佛教美术”的痕迹,逐步深信,让日本人模仿西方美术完全是一场灾难,由此形成了他具有独特体系的崇拜日本美术的理论,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建立了类似新古典主义的日本美术观,并展开了热情洋溢的批评运动。从此,日本古典文化财产复引起重视,过去的“书画骨董”改成了“美术”这一名称,而把“书画骨董”改为“美术”这一名称的手段就是“美学”。最早以“美学”把古典的老古董变成“美术”的是冈仓天心,他的成果是在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的课程“日本美术史”,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与讲演。
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883-1884年,文部省编辑局出版了由中江兆民翻译的法国人维隆(Véron)《维氏美学》一书,此书据称是“用汉语译创了‘美学’这个词”[5]。1925年,中国学者吕澂认为美学这个名词源于日人中江笃介在1882年翻译法人的著作,即指此事;当代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也认为,《维氏美学》是“汉字文化圈”中使用“美学”一词的最早记录。此类说法尽管依据不够充分,中江兆民的原创性难以确证,但中江兆民用他的译名来特指这一学科,“美学”之名得以“固定化”,则是确定无疑的。此后,日本的美学学科逐步建立。
1889年,中国人颜永京翻译出版了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 Haven)所著《心灵学》一书,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时日本“美学”一词已经基本确定下来,可见颜永京的翻译并未受日本人影响。
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外山正一作了题为“日本绘画的未来”的讲演。围绕这一讲演,外山与医学士森林太郎展开了论战,随后,森鸥外亦加入论战。森鸥外以德国哲学家、“批判的存在论”的创始者哈特曼(Nicolai hartman)的美学理论为武器,对外山正一痛加批驳,使外山的理论完全陷于沉默。森鸥外的“美学”,介绍了作为西欧人文学科一个分野的“美学”到底是种什么学问,成为“日本的美学”的出发点。尽管有过“唯有从德意志的美学出发的学院派才是美学主流”这一看法,但是能置日本美学学科原点的,却是由森鸥外带来的哈特曼的美学。此后,各大学陆续开起了美学课程,东京帝国大学于1893年、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紧随其后在文科开设美学讲座。日本美学学科得以完全成熟。
在中国学界,此期中国人开始知道了美学的存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出现了“美学”一词,该书的“美术”类所列第一部著作即为《维氏美学》。1900年,侯官人沈翊清在福州出版《东游日记》,也提到日本师范学校开设“美学”与“审美学”课程之事。1901年,京师大学堂编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一书,多次使用现代意义的“美学”概念;同年10月,留日学生监督夏偕复作《学校刍议》一文,也使用过“美学”一词;稍后出版的吴汝伦的《东游丛录》里,“美学”一词同样屡见不鲜。
以上都是一些零星的材料,真正对美学进行系统介绍的,当然首推王国维。1901年,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一书出现了“美感”、“审美”、“美术”、“审美哲学”、“审美的感情”、“宏大”等现代美学词汇,1902年,王国维所译《心理学》一书有“美之学理”一章,最早译介了有关“美感”的系统知识。
在中国,1902和1903年则是具有标志性的两个年头,本届哲学门的“美学”学科在中国得以定位。1902年,王国维翻译出版了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书中使用了“美学”、“美感”、“审美”、“美育”、“优美”和“壮美”等现代美学基本词汇,从哲学的角度最早向中国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并且书末所附《中西译语对照表》,“美学”一词竟重复出现两次,足见其重要;同年,在一篇题为《哲学小辞典》的译文中,王国维还较早介绍了“美学”的简单定义:“美学者,论事物之美之原理也”,并译Aesthetics为“美学”、“审美学”。1903年,蔡元培翻译出版了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最早介绍了“美学”的词源及其原初意义;同年,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分哲学为知、情、意三部分,分别对应的是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美学由此定位为一种“论感情之理想”的原理,同时与真和善并列的哲学学科。此年,由时中书局编译出版的《心界文明灯》一书也有“美的感情”专节,区分了“美丽”与“宏壮”两个美学范畴,还较早使用了“悲剧”一词。1903年,汪荣宝和叶澜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辞典性质的《新尔雅》,该书较早以通俗的辞典形式给“审美学”等词下了定义。
此后,中国美学学科开始进入教育体系。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这是“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学课堂之始(教会学校不计),但当时的大学文科却还未开设“美学”课。1906年初,王国维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在“文学部”的科目里,也正式列有“美学”一科。比较深入的介绍也在同时进行,美学学科体制基本形成并固定下来。1905年,留日学生陈幌参考日本的心理学著作并结合中国实例,编写出版了《心理易解》,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心理学书。书中率先介绍了西方美学家(罢路克)所谓“物之足使吾人生美感”之“六种关系”,即“体量宜小,表面宜滑,宜有曲线之轮廓,宜巧致,宜有光泽,宜有温雅之色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07年,杨保恒编《心理学》,介绍了美感“三要素”,即“体制”、“形式”和“意匠”,同时他还阐明美可分为优美、壮美和滑稽美三类,并一一加以解释。1908年,颜惠庆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久远的《英华大词典》,在译Aesthetics为“美学”、“美术”的同时,也仍保留着“艳丽学”这一美学对译词。1915年出版的《辞源》,设有“美学”专条,是中国流行词典中对“美学”一词早期的权威阐述。1915年,徐大纯刊载于《东方杂志》的《述美学》一文,列举了从柏拉图到桑塔耶那跨越两千多年的西方美学代表人物,陈述了美之性质、美感与快感、美的各种分类,并提出了“美在主观还是客观”的重要命题。1916年,蔡元培的《哲学大纲》明确了美学的学科定位,在哲学体系上将美学列入到“价值论”方面,同时又将“别美丑”的美学、“别真假”的科学、“别善恶”的伦理学加以并列,同王国维如出一辙。1917年,公弼在《存心》杂志上连载了一系列的美学论文,站在国际美学前沿的角度对美学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借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主张。
经由此,“美学”概念及其大体涵义逐渐为中国人所认知。而随着对西方美学了解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并经过此后的调整、固定和成熟,中国学者自己动手编撰美学专门书籍,进行理论的消化、阐释和创造的条件也日益成熟。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美学学科得以正式建立。这比日本晚了近三十年。
从上述中日美学源流与发展的考证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来华传教士、中国人和日本人,确实都独立地探索、思考过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译述之词,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综合性的;第二,美学新学语的生成,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并具有一个探索、思考、摇移、调整、固化并成熟的过程;第三,中国人真正的美学探索及美学学科的成熟要晚于日本近三十年,鉴于当时的中日文化关系,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习和接受某些美学知识是可能的,这从王国维的态度和作为中可以得到证实。
但是,如果非要在东方近代美学新学语的生成上争论个先后、找到个唯一的原创者;或说“美学”是由来华传教士先创,传入日本后再复传入中国;或说传教士、中国人、日本人各自独立地创译该词;或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直接接受等等,如果偏执于某一种说法,都不过是一种臆断和猜想。整体上看,文化的生成得益于多元因素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其中到底是何种元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殊难界定。所以,作为一门新知识、新学科的引进或创立,一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且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立足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上,都需充分利用当时的各种文化资源。王国维的美学贡献也是如此。“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8、[8](《显学》),我们要的即是结论之先的实证和审慎。
二、王国维对日本、西方资源的态度与作为
中国和日本美学发展史的近代阶段都是外发的,日本人是直接学习西方,而中国人则是通过日本的中介学习西方并开始直接学习西方。这种发展模式符合以下规律:某一新学科、新知识之生成,必然要经过一个学习与引进的“过渡之时代”,中国近代很多学术大师都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从对美学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及整体来看,王国维之学习与引进的深度与广度是他人所不可比量的,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中国美学的近代化,其标志是一整套相关的范畴术语在王国维手中或引入、或独创而得以固定下来。
作为美学这种外源外发的新学科、新知识,其范畴、概念与术语的生成自然有一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间的对译,及其结果的稳定性即固化的问题。对于王国维的美学探索而言,首先,他所面对的是同时代的日本近邻的资源可资借鉴和利用;其次,他对于直接向西方学习丰厚的哲学美学理论达到孜孜不倦的程度。王国维从他的日本老师田冈那里知道康德等人,并萌生了学习西方哲学之意,为此他在努力学习日文之外,又花费较大精力研习英文,目的就是直接阅读西文的哲学原著。据刘克苏《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一书载,狩野直喜来中国留学,就曾听藤田丰八说王国维“善读日文,英文亦巧,而且对西洋哲学深感兴趣,前途很可观”[9](P74)。王国维的日文比英文好,两相参照逐渐通晓英文著作之大要。1902年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所教所学即康德、叔本华的著作,康德的分析论佶屈聱牙,他只好先读叔本华,由此返回来再读英文版康德。据他的日记所载,1903年夏至1904年秋,他一直在读叔本华。可见,王国维对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思想的接受,不是从日本人那里间接来的,而是自己直接研读其著作的结果。王国维所用之伦理学讲义,更多来自他本人所译之书,除参酌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以外,还有英国西额惟克《西洋伦理学史要》,其中大量的人名、“学语”悉出英文,不少学理则源于讲分析论的康德、实证论的培根等等。据笔者统计,所见王氏译著计有22种,译自日文和英文的都有。至于他运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因为是“两相参照”,究竟系直接译自西语版本,还是从日本人那里接受来的,因缺乏作者本人的参考文献与注释,均无据可查。
因此整体来讲,王国维的美学术语系统和有关的西学理论知识,一部分是他直接创译自西文原版著作,一部分接受自日人译著。这里,日本人的知识对王国维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最著者当数早在上海东文学社时的老师藤田丰八。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中说:“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教学者,即藤田君。”[10](P608)王国维不仅跟藤田学英文和日文,同时也跟他学习西方哲学,尤其是学习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1900年底,王国维“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10](P609)。王国维一直对藤田评价很高,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藤师学术湛深,其孜孜诲人不倦之风犹不易及。开岁以后未交一文之修,而每日上讲堂至五点钟,其为中国不为一己之心,固学生所共知。”[11](P21)在之后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王国维和藤田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可以说,藤田对王国维学日语、英语和西方哲学,都起了重要的指导携助作用。
另外,在受日本影响方面,还有在通州师范学堂时的日本同事远藤民次郎(授外国地理)、吉泽嘉寿之丞(授理化),但其影响偏弱些。此后,王国维先后四次去过日本,与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岗谦藏、铃木虎雄(豹轩)、青木正儿、久野原吉、川口国次郎、隅田吉卫、古藤贞吉、田冈佐代治、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等过从甚密,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经史小学方面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与研究。其中尤以与藤田、内藤和铃木的交往为多,书信往来也相当频繁,这无疑对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产生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内藤湖南作为日本的著名汉学家,对甲骨文研究有素,王国维与其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有诸多互相启发之处。铃木虎雄作为王国维著作的译者,二人的交谊深厚,经常有诗词唱和,讨论作诗的美学问题、讨论国事等,他们在学问、心性,以及诗歌的美学观上有诸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正是由于铃木虎雄将王国维的著作译为日文,才使日本学界广泛了解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可以说,王国维通过与日本学者的广泛交往,使他们学术思想更为丰满扎实,无论是随藤田学外语和哲学,还是与内藤进行的上古史的探讨;无论是与铃木在翻译著作方面的讨论,还是与狩野、神田等的学术交往,这些都使王国维感受到日本学界学术前沿的空气和最新的治学方法。处于浓厚的日本文化熏陶之中,处于众多的日本学者朋友中间,王国维对于当时的日本文化界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其间探讨一些美学问题也应该是情理中事。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对于新学语输入之态度是开放的、实用的,并无国家民族之偏见。他在1905年写的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谈到了日本中介的问题(称之为“中间之驿骑”):“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的输入之意谓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后,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扦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12](P112-113)早在1900年,王国维就译出了《势力不灭论》,王氏所撰卷首《译例》云:“译语仍用旧译。惟旧译名有未妥者,则用日本人译语。”“人地名及书名,概标西文,以便稽核。”“则日人所定之语,虽有未精确者,而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则其不用之也谓何?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今之译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也。……然因此而遂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此又大不然者也。”[12](P114)据此来推断,如果日文有相应合适的译语,则王国维袭而用之是必然而正常的;否则,他会仔细揣摩另寻其它更合适的术语。
总之,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外源的、后起的知识门类,都有一个较长的探索、思考、调整、固定从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历史事件,绝非一人一时之事功;但是,总是要有几个核心的中坚分子作出最大贡献。在日本,如芬诺洛萨、中江兆民、森鸥外、冈仓天心;在中国,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尤其是王国维,在美学新学语的输入、转化和固化方面,以其开放性和准确性,不计来源,或直接转自日本人,或直接译自西语,取其合适合理者加以使用推广,确定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美学的基本范畴、术语与观念体系。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美学之出现,并不始于王国维;“美学”这一术语,也并非王国维之创造;王国维的贡献在于,通过消化吸收日本人的已有成果和直接从西语中翻译这两种途径,把一整套美学所需要的术语、概念、范畴比较集中地固定下来,推动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美学学科。
标签:王国维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术生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美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