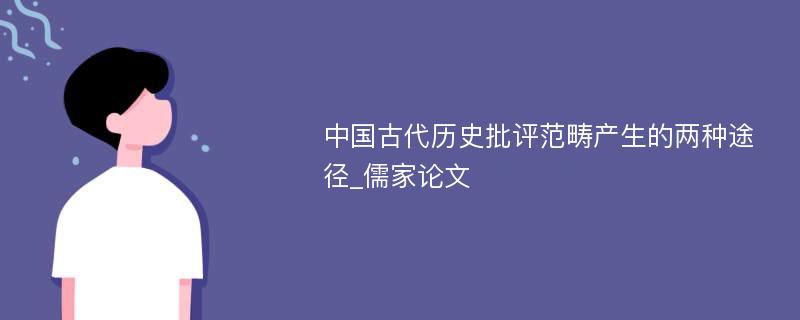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两种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范畴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而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探讨,尤为一些研究者所重视,①这不仅有益于从深层上推进相关研究,而且也会对史学理论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范畴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路径及类型,有助于从事物发展规律上提升对范畴的认识。 纵观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过程,史学批评范畴的形成大致经由两种路径,由此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前人提出的某一概念或观念,经后世史家不断阐发,使其内涵逐渐丰富并趋于稳定,而成为史家的共识;另一种是后人对前人提出的某些观念,加以总结和概括,使其内涵明确,成为人们的共识。简言之,前者是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概括和提升的过程。下面就以具体范畴为例,通过对其生成路径的分析,揭示范畴生成的过程及类型。 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的路径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史家在反思史学活动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概念或观念,经后人丰富与完善,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运用,并成为人们阐述史学某些特定问题的范畴。 例如,揭示史书要素和反映史家修养的范畴,就是遵循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这一路径形成的,体现了范畴形成的这一规律性现象。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较早提到史书构成要素的是思想家孟子,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将事、文、义三者视为史书构成的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三位一体,构成史书。 此后,史家不断对这些要素进行阐发和完善,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宋人吴缜和清人章学诚的阐发尤为重要。吴缜在事、文、义的基础上,阐述道: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③ 这段文字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提出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历史撰述的要素,并对“事实”作出了比较清晰地界定,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史家“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这里的“事实”既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历史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④二是发展了前人提出的事、文、义的命题。“事实”“褒贬”与孟子说的“事”“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孟子那里,“义”是第一位重要的,故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强调;而在吴缜这里,“事实”是第一位重要的。其“文采”包含着对“史文”的审美要求,这是在孟子所说之“文”的基础上,对史文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三是对三要素作出有逻辑的排列,以范畴的形式提出了在首重事实的基础上,重视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新认识,使这组范畴成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形态。吴缜是在批评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时提出上述作史三原则的,从而把历史撰述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章学诚对事、文、义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对三者顺序的认识上,强调了“义”的地位。他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⑤在这里,章学诚不是简单地表明尊重孔子、孟子的说法,强调“义”的重要,它的理论贡献在于用“所贵”“所具”“所凭”把义、事、文三者紧密联系在一个范畴体系中,且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从而成为一个明确的、严密的历史撰述的理论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吴缜与章学诚对孟子所言事、文、义的阐说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史学求真的本质,后者强调历史思想和撰史旨趣。可以说,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事、文、义。 再如,同事、文、义发展路径相近的是“史才三长”的理念,即才、学、识的提出及其发展路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回答他人提出的历史上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提出了才、学、识这一组命题,他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⑥ 刘知幾将史家应具备的修养概括为“才”“学”“识”,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三者的具体涵义,只是作了象征性的比喻,但从他对三者关系的论述,不难理解其内涵,即“才”是指史家驾驭文献、选择和运用体裁、体例及其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指的是包括文献、社会和自然等与历史撰述有关的知识。“识”则是指史家的识见,而“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既是“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史家的品德修养。⑦ 刘知幾之后,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的命题,常为人们所引用。有的学人还补充以“胆”、补充以“力”等。尤为重要的是,清人章学诚在才、学、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对前者予以补充和提升。所谓“史德”,其内涵除以往史家论及的正直、善恶必书等关乎道德修养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论及天人关系,即“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⑧这里的“人”与“天”,是他对历史认识主、客体的具体表达,即“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⑨。他深知“尽其天”之不易,所以他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⑩在他看来,撰史者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主观意志,但在主观上应有这样的自觉。章学诚将“史德”提升到关乎史学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层面。 近人梁启超赞同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也赞同章学诚以“史德”驾驭才、学、识的观点,他在综合这些概念含义的基础上,对其顺序作了重新调整,形成了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一史家修养的范畴体系。(11)其后,史学界普遍采用这四项指标来衡准史家,史家也自觉地将其作为自身职业操守和专业学养的最高目标。 从刘知幾提出才、学、识,到章学诚补充为德、才、学、识,再到梁启超调整为德、学、识、才,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这一组范畴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 二、综合概括与逐步提升品格的路径 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另一种生成路径,即综合概括与逐步提升品格的路径。我们知道,史学批评范畴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不会骤然产生,而是经过史家对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观念加以综合与提炼,最终以范畴的形式展现出来。“直书”与“曲笔”、“史法”与“史意”这两组范畴的形成,就属于这种类型。 首先说“直书”与“曲笔”。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提出了“直书”“曲笔”一组范畴,千余年来,人们沿用至今。这组范畴的提出,是刘知幾对前人提出的观念进行综合、概括的一个突出事例。为了说明其生成的过程,我们不妨采用“逆向”考察的方法,去追溯这组范畴的源头和流变。 孔子在《春秋》中评价晋国史官董狐不畏强权,记载“赵盾弑其君”一事时讲到“书法无隐”的精神。(12)此后,“书法无隐”不仅成为史家撰史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成为史学批评的一项重要标准,影响深远。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其突出特征是史家多从综合与概括的角度,阐说前人的观念,如南朝齐人崔祖思对孔子提出的“书法无隐”的阐述,就是通过比较古、今修史之差异而总结出来的,他称颂上古史官“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的精神(13),认为“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14)。在这里,崔祖思一方面表明他对古史官董狐、南史的敬仰之情,一方面也彰显了“书法无隐”。 与崔祖思大致同时代的刘勰,在分析自先秦至南朝梁以前史学发展史时,提出了“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的认识(15),清晰地阐明了据事直书与史学功能的关系,即史家以直笔撰写信史,是实现史学“奸慝惩戒”目的之前提。同时,他又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作结论:“辞宗邱明,直归南、董。”(16)其中“直”与上文“直笔”同义,意思是历史叙事当以《左传》为典范,直笔撰史应以南史、董狐为榜样。这是对直书传统的一次概括。北周史家柳虬从史家职责的角度指出:“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17)因此,当宇文泰行篡逆之道时,柳虬毫不犹豫地“执简而书其过”(18),其言其行,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直书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唐人刘知幾通过对唐以前历代史书个案的批评,总结这一传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对前人的有关论说加以综合,将“他善必书,己不讳恶”的著史之法(19),概括为“直书”,使之成为评价史家、史学的重要范畴和标准。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与“直书”相对立的作史之法和著史态度,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时有发生。刘勰所谓“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埋,[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也”(20)。南朝齐人崔祖思提到“述事之徒,褒谀为体”的现象(21),反映了“直书”之对立面的存在。而从刘知幾《曲笔》篇所论内容来看,“曲笔”之说,也正是其历考前史,总结唐以前史学史上“舞词弄礼,饰非文过”等“曲笔阿时”的情况之后而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可见,“曲笔”这一范畴的出现,同“直书”一样,也是刘知幾综合、概括前人思想成果的结晶。 要之,“直书”和“曲笔”成为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撰史原则与作史态度的史学批评范畴,而为后世史家、史学评论家所接受,并广泛地运用于史学批评的活动中,对剖析史学现象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次说“史法”与“史意”。“史法”“史意”这一组范畴的生成,与“直书”“曲笔”极为相似。清人章学诚在谈到他本人的史学特点和治史旨趣与刘知幾有何区别时说: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2) 在这里,章学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法”与“史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一组很重要的史学范畴。而这组范畴,并非仅仅说明他与刘知幾的异趣,也反映了清代学人对前人提出的有关概念的综合。孔子在《春秋》中运用一字褒贬的书法表达自己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晋人杜预将其归结为“五例”。其中,“微而显”“志而晦”和“婉而成章”三例(23),说的是《春秋》的文字表述之法,“尽而不污”和“惩恶而扬善”两例(24),讲的是《春秋》的记事之法。 刘知幾的《史通》以论“史例”见长,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5)。这里的“例”,是指史书的编纂形式,是“史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史例”提升到国法和是非的认识高度,反映了他对史法的重视,也彰显了“史例”的价值。此外,他以专篇讨论史料采辑、史文繁简和记事、载言等原则,不仅丰富了“书法”内涵(26),拓展了“史法”范围,也折射出唐代史馆制度下所形成的史书编纂规范,并在揭示“史法”发展趋向的同时,深化了对史法的认识。 南宋叶适虽对“史法”有不少论述,但从运用“史法”之概念开展史学批评的情况看,他所说的“史法”与刘知幾所言的“史例”不同,主要是从史载义理的角度揭示史学之意(27),更近于价值判断。对“史法”作出进一步总结的是清人章学诚。他综合以往史家关于历史编纂所涉及的丰富内容,将其概括为“史法”,使之与探讨撰述之旨、史家之意的内容相区别,这在史学批评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元人郝经将《春秋》书法的特点概括为“以一字为义,一句为法”(28),反映出后人对前代撰史之法的认识。这启发后世史家创法立制、讲求体例的自觉意识,也扩大了《春秋》“书法”的范围与内涵。 史家关于“史意”的探讨,肇始于孟子所说的“义”。秦汉以后,史家多重视“义”的讨论和贯彻。其中,南朝史家范晔和南宋史家叶适在这方面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而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则是其集大成者。 范晔强调“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29)所以他以其《后汉书》的传论“皆有精义深旨”颇感自豪。(30)其中的“义”与“旨”同义,即是借褒贬之“义”正一代得失。叶适既论史法,也谈史义。他认为“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31),这是强调史学之“义”的社会功能,提倡史家撰史应有高远的立意,以救世风世俗之弊。因此,他赞扬《左传》“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如影响之不违”(32)。此中之“义”,指的乃是史书之中的“德”与“义”。(33) 章学诚关于“史意”的认识源于他对《春秋》以来历代史家之“义”的全面综合与深刻领悟。他说: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於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34) 指出孔子之“义”乃为《春秋》之旨,事与文是反映《春秋》之义的途径,因而史义才是史学的意义所在。从他对事、文、义三者关系的解读中,不难看出章学诚对史学之“义”的重视,而从其对《春秋》之“义”的阐述,亦可见其“史意”的具体内涵。他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指出: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5) 他认为《春秋》之“义”当包括“推大道”“通古今”和“独断”三项内容。这说明章学诚的“史意”虽本于《春秋》之“义”,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几乎包括了《春秋》以来史家为史之意的内容。同时,他又将具有“独断”特征的“家学”与“史意”相联系,使之成为其“史意”的题中应有之意。不仅扩展了孟子之“义”,也使其具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可见,他是借孔子《春秋》之义彰显自身学说,实质上是章学诚对自己所推崇“史意”的阐发,显示出他对史学思想成果的综合、概括所达到的高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史意”与“史法”的区分,清晰地界定了史学不同层面的内容,拓展了史学批评的领域。但这种区分只是从研究对象的主要方面来说的。事实上,“史法”和“史意”彼此相互渗透,难以截然分开,“史意”本身也包含着透过体裁、体例等“史法”所彰显的史家为史之意。章学诚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虽重视“史意”,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36),但也并不忽视“史法”,他“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旨,竟成绝业”的治学心得(37),以及赞扬郑樵《通志》具有“卓见绝识”和“通史家风”的同时,也肯定其“创例发凡”之功(38),就是明证。 从“直书”与“曲笔”和“史法”与“史意”这两组史学批评范畴的形成,可以看出,它们是循着人们对个别的、分散的观念的综合、概括和提升这一路径发展而来的,这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结合上文论述的,可以认为,在史学批评史上,范畴的生成和积累是有规律可循的。认识这一点,可以加深我们对史学批评的认识,进而加深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 三、两种路径的辨证关系 上文论述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过程及其类型,只是几个例证。随着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自会提出更多的实例,以证这两种范畴类型的生成过程。当然,这两种范畴类型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其间绝无截然划分的界限。 从范畴本身来说,如刘知幾首次提出才、学、识“史才三长”论,但他不能没有对前人思想资料的继承。在此之前,论“史才”的学人甚多,如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9),说的就是孔子在史文表达方面所具有的才能。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0)。其中,“善序事理”指的是司马迁所总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之理(41)。“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说的是其叙事平实、准确,文与质相得益彰。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指的又是他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撰史的原则。事实上,这些评价已经涉及了史家的识与才。世人称赞荀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42),赞扬的则是其才与识。西晋史家华峤被誉为“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43),其评价的重点在于其卓越的历史见识。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44),说的主要是史才问题,即史文表述的能力。由此可见,以上诸家评史,事实上已经涉及才、学、识三个方面,只是还没有对其所论内容作进一步的提炼,并同时把才、学、识联在一起作为一组范畴体系提出来罢了。刘知幾才、学、识的提出,又经后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达到新的境界。可见,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从史家自身来说,刘知幾在才、学、识问题上,既是首倡者,又不断被后人所超越,而他提出的“直书”与“曲笔”,又是对前人的一种超越。章学诚因“史法”“史意”的提出超越了前人,但他以德、才、学、识之论虽超越了刘知幾,却又为梁启超所超越,这也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进而言之,学术发展是无止境的,即使像吴缜所提出的事实、褒贬、文采这一范畴体系,很接近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但对事实的界定和斟酌,对褒贬的标准和尺度,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即仍存在可以超越的空间。至于章学诚说的史法和史意,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止是作史方法,而是史家的历史观及其作史旨趣。其中,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梁启超强调的德、学、识、才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说,也不能脱离历史理论、方法论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抽象的存在,也是要置于当今学术环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怎样为现今的中国史学批评及其相关范畴的生成提供参考和借鉴,则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十分艰难的研究领域。 以上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形成的两种主要类型及其辩证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范畴类型被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是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所期待的。仅就本文所论及的内容看,不论是历代史家对有关概念或观念连续探讨和不断发展而成的范畴,还是对前人的观念进行综合、概括而成的范畴,它们都是史学批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史家在史学批评活动中不断认识和逐渐积累的思想成果。因此,研究这些范畴生成的路径及类型,不仅对史学批评范畴本身的深入研究是有益的,而且也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人们认识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评价其发展水平,总结其生成特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是中国史学得以继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它形成的机理、内在结构和文化内涵,对其形成的规律作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推进史学批评范畴的深入研究所必需的,亦当成为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①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江湄:《“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李珍:《“素心”与“史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刘开军:《论“史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瞿林东、葛志毅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毛春伟:《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求是》2010年第9期;罗炳良:《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②《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51页。 ③(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第622页。 ④瞿林东:《略说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求是学刊》2010年第5期。 ⑤(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9页。 ⑥(后晋)刘昫:《旧唐书·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页。 ⑦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29页。 ⑧(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第220页。 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第347页。 ⑩(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第220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家的四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2)《左传·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第1867页。 (13)(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崔祖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6页。 (1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崔祖思传》,第286页。 (15)(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页。 (16)(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译本,第153页。 (17)(唐)令狐德棻:《周书·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81页。 (18)(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1页。 (19)(唐)刘知幾:《史通·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7页。 (20)(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译本,第151页。 (2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崔祖思传》,第286页。 (22)(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23)(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左传序》,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页。 (2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左传序》,第4页。 (25)(唐)刘知幾:《史通·序例》,第88页。 (26)这里的“书法”,主要是指孔子在《春秋》中运用特定词语表达其对历史的看法。 (27)“义理”,指褒贬之义,与孟子的“义”一样,都是价值判断,即“义法”。 (28)《全元文》卷一二五,郝经《春秋制作本原序》,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29)(南朝宋)沈约:《宋书·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30)(南朝宋)沈约:《宋书·范晔传》,第1830页。 (31)(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唐书二·表》,第576页。 (32)(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春秋》,第118页。 (33)叶适认为:《诗》《书》是“古人以德为言,以义为事,言与事至简,而犹不胜德义之多”(《习学记言序目》,第118页)。 (34)(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第171-172页。 (35)(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第136页。 (3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第464页。 (37)(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家书三》,第92页。 (38)(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第464页。 (39)(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4页。 (40)(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2页。 (41)(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4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荀悦传》,第2062页。 (43)(唐)房玄龄等:《晋书·华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4页。 (44)(唐)房玄龄等:《晋书·陈寿传》,第2137页。标签:儒家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章学诚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