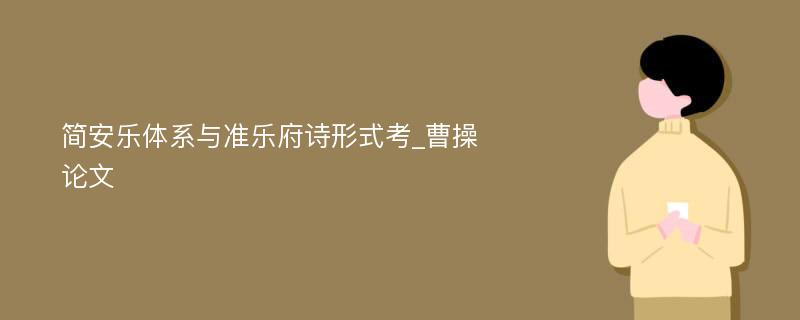
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形态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乐府诗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的具体情况现存相关史书如《三国志》等缺乏系统、明确记载,经过明清以来史家的爬梳整理及时贤如萧涤非、王运熙等先生的详细考订,大体眉目已出,本文只是在此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建安乐制及拟乐府诗的某些特点试作考述。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云:“汉末大乱,众乐沦缺。”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大肆烧掠,洛阳宫室荡尽,几成废墟,两汉几百年的文化积累顿遭破坏,乐师逃散,乐制毁废。在军阀割据、群雄混战之中,曹操乘时而起,出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需要,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但没有提到乐制的恢复情况。《三国志》卷二十九注引《魏书·杜夔传》云,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琮而得杜夔,夔“以知音为雅乐郎,……以世乱奔荆州,……太祖(指曹操—引者注)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南朝沈约《宋书·乐志》还补充说:“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杜夔所传古代雅乐,据《晋书·乐志》记载凡四曲:《鹿鸣》、《驺虞》、《伐檀》、《文王》,“皆古声辞”。除了杜夔所传雅乐后人可知其大概外,《南齐书·乐志》说:“魏歌舞不见,疑是用汉辞。”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曹操实际上控制了最高权力,汉献帝毕竟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雅乐仍然是汉宫廷音乐,曹操尚不能僭越,故言其时雅乐沿袭古辞于理为当。
曹操平荆州,除了得雅乐郎杜夔,还得到后为“建安七子之冠”的王粲。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被封为魏公,七月魏始建宗庙社稷;又《宋书·乐志》记载,“魏《俞儿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用之。王粲造”。又据《宋书·乐志》记载:“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诗而已。”可见,王粲除造《俞儿舞歌》之外,还写有《登歌》及《安世诗》,这些皆属庙堂雅乐。不过,尽管王粲是秉承曹操之命而撰作雅乐,但由于其时曹操尚奉汉帝,故其词仍称颂汉德,如《俞儿舞歌》云:“汉初建国家,区九州”、“汉国保长庆,来祚延万世”。
概言之,曹操在建安时期在乐制上所做工作主要是恢复,至于正式改变乐制则是曹丕代汉称帝之后的事。封建统治者基于一代有一代之乐的信仰,建国后都要做变乐改词的工作,从文帝曹丕到明帝曹叡都不例外。前引《宋书·乐志》之云:“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明帝太和初诏曰:……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又《晋书·乐志》载:“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叙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又曹植《鼙舞诗序》云:“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擂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典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这段话写于曹操死后,所谓“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明确提出一代自有一代乐曲,既然魏已代汉,自然另作新词。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由朝廷统一管理的音乐,一般人是不可以私造的,只有受统治者之命方可为之。雅乐如此,而产在于汉代民间的乐府是否如此呢?对此史书缺乏直接记载,只能间接推测之。《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包括“相和”在内的“赵代秦楚之讴”被汉乐府机构采集、编订之后,显然是施用于统治阶层的,尽管其使用并不限于宫廷,但一般人没有经过皇权特许、非乐官不得改作;魏明帝沿袭这种做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夕达旦”,其《遗令》谓:“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故《三国志》卷一注引《魏书》曰:“太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我们注意到建安时期曹操好乐、拟乐的大量记载,而其他人作合乐之词甚少,这当然反映出曹操通脱、好乐,同时也可能反映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可以随便依乐撰词。沈约《宋书·乐志》叙述南朝民歌吴歌、西曲“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之后云:“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调歌词之类是也”。《宋书》载录的“相和曲”十五曲中,除了《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为汉代古辞,余下九首一首为曹丕之辞,另八首皆为曹操之词。现存曹操诗歌除以上八首,其他诸作亦皆混入汉乐府民歌曲调之中,在相和三调歌(清、平、瑟三调)中便有其著名作品《短歌行》、《苦寒行》等。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雅乐是一种宫廷、庙堂之乐,用于汉献帝宫廷之中,而曹操则可以大好乐府,由于汉乐府旧辞已大量散佚,曹操便“造歌以被之”,《资治通鉴》卷一三四胡三省注谓:“魏太祖……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汉旧曲而曹操所撰新词。曹操在世如此,其死后乐府旧曲仍为最高层统治者管理。《晋书·乐志》称“黄初中,左延年以新声被宠”,“新声”显然为皇帝专用。事实上,拟作乐府必须要合乐,而一般士人并没有专门的伎乐队伍,故也不便于拟制。
现存建安拟乐府诗的数目也能说明这点。保存至今且明确可以判定为拟乐府作品除三曹父子之作以外,陈琳、阮瑀各有一首;左延年有《秦女休行》;王粲有《七哀》,《文选》著录则归入“诗·哀伤”类,不作乐府。当然,保存至今的数量并不等于当时数目。不过作为当时著名诗人,创作能力都很旺盛,写作拟乐府诗数量如此之少显然别有原因,这原因可能就是前边所述非奉最高统治者之命不得随意拟作这一无形规定。
似乎比较例外的是曹植写有大量拟乐府诗。从曹植后期辗转迁徙的遭遇看,其拟乐府诗合乐的可能性很小,这就暗示着曹魏建国之后甚至建安后期在拟乐府创作上的诗、乐分离的时代特点。汉末建安时期已经出现了歌、诗分途的趋势(注:详见拙文《建安诗歌形态论》,刊于《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此时文人士子仍然好乐,但他们开始了抉撰写书面之诗的新的艺术活动方式,曹丕《叙诗》中写道:“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诗歌表现了当时“仰而赋诗”的生动场面,诗往往就在那种场合下写出来的。既然他们会写诗,而且由于好乐,对乐府诗的体式又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在写诗时或者就不自觉地借用了乐府歌辞的旧有形式,这种拟乐府与配合乐府曲调写成的拟乐府歌词就有所区别了。实际上我们即使不考虑这一背景,单纯从诗歌内容看,由汉至晋的拟乐府诗的发展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时代特点:汉代宋子侯《董娇饶》、辛延年的《羽林郎》和民歌几无二致,而曹操的拟乐府则有强烈的写实性,到西晋陆机的《猛虎行》、《君子有所思行》等完全脱离了管乐,几成自我抒发的抒情诗。这就说明当作家根据曲调而填词时或多或少要受到曲调情绪或原歌词内容的影响,一旦作家摆脱其音乐曲调的影响,纯粹借用其形式,当作书面的诗歌来创作,那么这种拟乐府只是文人抒情诗歌的一种形式,已经不再具有音乐艺术和民间乐府的典型艺术特征。
建安是一个时段的概称,诗歌形态是有所发展变化的。汉乐府以叙事、写实见长;如果说曹操拟乐府已带有个人抒情成份,那么到曹植后期其拟乐府创作则脱离了音乐的拘束,不再受到原曲调或内容的限制,已经文人化,有些完全成为个人抒情诗了。举例来说,曹植的代表作《野田黄雀行》所采用的是标准的乐府题材,但原始的具有童话意味的素材在这里被作者用作抒怀的一个背景资料,向来解诗者都以为此诗别有寓意,暗指曹丕借口杀掉与曹植友善的丁仪、丁翼兄弟之事(注:见徐公持文《曹植》,载于《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第26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而这种暗示、寄托正是文人诗典型的艺术技巧、艺术手法。由此可见,当诗、乐分途之后,作为书面诗歌而写作的拟乐府必然受到文人诗歌创作模式的影响,所以出现二者功能趋同、艺术手法相似的现象。曹植作为广义的建安文学时代最后的一位著名诗人,其后期创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文学发展趋势。
当然,以上所论并不是说文人拟乐府诗完全消化在文人抒情诗创作之中,从其后来的发展看,仍然继承和体现了较多的写实性,具有作为一个特殊诗歌类型的共同性特征。
总之,本文认为诗、乐分途是建安时期由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拟乐府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今尚未见诸时贤论述,故不揣谫陋以述之,以就教于方家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