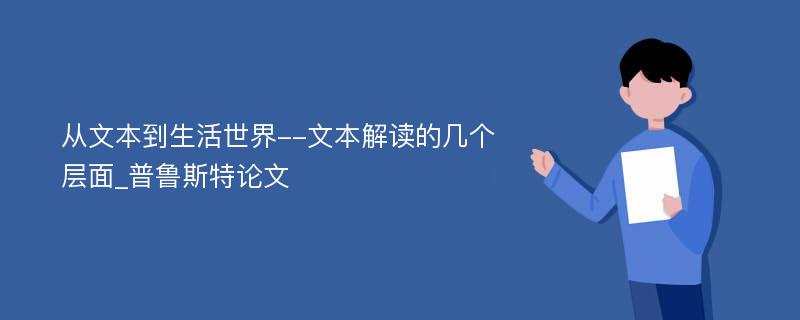
从文本到生活世界——文本阐释的几个意义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几个论文,层次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看一个例子。
圣伯夫采用简洁动听的措辞说《恶之花》“是一座建筑在文学堪察加边远尽头的小庭园,我称之为‘波德莱尔游乐场’(又是玩弄‘字眼’,才智之士对此可以引以为冷嘲:他竟把它叫作‘波德莱尔游乐场’。只有喜欢引用这类货色的饶舌家一类人在宴会上谈到夏多布里昂或鲁瓦-科拉尔时才可能做得出来,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波德莱尔是何许人)。”最后他竟用这种奇谈怪论作为结束:确定无疑的是波德莱尔先生“受到重视,让人们看见了,人们果然看到一个怪人走进门来,在人们面前出现的原来是一位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堪为表率的候选人,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谈吐高雅,在形式上完全是古典式的”。(注:普鲁斯特《驳圣伯夫》,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这是普鲁斯特对圣伯夫评价波德莱尔的再评价,括号内为普鲁斯特的批注。普鲁斯特非常不赞同圣伯夫对波德莱尔的评价。我们这里暂时不去讨论谁是谁非,而只是关注评论本身产生的意义层次问题。
我们看到,在这段评论里有几个层次,按照评论的生成顺序是这样的:作品(《恶之花》)、批评(圣伯夫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再批评(普鲁斯特对圣伯夫评价的评价)。《恶之花》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它是一个最初的文本,批评是在它之上产生的,而批评可以是面对一个文本的诸多批评的并列,也可以是对批评的再批评。后一种批评方式比前一种多出一个评价的层次(不过在这里并不是最关键的)。当然批评是可以叠加式进行的,比如韦勒克在提及这段公案时也基本上持与普鲁斯特相近的观点,不过出于一个批评史家的职责,他更理智地描划了圣伯夫的整体批评思想,在指出他的批评理论缺点的同时,也指出圣伯夫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有充分的和完整含义上的代表性、规范性,绝对不容忽视”(注: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以上的批评文本与作品文本一道构成了文本阐释的一部分,不过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文本阐释这个概念并不同于文学批评。应该说文本阐释与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文本阐释的最佳实践领域就是文学批评。不过它也有与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性质。从范围上来看,文本阐释包含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几个层次(上面列举的),文本阐释同样包括在内,它超出文学批评之处在于文本阐释更注重对批评的反思,对文学批评中所展现的文学场域进行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思考,进而得出文本阐释学的理论观点。它由文学批评中来,又超出文学批评,进入哲学的思考。
这里要对文本阐释进行一下意义层次划分,不过这种划分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一种误解:认为这种层次是意义一产生出来就具有的;意义,无论是在意义充实过程中的哪一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层次划分。这种误解很容易就会产生,因为无论怎样强调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都会导向一个后果:以一个文本的形式把这种阐释思想固定下来,并且在随后的阐释中把这种动态的意义以通观的方式进行总结,这是反思理性必然要做的事情,也是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反思理性的一大弊端:忽略过程本身的意义,只关心结果。所以,叠加的文本阐释会自然地将动态过程当作一个有头有尾的切片,将进程置换为结构,虽然它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新的意义,但是作品文本所表现的原初世界的意义却变得稀薄起来。
下面的划分不是从所谓的生活基础开始的,即不是从作品文本所表现的生活世界(注:生活世界概念来源于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同时它还源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分析的此在有限生存的概念。重点是人在生存中的直观体悟。这里用生活世界来代替“现实生活”的提法,一是因为生活世界概念比现实生活概念要广阔一些,而且它不那么客观化,好像只是一堆材料,它是人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发现,有更多的主体因素;二是为了避免以前的“文学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文论观点,这种观点把现实生活当作文学作品的根源,是先于文学作品的东西。而我这里恰恰认为生活世界是在文本阐释中被发现的基础,它是后于文学作品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论观念。详见下文的说明。)意义开始,虽然一般都认为生活世界意义是文本阐释意义的基础。(注:时下的文学理论往往认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活世界是最基础性的东西,所以生活世界理应排在文本阐释的最初位置。但这里却并不持这种平面化的看法,而是从阅读顺序的角度来探讨文本阐释问题。)这里以主体注意力的顺序为划分准则,以主体渐次意识到的层次来分层,用现象学描述和分析的方式,进行反思,寻找本体性的基础,甚而进入无意识层次。
1.文本自身的意义
首先闯入主体注意力的一定是一个公共平台性的东西,这就是文本。这个文本有点泛化,指的是对象的直观性表现,如果缩小一点儿,在话语领域内,就是文字描述。比如我们首先读到《恶之花》这个文本,沉浸于每一首具体的诗中,体味其意韵,才能对其进行评判。再如我们看书法展,首先看到的是作为客观对象摆放在桌上或挂在墙上的条幅,然后观赏到书法,理解到书法的妙处。这幅书法就形成文本的意义,它摆在那里,在一个公共交流的空间中,等待欣赏者对它发表见解,进行阐释,至于书法的作者是谁,暂时不是考虑的问题。(注:当然会有那种先看作者再发表评价的现象,这是一种比较初级的阐释方式,这里暂时不对这种阐释方式进行处理。)
这是文本自身的意义。在这个阐释阶段,意义还停留在文本的解读中。这个文本说了什么?哪些内容是它要表达出来的?它使用了哪些形式来表现?它独特的表现手法是什么?对这个文本的诸种描述形成这个文本初步的意义。不能轻视文本的意义,不能因为阐释文本的目的是探索生活世界的意义而把文本看作暂时的、容易消逝的;文本阐释本身就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而且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世界意义都要凝结于文本之中才能进入公共阐释领域,为他人所理解、评价、接受或反对。我们如何理解波德莱尔的意义?如果没有语言的帮助怎么能知道波德莱尔这个人?怎么能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文学成就?只有通过波德莱尔的作品,我们才能理解波德莱尔这个人具有哪些伟大的创作才华、特出的表现手法、某种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这些是要首先进行分析的。所以文本自身的意义应该是意义敞开的第一个领域。
文本意义是意义的第一个表现层次,这是对一个最初文本而言的。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称之为作家的作品,或者我们把范围再放宽一点儿,叫对象,我们面对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那种客观存在物,比如高山流水、长河落日之类,而是人的观念的对象,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这个东西就是对象。比如美,没有主体注意力的投射,就没有这类对象的存在,就没有美的存在。当然,那种客观存在物也可以在我们的意识中成为对象,只是这种对象与纯粹观念性的东西不同:我们可以凭借理性推论出,没有我们的观念,它一样存在。这里并不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这上面,因为它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中的对象怎样呈现。这个呈现我们就称之为文本。这是将文本扩大言之。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认识到了某个东西很重要,比如我看到了路边的一丛青草,认为它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可以入药,治疗疾病,如果我只是看了一眼,知道了它的作用,但是既没有把它采下来去做实验,验证它的作用,也没有告诉别人它的可能功效,而是转身走了,别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那么它就无从形成意义。假如我对它的功效进行了验证,可是我坚决不告诉别人,只是在心里知道这件事,那么它只是对个人而言有潜在的意义,但是别人依然不知道,这个意义还不是公共的。意义首先要在一个公共平台上进行交流,才能被认识到,才构成实实在在的意义。
极端的表现主义者曾经认为文学作品不是摹仿现实,而是将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进而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只是内心的情感强烈、充沛,那么就是作品。这个推论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你不表现出来谁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作品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没有呈现形式的私人意义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可能对个人有意义,但是对别人不形成意义。只有用一种公共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进行阐释,它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一句话,意义是公共的。
2.对文本进行阐释形成的意义
阐释首先是文本阐释,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在进入公共阐释领域之后,阐释的主动权就掌握在阐释者手里,但并不是说阐释就可以是任意的,可以任由阐释者随意发挥,阐释应该以理解文本的意义为准,作者的原意是很重要的。作品由作者创造,他所希望表达的意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作品的意义。这么说不是认为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原意,而是强调阐释的善良愿望,在阐释中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上,而不能为了某种理论构架或实际的需要,或以游戏的态度随意进行阐释。若没有阐释的善良愿望存在,阐释行为根本是残缺的,没有向心力的,很容易走向阐释的瓦解。善良愿望是阐释行为的内在动力,不是有阐释行为然后再强调进行善良的阐释,而是必须先有面对文本的严肃的善良愿望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阐释。(注:阐释的善良愿望问题首先是由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论争引起的。伽达默尔认为阐释一定要以善良愿望为基础,善良愿望是一种主体的努力,而德里达认为阐释的善良愿望就会导致阐释的霸权,伽达默尔基本上没有听懂德里达在讲什么,因为在他的阐释学思想中没有霸权问题。这里采取将善良愿望放低的阐释策略,不再把善良愿望当作主观愿望,而是认为只要对准文本进行阐释就是善良愿望的表现,基本上是采取伽达默尔的立场。)
文本本身具有意义,这是阐释时必须要注意的,阐释应该紧紧贴近文本,保持主体的紧张感,力图挖掘出文本的真正内涵。阐释包含着对未来的期望,期望阐释对未来时刻依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主体保持时时刻刻的紧张感。如果因为阐释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而放弃了阐释的善良愿望,把阐释当作一件快感游戏,这种阐释行为一定是瓦解阐释,因为阐释可以凭一己之见任意进行,阐释可以无限多,导致我们根本无法将阐释聚集在一起进行判断。所以阐释要以原初文本为指向。
阐释原初文本同样会形成一个文本,这是阐释的文本。阐释文本能够独立形成意义。对原初文本的阐释独立成为一个文本阐释的领域。原初文本是独一无二的,而阐释文本往往形成文本的叠加,对阐释的再阐释。
圣伯夫评价波德莱尔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而对他的伟大作品《恶之花》却含糊其辞,虽然波德莱尔对圣伯夫的评价表示感激涕零,但是普鲁斯特却对此愤愤不平,认为对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去评价他的作品而只是对他的某个不重要的品质说三道四,是极不负责任的。(注:参见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第96-125页。)这里我们看到,波德莱尔的作品可视为原初文本,圣伯夫对波德莱尔的批评可视为对其进行的阐释,这个阐释文本形成之后就具有自身的独立意义,普鲁斯特在这个阐释文本之上又进行了阐释,形成阐释文本的叠加,不同的阐释文本形成了不同的意义表达。韦勒克把这些文本阐释当作一个事件来处理,认为这是作品批评反对作家批评的一个例证。(注: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第41页。)象这样的阐释是可以进行下去的,诸多阐释形成了阐释文本自足的倾向,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批评与阐释本身可以敞开自己的阐释境域。问题是一旦过分关注阐释文本的自足性,忘记了阐释文本是对原初文本提出来的,那么阐释文本就会与原初文本脱离,失去本源性基础,毕竟文本阐释的真正目的是通达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生活世界。
所以我们在同意文本阐释有自身的意义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把文本阐释的意义当作本源的做法。
3.在阐释的反思或阐释的注意力转向中形成的意义
不局囿于文本阐释中形成的意义,就要重返原初文本里所显示出来的意义。这种重返不是天然的形成了,而是通过阐释的反思进行的,当阐释的路向显露的时候,可以看清阐释的大致方向,那么反思就发生了。反思代表阐释的注意力从一条途径上跳出来,以前注意力还埋头在这条途径上,无暇顾及其他,那么现在它可以回头看一下,看看周围,对比一下,就可能发生注意力的调整。这就是阐释中的注意力转向。它形成的意义往往是带有标志性的,注意力转向中形成的意义往往是对过去阐释意义的调整,使其离开原来的方向,进入新的方向。转向的标记是明显的。也可能加强原来的阐释方向,使阐释以更高、更自觉的意识沿着原来的阐释进行。
圣伯夫以一种传记学的方式来研究文学作品,必然就注重作家本人的经历、个性特征以及交游等等实际生活的情况,就像他在为波德莱尔进入法兰西科学院所做的陈辞,担心《恶之花》中的颓唐描写会吓坏了院士们,辩解说,波德莱尔是“一位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堪为表率的候选人,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谈吐高雅,在形式上完全是古典式的”。这也是从实际生活而不是从作家的作品着眼的辩护,而作品恰恰是对作家最重要的。圣伯夫的批评方法基本属于此类。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但在后世遭到强烈的批评。普鲁斯特的观点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坚决从作品来谈作家的成就。他以圣伯夫为批评的标靶,将批评方向彻底扭转,文本阐释意义也形成了剧烈的转向。当然这种阐释上的转向并不是经常发生的。韦勒克的批评要相对温和很多。他先描述圣伯夫批评取得的成绩,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最后指出其批评方式的局限,这就像走了一个较曲折的弧线,最终达到转向的目的。韦勒克的观点实际上佐证了普鲁斯特的观点,而且他以批评史家的理论修养将圣伯夫的批评纳入一个历史的视野,特别表现出反思的气质。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的意义有很大程度上说的是在注意力转向时形成的意义,因为这时形成的意义最醒目、最吸引人。圣伯夫的批评路向有普鲁斯特的批评做对照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韦勒克的评价也同样如此。而圣伯夫在运用他自己的批评方法时,其阐释意义并没有彻底地显现出来。从整体历时性观照的角度讲,注意力转向形成整体意义的高峰,而沿着某种方向进行阐释的意义则只是意义整体的谷底,我们注意到的往往是高峰,而少注意谷底。这也是我们在反思时需要注意的一点。葛兆光从普通信仰史的角度为形成整体历史意义的大众信仰鸣不平,认为以前的历史观念过分注重精英史,注重突显出来、吸引人注意力的部分,而对形成整体历史意义的大众信仰缺乏关注,认为这样造成了历史意义的遗失。(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他的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意义的层次有多种,注意力转向形成的意义容易被关注并不代表只存在这一种意义形式,应该努力发掘多种意义存在形式,使潜在的、隐含的意义也进入意义阐释的视野。
4.个体化体验中敞开的生活世界意义
注意力转向形成的意义有两方面的构成,一是作为客体的意义对象,一是作为主体的意义构造能力。在注意力转向的最初反思中,发现的往往是第一方面,即客体的意义对象,主体是继起的、被发现的东西。发现了主体,注意力就转向自身,认识到自身在意义构造中的主导作用。但主体本身如果没有对象激发并不显示意义,意义对象没有主体的意向作用也同样不显示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主体不是作为整体的经验主体,这个层次已经在文本阐释中出现过了,现在出现的主体是个体性的体验主体。(注:这里,我对体验与经验进行了区分,体验是个体性的,比较原初,还没有进入公共阐释领域,而经验则是整体性的,经过一定反思的,可以进入公共阐释领域。)它从整体经验的文本形式中跃出来,在注意力的回转中成为主体的对象,而它在自身的短暂停留之后发现自身联结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因为个体性体验直接从生活世界中来,它离生活世界最近,它所敞开的是带有含混形式特征的生活世界的意义。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生活世界意义。它是在注意力多次转向之后发现的,并且在反思中成为意义的基础,比如我们说文学作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恶之花》所表现的是巴黎的都市生活,等等。由于“基础”一词具有强大的重构能力,所以生活世界被发现之后,这个反思性(过程)往往在意义的阐释中被忽略掉,变成了以生活世界为起点对意义进行重建。这是一种误解。
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对意义的阐释都是从这个基点上开始的,它以生活世界为基础,个体化体验联结生活世界,显示生活世界意义,进而形诸文本,然后读者进行阐释。这是一般的意义阐释方式。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个体怎样认识生活世界,心中体验到的生活世界意义是否就是艺术,阐释以作者为准还是以读者为准,阐释在何种程度上是准确的,等等问题。
所以在此要强调,生活世界意义是后来才发现的,它是在阐释中被重新构造出来的,当然这种构造又不是任意的、无原则的构造,而是以一个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为指引的,主体对这个原初文本中呈现的生活世界充满了期望和想象,它是一个悬置的、需要充实的东西,阐释者要以它为方向。同时,阐释者也拥有进行新的阐释的权利。这个生活世界既是文本创造者的生活世界,又是文本阐释者的生活世界,两者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在阐释中,生活世界的范围得以扩展,阐释者对文本的解读不仅发现文本创造者那里的生活世界意义,也融入自己对生活世界意义的理解,所以它既指向一个本源,又不断拓展范围。概言之,阐释中形成的生活世界意义既是对作者原意的探寻,又是阐释者的创新,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成果。
5.生活世界意义重新回转文本
如果对生活世界意义有一个明确的意识的话,“生活世界意义回转文本”这个层次实际上已经在第二层次上发生过了。这里只是把曾经遮蔽的重新敞开,以澄明之光重新照亮晦暗之所。(注:虽然海德格尔说澄明也是一种遮蔽,但是它毕竟把曾经晦暗的东西显现出来了,至于以澄明的方式遮蔽起来的东西,则需要以另一种澄明的方式来显现它,所以阐释是循环往复进行的,不能以为一次性的揭示就完成了文本意义的探寻。从最本源的角度讲,阐释是无止境的,但对一次具体的阐释行为来讲,阐释又是有结论的,是某种阐释境域的敞开。)文本阐释的第二层意义中实际已经包含了生活世界意义,文本阐释具有的自足意义与文本所指向的生活世界意义既有间离,又有一致之处。如果一味强调间离,那么,文本阐释自身的意义就占了第一位,为批评而批评就成了合情合理的做法,文本阐释的不断叠加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最终可能导向恶意的文本增殖。这样一来意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像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那样成了话语的喧嚣,谁的文本多,谁的分贝高,谁的意见就对,谁在文本里表现的意义就最充分、最本源。所以在承认存在着间离事实的情况下,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文本阐释所体现的生活世界意义上,沿着这个方向来阐释,遵守阐释起码的善良愿望。
“生活世界意义回转为文本”意味着进行文本阐释的时候,以生活世界意义为指向,时刻关注文本阐释是否遗忘了生活世界意义。这么说不是表明生活世界意义是个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阐释中,最容易遗忘的恰恰就是生活世界意义,所以阐释者应该在阐释中时刻提醒自身进行意义的重返,如普鲁斯特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与重返一样。
穿越记忆的迷雾,在文本与生活世界的关注间震荡,也许本源性的意义,一种以个体性体验为指引的意义,在公共阐释领域中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