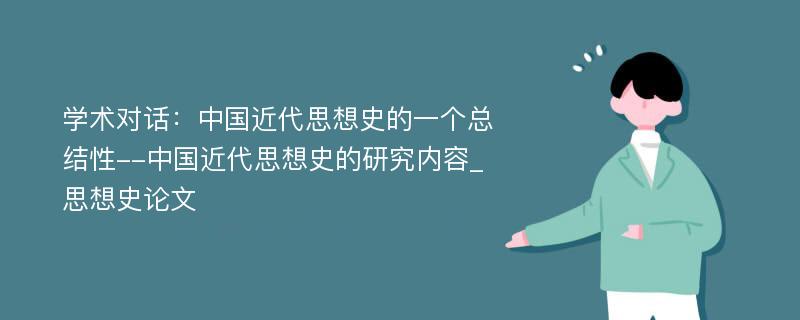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一——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思想史论文,学科论文,学术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3-0108-04
张宝明:大华先生,当下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应该说呈现出较为火爆的情势,但对其内容的丈量在学术界可以说是如同“丈二”。鉴于我们同在这块领地上耕耘,不如在我们繁忙中抽出时间率先梳理一下究竟思想史应该研究什么的问题。
郑大华:宝明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想说但却总被琐事“压倒”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史的研究就等于没有“进场”。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动因、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研究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大量有关哲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胡适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已经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然而改称思想史,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中又有许多哲学史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哲学史的内容所占篇幅相当不少。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却又大量地写进了思想史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入,中国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如此等等。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一家一户为特征的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了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了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上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希望学术界对此应有高度的重视,因为只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张宝明:大华先生在上面的阐述中说出了思想史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文化史、政治史、哲学史、社会史以及其他种种学科的关系;另一个则是思想史的研究内容问题。鉴于第一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离不开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利于问题的澄清。为了有利于问题的澄清,我建议把研究内容改为基本命题。尽管研究内容和基本命题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论述起来也许会方便些。毕竟,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这一问题太庞杂、太丰富,也太烦琐和广泛了,一旦说开来,真的不好收笔。我想,与其说今天我们该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该研究什么内容,毋宁说该研究什么基本命题来得贴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其实不只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不应是一个任何学科都可以作为研究命题的对象。上面大华先生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应该说,这样的概括非常具有浓缩性、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两大基本问题也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心命题。但是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难道其他学科诸如上面郑先生提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以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等等,哪一个学科不是围绕着“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提问并回答的呢?如此说来,这样界定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还是有些宽泛,甚至可以说大而无当。当一顶帽子既可以戴在张三头上、也可以戴在李四头上时,这样的“帽子”就不是为“某一个”订做的了。
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我们知道,无论是古代思想史的写作还是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范式,都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从思想家的思想变化、影响入手来撰写思想史。就目前学术界的情形看,从内涵上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样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诸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记得你曾这样评价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说:“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晚清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就学术分类来看,“知识”、“观念”、“信仰”不是同一层次或性质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思想史学者对思想史学者的批评,而且也是有代表性学者间的“对话”。虽然这段话不长,但其中涉及的问题都是带有针对性的,而且涵盖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也正是这段“对话”恰恰反映出思想史研究“深化”的艰难。在《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篇带有宏观意义的“微作”中,你也就如何加强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里我要说,总结“经验和教训”和寻找“规律性”不止是思想史这一学科的任务,而且也是整个史学学科的任务。我以为,这个设想还是有待于朝着可操作性的具体化方向演变。对此,我们可以从已有的思想史论著中汲取足够的教训。以郭湛波20世纪30年AI写作就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为例,即使出版社声称“选粹”,也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它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因为,在“基本问题”的背后,思想史还有自己的基本问题。
郑大华:的确,诚如宝明先生所言,作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命题,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学科提问和回答的问题,但它们的提问和回答则有层次之分。众所周知,无论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都属于观念史,而观念史是一个可分层解析的体系,其最高层是在哲学层面对“时代命题”的高度抽象的阐释,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哲学史;中间层是在思想层面对“时代命题”进行直接的整体性陈述,而所谓“直接的整体性陈述”,就是指对“时代命题”的一般性思考及回答,由此形成具体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就是思想史的位置;而其底层,则是从文化、学术、政治、经济等不同具体学科的侧面对“时代命题”的分析和表达,由此形成相应的文化史、学术史、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每个侧面的理论观点和主张的陈述,又构成不同侧面的专门思想史,如文化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等。观念史的抽象性、整体性(理论性)与具体性的层次差异,表明了哲学史、思想史和其他专门史在人们观念史中不同的层面位置。这种不同的层面位置,决定了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专门史对于“时代命题”的提问和回答是不同的。如上所述,“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则是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近代中国“时代命题”进行一般性的整体性理论把握和陈述而形成的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相互关系。
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想是分为不同层面的。以孙中山为例。他的“知难行易”学说属于观念史的最高层面,即哲学层面;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属于观念史的中间层面,即思想层面;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西方文化的论述,属于观念史的下层层面,即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部门史层面。思想史要研究的,不是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也不是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西方文化的论述,而是他的“三民主义”。因为他的“三民主义”是对近代中国“时代命题”进行一般性的整体性理论把握和陈述而形成的具体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而我们以前的一些思想史著作,由于对孙中山的思想没有进行层面上的区分,凡是他的思想,如“知难行易”学说、“三民主义”学说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西方文化的论述,等等,都统统被吸纳了进来,其结果造成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混淆不清,既可以说它是哲学史著作,又可以说它是思想史或文化史、学术史著作,没有在学科上把它们区别开来。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也是如此,其思想是可以分为不同层面的。我们写思想史,就不能写他们所有的思想,而必须有所选择,要选择他们对近代中国“时代命题”进行一般性的整体性理论把握和陈述而形成的具体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至于他们的其他思想,则可以视其属性交由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去研究。当然,他们的哪些思想是对近代中国“时代命题”进行的一般性的整体性理论把握和陈述?哪些思想又不是对近代中国“时代命题”进行的一般性的整体性理论把握和陈述?这就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判断,实际上也是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素养的一种检验和考察。至于宝明先生所说的“总结‘经验和教训’和寻找‘规律性’不止是思想史这一学科的任务,而且也是整个史学学科的任务”,这我完全赞同。但同样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和寻找‘规律性’”,各学科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和寻找的“规律性”也是不同的,哲学史学科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和寻找的“规律性”并不能代替思想史学科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和寻找的“规律性”。同理,思想史学科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和寻找的“规律性”也不能代替文化史、学术史和其他专门史学科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和寻找的“规律性”,如此等等。
张宝明:对话及此,大华先生的观念史层面划分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可以这样说,这一对话的基本意义也由此彰显出来。诚如大华先生所说:“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混淆不清,既可以说它是哲学史著作,又可以说它是思想史或文化史、学术史著作,没有在学科上把它们区别开来。”既然我们在学科不清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且以孙中山研究为例很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大华先生提出的隶属于思想史这个“中间层”的具体内涵问题:“中间层是在思想层面对‘时代命题’进行直接的整体性陈述,而所谓‘直接的整体性陈述’,就是指对‘时代命题’的一般性思考及回答,由此形成具体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就是思想史的位置”。居于“中间层”的思想史位置要解决的“时代命题”究竟是什么?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的“时代命题”,无论是观念史的哪一个层次都是要面对的。其实,哲学史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并没有说到底。就其实质,思想史才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的历史描述。前一个“思想”是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的思想家的思想;后一个“思想”是后来的学者关于思想家之思想的描述、检讨、肯定等等评价类的历史书写。既然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等都是关于历史上什么什么思想的思想之书写,那么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大历史学科的背景下,每一个分支学科都在关系“思想”的情况下,思想史还是应该有具体的关照对象。这个关照对象在本人看来就是与“人”有关的思考。这样说也许还是稍嫌抽象,同仁一定会反对:试问,哪一个学科不与“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呢!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的“人”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具体的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人文视角下的“人”,一个需要独立、自由,需要呵护、张扬个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的人际书写主要还是人文书写。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很多场合更愿意将思想史看成是人文思想史。二是当时当地的“人”,即是处于当时背景下的“人”与“现实”的互动下的“人”。很多思想史学者喜欢从“情”与“势”互动的视角研究思想家也是这个缘故。较为麻烦的是,在将人文思想史这个概念提出的同时,思想史与文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分离和交叉又暧昧、缠绵开来。不过,我以为,思想史的人际书写若是离开了人或者说抛弃了“人”这一世界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典范的。
这样一来,思想史的写作必先回答的问题就是:人应处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应该解决的对象。只是这个解决就是大华先生说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如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思想家面对时代的命题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与回答,而每一个思想史家面对思想家的不同反应和回答也都有自己的人际书写方法和自我评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本思想史章节中都会看到个人、国家、社会之关系论述的原因。环顾当下的思想史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内容总是带着近现代史的烙印、几乎一样的面孔,那么我们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还能有什么独立和个性可言?思想史有其自身的质地规定性,有其自身的切入点,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思想史研究进行到底!
郑大华:我非常赞同宝明先生的观点,任何历史的研究都离不开人。这里的人有两层含义或两个层次:一是“主体”的人,即历史的研究者,也就是“我们”;一是“客体”的人,即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是“他们”。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主体”的人(“我们”)和“客体”的人(“他们”)之间的对话。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思想史是如此,作为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莫不如此。就此而言,诚如宝明先生所说,思想史的研究的确是不能“离开”或“抛弃”人这一“世界的中心”的。不仅思想史,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有谁又能“离开”或“抛弃”人这一“世界的中心”呢?能离开了人,也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历史,又哪来历史的研究?当然,同是“主体”的“我们”与“客体”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但由于其关注点的不同,其对话的内容也必然会有不同。否则,也就不会有学科之间的区分。另外,我们讲历史研究不能“离开”或“抛弃”人这一“世界的中心”,但我们所讲的人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作为具体的生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人,他必然要受他所处的时空环境的影响,要思考和处理他所面临的或有可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宝明先生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等问题,对这些不同问题的不同思考以及得出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主张,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或对象的不同。这也就是我前面讲的观念史的层次问题。
回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这一话题上来,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我们所讲的思想史,是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等并列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非是人们的所有思想的大杂烩、大拼盘。如今许多思想史著作,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人们的所有思想的大杂烩、大拼盘。这种思想史看起来非常全面,既有哲学思想,又有文化思想,还有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什么思想,但实际上如此一来,则取消了思想史作为历史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的独立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既然思想史可以写进哲学史,可以写进文化史,可以写进学术史,可以写进其他什么史,那我们还需要思想史干什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或对象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或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观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中国近代思想史绝对不能等同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或其他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不是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的大杂烩、大拼盘,我们不能把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统统写入思想史的著作之中。在这一点上我和宝明先生是有共同认识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的讨论是抛“砖”,目的是为了引“玉”,我们真诚欢迎和希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和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只有讨论,才有可能取得基本共识,从而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张宝明:诚如大华先生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筐”,更不是一些诸多思想的大杂烩、大拼盘。过去有一句话很是流行:“市场经济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如果我们把思想史研究描绘成社会史的样子,可以“上天入地”,那无疑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万宝囊”。鉴于这样一个共识,也许,中国近代思想史,其实不止是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纳入写作视野的应该是活动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究竟该如何是好的问题。近一个时期,当思想史的写作者把“写法”首先瞄准“民间”社会之际,一个走样的思想史,一个丧失独立性的思想史,一个永远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思想史出现了。对此,我一直在追问:思想史的内容那样捉摸不定,你离我们究竟是近还是远?好在大华先生和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郑大华:的确,思想史的内容对研究思想史是关键,但近年来关于思想史的起点问题也应该关注,不知宝明先生以为如何?
张宝明: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作认真梳理,同时起点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史的研究命题,对此我们不妨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专门进行,这个问题急需同仁们关注。
标签:思想史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