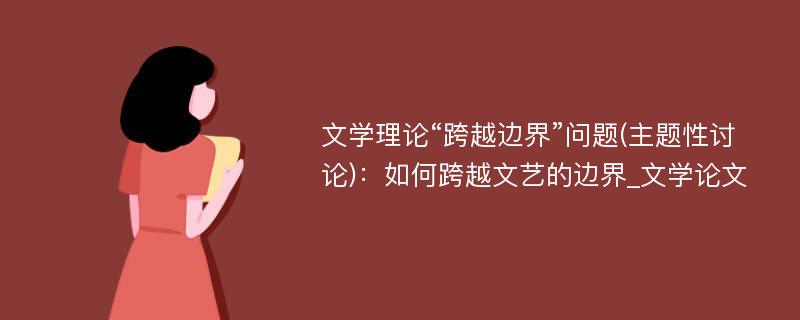
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专题讨论)——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边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有人进行反思。反思就是对现有的状态不满,想办法把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推进一步,这对文艺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拒绝反思。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的一些新锐教授发表了两组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一组发表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一组发表在《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他们提出文艺学的所谓“文化转向”,认为文艺学要“扩容”、“越界”。那么,这“容”要“扩”到哪里去,这“界”要“越”到哪里去呢?他们说,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已经“终结”或“将要终结”,因此,面对这“全球化”时代,这“消费主义”时代,这“图像”时代,这电子媒介时代,如果文艺学要生存发展下去的话,就要转移研究的对象,放弃那种以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要按照英国学者费瑟斯通的高论,把所谓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也有的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建立起“文艺学的主导范式”,把“身体美学”之类“确立”为“新的美学原则”,并颠覆康德的理性的审美观念,否则的话,美学、文艺学就要“面临深刻的危机”。
这里提出一大堆问题,可能够我们讨论好几年的了。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就文艺学“越界”的问题谈一点看法,别的问题将在以后一一予以讨论。
文艺学的边界要不要移动呢?当然是要移动的。但是,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是统一的。文艺学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大致上是确定的,否则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就不能成立。这些新锐教授的一个说法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深刻地挑战了文学自律的观念,以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经典的“文学”、“艺术”已经不是我们时代的“文学”、“艺术”,倒是那些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才更是今天的“文学”、“艺术”。他们这种理论岂不有点怪诞吗?他们为什么会说出这种怪诞的话来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们似乎认为今天的文学已经“终结”或将要“终结”,其中的一位教授以《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的蔓延》为题发表文章,透露出了这个“消息”:今天的文学已经“终结”(他们有时又说是“文学边缘化”,边缘化与终结是一回事吗?),所剩的只是“文学性”了。那么,这种“文学性”在哪里“蔓延”呢?是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蔓延。如果文艺学还要“苟延残喘”的话,那就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这就是他们的逻辑。问题是,这种逻辑符合当下的现实吗?
我承认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已成为了当下富人、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喜欢进出的场所或热衷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无人去否认它。但是,原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也同样存在着。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反腐倡廉的作品,不但数量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历史题材的作品,“帝王系列”、“才子佳人系列”,也同样数量多并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那些所谓的“纯”文学,有很强的“文学性”的文学作品,如杨绛的《我们仨》,一印就是几十万,日本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作品,引进中国只有几年时间,但印数已经超过百万。如今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接近一千部(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是十分粗劣的),各种散文、小说、诗歌选集的出版更如雨后春笋。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印数,要以千万册计,这其中纯正的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读者面涉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他们阅读的不可缺少的文学资源。为什么我们那些新锐教授眼中只有主要属于白领阶层的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而把正在发展着的文学置于视野之外呢?这里是否有一个学术立场问题呢?是否有厚此薄彼的倾向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把欣赏所谓的“身体”的美学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而且要否定原有的美学原则,“确立”这种充满商业意味和感性欲望的美学,这又是在为谁争夺“话语权”呢?
这些新锐教授把文艺学的边界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后,扩大到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之后,也觉得有点对不起“文艺学”这个学科,于是,他们转而称赞“文艺学的方法”。那意思是,原有的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不行了,不过那方法还是不错的呀!他们说,“一种研究是否属于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性的),即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而对于那些审美因素、商业因素、经济因素等混合一体的因素(如广告),则可以借用文艺学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审美/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维度”,这种研究“离文艺学的研究更近一些”。非常感谢他们如此称赞“文艺学的方法”。我们当然知道同一个对象可以从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对于文艺学的研究,我想重要的是对象,即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问题,至于方法那倒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文学本身有语言的、审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等多种维度,因此,用语言学的、审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等方法,去研究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都可能是文艺学研究。我们整天说要找到研究的新视角,其主要意思是寻找到一种与对象相适应的方法。因此,衡量一种研究是不是文艺学研究,主要地看研究的对象是否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必过分看重方法本身,方法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因此,那种否认文艺学原有的研究对象却只是认同文艺学的方法的说法不是有点奇怪吗?
我承认,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也的确没有不变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的边界不是固定的,是移动的。但文学的边界只能是根据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的移动而移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今天我们是否就可以撇开原本意义的文学,而把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看成是文学?这种看法是现实的吗?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边界的问题用得着这样下力气去讨论吗?当然用得着。因为在他们提出问题的背后,隐含了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是后现代,还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又如,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主义”是什么?是消费主义,还是求温饱“主义”,还是消费与求温饱并存?再如,文学是否会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对于费瑟斯通一类学者的舶来品,我们是拿来就用,还是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当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的时候,是否还要主体性?对于今天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