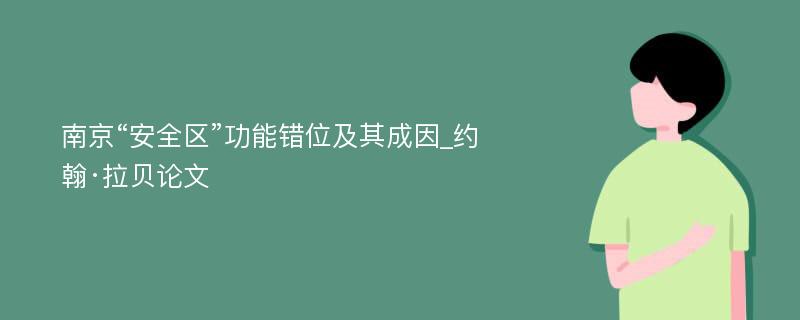
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区论文,南京论文,原因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性中善与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至少在特定环境中的显现是不平衡的。1937年末,南京“安全区”(the Nanking Safety Zone)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的成立是在人性泯灭的黑暗中代表人性善良一面的一个亮点。
当大多数中外人士争先恐后地撤离战火纷飞的南京时,却有十几位外国人不顾各自政府的警告毅然留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供那些没有能力逃走的穷人躲避战乱的“安全区”;当日军在南京疯狂施暴时,他们充当全天候的“卫兵”,保护难民,供给粮食,运送燃料,救治伤病,抗议暴行。
随着拉贝(John Rabe)、贝茨(Miner Searle Bates,中国名:贝德士)、马吉(John G Magee)、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中国名:华群)、菲奇(George S.C.Fitch,中国名:费吴生)等人日记和信件的发现与发表,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在更深层次上为人们所了解。人们对“安全区”的评价也从“安全区不安全”转变到“(安全区)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注: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个个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工作;一方面“安全区”内又发生了种种暴行。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日军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安全区”原先被设定的功能发生了错位。
一
所谓“安全区”功能的错位,是指“安全区”原定的主要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而一些次要的功能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那么,南京“安全区”建立的目的或者说原先为它设定的功能是什么?从“安全区”成立的原由上看,南京“安全区”是受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示而创建的。上海南市“难民区”最大的成功是其发挥了安全保护功能。难民区的发起人雅坎让(Jaquinot,中国名:饶家驹)设法使中国政府和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南市难民区的合法地位,因而在以后的战斗中及上海沦陷后,在南市难民区里避难的数十万难民生命得以免遭战火的涂炭和日军的屠杀。在此前提下,难民区的组织者们还为救济难民做了大量工作。
显然,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成功——安全保护功能和救济功能在日军进攻上海及战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正常发挥,给南京“安全区”的发起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市“难民区”创建的模式、方法及其所发挥的功能成为后来成立的南京“安全区”所效法的楷模。
拉贝在1937年11月19日的日记里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大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注: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当时拉贝还未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也不是“安全区”的发起人,所以说的不够全面。
后来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菲奇在1937年12月24日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们当中读过我上一封信的人会记得,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直在同日中双方谈判以便承认南京城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士兵和所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入内,这个区域也不得被轰炸和炮击。当情况变的非常紧急的时候,留在南京的20万人能够在此避难,因为很明显中国人在上海进行的了不起的,持续如此长时间的抵抗现在已经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士气也已丧失。日本的大炮、坦克和空中优势使他们遭到重大损失……日军在杭州湾的成功登陆从侧翼及后部进攻是他们失败的决定事件。南京的很快陷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注:December 24,1937 circular letter of George Fitch in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edit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p.4.)
我们再看看“安全区”重要发起人之一贝茨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的证词。他说安全区是“以饶家驹神甫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为榜样,这个委员会对那里大量的平民提供了相当的帮助,我们试图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在南京做相同的事。委员会成立之初是一个丹麦人为主席,有德国、英国、美国成员。但因为外国政府从这个城市撤走了几乎所有的本国公民,在日本进攻南京的时候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留了下来。主席是一个杰出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通过美国、德国和英国使馆的传递信息和斡旋,委员会同中国和日本指挥官接触。目的是提供一个小的非战斗区域,在这里平民可以避免战斗和遭到进攻的危险……委员会估计它的主要责任是在该城被包围,中国行政当局可能已消失,但日本军事当局尚未建立时,提供住房,如果必要的话在几天或者一两星期内提供食物”。(注: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IMTFE(《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庭审笔录》),第2625—2626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ecord Group 331,Entry 319,IPS))。)
可见,建立南京“安全区”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为平民提供一个躲避轰炸、炮击及免遭日军进攻的场所(即安全功能);二是如果躲避的时间较长,还要为这些平民提供住所和食物(即安置和救济功能)。很显然,前者主要的,后者为衍生的。这显然也是“安全区”名称的由来。
然而,南京的迅速陷落虽然使战斗对平民所构成的伤害危险很快消失,但占领军的故意施暴却使得难民长时间地处在新的危险中,因而南京“安全区”实际功能的发挥同预先设想的无论是在时间和规模上,还是在轻重次序上都有不小的变化,同时历史也赋予安全区一些新的功能。
“安全区”虽冠以“国际”的头衔,但实质仅为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而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安全区”的安全功能是否可以正常发挥完全取决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意愿。只要日本军方不合作,“安全区”注定不安全。
实际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对此是非常了解的,在发给日本驻华大使有关建立“安全区”建议的电报中委员会特别强调:“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在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注:拉贝:《拉贝日记》,第98页。)当迟迟得不到日本方面答复时,在12月1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只好决定“暂时把中立区称作‘难民区’,而不是‘安全区’。”(注:拉贝:《拉贝日记》,第123页。)
后来事态的发展显示,从严格意义上说,安全区从未能正式成立,因而其预设功能的错位也就在所难免。米尔斯在1月24日的信里说:“我们从未能向双方正式宣布安全区已开始运行,因为当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走,使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地发表这样的声明时,所有外国军舰已驶离南京,我们已无法发出这个声明,因为其他的通讯方式早已停止运行。”(注:Martha Lund Smally(edit.),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Documentation of the Nanking Massacre.p.44,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2月5日,日本在正式答复有关“安全区”的电报中,再次拒绝承认“安全区”,其借口是:“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利,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和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注:拉贝:《拉贝日记》,第135页。)“安全区”自己没有能力来实现“安全区”非军事化的目标,这不仅成为日军拒绝承认“安全区”的“前因”,也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安全区”无法发挥安全功能的“后果”。
日军不仅口头拒绝承认“安全区”,实际行动中也是如此。主要表现形式有:第一,轰炸和炮击“安全区”。“安全区”数次遭到日军炮火的袭击并有人员伤亡。菲奇在1937年圣诞夜所写的一封长信中提到,12月11日有数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南部,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附近炸死40多人;马吉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一发炮弹击中了安全区的一所房屋,有20人被炸死,其中7—8人被气浪抛到街上(注:参见杨夏鸣译:《马吉日记》,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拉贝在日记里也有类似记录。尽管同城南相比,落在“安全区”的炮弹要少一些,但这并非不是“安全区”功能发挥的缘故,而是因为“安全区”内没有多少军事设施。史迈斯在1938年3月8日写的一封信是很好的佐证。他说:“在战斗期间我们就睡在平时的床上,愚蠢地相信日本人会指示他们的大炮尊重安全区。12月13日下午,当我们在城中和他们的先头部队接触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在他们的地图上标出安全区,我的头发都惊得几乎竖起来。”(注:Martha Lund Smally(edit.),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March 8,circular letter from Lewis S.C.Smythe,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
第二,搜捕安全区内的警察、平民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按照原先设想,安全区应该是有明确的界限标志和有警察守卫的。拉贝在其11月3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第二条就是有关安全区入区的检查、安全区边界的守卫及警察人员的数目与安置。中国政府曾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来维护安全区内的治安,但日军入城后不仅在安全区内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而且也将这些警察和一些志愿警察拉去屠杀。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里格斯去解释和阻止时,还遭到了日军的殴打。“安全区”在日军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从中可略见一斑。
第三,大肆强奸妇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一就是性暴力犯罪,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发生在安全区内。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稍早些时候(指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我仅根据安全区的报告,更为谨慎地估计是8000例(强奸案)。”(注: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IMTFE(《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庭审笔录》),第2634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ecord Group 331,Entry 319,IPS)。)应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日本兵在强奸时,见到外籍人士会落荒而逃,但这并非是他们意识到“安全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对外籍人士尚有所顾虑。实际上,外籍人士从未能阻止日军进入“安全区”,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将日军从他们的住宅或是属于他们财产的地盘里赶走,或是阻止强奸犯罪。
二
正是由于日军上述的种种暴行,反使得“安全区”的衍生功能,即安置、救济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在时间、规模、还是在社会效果和历史意义方面都是如此。
从时间上看,国际委员会成员原先估计“安全区”的存在只须几天时间,最多数星期。“难民区初设之时,本会原冀近城战事告终之后,难民即可遄返故居,而本会责任亦不久即可完了”。(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8页。)但实际情况是“安全区”一直存在到1938年2月。在此之后,一方面是迫于日本当局的压力,更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另一方面,该名称也更能反映出“安全区”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即救济功能的发挥。事实上,直到1939年与1940年之交,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才基本上结束。(注: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
从规模上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先估计:“如果区内的私房主及私房的租户能向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昨天的报纸已公布,公共建筑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16平方英尺的话,这些建筑可容纳3.5万名贫穷的难民。”(注:拉贝:《拉贝日记》,第153页。)但实际情况是,难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先估计会有2000妇女来避难,但后来最高峰时达到1万人。整个安全区最高峰时有25万难民,在25个收容所里避难的难民也达到了7万人之多。(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8页。)
从效果上看,“安全区”的救济功能得到了应有的发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障了难民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粮食及燃料的供应。据斯迈思的调查,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平均82%的人从粥厂里取得粮食,“安全区”里有17%的人依靠粥厂。(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284页。)有如此众多的人依靠救济度日,还有日军的严重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区内却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另外,在卫生防疫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当难民流行脚气病时,委员会根据医嘱,“遂设法供给蚕豆,俾将必须的食物成分,增入米粥中,盖米粥为最贫苦之人之唯一粮食也。本会煞费苦心,经数星期之交涉,卒由上海方面运到蚕豆87吨,分成1077袋每袋重161.55磅以之分发各难民”。(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12页。)1938年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为16265难民接种牛痘疫苗,为12000多人注射了伤寒霍乱预防针。(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17页。)在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下,没有发生疫情,即使现在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区”救济功能的发挥与其安全功能的发挥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一般是作为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和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而后者往往取决于有没有外籍人士。如在安置方面,有条件的难民或是投亲靠友,或是租赁区内的房屋;赤贫者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统一安置到区内的公共设施里,而青年女性则被安置在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救济方面,不同收容所里的难民每天得到的救济粮基本相同。国际委员会还对各个收容所进行检查、做出评估、提出整改措施。在卫生方面,国际委员会下属的卫生委员会组织了400名人员专门负责街道清扫,在人多的地方修建和管理厕所。更重要的是,有1500多名中国人参与了安置和救济工作。国际委员会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不过我们设法使金女大有一定的安全,金大次之。沃特琳小姐、特威纳姆(Twinem)和沈夫人在照顾和保护妇女们时非常勇敢”。(注:Martha Lund Smally(edit.),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December 20,circular Letter of George Ficth,p.11,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菲奇也把相对的安全归功于个人而非“安全区”。美国使馆的副领事埃斯皮(Espy)在一份报告中不仅把相对的安全归功于外籍人士,而且把“安全区”本身视为是他们个人努力的一部分。他写到:“显然这些外国人在南京的存在这一事实,对日军的行为至少产生了一些制约的影响,使其有所收敛。毫无疑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外国公民的个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百姓免遭更大的不幸,使他们的财产免遭更大的毁坏,前面提到的安全区就是他们努力的证明。”(注:杨夏鸣译:《美国驻华外交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言》,《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第63页。)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下,“安全区”还是相对安全的。然而,把相对的安全归功于“安全区”本身则无法解释“安全区”里所发生的暴行的不平衡性。
三
在分析“安全区”功能错位的原因时,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由于日军的野蛮和残暴造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过于笼统。为什么同样野蛮、凶残的日军,在经过长时间、激烈的战斗并遭受重大伤亡后没有对在上海南市“难民区”及租界里避难的数十万难民进行大屠杀和进行大规模的性犯罪呢?单用野蛮、凶残难以解释。有人可能会说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大屠杀可以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惧、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这种分析符合逻辑,但无法解释日军不是大张旗鼓地宣扬南京大屠杀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这一历史事实。显然,上海南市“难民区”同南京的“安全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或是南京的“安全区”,实际上都是国际法里的“中立区”。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人之一奥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enheim)认为,“中立乃一国不参与战争而取得的法律地位,必须对交战国保持不偏袒的态度,并获得其承认”。(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根据这一理念,“中立区”应是仅用于人道事业,并被交战双方所承认的区域。
另外,1864年、1907年缔结,1906年、192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敌方领土或敌占领区内的和平居民,冲突各方应设立医院、安全地带和中立化地带,使其免受战争影响。”“对于占领区的和平居民,在一切情况下应尊重其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和仪式、风俗习惯。妇女应得到特别保护,以免其荣誉受辱。”
综上所述,一个规范的“中立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仅用于人道目的;一是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同时,交战双方对中立区的承认并非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一种道义或法律义务(如果是条约签字国的话)。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上海南市“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的根本区别是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尽管两者建立的目的——用于人道事业,是完全相同的。
时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后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日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谈到这个问题:“当上海附近的战斗在持续着,估计中国军队将要撤退时,成立一个由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雅坎让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建议在南市(上海南面的中国城)创建一个‘安全区’,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赞同,其目的是如果战火蔓延到那个地区的话,在那里收容中国人。一开始,雅坎让在《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Timparly)的陪同下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他们的设想,我采取了一些步骤,在上海总领事冈本(Okamoto)以及冈崎(Okqzaki)的协助下将这一计划赋诸实施,从一开始,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和海军司令长谷川(Hasegawa)对此就持积极的态度,这两位司令同意的这个计划,中国人也同意了这一计划。这以后,松井石根向委员会捐款一万日元以帮助赞助这一计划(海军司令长谷川Hasegawa也捐了款)。另外,12月8日本外相广田也给雅坎让发了一份电报,代表日本人民对这一人道工作表示赞扬和尊敬,并对他的成功表示良好的祝愿。”他还说明了日本当局承认上海“难民区”的原因:“1.这一地区纯为一个中国城,雅坎让和其他的委员会成员都是公平和无私利的。2.当有战斗时,委员会将收容和保护中国的非战斗人员,在战斗结束后,救济和保护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委员会同意不干涉这一地区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一工作完全是由日本军队控制的。3.由于法国租界同这一地区相连,租界当局愿意合作,委员会被认为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持‘中立’。考虑这一地区的位置,即使附近发生战斗,这一地区被认为能保持‘安全’。上海战斗进入最后阶段时,战斗曾蔓延到这一区域的边缘,然而没有炮弹落入该地区。撤到这个区域里的中国士兵被委员会解除了武装。日本军队没有进入这一地区。一切都很顺利,这样数以千计的房屋和25万中国人的生命得到挽救。”(注:Tranx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IMTFE(《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第2625-2626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ecord Group 331.Entry 319,IPS).pp21459-21463.)
从表面看,南市“难民区”发起和建立是法国人雅坎让的个人行为,但实际上南市“难民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有着外国政府的背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难民们以为租界安全,纷纷涌入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高峰时达70万左右。(注:《立报》1937年8月31日,转引自罗义俊:《南市区难民区略述》,载《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法租界当局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正式宣布戒严,关闭租界入口,大批难民滞留在民国路上。但到11月,大多数难民还是进入了租界。有关方面迫切需要找到安置难民的新途径。英、法等国驻沪领事直接或是间接地参与了难民区的建立和管理。“还在筹建阶段,就已确定难民事宜由英、法各国驻沪领事及教会方面共同推定人员,组织委员会处理。正式成立时,委员会名称为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全由外籍人士组成,其中有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普兰特(W.H.Plant)、法租界公董局的雅斯帕尔(A.S.Jaspar),饶家驹任主席”。(注:罗义俊:《南市区难民区略述》,《抗日风云录》,第179页。)而且,后来难民区的治安一度由外籍警察维持。南市陷落后日军也有进入难民区和向中国警察开枪的记录,但属偶发性质。显然,日军在对上海难民区及它后面的外国政府还是有所顾忌的。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当局承认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决定出兵上海,8月17日日本天皇召见了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并要求他“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戡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注: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这里所谓的“宜细察宇内大势”显然是要松井,注意西方列强的反应,在同中国军队作战时避免与列强发生冲突。松井对此心领神会,他在其后来的日记中写到:“最令人遗憾之事,乃列国军队对本次作战的态度。勿庸赘言,对中国享有权益之列国甚为关心本次作战,然彼等不思遵守1932年列国之停战协定,遵循该协定精神,阻止事件之发展,反同情中国政府及军队,直接间接立于中国军队一方,为中国军队作战提供便利,采取行动援助之。尤其英、法军队之行动,与我军作战以诸多不便,多有妨碍我作战之举。而我军则委曲求全,尽力谋求列国官宪极其军队的谅解,为了不使我作战损害列国官民而忍受一切不便,努力避免招致国际纠纷。”(注:《中国事变日志摘录》,转引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第109-110页。)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当日军于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成功,日军在军事上已取 得了绝对的优势,上海的陷落已指日可待,为了避免在当时正在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遭到谴责,日军当局顺水推舟同意南市“难民区”成立。在此之前(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南市难民区于11月5日正式成立。
相比之下,南京完全不具备上海所具有的类似的条件。尽管美、德等国的驻华使 馆对筹建“安全区”表示赞同,并协助传递信息,但南京“安全区”的建立纯属个人行为。加上,日军的一些将领对未能在上海围歼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而耿耿于怀,并将南京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场所。这就决定了南京“安全区”不可能得到日军的承认。这也是“安全区”功能错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安全区”从建立到解散,其间遇到了各种各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安全区”发起人之—米尔斯(Mills)在谈到建立“安全区”的经过时说:“我们的南京安全区完全靠勇敢,或者,如果你喜欢,靠信念,或者靠某种不考虑后果的大胆,才得以实施。”(注:Martha Lund Smally(edit.),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Docrmentation of the Nanking Massacre,p.45,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创建“安全区”的艰难及委员会成员对那些非个人所能克服因素的无奈。作为个人,这些外籍人士除了靠勇气和信念外,的确也难以再有其他的作为。这也可能是拉贝在万般无奈中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他说服日本同意建立“安全区”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安全区”的美籍人士是否也有类似的举动,但我们确实知道留在南京的14位美国人于12月20日联名给美驻沪总领馆发了这样一封电报:“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注:拉贝:《拉贝日记》,第235页。)我们还知道1935-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3个中立法案,规定:“凡由美国或美国其他属地之任何地点,将武器、弹药及作战工具输往任何中立港口,或输往任何中立国港口以便运至交战国港口,或输往任何中立国港口,以便转运至交战国或为交战国所用均属非法。”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对中日战争运用中立法的声明。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希特勒不可能帮助拉贝那样,美国政府也不大可能对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努力提供帮助,更何况这还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主权的问题。
因此,国际委员会只能把“安全区”建立在诸如“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注:拉贝:《拉贝日记》,第124页。)这类模棱两可许诺的基础上。事实证明这种许诺是靠不住的,日军很快就找到了不尊重“安全区”的借口——一些中国士兵在来不及撤离南京的情况下,放下武器,脱掉军装后躲进了“安全区”(根据国际法,放下武器的士兵应被视为战俘,屠杀他们是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此,这决不是开脱日军罪责的理由)。这也是“安全区”功能错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守军撤退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大批中国守军无法有序地撤走,滞留在城内,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安全区”。日军的既定方针是搜捕并屠杀——即所谓的“纪律肃正”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因而在“安全区”开始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搜捕行动。除了个别情况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从一开始“安全区”就规定了不应该有任何中国军人进入,何况日军已怀疑外籍人士是有意让他们到“安全区”来躲藏,更重要的是不象强奸、抢劫这类属于个人性质的犯罪,在一定的场合下,外籍人士尚能加以阻止,面对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战俘的犯罪,个人是很难终止这种犯罪的。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要求日军善待这些俘虏。日军不仅不按照国际法对待中国俘虏,而且在搜捕过程中,或者以此为借口犯下了屠杀平民的罪行。贝茨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有过详细的描述:“日本军官指望在城里发现大批中国士兵,这给安全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当他们没有发现这些士兵时,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士兵躲在安全区内,我们应该对隐藏这些士兵负责。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官兵及非军人在3个星期里日复一日地到‘安全区’的难民中搜捕前士兵。通常的做法是将安全区某个区域里或在某个收容所里所有轻壮年男子排好队逐个检查,如果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好几次我在现场,看到了整个过程。毫无疑问,难民中有一些人是士兵——即脱掉军装,放下武器,穿着平民服装的士兵,但这样被抓走的人大多数是普通的挑夫和劳动者,他们手上有老茧是常事。通常他们被带到城外并立刻被枪毙。”(注:《国际远东军事法庭庭审笔录》,第2631-2632页。)另外,很多强奸、抢劫等罪行也是在这一借口下进行的。日军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的上等兵东口义一的供词也证实了这点,他说:“1937年12月14日,步兵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在南京城内时,根据小队长市川中尉的命令,我作为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在分队长吉村军曹指挥下,以打扫战场和搜索隐匿武器为名,进入军官学校内的民房,结果发现看家的一名35岁左右的妇女,我用手枪威胁把她强奸。”(注: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因此,如果中国军队都能顺利地撤出南京的话,“安全区”可能会更好的发挥其安全功能,至少,日军少了一些犯罪的口实。
综上所述,由于日军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加之“安全区”的建立系个人行为,以及部分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躲进了“安全区”等原因,作为整体,“安全区”原先被设定的安全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安置和救济功能却上升到主体位置。本文的目的并非贬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他们所创建的“安全区”的作用,恰恰相反,是为了表扬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作风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为个人为保护难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希望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区”和“大屠杀”这一始终伴随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一对似乎矛盾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