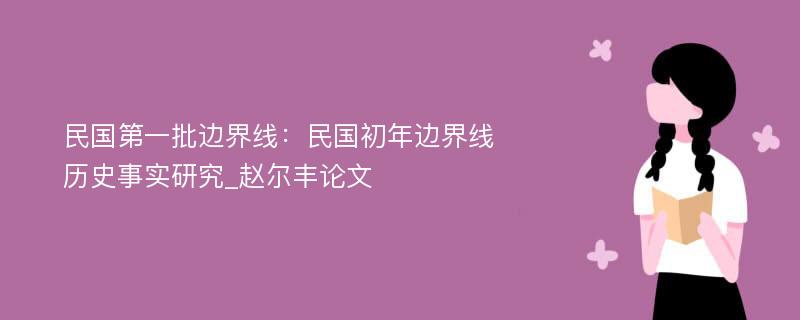
民国标界第一桩——民国元年察隅巡边标界史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察隅论文,史实论文,元年论文,一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清政府在西藏及当时的川滇边推行新政,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派遣程凤翔率部南下桑昂曲宗,进驻察隅,巩固边防,在中印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压必曲龚树立边界标志。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所关注。英国著名的中印关系学者拉姆将程凤翔所部进驻察隅置于英属印度改变其东北边境政策的过程中加以评论,认为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入“阿萨姆的喜马拉雅山区”是英属印度改变对东北边境政策的一个原因。①印度学者梅赫拉出于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寻找历史依据的目的,声言赵尔丰、程凤翔在察隅的作为促使英属印度加强了对边境地带部落的管理与控制。②两者均未考察中国对察隅边境地区的治理,有意或无意将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边境地区居民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部落民。我国学者吴丰培充分肯定赵尔丰、程凤翔为捍卫国土所作出的贡献,指出:程凤翔“在压必曲龚地区,插立国旗,以阻英人前进,尚为识大体者”。③笔者曾发表论文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依据中外档案文献的记述得出结论:察隅边境地区为中国固有领土,在程凤翔进驻察隅之前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在该地区进行了包括征收地税田赋在内的有效管辖;英国为了封锁、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实施将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山脊线的“战略边界计划”,谋图侵占我国门隅、珞渝、察隅固有领土;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驻察隅,目的是加强边防,捍卫国土;程凤翔在瓦弄以南压必曲龚树立大清龙帜,建立界牌,阻止英属印度侵犯。④ 程凤翔进驻察隅后一年余,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及川滇边形势骤变,英人扶持达赖十三世回藏,掀起“驱汉”狂潮,察隅被围困。1912年春夏之际,中华民国特使受命奔赴察隅,会同察隅地方军政南下压必曲龚建立中华民国界标。其时英属印度边境官员拔除这一界牌,企图销毁证据。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未对此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本文拟钩稽、考证、对比中外文档案文献的有关记载,发掘几被湮没的史实,理清该事件的缘由及经过,为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的真实走向再呈历史证据,并以此祭奠捍卫国土的先辈。 一、压必曲龚的中华民国界标 民国元年(1912)春夏,由成都出发的中国赴川滇边特使历尽艰险进入孤悬边塞,处于重围之中的察隅城。不久,赴川滇边特使等人又冲出重围,南下日马,顺高山深谷中的察隅曲,跨越簸荡虚悬的偏桥栈道,过瓦弄,穿石峡,进至压必曲与察隅曲交汇处的压必曲龚。他们沿路巡查当年1月间日马中国军营受令树立的用汉藏文标写“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的界牌,指示随行的日马军营人员将他们随即送来的新界牌树立于原界牌旁边,并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还查看了1911年末至1912年初英属印度派遣的非法入侵中国藏南地区远征队中的一支在中国树立界牌对面驻扎的营地。 1914年初春,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政治官员助理奥卡拉汉(O'callagham)再度溯洛希特河北上至门巩,在中国树立界牌处发现了这块新立的界牌。其时,英国经上述远征队的考察,对其所要实施的将传统习惯线北移至喜马拉雅山脊的“战略边界计划”原定的边界走向已有调整和修改,在察隅方向谋划将原定走向北推至瓦弄以北。奥卡拉汉于是将这块新界牌拔出,北上带至卡巴村,丢弃于森林之中。 中国特使赴察隅巡边立界牌事见诸英属印度方面的记载。 其一,英属印度东北边境萨地亚官员邓达斯的报告,兹翻译如下: 1912年7月15日,自密西米远征队撤离后专职东北边境的邓达斯(Dundas)报告,两个米珠密西米人(Miju Mishmi)数天前到达萨地亚报告,三位中国官员到叶普克(Yepuk)和麦尼克赖(Menilkrai)巡查。据米珠人说,这伙中国人不属于日马军营,而是来自中国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位似乎是重要的官员。他们沿洛希特(Lohit)河左岸而下,在临近英军在叶普克河营地时,对工兵和矿工雕刻在一块大花岗石上的两条碑文进行拓片(碑文一为团队成员的姓名及日期,一为孔子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检查了麦尼克赖的双语界牌(即上面所说的用汉藏语标示的“中华帝国四川省边境察隅南部边界”界牌),并指示将他们即将送来的另一个界牌树立在旁边,搭建木棚遮蔽风雨。他们沿着新路一直走到芒洛尔(Manglor)平地南端,始折回循原路返回日马。没有其他的密西米人在场,只有他们从丁内(Tin-ne)和其他村子带来的一队苦力,建立新界牌的命令就是向他们发出的,此外并没有直接或通过藏族向部落民发出其他命令。 中国团队可能就是“特别官员”Chiang Feng-ch'i及他的随员英语翻译Chao Yangyun和向导Shu Chi-liang,成都报纸曾报道了他们出发到边境,总领事务Wilkingson在1912年4月1日的信件中附上这篇报道。⑤ 其二,奥卡拉汉对他在门巩附近发现后被他抛弃在卡巴村附近林中界牌的记述,英文如下: The new post,a pine plank 7'×16' on which was inscribed neatly in English,Tibetan and Chinese:The southern boundary of Chuan Tien Tsa Yu of Chinese Republic established by special 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 and magistrate of Tsa-Yu,Kes Min Chin-Tsa-Yu,June9th 1912. 笔者试译如下: 在这块7×16英寸新松木牌上用英、藏、汉三种文字工整地题写:中华民国川滇察隅南界,特使Chiong Fong Chi、察隅县长Kes Win Chin立,1912年6月9日。⑥ 在上引两则史料中:Kes Win Chin,即苟国华的字。苟国华,字文卿,甘肃举人,以州判分发四川。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苟国华随军入川滇边,曾任边军左营帮带、车路监工委员。宣统二年(1910)新军后营管带程凤翔奉赵尔丰令进兵桑昂曲宗,南下察隅,招抚民众,调查人口地亩、钱粮赋税,择要施治。于当年十二月奏请清廷将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原梯龚拉改为原梯县、妥坝改为归化州,木牛甲卜改为木牛县,同属昌都府,颁布地方章程,设官施治。⑦宣统三年四月初四日(1911年5月2日),苟国华被委任为察隅县委员,赵尔丰下发的委任令称:“照得桑昂曲宗、杂瑜全境肃清,设治、划界、定赋诸凡待理。查该员堪以委任,特委为察隅委员,前往会商管带程凤翔接收办理。”⑧ 密西米人在我国民族识别中定为僜人,米朱是其一个分支。丁内(Tin-ne),1911年英人贝利从察隅南下萨地亚时曾经过此地,他记述该地在日马以南两天路程,中国树立界牌以北3英里。叶普克(Yepuk)河即汉文文档中的压必曲,为察隅曲支流。察隅曲,在汉文文档中又记为穆曲、绰多穆楚、杂瑜曲等,英文文献中记为洛希特(Lohit)河。压必曲与察隅曲交汇处称为压必曲龚。麦尼克赖(Menilkrai)即汉文中的门巩村,地处压必曲与察隅曲交汇处,中国树界牌处在该村附近,约当东经96度38分,北纬28度。W.H.Wilkingson,汉文译名务谨顺,时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 从以上记载来看,此次察隅巡边立界是辛亥革命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在西南边疆的一次彰显边界、宣示主权的行动。这次行动上承赵尔丰、程凤翔所部在压必曲龚树大清龙帜,立中华帝国边界之界牌,而在革命风暴摧毁旧制,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之初,于原有界牌旁树立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之界牌。建界牌之时为1912年6月9日。囿于笔者见闻,尚未得见此前有标示中华民国疆界的史料。如此说不谬,这当是中华民国标示国界的最早界桩。 二、危城孤军捍卫国土的壮举 然而,仅从上述英人记载,仍有若干问题不清楚。首先,派遣特使赴边建立界牌的背景、缘由如何?民国元年正是古老的中国辞旧迎新,事件频发,变化莫测的历史巨变之时。年初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未几即南北议和,孙中山交权,首都北迁。窃取中央权力的袁世凯对内加紧瓦解革命党、巩固地位,对外以乞求列强承认为要务,无论是临时政府或袁政权都未下达在全国范围内巡察标示边界的命令。达赖十三世鼓动“驱汉”,藏军围攻驻西藏及川滇边军队、官员,四川、云南筹办、组织西征,重在援救被围困军民,收复地方,也没有下令在川滇边和西藏巡察标示边界,为什么出使察隅的特使要会同察隅县地方当局及驻军于生死危急之际突出重围,甘冒风险南下巡边标界呢? 要解决上述问题还须从中国方面的记载探求。兹将笔者查录到的有关史料分述如下: 辛亥革命之际关于英人入侵察隅南界的禀报。《川滇边务档案》共收录了三份苟国华的禀报,一为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月6日)的《苟国华报顾占文据报有洋兵千余人至瓦弄等处》;一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12年1月11日)《苟国华报顾占文探查外人来界情形》;一为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苟国华报顾占文续探查外人来界情形》。此外尚有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川边巡防新军统领详报顾占文英兵突至热巴》。⑨ 上述禀报内容综述:宣统三年十一月间察隅县委员苟国华三度收到有洋人到察隅南界活动的报告:初八日(1911年12月27日)下察隅村长阿登报告,称据来热巴贸易的密西米人说有洋人来到密西米人居住境内;十八日(1912年1月6日)下察隅南界德能村村民报告洋人300余人各带兵器至德能村;同日,又收到热巴夷民报告洋人“约有千余人,已到瓦陇,距绒密两站”。苟国华得报一面行文当地驻军,请派新军前营右哨由鸡贡迅速开驻察隅预防,一面派杨万全赴瓦陇侦探,杨万全二十三日夜间至瓦陇,见河对岸有洋人巡行。访问当地居民,据称洋人来界“约有十日”,“日在界南一带修路,并未前进”。十二月初四日(1912年1月22日)苟国华与新军前营右哨卢哨长会商,派通事杨宗汉与哨兵晏大旂等顺河西岸下行探查。杨宗汉等人行至距瓦陇约50里处“遇外人二,随带背夫五人”,相互交谈,该外人要杨宗汉传告地方官,约于七日在路途相会。杨宗汉返回报告,晏大旂继续前往瓦陇。七日,苟国华与晏大旂应约前往路途中会见,但并未得见这两个洋人。晏大旂八日返回报告:他们到了洋人军营中,并与洋人官长交谈,洋人官长称:“彼等来此亦与吾边军分防各地情形相同,亦无他事也”;晏大旂侦探英营,“隐查人数,约有四百人之谱,均有器械,日在界南一带修路宽五、六尺”。 关于以上禀报中提到的地名德能、绒密、瓦陇等地,可与宣统二年(1910)四月间段鹏瑞受赵尔丰委派考察上下察隅地亩税收情况禀报中的记述相对照。该禀报记录下杂瑜西东两岸一带的村落及税收: 下杂瑜西岸一带项下:松工十户,每年出产两季稞稻。洒马七户,娃弄一户。 以上共十八户,水田八十三块,籽种一百五十三克。旱地二块,籽种二克。男女雇工共一百二十六丁口,牛三十一条,马、羊全无。 下杂瑜东岸一带项下:竹阴五户,作姑一户,常思一户,足音一户,墨溪一户,呷荷三户,浪巴二户,得哩一户,褥妈十户,汤沐四户,热登八户。 以上共三十七户,水田九十三块,籽种二百五十六克四批。旱地九十七块,籽种一百六十克零四批。男女雇工共二百四十一丁口。牛一百三十八条,马三十六匹,羊无。⑩ 其中,娃弄即为苟国华禀报中的瓦陇,即现在我国地图上通记为瓦弄的地方;得哩当为苟国华禀报中的德能,也为贝利所记的丁内;褥妈为绒密。这些地方与段鹏瑞上述禀报中提到的下杂瑜东西两岸各村落一样,在程凤翔进兵桑昂与察隅之前属西藏地方桑昂曲宗管辖收税。程凤翔进兵后赵尔丰报请清廷设立察隅县,委任苟国华为察隅委员,负责该县辖区内行政。 这里要强调的是:苟国华报告的洋人进兵察隅之事并非如与晏大旂交谈的洋人长官所说的“彼等来此亦与吾边军分防各地情形相同,亦无他事也”,而是英国与英属印度为了实施其“战略边界计划”进行的预谋已久的行动。 20世纪头十年,英国与俄国达成协议调整两国在亚洲的利益,缓和两者在亚洲的争夺,准备从亚洲收缩,加紧备战欧洲,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正当此时,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两国民族主义者相互声援;清末张荫棠、联豫在西藏,赵尔丰在川滇边推行新政,激发爱国主义,号召喜马拉雅山南侧诸国联合拒英,在诸山国反响强烈;赵尔丰所部程凤翔进兵察隅,巩固边防,在压必曲龚树龙旗、立中华帝国界牌,南下招抚抚僜人,设立原梯县、归化州。凡此种种,均被英国视为对其在南亚的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威胁,防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辐射英属印度及喜马拉雅山南侧诸国成为英国维护其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主要战略考虑之一。1910年10月23日,行将离任的英属印度总督明托提出“战略边界计划”,企图将英属印度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北移至山脊,建立战略边界,以便防堵中国,封锁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1) 1911-1912年间的冬季,英属印度组织三支远征队,打着讨伐杀死萨地亚助理政治官员威廉森的珞巴人的一支阿波尔的旗号,非法越境,勘测地形,搜集民情,为确定“战略边界”的确切走向做准备。米里人远征队由克尔伍德(G.H.Kerwood)率领,前往苏班西里河(Subansiri,在我国境内称西巴霞曲)及其支流地区;阿波尔远征队在鲍威尔率领下溯底杭河(Dihang,在我国境内称为藏布河)而上,征伐阿波尔人;继威廉森担任萨地亚助理政治官员的邓达斯率领密西米远征队。该远征队又分为两个支队,一个队考察迪邦河(Dibang,在我国境内称为丹龙曲),另一个支队溯洛希特河而上至中国插旗处后西行与另一队会合。总参谋部对远征队下达了关于勘测的原则及具体注意事项。总的原则是: 适宜的军事边界应该遵循主要的分水岭并把布拉马普特拉河、洛希特河及伊洛瓦底江等河流下流的支流囊括在我们一边,从一切角度来看山链是最有利的边界。 (我们)承认其他问题,如,原来属于西藏的边境部落及边境上独立的部落之间的居住分界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与中国间的边界问题,但是军事方面的因素应当置于突出的地位予以考虑。(12) 对于洛希特河流域的考察,总参谋部特别指出: 洛希特河。我们的界标应当置于在麦尼克赖中国树立旗帜的对面。在其附近的考察应尽力与从缅甸—中国边界向北延伸的共同位置连结起来。(13) 邓达斯亲自带领赴洛希特河的远征队。受苟国华令前往侦探的晏大旂曾到英人军营中,“与彼族官长一名都拉蓑,一名琐伏来相谈”。(14)这里所说的“都拉蓑”,即为邓达斯。邓达斯所带的远征队溯洛希特河而上,1911年下旬进入密西米人地区,1912年1月3日到叶普克河。这些情况基本与苟国华所得到的报告相符。 据邓达斯1912年1月14日报告:“两天前,3个藏族(原注:据另外的报告是两个中国士兵,而不是3个藏族)在麦尼克赖以外四分之三英里处,北距原来树立旗帜大约75码处,树立:1.一面绘有四爪龙的旗帜;2.一块木牌,上面用中文和藏文书写,意为:中华帝国川边察隅南界。1910年树立的旗帜还在原处。”(15) 考核此事,苟国华接下察隅村长阿登报告后于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专差雇丁通事杨万全改作蛮装,并派精壮夷民二名协同驰赴瓦陇一带确探情形”,据杨万全返回后报告: 该通事等于二十一日夜约二更时分,行至瓦陇,见河对岸边火光数十处,有洋人约二三十逡巡上下,带有兵器。其人身高面丑,不着中衣,新造草棚三四十间,并有白布帐篷两座,暮夜之间,亦难知其人数。该通事又访居民,称彼族来界,约有十日。(16) 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为公历1912年1月9日,寻访当地居民在第二天,即10日。邓达斯是1月3日到达叶普克河的,距杨万全寻访当地居民七八天,说“约有十日”,合乎常理。杨万全改着蛮装,与当地夷民同往,邓达斯将他们三人当作藏族,也在情理之中。 邓达斯所说的这三名藏族树立龙旗和建中华帝国界牌之事,则应当是苟国华接杨万全报告后,再指令杨万全所为,时间在12日。可惜尚未见到有关汉文文档。按理苟国华必定有向顾占文的禀报,是尚未查出,还是有突发事变,致使苟国华未及写,抑或写了未能送出,或送出而未能送达,均不可得知。在《清末川边档案史料》中,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苟国华禀报顾占文续探外人来界情形的禀报,是苟国华最后一次禀报。从其时西藏及川滇边骤然突变的局势而言,上述诸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仅两天就传到西藏,驻藏川军在会党组织的操控下发动兵变,始而“勤王”,继而“革命”,为抢劫财物擅自发兵攻打色拉寺,引发与西藏地方的内战。川军进藏时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人的唆使与支持下乘机发动“驱汉”运动。1912年初十三世达赖与英属印度总督哈定会见后,派遣其亲信达桑占东潜返西藏策动“驱汉”。驻藏川军攻打色拉寺后,“达赖授权其噶伦”动员“驱汉”,西藏地方政府以十三世达赖名义发布文告煽动:“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7)达桑占东入藏后组织了万余僧俗民兵,自任卫藏民军总司令,疯狂围攻中央驻藏机构与军队。“驱汉”狂潮迅速席卷川滇边,“达赖更密檄康地僧徒,嗾蛮民仇汉”。乡城、定乡、稻坝、贡嘎岭、江卡、乍丫、三坝、南墩、理唐、河口、盐井纷纷陷落,巴唐、昌都被围困。(18)察隅城虽然暂时未被攻破,但已被分割包围,城中文武官兵仅百数十人,在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的率领下苦苦支撑。 从成都出发的特使一行4月1日上路,历尽艰险与危难,到达察隅城当在5月底或6月上旬。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察隅城苟国华、蒋洪喜等人与特使会见,赞同共和,拥戴新生的中华民国,接受特使带来的民国委任,并决定在1月间刚树立的清朝龙旗及中华帝国界牌旁建立中华民国界牌。此时的察隅城孤悬绝境,四面被围,守军以寡敌众,粮弹殆尽,救援无望,生机几绝,用古诗“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特使与守城官兵仍作出了出城巡边建立中华民国界牌的决定,这是何等壮烈的忠诚与奉献,用该诗的最后两句“为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这里的“君”已不是帝制之下的国君,而是推翻千年帝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他们接受民国政府守土防边的委任,抱必死的决心来履行职责,捍卫祖国边疆。 要以言之,民国元年察隅巡边立界是在英国及英属印度推行“战略边界计划”谋划侵占我国门隅、珞瑜、察隅固有领土之时,在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及川滇边“驱汉”狂潮汹涌、察隅被重兵围困随时有城破人亡的危急之中捍卫国土的壮举。 三、壬子百年祭 刘赞廷编纂的《察隅县志略》记述了守城官兵的结局: 惟民国元年,藏番东侵以数千人来犯时,县知事为苟国华,与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誓死守城,蒋洪喜勇敢善战,藏番惧之,愿出五千金请汉官携带老幼由云南假道回川,弗允。被困三月,粮尽弹竭,于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全城文武男女及蒋之老母共一百四十七口,同时投江而死。(19) 文中说的城破之日是阴历,公历为1912年7月5日,此时距在压必曲龚建立民国界牌不足一月。在“驱汉”狂潮中,有不少被围困的驻藏机构和军队接受和议,假道撤离。察隅城的“文武男女及蒋之老母”接受民国守土护边之责,生死相许,毅然拒绝撤离回乡的苟且偷生之路,恪尽职守到最后一刻。他们的死悲壮惨烈,激荡着慷慨赴难殉国的浩然正气。 关于民国元年特使赴边会同察隅官员与守军巡边立界之事,笔者曾在《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及《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一书中简要地论述。(20)之所以没有写专文论述,原因是有一些事情尚未搜寻到确切和足够史料来作出完整和清晰的考证。 查到的关于四川当局派特使赴边情形仅在《民元藏事电稿》有9月18日《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献电遵示暂驻盐井并拟以一军守杂瑜波密等处请核示》及9月23日《国务院电蔡锷所称经营珞瑜波密一节珞瑜已有川员前往波密距滇较远就先探明地势勿得轻进》有极其模糊的记载。(21) 西藏与川滇边出现武装“驱汉”攻击围困驻藏机构与军队的情况后,四川与云南组织西征,但不久两省即在进兵路线及攻防区域发生龃龉。云南方面攻占盐井后拟再西进察隅、珞瑜、波密等地;四川主张藏事由川独任,不同意滇军由盐井西进,并要求云南退出盐井,由四川派员接任。上述蔡锷电报陈述云南方面的意见: 我军遵电暂驻盐井,不与川军逼处,惟滇边接壤之杂瑜、波密等处,既不属藏,亦不属川,紧与怒、俅两处西北相错。承献拟以一军实力经营,以屯以守。现英人修路,已抵亚必曲陇(即压必曲龚——引者),距杂瑜九十里耳,川军能长驱固善,否则以驻波密杂瑜之师一出江达而北,一度楚河而西,不惟形势利便,而近可置藏番之死命,远可戢强英之野心,退可与怒俅打成一片。 后电陈述袁政府不同意上述由云南进兵杂瑜、珞瑜、波密方略,称: 所称以滇军经营珞瑜、波密一节,查珞瑜已有川员前往,设波密系上年驻藏陆军平定之地,且道里距滇较远,应先探明地势番情,勿得轻进。 从蔡锷的电文可知英人进犯察隅的消息已传至内地,川、滇两地西征除援救被围攻的驻藏军民和镇压“驱汉”狂潮之外,还有“戢强英之野心”、守护边防的目的,四川方面派员入藏当然也包含这两重使命。国务院的电文中所说已经派出官员前往珞瑜,表明在派赴察隅特使的同时还向珞瑜派特使,或者两处特使均为一人兼任,先赴察隅再至珞瑜。电文发出的时间为9月23日,距特使出发的时间已近半载,而电文未提到特使赴边及返回的情况,可以料想是未收到特使的信息。那么,赴察隅的特使是在巡边立界后又返回察隅城中,最终与察隅军民共同赴难,还是继续前往珞瑜而不知其所终?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汉文史料,最主要的是没有查找到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所提到的特使出发的报道,对英文史料中所提到的界牌建立者究系何人难以考证。界牌上写的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是否就是务谨顺报告中所说的Chiang Feng-ch'i?如系一人,哪一个的拼写有误?上面提到的英文姓名及特使随员翻译、向导的英文姓名应复原为何种汉文姓名?他们的履历如何?建立界牌后命运如何?这些都未可得知。 2012年是特使赴边会同察隅军政巡边立界牌和察隅军民赴难殉国的百年纪念。上述诸多疑问未有答案,笔者只能草成此篇聊作祭文,并敬录《察隅县志略》中诗句,焚香遥祭察隅县殉国军民及特使一行。诗云: 千里孤军势已危,滇云假道愧谁知。齐东不没田横殇,塞上悠归赵母悲。羌笛吹来壮士血,戍楼人去儒林碑。遗留唯有英雄泪,一瓣心香万古垂。(22) 诗中“戍楼人去儒林碑”是否指特使一行告别被围困的察隅城?也没有确证可考。 文中照录界牌上及务谨顺所写的特使一行人的威妥玛拼写的姓名,但笔者多么希望有一日能恭书他们的汉文姓名而祭拜之。一年多时间又过去了,考证仍无进展,看着这些史料,心中如同揣着一团火,不吐不快。刊布此文,切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共同发掘出新的史料加以考证,使他们的英名得以昭示于天下。 ①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London,Routledge & Kegan,1966,XVⅢ. ②Parshotam 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A Study of the Triangolar Contest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China and Tibet,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part Ⅱ. ③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④参见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计划与赵尔丰、程凤翔对察隅边防的巩固》,《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⑤IOR,Political and Secret Memoranda,I/P & S/18/B.189,Dundas to Assam Government(No.337M,15[th] July 1912).Assam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of India(No.15 P.T.),22[nd] July 1912(P.3323 A/12). ⑥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Proceedings,December 1914,Procs.156-84.see Parshotam 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1974,p.83. ⑦参见四川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5、835—837页。 ⑧四川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928页, ⑨参见四川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133、1135、1136—1137、1137页。 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638页。 (11)关于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计划,参见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IOR,P and EF,1910/13,印度政府外事秘书致阿波尔远征队指挥鲍威尔,1911年9月25日。 (13)IOR,P and EF,1910/13,印度政府外事秘书致阿波尔远征队指挥鲍威尔,1911年9月25日。 (14)《苟国华禀报顾占文续探外人来界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136页。 (15)IOR,L/P & S/18/B,《密西米远征队日记》,1912年1月。 (16)《苟国华禀报顾占文探查外人来界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135页。 (17)参见朱绣编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18)关于辛亥革命后西藏政局及十三世达赖的武装“驱汉”,参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二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刘赞廷:《察隅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参见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周边疆:1911-1947》第一章。 (21)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0页。 (22)刘赞廷:《察隅县志略》,《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二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