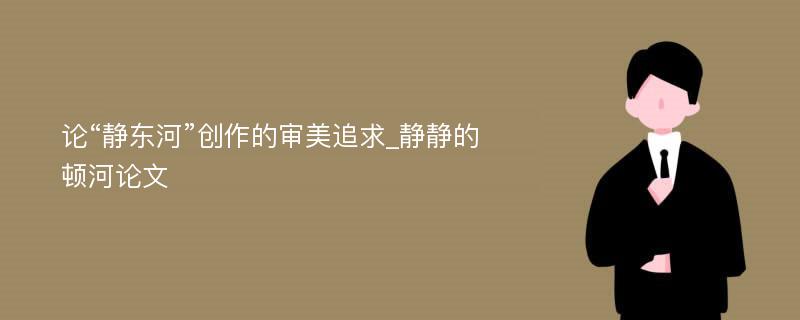
论《静静的顿河》创作的美学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顿河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从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创作中对体裁的要求,题材“反角度”选择及主人公形象塑造中提出的新的审美理想等所表现的创作思想的深化入手,阐述肖洛霍夫这一时期美学追求的新发展及其意义,并论述了这一美学追求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超越性。
关键词:美学追求 反角度 审美意识 价值论
肖洛霍夫是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在苏联作家中,唯有他兼得两种标准迥异的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和斯大林文学奖,他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的一颗文学巨星。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尤其是《静静的顿河》(以下简称《静》)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被视为经典之作而享有盛誉。这清楚地说明,肖洛霍夫的创作确实具有一种“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1〕美学品格, 而《静》的创作更是鲜明地标识出作者不同寻常的美学追求。
肖洛霍夫曾在斯德歌尔摩诺贝尔授奖仪式上明确表示,他的创作是为了“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说出真理”,并坦言:“人的命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命运,未来的人的命运,永远使我不安。”唯其如此,他始终锲而不舍地力求用自己的创作“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并且要“在人类心灵中坚定对于未来的信念”。〔2〕这些剖白明确表达了作家创作的美学追求:求真求善,他把实现这一追求视为艺术家神圣的使命。在《静》的创作中,在表现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时期悲剧的成因时,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肖洛霍夫这一美学追求的力量。
肖洛霍夫创作《静》的年代,正是苏维埃政权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哥萨克及中农群众,是现实摆在苏联政权面前的迫切问题。历史已经为此提供了惨痛的教训。可以说,也正是这种历史过程中的悲剧促成了作家创作思想的深化,因此,在《静》中,作家得以从更复杂更深刻的层次来发掘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成因,以此来寄寓他对于国内革命和战争期间哥萨克悲剧的反思。
在第一卷开篇的一章中,作品叙述了葛利高里的爷爷、老麦列霍夫的一段罗曼史:普罗珂菲不顾众人反对娶了名土耳其女俘,但最终却成了野蛮风俗和愚昧偏见的牺牲品。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麦列霍夫家族酷爱自由、不畏强力的逆反性格,而且为葛利高里悲剧的历史根源作了一番浓墨重彩的渲染。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以强烈的内聚力、一体感及自我意识著称的族际体,17、18世纪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拉辛、布加乔夫等都是哥萨克人。因之,历代沙皇不得不对哥萨克采取镇压和安抚兼施的政策,用土地诱使其就范,使哥萨克成为沙皇的御用军,悲剧性地充当了“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20世纪初,哥萨克又被充作警察和宪兵,成为镇压俄国革命的帮凶。列宁曾经指出“哥萨克是俄国一个保留着特别多中世纪生活、经济和风俗习惯特点的边区的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阶层”,但同时,对于哥萨克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列宁也并未因此作出形而上学的结论,他认为,“大多数贫穷和中等的哥萨克比较倾向民主派, 只有军官和富裕的哥萨克上层才是彻头彻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3〕列宁这番分析的预见性在革命发展中得到证实,而肖洛霍夫《静》的创作,则在苏维埃文学史上,第一次真实体现出哥萨克这一特殊精神面貌,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描写了这个被定性为“俄国帝国主义工具”的特殊群体所经历的悲剧道路。唯其如此,在《静》中,作者不是正面描写哥萨克参加国内战争的经历, 而是描写了“白军对红军的斗争”〔4〕,作品表现形式上这种“反角度”选择,正反映出作家创作意图的不同寻常和他所思考的问题之艰深。
1923年,肖洛霍夫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清楚明了地表达了他对顿河哥萨克叛乱的看法——“现在就暴动问题谈几点意见:一、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二是这种情况被在顿河上游地区的邓尼金特使所利用……我应该反映斗争哥萨克政策和镇压中农哥萨克的错误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5〕在《静》中,作家对这一被扭曲的历史作了真实的艺术再现。作品第三卷第十章描述了1919年元月哥萨克受革命的感召,开放了自己的战线,红军因此一枪未发而进入顿河地区。但是,大约一个月后,托洛茨基违背俄共(布)中央顿河军事委员会及共和国军委员会的承诺(哥萨克中放下武器的人,都保证其安全,任其回乡劳动或参加红军),向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各团建立军事法庭,用大规模的镇压对付曾自动放弃一百俄里战线的哥萨克……这不仅造成了上千万顿河哥萨克的历史悲剧,也导致了苏维埃共和国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给整个苏联的局势造成致命的危险。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历史事实是被缄口不提的,但肖洛霍夫却以惊人的胆识卓见,将它作为中心事件写进了作品中并以此说明顿河暴动的真相,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主人公悲剧命运中不容忽略的政治、历史原因。从这个方面来看,葛利高里的悲剧可以说是国内战争期间哥萨克悲剧历史性的延伸和深化,它给苏联人民提供了沉重的教训,表现了作者对革命与人道主义关系深沉的思考。
从创作主体意识的角度来说,对于顿河暴动历史真相的描写,已不再象作家早期创作《顿河故事》那样表现为自身经验的直接反映。作为一种更高的美学追求,在《静》的创作中,肖洛霍夫更善于隐蔽自我,使作品表现更深刻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作者是通过各类型人物所代表的各种观点展开双方或多方的自由论争,使其充分阐述出各自的合理性。因此,西方评论界将肖洛霍夫称为“具有高度真实感、客观性”的作家。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曾说过:“事实上,作者对他们(指作品中人物)既无同情,也无谴责,他们在作者笔下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这就是这部细腻的,有时是动人心魄的纪实著作最有价值之处。”〔6〕此处, 把作者在创作中是否流露主观倾向当作审美价值取向的标准是否恰当,本文姑且不论,但就《静》整体创作而言,认定肖洛霍夫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既无同情,也无谴责而纯属客观表现的说法,显然有违事实。实际上,作者对于历史事实真实客观的描写,并不意味着其主观倾向的消失,恰恰相反,提出这些历史事实,本身便是作者的介入。它直接体现了作者“求真、求善”的美学追求。
在《静》四部八卷的创作中,头两卷作者侧重强调人物内心冲突对其行为的主观作用,以求探讨主人公悲剧成因中主观方面的因素;而在后两卷,尤其在末卷中,作者强调的是外部环境对于人物悲剧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以期表现主人公悲剧成因中客观方面的因素。而作品中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则是由于作者本人创作过程中受社会环境,时代气氛影响产生的主体意识的变化所导致。在肖洛霍夫创作后两卷的3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所引伸出来的规范、原则、传统和教导遭到骇人听闻的破坏和蹂躏,形成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由此产生了群众性迫害,就是实践领域中的专横,思想领域中教条式的顽执和主观主义。”〔7〕正是这种环境使作者对于革命与人民历史命运关系的思考更趋深沉,因而表现在创作中,对于道德和人性的价值取向便愈来愈具体鲜明,对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形成,也由客观冷静的分析变成明显的同情。所以,在《静》第三、四卷中,造成葛利高里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因素愈来愈成为主要原因而对主人公悲剧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当葛利高里意识到自己再次参加暴动是又一次错误选择时,便力图自拔,主动投奔了红军布琼尼骑兵部队,为赎罪而奋力杀敌,但他并未因此受到谅解和信任,最终还是被遣送回乡。回家后,以妹夫珂晒沃依为代表的村苏维权政权更无宽恕之意。他在得知肃反委员会准备抓捕他的消息后,不得不又一次深夜出逃,并且逃亡中又不幸落入佛明匪徒中。显然,这些悲剧性遭际的描述表明了作者对一些过火政策及非革命人道主义错误行径的抨击,而对主人公的行为则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和惋痛。这里作家强调的不再是主人公因内心矛盾和无所适从所造成的迷误,而是强调了主人公知迷而无路可返的困境。作品中,珂晒沃依的形象深刻标明了作者对造成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的指向和关于革命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在珂晒沃依身上所表现的政治原则的刻板性、严酷性,也将葛利高里身处逆境时仍保持的善良与正义的人性美衬托得非常鲜明突出。在这种对比中,明显流露出作者的道德意识及其由此所产生的严峻的道德判断,从而体现了作家想让人们“变得更好些”这一“求善”的美学追求。
从俄国文学的传统而言,作家的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结合历来是非常紧密的,托尔斯泰的创作便是个典范。苏联文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其间,肖洛霍夫的创作又是突出的一例。不过,在肖洛霍夫早期创作中,道德意识还未在其主体意识中占主要地位,比之表现得更明显的是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到《静》的创作阶段,作家的道德意识愈来愈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在作家笔下未产生象托尔斯泰作品中那种道德自我完善的主体形象系列,但此时作者本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已深深渗透在对人物的爱憎褒贬和人格的评价之中,形成了一种严峻的道德判断。在《静》头两卷中,这种道德判断表现得较为含蓄,它和政治、历史、哲学、审美诸多因素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冷静客观的评述;而在后两卷中,由于作家美学追求中现实意识的强化,使其对人物的道德判断超越了其他因素而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以致成为评价人物的主要价值取向,作品因此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色彩。但是,承认这一现象的存在,丝毫也不意味着作家本人的立场站到哥萨克农民方面,或者更为甚之,已经站到白军方面。事实上,作家这一阶段的创作既有自我的对象化,同时又超越了自我对象:一方面,作家将自己的同情挚爱,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情感倾注于人物身上;另一方面,他又客观地表现了主人公本身的种种局限性,因此,作家是站在比人物更高的立场上来表现人物的命运,评价人物行为的。从整部作品所表现的作家的美学追求而言,肖洛霍夫通过主人公悲剧所否定的并不是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历史行为,也不是革命中无可避免的暴力行动;作家否定的只是在革命过程中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的压抑个性和人的价值实现的历史因素,他满腔同情的并不只是作为中农哥萨克的葛利高里,而是一个诚心实意追求正义之道但却知迷而无路可返的“人”。这种否定和同情来源于因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产生的美学追求之中,它不是作家对信仰的怀疑,而是一种对之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深远意义上的肯定。在《静》的创作中,作家的立场之所以越来越贴近主人公,就是因为作家将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深沉思想传给了他笔下的人物。他将自己关于革命与人道主义,历史进步与人的价值实现等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注入了形象之中。
当然,从审美角度考察,这种过于贴近的表现方式可以说是有得亦有失。在《静》头两卷中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使作家本人与作品中人物保持一定距离,相应产生了一种审美尺度,有利于读者对作品进行审美观照;后两卷中作家与主人公过于贴近的立场使两者间心理距离宛若消失,虽然这样更能激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审美观照的艺术尺度,所以,后两卷作品给人以强烈震撼并不主要来自主人公内在的精神美,崇高感,而是给主人公带来厄运的生活的残酷。这对于肖洛霍夫所欲达到的“表现人的魅力”的目的,不能不有所影响。
然而,《静》在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诚如罗曼·罗兰所言,“在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另一股则蕴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它滋养着新的时代,给他们的人民带来永久的光荣。”〔8〕《静》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不朽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超越,对于作家本人创作的超越,因而实现了作家不同寻常的美学追求。
首先,《静》的创作对肖洛霍夫本人的创作历史是一种全面的超越。作家从早期凭籍主观经验来对于社会、人生作单镜头观察进入到对时代和生活整体作哲学的、历史的、民俗心理的广角度摄取;在体裁上,便出现了长篇的宏伟规模,以此来容纳作家对生活更为复杂深刻的认识;作家所描写的对象,不再是历史进程中单个人或者一个个家庭的变化,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和哥萨克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因此,在内容上也呈现出史诗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静》中主人公悲剧形象的塑造,标识着作家艺术形象创造的突破性跨越,形成了一种具有悲剧史诗性的特点——由人物性格的矛盾来透视时代的矛盾;由人物的矛盾性格体现出作为“历史的生成物”的人物形象与过去、现实、未来的联系;以其超越自身意义的追求来确定人物在民族历史长河以及社会整体中的位置。在《静》中,主人公的追求既是俄国文学中具有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一传统的继续,又是比这种传统的探索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追求,它不仅包含着人民对社会的改造,包孕着民族对自己命运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自身的更新和改造,因此,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哲学意义。这反映出作家的美学追求已经突破了早期创作那种单纯对存在进行客观真实概括的认识论范畴,而进入更为深广的具有哲学概括意义的价值论范畴。作品通过主人公独特的悲剧命运,寄寓了他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深思,并从中揭示人生的价值、人类生存的需求及意义这样一些带有普遍性、抽象性的哲理。正是这种由审美情感抽象而出的哲学价值观点,形成了作品深层的价值论思想,从而使作者的审美情感具有一定的哲学深度,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容量和主人公形象的美学意义。
艺术风格作为审美个性的重要标志,同样也表现出作品这一美学追求的超越性。在肖洛霍夫早期创作中,不论是悲剧性作品还是喜剧性作品,都呈现出单一性;而在《静》中则表现为一种悲喜剧交融的复合色。作品中潘台莱,普罗霍夫这类喜剧性人物的出现,作为悲剧主人公的衬托,既表现出作者对主人公积极的人生观之肯定,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因袭的历史重负的沉痛否定。凡此种种,无不表现了《静》的创作是作家创作历史上一次全面的自我超越。
作为一名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在肖洛霍夫的美学追求之中,不仅有对自我的超越,而且还有着对于历史、现实的时代超越。在俄国文学中,将农民或者哥萨克作为艺术描写对象的不止肖洛霍夫一人。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托尔斯泰的《哥萨克》,都塑造了哥萨克村民动人的文学形象。然而,以如此恢宏的规模和深刻的意念,将哥萨克作为历史的主人,表现其在重大历史时期的生活道路,命运及其心态的,肖洛霍夫却是第一个,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个。他以自己如椽之笔,展示出顿河哥萨克在传统与现实交织的困惑中,怎样带着生活给他们的全部难题走向未来,因此而打破了历来关于哥萨克是“俄国帝国主义御用工具”这种一统天下的观念,为“千百万苏联读者和外国读者带来了时代的伟大发现”〔9〕《静》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更深沉地表现出作家美学追求所具有的极大历史穿透性和某种预见性。葛利高里形象及其悲剧不仅为俄国各阶层、不同时代人们喜爱,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广大读者所接受。因为葛利高里生活的时代,不仅是俄罗斯民族处于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大动乱的岁月。经济危机不断发生,世界大战的爆发,各种固有的矛盾和危机的加剧,人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现实将人们抛入了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曾几何时,“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变得愈来愈渺小,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诚然,这种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一种表现,也不失为作家一种抗议的手段,但这毕竟是消极、悲观的,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文学的主流。所以,为了恢复人在文学中的尊严,为了呼唤人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为了召唤人们以自己的行动确立自身的价值,20世纪世界文坛上出现了积极的文学潮流,这些文学作品提倡以坚毅精神与生活斗争,呼唤人们努力在种种逆境中打开一条出路,在污泥浊水中保持人格独立和尊严……这是一种重新关注人,重新注重人的价值和自由的新的文学,在本世纪对人们的生活已经造成而且还必将造成广泛影响。《静》中主人公葛利高里性格的内涵和特点恰恰体现了世界范围,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极为关注的人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意义,因此,各国的读者,后世的人们,都能从中发现自我,发现生命力量的伟大,并相应产生一种灵魂的震颤与共鸣。这种力量是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是一种永恒的艺术生命力,《静》也因此获得一种不同凡响的超越性,成为不朽的伟大作品。
注释:
〔1〕引自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2页
〔2〕《在斯德歌尔摩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转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469页
〔3〕《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16—17页
〔4〕转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87页
〔5〕〔6〕转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459页
〔7〕[苏]《俄罗斯文学》1965年第2期:赫瓦托夫《葛利高里形象与构思》
〔8〕《法国作家论文学》第33页
〔9〕转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