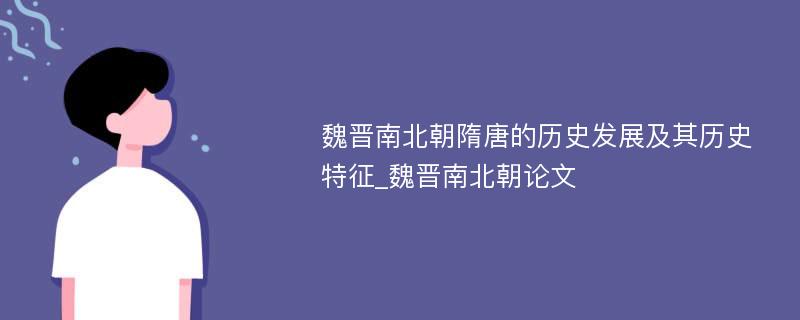
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隋唐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我院历史系为庆贺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七十寿辰,约请校内外作者撰文,拟编辑出版一本《古史论集》;瞿林东和下面孟繁清、孙继民先生的三篇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报征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先行发表出来,以示同贺。
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必首先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发展,才有可能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同历史的联系,进而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的面貌和特点。这是阐述一个时期的史学之各种表现及总的进程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各有自己的根据。本文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这主要是基于门阀地主在这个时期占有统治上的主导地位而确认的。①当然,这两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把它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基础上,也还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待。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齑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②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到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的评价的。他说:
自有晋南徒,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述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③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看法。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北朝的魏、齐、周、隋四朝(魏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实则是六朝,隋出于北朝故列于此)。唐初君臣的这种认识,从政治上看,他们并不认为在分裂时期的一些皇朝都是无所作为的;从民族上看,一方面他们固然还不能摆脱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到各族关系和密切对于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唐初提出了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其后,在承认前人所修《魏书》史学地位的基础上,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反映出对于这些皇朝历史地位的尊重。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新撰的《晋书》,是唐初史家所撰前朝史中对少数民族仍不免歧视而又比较突出的。即便如此,《晋书》对十六国的历史还是重视的,并采用“载纪”这种特殊的体例予以表述,而在具体的评价上亦根据事实有所肯定。如在对石勒的评论中有这样的话:
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睨,戮彭祖于裘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蹑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澈号,拥旧都而抗王室,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④
又如记符坚之事,其中讲到: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
……
坚以境内早,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谦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舞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央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键,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⑤
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于十六国中的后赵和前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随意否定的;即便是对十六国中的其他各个割据皇朝,也不能完全视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移,民族纷争与民族融合,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也促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对此,隋与唐初统治者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既有“君临万国”、“抚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四海又安”、“天下大同”⑥局面。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呼万岁。”⑦在这里,李渊和李世民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胡、越一家”、“四夷入臣”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喜悦和称颂。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民族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新发展,尤有深刻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他十分认真地总结了民族关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史载:
上御举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上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生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之坚,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人,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巽,无代无之,肤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丙一人。自古皆责中华,戮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⑧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是把能够同时做到“平定中夏”、“服戎、狄”看作政治上成功的大事,看作是他超过前人的主要标志。唐人所谓“天下一家”的观念,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也有多民族的含义。
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门阀时代,即门阀地主在统治阶级中占领导地位的时代。门阀地主的形成有不同的来源,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在政治上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它兴起于魏晋,消失于唐末,是这一时期封建统治的特殊形式,有其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戚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⑨郑樵说的“隋唐而上”,当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说的“近古之制”,也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典型而延续至隋唐。五代以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以说,谱学的兴衰同门阀的兴衰是一致的。郑樵从官方、私家的谱系之学与谱系之书的盛衰,中肯地道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时期,吴、蜀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有积极的措施。这不仅为他们的割据称雄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西晋末年,北方动乱,晋室东渡,人口南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宋书·州郡志》记载了“遗民南渡”和侨置郡县的一些情况,勾勒出一幅幅人口南迁的历史画面。人口南迁。不独是门阀士族的南迁,更是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同时也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南传和中原思想文化的更大规模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南方的城市、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则“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货十》记,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而至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其绝大部分出于江南,可见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庚之风扇焉。”《州郡十三》又记荆楚风俗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后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时期南方社会历史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这个时期,中国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更广泛的、更大规模的发展。通往中亚和南亚的商道,到隋朝已发展为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至拂国(今叙利亚)。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过葱岭,至波斯(今伊朗)。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附近),经于阗,过葱岭,到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带)。中道和南道,还更向西延伸。向东的海路联系,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规模最大。三国时,日本曾遣使来中国;南北朝时,它同波斯一样,也曾派人来中国报聘。隋唐时期,日本更是经常不断地派使节来中国,这些使节被称为遣隋使、遣唐使。随同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的,还有许多学问僧和留学生。唐时,日本来中国最大的使团达到500人之多。盛唐时期,中国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其中以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最为频繁。在文化联系方面,各种宗教的传入和发展,是最具时代特点的。其时,外来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分别由波斯和阿拉伯传入。而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激发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热情。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东晋时西行求法的有37人,南朝刘宋时有70多人,北朝时有19人,⑩至唐代仍有发展。东晋的法显(约338-423)和唐初的玄奘(602-664),是西行求法僧中成绩和影响最大的。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西行求法,经十三四年回国,纪述其所经历之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情况和山川风习,成《佛国记》一卷。此书是关于中外海陆交通最早的详细记录。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自长安出发,取道高昌、热海(伊塞克湖),渡阿姆河,经迦毕试(喀布尔附近)而入印度。历尽艰辛。玄奘在印度刻苦学习、参加论辩、从事译书、介绍大唐情况,受到宗教界和政界的礼遇与尊重。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载誉归国,受到唐太宗的召见。此后,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大规模的译场,致力于前所未有的译经工作,译成经论75部,共1335卷,译笔忠实而流畅,远远超过前人。他又与弟子辩机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他所亲历的111国及得之传闻的28国的山川、风习、宗教传说,是关于西南亚及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佛教的发展和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总的趋势是:中国文化雍容大度地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而中国文化也大大扩展了它的辐射面。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显示出极鲜明的特点,玄学的兴起和儒释道的合流,是这一特点一先一后的突出表现。
在这样一个总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着的史学,一方面受着前代史学和史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受着当代社会的启迪、要求和推动,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风貌:
——从私人撰史的兴盛到官方修史的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趋于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大壮观景象。察其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史官制度的不健全,担任修史的人往往任非其才,以致促使私人撰史的发展。《隋书·经籍志二》大序说:“自史官放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以来,其道愈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这很形象地概括了当时官史、私史不同的发展情景。第二,是门阀政治与门阀习气的推动,《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后序援引《周官》古义说:“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义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显然,作者是以此来说明魏晋以来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及其影响下的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于是,“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同书谱系类后序称:“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从“晋世”至南北朝,重家传、尊本望、撰谱系,成为时尚,著者蜂起。第三,是史学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推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至隋,“《汉书》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编年体史书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少学者“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如荀悦《汉纪》,“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即便是《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一类的杂史。“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11)可见,史学自身的影响,是推动这一时期私人撰史之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私人撰史,多有名家,如魏之鱼豢,西晋之王铨,南朝宋之范晔、齐之臧荣绪、梁之吴均,以及北魏之崔鸿,皆声名卓著。这个时期的史官也涌现出一批人才,刘知畿举魏晋时的华峤、陈寿、陆机、束、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时的徐爰、苏宝生、沈约、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他论北朝史官,于北朝提到崔浩、高闾,于北齐、北周则称“若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亦各一时也”。(12)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史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从私人撰史的兴盛到官方修史的发达,中间经过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明确宣布:“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3)隋皇朝表明:官方不仅要垄断修史,而且要垄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使私人撰史成为畏途,史学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第二个转折,是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于禁中,正式成立了修史的专职机构,并在20年中修成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和《晋书》,奠定了官方修史走向发达的基础。唐代历朝皇帝的起居、实录以及贯通的国史,都由史馆撰写出来。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共180卷,刘知畿著史学评论著作《史通》,杜佑著《通典》,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等,这些名作虽出于私人撰述,但都跟史馆或官方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条件有直接关系。今存《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撰成于唐代,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官方修史发达的程度。宋、元、明、清等皇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官修史书方面不断做出了重要的成就,而私人撰史也相应地得到发展。这一转折,在中国史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书种类与数量的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这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各自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从《新唐书·艺文志》序提供的数字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数量的比较中得其大体;《汉书·艺文志》撰成于1世纪末,它以史书附于“《春秋》类”之后,著录西汉时人的历史撰述6种343篇。《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上去班固去世之年(92年),凡564年,其中前120余年是东汉中后期,后60余年是隋与唐初,中间的370年左右是魏晋南北朝。《隋志》史部后序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它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14)它们约占《隋志》所著录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这些史书,除极少数是东汉人及隋朝人所撰,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这种发展更为明显。《新唐书·艺文志》序称:宋代以前,“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15)如以唐代学者所著书平均分配于四部,史部应得7100多卷。这是唐朝开国以后大约100年间的成就。以这个数字的年平均数,同魏晋南北朝370年间史书著述的年平均数相比,则多出一倍左右。这是盛唐时期的情况,中、晚唐时期可能会有些变化,但不会相去太远。这就证明,隋唐时期史书在数量上的发展,又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多了。南朝梁武帝时阮孝绪撰《七录》,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阮孝绪考虑到“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特“分出众史”,立为记传录。记传录包含“众史”又分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史书不仅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必须按其所记内容进行仔细分类,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大致确定了中古时期史书分类的原则和方法。刘知畿著《史通》,以“正史”同“偏记小说”相对待,认为“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他说的“近古”,主要指魏晋南北朝。他把“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概括为10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16)这也足以表明史书种类的增多和史家视野的开阔。
——“正史”地位的突出。《史记》创纪传体通史,《汉书》继承《史书》而断汉为史,从而创立了“正史”。而“正史”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得以不断高扬而显得非常突出。《隋书·经籍志》史部以“正史”为13类之首,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正史”地位的尊崇。其正史类后序说:自《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今依其世代,聚而偏之,以备正史。”它所著录的,自《史记》以下有西汉史、东汉史、三国史、晋史、南朝宋、齐、梁、陈史,北朝北魏史、北周史等以及有关的注释和评论,凡67部、3083卷。这是中国史学上在官修史书中第一次把“正史”的名目用以统称纪传体历代皇朝史,并将其置于史书的显赫地位,这从两个方面加强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一是对于“正史”的反映一代社会历史面貌之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化了,一是对于撰述前朝史之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了。这从唐初李渊的《修六代史诏》、李世民的《修晋书诏》看的十分清楚。自《隋志》以后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的这种地位从来不曾有所改变。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仍然是人们研究、认识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基本依据。
——家史、谱牒和别传:史学的门阀风气及表现形式。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大量涌现出来,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一时期门阀风气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刘知畿在《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谱》、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谓之家史也。”这里,刘知畿指出了家史的性质,它出自“高门华胄”,具有“思显父母”、“贻厥后来”的作用。他举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史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志》以家史入“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今从《隋志》,分而论之。
《隋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史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肃家传》、《太原王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曹毗《曹氏家传》、范汪《范氏家传》、纪友《纪氏家传》、明粲《明氏世录》、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等。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等5种,《隋志》未著录。”(17)这34种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也只存片言只语。然而,南北朝的家传,在作为正史的《宋书》和《魏书》的列传中,在《南史》、《北史》的列传中,还往往可以见其踪影,这几部正史的列传常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当时所流行的家传的形式。家传的发展,延续到唐代。《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的多种家传中,有些是出于各家之手,如令狐德《令狐家传》、张大素《敦煌张氏家传》、颜师古《安兴贵家传》等。
家传是家史的一种形式。家史的另一种形式是家谱,家谱则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当然,谱牒之书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的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这是谱牒同家史的一个区别。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家史多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性的总谱多出于官修。《隋志》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凡34种,是属于魏晋南北朝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仅《世说新语注》引用的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进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撰述之盛。在唐代,谱牒撰述仍保持了一段兴盛时期,自中唐以后开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同门阀的衰落是一致的。《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自《大唐氏族志》以下。唐人所撰谱牒多种,有总谱、皇室谱、家谱等名目,作者更是名家辈出,如柳冲、洛敬淳、韦述、林宝、柳璨、萧颖士、柳芳、柳、刘知畿等皆为世所重。
谱牒撰述之盛推动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一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者谱学的奠基人是东晋贾粥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的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子、孙渊“三氏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南朝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王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刘湛为选曹,乃撰《百家谱》,“以助铨序”。(18)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同时,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15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谱学兴起以后的事了。(19)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之时。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于是,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这次改定是:“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30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20)谱学在唐代,也有它发展的辉煌时期。盛唐时,太宗招修《氏族志》、高宗诏修《姓氏录》、玄宗诏修《氏族系录》,是这一辉煌时期的主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氏族志》的修撰“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仆等级”,贯彻了“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21)《姓氏录》的修撰,更是明确地贯彻了“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的原则,(22)故“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23)《姓族系录》的修撰原则也大抵如此。这时的谱牒已不同于东晋南朝时的谱牒,而是以皇家的权力和声望混士、庶于一书之中的谱牒了。尽管“姓氏之学,最盛于唐”,(24)但正是在它的发展达到辉煌之日,也是它开始转向衰落之时。唐代谱学自玄宗以后,逐步走向式微。中、晚唐之际,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流传至今,人们或可据此去追想唐代谱学辉煌时期的盛况。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发生、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立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25)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之间的联姻,也要相互考察谱牒,以确保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社会现象,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大力推行科举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相当程度的继续。(26)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所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陨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这里说的“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的世风,正是“姓氏之学,莫盛于唐”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牒之学成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这个时期的“品藻人物”的风气的盛行,又促进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按刘知畿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的形式出现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人、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多人合传,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如《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80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前者更多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论行迹。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所著录的情况来看,唐人所撰别传,一方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别传的遗风,一方面也显示出新的特色,如许敬宗撰《文馆词林文人传》、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弈《唐登科记》等,都跟科举制的实行相关联。
——佛教史学的兴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佛教撰述借用了史书的形式和名称表现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史学即佛教史学。《法显传》、《高僧传》、《大唐西域记》、《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续高僧传》等,都是出于佛教僧人之手的名作。如南朝梁时僧人慧皎(497-554)所撰《高僧传》14卷,分为10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记东汉至梁初中外僧人257人,附见200余人。所分10门,也是“类聚区分”之法,为中国史学第一部类传体佛教史籍,“后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27)唐时僧人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30卷(明、清藏本为40卷),仿《高僧传》之体例而略有变通,所分10门是: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全书收录自梁初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160余年间485位僧人,附见者219人。(28)它们不仅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史料,而且也是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佛教史籍,还记载了中西交通的情况和一些域外情况,对于说明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佛教史的撰述,也有出自世俗作者之手的。北魏扬(或作阳、羊)衔之(?-555)所撰《洛阳伽蓝记》5卷,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全书按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个方位。记述了大约半个世纪中洛阳佛寺园林的兴衰之迹,其中涉及到奢华宏丽的佛寺40余座,反映了北魏佛教之盛和僧侣地主生活面貌。书的内容,兼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建筑、苑囿、风俗、人物等,可补正史之缺。
正像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是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样,认识这一时期的佛教史学,是认识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方史、民族史位置的日益提高。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者。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29)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畿《史通·杂述》篇论“郡书”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同篇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风俗。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畿说的“郡书”;其地理类著录诸书,范围要比刘知畿说的“地理书”广泛得多。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12卷,是这时期出现的地方史的代表作。“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此书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到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其卷1至卷4,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卷5至卷9,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42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这几卷,是关于梁、益、宁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用汉、蜀汉、两晋纪年的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10与卷11,是《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300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20人。卷12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401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不见于卷10和卷11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述及本人家世,这或许跟作者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华阳国志》有三个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泰文献。象《华阳国志》这样有丰富内容的地方史,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不多见的。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地方史的撰写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通过三个途径反映出来。一是皇朝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如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陈寿《三国志》等,都有民族史专篇。范晔《后汉书》晚出,综合前人成果,写出了这个时期问世的“正史”中最有份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中的有关专篇相衔接。二是以当时的皇朝史或“国史”的面貌出现,多以反映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史事。《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所著录者,大部属于此种史书,其中以《十六国春秋》为突出代表;此外,如“正史”类所著录的魏收《后魏书》、魏《后魏书》,不仅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历史,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还记述了鲜卑族以外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到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论述上的开扩视野。
隋唐时期的地方史、民族史撰述,在数量上更有所增加。裴矩《西域图记》、许敬宗等《西城国志》、李仁实《戎州记》、李璋《太原事迹记》、张文规《吴兴杂录》、吴从政《襄沔记》、林《闽中记》、袁滋《云南记》等,几乎涉及到东、南、西、北的地方史。民族史撰述方面,感唐与中、晚唐各有高潮和特点。感唐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初史家关于前朝史的官修正史之中。如鲜卑族宇文部统治者建立的北周史《周收》,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统治者先后建立的“十六国”史《晋书·载记》,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撰述。中、晚唐的民族史撰述大致有两个侧面,一是关于中原与“四夷”的关系史,一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其中也涉及到这些地区同中原之关系的历史。前者如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李德裕《异域归忠传》、高少逸《四夷朝贡录》;后者数量多、方面宽,其中以关于云南地区社会历史的撰述最为突出,如韦齐休《云南行记》、李德裕《西南备边录》、窦滂《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达奚洪(或作宏、通)《云南风俗录》、樊绰《蛮书》(一作《云南志》)等。这些书,大多撰于晚唐时期。自南宋以后,这些著作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樊绰的《蛮书》。《蛮书》10卷,其各卷内容依次是:“云南界内途程”,记当时由内地进入云南的交通及其途程;“山川江源”,记云南境内主要山脉河流的名称方位或流向和其他自然条件;“六诏”,记六诏的由来及其与唐的关系;“名类”,记云南境内其他各族概况;“六睑”,记云南各州概况;“云南城镇”记主要城镇的建置、布局、兵防,以及居民、交通、自然形势等:“云南管内物产”,记农时、耕稼方法、手工技艺、特产及其分布;“蛮夷风俗”,记云南各族的服饰、仪容、婚俗、节日、度量、房舍、丧俗、葬式、语言等;“蛮夷条教”(一作“南蛮条教”),记南诏的政治、军事制度;“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与南诏毗邻的地区之概况。这是一部包含云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内容丰富的民族史著作,而书中关于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史的叙述则占有突出的位置。
诚然,这里所说的地方史、民族史、它们在内容上有时是交叉的,如《华阳国志》中包含了西南民族史的丰富内容,它的卷1至卷4,不但记载了30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与分布,而且对其中重要者如巴、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传说、历史、风俗及同内地皇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记述,有许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不曾见到的。同样,在《蛮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地方史内容,民族与地域的关系本十分复杂,我们自亦不可作简单的看待。
——创新意识与批评意识的增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封建皇朝的历史意识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也在进一步提高,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学家的创新意识的增强,一个方面是史学家的批评意识的增强。在创新意识方面,如陈寿撰《三国志》,以一书叙三国史事而特别显示出来的总揽全局的史识;袁宏撰《后汉纪》,创“言行趣舍,各以类书”之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范晔撰《后汉书》,特重史论,刻意于此有所创造并取得了成功;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之方法,以“务在周悉”为宗旨,走出了一条注史新路。《五代史志》(即《隋书志》)汇南北于一体,综五朝为一书,总括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的典章制度;《晋书》承前人所创而灵活运用,予以发展,以“载记”记“十六国”史,写出了完全意义上的两晋时期的历史;李延寿继承父志,贯通南朝史与北朝史,撰《南史》、《北史》,使各自成编而史事互见,删南北相互诋毁之词以张一统之格局,是继《三国志》后历史编篡上的又一杰作;中唐史家佑以明确的经世目的、严密的逻辑思想,博采五经群史,前人论议,通叙历代典制,撰成巨著《通典》,创立了典制体通史,开拓了历史编纂领域等等,都是在创新意识趋动下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在批评意识方面,西晋张辅论马、班之忧劣。从史文烦简、述事原则、价值标准、“造创”与“因循”等几个方面,以比较的方法,评论了《史记》、《汉书》,开这一时期史学批评之先河;南朝梁人刘勰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视史著为一文体而加以评论,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涉及到自先秦至东晋的史学发展的历史、史学功能、信史原则等,论述之中,于人于书,多有批评。张、刘都不是史学家,但他们的史学批评思想对启迪这一时期史学批评意识有重要的作用。其后,北周史官柳虬论述史学功能与直笔形式的关系,抨击了史官“密为记注”的记事方法;《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及各类后序,对史官的职责与要求,史学功能,以及各类史书的源流与得失,多有评论,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史学批评家刘知畿承史学发展的丰富成果,受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的启迪,面对“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的状况,乃“商榷史篇”,“辨其撮归,殚其体统”,撰成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提高到更加自觉的和更富有理性的阶段。中、晚唐之际,李翱提出历史评价应“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的命题;皇甫对“良史”提出理论性认识,认为“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柳宗元指出,史官的职责是“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批评人们对史官职守的不正确认识。这三人,虽非一般史家,但都跟史学有许多联系,他们的这些认识在中、晚史学批评上占有引人注意的位置。所有这些史学批评上的成就,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方面的进展,是中国古代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注释:
①参见白寿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16-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拙文《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见《稽古录》卷13“臣光曰”。
③《唐大诏令集》卷81。
④《晋书》卷107《石季龙载纪下》后论。
⑤《晋书》卷113《苻坚载纪上》。
⑥以上均系隋文帝语,见《全隋文》卷1。
⑦《资治通鉴》卷194。
⑧《资治通鉴》卷198。
⑨《通志·氏族略》序。
⑩参见《中华文明史》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88页。
(11)以上分见《隋书·经籍志二》正史、古史、杂史各篇后序。
(12)《史通·史官建置》。
(13)《隋书》卷69《王劭传》。
(14)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在著录803部,附亡书64部,合计867部。其所著录四部书存亡合计4757种,49467卷,此数不包括道经、佛经之数。
(15)《唐会要》卷36《修撰》条载:开元九年(727),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200卷,其所著录2655部,48169卷。此数与《新唐书》所说有出入。
(16)参见《史通·杂述》。
(17)参见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
(18)《南史》卷59《王僧孺传》。
(19)参见《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20)《南史》卷59《王僧孺传》。
(21)《旧唐书》卷65《高土廉传》。
(22)《新唐书》卷223上《李义府传》。
(23)《新唐书》卷95《高俭传》。
(24)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序。
(25)《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26)详见拙作《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载拙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27)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24页。
(28)参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29-30页。
(29)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21页。
标签:魏晋南北朝论文; 隋书·经籍志论文; 南北朝论文; 门阀士族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隋唐论文; 唐朝论文; 门阀制度论文; 汉朝论文; 春秋论文; 宋朝论文; 史记论文; 汉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