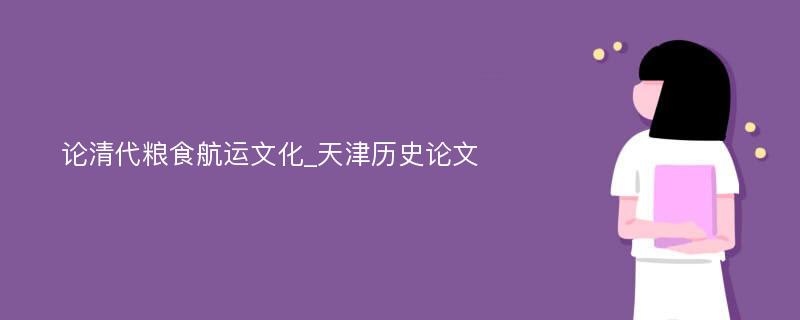
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海运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化”,按照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的说法,即“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定义至今仍然受到广泛认同,并成为人们判断文化的重要标尺。清代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出现于道光六年(1826)和二十八年(1848),自咸丰以后,海运成为漕运的主体,一直持续了60余年。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祭海神、组建船商会馆和创作大量海运类诗歌的局面,使得漕粮海运文化蔚然兴起。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正于方家②。
一 祭祀活动兴盛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天后、风神和海神关系海运安危,故祭祀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其中尤以人们对天后的祭礼为重要。清初,政府对加封天后之事即颇为关注。康熙十九年(1680)、乾隆二年(1737)、二十二年、五十三年及嘉庆五年(1800),清廷曾先后对天后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孚显”、“神赞顺垂”之神的名号,以示推崇③。
道光六年(1826),清廷首次推行漕粮海运,祭祀活动立即被提上工作日程。二月初一日,是海运船只初次放洋的时间,江苏巡抚陶澍随即赶到宝山县漕运船只的出海口处,祭风神、海神,并前往上海县黄浦江岸的天后庙敬香,以祈求海运平安④。此次海运分为两批进行,在第二批漕粮交兑结束后,陶澍又上疏道光帝,奏请加封海神。他声称,第一次海运船只行经黑水大洋时,迭遇风暴,“危急时若有神助,并未损失一人。即有遭风断桅,各船米石毫无漂失,利漕安澜”。六月十七日,道光帝降谕:“览奏实深钦感,著发去大藏香十柱,交陶澍祗领遣员诣各处神庙,敬谨祀谢……并发去御书匾额,交该抚敬谨悬挂,以答神庥。”⑤道光帝还为天后加封号“安澜利运”。通过君臣的互动,以强化神灵保佑漕粮海运的印象。
到了二十八年,清代实施第二次漕粮海运,与道光六年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对海运善后事宜的处理仍然是从加封海神开始。根据江苏当局的奏请,礼部对加封之事进行了议复,议复称:江苏巡抚陆建瀛于督办之初,即叩祷天后、风神、海神,结果仍然利漕安澜,“并无一船松舱伐桅之事”。参考原来的规矩,他们决定此次加封天后为“恬波宣惠”,风神为“宣德赞化”,海神为“灵昭镇静”⑥。此后,随着历次漕粮海运的进行,天后又迭受加封,甚至其左右护法也得赏赐,敕封金将军、柳将军,以致最后礼部都不得不表示,必须要对封号进行限制,否则,“转不足以昭郑重”⑦。
如果考察漕粮海运的经历,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所谓“利漕安澜”、“并无一船松舱伐桅”皆为自欺欺人之语⑧。即便如此,清廷仍然对这种自我麻痹的活动乐此不疲。咸丰二年(1852),山东巡抚李僡奏称,登州镇总兵武迎吉护漕粮海运沙船驶入东洋时,将近石岛地方,“忽大雾弥漫,茫无涯岸,望空祷祝,立时风恬日朗,此外遇有风涛之处,无不化险为平”⑨。情况更是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对于这种宣扬神力的机会,咸丰帝当然不会错过,他当即为登州海口天后、风神和海神庙发去大藏香十柱,并逐一加封号:天后加封“导流衍庆”,风神加封“扬仁佐治”,海神加封“助顺安澜”⑩。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清代的漕粮海运一度中断。随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逐步收复江浙地区,漕粮海运得到恢复,与此相伴随,祭祀、加封的活动也尾随而至。同治十年(1871)清廷又出现了加封天后等神的活动。署江苏巡抚恩锡奏称,本年的漕粮海运,“风恬浪静”,“所装米石颗粒无损”,全赖诸神保佑。最后经礼部议复,天后加封“嘉佑”,风神加封“昭应”,海神加封“恬波”(11)。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天后还因“护漕有功”,受颁匾额“泽被东瀛”(12)。可见这种活动的持续性。
除了天后、风神类似全局性的神灵受到祭礼,一些地方性的神灵也逐步受到重视。上海系沙船出港之地,伴随着漕粮海运而举行的祭神活动,显得最为丰富。上海当地的海神庙曾屡次因漕运平安而受封,除“灵昭镇静”、“助顺安澜”和“显威济运”等封号外,每次祭祀还会配有祝文,写得宏大壮观:“惟神德秉重,乾功宣习,坎神化常,符乎六位,精灵分著于五方。允襄水土之平,经流循轨;广济云雷之用,膏雨应时。维斯财赋之雄藩,端赖阴阳之顺序。敢志昭报,庶竭愚忧,谨布几筵,肃陈牲币。”(13)上海城隍庙也颇受重视。如同治十一年(1872),署江苏巡抚恩锡奏请加封天后等神之时,还同时请加封上海城隍庙。虽因礼部曾有咨文,“请加城隍封号,只称某省府州县,城隍之神不准称公侯伯爵字样”(14),但朝廷最终还是同意,对城隍破格加封“灵佑”称号(15)。
晚清的漕粮海运由江苏和浙江共同举行。浙江自实施漕粮海运以来,便与江苏携手进行祭神活动。比如在最开始实施海运的咸丰三年(1853),浙江海运总局的官员即与江苏官员于二月初一日共同“恭祀海神”。虽然浙江巡抚黄宗汉无法赶往上海,他仍特意“发祭帛”,交由海运委员仲孙攀等人代祭(16)。在以后的海运过程中,这种联手的祭祀活动得到了持续,如到了同治五年(1866),沙船放洋前,浙江照例领祝帛以祀海神,巡抚马新贻也从浙江为上海省局“发来印帛三端”(17)。二月十一日,两省委员共同祭祀,“撰拟祝文,同宪发祝帛,虔备牲牢,恭诣各庙斋沐行礼”(18)。
祭祀活动虽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举行,但经过长时间的大力鼓吹与推行,时人对于神灵的虔诚和崇拜心理无疑会得到加强,这也充分显示出,漕粮海运这种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保持着一种持续而良好的互动关系。
二船商会馆及相关建筑蔚起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器物”层面的建筑,既是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与漕粮海运相关的建筑而言,既包括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庙宇,又包括与商人组织相关的会馆。
上海的天后宫建立得很早。康熙五十四年(1715),上海沙船众商即建天后宫,至光绪年间未改,“有司岁祀于此”(19)。天后宫设立于小东门外,这里酬神演剧,几乎无日不有,有诗证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20)除此之外,上海还有和海运相关的海神庙、风神庙建筑,并且也因漕粮海运而地位突出。如海神庙,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海防同知刘元楷等人重建于薛家浜海运局旁,而原来位于老白渡的海神庙,则在光绪七年海运局迁址后,仍然“庙制如旧”(21)。
上海还有一处“愍忠祠”,于光绪六年就原来之万福宫后楹改建,系祭祀光绪元年(1875)漕粮海运时,在“福星”号轮船中失事而溺毙的海运委员(22)。本次海难发生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对受害各员“优恤建祠”(23),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吴元炳和浙江巡抚杨昌濬等人也加以声援(24),得到吏部的同意,决定在天津和上海各建一处“愍忠祠”(25)。天津专祠很快就修建起来。据江苏粮道英朴报告,他在天津东门外小闸口下风神庙南首购买民间基地,兴建“愍忠祠”,于光绪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安设主位,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率属躬亲致祭”(26)。李鸿章还专门就此事进行了奏闻(27)。上海专祠则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初因城内人烟稠密,无地可买,直到四年,西门内万福宫房屋(又名茅山殿),“假神诱惑,男女混杂”,被上海县县令莫祥芝没收,才得以改建,“去邪崇正”(28)。所有工程于七月二十二日完工(29)。八月十七日,苏松太道刘瑞芬前往致祭(30)。护理江苏巡抚谭钧培也将其事一并奏闻(31)。
作为海运的终结地,天津与海运相关的建筑也相当多。元代海运以直沽为终点,延祐三年(1316),大直沽建天妃灵慈宫。泰定三年(1326),小直沽又建另一处天妃宫。明清两代在丁字口、芦北口、咸水沽等地,亦修建天妃宫16处。康熙三年,晋封天妃为“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天妃宫因此而改名“天后宫”。
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为虔”。海运之人到天津后,多数要到天后宫进香。即如天津东门外之天后宫,“金碧辉煌,楼台掩映,即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庙前一带即以宫南宫北呼之”。此处向例于三月十五日启门,善男信女络绎而来,“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为赴庙烧香,许多人不远数百里而来,“所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俱写天后进香字样,红颜白鬓,迷漫于途,数日之内,庙旁各铺店所卖货物亦利市三倍云”。难怪有人写诗赞曰:“三月村庄农事忙,忙中一事理难忘。携儿偕伴舟车载,好向娘娘庙进香。”又有人称:“我闻圣母奠海疆,载在礼典铭旗常。初封天妃嗣称后,自明迄今恒降康。津门近海鱼盐利,商舶粮艘应时至,维时拯济免沦胥。”(32)
为海运而建的天后宫,地势宏敞,为津市适中之地,在天津的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天津商会决定在天后宫举办商业劝工会,“自系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劝工会每年三月、十二月在天后宫办会,会期以一月为限,各种物品均准陈列,“任人游览,彼此互相贸易”(33)。由于这种重要性,使得到后来有好事者想禁止天后宫活动时,便立即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与天后宫相关的铺户200余家,联手上诉:天后宫历年进香,“于商等不无小补”;每届劝工会,更是广开销路,“是此宫南北全街铺户依为屏幛,否则货物滞塞,何堪设想”(34)!此议当即做罢。
如果说寺院庙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与海运相关的宗教场所而存在的话,那么作为承担晚清漕粮海运的主体——沙船商人,他们所建立的会馆,则更多地显现出一种的行业特色。
清代上海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海运事业相关,这就使得与海运相关的各种会馆、寺院等建筑蔚然兴起。最迟在康熙五十四年,上海就出现了沙船业的会馆“商船会馆”。到乾嘉时期,会馆更多,如乾隆十九年(1754)徽州宁国人在上海斜桥南堍建立的徽宁会馆;二十二年福建泉州、漳州人在咸瓜街建立的泉漳会馆;四十八年广东潮州人在洋行街建立的潮州会馆。
漕粮海运兴起后,类似的会馆更见繁兴,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沙船出口时须取泥压载,“泥夫每多竞争,遴夫头以资督率”,会馆之事则延请董事主持,办事处称商船公局。在商船公馆之左,又附设有“办理水手伤亡之承善堂”。更令人叫绝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们还复附设商船小学校。
浙江人也在上海建有自己的会馆。浙江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浙江宁波人在荷花头修建,后被毁坏。咸丰五年(1855)时,因浙江商人承运漕粮海运,“无议事所”,积资重建,并改名“浙宁会馆”。光绪七年(1881)时,又以历年所积捐款增置基地,重建大殿、戏台、看楼,阅三载告成(35)。
除此之外,上海还建有为漕粮海运服务的海运总局。江浙两省均分别在上海建屋修房,设立自己的办公处所。比如浙江自兴办海运以来,即于上海设立浙江海运沪局。考虑到赁借民居“非久计”,咸丰七年(1857),海运委员王庆勋等人在上海捐建局房一所,共计面积四亩九分九厘一毫。兴工筑造后,共得房屋大小共四十余间,所需经费由海运商船及各州县摊捐(36)。
与上海类似,天津也设有江苏和浙江省的漕粮海运局所。浙江粮道行馆和浙江海运公局均设于东门外南斜街,江苏粮道行馆和江苏海运公局则设于城东南闸口。为方便在天津处理有关事宜,长期进行漕粮海运的沙船主们,还在同治十年(1871)四月,在天津小闸口西大街南石院,花银1000两,购得民房一处,建立“江浙沙船公所”,并派专人看管,生活津贴由船捐利息提供(37)。
正是随着庙宇与会馆的纷纷落成与日益发挥作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与政治行为的漕粮海运,其文化蕴涵才得到了更好的传播。
三 诗词歌赋叠出
清代共进行了61次的大规模漕粮海运,前后延续80余年(38),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由文官所主导的经济活动,在文学方面,结果是两本诗集的撰成,以及无数篇章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烟开岛豁黄龙远,潮满神停白马看。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39)道光六年海运之初,陶澍与该省海运官员齐登吴淞口炮台,纷纷作诗唱咏,以兹纪念。如贺长龄作诗:“宵旰畴咨诏屡宣,抚时能不念艰鲜。竟开创局重溟远,赖有中朝一德贤,敢以度支烦国帑,未须营造等官船。海滨快睹千樯集,朝北高帆尽似仙。”(40)他在诗中指出,海运系由道光钦定,陶澍不避艰辛,而英和则为创议人,因当时流传谚语“夏至南风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故他的诗名中出现了“朝北高帆尽似仙”的句子,颇有写实之意。
负责此次漕粮海运之押尾工作的京口协副将汤攀龙也写诗:“海出重洋拥翠澜,观澜原合大臣观。片帆似较千夫易,一念能回往岁难。金简公先迎日春,银涛我拟借风看。春明二月来时路,万口争传策治安。”(41)林则徐更是为此次海运一口气写出四首诗。比如第一首,“手障东溟奠紫澜,万樯红粟拥奇观。直从佘滧开洋驶,不似膠莱辟路难。辽海云帆诗意在,吴淞翦水画图看。旌悬五色天风送,破浪居然衽席安”。最后一首则表示,自己虽然无力参预海运,但仍然对此事关心有加:“媤未瀛壖橐笔从,养疴曾荷主恩容。遥闻令肃防中饱,更悯民劳缓正供。食货成书垂国史,积储大计仗儒宗。八州作督浑闲事,重是循墙矢益恭。”(42)事后,由陶澍主持,对此次海运所得诗篇进行编辑,汇成一书,是为《海运诗编》,成为清代漕粮海运的第一部歌咏诗汇。
咸丰四年,又有钱炘和之《海运纪事诗钞》一书的出现。据其自序云:海运运行已经有数年,如他本人即亲办五次,尤其本年海运,“以烽烟未靖,南北戒严,方虑水邮多梗,迺估帆云集,顺轨如常”,于是他加以搜集整理,得以成册。在书中,他记录了曾参加过道光六年海运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诗篇:“宸谟不是法元明,航海吴粳达帝京。道租秋防臣力瘁,筹深旰食圣心诚。”(43)又比如收录粮道王友端的诗:“漕法超元更轶明,旁门也许达神京。”(44)对漕粮海运大加赞扬。
非常明显,作为一种由官员主导又公开出版的诗集,阿谀奉承是其主色调,要寻找漕粮海运的真实声音,恐怕还得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据参加了道光六年海运的船商施彦士回忆,他于二月初十放洋,刚驶出即遇风驶回,经修理后再发。二十六日,因遇风漂至朝鲜国万倾县西南群山岛,回棹近石岛后又遇风,漂至沙头山,至三月初九日始抵芝罘岛。对于这一段经历,他写道:“初放佘山洋,大臣躬祭告。牡牢沈海水,不才不自量。率先挂帆驶,初遭风打头。继损桅中止,一身何足言!”(45)可见漕粮海运的危险性,并不如政客笔墨中所言,“如履平地”。
作为一种牵涉到各方利益的经济活动,漕粮海运必然会招致不同的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这些都在散落于各处的文人诗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高凌雯所辑《天津诗人小集》中录有梅存栋的两首歌咏漕粮海运的诗作,第一首称赞道光六年之海运:“一线平流万里开,熙朝真有济川才。何愁输挽艰渠运,喜有艨艟越海来。神力暗凭吊岛屿,仙风徐引到蓬莱。津沽夜雨桃花涨,取次云帆片片回。”认为此次海运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第二首诗则云:“勇断吁谟出对明,重臣翊赞力非轻。天储一夕真飞至,海路千年此创成。十滧浪高浮画舫,万帆春暖送香粳。东南顿觉舒民力,况见黄流指日清。”(46)则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漕粮海运的美好祝愿,殷殷之情,呼之欲出。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筹建及其大规模地参加到晚清的漕粮海运过程中来,这种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作的优点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载客载货,南北往来,以便商民贩运,并可装粮载兵,裕国便民,两有裨益”,所以有人特意赋诗:“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多少官商来往便,快如飞鸟过云天。”(47)但另一方面,由于轮船的逐步主导漕粮运输,针对轮船抢夺沙船生计的现象,有诗人则表达了强烈的抵制情绪:“北道何以贫,云自轮船起。一从市舶开,舍此争趋彼。大道少人行,小民失生理。赫寇如旱灾,亦地数千里。轮船夺利多,一线灾如水。剜肉莫医疮,去角徒予齿。感此重欷歔,不敢言铁轨。”(48)由轮船而及之于铁路,不论其观点的正确与否,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一首诗的确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对于和漕粮海运相关的各种历史事件,也在诗中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同治初年减漕运动兴起后,有人特写诗记事:“鄂城三次失,小民罹锋斧。文忠减漕粮,民气忠义作。”(49)认为减漕运动为争夺民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有人做诗纪念称:“折漕昉自石渠编,锄莠吾思骑尉贤。忠魂沈泉遗恨在,搬仓群鼠殄何年。”作者自注,《石渠余记》作者王庆云即主张折色,而“京仓弊尤深,窟穴其中,有仓老鼠之目,亦曰仓匪。王湘岑为京师左营游击,所辖京通一带,皆仓储所在,缉治仓匪最严,匪甚恨之。拳事起,习拳者皆此辈,故湘岑遇祸最惨,事后觅遗骸不得,以衣冠葬”(50)。反映出义和团运动对漕运的另一种影响。
晚清漕粮改折诏是中国漕运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次改折活动中途而废,效果大打折扣(51)。关于其中的周折,有人作诗曰:“除蠹重教议折漕,芝轩主计独贤劳。道谋至竟多牵掣,闻道长安米价高。”(52)真实反映了晚清漕运改折诏发布的艰辛及漕粮废而不止的内在原因。
诗以言志,笔者以为,出于各自立场、各自目的而涌现出的大量诗歌,既展示了清代漕粮海运的多姿多彩与波澜壮阔,又表现出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性,通过对相关诗文的解读,对于展开对清代漕粮海运全方位的研究,自然会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通过60余年的实践,漕粮海运已经逐渐形成了以祭海神、修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一道风景线。笔者以为,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当然,这一文化现象的独特魅力,还很有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必要。
注释:
①[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页12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②学术界关于清代漕粮海运的研究均集中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关于文化方面的研究显得极为薄弱,具体情况请参见拙作:《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③《礼部奏议复海运得邀神佑请加封号》,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一《奏章文移》,光绪十年刊本。
④此日,陶澍作《丙戌二月一日海运初发偕同事诸君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作》以兹纪念,见陶澍:《陶澍集(下)》页563,岳麓书社,1998年。
⑤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整理:《道光起居注》道光六年六月十七日,国学文献馆出版社,1985年。
⑥《礼部奏议复海运得邀神佑请加封号》,《重订江苏海运全案原编》卷一《奏章文移》。
⑦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一二《祠祀·秩祀》,民国七年刻本(1918)。
⑧参见拙文:《道光初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⑨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整理:《咸丰起居注》,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学文献馆出版社,1983年。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署江苏巡抚恩锡折。
(11)《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折。
(12)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13)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一二《祠祀·秩祀》。
(14)《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署江苏巡抚恩锡折。
(15)《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折。
(16)仲孙攀等:《沪局禀恭祀海神日期》,黄宗汉等纂:《浙江海运漕粮全案初编》卷四《沪局事宜》,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咸丰三年刻本。
(17)《省局详送祝帛请盖印饬发》,马新贻等纂:《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新编》卷五《沪局事宜》,同治六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8)《省局转沪局恭报海神日期》,《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新编》卷五《沪局事宜》。
(19)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20)贵芳:《宝山、沙船和商船会馆——记明清两代上海海运业的盛况》,《解放日报》1956年8月4日。
(21)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一二《祠祀·秩祀》。
(22)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一二《祠祀·秩祀》。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2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25)《吏部奏轮船在洋失事淹毙员董议请再加衔袭职》,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六《恩恤事宜》,光绪十年刊本。
(26)英朴:《苏粮道咨津郡捐建在洋遇难员董专祠》,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六《恩恤事宜》。
(2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五月十四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28)莫祥芝:《上海县禀在洋遇难员董奏准建立专祠禀请委勘兴工》,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六《恩恤事宜》。
(29)周相辅等:《周相辅等禀改建愍忠祠房屋工料一切经费实支清册》,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六《恩恤事宜》。
(30)刘瑞芬:《苏松太道详上海建造海运殉难员董专祠告成请奏咨立案》,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六《恩恤事宜》。
(31)《军机处录副奏折·洋务运动·招商局》,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江苏巡抚谭钧培折。
(32)张寿:《津门杂记》卷中《天后宫》及附诗,光绪十年刻本。
(33)津商会二类1043号卷,《天后宫商业劝工会开办经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页80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34)津商会三类1921号卷,《天后宫南北大街200余户铺商恳请切勿关闭天后宫以保护商业文》,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页1087。
(35)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36)《浙抚咨明苏省上海建造浙江海运沪局官房并地基钱粮由省局解完》,《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新编》卷五《沪局事宜》。
(37)津商会三类292号卷,《商船公所原契底一纸》,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三,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页1105-1106。此公所后归入日本租界,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时,曾引起纠纷,据公所之人曾铸与朱佩珍上控,夏寅斋之子夏惟善于其父去世后,仍借住其中,“并有图售情事”,所以要求其迅速迁出。结果据查,夏寅斋并未故去,其子也并未在身边,而原有船捐被原董事王介眉独占,故津贴全无,而该公所因日本租界开马路,两次被拆去房屋二十余间,而未拆之屋也是行将倒闭,故他反而要求上海商会查明原有船捐是否还有存款,以便接济自己。双方之词均参见津商会三类292号卷,见该书页1104-1108。
(38)清代漕粮海运首次始于道光六年(1826),结束于宣统三年(1911),共计举行61次,前后长达86年,参见拙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页503-513。
(39)此日陶澍作《丙戌二月一日海运初发偕同事诸君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作》,以兹纪念,见陶澍:《陶澍集(下)·序》,页563。
(40)贺长龄:《附和作》,陶澍编:《海运诗编》,道光六年刻本。
(41)汤攀龙:《附和作》,陶澍编:《海运诗编》。
(42)林则徐:《附和作》,陶澍编:《海运诗编》。
(43)穆彰阿:《海运纪事》,钱炘和:《海运纪事诗钞》,咸丰四年刻本。
(44)王友端:《天颜入觐告成功》,钱炘和:《海运纪事诗钞》,作者还自注云:“漕政漕海运为旁门”。
(45)施彦士:《海运纪行诗》,《海运刍言》,崇明施氏求已堂,道光十三年刊本。
(46)梅(存栋)树:《海运》,《欲起竹间楼存稿》,见高凌雯:《天津诗人小集》第8册。
(47)张寿:《津门杂记》卷中《轮船招商局》。
(48)易顺鼎:《自沆上至江上杂诗十五首》,光绪十八年作,见汤瑞琳:《清季诗史初稿》页172,燕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士论文,1940年5月。
(49)刘人骏:《阅申报有感》,前揭汤瑞琳:《清李诗文初稿》页174-175
(50)郭刚沄:《庚子诗鉴》第七,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4月。
(51)参见拙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页352-359。
(52)郭刚沄:《庚子诗鉴》第七。另作者在此诗之后注云,江浙仍运本色百万石,张之洞询问时得旨,起运本色系暂时办法,以后仍全数改折,但不得行,“去弊之难如此”。
标签:天津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海运论文; 天津天后宫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道光论文; 光绪论文; 同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