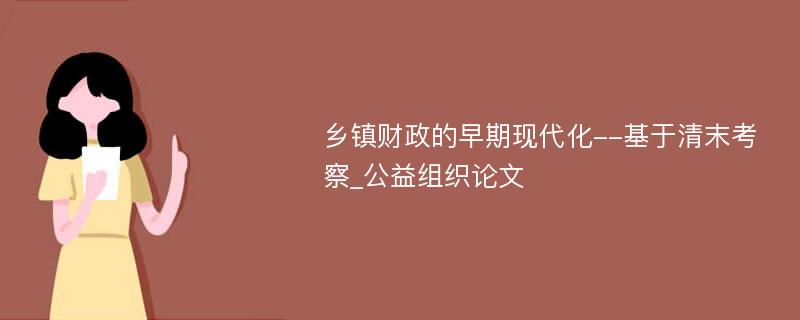
乡镇财政的早期近代化:立足于清末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立足于论文,乡镇财政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末年的中国在经济结构展开近代性变迁的同时,政治结构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型。①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在地方层级上,国家政权止于县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改变,县以下不再是传统王权与地方绅权的交接点。从清末地方自治开始,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县政权开始建立了深入基层社会的权力触角,如区、乡(镇)、街坊、村里、保甲等各种名目的基层组织。随着政权重心的下移,财权也应相应下移。只有这样的良性互动,才能保证政治权力结构的平稳转移。清末风起云涌的地方自治运动导致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也成为财政分权、建立乡镇财政的重要历史契机。正是伴随着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中国乡镇②近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也开始产生和发展。虽然清朝末年乡镇财政近代化仅开端绪,但其运行模式对民国乡镇财政的近代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面临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乡镇财政改革的难点。
一、清末乡镇治理的近代转型
财政作为公共资金的提供者,它与政府的运作方式如影随形,清末近代财政在县以下的出现与清末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大国,但中国古代的这种集权的政治核心不是无所不能、无限制性的政治核心。因为在古代社会交通、通讯及农业社会税收有限等“硬约束”下,少数政府官员很难将自身力量延伸到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外,中央政权和各级官府权力在社会底层往往鞭长莫及。“政治核心”的限制性,使中国古代政府长期依靠民间的力量来管理乡村,运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节约乡村治理成本。国家政权只及于县一级,县以下没有国家的行政机构和正式官员。乡绅因人格和财产方面的优势,承担了县以下的公务职能,成为乡间权威的支配者,政府也是通过绅权将政令执行于民间。
除了受政府委托的乡绅承担公共职能外,中国基层社会很早还形成了一些自治性组织,也承担乡村社会的公共职能,如《周礼》所载之乡遂制度,秦之什伍,汉之县亭,两晋六朝之邻里,隋唐五代之邻保,宋元之保社,明清之保甲等。行使公共职能必然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但是政府并不为县以下的公共事务的行使拨付经费,其经费或来源于据田产面积按比例劝捐,或来源于本地居民的摊派。
中国县以下近代意义上的行政体系和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始于清朝末年的“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清政府为了强化对乡村的控制,开始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推行国家政权建设,建立新式学校、设立警察体系、划分行政区域、建立自治组织,将国家权力轨道向乡村铺设,使公权力逐渐延伸到县以下。“新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近代化改革则对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正如当年出使俄国的大臣胡惟德在一份奏折中所指出的:“小学教育所以造就国民,民间子女皆须就学,以户口计之,一县之中当有小学校数十处,造就教员,又当有师范学校。而建筑校舍,则当相度地形;稽查学龄,则当编订户籍。又如水陆道路所以便利交通,近岁内地杂民、外人日众,每议我国道路秽塞,行旅艰难。此后工商繁兴,学校林立,市廛罗布,车马骈阗,在在与道路有密切之关系。他如卫生事宜,所以图国民身体之健全,则当清洁市衢,建修病院。积储事宜,所以备社会不时之灾歉,则当收敛米谷,存蓄金钱。自余庶务,至纤至细,亦非绅士数人所能分任。”③
以上所列“新政”,乡村社会所承担的有关教育、道路、卫生、救灾等公共事务与古代社会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具有更强的标准化、专业化特点,原有的非常简单的行政机制已难以适应,必须在县以下建立科层化、普遍化的常设行政系统和设立职业化、通过选举程序得到任用的行政人员以履行复杂的公共社会职能。
清末县以下的近代行政体系主要包括单一职能的教育、警察等“官治”行政系统和综合职能的“自治”行政系统。
中国县以下的官治行政系统是从教育、警察等单一职能性行政开始的。1903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其中,在县以下设立初等学堂和实业学堂。为了推行新学制,1906年清政府颁布《劝学所章程》,其中规定“各府厅州县应就所辖境内划分学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任一学区内劝学之责”,④垂直隶属于州县劝学。这是中国近代在建立区乡行政方面的最早官方创制。随后颁布的《学部札各省提学使分定学区文》明确了县以下教育经费的地方自筹政策:“教育之兴,贵于普及;而兴办之责系于地方。东西各国兴学成规,莫不分析学区,俾各地方自筹经费,自行举办。”⑤此后,各地照此规定在州县以下划分学区,开征“学捐”,向各学区派驻教育行政人员——劝学员或乡视学、学董。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学务划分为自治范围,垂直隶属于县劝学所的劝学员开始由隶属于同级自治公所的学务专员、学务委员取代,学区这种单一职能的乡镇行政形态也不复存在。与学务权力下移乡镇的同时,当时开征的各种学捐的权力也由县级下移到城镇乡征收。
清末预备立宪中1907年颁布的《各省官制通则》还仿效西方,在各州县境内划分警区,设置“区官”,掌管本区巡警事务,已含有将警区作为准行政区、将警官作为准行政首领之意。警政经费也是由地方“就地筹款”。
清末在州县以下普遍设立行政组织肇始于地方自治新政的展开。清末的地方自治分为两级,府厅州县地方自治为上级自治,县以下的城镇乡级自治为下级自治。清政府首先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1月18日)仿照日本《市町村制》,颁布了宪政编查馆订立的下级地方自治的法律文件——《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9章112条)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6章81条),对下级地方自治的运作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⑥
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有区域过广、人口在10万以上的则再在其境内划分为若干区。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团体,实行议事与行政分立,城镇设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议事会和乡董。
城镇议事会主要议决下列事项:本城镇乡自治范围内应行兴革整理事宜;本城镇乡自治规约;自治经费岁入预算及预算正额外预备费之支出;自治经费出入决算报告;自治经费筹集办法与处理办法;决断选举之争议;自治职员办事过失之惩戒;关涉城镇乡全体赴官诉讼及其调解之事。议事会所议上述各项,由议长、副议长呈报该管地方官查核后,交董事会或乡董执行。议事会每季度举行会议1次,“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凡议事可否,以到会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⑦
董事会为执行机构,其职权有以下几项:议事会议员选举及其议事之准备;执行议事会议决各事;办理律例章程规定之事,或地方官交办各事;议决各事之具体执行办法。董事会每月举行会议1次,“会议时,非董事会职员全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不得议决。”⑧。
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⑨
1.地方文教。包括经办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阅报社以及“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学务之事”。
2.地方卫生。包括清洁街道、蠲除污秽,设立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办理“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卫生之事”。
3.地方公共设施。包括改正、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设置路灯以及“其他关于本城镇乡道路工程之事”。
4.地方实业。包括改良种植、牧畜及渔业,设立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改良工艺,整理商业,开放市场,防护青苗,筹办水利,整理田地以及“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农工商务之事”。
5.地方公益。包括救贫、救荒、保节、育婴、施衣、放粥,成立救生会、救火会,采取义棺义冢、保护古迹以及“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
6.地方公共营业。包括开办电车、电灯以及自来水等业务。
7.地方自治经费的筹措。
从以上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范围看,它基本涵盖了现代国家基层政权所承担的几乎所有公共职能,与传统里甲、乡地组织主要以支应官差、为封建官府催粮征赋、报案传人等为己任不同,它主要承担兴办新式教育、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发展近代实业、建设近代公共设施、提供社会保障等现代社会公共职能,实开中国固有的基层治理结构近代化之端绪。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的同时,清廷发布上谕强调城镇乡为自治初基,亟应首先开办,“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地方选举正绅,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将城镇乡自治各事宜,迅即筹办,实力奉行,不准稍有延误”。⑩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乡镇一级的地方自治,如在各省省城和府厅县设立自治研究所,讲授《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课程,培训推行地方自治的人才。地方督抚对于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也比较重视,较为积极。
由于清廷上下内外合力推进城镇乡地方自治,在短时间内,城镇乡自治就形成一股热潮。
从各地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实际运作看,清末基层社会开始显示出若干新气象。如直隶县实行地方自治的乡镇“(议员)除少数奔竞者流,多为一般老成耆德,不喜事,不畏事,不迎合官府以损议会之尊严,不要誉乡闾以侵官治之权限,据理而争,尊章而行,运用之妙,可为楷则”。(11)而南方的浙江嘉兴秀城区议事会办理议案卓有成效,1911年的春季常会,“会议上议员发言秩序井然,提出议案20余件,其中理由充实、办法周密者虽然不多,最终成立议案亦有11条”。(12)
江苏川沙县1909年开始进行城乡地方自治选举,全境划分川沙城和5个乡,一共6个选区。先进行城乡议员选举,再从中选出城董、乡董、乡佐等自治职员。选举结果报告同知后,得到批准由同知发给执照,正式成立城、镇、乡自治公所。1910年3月,川沙城设立自治公所,11月,5个乡自治公所也相继成立。短短的1年时间内川沙城乡自治公所先后列出了道路、运河、卫生方面的议案12件;教育方面的议案14件;慈善方面的议案7件;筹措自治经费和确保自治公所场所方面的议案7件;废除“陋规”方面的议案10件;取缔女巫、“素党”方面的议案1件;保护农作物幼苗、禁止随便饲放羊群案1件。
1909年6月,苏州商人施莹等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限期成立,凡属商民,均有应尽之义务,”(13)稟请创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获得批准。随后,苏州其他街区纷纷仿效创办市民公社。苏州市民公社“克尽义务”,“凡清道、缮路、通沟、燃路灯,次第皆举,而尤所注意者,弭盗防匪,预弥缝于无形。所有从前隐患,一扫而空,故在地铺商,咸觉平安无事”。新兴的工商阶层以街道为行政区域组织的市民公社不仅拥有《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的各项自治权,而且还办理巡警和裁判所,掌握了地方治安权和一部分司法权,在城市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4)
二、清末乡镇财政的近代化
与中国传统政治上的高度的中央集权相适应,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也是集中于中央,一切财政收支原则上都是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的,地方官仅是中央政府的征税代办人,“地方政府的预算和支出,包括薪水和办公费,都由户部来规定。”(15)州县的财政收入抵扣规定的支出后,余额上交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调拨。县以下的公共事务如修桥补路(16)、兴办教育、维修水利(17)等,或由私人付费(如私塾),或由私人自愿捐助。
事权与财权是密不可分的,公共权力的下移必然要求财权的下移,正如当年《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天下事非财不举,地方而欲自治,必有财以为实行自治之支费,而后乃可以收效。否则,虽日讲自治利益,日颁自治制度,亦犹海市蜃楼,终归乌有而已。”(18)
但是,清末办理“新政”和地方自治,州县学务、卫生、善举、实业等事业均被清政府定位为国家政务之外的地方自治事务。清政府规定,地方自治的所需经费不许动用国家租税,几乎完全由地方自筹。由于所需经费巨大,无法采取传统的私人募集、私人经理的方法筹集和运作,于是各城镇乡纷纷设立地方财务机关,筹措地方公共收入,从而产生了乡镇地方自治财政。正如一些地方志所载,“自昔官治时代,财权悉操之官,无所谓地方费也……自创设警察、学堂、自治、实业诸政,所费恒以万计,一切悉责之地方,而赋税正供已尽数提解以去,丝毫不为地方存留。于是地方不能不筹款,如随粮附征,补助公益、附加税等项目,日益繁多,不能不专设管理机关,势使然也。”(19)
清政府宪政编查馆的一个上奏中,在谈到自治财政经费时,对地方自治经费已作了筹划:“万事非财不举。地方自治既不能动用国家正款,则于旧有公款公产而外,不能不别开筹措之途。然若漫无限制,则浮征滥费,势所难免,而甚者会敛逾等,或至与国税相妨。则尤与自治宗旨相反,故特于经费章程内明定收捐之制,而仍规以定率,以至管理征收预算决算检查,俱各详示准绳”。(20)
为了保障城镇乡地方自治承担的公共事务,《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专列《自治经费》一章,对城镇乡地方自治的有关经费来源、管理、征收、预算和决算等财政问题作出了规定,规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的收入来源为三项:公款公产、公益捐和罚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赋予县以下的组织以税费征收权。
公款公产主要包括社仓或义仓(21)的积谷或积款、学田学款以及由私人捐助而形成的其他财产,如祠堂、寺庙的屋宇和产业。这些地方社会长期自我管理的产业普遍被转入各项地方自治事业的名下,成为乡村地方财政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甚至成为乡村地方自治初期的主要财政来源。其中的不动产如书院、寺庙等大多用作小学堂校址,有的也用作自治机构的办公场所。(22)
公益捐又分附捐和特捐两种。所谓“附捐”是指“就官府征收之捐税,附加若干,作为公益捐者”,其数目“不得过原征捐税定数十分之一”,“由该管官吏按章征收,汇交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收管”;“特捐”是指“于官府所征捐税之外,另定种类名目征收者”,“由城镇董事会或乡董呈请该管地方官出示晓谕,交该董事会或乡董自行按章征收”。(23)公益捐在城镇乡地方自治以前就普遍征收,且名目繁多,城镇乡地方自治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开征新捐。
附捐是国家税项(当时乡村地区主要是田赋)下征收的一种捐税,不能随意增加种类和比例(最高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而特捐各地方可以自立名目“酌设”,它为乡镇财政打开了方便之门。公益捐的征收实行属地原则,“凡于本城镇乡内有不动产或营业者,即本人不在本地方居住,亦一律征收”。(24)清末乡镇各种为地方自治开征的公益捐,征收的程序基本上必须贯彻民主的形式,通过“合邑”的决议才能进行。具体做法是由地方官出面,邀集当地绅商学界举行会议,议定经费征收管理办法,由董事会或乡董负责征收。“地方何项可以酌提,何项应行追缴,自应凭众公议,就近稟明地方官,察酌办法。”(25)
由于乡镇地方公款公产和罚金极少,实际上,清末乡镇财政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种名目的公益捐,国家财政没有提供支持,几乎完全依靠乡村社会自身的财力。中原地区的河南为例,各种公益捐,“有抽之于花户者如串票捐、契税捐、契尾捐、房捐、亩捐、随量捐之类是也。有抽之于坐贾者如斗捐、商捐、铺捐、油捐、火柴捐、煤油捐、量坊捐、变蛋捐之类是也。又如枣捐、瓜捐、柿饼捐、柳条捐、柿花、芝麻、花生等捐则就出产之物而抽收。如戏捐、庙捐、巡警捐、册书捐等则因特定之事而抽收。”(26)如以清末乡镇财政中的最大一项支出——教育经费来说,“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捐和学生纳费,出自官款者仅占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城乡捐税和劝捐”。(27)基础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理应由国家提供。特别是在当时乡村社会经济落后、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强制性要求各地开设中小学堂、蒙养院,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相关费用而完全要民间自筹,这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经费由城镇乡议事会议决管理方法,由城镇乡董事会或乡董负责管理。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还规定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预决算体制。城镇乡董事会或乡董“每年应预计明年经费出入,制成预算表,于每年十一月议事会会议期内,移交议事会议决”,议决后“于本地方榜示公众”。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变动,“非经议事会之议决,不得提用他款”。城镇乡董事会或乡董“每年应将上年经费出入,制成决算表,连同收支细帐,于每年二月议事会会议期内,移送该会议决”。(28)作为财政核心内容的预算被誉为立宪的灵魂所在,随着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展开,从清末开始预算观念开始为基层民众所了解,预算制度开始在中国最基层的公共财政体系中构建,它成为乡镇财政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对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出入经费还进行定期和临时检查,“定期检查每月一次,由城镇董事会总董或乡董行之。临时检查每年至少一次,由城镇董事会总董或乡董,会同该议事会议长、副议长及议员一名以上行之”。(29)
由此可以看出,城镇乡地方预决算体制及地方财政体现出分权和透明的民主特色,与封建财政不可同日而语。
城镇乡地方自治财政的出现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财政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它不仅是财政层级的增加,而且是财政体制的巨变。在中国传统的“绅治”时代,由于不存在乡镇行政组织,因此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乡镇财政,乡镇公共事务经费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临时性,因事而兴,事毕而息,既无经常性收支,也没有常设管理机构;二是私人性,所需经费主要靠私人自愿募集,而不是靠以公共权力和有关制度为依托的强制性税费。而在地方自治中产生的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财政无论是从经费来源的法定性、公共性,还是管理的民主性方面看,都体现出近代公共财政的特点。
但是,乡村社会公共财政的构建对乡村传统社会心理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比如在教育支出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教育基本上为私塾教育所垄断,儿童达到就学年龄,家长或把孩子送到塾师开办的私塾,或延揽塾师在家设馆,谁受教育谁付费,完全出于自愿。官方也在乡村设立若干“社学”和“义学”,(30)主要由民间募集资金,实行免费教育。但新式教育的收费方式却完全不同,每一个公民无论享不享受教育服务,都必须支付公共教育经费,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直隶邯郸县,“城乡共计官立一所,公立六十所(初等小学堂),每年费津钱万缗,均出自地亩,是担学费者已及全境,而入学堂者仅止数村”。(31)加上当时乡村社会自治水平低下,公共经费的征收并没有经城乡自治议事会议决,并由董事会实施,而往往实行包税制(32),一些承办公共教育的包税人以办学为名横征暴敛、上下其手,给乡村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公共财政的构建不仅没有成为乡村社会稳定的支柱,反而成为乡村社会动荡的根源。
税权的划分比较复杂,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单一制传统的国家要向分税制演进,牵涉政治经济的许多方面。清朝末年,中央与地方要员对于在全国财政体系中,是否应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11年1月13日),两广总督张鸣岐提出地方税应分三级的“真电”:“将来地方行政应以省为一级,府厅州县为上级,城镇乡为下级,有一级之行政,即应有一级之税”,地方税因此应“分为省税、府厅州县税、城镇乡税三种”。江苏巡抚程德全对此立即发表不同意见,认为“城镇乡人民之负担,犹是府厅州县人民之负担”,“真电谓地方行政城镇乡为一级,似于行政法有抵牾之处”,“真电谓地方行政城镇乡为一级,即应有一级之税,似于实际上有难行之处”。“现定税法似宜以行政纲目为标准,先分国家地方两级,地方税中分官治自治两种。”(33)对于张、程二督抚的争论,有的督抚赞成张鸣岐,如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浙江巡抚增韫、吉林巡抚陈昭常等,他们请张鸣岐主稿会衔电奏。但大多数督抚支持或倾向于程德全的看法。(34)
从中国近代乡村财政运行的实际效果看,由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近代工业化民主社会过渡的早期,乡村一级设立完全独立的财政体系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落后和巨大的不平衡,使乡村社会难以承担应付公共品供给的巨额开支和实现全国乃至全省和全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次,民主化程度的低下也会使乡村公共财政体制运行难以为继。乡镇财政是否应单独建立的问题,在民国时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界一直都没有取得共识,它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民国时期的学者彭雨新所指出的:“从乡镇事业范围言,过去地方政务之推行,无一不归于乡镇”,乡镇“非有较大之财政权力,无以推动事业,故从此点言,乡镇财政如能早日建立,则地方自治事业之发展,当亦早见成效。”但另一方面,“财政分配之单位愈多,则财政收支之手续愈烦,而其弊端亦愈易起。”(35)
清朝末年,在是否建立城镇乡一级财政的争论声中,不少实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的乡镇开始了近代乡镇公共财政的实际运作。如江苏嘉定县钱门塘乡自治财政收入包括漕银附加、归公无主田地、房捐、酒捐、路灯和水栅捐。其中,漕银须经省谘议局议决,其他各项均经乡议会议决。财政开支方面,如重建市西巷门、给发孤贫口粮、雇夫扫除街市积秽、备置义棺、补助桥梁建筑、添设初等小学、添设图书、购置防火设备、疏通河道等,均须乡议会议决。(36)
前面提到的江苏川沙县城、乡自治公所分别于1910年3月和11月先后成立后,议决了有关征收自治经费的议案7件,具体包括:征收自治经费(2件);荒地和新增淤沙地收归自治公所管理,其收入充作自治经费(2件);确保自治公所房屋(1件);在城壕养鱼、其收入充作自治经费(1件);从土地、房屋买卖的手续费中抽取二成充作自治经费(1件)。试图通过养鱼、清丈荒地和新增淤地等方法筹措自治经费。由于严重入不敷出,又少有“公款公产”来填补,所以该县九团乡议事会议决自治公所从次年(1911年)起,按照加收一成的税率征收附加捐,并得到同知的许可。1910年底,九团乡议事会还议决,把以往由保甲、书差向乡民索取属于官治不正规收入的“陋规”改为自治经费。该决议也得到同知的批复:今后各地投保时,一律缴大洋10元,以一半拨充办公经费,一半拨充自治经费,“庶几行政自治两无偏废”。(37)
由于各省地方自治议事会直到1910年才普遍成立,因此清末乡村财政的运作仅开端绪。
三、近代化追求与财政困境:乡镇财政近代化评析
清末乡镇财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近代西方财政体制为参照建立基层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探索,开启了中国乡镇财政近代化的序幕。但是当时朝野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向社会基层铺设国家权力上,没有相应注意事权的合理划分,特别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地方财力与其承担事权的极不匹配,也没有对民主财政所需要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环境给予必要的关注。而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健全的民主制度是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建立的两大基石。
从总体上看,清末乡镇地方自治事权较广,而财权有限,许多本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公共事务如治安、教育,由于中央财政已濒临崩溃,缺乏统一筹划与调拨公共品经费的能力,只能采取专项办法临时筹措,并下放筹款权力于地方,“就地筹款”,由地方百姓负担。这反映出清王朝近代化追求与财力不济的窘态。
事权与财权的脱节,造成地方自治经费入不敷出,只得以各种名目的“特捐”和“附加”向早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摊派,使本已处于倒悬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极端匮乏的乡村民众又加重了几重负担。如山东莱阳县以举办地方自治为名,加征亩捐、房捐、人口捐。(38)河南中牟县为办学而抽收的“羊捐”规定“每羊一只大羊抽收一百文,小羊一只抽收钱五十文。”(39)湖北麻城县“清末自治经费取给于屠宰捐。凡屠户宰猪一头,每斤收捐四文,按季汇缴”。(40)江苏宜兴一些地方,打着办自治的旗号,“每石加收自治经费40文。”1906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说:“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41)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清政府办的是自治局,倒不如说是筹款局,刮地皮局。(42)
乡村地方自治经费中教育所占比重最大,教育经费的摊派最严重,清末乡村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宾兴费、考试费和乡村书院经费等;二是庙产、祠产、会产等公产收入及迎神赛会演戏的费用;三是新增教育捐税。其中尤以第三项为大宗。(43)与用一间房子、几张桌子、一个塾师就能开办一家私塾不同,新式学堂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虽然传统教育资源被移作学堂经费,但维持巨大的学堂经费开支,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筹措更多的经费。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清末各地纷纷开征种类繁多的教育捐税,如浙江定海厅以学捐为名征收的捐税就有“米捐、茶叶捐、牛捐、猪捐、石宕捐、缠脚捐、放脚捐、婚纸捐”等数十项之多。(44)河南中牟县截止1908年共抽收车捐24万钱,羊捐24.862万钱,柳条捐8万钱,盐斤加价捐9.768万钱全部用于教育经费,另外抽收斗捐70万钱,枣捐40万钱,花生捐9万钱,牙帖捐27.96万钱用于教育和警察经费。(45)清末徽州祁门县“西乡学堂抽园户茶捐岁墨银两千余元,南乡学堂岁墨银一七八百余元,东乡初等小学四所,约共墨银六百元,皆取之园户茶捐”。(46)浙江嘉兴县徐婆寺镇绅士利用寺产设立胥山学堂,同时抽收茶捐、酒捐、米厘、鲜肉捐、蚕种贩用捐等捐税。(47)
除了事权与财权的不相匹配外,清末乡村公共财政的构建也严重受制于乡村社会缺乏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的保障。清末国家政权的组织触角向县以下乡村社会不断下延的过程中,乡村政治文化生态陷入整体性的危机。美国学者杜赞奇认为,中国近代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极大地侵蚀了传统地方精英的权力资源,使得原在国家与乡村之间充当中介并偏重保护乡村利益的乡村领袖被一种掠夺、赢利型的经纪性人物所取代;国家依靠后者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对后者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后者在充当国家组织助手的同时,利用国家所给予的法理权威谋取个人利益,从而形成国家与赢利型经纪合作榨取乡村的局面。(48)
杜赞奇的这一论述对清末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具有相当的诠释力。就连清廷内部官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复委其责于乡绅,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技,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官长,藉端牟利,朋比为奸。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惟恐搜刮不尽,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家蓄一鸡一犬有捐,市屠一豕一羊有捐,他如背负肩挑瓜果、菜蔬、鱼虾之类,莫不有捐,而牙行之于中取利,小民之生计维艰,概置弗问。其开销经费也,一分区之内在局坐食者多至一二十人,一年度之间由局支出者耗至二三千圆,以一城数区合计之,每年经费不下万金。而问其地方之善堂如何,学校如何,劝业如何,卫生如何不曰无款兴办,即曰不暇顾及。所谓办有成效者,不过燃路灯,洒街道,或设一二阅报社、宣讲所而已。而旧日育婴堂、养老院、义塾、社仓、宾舆、乡约、施药、施茶、积存诸公费,非皆挥霍尽净不休。(49)
清朝末年地方自治中,乡镇财政因政治民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各种财政舞弊案件五花八门,多不胜数。如直隶易州自治局张某、祖某藉口筹措自治经费,擅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津钱3万余吊,又陆续勒捐2万余吊,全部中饱私囊。张某还借调查户口之名,按户敛钱。乡民以天不下雨,秋收无望,坚不肯纳,张某大言恐吓,谓顽民阻挠新政,非送官究办不可。(50)江苏自治研究所毕业生一到乡下,就“广刷报纸,散卷开贺,为敛财之计,甚有勒派分资者”。(51)
清朝末年,当城镇乡地方自治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时在全国许多乡镇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对乡镇地方自治的“自治风潮”,其中由于教育负担引发的事端最多。如浙江遂昌县学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早已引起民众不满,“今番自治学员周寰来乡,诿称调查选民,勒派鸡猪牲捐,众心不服,誓灭学堂,以安农业,并要求退还前任所捐租,”遭到知县镇压,群起焚毁学堂,“将自治事务所捣毁”,“因巡警劝护,迁怒巡官,”民众拥入县署衙门,“将巡警总局捣毁。”广东连州乡民闻有编订门牌之举,“疑为学堂筹办人捐,”群起捣毁学堂。(52)1910年江西宜春发生毁学事件,全县百姓都被动员起来,导致“各乡学堂被毁者十余区,停办者七八区,乡学一无所存。”(53)同年,直隶丰润县发生的毁学风潮中乡民约定:“以毁学杀绅为主,打死学堂一人,奖东钱四千吊,被打而死者,每年养家钱一千吊,以十年为度;伤者每日养伤钱一吊,打死学人而抵命者六千吊;由学堂构讼之费,由席户均摊,倘再不敷,每席一张,捐铜元四枚。有犯会规者,打死不论。”(54)
清末乡村骚乱固然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因素,即国家政权轨道向乡村铺设导致事权下移而财权没有相应下移造成的乡村经济负担的加重。据统计,在清末发生的170起毁学事件中,有94起由教育经费问题引起;而在浙江发生的256起乡村教育诉讼案件中,也有162起与教育经费有关。(55)清末发生的各种自治风潮矛头具体指向各城镇乡基层自治组织,但它实质上是民众对国家近代化政策使他们未受其益、先尝其害的现状的抵抗。
大量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而苛捐杂税是乡村不安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农村社会长期动荡的主要根源。有学者对1927-1936年间中国的宏观税负作了研究,指出这10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各年依次为2.074%、2.186%、2.195%、2.45%、2.51%、2.52%、2.954%、3.6%、3.211%、3.49%。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说1927-1936年的税收负担过于沉重,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56)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也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总支出“只占国民总产值的极小一部分,1931-1936年为3.2—6.0%。”而同时期“美国可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为8.2%,1933年为14.3%,1941年为19.7%。”(57)中国财政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现代经济部门规模的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之所以感觉税收负担沉重,主要在于难以纳入正式统计口径的税外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费”太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的动荡与清末相比有增无减,国民政府针对乡村的苛捐杂税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效果不佳,其根本原因在于乡村所承担的公共职能与其财权不相匹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建立一个从中央直接统到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巨型官僚机构,1929年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的组织设立区、乡(镇)、闾、邻四级,县以下的公共职能膨胀。乡镇一级政府财政收入除了一小部分由县级政府补足外,大部分实行就地筹款,除了沿袭清末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的办法以外,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弥补财政亏空。如以浙江嘉兴县双云乡为例,1948年1月、3月和6月的财政收入包括三个部分:乡村各茶店代募经费、各保募捐费和县政府补助经费。其中茶店代募经费三个月份各占总收入的14%、20%和9%;各保募捐分别为63%、68%和57%;县政府补助分别为23%、12%和34%。(58)可见,该乡财政收入中,募捐占到总经费的70%以上。
具有近代化气象的乡镇地方自治不仅没有稳固基层政权,反而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民国以后,中国基层政权的近代化一直没有稳固的财政保证,近代化变革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乡村社会成为国民政府政治版图中的破碎地带,成为酝酿各种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国外有的学者也认为,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乡村税制的不合理和征收的黑暗和腐败。(59)国民政府时期也展开过乡镇造产运动(60)等推进乡村财政建设的变革,但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敝而收效甚微。可见没有民主素养的培养,特别是有效财政体制和充裕的财政作保障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走向歧路。
注释:
①唐德刚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清朝末年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型(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页)。
②本文的“乡镇”概念是近代中国县的下一级行政组织的通称。
③《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5页。
④《学部奏咨辑要·学务官制及劝学所章程》,山西浚文书局1909年版。
⑤参见田正平、陈胜《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
⑥次年,清政府又颁布了上级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末县一级地方自治基本上没有展开,只有极少数县进行了县议员选举。
⑦《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6、734页。
⑧《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6页。
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28—729页。
⑩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95卷,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1458页。
(11)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2)《全浙公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参见丰箫《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13)《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88页。
(14)参见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1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6)中国古代交通干道和主要桥梁一般由州县官负责建设和维护,而一般的道路和桥梁则由乡绅和富人集资修建和维护。
(17)中国古代主干河流(如黄河、永定河)上的蓄水和防洪等水利工程,属于河务管理官员的职责,并由朝廷经费资助。但是,支流、水库和仅仅供当地农业灌溉用的堤坝等水利工程,则主要由当地百姓自己去办,通常的做法是按田亩面积劝捐或通过摊捐的方式建立一个特别基金。
(18)《论今日征地方税以为实行地方自治之用》,《东方杂志》1907年第2期。
(19)陈宝生等修:《满城县志略》卷5《县政》,1931年。
(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26页。
(21)“社仓”和“义仓”都是存放本地居民自愿捐献粮食用的。当地老百姓可以从该仓借粮,返还时根据收成的好坏收取一定的利息;收成不好时可以免息。这种粮仓一般由当地居民推举并经州县官批准的人员(社长)进行管理。“社仓”建于乡村地区,而“义仓”建于城镇地区。
(22)如1910年成立的直隶文安县盛芳镇设正、副会长各1人,文牍兼庶务1人,书记1人;董事会设总董1人,董事1人,名誉董事4人,议事会、董事会“以本镇关帝庙后院东上房三间为会场”(陈桢修:《文安县志》法制志,1922年)。
(2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8—739页。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9页。
(25)《浙江日报》1908年7月28日。
(26)《河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捐》,第22页。
(27)张沛:《旬阳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2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9页。
(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39页。
(30)“义学”在城镇和乡村都有设立,而“社学”则只在乡村地区设立。
(31)李桂林:《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2)在包税制下,捐税的承办人通过向地方自治机构提出认捐数量,从而获得捐税的收取权,除去上缴部分外,余者归包税者个人所有,收税者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成为赢利型经纪。如浙江省仁和县茶捐由黄联芳包收,按月递解给该县各小学堂(参见佚名“本司支批茶董黄联芳稟请饬严追欠捐并分设学堂文”,《浙江教育官报》1908年第4期)。包税制的优点是可以使收入确定,缺点是容易造成横征暴敛,中饱私囊。
(33)转引自龚汝富《近代中国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之检讨》,《当代财经》1998年第1期。
(34)参见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35)彭雨新:《县地方财政》,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36—137页。
(36)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7)参见黄东兰《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的反应——川沙‘自治风潮’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38)《中国大事记补遗》,《东方杂志》1911年第8期。
(39)《河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捐》,第23页。
(40)余晋等纂:《麻城县志》卷9《县自治》,汉口中亚印书馆1935年版,第9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版。
(4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杂志选辑》,云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4页。
(43)参见田正平、陈胜《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清末各地教育经费的来源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如当时四川巴县乡村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庙产和会产(参见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4)佚名:《舟山乡民事变记》,《申报》1907年8月5日。
(45)《河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捐》,第23页。
(46)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科·祁门绅士办事之习惯》。
(47)佚名:《本司支批嘉兴县详徐婆寺镇官小学改公立文》,《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8期。
(48)(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7页。
(50)参见周积明、谢丹《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江汉论坛》2000年第8期。
(51)《时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52)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53)佚名:《江西袁州乡民暴动余闻》,《东方杂志》1910年第11期。
(54)佚名:《直隶丰台乡民抗捐纪事》,《东方杂志》1910年第11期。
(55)参见田正平、陈胜《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
(56)赵新安:《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5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58)参见丰箫《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嘉兴县乡镇财政试析》,《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59)(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60)为了解决乡村政权的财政经费问题,国民政府于1942年5月颁布《乡镇造产办法》,将造产收入列为乡镇经费来源的第一位,乡镇设立造产委员会。规定乡镇大力举办公有农场、公用水利、公养鱼塘、隙地种树、荒山造林、简易工业等事业。乡镇造产运动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在推行过程中普遍存在侵犯农民产权、否定等价交换原则及实行超经济强制的现象,实际上造成了与民争利和残民以逞的结果。
